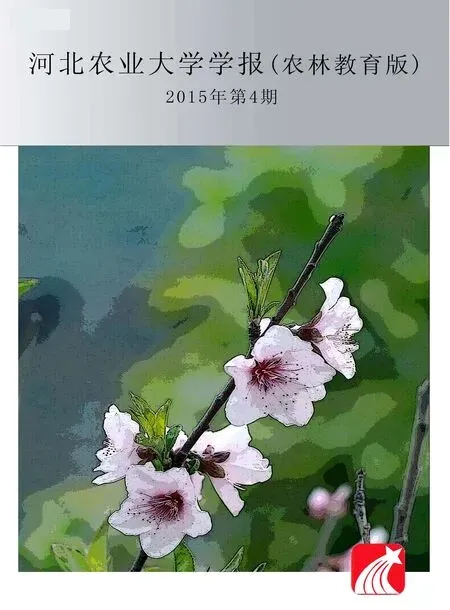高校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异化与消解
2015-03-17王玉蓉
王玉蓉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安徽合肥 230032)
社会学、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指人自身之外的社会关系、心理关系交织而成的抽象空间[1]。辅导员社会空间指辅导员自身之外的社会关系、心理关系交织而成的抽象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2]。
辅导员社会空间是辅导员工作生活中衍生的产物。辅导员社会空间因其具有能动性,影响和制约辅导员工作的重心、实效和辅导员的切身感受等,从而其状态关系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大学生教育的落实和品质,甚至影响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力量不是促进、推动辅导员的健康发展,而是控制、阻碍辅导员的健康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辅导员在辅导员社会空间被异化,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辅导员社会空间控制、阻碍着辅导员健康发展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对辅导员自身发展和积极作用发挥产生阻碍。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直接后果是辅导员发展的异化,以及辅导员在异化了的社会空间中逐步丧失了应有作用。
下文从辅导员社会空间视角讨论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表现、归因和消解方式。
一、高校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表现
(一)辅导员价值空间异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劳动的意义发生变化是异化的表现之一[3]。价值观是价值空间的核心,辅导员价值观是辅导员价值空间的核心。辅导员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成为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并加以保护的专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是辅导员价值空间的主导价值观。
然而,实际辅导员价值空间却出现了理想信仰被世俗化的异化现象。部分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对马列主义思想自身没有深刻的体会和领悟,从而不能将个人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充分结合,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部转化为自身的思想品质。个别辅导员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假、大、空”,羞于在大学生中宣讲精神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真正融入辅导员价值空间。
辅导员价值空间异化导致辅导员信仰淡薄,理想世俗化,无法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无法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
(二)辅导员文化空间异化
文化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说,文化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消极的是使人“异化”,积极的是使人“人化”[4]。辅导员要完成大学文化使命,就要本着人文关怀,以民族良心与社会良心的立场,以自身利益以外的教育问题、社会现象为中心,对内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对外关心社会、针砭时弊,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然而,辅导员人手少、事务杂、任务重,迫于行政压力,以“命令驱动”替代了“使命驱动”。被异化的辅导员不得不依从高校与社会所期盼的理想角色行为模式,迎合社会大众对当下学生工作者所提出的超职业化要求,着力在多向交织、多重道德期望的角色冲突中演绎好教育管理者视阈中辅导员应当成为的“全才”、“完人”和“圣人”与社会视野中学生的“人生导师”、“知心朋友”、“德育楷模”等角色,放逐了大学使命,丢失了人文精神[5]。
辅导员文化空间遭遇了行政暴力带来的话语霸权的包围,出现了文化使命被工具化的异化现象。原本从属性的行政管理带来了过强的共性约束,原本应占主导的文化陶冶逐步被挤压、侵占,大大削弱了辅导员文化空间的人文意蕴与文化感召力,出现文化使命被工具化的异化现象。辅导员文化空间异化的实质是辅导员文化空间在大学文化使命与高校行政命令两者张力作用下,偏离常态而出现变形。
(三)辅导员感知空间异化
感知空间(或知觉空间)是辅导员作为心理学个体所感知或体验的心理空间,也就是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所说的“被知觉的空间”。辅导员不只是在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空间“磁场”中工作生活,也在不断创生自己的感知空间。如果说辅导员价值空间、文化空间是从辅导员社会关系形成的客观空间来研究,那么辅导员感知空间就是从辅导员心理关系形成的主观空间来研究。
目前,很多辅导员在责任的弥散性和成果的无形性的张力下,理想的“光环”逐渐黯淡,感知空间充溢着失落、茫然和孤独,崇高感被放逐。
社会上普遍认为只有从事教学才是“育人”,辅导员不过是处理大学生琐事的“服务员”,属于丢掉专业的“不务正业”之流。同时,“专职辅导员是指副处级以下一线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员”[6]。这就从行政级别上暗示了辅导员只是一个初级岗位,“辅导员”成为新手和基层人员的代名词。很多辅导员感到自己处于高校行政体系的最低层,扮演着“跑龙套”、“打酱油”的角色。繁重的学生事务、卑微的职业地位、使人身心憔悴的心理期待与艰辛而迷茫的职业生涯不断地把辅导员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5]。对知识分子而言,自身价值不能得到社会舆论尊重,也无法得到行政级别认可,在渴求自尊与缺乏认可之间,在心理预期与个人成就之间出现巨大落差,导致辅导员感知空间充溢着失落。
同时,职业发展空间狭小导致辅导员对职业前途茫然若失。“专职辅导员任期一般为4~5年;任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本人的条件和志向,再有计划地定向培养”[7]。政策的这种流动导向性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辅导员工作并非一项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调查显示,辅导员在角色扮演过程中,42.1%的辅导员会经常莫名其妙地不安;38.6%经常感到压抑[8]。非职业化的工作性质让辅导员难以树立起牢固的职业认同感,导致辅导员感知空间充溢着茫然。
此外,辅导员往往单独负责某学生管理单元,辅导员之间很少协同合作。再加上源于“局内人”的本体性安全或同一性需要,辅导员之间往往各自为政,互不干涉,遇到困难也无人援手,只能向隅而泣,导致辅导员感到的不是团结而是孤立。孤立感挤对了辅导员的幸福感、驱逐了辅导员们的工作热情,导致辅导员感知空间充溢着孤独。
理想信仰世俗化、文化使命工具化、崇高感被放逐是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具体表现,异化了的感知空间阻碍了辅导员发挥其应有作用。
二、高校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归因
(一)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
首先,辅导员队伍年轻化倾向是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的年龄因素。调查显示,70.1%的辅导员年龄在30岁及以下[9]。受限于年龄因素,辅导员思想境界、政治心理的成长还未成熟,未能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严峻性,没有形成完善的政治价值观体系,从而造成政治意识淡薄。辅导员队伍的年轻化,跟不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势需要[10]。
其次,政治理论超前政治实践是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的实践因素。以“80后”为主体的辅导员没有经历战争的洗礼,没有体验建国初期我党开创事业的艰辛,缺乏在政治活动中进行自我鉴别、比较、判断、取舍的成长过程,从而没有机会在政治实践中外化和固化自身的马列主义认识,进而形成系统、深刻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也就无法用本应已内化的政治意识指导实践。
最后,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负面影响是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的环境因素。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各种西方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各种价值观也“鱼贯而入”,碰撞、激荡。其中,物质主义和商业文化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从一定程度上撼动了部分辅导员的政治意识。
队伍年轻化、实践缺乏化、文化多元化导致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这是辅导员价值空间异化的直接原因。
(二)辅导员评价机制功利化
目前,在辅导员评价机制上,高校一般从德、能、勤、绩4个方面对辅导员进行考评。但较难量化的“德”、“能”、“勤”考评项目蜕变成实际的“花瓶”。可量化、好比较、难掺假、显实效的“绩”成了辅导员考评中的实际操作标准[11]。
辅导员忙于抓学风、跑就业、办活动,量化简化了管理,但是丢掉了精神。究其根源,高校评议组期望辅导员培育出受就业市场欢迎的大学生与党期望辅导员培育出具有崇高政治信仰的大学生之间产生矛盾。辅导员评价机制功利化的直接结果是,市场经济诱惑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大学文化使命的导向作用在日益弱化。可见,行政机构主动顺应市场需求的实用导向在辅导员评价机制中的引领,是辅导员文化意蕴边缘化、经济效益中心化的重要原因。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功利化、世俗化观念不断在辅导员文化空间中推广。
辅导员评价机制功利化导致辅导员文化空间出现了文化使命工具化的异化现象。异化了的辅导员文化空间致使辅导员工作重心偏移,阻碍了辅导员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辅导员管理机制行政化
按教育部规定,辅导员受高校和学院双重领导,他们需要同时对多个部门负责,工作职责宽泛、工作业绩无形。专业化水平有限的辅导员很难满足多元化的期望。
辅导员在教育“慢”的艺术和行政“快”的节奏的张力下显得格外焦虑不安。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面对繁重驳杂的工作,辅导员几乎都用重管理轻教育的工作方式化解矛盾。管理是立竿见影的,教育是润物无声的。更重要的是,管理学生不仅和教育学生一样是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而且是辅导员接受的行政命令。毋庸置疑,行政命令一旦未能按时、按量完成就是失职。教育则不同,教育是长期的、隐形的、个性化的,没有时间节点,没有量化标准,甚至没有测量工具。如果说教育质量是衡量优秀辅导员与平庸辅导员的标尺,那么日常管理落实与否就是裁定辅导员是履行职责还是玩忽职守的金科玉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辅导员工作被动应付,甚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限的时间、精力,在实施教育的良知和完成任务的良心冲突面前,多数辅导员只得选择先完成任务再伺机教育。
于是,“命令驱动”替代了“使命驱动”,辅导员由塑造学生的精神导师,降格为服务学生的琐事管理员,沦为高校这台高速运转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感知空间崇高感被放逐。
三、辅导员社会空间异化的消解
(一)构建学习教育机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但部分辅导员政治意识淡薄、专业思想缺失,把自身定位为大学生事务的管理者,而忽略了辅导员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者、传播者和维护者,导致辅导员价值空间理想信念淡薄和角色认同感缺失。教育部要求高校要为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创设必要条件[12]。高校应积极构建有效的学习机制,加强对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辅导员的角色认同。
内容上,高校应紧抓党性教育,进一步加强辅导员的党性修养。按照教育部要求,辅导员都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高校应把对辅导员的教育充分纳入党员教育体系中,以优秀党员事迹为正面典型,把党性教育与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辅导员工作相结合,把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结合,寓教于理,寓教于情,寓教于行,增强辅导员党性教育的感染力、说服力与凝聚力,提高辅导员的思想觉悟和党性修养。形式上,高校对辅导员的教育应形成普及教育、长期教育和经常教育的长效机制,而不应是个别教育、短期教育和突击教育,帮助辅导员形成终身学习意识[13]。高校应依托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积极采取启发式和参与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采用专题讨论和典型示范的教育方式,定期组织全体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引导辅导员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构建学习机制,不断强化辅导员的角色认同,逐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辅导员价值空间,使辅导员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构建激励保障机制,加大政策扶持
如果说构建学习教育机制是引导辅导员苦练内功、提升境界,那么构建激励保障机制和环境育人机制则是进一步改善辅导员的社会空间。
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但在功利化的评价机制下,辅导员文化空间遭遇了行政暴力带来的话语霸权的包围,出现了文化使命被工具化的异化现象。部分辅导员重管理轻教育,丧失了成为大学生精神领袖的作用和地位。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辅导员基地,完善辅导员考评晋升制度,整合辅导员队伍,拓宽“出口”路径,解决辅导员职业前景模糊等问题。
第一,相关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建立完善辅导员基地,构建激励保障机制。辅导员基地的服务管理机构、研究培训机构、心理疏导机构等能明确辅导员岗位职责,厘清辅导员工作范畴,落实辅导员研修制度,加大辅导员骨干培训,为辅导员提供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帮助辅导员走出行政霸权的阴影,开辟积极健康的辅导员文化空间。
第二,高校可以运用多层次的考评方式,减少量化考评,增加综合考核,减轻辅导员的行政压力,以增加辅导员文化空间的人文意蕴与文化感召力。高校可以采用绩效考评、差别化考评、个性化考评、分类考评等方式综合考评辅导员的工作业绩,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考评方式,注重激发和考评辅导员对大学生的文化陶冶作用,丰富辅导员社会空间的人文精神。
第三,相关部门应努力创设条件,保证辅导员队伍的良性循环,为辅导员提供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发展路径,解决辅导员的后顾之忧。实践表明,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改变目前辅导员辅助性地位,真正使他们“干事有平台、工作有条件、发展有空间”,营造、维护和谐宽松的辅导员文化空间[14]。只有得到必要的职业保障,辅导员队伍才会稳定,广大辅导员才会有献身事业的激情和动力[15]。
(三)构建环境育人机制,加大舆论导向
如果说构建激励保障机制是改善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小环境,那么构建环境育人机制就是改善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大环境。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但辅导员感知空间职业归属感缺失,崇高感被放逐。部分辅导员轻视辅导员岗位的重要性,精神倦怠,被动敷衍,工作热情不高。
在数字加网络的新媒体时代,新闻媒体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作用,积极宣传辅导员先进典型,提升辅导员的社会地位,曝光辅导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改善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大环境。宣传是工作的放大镜。加大对辅导员工作的舆论宣传能从时间上延续辅导员工作、从空间上让更多人理解辅导员的作用和价值,强化辅导员的责任意识,提升辅导员的社会地位,激发辅导员的工作热情,从而丰富繁荣辅导员文化空间。加大对辅导员正面典型的舆论宣传还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和谐的舆论环境和育人环境,重建辅导员的认同感和崇高感,消解辅导员异化的感知空间,从而促进辅导员自身发展和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此外,辅导员自身也可以运用社交软件打造的信息发布平台和沟通平台,宣传辅导员工作,揭示辅导员发展瓶颈,自下而上加大舆论宣传,改善辅导员社会空间的大环境[16]。
[1]唐巴特尔.论社会空间的基本形式及其方法论意义[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1):18-2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54.
[3]马建青.“异化劳动”范畴的双重向度论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2):70-73.
[4]郑敏.马克思与萨特异化理论之比较[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1):86-89.
[5]赵宏.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伦理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辅导员主体性视角[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81-86.
[6]教育部.关于界定直属高校专职辅导员范围的通知[Z].北京:教育部办公厅,2008.
[7]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Z].北京:教育部党组,2000-07-03.
[8]戴家芳.高校辅导员角色现状描述、评价及其归因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0(3):99-102.
[9]周家伦.高校辅导员理论实务与开拓[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70 -72.
[10]柯晓蕾.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刍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2):117-118.
[11]程建坤.功利与自为:辅导员专业发展的异化与回归[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3):89 -92.
[12]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Z].北京:教育部,2005-01-13.
[13]林宏.积极转变角色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2):150-151.
[14]赵典庆,李海鹏.努力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情况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2):75-82.
[15]曲建武.立德树人与辅导员队伍建设[J].思想教育研究,2013(7):14-16.
[16]李胜彬.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社交软件在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7):294-296.
(编辑: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