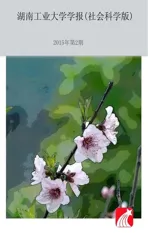此小说非彼小说
——谈《中国小说史略》的瑕疵
2015-03-17张泓
张 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此小说非彼小说
——谈《中国小说史略》的瑕疵
张 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1231)
我国传统小说是指真实的琐碎事件,现代小说则是指虚构的完整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符合前者标准的笔记和符合后者标准的传奇、话本兼收并蓄,犯了体例驳杂的错误。鲁迅之所以这样做,与他倔强的个性有关,更与他对我国传统笔记的偏爱有关。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此后众多的研究者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一直照搬《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由此造成小说观的混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笔记;传奇;话本
在古代小说的研究队伍中,鲁迅可以称为是奠基性的人物,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鲁迅,就没有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而《中国小说史略》则是鲁迅最重要的研究专著,出版以来,几乎获得众口一词的夸奖。赵景深认为:“《中国小说史略》是同类书中的最好一部,可以说是权威的著作。”[1]谭正璧也称赞道:“取材专精,颇多创见”[2]。因为鲁迅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导致《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专著虽然层出不穷,但“这些著作仍然在它所创设的框架下和体系内运作,只有量的增加,并无质的突破。”[3]如胡怀琛在《中国小说研究》中虽然一开头就说“我们要讲小说,第一步,要说明‘小说是什么?’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把‘小说’二字,下一个确切的界说。”[4]但他照样没有给小说下一个定义,而接着讲的是《中国小说二字之来历及其解释》,这就和《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几乎一模一样。
近年以来,随着古代小说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阳健的《中国小说史略批判》,该书从文献、观念、体例、评骘等四方面对《中国小说史略》作出了全面评价,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但该作对鲁迅的小说观语焉不详。笔者认为《中国小说史略》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资料不全,作为一部90年前的专著,资料上的欠缺在所难免。鲁迅把我国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导致该书体例不统一才是最大弊端。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此后众多的研究者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一直照搬《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在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和古代小说史的撰写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大家把鲁迅当作神一样对待有一定的关系。
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一篇中有一句著名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5]39这句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第二点是“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认为符合这两个要求的才是真正成熟的小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作者有意虚构生动故事的才是真正的小说。这观点现在已成为定论,也就是说在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之外,还必须加虚构,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小说。
鲁迅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似乎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在提到六朝志怪时就说:“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22也就是说尽管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似乎是虚构的,但当时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时人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的,他们只是记录社会上的传闻而已,所以鲁迅认为这些仅仅是小说的雏形,并不是真正成熟的小说。
但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把《搜神记》等作品视为小说的雏形可以理解的话,把《世说新语》等作品也视为小说的雏形就很难让人信服了。因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前者毕竟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后者即使用现在的标准来要求也是真实的。
根据鲁迅的小说标准,我们把《左传》和《史记》中的著名记载和《世说新语》做一个对比即可明白,到底哪些才更像小说?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6]
《左传》中的这段记载虚构意味非常浓厚,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过:“鉏麂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7]钱钟书也说:“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8]271除虚构以外,故事内容又婉转曲折,按照虚构和故事两个标准,我们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列入小说的范畴。
项王军壁核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9]
针对《史记》中的这段记载,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引用清代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8]454按照虚构和故事两个标准,我们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列入小说的范畴。
至于《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士族文人有关品行和清谈的言行轶事,其材料大多来源于旧闻轶事和民间传说,其中大多数内容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比如全书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可以在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唐人修《晋书》时,其中很多篇章直接来源于《世说新语》,虽然后人对《晋书》的评价并不高,但从中也可知《世说新语》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中当然也有不真实的地方,道听途说自然就会失实,但失实的篇章并不占主体,所以它和志怪的失实有本质区别,而且其与《左传》、《史记》等为了让故事完整而故意虚构更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所以《世说新语》的故事性远远比不上后两者。且看《世说新语》中的几则: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10]133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10]136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10]142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10]143
以如此三言两语记载真实人物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虚构和故事两方面都非常欠缺,正如宋人的评价:“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11]这样的作品又怎可以称为小说?
如上所述,以故事性和虚构性两方面来要求,《左传》和《史记》中的某些篇章都远比《世说新语》更接近小说。但奇怪的是鲁迅对很多小说要素齐备的作品置之不理,而把《世说新语》单独列为一章,原因何在?
古人把《世说新语》称作小说而把《左传》和《史记》称为史书,我们只能认为鲁迅此时是以古人的标准来界定何者是小说。
二
如果把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做一个比较,会发现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中国注重继承,而西方则注重创造,表现在文艺创作中,中国注重真实,而西方则注重虚构。“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史述,是一种典籍。”[12]247而“现代小说观,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小说既是作者的创造物,其人物、情节自必为虚构的。”[12]248
撰写小说史,首先必须给小说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界定了什么是小说,才能给古代小说划定一个范围,也才能给古代小说史制定一个框架。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自始至终没有给小说下定义,而用《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来代替,这里所提到的小说又都是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这就给我们一个印象,似乎鲁迅把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混为一谈,他根本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鲁迅又岂能不知两者之间的不同?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曾经说过:“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5]194这段表面看上去纠缠不清,似乎很难让人理解的话语探讨的是小说的起源问题。小说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稗官还是神话?鲁迅为了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把起源于稗官的称为小说书,而把起源于神话的称为小说。前者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而后者则是以现代小说观为标准划定的小说。从中可知,鲁迅很清楚我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截然不同。
既然鲁迅清楚地知道我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为什么还要把两者混为一谈?只能说明他是有意为之。
鲁迅的个性决定了他是绝对不可能拾人牙慧的。20世纪初,在文学界出现了一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热潮,当时人们普遍采用西方小说标准来衡量中国小说,把中国古代小说全盘否定。钱玄同明确指出:“《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12]23他认为除了《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书以外,其他的古代小说“有价值者则殊鲜”[13]24,“无足置齿者矣”[13]24。所以“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日而语。”[13]24甚至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13]34,“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14]600-601
即便注重传统的胡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思潮的影响。他一方面指责钱玄同的言论“似乎太过”,但又说《聊斋志异》“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耳。”[14]587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他也认为想象力不够,虚构不足:“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像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14]607可见创造性是他评价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
鲁迅的脾气一向是不喜欢人云亦云的,如以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为标准,则我国古代的小说浩如烟海,很难创作出有影响力的小说史专著;全盘采用西方观念则和其他文人一模一样,这又是他所不屑的,所以中西结合的方式成了他最终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偏爱。鲁迅偏爱魏晋文学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对魏晋时期洒脱、清俊的文风,感到由衷赞叹。刘半农曾经赠送给鲁迅一副对联,上联是“托尼学说”,下联就是“魏晋文章”,鲁迅并没有加以反对,可见他内心是赞同的。
鲁迅偏爱魏晋文学与他推崇魏晋风度密切相关,对于魏晋时期特立独行的文人,鲁迅是引为同类的。许寿裳曾经说过:“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老实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15]202
正因对魏晋风度的推崇,所以鲁迅把专门表现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划入小说的范畴,在清代又专列拟晋唐小说一章,把《聊斋志异》列为拟唐小说的代表作,把与《世说新语》风格相近的《阅微草堂笔记》列为拟晋小说的代表作,而对后者的论述在篇幅上又超过前者,以此来表现他对古代笔记的推许。
鲁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评价多为正面之词,如“立法甚严”,“尚质黜华”,“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雍容淡雅,天趣盎然”,其原因正是《阅微草堂笔记》“追踪晋宋”;唯一不满的是“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议论。”[5]133可见,鲁迅是把《世说新语》作为标杆来要求往后的作品。
鲁迅对魏晋时期洒脱、清俊文风的欣赏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他评价《世说新语》道:“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5]34,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鲁迅曾说过:“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16]在塑造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时,就重点描写她的眼睛:“瞪着的眼睛”,“眼珠间或一轮”,“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眼盯着我”,“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没有神采的眼睛”,“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瞪着眼睛”,“眼光也分外有神”,“眼睛窈陷下去”等等,这种遗貌取神的创作手法和《世说新语》如出一辙。
三
因为别具一格的创作目的以及对魏晋文学的偏爱,鲁迅把《世说新语》及与之相似的古代笔记也纳入了小说的范畴,但如此安排《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又形成了一个悖论:鲁迅在评价唐传奇时用的是现代的小说观念,而在论及《世说新语》时候,又用的是传统的小说观念。“鲁迅的小说观常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当他处于自为状态,用的是西方的文学观和方法论;而当他处于自在状态,用的又是中国的文学观和方法论。”[17]
这从《中国小说史略》的篇章安排中也可见一斑,第一章《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谈的是我国传统小说观的演变及发展,重在要求小说的真实;第二章《神话与传说》又在论述西方小说观的起源,重在要求小说的虚构。
由于鲁迅独特的地位,他这种明明是混乱的小说观却被评价为他的创新之处。非常注重辨体研究的陈文新评价道:“在‘五四’学者中,鲁迅是颇有个性的一位。他既不拒绝引进西方理论,又尊重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中国小说史略》一方面以是否‘故为幻设语’作为小说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之一,提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又从传统的小说观出发,迹其流别,以相当充裕的篇幅评述了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人的杂俎以及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并很有见地地将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18]韩国学者赵宽熙也认为:“鲁迅小说研究杰出的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时,不依赖西方的观点,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对于小说的认识价值,肯定并接受来自于西方的影响,鲁迅又致力于追求中国小说史的固有发展模式。”[19]他认为这样做的长处是,“将中国小说史的计年更加提前。”[19]因为“现在通用的小说实际上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受到了很多西方的影响。如果从这种立场上来看,说中国自古没有小说的观点也是可能成立的。”[19]说得明白点就是如果用西方的小说观来衡量,我国的小说产生得很晚,因为鲁迅把西方的小说观和我国传统的小说观相结合,这就让我国小说史的计年大大提前。
鲁迅把《世说新语》等笔记划入了小说的范围,给古代小说史指定了框架,由于他巨大的影响力,导致后代小说史的撰写都以此为标准。这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在我国古代汗牛充栋的文字作品中,只要符合虚构的故事这一点的就是小说,因为它符合西方的小说观;另一方面,有些作品虽然既是真实的,又没有故事,但也是小说,因为古人把它称为小说。这样我国古代的小说数量就大大提高,但由此造成小说观的混乱,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0:5.
[2] 谭正璧.谭正璧学术著作集:3卷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3] 王齐洲.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72.
[4] 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2.
[5]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0-431.
[7] 纪 昀.阅微草堂笔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3:275-276.
[8] 钱钟书.管锥篇:1卷 [M].北京:三联书店,2007.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236.
[10]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孔平仲.续世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
[12] 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2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4] 胡 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 许寿裳.许寿裳谈鲁迅[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6] 鲁 迅.鲁迅全集: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9.
[17] 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65.
[18] 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4.
[19] 赵宽熙.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694-699.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is Novel is not that Novel ——On the Flaws ofABriefHistoryofChineseNovels
ZHANG Ho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Zheji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Tourism, Hangzhou, 311231 China )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s refer to the real trivial events, while the modern novels are complete fictional stories. InABriefHistoryofChineseNovels, Lu Xun’s eclectic approach of combining the real notes and legendary stories commits the mistake of heterogeneous style. The reason why Lu Xun did so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stubborn personality, even more related to his preference for China’s traditional notes. Due to Lu Xun’s great influence, many subsequent researchers dared not go one step beyond and copied his framework of Chinese novels, which leads to a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novel and leaves us a pity.
Lu Xun;ABriefHistoryofChineseNovels; notes; legend; text of a story
10.3969/j.issn.1674-117X.2015.02.014
2014-05-16 作者简介: 张 泓(1968-),男,浙江浦江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I207.41
A
1674-117X(2015)02-00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