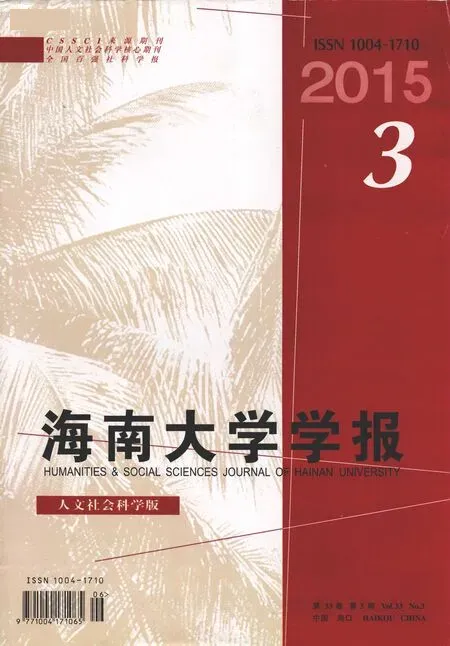《神曲》中的“水”与“土”
2015-03-17朱振宇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朱振宇(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神曲》中的“水”与“土”
朱振宇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在但丁的《神曲》中,水与土所象征的自然元素再现了但丁心目中救赎历史的图景,也参与了朝圣者的心灵旅程。因此在但丁的史诗中,关心水与土就意味着关心人的处境。这种为自然元素赋予精神寓意的写法来自《忏悔录》,在本质上,《神曲》是与《忏悔录》一样的精神自传,二者都隐含着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其中《神曲》中的上升方式是柏拉图的灵魂小宇宙学说与亚里士多德天体宇宙论结合的产物,在其中,心灵之旅的最后结局是人与自然的合一。
[关键词]但丁;《神曲》;奥古斯丁;维吉尔;灵泊
在汉语世界的但丁接受史上,《地狱篇》第4歌古代圣贤云集的Limbo受到过较多的关注,但译者们对Limbo一词的翻译莫衷一是。数年前,林国华在其“灵泊小议”一文中对这个词的翻译史进行了归纳和点评,提出一种兼顾音译与寓意的译法:“灵泊”。作者追溯了汉语史上“泊”字的本意“浅水”,并指出,“泊”字由于这种本意而具有“边缘化”与“放逐”两重含义,既符合地狱中Limbo的地理环境,也符合Limbo中灵魂的状态①关于Limbo翻译的汇总见林国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灵泊’小议》,收入林国华、王恒主编《罗马古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3-17页。。
笔者认为,“灵泊”是一个“雅译”,其原因不仅在于它准确再现了《地狱篇》第4歌中的自然环境和灵魂处境,并且指出了灵泊是作为“水”与“土”交界的地方,触及了“水”与“土”在《神曲》中的精神寓意。笔者将试着阐述这种精神寓意并对这种寓意书写进行溯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Limbo的一种理解。
一、神学地理
“水”与“土”勾勒出了《神曲》的精神地理轮廓。在《地狱篇》最后一歌中,但丁借维吉尔之口叙述了地狱和炼狱的形成。维吉尔说,由于撒旦的反叛,他被逐出天国,从南半球的天上坠落下来穿透了地表。为了躲避堕落天使的冲击,南极附近的土地躲闪到了人类居住的北半球,而地球中心的陆地则从表面回缩,在撒旦身体的周围形成了巨大洞穴——地狱,收缩的土地冲出地表,形成了南极陆地上的山峰——炼狱山。人类曾经居住的伊甸园就坐落在山顶,自从亚当犯罪,南半球山顶的乐园就变得荒芜②本文中出现的《神曲》译本均为田德望先生翻译。[1]34.121-126。从这段叙述可见,在但丁的视野中,土地的位移与灵性世界中发生的神学事件有着直接的关联。从地球的角度看,撒旦叛变的结果是“土地的丢失”,就像朝圣者在走出地狱后自己说的“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天然的地窖”[1]34.98。始祖叛变的代价也是失去曾经拥有的“乐土”,而获救的希望也在失去的“土地”——炼狱山上。在此:土的匮乏对应着善的缺失,土地的重获意味着灵魂得救。
与这一段“土地”演变史对应的是《神曲》第14歌,在那里中,但丁仍然借助维吉尔之口对地狱中4条河流的来历进行了解释:
在大海中央有一块已经荒废的国土,叫克里特……山中挺然屹立着一个巨大的老人,他的肩膀向着达米亚塔,眼睛眺望着罗马,好像照自己的镜子似的。他的头是纯金造成的,两臂和胸部是纯银做的,胸部以下直到腹股沟都是铜的;从此往下完全是纯铁做的,只有右脚是陶土做的;他挺立着,主要是用这只脚,不是用另一只脚支撑体重。除了金的部分以外,每一部分都裂开了一道缝,裂缝里滴答着眼泪,汇合在一起,穿透那块岩石。泪水流入这一深渊,从一层悬崖落到另一层悬崖,形成了阿刻隆,斯提克斯和弗列格通;然后由这道狭窄的水道流下去,一直流到不能再往下流的地方,形成了科奇土斯。[1]14.94-119
由于“克里特老人”的身体由金、银,铜、铁和陶土构成,批评者们得以辨认出的原典首推《旧约·但以理书》第2卷,在巴比伦之囚后,巴比伦之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却不记得梦里说的什么,身旁的哲士中无人能将梦的内容告诉他,王发怒,要处死所有的哲士。但以理从王的护卫长亚略那里了解到王的命令,于是就请求宽限,说自己可以将梦的内容和寓意告诉王。但以理的同伴向神祈求怜悯,求神将这事的奥秘指明,夜间但以理得到神的异象,明白了王的梦。亚略将但以理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但以理将王的梦说了出来:
王阿,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2]Dan.1:31-35
但以理解梦说,这个人像象征着巴比伦今后的历史,拥有强大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金头,在他之后,不如当下帝国的白银之国、掌管天下的铜之国和压制列国的铁之国接踵而至。后来的帝国必将分裂,就像人像那半铁半泥的脚。但以理睿智的解梦征服了尼布甲尼撒,他敬拜但以理,令他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2]Dan.1:37-48。
在第14歌中,“克里特老人”的身体结构与尼布甲尼撒梦中的人像的确非常相似,由于但以理将梦中人像身体的不同元素解释成帝国历史的各个阶段,由此可推知,维吉尔口中的克里特老人是某种历史的缩影。但在做出推论之前,须注意到,“克里特老人”与尼布甲尼撒梦中的人像存在如下不同:(1)尼布甲尼撒梦中的人像没有处所,但在维吉尔口中,这个老人有具体的处所——大海中央的“克里特”;(2)维吉尔说,老人“眼睛眺望着罗马,好像照自己的镜子似的”[1]14;(3)老人的眼泪汇成了地狱中的4条河流。
在《埃涅阿斯纪》中,“克里特”是一个错认的故乡,埃涅阿斯的父亲安奇塞斯得到神谕,流浪的特洛伊人应该到“祖先的地方”去寻找西土,老安奇塞斯解错了神谕,将“故乡”理解为母系祖先的居所克里特岛,于是,特洛伊人未经仔细思考就欣然向克里特进发,在到达目的地开始建城时,上天惩罚了特洛伊人的错误,降下瘟疫和灾荒,人体羸弱,大地上五谷不生。家神在梦中指点了真正的西土所在,那就是拉丁乌姆,是安奇塞斯的父系由此出走的地方[3]。在14歌的语境中,作为《埃涅阿斯纪》作者的维吉尔用自己诗歌中代表错误的地方来指称老人的所在,解释《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堕落之后的历史。
德林(Robert Durling)追溯了这种“迷误之地”在《圣经》解释史上的对应者:奥古斯丁追随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的记述,认为克里特岛上有一个巨大的人的身体;后来的作家曾把克里特与拉丁语的陶土一词“creta”联系在一起,因此克里特岛上的人就意味着“陶土做的人”,在《旧约》中,第一个陶土做的人是始祖亚当。维吉尔将克里特岛上的人称作“老人”(veglio)[1]14.103,在但丁时代的意大利,与这个词语的现代英语“old”一样,兼有“老的”与“旧的”两种含义,因此,从《圣经》角度看,克里特老人实为“陶土做的旧人”,这旧人的形象象征着人堕落后的处境,作为人高级自然的理智就像是老人的金头,固然天生美好,但人体的其他部分象征的低级自然却由于原罪而受到了伤害③这个解释见Robert M.Durling为《地狱篇》第14歌写的疏解,见其编的Infern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555-557.Durling还指出,整个的地狱可以被看做一个“身体”,p552-555.。
确定了老人形象的神学意义,就可以解释克里特老人与尼布甲尼撒梦中人像的其他两点不同:老人看罗马就像揽镜自照,因为罗马和老人都是堕落后的人类社会的写照,罗马城就是亚当之城;从克里特老人眼中流出的4条地狱河流,象征着因原罪而派生的种种罪恶。将《地狱篇》第34歌和14歌结合观看,可以读出但丁眼中人类世界地理的形成史:撒旦的堕落引起了土地的丢失,造成了北半球巨大的洞穴,人堕落之后,旧人之土做成的“自然”也像人类曾经的大地一样失去了完整,像旧人眼泪流进了身体的裂缝一样,源自旧人眼泪的罪恶之水填补了北半球洞穴的部分空间,形成了地狱。
《神曲》中四条冥河的名称无疑来自《埃涅阿斯纪》卷,但在维吉尔叙述中,四条河流没有统一的来源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地狱篇》中,四条河流构成了地狱3部分(放纵、暴力、恶意)的界河④维吉尔在《地狱篇》11.79-111对朝圣者解释了地狱的这种三分结构。,它们甚至就带有以其为边界的罪之特征:(1)阿刻隆(Acheron)是地狱界河。(2)斯提克斯河(Styx)是一个泥沼,犯暴怒和抑郁罪的恶灵在其中受罚,暴怒者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他们不仅用手,而且用头、用胸膛、用两脚相互殴打踢撞,相互用牙齿把对方的身躯一块块地咬下来”[1]7.112-114。抑郁者则沉入河底,永久地憋闷着[1]7.117-126。污浊的泥沼与情绪失控而丧失理性清明的昏暗有着想象的相似,这一点不言而喻。(3)弗雷格通河是一条血河,这条河以及周围地带惩罚的是犯有暴力罪的人,他们对邻人(杀人犯)、对自己(自杀者)、对上帝与自然施暴(渎神者,鸡奸罪者,高利贷者)。从文本语境推测,血河弗列格通是一条沸腾的河,因为这河流“使它上空落下来的火焰统统熄灭”[1]14,在河畔还有一片火雨纷飞的沙地[1]14.28-39,在托马斯传统中,暴力罪属于灵魂中“血气”部分的罪,用沸腾的血河表现血气之罪十分贴切。(4)科奇土斯湖是一个冰湖,犯有背叛罪的灵魂冻结在其中,背叛意味着割断上帝给予的爱之纽带,爱由于背叛而止息,犹如河水停止了流动,冻结在冷酷之中。与四条河流有着相同的起源相似,地狱的所有罪行都能找到原罪的影子。
因此,土地缺失形成的洞穴与四条地狱之河勾勒出的地狱,实为“旧人”的形象,在《新约》中,与“旧人”对应的,是因基督救赎而诞生的新人,像《以弗所书》中说的: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里的仁义和圣洁。[2]Eph.20-24
回到诗歌开篇,旧人的形象对应着朝圣者陷入的“幽暗的森林”(selva oscura)⑤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注释者都认为,“幽暗的森林”首先指的是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罪恶。安东尼·E.·卡塞尔梳理了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史,见Anthony E.Cassell ed.,Inferno I,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P1-7.[1]2。纽曼(F.X.Newman)追溯了“森林”(selva)一词在中世纪寓意的变化,他指出,中世纪教父们用silva一词指代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物质”(hyle)一词的拉丁译法⑥参见F.X.Newman,“St.Augustine’s Three Vis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edy,”Modern Language Notes(1967),P64-65.。在《蒂迈欧篇》以及受其影响的罗马思想传统中,“物质”被认为是罪恶的来源,就人而言,正是物质性的肉身带来的欲望阻挡着灵魂的飞翔。奥古斯丁修正了将罪恶的起源单纯归于肉身的看法,他认为罪恶来自恶的意志,但他同时认为,由于人的原罪,人的肉身堕落了,情欲及其他不当欲望的产生就是肉身堕落的标志[4]2-3。而秉承奥古斯丁传统的但丁,在此处所写的“幽暗的森林”(selva oscura)意味着有罪的身体⑦参见John Freccero,“the Firm Foot on a Journey without a Guide”,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28.。此歌接下来下的诗句说:“我说不清我是怎样走进了这座森林的”,这诗句充满了肉身化的意味:朝圣者就像每个尘世中的人,在初生时未经自由抉择就承担了因始祖的原罪而变得残缺的肉身。在这里,有罪的身体与有罪的世界合一,就像从始祖亚当身上繁衍出了整个人类世界,而每一个个体都由于继承了始祖的原罪可被看做“亚当”本人。因此,诗歌中的朝圣者并非仅为历史中的某个人,而是救赎历史的见证。因此,诗歌的第一行才写成了“在我们(nostra)人生的半途”[1]1,而非“在我(mia)人生的半途”。
将《地狱篇》第1歌、14歌和34歌连读,则不仅可以看到自然史与救赎史的合一,也可以看到自然元素与“我”心灵旅程的关联,因此在《神曲》的世界里,关怀土与水意味着关怀人的处境。
二、自然元素、心灵之旅与救赎历史
在《飨宴篇》(il Convivio)中,但丁称赞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精神自传的典范力量,将这部作品的内容称作“人生从坏到好、由好到更好、再由更好到最好的进程”[5]I.ii.12。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总结的人生三阶段也可以看作其后来创作的《神曲》三部曲的主题,而《忏悔录》毫无疑问可以看作《神曲》中心灵旅程的先驱。事实上,在《忏悔录》中也能找到《神曲》里自然元素的精神寓意。在书末的第13卷中,奥古斯丁用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业绩为“创世七日”赋予了象征寓意:
但如着眼于象征意义——我以为圣经所以把祝福仅限于水中生物与人类,真谛即是如此——则无论在精神与物质受造物中,——犹如在天地之中,——无论在良好的与败坏的灵魂中,——犹如在光明与黑暗之中(第一日),——或在传授圣经的神圣作者中,——犹如在诸水之间的穹苍,——或在痛苦的人类社会中——犹如在海洋之中,——或在虔诚信徒的持身方面——犹如在陆地之上——或在现世的慈善工作方面,——犹如在花草果树之间……我们都能找到芸芸众生。在这一切之中,众生都在生长蕃息;……犹如水族的孳生,为我们沉溺于罪恶的肉体是必须的;而思想概念则犹如人类的嗣胤,是由我们理智所诞生……大地的干燥是由于渴求真理,但大地是属于理智范围。[6]13.24
在这段文字中,奥古斯丁将自然世界与人类精神世界进行了比拟,可以明确看出,水对应着沉沦在罪中的人类世界,花草树木代表着慈善,陆地则代表着信仰,“大地的干燥是由于渴求真理,但大地是属于理智范围”,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第13卷中的这段《创世记》释义在《忏悔录》中的地位?这个段落涉及的自然元素与救赎历史,与奥古斯丁记述的个人经历有无关联?
以布朗(Peter Brown)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忏悔录》的前9卷是奥古斯丁真实的个人史,后4卷则是论述心灵结构的一般原则,前9卷与后4卷无论在主题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距离⑧Peter Brown的奥古斯丁传记体现了这种思路,Augustine of Hipp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以斯蒂芬尼(William A.Stephany)和麦克马洪(Robert McMahon)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既不应将前9卷看作死板的历史事实,也不应将后4卷进行断章取义的哲学分析,布朗研究思路的最大弊病,乃在于无视《忏悔录》作为奥古斯丁精神传记结构上的完整。
斯蒂芬尼通过对《忏悔录》文本结构的分析指出,《忏悔录》前9卷记述的个人经历并非仅仅是奥古斯丁的个人生活史,而是作为救赎历史见证的每个人故事的缩影。按照斯蒂芬尼的分析,《忏悔录》前9卷以卷5为核心,存在着明显“下降—上升”的对称结构:第1卷肉身的诞生对应第9卷灵魂的重生;第2卷邻家花园中的偷梨对应着第8卷米兰花园无花果树下的皈依;第3卷与第7卷的主题都是哲学,在第3卷中摩尼教的谬论使奥古斯丁陷入迷误,而第7卷中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使奥古斯丁接近信仰;第4与第8卷的主题是爱与友谊,在卷4中奥古斯丁为虚假的友谊的失去而哭泣,卷8中真正的友谊给予了他心灵的慰藉;第5卷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去了罗马,在这里他濒临肉身与精神的“死亡”,也赢了人生中的转向……这一系列个人经历中隐含的“下降—上升”结构,再现了基督从“道成肉身—殉难—复活”救赎历史的一般模式。因而《忏悔录》的精神自传并不仅属于历史上的奥古斯丁自己,也是每个人心灵旅程的见证[7]。
麦克马洪接着斯蒂芬尼的结论,对前9卷与后4卷的关联进行了探索。认为救赎历史将前9卷的个人历史与第13卷的《创世记》解释联系在一起,指出在前9卷各卷中,可以分别在奥古斯丁的修辞中找到与上帝“创世七日”呼应的字句,这些修辞夹杂在前9卷的叙事中。比如,在描述早年沉溺于肉欲时,奥古斯丁将此世的生活比作“习俗的洪流”和“无涯的苦海”[6]1.16;此后在追寻信仰过程中,又将失落信仰比作“沉入了海底”[6]6.1,这些段落中,水的比喻显然与末卷中水的寓意吻合。再如,在《忏悔录》5-7卷中,奥古斯丁先后记述了自己从迦太基渡海来到新的土地——罗马[6]5.8、莫妮卡的追随[6]6.1以及内布利提乌斯来到米兰[6]6.10,而上帝的王国则被称作“和平之乡”[6]7.21。在走向新土地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及亲友们好似在大海中沉浮的不坚定的信仰,渐渐踏上了坚实的地基,这与上帝在第六日创造中从海洋转向了陆地的举动彼此呼应。
正是这些看起来不过是一些修辞手法的细节,将个人生平与《创世记》中记述水与土的创生过程联系在一起。由此出发,可以将《忏悔录》理解为具有“9-3-1”的结构[8]147。前9卷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常人经历,这种经历中的“沉沦—死亡—再生”结构再现了上帝在尘世的具体工作,10-12卷为心灵的一般原则,其主要内容为心灵“回忆—注意—期待”的三位一体结构,人通过自己心灵中的三位一体接近上帝的三位一体:人通过自己的历史与心灵结构得以接近上帝,因为神在记忆之内,又在记忆之上。最后一卷用上帝之言《圣经》将个人历史与救赎历史联系在一起,包含《创世记》释义的13卷因而相对独立,是作为“本源”的一卷,从这一终卷的角度看,全书从数字1开始,以3倍再3倍的方式呈反向放射结构,以这种结构勾勒出从本源的“整一”到个体历史“杂多”的流溢过程。
麦克马洪指出,在《忏悔录》前9卷中,作为作者的奥古斯丁往往站在终末的角度插入叙事,对以往的自我进行评价。正是这种看似杂乱的结构引导着文本情节的前进,像主人公奥古斯丁与代表上帝发言的奥古斯丁之间的一场对话,历史中的自我在与最高存在的对话中以螺旋形上升着。个人的“言”——精神自传的叙事——通过这种螺旋形的对话(dailectics)回溯到上帝的“言”——《圣经》[8]148-150。
如果说在《忏悔录》中,这种螺旋形的推进还只是在修辞上存在,那么在《神曲》的三部曲中,螺旋形就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朝圣者的行走路线。朝圣者在地狱中是螺旋下行,最后他穿越了地狱的底部,调转了身形,在炼狱山以螺旋形路线环山而上,而后在天国中随着诸天在旋转中上升,直到在天国花园中见到上帝,于是朝圣者依环形绕上帝旋转。
问题或许在于,地狱、炼狱和天国三界中的旋转方向是否一致?显然,只有肯定的答案,才能确认朝圣者的旅程是连贯的。诚然,由于天国在南半球上,从天国的角度看去,朝圣者在地狱里的下降其实也是上升,他的精神旅程因而在纵向上是连贯的向上行进的,然而在横向维度上情形如何呢?
弗里切罗(John Freccero)通过文本细节中存在的一个矛盾获得了答案。他发现,但丁在地狱中的旅程是按顺时针方向螺旋进行的⑨此时朝圣者和维吉尔坐在格律翁背上盘旋向下,诗人说“我从右边已经听到旋涡在我们下面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这似乎意味着,他身体的左侧在外,靠近堤岸,而他身体的右侧向着地狱的中心,由于但丁肯定是在前进而非倒退,因此其方向是顺时针。[1]17.118-119,诗人这种行进方向称为“向左”,而攀爬炼狱山时则按逆时针螺旋进行,诗人将行进方向称为“向右”[1]19.79-81;22.121-123。诗人的说法与现代意大利语的习惯相悖,在现代意大利语中,顺时针是向右,而逆时针是向左。弗里切罗通过思想史的考证断言,只有回溯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于现代人而言,“左”和“右”是相对的方向,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左和右的方向却是绝对的,在《论天》(De caelo)第2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宇宙自东向西的运动称为右⑩⑩De Caelo,II.2.285b.,而《论天》则是但丁天体宇宙论的来源之一。在《神曲》的宇宙中,由于天国在南半球上方,而堕落后的人类生活在反方向的北半球,所以从北半球的角度看,诸天运动的方向就是“向左”,因此,无论朝圣者在地狱中向左行进的旅程还是在炼狱山调转身形后向右的行进,都是在追逐群星运动的方向。由此来看,朝圣者从地狱到天国的进程是连贯的[11]John Freccero,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第72页。
弗里切罗并未止步于探索《神曲》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来源,他将《神曲》中明显的螺旋形路线回溯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指出在这种传统中存在心灵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对应,而这种对应恰恰是《神曲》的自然哲学与心灵之旅得以统一的本源。根据《蒂迈欧篇》的创世神话,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有着相同的本源,大宇宙与小宇宙都以三种方式进行运动:环形运动是属灵的、完满的运动,线性的运动属于物质世界,二者的结合是螺旋形运动,这种复合运动在天体运行中表现为诸天公转和自转的混合;在人身上,环形运动意味着理智的运动,直线运动意味着纯粹身体的行为,二者结合则是肉身化的灵魂的特征。根据《蒂迈欧篇》,灵魂来自诸天,在进入罪孽的肉身时,其环形运动由于肉身的介入而受到打扰,只有通过古典教育才能恢复灵魂的环形运动,意味着将摆脱肉身的羁绊,向天国故乡回归。
基督教传统否认肉体本身的罪恶,因而在奥古斯丁以及其他拉丁教父那里,“线性运动”由物质运动的特征变成了灵魂流连于外物的象征,丢尼修(pseudo-Dionysius)对天使运动方式的分析就体现了这种对《蒂迈欧篇》灵魂运动模式修正[12]丢尼修,《论神圣的名字》(De div.nom.)IV,8。。他指出,天使灵性的运动有三种方式:当其敬拜上帝时,进行圆形运动;当其照料人时,进行直线运动;两者结合时进行螺旋形运动。同样拥有灵性的人也能够进行三种理智的运动:当人的心灵进入自身思考的最高存在时,进行圆形运动;当人的心灵执着于外在事物时,进行线性运动[10]81;在《神曲》中,朝圣者的心灵旅程是一个在罪的诱惑与上帝的恩典交错中不断反思而前进的过程,螺旋形的行进轨迹是这种心灵旅程的完美再现。由于小宇宙与大宇宙(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同源的,于是,就像在《忏悔录》中一样,这种回溯性的螺旋形轨迹将个人的心灵之旅与救赎历史和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对于奥古斯丁和但丁来说,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像笛卡尔哲学之后那样彼此疏离,在他们的世界里,自然哲学无不是精神哲学。
正是由于心灵旅程与“大宇宙”之间的同源,以“水”与“土”为象征的自然元素才在诗歌的字句与寓意层面上参与了朝圣者的旅程。不难发现,在《神曲》每一部曲的开端和结尾,都有渡河或航海意象出现,在地狱开始,诗人将朝圣者比作在“灵魂沉船后”脱离海难的人:
犹如从海里逃到岸上的人,喘息未定,回过头来凝望惊涛骇浪一样,我的仍然在奔逃的心灵,回过头来重新注视那道从来不让人生还的关口。[1]22-27
而后,朝圣者在维吉尔的引领下穿越了地狱中的4条河流。在炼狱的海滩上,诗人“天才的小船把那样残酷的大海抛在后面……扬帆向比较平静的水上航行”[9]1.1-3,登上炼狱山坚实的土地,在山顶越过了源自天国的勒特河与欧诺尔河;而在《天国篇》开篇,诗人自比为“一面唱歌一面驶向深海的船”[1]2.3,在进入天国花园前,朝圣者看到来自上帝的光汇成了一条河。在三部曲中,对“土地”的追寻最终都变成了对宇宙秩序等级更高的“土地”——“群星”(stelle)的追随,这个词出现在每一部曲的结尾:“重新见到了群星”[1]34.139,“准备上升到群星”(《炼狱篇》33,145)[1]33.145,“太阳和其他的群星”[1]33.145。弗里切罗注意到了“星辰”一词的拉丁文写法sidus,朝圣者追随群星便意味着与群星在一起,那便是“consideration”——冥想,这是《神曲》的最高境界,即人与宇宙的合一[13]John Freccero,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226.[10]226。
三、但丁与维吉尔:水际的诗人
在此回看地狱中Limbo的风景,Limbo的中心地带是一座被七道高墙环绕的“高贵的城堡”,“周围有一条美丽的小河防护着”,城堡里还有“青翠的草坪”[1]4.106-108;111。这美丽的风景让人想起《埃涅阿斯纪》第6卷中的乐土。然而稍省查便能察觉这美丽风景中隐含的悲凉:根据维吉尔在《地狱篇》第14歌的说法,地狱中所有的河流都源自克里特老人的眼泪,因而那“美丽的小河”或许是地狱入口处的阿刻隆河的支流,而它在本质上则肯定是一条“死亡之河”。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灵泊化身的维吉尔,他在《神曲》的精神之旅中出现和消失的地方,同样是由水与土构成的道德风景。
在《神曲》开篇的场景中,朝圣者挣扎着走出象征罪恶的幽林,在山谷尽头的一座小山脚下:“瞥见山肩已经披上了指导世人走各条正路的行星的光辉”[1]1.17-18,阳光的温暖使他暂时复苏,“犹如从海里逃到岸上的人……回过头来凝望惊涛骇浪”[1]1.22-24,他顺着一条“荒凉的山坡”(piaggia diserta)前行,但三头野兽出现,最后出现的狼将他逼退[1]1.44-60,朝圣者最初的旅程就这样宣告失败。在第2歌中,由维吉尔转述的露西的话吐露出了从天国角度如何看朝圣者的处境:“没看见他正在风浪比海还险恶的洪流中受到死的冲击吗?”[1]2.108换言之,在天国的视野中,朝圣者是从那荒凉的山坡被逼回到以狼为象征的欲望洪流。维吉尔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可以推知,他出现的地方是死亡河畔的“荒凉山坡”[14]Freccero曾指出这荒凉的山坡就对应着灵泊,但未给出特别的论证,见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第54页。其实文本的证据并不难找:在这水边“荒凉的山坡”上,朝圣者瞥见了古代哲学的光芒,又在此碰到了诗人的荣耀维吉尔,在地狱中,二者都居住在Limbo中,因而由此推断,“荒凉”的山坡象征着灵泊。。
与此对应的是维吉尔消失的地方,那是在伊甸园勒特河畔的土地上,当贝雅特丽齐从天而降时,朝圣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头寻找维吉尔,“但维吉尔已经走了,让我们见不着他了”[1]30.49,随后是贝雅特丽齐的劝诫,让他不要为维吉尔哭泣[1]30.55-57。已有无数论者对这个场景的前前后后进行过分析,但笔者以为,维吉尔消失后出现的一个比喻最值得注意,因为在那个比喻中,朝圣者再次将自己比作将要出海的人:
正如一位海军上将站在船头和船尾,视察在别的船上旅行职责的人们,鼓励他们做好工作;
同样,当我听见直呼我在此处必须记载的自己名字的声音,转身去看时……[1]30.58-62
这出海的比喻,正好构成了对开篇场景中沉船比喻的回应。
维吉尔在死亡河畔出现,又在天国的河畔消失,正体现着林译所说灵泊的“边缘”特点;而彼此呼应的沉船和起航的比喻,则对应着现代汉语中“泊”的意思:“停船,靠岸”。化身为维吉尔的“灵泊”是一片能让灵魂航海的人栖息的土地,异教圣贤的灵魂由于缺乏信仰而在此搁浅,作为基督诗人的但丁却不能以此作为永恒的港湾。
对于无法进入天国的异教圣贤而言,“灵泊”确实有放逐的意味。但笔者以为,不应将这种意味作过度延伸,因为在《神曲》的世界里,彻底被放逐的灵魂只有《地狱篇》第3歌中那群“既不背叛也不忠于上帝”的天使和灵魂[1]1.38-39,而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位于阿刻隆河彼岸的灵泊是有地位的。在撒旦坠落后,由于土地遗失而变得残破不堪的地下世界里,灵泊是唯一美丽而完好的地方,它就像克里特老人金色的头颅,也像圣托马斯对人类处境的断言:人堕落后,灵魂的低级部分都遭到了败坏,但灵魂较高的部分保存着善[15]。
对于开篇场景中朝圣者瞥见阳光而得到恢复的比喻,解释史上一般将他瞥见阳光的动作看做但丁早年特别是写作《飨宴篇》(Il Convivio)时代的哲学努力,即研习亚里士多德使但丁暂时摆脱了灵魂的苦境。但朝圣者被逼了回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没有起到作用,这位古希腊哲人也从未走出过灵泊;维吉尔却成功地引领但丁穿越的死亡之河,来到天国的边界。这似乎意味着,在救赎的道路上,诗比哲学更接近信仰。
不应忘记,在基督殉难之前,灵泊是以色列祖先们的居所,由于信仰,他们最终得进天国。在这些祖先中有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穿越红海和沙漠,抵达约旦河,他在约旦河畔死去,而以色列人则在约书亚引领下进入应许的土地[16]。在致斯加拉大亲王的书信(Epistola a Can Grande della Scala)中,但丁以出埃及的故事为例解释了自己诗歌的四重含义[17],——将这救赎历史中的片段套用在《神曲》的旅程上,或许可以说,那一开始阻挡朝圣者、又在维吉尔引领下穿越的死亡洪流就像红海,但丁在其中脱胎换骨的勒特河与欧诺尔河就如约旦河,维吉尔是但丁的摩西,而但丁则是人们的约书亚。
[参考文献]
[1]但丁.神曲[M].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
[3]维吉尔.埃涅阿斯纪[M].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M].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5]ALIGHIERI Dante.Il Convivio[M].trans.Richard H.Lansing.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0.
[6]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STEPHANY William A..Thematic Structure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J].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982 Patristics,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Conference held at Villanova University,November 1982:1-28.
[8]MCMAHON Robert.Augustine’s Prayerful Ascent:an Essay on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Confessions[M].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
[责任编辑:郑小枚]
Water and Earth in Dante’s Divine Comedy
ZHU Zhen-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In The Divine Comedy by Dante,water and earth,as symbols of natural elements,reproduce the poetic vision of redemptive history and participate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the pilgrim.Therefore in Dante’s epic,the care for earth and water means the care for the human condition.The spiritualization of natural elements,as a kind of writing method,may be traced back to Confessions,and The Divine Comedy and Confessions are the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in nature,both implying an upward spiral structure.The way of ascent in The Divine Comedy is the combination of Plato’s microcosmic theory of mind and Aristotle’s cosmology,in which the ultimate goal of spiritual journey is the unification of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Dante;The Divine Comedy;Augustine;Virgil;Limbo
[作者简介]朱振宇(1976-),女,北京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世纪及古典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506101-F51401)
[收稿日期]2014-11-04
[中图分类号]I 063;B 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5)03-00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