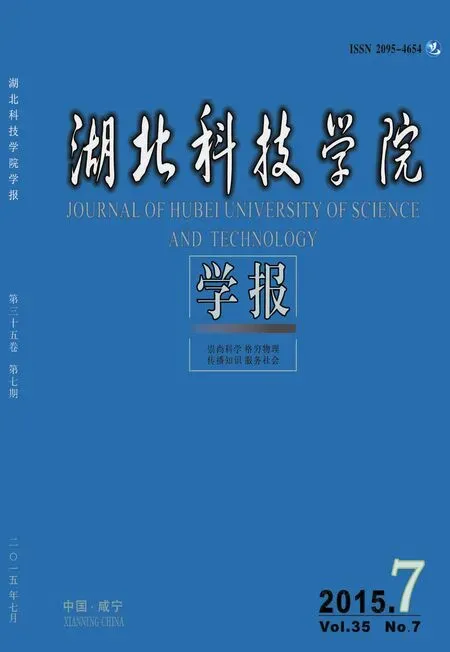论鲁迅《野草》中的“梦”
2015-03-17刘秀芳
刘秀芳
(广东培正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论鲁迅《野草》中的“梦”
刘秀芳
(广东培正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野草》是对“梦”的集中书写, “梦”不仅是《野草》独特的结构方式和言说方式,而且最恰切、最个人、最凝炼地表现了适时鲁迅复杂的内心体验与人生哲学。同时,梦是“独语”的极致,《野草》借由一连串完全属己与不可复制的文学梦,最大限度地开拓了《野草》的艺术空间与艺术深度。《野草》的“梦”体现了鲁迅对于文体选择的高度自觉。
《野草》;梦;结构;言说;独语
《野草》写于“五四”退潮时期,自1924年开始创作,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散文诗集。区别于其他作品,《野草》隐含着深邃的哲理性,鲁迅先生说自己一生的全部哲学都包含在《野草》里了[1]。李欧梵在《〈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一文中说:“鲁迅是怎样把他的感情转化为艺术的呢?这样一位认真的艺术家是不会像当时的青年作家那样直抒自己受挫折的感情的,他必须找到能够包容他哲学沉思的适当形式,必须构筑起适合于这一目的的语言……这是我分析《野草》的起点”[2]。这里的“适当形式”,就是《野草》中奇崛的“梦”。《野草》之“梦”,是本文分析的起点。
一、《野草》独特的结构方式与言说方式
鲁迅说《野草》的“技术不算坏”,这“技术”自然离不开“梦”。《野草》是一部连同题辞在内共24篇的小小散文诗集,全集由奇特的“梦”来结构和言说,想象大胆、情节怪诞、意境幽深,彰显了鲁迅高超的创作技艺。
(一)梦的结构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死火》)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失掉的好地狱》)”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墓碣文》)”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颓败线的颤动》)”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学上预备作文……(《立论》)”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死后》)”
如上,除却1925年4月至1925年7月的《死火》《狗的驳诘》等这连续七篇同以“我梦见……”开头的文章外,另有《影的告别》“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好的故事》“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等,也是以梦的形式构思成篇。这些单篇的梦是鲁迅心灵炼狱中开出的一朵朵“惨白色小花”。与此同时,从全部散文诗集着眼,《野草》开篇以《秋夜》入梦(花、叶、枣树的梦),到终篇《一觉》“忽而惊觉”, 整部诗集显出梦与醒的前后呼应,从而蝉联贯通成了一个宏观的完整的长梦结构。再有,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有一伟大的男子”“讲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我”不仅是一个做梦者,而且在梦中也是一个听梦者,这篇文章便形成了一个“梦中梦”的嵌套式结构。可见,“梦”是《野草》的载体,也是《野草》选择的结构方式。《野草》就是一个梦。
(二)梦的言说
写有“梦”的文字,在鲁迅《野草》以前的篇章中并不少见,譬如“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华盖集·题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然而,以“梦”为题材来创作、以梦呓之语来言说,《野草》才是最集中的体现。《野草·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充实”与“空虚”是两种截然相悖的言说结果,虽然反向言说将成倍地扩大言说的空间。于此,惟有“梦”的体式才能巧妙地达成《野草》言说的结果,“梦”的醒觉、“梦”的真伪、“梦”的新旧、“梦”的轻重……惟有“梦”才能给予言说矛盾一个合理的载体,而且与此同时,“梦”也赋予了言说本身亦“沉默”或“开口”的自由。
林贤治说,“鲁迅的言说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语境’问题。要解读他,必先解读语境”。[3]关于《野草》的语境,鲁迅自己多次说明,“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参照历史,鲁迅《野草》集中写于1924年至1926年间,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低谷,“《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碰了许多钉子”的黑暗境遇我们可想而知,在如此语境下势必需要一种更加隐晦曲折同时也更富内蕴的体式来言说和承载鲁迅的“心音”。《野草》的措辞“就很含糊”,但当然绝不是“随便谈谈”。
(三)自觉的文体选择
这种体式就是“梦”。关于“梦”,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做梦有潜意识——梦的变形伪装——梦的显象三个阶段,是人的潜意识活动的产物,是一种(被压抑的、被压制的)愿望(被伪装起来的)的满足,因此是缓和人生矛盾、宣泄情感和调整人格的方式之一,而梦境多有非理性的内容与形式。当然,文学的梦是不同于现实的梦的。文学的梦是作家对现实的梦的再创造,这个关于“梦”的写作固然包含有梦的特征,但“梦”在作品中以何种面目出现,是由作者的叙述目的决定的,文学的梦始终脱离不了作家理性的轨道。如果说现实的梦是荒诞的,那么文学梦里隐含着的却是一颗清醒而冷静的心,只是它也披着“荒诞”的外衣罢了。所以,如果说现实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那么《野草》之文学梦表现为鲁迅创作言说、情感体验、生命哲学等全部需要的满足:不仅适时创作的特殊“语境”需要梦的自由、奇幻、无序、模糊、象征性来排解、反抗、转移甚至掩盖此时“难于直说”的复杂思想,而且鲁迅个人再度成为“游勇”,“布不成阵”却又始终冷却不了的“战斗的意气”需要梦的情绪、跳跃、无拘无束甚至桀骜来宣泄、消解、释放、抒发、突破甚至安置其个人的焦灼难平的情感及孤独的灵魂。当然,对于鲁迅这位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体大师来说,“梦”从来就是《野草》创作的一种自觉选择。
二、灵魂深处的极致“独语”
(一)区别于“闲话”的“独语”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分别“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4]。与“闲话”相对,“‘独语’是主体在特定时空结构下,基于‘外在生存性裂伤’的触动和撩拨,沉入心灵深处的冥思,是对自我存在的反身回顾和灵魂审视”。即从外在环境来看,“生存性裂伤”的疼痛会导致个体形成 “不可对话”“不能对一话”“不必要对话”的心理状态,在此状态下会产生独语的心理诉求;其次,从主体内在的心理结构来看,当外在机缘对生存性裂伤有所触动和碰撞时,主体就会自然地沉入自我追问、自我回应的心灵独语中。“独语”是不需要听者(读者)的,甚而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紧张与排拒为其存在的前提。在“独语”的心理结构中,外在世界沉寂四周,内在心灵世界却因精神的内敛而得以格外彰显。独语体文章通过多重意象的选取折射着主体的深层生命体验和了悟;相反的,也正是独语主体的深层生命体验和了悟照亮了文章中重重意象。“独语”是唱在诗人心里的歌。
(二)极致的独语方式
鲁迅早在1919年就写了几篇“自言自语”属“独语”的散文(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而《野草》“独语”的密度、以及《野草》之“独语”以梦为载体在诗集中所表现出来的属己性、张扬出来的排斥力是先前的其他创作都难以比拟的。鲁迅珍爱他的《野草》,《野草》是鲁迅的“独语”。《野草》之力充斥着全篇,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换而言之,“独语”创作视角由外而内的转换决定其艺术媒介和表现方式等必然的变化与再创造,“梦”这一特殊媒介与表现实体对《野草》的融入,使《野草》的“独语”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写实的摹写,《野草》这个长梦里的所见、所言与所想无不绚烂、无不奇突、无不诡谲、无不自由、无不张扬、无不豪放,热闹冷峻,洋洋洒洒,自如收放,势不可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创造者的艺术想象力。《影的告别》:“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孙玉石先生解释说:“下面的全篇,均是‘影’告别‘形’,也就是‘你’的时候的‘影’所作的独白。这‘独白’,可以说是鲁迅内心矛盾和生命哲学的最紧张最曲折的表述”[5]“梦”是极致的“独语”。
“梦”是“独语”的极致还表现在:第一,两个“我”的重叠与互斥。《野草》不仅有七个连续的“我梦见……”开头,而且还刻意写“我”从梦中突然醒来,强调这是一个梦魇,以求截然拉开做梦的“我”和梦境遇中的“我”的距离,“梦”可谓是鲁迅《野草》中最大的障眼法。梦不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它在艺术上创造了两个“我”的对话。两个“我”在《野草》中会有各自独立的话语权并产生或合或斥的双重音效果,这和“自言自语”的单声道是不同的;“也可以说在大多数诗中是诗人和自己做了一系列的对话,其中包含的问题和冲突组成了作品意义的范围”。[6]这样,《野草》之“独语”借助于“梦”的体式获得了双重甚至更多重的艺术内涵与艺术价值。第二,“我”梦的不可替代性。梦的主体是“我”,即确定做梦人“我”是此梦唯一的行为主体和仅有的感受者,他人不可替代。同时梦可以被做梦人“我”复述出来,但梦中的经历与内容具有单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即总会出现言有尽而梦无限的情况。如此,“梦”的独语也就赋予了有限文字以最大限度的表现张力,给人以视觉上、精神上的最大冲击。王尧在《乡关何处》中说“《野草》式的‘独语’方式,给人以震撼,但你无法接近他在生命、在心灵中‘探险’的深处。”王尧继而对比道,读周作人独语的文章,“可以同他一起乘乌篷船,一起吃茶去”,可是对于鲁迅,“我们可以遥望天边冥想他,但无法说清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被“震撼”,却难以也不能与之共鸣,因此“鲁迅永远是孤独的”!第三,“梦”造成“独语”在时间上的即时性和不可逆性。李欧梵先生曾说:“七篇梦诗中,有四篇写诗人在最后突然醒来了,似乎是再次告诉读者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梦魇,是非现实世界。梦中叙述者提供的那一点点与现实的联系,充其量也是消极的、短暂的。”梦的即时性也说明“梦”受制于当时的外在环境因素,而且就算是“我”本人在梦醒后也不可能尽述梦境,而且更不可能再有重复梦魇的出现。鲁迅自言,“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因此,如果说《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独语体”的创作潮流与传统,后续作家可以争相学习并仿效之,那么《野草》中的梦“全属于我自己”,他人根本无法进入、更无从仿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梦”的属己性,让《野草》本身收获了在鲁迅的创作中,乃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不可能再被复写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
《野草》是鲁迅最深邃、最幽美的生命诗篇。哲人海德格尔说,“激情中的这种伸展并没有使我们简单地超出自身,而是把我们的本质聚集到其本真的基础之上,把这个基础首次在这种聚集中开启出来”“我们才得以扎根于自身,并且目光尖锐地掌握住在我们周围和在我们之中的存在者”。《野草》之“梦”就是如此吧!
[1] 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古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3.
[2] 李欧梵.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4.
[3] 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38.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0.
[5]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8.
[6] 李欧梵,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0.
2095-4654(2015)07-0071-03
2015-03-20
I210.9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