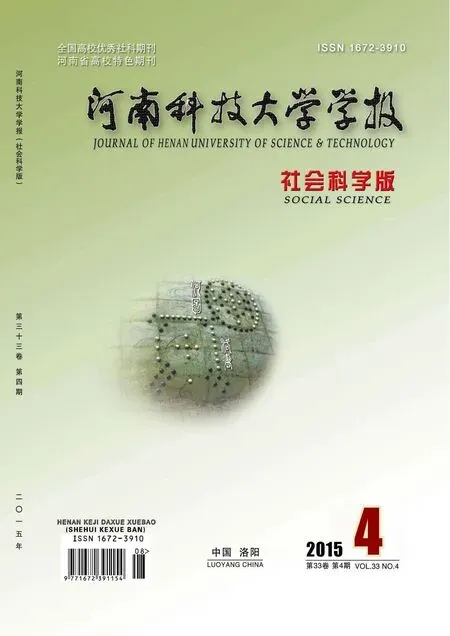论秘密收养制度
2015-03-17席虎啸
摘 要: 秘密收养作为一种主要的收养方式,在整个收养制度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虽然公开收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秘密收养的法律地位,但秘密收养依然有广阔的生存空间。然秘密收养制度毕竟保留了与生俱来的缺陷,不得不予以规避。鉴于此,通过协调送养人隐私权与被收养儿童知情权之间的冲突、细化责任承担方式、明确收养行为效力等举措来完善秘密收养制度就变得迫在眉睫。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4-0105-04
DOI:10.15926/j.chki.hkdsk.2015.04.020
收稿日期: 2014-12-21
作者简介: 席虎啸(1990—),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人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总有一种排他的占有欲。这一心理因素在收养法领域也有体现,集中表现为秘密收养制度。收养人为了保障自己对被收养儿童的单独占有权,防止被收养儿童在得知收养事实后影响既已建立的父母子女关系,而在收养关系成立时通过协议约定保密义务。秘密收养制度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其合法性值得肯定。收养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侧重于保护收养人的利益,到重视维护被收养儿童的利益,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导致秘密收养制度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公开收养制度所取代 [1]。虽然公开收养制度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但是秘密收养制度始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此一来,如何完善秘密收养制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一、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问题
我国《收养法》第22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显而易见,立法仅肯定了收养人与送养人之间的保密义务,而忽略了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问题。虽然收养协议是收养人与送养人之间缔结的双方民事法律关系,但涉及的民事主体有三方:收养人、送养人和被收养儿童。众所周知,收养关系生效后,收养的实际效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收养儿童的行为表现,但被收养儿童的行为表现具有或然性。正常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被收养儿童就能融入新家庭并健康成长,可一旦他知道自己被收养的事实,谁也无法预测其有怎样的反应。也许他早已习惯了现有的生活环境而坦然面对,也许他会暴躁地责怪亲生父母的无情或埋怨收养人的欺骗,还有可能会因这个“意外的消息”而身心备受煎熬,从此心中烙下阴影而变得叛逆。因此,我们应重视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对收养关系的影响,并从微观层面对其作出合理规制。
笔者认为,构建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收养人主动将收养事实告知被收养儿童;二是被收养儿童通过其他途径对合法的“伪造身份”产生怀疑时请求告知收养事实。前者中的收养人积极公开收养事实,虽属于尊重被收养儿童知情权的表现,却无形中隐藏了一种巨大的“善意伤害”。理由在于:被收养儿童是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精神抗打击能力差,此时贸然告知其真相实则弊大于利,基于为儿童利益考虑,立法应该限制收养人主动公开收养事实的权利,只有等到被收养儿童年满18周岁时收养人才享有主动告知其收养事实的权利(16周岁以上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独立生活的被收养人同样属于可告知对象)。后者中的被收养儿童通过其他途径发现收养事实而要求知道亲生父母情况时,则收养人不得阻止被收养儿童行使知情权。但收养人也应尽到审查义务,不能轻易就告知收养事实,要对被收养儿童提出的“怀疑证据”进行初步鉴定。例如,儿童感觉自己长得不像收养人而开玩笑说自己不是其亲生的,这时就不能草率地告知其真相;倘若被收养儿童通过血型发现收养人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时收养人就有义务坦白告知,此乃上善之策。否则,执意隐瞒终将导致被收养儿童不信任的后果,走到隔阂加深或矛盾加剧的地步实属愚蠢之举。
二、送养人的知情权问题
按照《收养法》第23条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就意味着送养人必须丧失知情权吗?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只有在立法设定的正常情况下才不需要赋予送养人知情权。所谓的正常情况是指收养人能够积极履行善良家长的抚养义务和监护义务。然而这种正常情况只是立法者在静态管理中的理想希望,实际上它可能处于潜在变化中,例如收养人虐待、殴打被收养儿童,或者收养人家庭发生变故无能力再抚养被收养儿童等。
一项制度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事后怎样解决问题,而在于事先如何预防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等到不利于被收养儿童的事情出现时才授权送养人行使知情权,而是在收养关系成立时就应允许收养人行使知情权。笔者认为,送养人的知情权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通性质的知情权,即正常情况下亲生父母对子女成长情况的关心与了解;二是特殊性质的知情权,即非正常情形下送养人介入被收养儿童的生活,并改变原有的收养协议。可问题在于秘密收养制度中送养人如何才能做到既保守收养秘密又获取被收养儿童生活信息。有学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匿名收养”制度,即收养时不向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公开收养人的身份。这种“匿名收养”一般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终止被收养儿童与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然后再以法定的秘密收养方式和程序收养该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生父母无法直接从收养人处了解情况,因此应当允许亲生父母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请,委托该机构对被收养儿童的生活进行了解进而告知亲生父母 [2]。
但“匿名收养”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在我国是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匿名收养”制度缺乏可移植性。因为在国外收养儿童必须通过政府专门设立的收养机构进行,公民之间不能通过缔结协议而直接收养他人的子女。这一点与我国截然相反。我国若直接移植“匿名收养”制度,则需要创设一套新机制。首当其冲是设立专门的收养机构,难免要大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之制度具有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特点 [3],超前制度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也未可知;更何况我国收养规模日益庞大,完全依靠收养机构反馈被收养儿童生活信息运作起来困难重重。所以,我国移植“匿名收养”制度并非明智之举。既然法律移植路径不可取,我们就应转向求助于本土资源。考虑到收养行为的产生在我国不是由专门机构主导,而是由公民主导,因此无法禁止送养人通过各种途径行使知情权,权宜之计只能是在承认其知情权的同时合理分配责任。为此,笔者建议设置多倍赔偿制度,加大对过度行使知情权而不履行保密义务的送养人的制裁,迫使送养人平衡对待权利与义务。此举虽属事后救济,不能从源头上事先杜绝侵权事实的发生,但至少对送养人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指引作用,毕竟权益的背后隐藏着风险。
三、送养人的隐私权问题
俗话说“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但在收养领域存在一个打破常规的现象,那就是被收养儿童的亲生父母在订立收养协议时完全放弃了与子女有关的一切权利,也拒绝子女获取与自己有关的任何信息。于是,秘密收养中送养人的隐私权问题开始进入法律视野。
立法保护送养人的隐私权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有权利要求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被打扰。送养人作为父母当初将子女送给别人抚养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必然经历心痛欲绝的过程才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基于被送养子女很少有原谅亲生父母的考虑,为避免子女长大后找自己“算账”,防止造成二次伤害,父母最好的选择只能是“眼不见心不烦”地消失。另一方面,送养人一般或是贫穷,或是残疾,或是有传染病,以至于不便抚养子女,换句话说,送养人的条件比收养人差,父母也怕子女得到自己的信息后与收养人关系就变得不再和谐,影响其原本美好的生活。
但问题在于送养人基于单方法律行为能排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吗?更何况这种单方法律行为还具有抛弃身份关系而非财产关系的性质。这涉及到如何协调被收养儿童知情权与其亲生父母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送养人的隐私权有保护的必要性,但法律必须要限制它的权利行使空间,可采取“生前限制与死后自由”相结合原则。具体而言,若送养人与收养人在收养协议中约定禁止公开其身份,且生前未授予收养人公开权,那么收养人应尊重其隐私权;若送养人死亡,即使协议有禁止性约定,则收养人也可不受原有限制而公开收养秘密。如此安排,既尊重了送养人的隐私权,又不至于过度排斥被收养儿童的知情权,恰到好处地缓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四、秘密收养的效力问题
秘密收养制度成立的核心要件是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结收养协议。可问题在于满足形式与实质要件的收养协议就理应具备合法性吗?还是说收养协议起初的合法性受到后来法律实效因素的挑战?笔者认为从收养制度的历史渊源中可以找到头绪。收养制度的生效原则最初采纳自由协商主义,而后过渡到行政登记主义,近来法院裁判主义又成为实践新宠儿。
自由协商主义是将收养协议完全等同于一般契约,它按照合同法的框架来构建收养法的制度体系,完全忽视了收养制度独特的身份性。行政登记主义较自由协商主义有所进步,开始重视对收养行为的监督,有利于保护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鉴于此,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的效力采取登记要件,未经行政登记的收养行为属于事实收养或民间领养,而不构成法律收养。
然而,行政登记主义只适用于收养协议成立之际以及双方当事人全面履行收养协议的正常情况,而解除秘密收养协议时行政登记主义已效力大减,不能再有效规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笔者建议解除秘密收养协议应采取法院裁判主义,借用法院的力量来调整收养行为。一方面,从法的调整对象来看,收养法虽归于民法范畴,但收养法属于特殊法,其人身性决定收养行为的解除与一般民事行为的解除不同,不可混同适用,否则会放任收养领域非法现象的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收养行为在解除权和撤销权的行使方式上不作区分,必须通过法院才形成解除与撤销效力。另一方面,解除收养协议属于身份关系的变更,涉及亲属、家庭和继承等一系列法律关系,对收养人、送养人和被收养儿童三方当事人都影响巨大,并不是简单的财产性质的合同。众所周知,财产性质的合同绝大部分内容牵涉金钱,解除此类合同无非是赔偿问题,其合同利益或损失可以弥补,但是解除收养协议对当事人的身心伤害是无形的,纵使巨额赔偿也难以消除影响,更何况收养协议的解除是一揽子工程,涉及家庭、合同、侵权等内容,从任务量来看,法院更专业、更高效。
五、秘密收养的责任承担问题
秘密收养制度中,收养人的主要责任是对被收养儿童尽善良家长的抚养义务,送养人的责任主要是遵守收养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若双方都未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怎么办?《收养法》第30条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显而易见,此款规定不够全面。一方面该法第30条的责任承担与分配只强调了收养人和送养人的损失,丝毫未提及被收养儿童的损失;另一方面,收养协议既然具有人身性,为何精神损害赔偿未明文列举,而是大肆渲染物质赔偿呢?
秘密收养中被收养儿童能否提起损害赔偿?按照法律规定,任何人受到伤害都有权利向加害人主张赔偿,儿童也不例外。对于亲生父母造成的伤害,要区分善意和恶意。善意伤害是指亲生父母受主客观条件限制被迫将其送养给他人抚养,单方面改变了儿童的身世,剥夺了儿童的同意权,但出发点是为了儿童,故这种伤害不在赔偿之列;恶意伤害是指收养生效后,亲生父母未履行保密义务变相插手或干扰被收养儿童的生活,对其造成不良影响,此时可请求赔偿。当然,养父母也可能伤害被收养儿童,例如被收养儿童遭遇重大疾病需要血亲援助的时候,养父母拒绝提供送养人信息,导致被收养儿童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或被收养儿童已经成年,养父母仍然不告知其亲生父母的情况,故意侵害其知情权。我国《收养法》第23条规定,收养关系生效后,养子女与亲生父母不再具有父母子女关系,仅与养父母构成拟制父母子女关系。若按照“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具有可诉性”的传统观点,那么被收养儿童无权向养父母主张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必须摒弃,一方面不符合保护未成年权益的人权要求,另一方面严重违背法治精神,当下的坚定立场应是侵权的成立不受既已生效的父母子女等亲属关系的影响。或许有人认为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因为被收养儿童的财产由养父母保管,即使获得赔偿也是将养父母的财产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而已。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只是反映了实然法与应然法的脱轨,并不能据此否定应然法的正当性。
秘密收养制度的责任构成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答案是肯定的。秘密收养涉及身份关系的变动,若发生严重人身损害理所当然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收养法》未提及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因在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最初只存在于学理之中,长期未获得法律支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合法地位才得以初步确立,之后2010年《侵权责任法》又全面巩固和完善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收养法》出台较早。因此,收养人、送养人和被收养儿童在特定情形下都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可问题在于收养关系已经解除还能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吗?笔者认为,收养协议解除与损害赔偿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就因果关系而言,有因才有果,但解除收养关系与赔偿损失同属“果”,两者不是因果对应关系,故解除收养关系并不影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