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运营商屡屡“中枪”为哪般?
2015-03-16作者金峰
作者 | 金峰
“3·15”运营商屡屡“中枪”为哪般?
作者 | 金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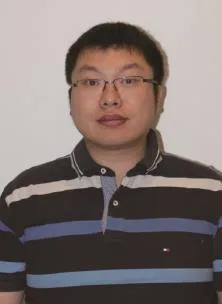
央视“3·15”晚会前,笔者原以为只有中国移动难逃此劫,最后却发现三大运营商无一幸免。其中,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栽在了骚扰电话上,中国联通栽在了“黑卡”上。接下来,运营商又被国内媒体集中口诛笔伐了好几天。那么,运营商再次“中枪”究竟为哪般?
可曝光、有共鸣的媒体选材使然
在国内,媒体报道的选材尚未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一些政策上需要重点扶持的行业不宜过多暴露问题,例如3·15晚会前传闻将被重点曝光的是互联网行业,但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晚会并未过多涉及;而一些领域,由于涉及到国家标准而导致的质量欠佳也不宜被曝光。
一些企业如果能量强大,过往被曝光后又能让媒体快速封口,也不宜被曝光。于是挑来挑去,运营商几乎年年都成为乱枪扫射的对象,因为他们规模大,政策不用小心呵护,加之暴露的问题中有不少确实违反了政策法规,而年复一年的曝光,也从未有宣传部门的干涉,它们自然成为曝光的最佳对象。
此外,从“3·15”的特性而言,是一个让广大消费者解气的盛宴,曝光的产品与服务必须要符合普通消费者长期存疑又能直接感知的领域,运营商的产品与服务无疑符合这些特征。
首先,运营商是国有企业,而且被消费者认为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消费者在看待运营商时往往带着借助垄断赚了很多钱且服务也很差的惯性思维,而媒体也会将其作为国企代表加以利用;其次,运营商提供的是普遍服务,媒体的每个受众也都在使用,曝光运营商能让受众产生共鸣。
曝光的问题是经营压力的体现
如果真的像某些专家所说,将运营商打造成为纯公共服务的组织,那么收入多少、有无增长与运营商就毫无关系,运营商也不用费尽心力地寻找收入增长点,也就不会有相应的问题产生。可惜运营商是市场经营主体,并且国家还在想法设法让这个市场加入更多的竞争者,如虚拟运营商等。在这种情况下,运营商必然要寻求不断增长。
对运营商这类大型企业,市场经营的指标是层层分解下达的,按照一般的惯例,指标向下传递呈现出“牛鞭效应”的特征,也就是说总部如果要求增长1%,可能层层传递到最底层的执行端时,就需要增长5%,这其中既有各分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也有上层部门为确保完成指标的考虑。最终的结果是,市场经营的末梢部门和员工肩负着较大的压力。
从央视“3·15”晚会曝光的几个运营商案例看也确实如此,例如湖南常德联通卖“黑卡”,原因就是该部门年底指标未完成,不得已先把卡激活,而渠道用微信传用户的身份证图片作为实名认证也是在配套工具尚未跟上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用户可不愿买了卡,再自行跑到营业厅中办理激活。至于非实名制的卡,媒体虽已对其危害言之凿凿,但用户却希望即买即用,同时担心个人详细信息提供后造成隐私的泄漏。
至于移动与电信的骚扰电话,众所周知,现在运营商期盼普通用户每个月多打几分钟电话几乎是一种奢望,而一些业务部门拥有的资源只有语音,想要保证收入的稳定,甚至有所增长,只能在企业的营销电话上做文章,至于什么穿透技术、电话号码池等,也只不过是最终的工具。
运营商独自承担净化行业之责略失公允
目前,公众有这样一种观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让他们厌恶事情的存在,都是运营商的责任,因为运营商在其中获利了。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去指责出现在浏览器、APP中的广告,因此笔者认为把这些全部归罪于运营商略失公允。原因何在?
首先,运营商不能拒绝提供服务。运营商提供的管道服务是普遍服务,在国家没有明确政策规范的前提下,并不能主动拒绝向骚扰行为的制造者提供服务,这就如同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电动机器污染了环境,而电力公司并不能因此停止供电。
其次,用户所厌恶的,法律却尚未禁止。例如骚扰电话,虽然公众厌恶,媒体质疑,但若要进行规范化管理,甚至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义。但事实却是目前不少的定义与管理规范尚且缺乏,例如同一个电话,对某些用户而言是骚扰,对另一些用户就不是,难道就因为部分用户的厌恶就将其封号?
最后是技术手段尚未成熟。一些用户认为,运营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所谓的垃圾短信和电话等加以过滤,例如通过对文字的识别过滤垃圾短信;通过对语音的识别过滤骚扰电话。但显然,这高估了当前的技术水平。例如目前的文字分析识别远未到精确的程度,尚不能分析“真假房东”的短信,语音分析更是处在初级阶段。更何况,即便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用户可能又会抱怨自己通信的隐私被运营商截取,那时运营商恐怕又要背上窃听的罪名了。
今年央视的“3·15”晚会,运营商成为了用户和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运营商是否应该独自承担净化行业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