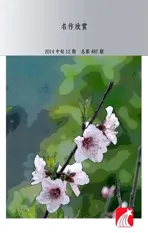评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亚瑟王之死》中对“英国性”的创造性再现
2015-03-15郭瑞萍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石家庄050000
⊙郭瑞萍[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00]
作 者:郭瑞萍,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米勒(J.Hillis Miller)曾言:“我们需要对‘同一’故事一遍遍重复,因为这是用来维护我们文化中基本的意识形态的最强大的方式之一,也许是最强大的方式。”①在米勒看来,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髓,需要不同时代人们的重复和延续,而改编是延续经典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不同时代作家对同一部作品改编的目的各不相同,既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有改编者对原著独特的思想观照。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亚瑟王之死》(The Death of King Arthur,2011),也蕴含着作者在后现代语境中对原著的特殊认识与思考。阿克罗伊德在评论丁尼生的诗史《国王之歌》(Idylls of the King,1885)时曾说:“亚瑟王的真正意义是:他不但没有死,而且还会重生,代表英国人的理想……这部史诗表明,亚瑟王传奇不只是传说,更是伟大民族神话和象征的源泉。因此,丁尼生在追溯亚瑟王的悲剧人生时,同时也是在追溯民族文学的源泉。”②这样的评价也适用于阿克罗伊德本人的创作实践,他在改编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时,不仅在复现一个古老的故事,同时也在通过亚瑟王的故事追溯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渊源。
《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自问世以来影响了许多佳作,不仅成为好莱坞大片《亚瑟王》的经典蓝本,而且也成为后来许多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取材于亚瑟王传奇的作品从古至今不绝如缕。③阿克罗伊德的《亚瑟王之死》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马洛礼作品的创造性再现,将几个世纪以来的“亚瑟王热”推向高潮。对“英国性”的重视与思考是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共同特征,他对《亚瑟王之死》的改编也是如此。在阿克罗伊德看来,“英国性”主要是指英国民族特质,是英国文化、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象征。在改编过程中,阿克罗伊德能超越意识形态束缚,对情节、人物和结构等进行巧妙整合与提炼,并通过糅合现代人生体验,为原著注入时代元素,使“英国性”得以最好的延续和体现。
一
阿克罗伊德在改编《亚瑟王之死》时所运用的改编策略基本上属于“忠于原著”的改编或“还原改编”。作者主要通过缩写和重组再现马洛礼的原著,生动、简洁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如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普尔曼(Philip Pullman)曾评价说:
我认为阿克罗伊德的《亚瑟王之死》十分精彩。这部作品最让我钦佩的是叙事的清晰。这个故事要求叙事风格既简洁又庄重,兼顾好这两种技能并非易事,但阿克罗伊德非常娴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好任何事情。我非常欣赏这个版本。④
普尔曼的评价很好地表达出阿克罗伊德的改编才能。具体而言,阿克罗伊德对原著的改编主要体现在题目、语言、叙事结构、内容和主题等方面。作者本人对此曾明确表述:
在我的改编本中,我将法文题目Le Morted D’Arthur改为英文The Death of King Arthur,这样可以更好地传达原著的意蕴。改编本没有完全拘泥于原著的形式,我把马洛礼的中世纪散文改为当代散文。为了达到简明效果,我还将原著缩写。我希望通过改编,使亚瑟王故事的精髓能被清晰呈现,人物更加令人信服。原著中的一些内容杂乱而重复,这虽然可能使中世纪读者感兴趣,但不符合现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也改写了原著中相互矛盾的部分。尽管我对原作有所改动,但我希望依然能传达出这部经典的庄严和悲怆。⑤
这段话基本阐明阿克罗伊德的改编策略和意图:即通过对语言的现代改编和对原故事的缩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亚瑟王故事的精髓,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著的庄严和悲怆,让现代读者产生共鸣。
阿克罗伊德将原著的题目由法文改为英文,看似简单的改动却使文本意义发生根本改变。因为在简单的语言转换背后隐含着作者对这部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定位,更加突显出这部作品作为英国民族史诗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作者对亚瑟王英国身份的认同。此外,在改编中,阿克罗伊德还将原著的语言转换为简洁而优美的现代英国散文,不仅证明作者可以同时驾驭中世纪散文和现代散文的娴熟能力,而且也表明现代英语语言完全可以承载并展现经典文学的魅力。
除题目和语言外,阿克罗伊德对叙事结构和内容也进行了大胆调整。通过梳理和分析两部作品的故事架构可以发现,阿克罗伊德把整个故事的长度从原来的八百多页减至三百多页,有意删减掉那些穿插场面,使情节线索更为自然显明,叙事更加流畅、紧凑。为保持原著的风貌,阿克罗伊德和原著的作者一样,也在几个明确的主题之下串联故事,以原著中几个核心人物和事件作为情节枢纽,以亚瑟王出生开始、亚瑟王朝的毁灭终结,既简洁而唯美,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诱人的故事和精彩的场面,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可读性。例如,阿克罗伊德将原著的21卷压缩成6部分:依次是“亚瑟王的故事”“兰斯洛特的冒险”“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圣杯传奇”“兰斯洛特骑士与桂乃芬”和“亚瑟王之死”。通过比较和分析阿克罗伊德的改写本与马洛礼的原著会发现,阿克罗伊德的《亚瑟王之死》中的6个部分中,如果把第2和第3部分,第5和第6部分合并在一起压缩成4部分,就会和原作中的4大部分对应,可见结构的重心并未有太大转移。然而,阿克罗伊德的叙事结构却比原著更清晰、更有层次、更对称而完整。如第4部分是“圣杯传奇”,居于作品结构的中心位置。第1部分以亚瑟王出生开始,第6部分以亚瑟王之死结束,首尾形成呼应。第2部分和第5部分都以兰斯洛特为题目,两部分不仅前后一致,而且也和首尾两部分构成并列。同时第3和第5部分各自讲述的两对爱情故事也形成对照。可以说,阿克罗伊德建构故事的风格体现出典型的英国教堂建筑特征: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结构对称而严谨,各部分之间形成有机整体,显示出严肃而端庄的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可见,阿克罗伊德试图让改编后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彰显着英国文化特色。
哈琴(Hutcheon,Linda)曾言:“当情节被浓缩和精选之后,它们有时会更为有力。”⑥改编后的《亚瑟王之死》不仅加快了故事的节奏,也加速了故事中人物最终悲剧命运的到来,在形式上更好地传达出人生短暂的命题,使整部作品叙事更加有力。史密斯(Witness Zadie Smith)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白牙》(White Teeth,2000)被改编成电视时也曾谈到缩写的优点,他说:
为了使这部作品更赋有魅力,缩写是必要的,至少一种变化是启迪性的……篇幅虽然被缩短,但嵌入了改编者的动机,并达到艺术简洁的效果。我为之震惊,因为它使我明白,如果在创作小说时我能运用同样的策略,也许我会写得更好。⑦
阿克罗伊德对《亚瑟王之死》的改编可谓达到了史密斯所说的这种效果。虽然它只是一部简写本,但是经过阿克罗伊德的精心选材和安排,完好地保留了原著的精髓,传达的信息和原著却一样丰厚。
二
阿克罗伊德的改编不只是简单删除情节上的各种枝蔓,而是立意明显高远了。虽然改编会受到不同时期主流文化诉求的影响,但是更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有关。阿克罗伊德的《亚瑟王之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这部作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意蕴值得人们重新阅读和回味。虽然骑士制度已经衰落,但骑士文学所倡导的忠诚、宽容、诚实、勇敢等美好品质也应是现代人的道德诉求,因此,阿克罗伊德不只满足于再现一个浪漫传奇故事,而是旨在最大限度地从不同维度创造性地再现和传达出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英国性”内涵。阿克罗伊德始终强调一种理念,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世代传承的信仰、传奇和风俗等历史文化传统,它是凝聚一个民族并产生民族认同的元素和力量。对他而言,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是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因此诱惑着不同时代的英国作家用各种艺术载体对其进行改编。阿克罗伊德的改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传统的延续,并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塑造挖掘出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民族性格特征。鉴于此,阿克罗伊德没有过分渲染打斗场面,而是更关注事件和人物本身,并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精心描述表达其对历史和传统的独特认识和思考,挖掘出作品中的英国元素。
亚瑟王和兰斯洛特两个中心人物是阿克罗伊德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和“民族性”的象征,因此,在作品中,阿克罗伊德对他们着墨最多。
在阿克罗伊德的笔下,亚瑟王是“世上最高贵的国王和骑士”⑧。首先,当前任国王尤瑟(Uther Pendragon)去世后,主教听从梅林的建议召集所有的贵族骑士,凭借一把插在教堂墓园石块中的“石中剑(calibur)”来选定新国王,宝剑上的铭文是:“拔出此石中剑者,即为不列颠之王”。经过多次尝试,除亚瑟之外无人能将其拔出,于是亚瑟成为不列颠的新国王。阿克罗伊德借此强调了亚瑟王的高贵出身,因为亚瑟后来被证实是老国王的儿子,所以只有他才能将剑拔出。其次,在执政初期,亚瑟王便征服整个北部地区和苏格兰,拓宽了英国的疆域,使不列颠迎来了空前的统一和强大。因此,他被视为所有国王中最伟大的,例如,作者借鲍斯爵士之口说:“亚瑟王和马克王完全不一样,亚瑟王永远讲信义。”⑨
阿克罗伊德对兰斯洛特更青睐有佳,认为他是“骑士之花”。例如,他写道:“从来没有任何骑士赢得过如此多的荣誉。整个世界都在赞美兰斯洛特爵士。”⑩在作品中,作者借不同人物之口高度赞扬兰斯洛特的伟大品格。如亚瑟王的姐姐把兰斯洛特囚禁后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骑士。”[11]塔昆爵士在和兰斯洛特交战时说道:“你是和我交过手的最强大的骑士。”[12]特里斯坦和兰斯洛特的侄子勃里奥伯勒斯爵士决斗时说:“你是兰斯洛特的侄子?那我不会再和你打了。我太爱那位盖世无双的骑士了。”[13]王后桂乃芬曾对兰斯洛特的儿子加拉哈说:“兰斯洛特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士,并且有高贵的血统。你和他很像。”[14]深爱着兰斯洛特并为他殉情的艾斯特罗特少女伊莱恩表白道:“上帝保佑,他是最完美的骑士。他是我在这个世上爱过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位。”[15]高文对伊莱恩说:“小姐啊,你真好福气,他是世上最勇敢、最尊贵的骑士”[16]。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兰斯洛特兄弟之口高度赞扬兰斯洛特的伟大一生,他写道:
兰斯洛特啊,您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骑士的领袖,您如今虽已躺在这里,但我还是要说,人世间没有一个骑士是您的对手。在持盾的骑士中,您是最谦逊的;在骑马的武士中,您是最诚实的;在跟女人相爱过的有罪的男人中,您是最忠心的;在佩剑的骑士中,您是最仁慈的。普天下所有的骑士,没有人能比您更善良!在聚宴厅陪伴贵妇人的男人们中,没有谁比您更温和、更优雅!在手持长矛与仇敌作战的骑士中,没有人比您更威武、更豪迈![17]
作者通过众多人物之口多维度地展现出兰斯洛特的人格魅力。
同时,阿克罗伊德还通过兰斯洛特的具体行为赞扬他的宽容、大度和忠诚。作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亚瑟王和高文由于误解而率军征讨兰斯洛特时,他不但不想与他们为敌,反而命令自己的手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亚瑟王和高文的性命。如鲍斯骑士与亚瑟王交手时将国王挑落下马,然后便拔出宝剑问兰斯洛特:“要不要让我现在就结束这场战争?”[18]他打算就此杀掉亚瑟王,兰斯洛特连忙制止说:“千万别杀国王,你如果再敢碰他一下,我就要你的命。我决不能眼睁睁看着敕封我为骑士的高贵国王被你杀死或蒙受耻辱。”[19]说完这话,他随后将亚瑟王扶上马。
阿克罗伊德认为这些古人所表现出的忠诚、宽容、勇敢等典型的“英国性”特质值得一代代人的继承和发扬。
三
阿克罗伊德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者,在改编中,他还通过讲述亚瑟王和兰斯洛特的个人悲剧引发人们对“英国性”中悲剧精神的认知,从而达到对全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
首先,阿克罗伊德通过展示古人的悲剧命运使读者体验到他们所承受的生命之重,从而揭示出“英国性”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早年亚瑟王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同父异母的胞妹发生关系并生下莫俊德。后来当亚瑟王与兰斯洛特交战时,莫俊德趁机造反,从而导致亚瑟王战死,亚瑟王朝和他的圆桌骑士也被毁灭。
阿克罗伊德还描述了兰斯洛特与桂乃芬王后的爱情悲剧。例如,在小说的结尾,当兰斯洛特在修道院找到桂乃芬后,他们最后诀别之前的对话凄美感人。小说中写道:兰斯洛特最后来到一座修道院,桂乃芬一眼就认出他并当场昏厥在侍女的怀里。醒来后,桂乃芬当着众人指着他说:
这场战争及世上那么多优秀骑士的死亡都因眼前这个人和我而起。正因为我俩相亲相爱,才导致我的高贵的夫君死于非命。兰斯洛特,我告诉你,如今我已下定决心要赎清自己的罪孽!我相信,只要上帝慈悲,我死后仍能见到基督的尊荣。尽管我先前罪孽深重,但在末日审判那天,我仍能像圣人那样坐在上帝身边。兰斯洛特啊,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分上,我衷心恳求你,以后再也别来见我。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离开我,回到你自己的王国,好好管理它,使它免遭战争和灾难。正因为我爱过你,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由于你和我的爱,最伟大的国王和最高尚的骑士都已遭到灭顶之灾!兰斯洛特,快回到你自己的王国去吧,在那里娶一位好妻子,与她好好过日子吧。我由衷地恳求你,请你为我向主祈祷,求主宽恕我的罪过。[20]
听完王后的这些话,兰斯洛特问道:“亲爱的王后,你是要我现在就回到自己的王国,娶一个女子为妻吗?不,王后,不可能,我今生决不违背对你的诺言。我也要像你一样,从今以后过修士的生活。我会永远为你祈祷。”[21]兰斯洛特接着说:
你不相信我的话?难道以前我违背过对你的诺言吗?我会像你一样与世俗一刀两断。在寻找圣杯时,如果不是因为你,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我更多地得到上帝的恩惠。好吧,王后,我也会和你一样去修行。如果你愿意享受人间欢乐,我会将你带回我的王国。但我发现你变了。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一定会虔诚地祈祷。我会找到一个修士,做他的信徒,过简朴的生活,赎自己的罪孽。[22]
自此分手后,他们各自在修道院的忏悔中相继离世。
小说中另一对恋人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同样以悲剧告终。阿克罗伊德在作品中指出:“他们的命运很不幸。”[23]在小说的后文中作者让兰斯洛特讲出他们的悲剧结局。兰斯洛特说:“如果我救出王后,你们说我得将她安置在哪里呢?”鲍斯爵士说:“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当年您是如何帮助特里斯坦爵士的?您不是将他和伊索尔德安置在你的快乐园将近三年时间吗?”兰斯洛特说:“我不认为特里斯坦是个值得效仿的好榜样。你们难道忘了当他将伊索尔德交还给马克王后,那位伪善的国王用利剑刺杀他吗?趁他在伊索尔德面前弹琴时,国王用一把利剑刺进他的心脏。”[24]
阿克罗伊通过展示这批古人的悲剧命运、生命之重和高尚品格使读者体验到他们不得不化为历史的人生悲凉,不仅使作品达到强烈的悲剧效果,而且还通过英雄人物的命运揭示出“民族性”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
麦基(Robert Mckee)曾说:“一个讲得好的故事能够向你提供在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那一样东西:意味深长的情感体验。”[25]在《亚瑟王之死》中,阿克罗伊德做到了这一点,他使读者经历到一场场震撼人心的情感体验。他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完全由中世纪文明滋养的浪漫传奇式人物,而是被作者赋予更多现实人性之美,甚至已成为一种隐喻。
其次,阿克罗伊德通过描写古人的悲剧故事揭示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悲剧性格。他指出亚瑟王、兰斯洛特和加拉哈等人物所彰显出的“庄严和悲怆”“无常和失落感”[26]“忧郁、勇敢、耐心”“责任、牺牲、奉献”等都是英国民族性格和民族情感的一部分。例如,加拉哈在临死前对鲍斯爵士说:“请传达我对我的父亲兰斯洛特的问候和爱戴,并提醒他在尘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27]。又如,当兰斯洛特将王后送还给亚瑟王后不得不离开亚瑟王宫时说:“命运无常。命运的车轮不停地转动。没有永恒之地。运气不会青睐一个人太久。对我也是如此。”[28]需要指出的是,在阿克罗伊德的笔下,虽然这些人物相信命运,但他们并不是悲观的宿命论者。相反,他们在命运无常面前表现出超凡勇气,如兰斯洛特去寻找圣杯前对亚瑟王说:“所有的人都得死,先生,但我们要死得荣耀。”[29]对阿克罗伊德而言,那些骑士虽然已成为古人,但他们所彰显的民族精神是不朽的。如在小说中被认为最完美的骑士加拉哈说:“我的身体将死亡,但我的灵魂将永生。”[30]作者对亚瑟王之死的描述也传达出这一信念,如小说中写道:“有些人说亚瑟王没有死,当我们需要他时,基督会派他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31]我只能说他也许已经转世,在他的坟墓上写有这样的碑文:亚瑟王长眠于此,他将转世再为王。”[32]阿克罗伊德认为:“亚瑟王或许是民族想象的一个虚构形象。然而,他是马洛礼的天才发明,因为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在英国人的情感中享有牢固而永久的地位”,因此,《亚瑟王之死》是“英国民族想象的内核”[33],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是英国民族形象的代表,“亚瑟和他的王国的悲剧命运和民族情感是一致的”。阿克罗伊德认为,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忧郁”“无常和失落感”“庄严和悲怆”等性情都是“英国性”的一部分。
以上分析表明,阿克罗伊德对马洛礼悲剧故事的再现不只是复述古人的故事或对艺术本身的一次探索,而是试图将原著中的英国文化元素复活,使当代人体验到英国传统文化的力与美。
阿克罗伊德对情节的浓缩“赢得的是故事结局快速到来的宿命感”[34],更好地传达出作品的悲剧主题。简洁的风格使阿克罗伊德的作品既犹如梵高的画,给读者留下“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印象和感觉以及无限的想象、回味、思考的空间和余地,“获得的是一种言外之意,趣外之旨”[35]。
通过改编,阿克罗伊德不仅使英国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得以继承,同时也将他对于“英国性”和人类悲剧命运的思考化在了古人的故事中,并利用古人的故事传递出对现世的人生体验和心灵感悟,体现出作者能把过去生活提高到当下存在的鉴赏能力和融合能力,使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忧患意识。例如,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今天……爱情热得快,冷得更快。古人的爱并非如此……在亚瑟王时代,相爱的人之间有真情又相互忠诚。”[36]又如,在作品的另一处,当作者叙述亚瑟王的儿子莫俊德背叛亚瑟王时写道:“英国人从不稳定和真诚,总是喜新厌旧。没什么能使我们长久地得到满足。”[37]这些句子显然承载着作者对“民族性”的历史思考和自觉意识。
桑德斯(Sanders,Julie)曾说:“尽管受多种习俗和传统以前知识和文本的约束,但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同一文本的接受各具特色、相互不同,在此意义上,古老的故事成为新故事,犹如首次被讲述和阅读。”[38]阿克罗伊德的故事也一样,虽然阿克罗伊德和马洛礼讲述的是同样的故事,但由于语境和读者都发生了变化,它的作品由于当代读者的新阐释产生新意,因此,在他的笔下,古老的故事因读者的参与变成一个新故事,传递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阿克罗伊德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纯美的理想主义者,通过改编,他把现实与理想融合,将过去与现在通过“英国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既有历史的味道,又有理想的唯美,流露出作者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珍视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
① Miller,J.Hillis. “Narrative”.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2nd.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eds.),Chicago:University of Yale,1995:72.
②[26] [33] Ackroyd,Peter.Albi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New Nork:Ranom House,2004:123,115,115.
③ 如16世纪时英国诗人斯宾塞的长诗《仙后》采用了亚瑟王传说的素材,19世纪,丁尼生在组诗《国王之歌》中再现了马洛礼的主题,莫里斯写了《桂乃芬辩》,史文朋创作了《纳斯的特里斯坦》。20世纪,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中以寻找圣杯作为构架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型。
④ Pullman,Philip.The Death of King Arthur-The Immortal Legend.Retrieved June 16,2013,from http://www.amazon.cn/Death-of-King-Arthur-Ackroyd-Pe-ter/dp/0140455 65 5/ref=sr_1_24s=books&ie=UTF8&qid=1371396479&sr=1-24&keywords=Peter+Ackroyd
⑤ ⑧ ⑨ ⑩[11] [12][13][14][15][16][17] [18] [19][20][21][22][23][24][27][28][29][30][32][36][37]Ackroyd,Peter.The Death of King Arthur.New York:Penguin Group,2011:17,299,274,88,70,75,107,179,241,242,315—316,285,285,311,311,311—312,167,274,222,291,178,220,308,251,300.
⑥[34] Hutcheon,Linda.A Theory of Adaptation.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6:6,157.
⑦ Smith,Zadie. “‘White Teeth’in the Flesh.”New York Times.(11 May),Arts and Leisure,2:1,2003:10.
[25]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1] 这句话在马洛礼的原著中是:“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阿克罗伊德的这一改动更好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观,他坚信,亚瑟王所代表的民族精神长存。
[35] 朱维之,赵澧,崔宝衡:《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38] Sanders,Julie.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