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的诗
2015-03-09翟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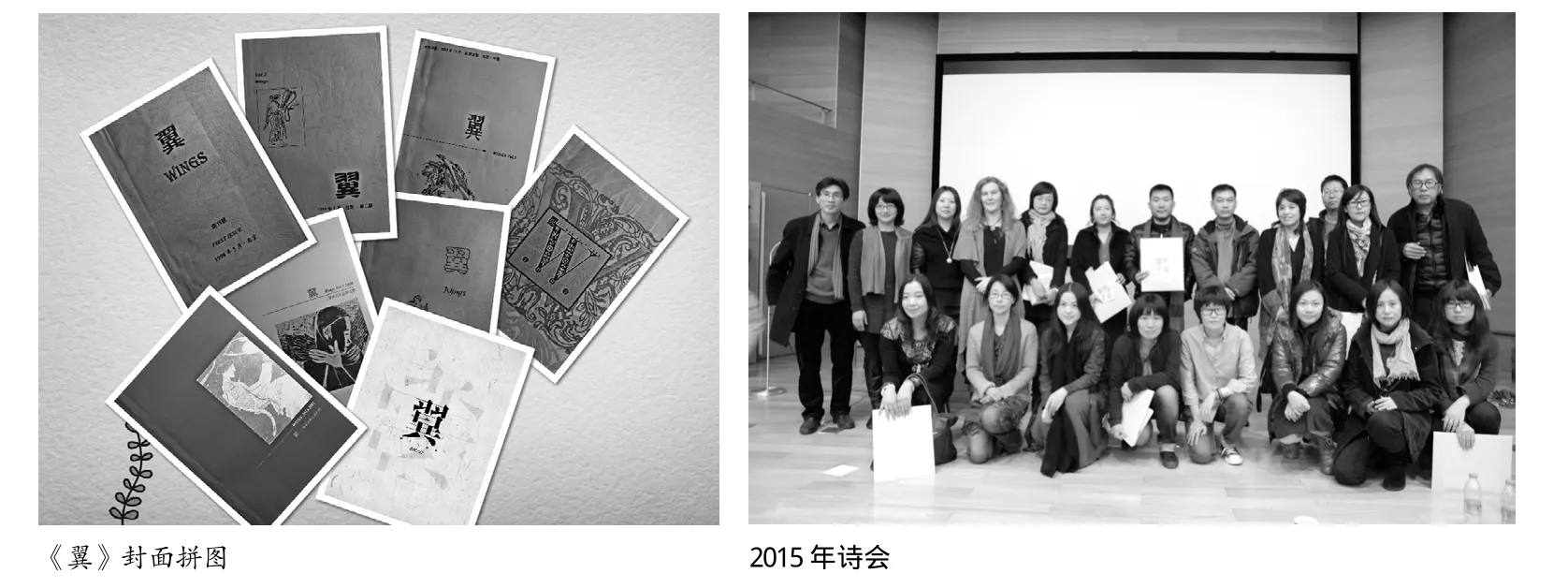
致阿赫玛托娃
因为晨昏酗酒般的黄色公寓
我向你致敬
因为优雅不足以烘烤成面包
我向你致敬
因为蜿蜒队伍中你曾佝偻而立
我向你致敬
因为绕行三圈 后人最终辨出这居所
我向你致敬
统共三间的房屋你搬来搬去
如今只剩黑白肖像瞪着你
没有主人公的房间人流不息
没有主人公的长诗无人续尾
唯有三间居所遗世而沸腾
唯有当年穿行于此的脚步
鼠窜的、心悸的、懒洋洋的
甜蜜的脚步
唯有当年的咆哮、蝇语、尖叫
以及酒和血都浇不透的心中块垒
唯有黑暗 能回到过去
除了旧皮箱仍在刀锋般闪亮
它塞满另一世界的书信
除了解说员日复一日口干舌燥
除了未来的客人
谁千里迢迢来与你促膝谈心?
除了把你的生命向全世界敞开
喷泉宫,你还能怎样?
除了在楼梯拐角处签下留言
向你致敬 除了自拍
除了风驰电掣般狂按快门
然后气息奄奄地融入商业大街
我还能怎样?
一个三流的时代
争取一个三流的下午已属不易
许多聪明人来至这里 来了又走
许多书籍 美丽精致
镶嵌画般装潢了你
如同这幢看似简朴的故居
装潢了你的苦难
唯有苏联的心灵不能装潢
唯有一代人的存在永不落幕
唯有诗 不能弯曲
我立足于此
仍然听见他们来自地底的声音
蓝蓝的诗
共时性
茶杯。空药盒。有了裂纹的塑料盆子。
在树枝上蹲着的喜鹊。干花。死去的木棍。
筷子。碗。油漆剥落的铁门。
旧地板。从墙角迅速溜跑的蟑螂。
数字。符号。舔嘴唇的舌头。风吹光的道路。
一滩干鼻涕。棉球。碎蛋壳。指甲。
粘着眼屎的眼睛。广告。窗户。
用袖子擦眼泪的女人。收破烂人踩扁的鞋跟。
微博上被PS过的假照片。元首的死。
烛火,钥匙。拷打和强奸。化成纸浆的书。
煤气表。银行帐户。希格斯粒子。
无人的葬礼。牙刷。发霉的牛奶。
你练习着眼力,目光炯炯。镜子。台上可耻的脸。
它们是你的角膜。针头。输液管。
塞满沙子的喉咙。它们是你的存在。
助产士。时针画着圆,没有终结。
你写。你看。继续看。这面小鼓
敲着,你呼吸的节奏。
曹疏影的诗
3月12日,兼寄萧红
那么多死亡挂在她身上
我想为她一一摘去
刀子下的死,烂完了的死
病毒和绿牙齿滋生的死
坑里的死,白脑袋兔子
它那死一般的死
大鱼在江水下吞吃血块
度过她一人那么多寒冬
我来到香港岛的灯火里
想帮她熄灭那些残忍的火焰
可那么多死亡挂在我身上
不会疼的死,笑着的死
桥上的、发烫的液晶屏里的死
散步时的死,被死亡梦见的死
次次总需一只验孕棒。
那上面的空白是灵魂能否生育的放行灯,
也许也是为触碰高级失误了的阅读。
宇向的诗
隐 匿
沿着一个我,就看见
她游荡在暮年里
永远一个人
不愿种花,养猫,缝制新衣
不愿登堂入室
看上去她不恐惧,或许心怀恐惧
也不渴望,或许深藏渴望
一次次
避开规劝她的人
就像闪躲一枚枚子弹
她是《第一个人》是《局外人》
关于“自杀”
也属于严肃的诗
沿着另一个我,就看见
她在午后的太阳里
培育植物。烘烤蛋糕
坐在钢琴前弹奏圣歌
她试图让自己深信
旁边一排排洁白的孩子
煦风般拂过稻田
可这些救不了她
她来自别人的性交
属于毒气和憎恨
以色列在黑暗里
在我的黑暗里,她是
另一个被毒与被憎的
名为上帝的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