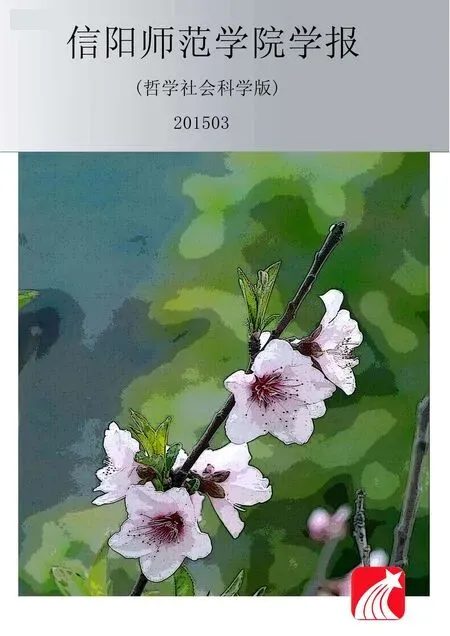论新启蒙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2015-03-01张江芬
张江芬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论新启蒙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张江芬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新启蒙运动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所内蕴的生命力的现代表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实践要求。新启蒙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新启蒙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就中国文化现代化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新启蒙运动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加强了中国文化精神主体性的挺立,并确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开展的实现路径。
新启蒙运动;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主体性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兴起的新启蒙运动,是一场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追求“民族自觉和自信”的思想文化运动。目前学术界对新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做出了阐释,认为新启蒙运动较五四启蒙而言是胜利了,因为它依靠了强大的世界性思潮,而且根植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它的胜利是各种合力的结果[1]。但也有论者对新启蒙运动提出了质疑与批评,认为新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化”思潮本质是外来文化的“传统化”,并没有把握近代中国国情的实质[2],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影响甚微。本文以新启蒙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为视角,考察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运动开启的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影响,希望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起与建构有所帮助。
一
随着清王朝国门的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师法西方文化的声浪伴着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推向高潮。此后一段时间里,主要以否定性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偏颇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占据着一定地位,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新启蒙运动在发生学意义上是顺应着“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3]190的时代需要而发生的,与新文化运动不同的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更强调传统的价值,及其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意义。新启蒙运动发起人陈伯达指出“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一方面要“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4]6-13;另一方面“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5]169。张申府也认为“对于文化,中国有其特殊的贡献”[3]201。“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6]161。可见新启蒙运动在发生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
其一,就新启蒙运动发起的文化生态背景而言,当时,国民党为加强其思想文化控制,以尊孔复古作外衣,大力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北“满洲国”推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政策,同样利用传统儒家文化里“仁义道德”和“王道政治”等理论资源为其侵略作辩护,共同将传统文化推向了灭绝的边缘。此时,如果不发生一场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将难以解决自身生命力衰竭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陈伯达提出“启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救中国的思想”[5]。张申府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本就是中华民族的反文化侵略的运动,换言之,也就是文化上的反侵略运动”,“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国家,要有一个新的文化或文明,自必然要反抗文化上的奴化,自必然要反抗文化上的侵略”[3]334。艾思奇也认为“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和“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新启蒙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7]744。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民族危机面前焕发出了其内在的韧性。中国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体现在其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上。正如不少论者所言,中国文化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是“生命典范”式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将代表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生命的“圣贤”视之为人之文化生命之本的孝道伦理,就内在地包含了自身面对圣贤而观照到承续并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生命的历史责任感,这种关联即是文化传承性的内源。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在近代以来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现代化文化的严重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的危急关头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将之推向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无疑表征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经历一系列探索的失败后,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距不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从而,从对传统的批判与解构逐步走向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同样,新启蒙运动也正是以挽救民族破灭危机,唤起全民族的自我觉醒为源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文化救亡运动,某种程度上正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为中国文化的绵延与发展提供了内在驱动力,从而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这也成为理解新启蒙运动之于传统文化而言是内发性的重要依据。
其二,在新启蒙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化的理论自觉。正如不少论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内思想文化界面临“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由此引发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逐步分化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现代思潮,三方分歧主要在于文化取向之争,并在实践上各自给出了自己的药方。自由主义代表胡适主张渐进改良的实现方式,他针对北洋军阀混战提出的“好政府”主张和“联省自治”的政治方案,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失误在于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核心主体力量缺乏深入认识;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中国本位论”,以回归、捍卫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为首要职责和基本价值取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章士钊提出的“农国论”,梁漱溟所践行的乡村建设均属此列,但无一不遭到了现实的重创,可见,文化保守主义也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深入。作为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汇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理论修养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力主争夺文化领导权,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马克思主义主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科学指明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之路,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实践上的挫败足以说明其不能担当文化领导权的重任。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势必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普遍的文化启蒙,启迪大多数民众的智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在共产国际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目光逐渐由五四时期的“世界性”转向了“民族性”,对于文化民族性的突显,是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不同思想派别的基础,对于全面思考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说,新启蒙运动的开展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力量的壮大,以及文化危机带来的“民族意识”觉醒所产生的理论自觉,正如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艾思奇所说: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自觉运动”[8]298,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而言,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二
中国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及如何实现自身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至关重要。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大联合运动,文化主导权从一开始便是各派知识分子争夺的着力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陈伯达认为:“新哲学者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4]14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申府则认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与逻辑经验论的合流。”[3]345两者都宣称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创建一种新文化,并认为文化有精华和糟粕、内容和形式之分,新文化就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何干之主张“一方面保存着中国文化史上最精良的传统,一方面又接受西洋文化的最新成果……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9]138-140。张申府认为新文化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3]192。这种辩证性的认识态度贯穿新启蒙运动始终,无疑正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影响。
其一,新启蒙运动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体现在重新认识和定位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价值上。陈伯达指出:“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10]67吴承仕认为:“扬弃古代文化,即是忠实的接受和保持古代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即是忠实的扩大和培植固有文化。”[11]252-254张申府认为孔子儒学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他明确指出:“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3]239艾思奇提出“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在所不惜”[8]302。由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新启蒙运动者披上民族的外衣、打上中国的标签,就成了凝聚人心、抗敌救国的旗帜,新文化的发展也直接让位于民族利益。
在新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上,陈伯达从形式上力主“新酒装进旧瓶”,主张“文化的新内容与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10]51。他提出“我们有义务充当民族精粹的保护者”,恢复和展现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使“中国古代的‘圣经贤传’不为敌人利用为愚弄同胞的工具”,要将“服务支配者个人的奴隶道德,转变为及改造为服务民族、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为民族社会大众而牺牲的道德”[10]92。张申府则主要从内容上提出以中国既有文化为根基,促进中西文化综合交融的新文化建构设想,他认为:“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3]192他还试图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迎合西方文化,如他所言“礼者理也,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礼’不过是把情理加以条理,或说加以调理”[12]40。显然,这种简单的范畴比附概念和转换缺乏深入的思考,陷入了“传统化”的误区。可见,严峻的社会情势所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以及缺乏对中国现实环境以及新文化建设、发展问题的深入考察,使得新启蒙运动初期,无论是在形式或是在内容上,发起者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探索仅简单地依附于政治救亡的需要,所阐述的理论与见解并未超出旧文化旧传统的言说范畴。
其二,新启蒙运动对中外文化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规定和影响着新启蒙运动的内容和走向。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然伴随着与中国具体实际、传统文化的交融汇合。新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在民族意识高扬的洪流下得到了思想文化界的响应和推动,并从学术领域拓展为引领民众精神趋向的全国性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被正式提出,并迅速得到了思想文化界的认可和阐释。艾思奇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方法,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理论策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客观地运用于研究中国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指出“中国化”最主要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8]779。陈伯达强调“要创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就要善于了解、研究和综合中华民族各方面历史及所创造的文化事物,并加以新的改造和发挥”[13],并提出应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分析和整理中国古代哲学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
另一部分流落到中西部的新启蒙运动者也积极响应了“中国化”思潮,柳湜专门写了《论中国化》,提出中国化是贯通全学术领域的,是国内国际一切优良传统的交流,代表着“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为它的任务”。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有条件的(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会贯通”[14]854-855。张申府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化”的认同,他认为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3]304,并进一步阐释了其“三流合一”的文化构想,认为儒家的“仁”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法则,“中”是价值的标准,两者能够合流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一物两面,并指出“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15]471-472。
从以上分析可知,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对于中国新文化建构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批判继承五四运动到“辩证综合”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探索上,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新启蒙运动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是通过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文化主体性来实现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论产物与生发自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它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正是其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合流,并逐渐融为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同时,以成就“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为旨归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受到具有扩展与侵略本性的异质现代文化强烈冲击,以其内在生命力推动自身走向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特质满足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及对现代性的期许。一定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认同感,既反映了历史事实,又符合认识的逻辑必然。如果说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主要是由破到立,寻求重建,那么,新启蒙运动确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演进路径。
三
学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新启蒙运动在思想文化界的意义分歧较大。应当说,新启蒙运动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自身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着眼于新启蒙运动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历程的发展链条中的一部分,对其历史意义进行考察,那么,新启蒙运动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
其一,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精神挺立的加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质疑和批判,思想文化界对于挺立中国文化精神主体性缺乏重视。新启蒙运动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批判继承态度,重新阐述传统文化的合理价值,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陈唯实认为新启蒙运动目的不但在破,而且在立,“努力著作关于中国的文化”[16]41,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张申府认为“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固是今日中国所需要”[3]190。柳湜提出建立真正全民族的文化运动,应“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并“培养独立思想的精神”[9]721。何干之则对新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做了概括,他指出新启蒙运动是思想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理性运动,更是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可见,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焦点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国家意识逐步转向民族意识,正如许多论者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方向是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外在冲击下被动进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其内蕴的生命力使现代化逐步内化为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理想,实现了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转折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性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内化为自觉追寻的目标。当传统文化再次面临存亡危机之时,新启蒙运动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合理价值及意义的重新诠释与阐发,以及对建设中国新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民族”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内在主体性精神挺立的表现。在民族存亡之际而引发的民族意识,正是来源于传统文化注重传承的内在生命力所产生的驱动力,以及它自身稳固而独特的精神特质,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特质,使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得以延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开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
其二,新启蒙运动确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新启蒙运动作为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场文化运动,其基本的目标是建设中国新文化,并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做出颇有见地的探索。在文化立场上,新启蒙者认为新文化应培养民族精神和体现民族特色,在内容上必须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普及于大众。这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这种文化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民族性的强调顺应了抗战救亡背景下的民意诉求,科学性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大众化则从某种程度上蕴含民主性,这三个方面满足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新启蒙运动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开放的心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在文化层面上,是依据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辩证方法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并明确提出“中国化”是文化重建,是文化精神的重塑和文化结构的重构,这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要求。
新启蒙运动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证,使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路径得到了正式确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新启蒙运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腐朽落后的成分批判解构的同时,也使其合理价值得以重新确立,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第二,新启蒙运动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现了中国文化主体的转换。其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启蒙运动构建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主体文化,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文化开展的现代形态,促进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开展。第三,新启蒙运动参与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探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为原则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说,在新启蒙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奠定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主要是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新启蒙运动则正式确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实现路径。
立足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的探索接续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新启蒙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承继性。正如不少论者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其后的时代使命则是要“建设一个既具有现代性又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17],那么新启蒙运动参与者强烈的“民族”意识,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着力推崇,彰显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构起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可以说,新启蒙运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历程中的有机环节。
当然,新启蒙运动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特殊的历史时刻下发生的历史事件,自身难免存在历史局限性,在严峻的社会形势面前,爱国救亡和民族主义成为新启蒙运动与生俱来的两个符号,新启蒙思想家更多的是从政治救亡的需要上寻求运动发起和开展的历史合理性,铸成了新启蒙运动难以摆脱的政治包袱。同时,新启蒙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所开启的文化格局和路径,也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促成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建,文化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承续性,这正是新启蒙运动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意义所在。
[1] 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J].炎黄春秋,2003,(3):11-15.
[2] 庞 虎.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5):186-191.
[3]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4] 陈伯达.真理的追求[M].上海:新知书店,1937.
[5] 陈伯达.思想无罪[J].读书月报,第1卷第3号,1937.
[6] 张申府.所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7]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 何干之.何干之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10] 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M].上海:生活书店,1939.
[11] 吴承仕.吴承仕文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12] 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M].北京:生活书店,1939.
[13] 陈伯达.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J].解放,1938,(46):28.
[14] 柳 湜.柳湜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5] 张燕妮.张申府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16] 陈唯实.抗战与新启蒙运动[M].武汉:扬子江出版社,1938.
[17] 李翔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族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再探讨[J].教学与研究,2003,(10):30-36.
(责任编辑:蔡宇宏)
2014-11-26;收修日期:2015-01-3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4JD710019)
张江芬(1985-),女,湖北荆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G129
A
1003-0964(2015)03-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