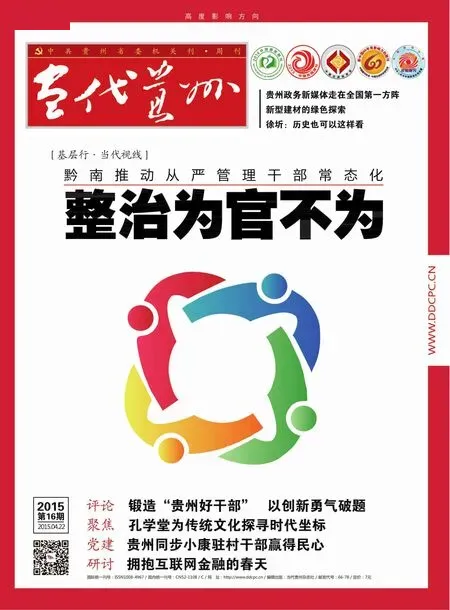传统士大夫人格典范:阳明之父王华(二)
2015-02-27张新民
在明代政治生态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王华、王阳明父子两人,始终能做到了从“道”而不从“势”。他们都视宦官干政为非法,痛恨权力世界的黑暗,体现了传统士人特有的风骨和气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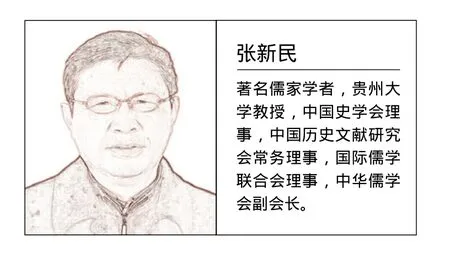
家庭教育从来都是人生成长的第一课堂。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从“修身”、“齐家”的私领域,逐渐走向“治国”、“平天下”的公领域,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成己”、“成人”、“成物”的人间社会建构事业。
阳明从小受父亲及祖父的培养教育,濡染儒家思想,不仅传承了孝友、廉洁、正直的家风,而且怀抱重建人间社会秩序的悲心大愿,反映家庭与社会双重影响对人格塑造的重要。上篇已提到父亲王华仕宦生涯对阳明人生作为的影响,这里不妨再补述三件大事,均直接关涉阳明的出处进退行为选择,或许也有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阳明的精神世界。
首先,正德元年(1506)武宗皇帝即位,时年不过十五岁,宦官刘瑾大权独揽,借机作威作福。阳明勇于站出来,为惨遭迫害的朝臣说话,数落其奸邪罪行,遂得罪刘瑾,无辜入狱。刘瑾既将阳明打入大牢,又迁怒于他的父亲王华,只是因为刘瑾未发家时,曾从王华同乡方正学习过书史,早就听说他处家孝友忠信的不少故事,心中尚存一丝敬意,而王华却根本不知道有此一层关系。故刘瑾知道王华乃阳明之父后,便暗中派人拉拢王华:一方面以丞相的高位引诱他,一方面又要他亲自上门为儿子谢罪。但王华却坚决拒绝见面,他根本不在乎官场升迁,自然不会为儿子求情,惹得刘瑾大为恼火。其实早在阳明下狱之前,不少胆小官员震慑于刘瑾呼吸之间,即可让人成祸成福的压力,奔走其门者有如集市,但王华却从不理睬,视之有若无物。以后类似的情况屡有发生,王华均采取不交往、不合作的态度,激怒刘瑾远非一次两次,只是因为王华无任何可加之罪,刘瑾只好强忍住性子,最后千方百计,终于找到一件与王华无关的礼部旧事,才传旨令他致仕。王华闻命后高兴不已,当天就急忙束装南归,并不无感叹地说:“从此可以免祸了。”据阮葵生《茶余客话》,王华致仕闲居家乡后,晚年曾大书堂联一幅:“看儿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黄绾说他“在朝则引身以求退,在野则忘之而无辩”。反映王华、阳明父子两人,在当时政治生态极端恶劣的情况下,都能做到从“道”而不从“势”,都视宦官干政为非法,且极为痛恨权力世界的黑暗,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强项令”,体现了传统士人的风骨气节。
其次,阳明惨遭刘瑾下狱贬谪后不久,有人以“同年友”事向朝廷诬毁王华,不少人都劝他主动向朝廷辩明清白。他笑着回答:“那人的确是我的同年友,我若替自己辩白,就是攻讦朋友的阴私,不是更有损于人品节操吗?”因而始终不为自己的委屈置一词。后来,阳明复官京师,听见士夫议论纷纷,遂具本向朝廷奏辨。王华知道后,立即驰书制止说:“你以为这是我平生的大耻吗?我从来没有什么可耻的事,现在无故揭发他人的阴私,反而为我添加了耻辱。大家都说你的才智远超过我,现在我是真不敢相信了。”可见虽为父子,亦以道义黾勉,决不为个人的清白,做出损害别人利益的事。他们父子二人,从此都再不为这事发一言。时人称王华“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孥,曾无两语。人有片善,称之不容口;有急难来控者,恻然若身陷于沟井,忘己拯救之,虽以此招谤取嫌,亦不恤;然于人有过恶,亦直言规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这一性格特征在阳明身上也有反映,当然也会影响到他在政治活动中的行事风格。
第三,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乃是有明一代的国家大事,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表面看事起偶然,其实就阳明而言,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原因是王华深知朱宸濠的为人,早就怀疑他会作乱,曾私下对周围的亲人说:“将来天下发生祸乱 ,必从这人开始。”这一预见必然对阳明有所影响,遂能在惊愕仓卒之间,从容应对,克敌制胜。而无论战事爆发时传闻阳明已死,或捷报传来大家共贺,乃至有功者反遭嫉恨迫害,一时谣言纷纷四起,甚至灭族之祸亦有可能从天而降,时致仕闲居绍兴的王华,闻讯后都始终淡定自若,坚信阳明的行为完全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最后则不仅家族免于无辜屠戮,即父子亦能相见畅饮尽欢,可说是家、国、天下的命运已完全合为一体,阳明最终仍以自己的人品清操及赫赫战功,让老人问心无愧地撒手人寰。而他们父子两人的人品清操,亦长久地传为历史佳话,不仅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且足以激励来者继续奋起。
(责任编辑/王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