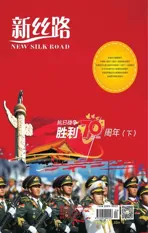探索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思想
2015-02-25孙海波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孙海波(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探索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思想
孙海波(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现代主义思想使穆旦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中的奇异风景。诗歌评论界和文学史界对穆旦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足以和郭沫若、徐志摩、艾青等齐名的一流的诗人。古典诗歌表现温情脉脉的美好理想,穆旦诗歌穿透美丽温情的表象,向人们展示世界赤裸残酷的真实本质。古典诗歌中诗人是群体的代表,传达普遍的愿望和理想;穆旦诗歌则强烈突出了个体内心体验,并揭示人们注定要不断痛苦挣扎的命运。
穆旦;现代主义;自我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穆旦的诗歌却与传统泾渭分明。传统文学追求意境创造,追求天人合一,穆旦却背弃了传统,走出人类的伊甸园,揭开世界的“摩耶之幕”。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孤独的主体,像西西弗斯一样顽强而又徒劳地对抗一切,感受心灵上的颤抖战栗,痛苦哀伤。他以孤独痛苦的自我个体对抗一切,完成不可能完成的自我救赎的任务。
穆旦的诗歌创作开始于30年代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高中之时,少年的他在那时已流露出早熟与早慧的特点,在诗中表达了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对人生哲理、宇宙奥秘的探求。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随校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开始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诗歌才华。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主义思想,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他结合自己的现实体验,写出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诗歌,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激荡人心的精神世界。下面,笔者从传统世界的失落、个体内心体验的凸显、痛苦挣扎的人生命运等几个方面分析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思想。
一、传统世界的失落
穆旦诗歌给人最显著的刺激就是他展现了一个与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他的眼光像锋利无比的剃刀,扫除一切浮华,穿透温润的肌肤,深入骨髓,道出其中的秘密。他把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矛盾、危险、残酷但又无比真实的世界中。赤裸裸的真实那么刺眼,让人心惊胆寒,激发起读者生死存亡的本能欲望。他的诗歌中没有传统意境的宁静和谐可以使人在其中安歇,找到精神的归宿;没有美丽的景物、优美的旋律、温馨的情感。有的只是直面人生的冷漠、孤独、无奈和痛苦。
在《蛇的诱惑》小序中作者说:“创世以后人住在伊甸乐园里……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来。”这是《圣经》中的古老传说,然而作者“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这条蛇诱惑我们,有些人就要被放逐到这贫苦的土地以外了”。上帝曾给人伊甸乐园,但人偷吃禁果有了知识,被逐出乐园来到属于自己的大地上;而现在作者却要更加深入认识自己,走出这贫苦的大地,失去任何依托,要孤独地自己生存了。“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命的命题……”在新的世界中人们将无处可逃!蛇的第一次诱惑使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但还有安身立命的土地;蛇的第二次诱惑使人类又被逐出贫苦的土地,无立身之所。蛇的第一次出现是人类的自我觉醒,从虚幻的伊甸园来到现实生存的土地上;蛇的第二次出现是诗人个体的觉醒,摆脱贫苦的土地,来到现代主义的世界中,面对“阴暗的生命的命题”。
没有了上帝,没有了乐园,甚至没有立足的大地,世界将会怎样?穆旦摆脱现实的迷惑,不再心存幻想,不再赞美爱情、讴歌生命,摒弃了温情、浪漫、理想。他看透世界、人生以及生命,深刻体验荒诞、悲剧、残忍的本质,并讲出这些真理,呈现出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诗人在社会纷繁的现实表象后发现了阴谋与混乱,但他冷酷的洞察力并没有停留在对“现时”社会的抨击、批判上,而是进一步指向对人类历史终极真相的追问,诗人的身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搏求者,也是一个广阔人生的探险者。现代主义的世界便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古典主义的世界截然不同。在一般人的思想中,生命、春天、爱情、人生总是美好、幸福的,人们满怀热情、勤奋劳作就能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在穆旦看来却恰恰相反。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人们歌颂春天,陶醉在缤纷的色彩和馥郁的芬芳之中,可穆旦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本质。他在1942年的《春》中写道:“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诗人在花团锦簇后面发现了生命的本质:欲望。这正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所强调的:“世界和人自己一样,彻头彻尾是意志,又彻头彻尾是表象。此外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诗人振聋发聩的语言揭示触目惊心的本质,让读者看清生命的痛苦和挣扎,来到欲望的无底深渊之前,战战兢兢,无限惊异、眩晕和恐惧。
爱情是诗歌的永恒主题,给人无尽的美好幻想,是苦难人生的慰藉。穆旦的诗歌中也有燃烧的爱情,但没有缠绵和倾诉,没有希望和白日梦的幻想。在1942年《诗八章》中穆旦说:“那燃烧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燃烧是什么?在许多诗人的篇章中,爱情的火焰常放射出最美的光芒,璀璨夺目,给人永恒和神圣的意味。但穆旦认为“那燃烧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不过是生命发育成熟后的欲望要求,诗人说:“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爱情不过是偶然的游戏,人不过是上帝玩弄在手里的玩偶,没有一点自由,更谈不上什么永恒和神圣。没有什么“心有灵犀”,人和人之间“永远相隔如重山”。
二、个体内心体验的凸显
世界和人生是虚幻、荒诞的,是充满痛苦的悲剧,那么人能够在哪里生存?抛弃这样的世界和人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孤独的自我。现代主义诗人将探究的目光转向自我、转向内心深处。现实的世界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必须要在内心中寻找真实,寻找生存的依托,哪怕是用痛苦来对抗虚无。“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
穆旦诗中的思想含量很大,很多诗句甚至类似于抽象的思辨,但这样的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不安,其原因在于诗人常常将心灵的活动转化成身体的感受,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穆旦于1940年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我》:“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永远是自己,锁在更深的绝望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诞生就是一个荒诞的悲剧,被抛到荒野上,一个绝望的世界上。孤独、残缺、荒诞、绝望,这是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情感。自我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是生存的根基,除此之外则是虚无。所以,怎能不探索自我来寻找真实的意义?
在1976年创作的《听说我老了》这首诗中,诗人这样写道:“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但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只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穆旦珍爱“赤裸的我”,在“深心的旷野中”,“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诗人一生都在探索自我内心世界,从自身来观照人,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病去世。他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者,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他远远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那些意气风发的壮志豪情,或幸福快乐的颂歌赞曲,在这样的诗句前显得何等浅薄、苍白、愚昧和虚伪。
穆旦对诗歌中语词的选择,诗行的展开模式中也处处渗透着“张力”意识。阅读他的诗作,读者会发现他十分偏爱从对立、矛盾的地方着笔,通过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较量,形成诗歌曲折深入的表现力。譬如:“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三十诞辰有感》)
个人感受的凸显是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穆旦的诗歌中有对个体生存的虚无、荒诞之感的直接阐述。在早期诗歌中,穆旦就认为人们正在遭遇一个新的时代,必要经历一番风雨、水火的洗礼。他在1939年的《从空虚到充实》中写道:“我知道/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因为我听到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死亡的洪水吞噬了古旧的世界,现在到处充满了死亡,人要永远面对着死亡,这是人的宿命,不管愿意不愿意。
如果说知性与感性的结合,是现代诗学的一个理想,那么“用身体来思想”则是其具体的方案,穆旦的写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验证了诗歌想象力对现实、观念、感觉的重新组织能力。“真理和牺牲”不再神圣、崇高伟大,而且因为虚伪、狂妄和欺骗,所以让人更深地低下“忏悔”的头。那么人应当怎么做呢?穆旦于1947年创作了《我歌颂肉体》,这让人不禁想起美国著名民主诗人惠特曼的一首诗《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他“歌唱带电的肉体”,因为“这些不仅是肉体的构成和诗篇,也是灵魂的构成和诗篇”。惠特曼的诗歌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信心和力量,要拥抱、享受和创造世界。然而穆旦诗歌中的肉体却与黑暗、彷徨联系在一起,甚至让人哀怜:诗人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找到了依托。穆旦写道:“我歌唱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肉体是“被压迫的,和被蹂躏的”,但唯有肉体是“肯定的岛屿”,是生存的基石,“因为光明要从黑暗里出来:/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丽的真实,我的肉体。”而“思想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在这个世界上,人如何拯救自己?思想其实不可靠,或许肉体能告诉我们自己的存在,肉体承受着黑暗、压迫和蹂躏。
三、痛苦挣扎的人生命运
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难开掘,使穆旦诗中的“自我”形象地呈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人生不过是一个无奈的过程,而且永不得安歇。上帝死了,人独自支撑这个世界,尽管那么脆弱无力,孤独无援。在1941年的《潮汐》中,诗人极大地突出自我,自我成为主宰,成为神,而这个神是异教的神,与希望、梦想、安宁和幸福背道而驰:“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不能够挣脱,爱情将变成仇恨,/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颠覆了一切,但要以血肉之躯,泥土一样的身躯,承担这坍塌了的世界。这“异教的神”即是现代主义的“自我”。
自我的分裂残缺不只是诗人主观的心理感受,它更是不断的自我剖析、自我质问。《蛇的诱惑》以“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之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一宗教故事为象征性背景,描述了一个青年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外部环境描写与内心独白的交替闪现让人联想起艾略特的名诗《普罗甫洛克情歌》。
穆旦以自我扛起所有的一切,扛起整个世界:“他树起了异教的神”!
宗教中的“神”给人信仰,当一切是虚幻的假象、是痛苦和失败时,唯有信仰能给人勇气和力量,给人继续生存的理由。“他树起了异教的神”,穆旦信仰的对象不是崇高伟大的上帝,而是一个真实、弱小但要求生存的自我。所以更需要信仰!信仰自我!以自我来支撑生存的世界,哪怕是无限的痛苦和悲哀。
现代主义诗人始终探索自我,咀嚼自己的痛苦。在1976年的《智慧之歌》中,诗人写道:“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诗人自己支撑着世界,自己又能怎样?1976年的《自己》是对诗人一生的回顾和总结,但每小节的结束,诗人都在做这样的表白:“不知那是否确是自己。”现代主义者永远在寻找自己,却又永远找不到自己,饱尝无尽的痛苦,却绝不欺骗自己。
对于自己诗歌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穆旦有清醒自觉的认识。在1940年的《玫瑰之歌》中,他用三个小标题大致描绘了自己的思想历程:“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里”、“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吗?”他探寻新的生命,走进一个充满困惑和痛苦但真实的现代主义世界。在《玫瑰之歌》中他说:“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中死去。”他用最深刻的思想展现新的世界,用最强烈的情感激荡、震撼古老的心灵,用最坚硬沉重的语言建造了纪念碑,指引人们走向新生:“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
这就是穆旦的诗歌,“他树起了异教的神”!王佐良称赞穆旦的诗歌创作是“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穆旦的诗歌确实是高耸、险峻的山峰。这山峰白雪皑皑,寒气逼人,重云积聚,爆发刺眼的闪电和震耳的雷鸣!这山峰是让人惊异的景象,象征着激荡、悸动和战栗的现代主义思想。
[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3.
[2]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M].郑羽,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58.
[3]丹尼尔·贝尔.文化:现代与后现代[M]//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4]穆旦.蛇的诱惑[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