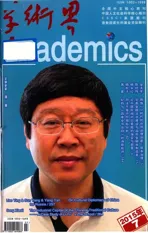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2015-02-25郭奇林
○郭奇林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使命,古语为“使者所奉之命”〔1〕,今天说“使命意识”强调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历史上,“使命意识”的主体往往烙有精英和男性的印记。打破这种性别领地只是近代的事情。辛亥革命时,为响应民权思想的号召,妇女作为群体逐渐萌发了自己的使命意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妇女界对社会和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刻,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亦超出性别解放,开始融入社会革命的视野。但1930年代日本侵华打破了这一进程,民族矛盾超越性别解放和社会革命而为第一位矛盾。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中国妇女使命第一次将人身解放与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并形成了一个“自身解放”与“时代需求”相结合的主从复合体,主体是妇女人格、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利的解放,客体是社会背景提供的实践选项与实现途径,而参与客体社会运动则成为妇女实现主体解放的必要行动。
目前看,抗战初期国统区舆论界广为讨论和宣传的妇女使命问题还没有专文论及,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妇女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对妇女使命的关注可以展示抗战特殊历史时期妇女动员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这一动员中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本文以1937—1939年间《东方杂志》妇女专栏的文本为中心,重点考察其如何将妇女使命与抗战结合起来,又是如何处理和回应妇女人身解放这一主题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效果如何?从中给出合乎事实的解答。
一、抗战初期《东方杂志》对妇女使命的讨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与“抗敌参战”成为时代的主题。妇女运动在战时非常环境中出现了新的高潮。报刊媒体刊登的文章,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女性参加抗战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指导作用。妇女使命的讨论在这一宣传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全民抗战”的呼声中,妇女使命讨论的主旨主要是“救国”和“参战”。为此,《东方杂志》大致从三个层面作了历史的、逻辑的阐明。
(一)战争与妇女使命
战争中妇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她们可能会失去丈夫、儿子和其他亲人,自身也要面临不可知的侵害。因此,妇女对战争有天然的抵触。对于几千年都被排斥于社会和政治之外的中国妇女来说,她们不能制止战争,只能憎恶和逃避。要想发动妇女,就必须改变大多数妇女对战争不加分别的认识和态度。《东方杂志》的态度是:“尽管战争是残酷的,特别是妇女都诅咒战争,但从社会历史的观点看,战争却是解决历史大问题的一种必须手段”。陈碧云在“卢沟桥事变”后所写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一文是代表。该文通过伦理分析指出,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正义的战争能够帮助民众获得解放,推动历史向前进步,所以对战争的态度不单从形式上,更要从内容上去考察。从这个观点出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进步的,并且是革命的,是中国人民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不光是民族解放的必要过程,也是全国妇女赢得自身解放的最好契机,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中,因为有许多妇女积极地参加,所以妇女在好些州中取得了部分的参政权和遗产继承权。”同样,如果这次战争获得胜利,“不但可以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脱离其他帝国主义的束缚,使中华民族得以逐渐走上真正民族复兴的大道。”〔2〕
(二)抗战与妇女使命
《东方杂志》较早意识到妇女参加抗战的意义,并注意首先唤起广大妇女的责任意识。如卢沟桥事变前即富有预见性地指出:中日战争不仅难以避免,随着德日、意日反共协定的签署,势必加速日本远东的侵略行动,这种“事实已不容我们有丝毫的瞻顾和彷徨了!”面对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着重从女性视角讨论了“得过且过”态度的危害,尤其是许多妇女在敌寇日深时依然过着“封建时代的违反现时潮流的死生活”〔3〕,疾呼全国妇女要从旧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国家为民族的自由而战。其后《东方杂志》连续在多篇文章中发出同样的呼吁,试图从舆论上唤起妇女投身抗战事业。
为了唤起妇女的抗战意识,《东方杂志》多把战场见闻实情拿来做宣传的素材。如陈碧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写下《日军侵略下上海妇孺所遭受的劫难》一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上海的恶行。1938年11月12日上海被占领,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浩劫是难以计算的,仅当时中华慈幼协会统计,“三十余万难民之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儿童,其余二十余万人中有一大半是妇女。”进入调查范围的三万六千余死者中儿童和妇女约占三万,妇女和儿童占难民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又转引《大美晚报晨刊》的记载,上海南市普育堂收容了一百多个因日军进攻而失去父母的难婴,在日军的封锁下牛奶断绝自来水也没有,孩子都先后饿死。这些真实的见闻是动员妇女最有力的武器。
此外,还特别强调抗战的持久性与妇女参战的关系。在南京失陷前,陈碧云就谈到了长期抗战和妇女应承担的使命:“我们如果要想长期抵抗拥有优势军备的敌人,就非迅速把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而“下层的贫苦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她们的体力差不多和男子一样,其耐劳忍苦的精神并且有超过男子”,“如果想同日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抗战,我们必须将年青而身体壮健的妇女武装起来”。〔4〕
(三)妇女自身解放与抗战使命
妇女参战意义重大。但中国妇女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她们深受双重压迫,即帝国主义侵略的摧残和国内封建残余的束缚。要想妇女们自愿地加入抗战队伍,人身解放问题无法回避。《东方杂志》首先回答了这个迫切的问题:妇女为什么同男子一样要承担抗战的使命?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必须从民族解放中求出路”,抗战于妇女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常是籍着被压迫民族内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一切陈腐的宗法的道德习惯来镇压束缚一般人民大众。”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就采取这样的方法,在满洲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代表腐旧势力的傅仪作傀儡来统治满洲的人民。在这种情形下“妇女的地位更见低落”〔5〕。
那么如何去解放妇女,使她们不受羁绊地参战?这一问题具有双向性,即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伴生着妇女的真正解放,权益的最终实现;妇女的觉醒和人身的解放亦是妇女参战的一个必要前提。但前者是愿景,还无法兑现,后者才是关键。正如王孝英指出,“我们要挽救国家的危亡,然而这决不是脑筋里充满了封建思想,手脚戴上了桎梏,身上紧缚着层层叠叠背乎人伦的锁链的妇女所能做得到的!”“假若妇女不从固有的一切束缚下解放出来,又哪里有时间有勇气有条件和男同胞一致对外?”〔6〕陈碧云从政治上给出的解答是:要解决妇女的动员问题,必须“使妇女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取得政治上的一切自由,直接参与政权。”“只有如此,妇女才能从多重的压迫和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发挥她们伟大的力量。”〔7〕同时,立即开放民众运动,不分男女老幼阶级群体都有机会来参加这次民族解放的斗争,战胜敌人才会有希望。李纯青注意到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如宗法制度的危害,妇女经济上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希望妇女参政员要发挥喉舌作用,“借政府的力量加以改善”。〔8〕姚贤慧认为,动员妇女要从大多数妇女的幸福上着想,“妇女只有求得经济之独立才能与她们的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她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乃是由事业上得来”。并倡言效法英法美等国广泛开设托儿所,解除妇女们的后顾之忧,让那些“有着服务社会热忱”〔9〕的妇女有机会加入抗战的队伍。
随着战争的进程,《东方杂志》的宣传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由“参战”和“支前”逐渐转向“生产”与“护养”,有一个从“前方”向“后方”的转变,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如何设立战时保育院、进行战时儿童抢救和教育、战时妇女生产支前等问题。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客观上战场的变化对妇女动员工作的影响。1939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战场相对缓和,面对日本的封锁和轰炸,后方生产保育工作需要更多的投入。二是女性动员事实上受到诸多制约。抗战宣传的受众首先是知识女性,她们多集中在后方城市,是舆论宣传的执行者,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往往需要吃苦耐劳和持续性,这方面的人手和人员历练不足使动员工作常常虎头蛇尾。〔10〕三是国民政府地方保甲制度长期不得人心,尤其在乡村难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果靠政府以政治力量去动员保甲长来发动农民的话,结果徒然增加他们对于政府的反感,这种例子,见于各省民众运动中太多。”〔11〕陈碧云在总结抗战十八个月来妇运工作中写道:“我们妇女组织在抗战一年多不但没有发展起来似乎反而缩小了,这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坏现象”。〔12〕显然,国统区后方在宣传和发动妇女工作上遇到了一定的挫折。从《东方杂志》对战时中国妇女使命讨论的这种“前”“后”变化看出,随着战争的磨砺,妇女参战的宣传动员遇到了诸多问题,不得不进行反思,且由最初的理想和激进开始向理性和现实回归,这时妇女的使命宣传亦更多地注重性别分工和女子特殊的作用。
二、妇女参加抗战的实践及效果
抗战一年多妇女参战动员成效如何,当时还没有很好的统计,从《东方杂志》相关文章的评价来看,江西妇女工作是一个典范。从安义县的实例大致可了解下后方妇女动员工作的开展情况。
该地区妇女干部多是东北和平津逃亡来的大中学生,由她们对农村妇女进行集中训练。具体分三步。先是对县里较优秀分子作短期培训,然后由这部分干部对各乡抽选出来的妇女进行普遍训练,以保为单位,每甲选出一名妇女受训,这名妇女在培训结束后就是妇女组长,妇女组长再联络本甲妇女进行最基层的动员工作。第二步是普训工作,普训时间为一周。先是清洁工作,替妇女们剪去污秽的发,督促她们放足、洗澡,然后精神谈话解释受训意义。第二天正式训练,包括:早上三十分钟秩序操练、十五分钟时事报告、精神讲话、公民训练(对中国的认识、敌人的认识)、识字、军事常识(自卫的能力与组织)、破获汉奸、军民合作、如何认识敌人、个人卫生、救护训练(止血法、消毒法、骨折急救法)、防空防毒的基本要领和演习。此外还有唱歌,讲诉民族英雄故事,小组谈话等内容。以上是一天的课程。对妇女队长的普训结束后,下一步进行具体的分工,以乡大队为单位下分各职能股,由乡妇女队长负责推动。〔13〕
由于得到江西省当局的扶持,各县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除上文的安义县,贵溪、星子、弋阳等十几个县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其中星子县“一个星期内集合了四千多个妇女来受训”。这种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工作反映了抗战背景下动员妇女参战的紧迫需求。但工作尚未完全展开,而环境已发生变化,由于日寇迫近,宣传和发动工作不得不暂告结束。从安义县的工作可以看出,抗战宣传动员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需要青年知识妇女的热情投入;国民政府的支持有利于组织工作的开展;农村妇女抗战动员工作亟待开展;妇女工作实践比预想的要难得多。江西妇女工作成为模范,反映了积极的一面,但并不能够说明整个国统区后方妇女动员工作的实际情况。白霜在《怎样开展华南各省的妇女工作》一文中指出,尽管“各地纷纷组织妇女团体,……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但“仔细考察一下,妇女动员的数量还是微乎其微”“女工和农妇没有切实地组织起来,没有发挥她们本身的力量”。〔14〕陈碧云亦指出,抗战一年多来,“有不少妇女是比从前更觉悟更活动起来参加某些工作了,但始终只是少数而已”,妇女动员工作距离期望还很远。这些工作方向,“虽然未免老生常谈”,“可惜过去实行的尚少,如果认真实行起来,对抗战的帮助是有效的。”〔15〕信心似乎有所下降。
但如果放眼全国的话,妇女参加抗战的活力和效绩实在是近代以来空前的。如广西的女学生军全国闻名。她们过着士兵的生活,睡稻草,吃粗饭,在火线下参加救护工作,在很多战役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16〕1939年1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谈到广西的女学生军时说,她们“至今已毕业了两班,共一千余人。她们现在都分散在前线工作。她们的成绩很不错,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好几次我军迫于敌人猛烈的炮火想要退却,但女学生军们坚持要与阵地共存亡,男将士们受了她们的激励打了胜仗。”〔17〕又如晋察冀边区几次反扫荡中表现突出的妇女自卫队。该自卫队是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组织组建的妇女群众武装组织。自1937年冬创建,1939年得到普遍发展。她们或组成游击小组,扰乱敌人后方,或连夜将弹药送到四五十里外的前线,或直接参加攻打县城的工作。有的地方还将自卫队员编成“青年妇女班”“老年妇女班”“有孩子妇女班”“无孩子妇女班”“大足班”“小足班”等,她们站岗放哨,盘查路条、搜集传递情报、扒电线、毁公路等。〔18〕
此外,各地妇女主要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来支援抗战。如山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由于敌人的烧杀、强征苦役、抽夺壮丁,导致劳动力匮乏经济萧条。敌后抗战形势尤为艰难。战士们“在险峻崎岖、荆棘丛生的山道上行军”,“没有鞋子赤着脚”,“十冬腊月遍地覆盖着冰雪,有些部队还穿着破旧的单衣”。〔19〕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巩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敌后广泛发动妇女运动,成立了妇救会,鼓励妇女参加各种生产,积极拥军参战。由于男劳力严重不足,各家就自行组织互助组。一位抗日家属多年后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为了掩护八路军和干部们利用青纱帐活动,我家里带头种高杆作物,高粱呀、玉米呀、麻籽,这都是高杆作物。这秸秆哩到收的时候光把穗收了,秸秆冬天才收回来,以延长八路军在野外隐蔽打游击的时间”。〔20〕
这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开始在以妇女生产为主力的敌后乡村踊跃地开展起来,一大批妇女干部脱颖而出,妇女们的积极参与巩固并扩大了农村社会基础,为打破敌人封锁,支援长期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由于侵华战争的破坏,仍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被迫迁徙或流浪于国统区后方。国民政府在“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下,对部分难民妇女进行了救助,从中吸收了部分青年和有知识的妇女从事生产、救助及辅助工作。如“为士兵缝制棉衣”,“制作被服”,或从事“救护难童”,辅助开展“扫除文盲”等各种活动。〔21〕1938年8月,在抗战经济最危急的时期,由路易·艾黎(新西兰)、埃德加·斯诺(美)和卢广绩等人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开始在西北地区展开,并逐渐推向东南和西南地区的18个省。“工合”为安置难民妇女同时发挥她们的生产能力做出了不小的业绩。1940年的时候,工合织物合作社已获得了国民政府一百五十万条羊毛毯子的军队订货,而从事这一生产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妇女。斯诺在谈到成都及近郊各村的生产状况时写道,“当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有大约五千个妇女和姑娘在纺羊毛,而当地工合的职工每天已出产一千二百条毯子了。”〔22〕
妇女参加抗战的效绩还体现在妇女社会地位和参与社会事务能力的提高。如国民参政会议中有十五名女性代表,算是妇女参政的一个进步,但在总数二百四十人的比例中显得太小了。敌后根据地则良好地执行了“妇女平等”和“民主选举”的政策。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中提出,“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在《选举条例》中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周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第二次参议会选举中,有17名妇女当选为边区一级参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一级参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边区乡一级参议员。1940年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时,共有1926位妇女当选为村长、乡长、区长,有5052名妇女当选为村代表。这些妇女成为当地群众和妇女团体的中坚力量,在她们的带领下,生产、支前、警戒、救护等项工作均得以有效进行。
为了提高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支援抗战事业,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扫盲和教育活动。如国统区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下开展了乡村服务工作,她们训练了一批妇女和青年女子学员深入农村,负起唤醒、教育、组织及指导民众的使命,至1945年,开展了两湖14县及四川省56县的乡村工作。〔23〕抗日根据地则积极培养妇女技术人才,并普及和提高她们的公民意识及文化素养。如各级妇联利用闲暇时间开办夜校、识字组、冬学等社会教育形式。通过学习,边区文盲妇女一般能认300到400个字,能读普通报纸、信件,成绩突出的还被送进女大、延大等校深造。如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到1941年时已培养了100多名女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还成了由650余名女学员组成的女生队,整个抗战时期抗大培养了2000多名女学员。此外,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师范学院等都招收女学员学习。〔24〕这些女学员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她们“从占领区日本防线后面几百英里外跟着危险的游击队来”,甚至还有“几个美国女郎”,她们“跋涉五百英里去进一个窑洞的大学”,“在那里还得种植自己的菜蔬”。初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对此曾颇感惊讶,但当他看到“那精神比美国大部的女子学校好得多了”的时候,明白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镇何以“成了全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25〕
可以说,抗日战争推进了妇女运动,在全民抗战和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妇女动员参战、支前和生产建设工作均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开展,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三、中国妇女使命讨论中的苏俄因素
在宣传中国妇女抗战使命的同时,《东方杂志》对苏俄妇女的参战行为大加赞许,对其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显然是将苏俄妇女作为中国妇女参照和学习的榜样,将苏俄妇女的解放视为中国妇女在抗战胜利后的美好愿景。
(一)苏俄妇女与卫国战争
陈碧云在《苏联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一文中盛赞了苏俄妇女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她们在全力维持后方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同时,还直接参加了前方的抗战。如1919年著名的顿巴斯和罗干斯克战役,同年秋的彼得堡之役,妇女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在前沿阵地上的表现让那些怯懦的男兵大受激励,“深深地感到羞耻,重新回到前线拼死抵抗去了。”〔26〕作者期望中国妇女发挥同样的作用。
(二)苏俄的胜利与妇女解放
黄雨青在《深堪羡慕的苏联妇女生活》中,用一系列数字描述了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妇女赢得的人身解放。如:职业妇女人数达850万;1936年专科在校女生人数比1928年提高了近4倍,大学女生人数由1928年的48 000人增至1936年的198 500人。政治上尤其值得称道,1934年在农村苏维埃中妇女占1/4名额,而在城市这一比例是1/3,全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代表中妇女有184人,这和1938年国民政府第一届参政会议上只有10名妇女代表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最能体现妇女权益的是对怀孕妇女的一系列关怀,如:怀孕妇女可获得免费医药优待;孕期中不得安排夜工和繁重工作;婴儿出生后妇女如果要工作可以把孩子放在国家办的托儿所,而这些妇女妈妈在工作之余“并未失去其优美的女性”〔27〕。
(三)苏联妇女的解放与中国妇女的解放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将苏俄1918—1921年的卫国战争比作现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的苏俄不仅要抵御内部敌人的破坏和进攻,还要面对英法德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反共”名义下从外部进行的围攻,形势可谓“间不容发”。这和中国内有伪满汉奸组织,外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情形何其相似。苏俄在经济上实行战时的共产主义政策,政治上则全民皆兵,动员全国的人力参战,尤其是广大妇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承担了全部的后勤保障和生产任务,还直接参加了历次战役。因此,苏俄卫国战争的经验恰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镜鉴,苏俄妇女奋勇参战的事迹同样可作为中国广大妇女参加抗战的榜样。
作者的分析并未结束。俄国妇女向来被称之为欧洲最落后的一群,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突然变成欧洲最先进的一群呢?特别是那些落后的农妇大众,何以能很快达到这样觉醒的程度?原因不单纯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鼓励,“而是由于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在生活上给予妇女们之实际利益和实际训练所养成的”〔28〕。根据乔治·鲁德的研究,下层妇女更多是在反饥饿斗争中本能地行动起来,在事关生存危机的问题上参与大革命,但她们的行动也并不表明她们一定是支持革命的,她们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摆脱饥饿。〔29〕也就是说任何伟大进步的历史运动,必须要从人们的实际出发,对于他们或她们的切身利益要有密切的联系,然后才能使之自愿地积极地起来参加。对于中国的抗战,要让民众和广大妇女积极地起来反抗敌人,还必须把他们切身的利益与之联系起来,如一般的民主自由权,制止贪污、土豪劣绅、高利贷者及投机商人的压迫和剥削,救济难民灾民等。让她们感到“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四、结 语
《东方杂志》对妇女使命的关注,是时代的催生,也是妇女自身解放需求的一种反映。妇女占人口的一半,但受封建和传统压制一直游走于社会边缘,日本侵华唤醒了中国民众,妇女群体于是萌发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不曾有过的斗志。但她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不熟,急需教育和引导。在这种背景下,智识妇女承担了抗战宣传和教育的重任,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妇女抗战的动员中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妇女运动的“范围比战前普遍和深入”,“动员对象已由城市智识妇女和青年女工转向到大家闺秀和乡村妇女”〔30〕。不可否认,仅从国统区看,这种动员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东方杂志》认识到妇女参战对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进行了积极地宣传和指导,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妇女参战工作受到了实际困难的影响。这种困难,一方面来自战场的变化,沦陷区工作开展艰难;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抗战政策的一手控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上海抗战时期中,有许多妇女都非常积极的要求做抗战工作她们甚至捆好了铺盖,……但是都因为抗战工作统制太严她们找不到工作做,有的也甚至因此悲观消极。”〔31〕对抗战民运的限制使很多妇女投报无门,也直接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和热情,如上文提到的被誉为全国妇女工作典范的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妇女动员工作“四年来已扩展至四十四县,训练妇女队员凡五十万”,但在国民党的干涉下于1942年10月省县妇女指导处全部裁撤,交由国民党社会部接收〔32〕。此外,对妇女用工在事实上的种种职业限制,也使得妇女动员实际效果与宣传的正态效应大打折扣。〔33〕
作为一份民营报刊,《东方杂志》深处后方本身受到当局新闻言论的限制,这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看向全国的积极视野,尤其是北方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出现的新气象与新成就,因而也无法提出更多现实的指导建议。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成就,给了媒体拿来参照中国抗战的精神借鉴:希望中国妇女像苏联妇女那样积极参战,希望中国的胜利也带来苏联妇女那样的解放。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正如陈碧云认识到的,苏联妇女的参战首先是苏维埃政府对妇女切身利益的保护,而没有制度和利益的保障只靠单纯的宣传是无法实现这种动员的。〔34〕《东方杂志》对战时国统区妇女使命的宣传,以及援引与中共妇女政策极为相似的苏俄模式作为实现妇女动员和解放的愿景,客观上也反映了国共双方在参战动员问题上的制度性差异,这种争取民众方式上的不同,使得双方最终赢得的结果大相径庭。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2〕〔4〕陈碧云:《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东方杂志》1937年第18-19期,第34卷18-19号。
〔3〕〔6〕王孝英:《非常时期妇女应负的使命》,《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第34卷1号。
〔5〕〔31〕莫湮:《妇女怎样认识抗战与怎样参加抗战》,《东方杂志》1938年第1期,第35卷1号。
〔7〕陈碧云:《妇女与民主政治》,《东方杂志》1937年第22-24期,第34卷22-24号。
〔8〕李纯青:《妇女参政员的责任》,《东方杂志》1938年第15期,第35卷15号。
〔9〕姚贤慧:《妇女职业与儿童幸福》,《东方杂志》1937年第13期,第34卷13号。
〔10〕〔12〕〔15〕陈碧云:《我国妇女今后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东方杂志》1939年第5期,第36卷5号。
〔11〕罗淑章:《怎样办妇女干部训练学校》,《东方杂志》1938年第3期,第35卷3号。
〔13〕池振超:《江西妇女工作的实况》,《东方杂志》1938年第17期,第35卷17号。
〔14〕白霜:《怎样开展华南各省的妇女工作》,《东方杂志》1938年第11期,第35卷11号。
〔16〕〔21〕〔30〕〔33〕李泽珍:《建国三十年与中国妇女运动》,《东方杂志》1941年第2期,第38卷2号。
〔17〕《申报》(香港),1939年1月31日。
〔18〕〔24〕张文灿:《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9-240、252页。
〔19〕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页。
〔20〕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06页。
〔22〕〔25〕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III),宋久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76、227-230 页。
〔23〕夏蓉:《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26〕〔28〕〔34〕陈碧云:《苏联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东方杂志》1938年第17期,第35卷17号。
〔27〕黄雨青:《深堪羡慕的苏联妇女生活》,《东方杂志》1938年第15期,第35卷15号。
〔29〕裔昭印等著:《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8-309页。
〔32〕《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处长杜隆元致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电》,会字第1302号,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1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