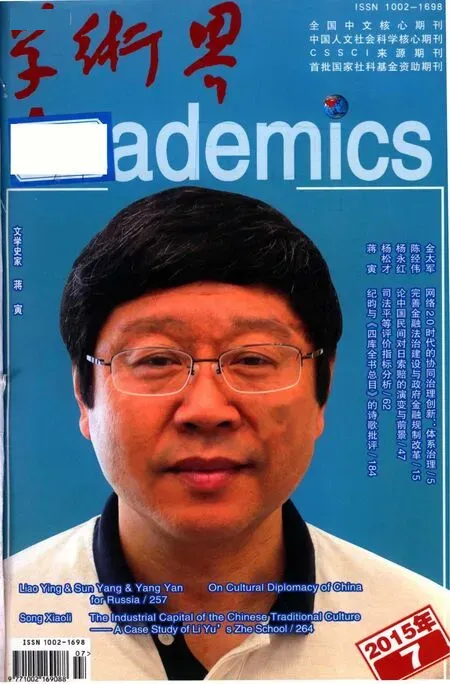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特征
2015-02-25应克荣
○应克荣
(淮南师范学院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在煌煌大唐的文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奇女子:她们饱读诗书,博通古今;她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她们能歌善舞,衣袂飘飘;她们与名士交结,比肩同行;她们与文人谈诗,不让须眉。她们是被遮蔽的女性历史的书写者,是大唐诗国里的幸运儿。她们的诗文创作,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绚丽的篇章。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她们的诗文创作,除了深切抒发女性的喜怒哀乐、表现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人生命运外,大量作品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到抒情方式等都表现出对男性作家的刻意模仿。在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女性社会地位相对提高、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历史环境中,这一“拟男化”文学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拟男化”现象的剖析,探索唐代妇女自我意识觉醒中复杂的心路历程,从而揭示女性解放历史长途中的“特定瞬间”。
一
与前后时代女性诗人相比,唐代女诗人不仅在女性很少涉及的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方面大显身手、独领风骚,而且在女性常写的闺怨、爱情及日常生活题材方面也呈现出男性化的倾向。在审美情趣上,唐代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骑射、胡服、袒胸露背、抛头露面,追求阳刚之气。在诗歌风格上,追求格调高远、意境雄浑的士大夫风范,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这一切,都使得唐代女性书写呈现“拟男化”的特征。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拟男化”现象成为唐代女性文学独特的时代风范。具体表现在:
(一)诗歌题材的男性化
一是战争题材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的影响,锁在深闺,见闻极少,生活范围局限在闺帷之内,眼光见识也往往局限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因而,女性书写的大都是一些伤春悲秋、风花雪月的题材,其内容绝大部分是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对自身命运的悲叹,很少涉足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但唐代相当多的女诗人却有意识地跨越了这种文学题材的性别鸿沟,闯入男性审美天地“叱咤风云”,写出大量不让须眉的边塞诗、政治诗。如鲍君徽《关山月》:“高高秋月明,北照辽阳城。塞迥光初满,风多晕更生。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霜凝匣中剑,风惫原上旌。早晚谒金阙,不闻刁斗声。”气势雄阔、铿锵豪迈,置于岑参、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中也不逊色。
又如薛涛一系列边塞诗所表现出的对国事的关心和政治上的识见,完全可以与“唐才子”们竞雄。其《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罚赴边上韦相公》《筹边楼》等不仅表现出诗人对边关士卒的同情、对战事的关注,更体现了诗人过人的远见卓识。《筹边楼》云:“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以过人的远见,站在边关战略高地吟唱出“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的雄放诗篇,以至于明代钟惺评价为:“教诫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1〕
二是政治题材的诗歌。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庙堂”为男性独霸,“女不言政”“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男性对女性的普遍要求,女性也以此自我定位,因而,女性一般自觉地远离政治舞台,也不关心政治。但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却不时出现女性的身影:长孙皇后、贤妃徐惠、武则天、太平公主、永泰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宋氏五女、薛涛、鱼玄机……在文学创作上,她们创作出指点江山、意气风华的政治诗篇,字里行间洋溢着“雄性”的豪迈。然而,也就是在这“雄性化”审美趣味中,女性特有的美学意蕴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了。武则天、徐惠、宋氏五女、薛涛都表现出这一特点。
武后诗文集,多至百余卷。《全唐诗》里保存她的诗歌47首,其中39首是“颂”诗。这些“颂”诗,堪称是武则天的“政治宣言”。这类诗最突出的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开创太平基业的信心与决心。如《唐明堂乐章·皇帝行》:“仰膺历数,俯顺讴歌。远安迩肃,俗阜时和。化光玉镜,讼息金科。方兴典礼,永戢干戈。”〔2〕
“颂”诗是古代祭祀时的郊庙歌辞,与男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宗庙祭祀作为古代五礼之首,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最高礼仪,也是国家层面的政治行为。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祭祀尤其是郊庙祭祀历来是男性的专属行为,武则天身为一代女皇,曾多次主持祭祀,留下了大量的“颂诗”。武则天的此类诗歌向世界表明:她不是普通的女性,而是指点江山的一代帝王。作为一位胸怀抱负、大有作为的女性政治家,只身闯入男性权力的最高端,亲身体验着男性政治生活。因而,其文学创作的“雄性化”审美趋向是外在生活强制的必然结果。这一层面是可以理解的。
上官婉儿、宋氏五女,作为宫中女官,创作了大量的应制诗。应制诗是封建时代臣僚奉皇帝所作、所和的诗。应制诗以宫廷生活为背景,内容多为歌功颂德、歌舞升平,讲究词釆华丽,注重诗歌技巧。应制诗的创作主体大都是皇上身边的御用文臣,基本是男性。上官婉儿、宋氏五女以宫廷女官的身份参与宴游唱和,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其诗歌创作便以男性的视角,以宫廷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政治眼光,追求典雅大气的诗风,完全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如上官婉儿现存应制诗四题六首:《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驾幸三会寺应制》《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其阳刚之风放在初盛唐男性诗人中也不分伯仲。
三是日常生活题材。在日常生活题材中,“拟男化”写作常表现为,女性作者以男性的口吻,以男性道德观教育、训诫同性,可谓“代男人言”的典范。宋若昭的《女论语》就是其中的代表。
《女论语》全书共十二章,内容可以分为“女孝”“妇德”“母德”三个方面,旨在教育女子如何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堪称是女子一生的教科书。《女论语》从日常生活出发,明确具体地劝诫女性自觉遵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刚女柔的社会规范,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心理特征。而这男性价值观念与文化心理,却恰恰是由女性作者自觉自愿地“完美”表达出来的。
四是情爱题材的诗歌。在情爱题材的诗中,唐代女性也往往跳出幽怨哀伤的传统情调,转而追求士大夫化的审美品位,如薛涛那首被誉为可与唐才子竞雄”的名篇——《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含蕴不尽的诗境虽然点逗出异性间难以言明的相互慕悦,但女诗人却以“送友人”的诗题,将男女私情转化为朋友之间的友情,并借用《蒹葭》中的意境以象征。这就无形中从女性狭小私密的闺阁,闯入男性世界的开放空间,以社会化的友情来升华男女私情,从而自觉地抛弃了爱情诗中本属于女性的情爱话语权,含蓄蕴藉,端庄雅正,完全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标准。
(二)审美追求的男性化
传统社会里,女性一直是依附于男性的没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第二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及生活方式上,更扩展到审美意识及“两性美学”上。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压抑遮蔽下,女性成为男性欣赏和定义的对象、客体,失去了做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人自立为主体并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主体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观念表现。”〔3〕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卑弱、被动、封闭、内向的性格,“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4〕唐代女性在两性美学追求上,表现出一定程度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有意味的是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却恰恰通过其诗作中审美趣味的男性化追求表现出来。其中复杂微妙的文化心态及其历史意义,值得注意。
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薛涛,作为地位卑微的乐伎,本是任男性欣赏、驱使、摆布甚至像物品一样买卖、赠送的角色,但她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奋力“以诗自拔”,其《寄旧诗与元微之》:“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下咏花怜暗澹,雨朝题柳为欹垂。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好男儿。”让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采:诗中既有“细腻风光我独知”的自觉与自信,又有“总向红笺写自随”的自在与自随,更有在女性被动的社会定位中冲破身份束缚,与所爱之人共作“好男儿”的强烈意愿。这正是诗人不再俯仰随人、活出自我、活出个性的宣言与告白。然而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却是以“好男儿”的角色认同与向往实现的。这种难能可贵的“主体意识”中缺失的最终恰恰是“女性”。
审美趣味男性化的集中体现就是自觉追求作品的阳刚之美。中国文化传统对两性性别特征做了明确的规定:“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女性的柔、静、卑、顺对应着男性的刚、动、贵、健。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气质和身体都应该是柔弱的,柔弱被看作是女人生来具有的天性。唐人同样继承了传统的女性观,同样主张女子应该柔婉顺从。但唐代女性性格中还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阳刚之美。这种追求既表现在服饰、妆容上,唐代女性喜着胡服男装、袒露胸颈;更表现在精神气质上,唐代女性少有禁忌,自信、开朗、热情、奔放。唐代女性既可以胡服骑射、抛头露面,也可以到郊外踏青、去市里听戏看球,还可以与男性一起吟诗作赋,诗酒唱和,享受着其它时代都没有过的自由。
(三)艺术风格的男性化
谭正璧先生曾说过:“女性的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的天国里一个最美丽的花园。”〔5〕的确,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思路,“温柔婉约是最适宜于女子的着笔,是女性文学最重要的风格之一,大多数女性诗人也是按照这一风格特征进行文学创作。”〔6〕纵观唐代女性诗人的诗歌,从长孙皇后、徐贤妃、一代女皇武则天,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宋氏五女到鱼玄机、李冶、薛涛,她们的诗歌,除了女性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蕴含在诗歌中的更多的是理性精神和鲜明的个体意识,最终凝结为男性化的艺术风格。
徐慧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一文,颇具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理性精神。此文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发挥骈体文长于说理的特点,欲抑先扬,首先肯定太宗的丰功伟业,然后笔锋一转,劝谏唐太宗罢兵高丽,停修土木,与民休养生息。观点鲜明,论证有力,笔锋犀利,感情真挚,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女性作者写就的政论文,历来备受史家赞誉。元代戈直在评《贞观政要》时说:“人臣进谏于君,古人拟之以之批鳞,虽士夫犹以为难,况妇人女子乎?”〔7〕的确,徐慧此文忧国忧民、见识卓越,置诸唐初魏征、温彦博等的“直言极谏之文”的行列,也不逊色。
上官婉儿曾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8〕她品评诗歌的最高审美标准是“健举”,而且这一标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诗歌创作更是实践着自己的美学追求。《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三冬季月景龙年,万乘观风出灞川。遥看电跃龙为马,回瞩霜原玉作田。”诗中的意象:三冬、万乘、景龙、灞川、龙马、霜原等都是宏大、健壮、雄浑,虽为应制诗却也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健举。
李冶、薛涛、鱼玄机等,更注重诗歌创作的立意境界、格调气骨。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采用性别跨界的方式写诗,在创作中往往戴上性别面具,肆意书写男性之雄风。这种群体性的“拟男化”的自觉追求形成唐代女性文学的独有现象。李冶被誉为“女中诗豪”,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价李冶云:“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不以迟暮,亦一俊妪。”“形气既雄”既指李冶外貌精神性格方面的男性化,同时还包括李冶诗歌创作中的男性化。李冶模拟男性的生活和创作,诗意放荡,谈笑戏谑,无所顾忌,也使她的诗风更显雄健、豪放。
薛涛的诗歌自觉追求一种“无雌声”的超性别写作。她的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常常超越闺阁的小儿女情趣,以男性化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人生,从而开拓了更为宽广的诗境。她在意识深处总是有意无意地贴近男性世界。于是,其诗作在女性柔弱凄美的传统风格中注入了清刚俊爽的气骨,显得沉雄豪迈。“自有兼材用,那同众草芳。献酬樽俎外,宁有惧豺狼”(《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蜀门西更上青天,强为公歌蜀国弦。卓氏长卿称士女,锦江玉垒献山川”(《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酬人雨后玩竹》),而正是这种自觉地男性化追求中,薛涛等一代才女,不自觉地扬弃着自己的女性身份。
二
唐代女性书写“拟男化”现象的出现,既是唐代开放开明的时代风尚造就的,也是唐代女性主观努力、自我锻造的结果。同时,更是在唐代特定社会环境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际,为实现自身价值、寻求自我定位的“反常”文化心态的艺术展现。
(一)客观社会环境
大唐经济发达、物质丰富、思想活跃、世风开放,正值封建社会的辉煌盛世,这使得唐代女性地位较之其他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女性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事务、参与诗歌创作的热情较之其他时代大增,女性与男性接触交流的机会也大大提高。唐代开放的世风为女性的“拟男化”诗歌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唐初统治者面对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状况,采取了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最高统治者这种对各民族“爱之如一”的态度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使得唐代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的局面得以最终出现。“各民族融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文化持久与反复的冲突和交流,破除了各个民族交流的障碍之后,多元文化终于在唐代得到充分显现”。〔9〕唐代不仅融合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精华,而且还能接受吸纳外来文化。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创造了辉煌灿烂、流光溢彩的唐代文化。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为唐代女性“拟男化”书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
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和各民族间的频繁交往,使得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同化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胡族风俗的影响,流传已久的儒法道统也受到胡族风俗的冲击。唐朝的皇族有着鲜卑的血统,受少数民族风俗和文化的影响较深。少数民族婚姻关系较为自由,女性所受拘束较少,社会地位较高。这种社会环境使唐朝妇女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地位都有所提高,唐代的妇女更有着前代和后代妇女都没有过的自由,她们可以抛头露面;可以离婚再嫁,也可以选择终身不嫁;她们可以到郊外踏青,也可以在市里听戏,还可以与男性文人唱和应答以诗会友。这种社会风气为唐代女性“拟男化”书写提供了有利的创作条件。
“拟男化”现象的产生与唐代道教的盛行也不无关系。道教在唐代被列为三教之首。道教以老子为鼻祖,以《道德经》为宗教经典,从阴阳和合的理论出发,形成了“重阴阳,等男女”的鲜明特色。“尊重妇女、男女平等是道教最具人文色彩的亮光。中国道教所具有的阴柔色调,以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丰富了女性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内容。”〔10〕《老子》哲学可以说是女性哲学,推崇的是女性的阴柔之性,崇尚的是“柔弱胜刚强”。“在道教中,女人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辱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神格,独立意志、愿望的重要角色。神仙谱系‘三仙’‘九品’中均有‘成仙真’的女子的位置。道教在发展演变过程当中,不少杰出的女道士跻身领导地位,她们为弘扬道教尊重女人之教旨精神做出努力,同时为女人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11〕
(二)主观心理原因
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审美形态的产生,除了社会的客观原因外,与唐代女性的男性化心理趋向有密切关系。“女性的男性化心理,就是指女性突破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群体特征及行为方式的理解(如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等),用男性化的眼光去观照世界、进而用男性化的态度去处理问题。”〔12〕
武则天从驯服烈马到君临天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拟男化心理的实践过程。相传唐太宗得到一匹烈马,名号“狮子骢”,性烈难驯,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当时武则天只有十几岁竟有如此胆识,足见少女时期的武则天对强悍勇猛的男性性格的崇拜;太宗和高宗时的两次入宫为妃,进一步强化了她对男性及权力的认同感;登上帝王的宝座之后,更是处处模仿男性甚至像男性皇帝妻妾成群一样豢养男宠。这一过程也是武则天由一个崇拜男性的少女,逐渐成为了一个模仿男性心理的后妃,再到完全男性化心理并极度崇拜权力的一代女皇的心路历程。因而武则天以女儿之身登上帝王的宝座,她没有也不可能以女性心理去治国理政,她必须以男性统治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去运行权力,管理朝政,排除异己。正因如此,武则天的诗歌创作更多展现了她的帝王之威而不是儿女之情。
上官婉儿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称。自幼生活在掖庭的她,成长的环境中没有男性世界可以参照,因此,她从小便是没有性别意识的女孩。成年后,她的男性心理和性格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武则天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跟随武则天之后,更是崇拜模仿武则天的一举一动。其所从事的掌管宫中制诰的工作正是男性士大夫的职责,上官婉儿是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更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男性化心理。可以说,“上官婉儿的男性化心理的完成可以看做是一种自然性的结果,出生掖庭导致了她对自身性别的漠视,对男性性别与权力对应性的模糊感,进而促使了她对武则天全方位的认同,最终成为了一名拥有男性化心理的宫廷女官。”〔13〕
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时,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终身未嫁。从《旧唐书》“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德宗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的记载,可知“誓不从人”,〔14〕是她们主动的选择而不是他人或环境的逼迫。选择独身,就意味着她们自觉放弃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选择放弃传统女性赖以安身立命的身份。她们放弃了传统女性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人生三部曲中的后两步,也就是在对抗儒家三从四德的行为规范,她们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男性的附庸,她们希望能够和男性一样,凭借才华学识扬名立万、光耀门楣、荣显父母。最终她们也得偿所愿,被唐德宗召入宫中,但“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宋氏姐妹这种拟男化的心理和行为“反映了她们不愿认同女性角色,一贯以男子自居的心理”。〔15〕
薛涛,一生经历了对男性从依附到背离的过程,完成了从思想到行为的“拟男化”。第一次是对父亲的依附,但随着父亲的去世,薛涛为生活所迫加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开始自食其力的人生。第二次是对节度使韦皋的依附,在最初的几年得到了韦皋的宠爱,但后因故被罚赴边,放还后主动脱离乐籍。第三次是对“元稹”的依附,薛涛也曾为爱情痴狂,对元稹暗许芳心,但最终元稹离她而去,从此薛涛选择“孤鸾一世”的生活。在经历了失怙、失宠、失恋的打击之后,薛涛深深认识到男性的不可依靠,她也由最初对男性的崇拜依附到积极参与并融入男性文化圈再到以男性的姿态生活,实现了从心理到行为的全面“拟男化”。心灵深处的男性化意识自然导致文学创作的“拟男化”倾向。
综上所述,唐代女性书写表现出“拟男化”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诗歌的题材上、内容上,也表现在诗歌的风格和审美的追求等众多方面。不仅有李冶、薛涛、鱼玄机等底层女性,也有长孙皇后、武则天等宫廷女性。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现象贯穿于唐代初、盛、中、晚的每一个阶段,堪称古代女性书写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与诗人拟男化的心理有关。
三
唐代女性“拟男化”写作是唐代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使然。唐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思想文化上的兼容并包促进了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实现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推动了女性创作的兴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拟男化”的写作,是唐代女性寻求性别身份定位或社会认同的迫切期望、展现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种文学表达,是她们努力突破自身性别上的局限、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女性意识之彰显,也是女性不甘心自身地位、冲破自身身份藩篱的体现。
“拟男化”写作是对女性自身角色地位的否定和放弃,是女性的自我异化,是社会层面喜剧下的性别悲剧。“天地之间,一阴一阳。生人之道,一男一女。”〔16〕人类社会原本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心理、体力等方面各具特色,各有优长,本无优劣尊卑之分。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处于统治的、支配的、主动的地位,女性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受歧视、从属的地位。“拟男化”是女性对男性的崇拜和模仿,无论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生存的需要,抛弃自身的性别角色定位,进行跨性别的书写,不能不说是一种性别的悲哀。女性“刻意把自己作品的精神面貌弄得与男人的感情世界一模一样,精致地制造出一片假性情,以求文化心理上的满足,以求传统艺文权威界的承认。隐遮、阻抑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波澜,丢弃了女性自我的角色心理和艺术品位,结果作品大多苍白乏力,气格平庸,无论审美情趣或人文思想上均几无可取。这既是模拟文学的悲哀,又是迷失了自我的教训。”〔17〕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拟男化”写作现象的某种心理原因,然而却未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古代女性在作品中刻意男性化的深层心理与文化原因。
笔者认为,唐代女性诗文创作的“拟男化”现象,根本原因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性别意识的自觉之间的“时间差”。如前所述,唐代社会相对开放,礼教与各种政治束缚较前后时代都宽松得多。为国家建功立业,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成为唐代各界人士尤其是文人阶层广泛憧憬的人生境界。因而,唐代士人意气风发,表现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整个社会充满着“青春朝气”。人的主体意识的普遍苏醒,成为唐代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感受着时代脉搏、有文化有教养的唐代女性作家自我意识逐渐萌生。她们原本“安分”的心开始“骚动不安”,她们开始自觉地、想方设法逃离男权文化强加给自己的“女人”角色;开始拒绝平庸,渴望壮怀激烈、建功立业的非凡人生;寻求施展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机遇。在中国文学史上,虽前有蔡文姬、后有李清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慷慨悲歌,但像唐代女性这样群体性抒写豪情壮志,则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然而,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虽有所提高,但男女关系总体看,却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样,是一以贯之的男权社会。唐代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地位、没有承认女性独立的社会角色,没有承认作为与男性相对应的“另一半”自身的社会价值;唐代女性作为男性依附品地位没有改变。于是,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涨与依附地位的依旧以及努力逃离这种依附地位之间,又形成尖锐的矛盾。唐代妇女比任何时代都美,但却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意识;唐代妇女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才情与自尊自强的精神风貌,但仅是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没有女性意识做基础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结果只能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向男性意识“认祖归宗”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正是在这“认祖归宗”的过程中,误把男性做“本性”,犹如“直把杭州作汴州”。女性,作为人类两性中的一半,其内在生命激情的勃发,其自我意识的高涨,恰恰是通过自己抹去自身的性别身份、向另一半无条件认同来实现的。于是,“拟男化”写作便产生了。这被看做是女性解放历史长河中悲剧性的一幕,但也可以说是喜剧性的一瞬间。
然而,在妇女解放的漫漫长途中,这种“拟男化”的异化现象,又恰恰是妇女逐步觉醒、最终形成真正的“女性意识”无法绕过的历史环节。这种所谓的自我意识的丧失,恰是其后女性意识觉醒的内在动力:通过向男性世界的认同寻求自身的存在价值,再通过这种自我价值的认定,实现自身性别身份的最终确立。在这种历史视角下,笔者认为,古代女性文学“拟男化”,应该说是正常的文化现象,既谈不上女性文学的“悲哀”,更不是什么值得反思的“教训”。在21世纪的今天,当女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形成了真正的女性意识之后,现代中国魅力四射的“女性文学”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是很好地解释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异化——复归本性”的历史发展轨迹。
“拟男化”写作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出现就是对拟男化的匡正。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匡正了以往遏止乃至泯灭性别特征的偏颇,突出性别意识和女性的主体意识,体现女性自觉意识。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她们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由社会层面到心理层面,由“美的结构”到“恶的构成。”〔18〕并且随着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从创作到批评都注入了更多的女权色彩。“突破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附属于父权文化、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和审美情趣狭隘的格局,以自己的实力和平等的姿态与男性展开文学上的对话,在与男性文学的不断冲突交融中,共同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灿烂奇观。”〔19〕
今天,女性书写不仅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争取女性表达自己、诠释自我的途径,更是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
注释:
〔1〕〔明〕钟惺:《名媛诗归》,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2〕其意思是,移唐国祚是上承天命,下顺民意的。远近的敌对势力都肃清了,实现了社会的和平安定。天下富裕,上下祥和。于是举行典礼,希望大周国永远河清海晏四海升平。
〔3〕方世南:《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异同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3期合刊。
〔4〕翟瑞清:《20世纪中国女性主体地位的演变轨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5〕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6〕丛小燕:《唐代女冠诗风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7〕〔唐〕吴兢:《二十五别史之贞观政要》,〔元〕戈直评,齐鲁书社,2000年,第293页。
〔8〕《唐诗纪事》卷三《上官婉儿》条记载:“中宗景龙三年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竟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9〕曾宪利:《试论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10〕〔11〕李素平:《道教对女性的尊崇》,《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12〕〔13〕胡敏:《武则天诗文男性化审美形态研究》,湘潭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14〕〔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198页。
〔15〕转引自郭海文:《依附与背离:宋若昭诗文探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6〕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绪言》,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17〕胡明:《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8〕姬宏:《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简论》,新疆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9〕王传满:《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与发展》,安徽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Analysis on Affordable Housing Financial Mechanism in USA〔*〕
- Studies on the Models of Childre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Investigating Learners’Satisfaction Towards MOOC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Western Ethics History Course〔* 〕
- A Correlational Study between Teachers’Emotional Factors and Class Interactive Teaching Efficacy〔*〕
- 早期天主教汉文小说《儒交信》论略
- 我国各时期印花税票题材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