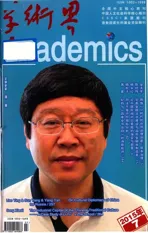《白鲸》:一部倡导生态正义的海洋史诗〔*〕——兼与王诺教授等商榷
2015-02-25○央泉
○ 央 泉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8)
一、引 言
20世纪以来,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白鲸》因为描写了亚哈疯狂追击白鲸莫比·迪克并最终导致了船毁人亡的结局而倍受评论界的关注,但中外评论界大多认为《白鲸》是一部反生态的文学作品。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劳伦斯·布依尔就指出,虽然小说成功地将一个动物塑造成主角,但因为“麦尔维尔的环境想象太过于人类中心主义”〔1〕,所以作者对鲸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吝惜而节制的”〔2〕。我国生态批评学者王诺教授在其专著及论文中也认为《白鲸》这部小说的“基本倾向是反生态的”〔3〕。或许是因为布依尔先生和王诺教授在生态批评界的影响,我国评论界大多认为《白鲸》是“反生态的”〔4〕,有的甚至指责《白鲸》的作者“绝无一丝爱怜海洋生物之意”〔5〕,笔者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不同见解。
不可否认,《白鲸》的确描绘了以亚哈为首的“裴廓德号”誓死追杀白鲸这样一个捕鲸故事,从生态批评视角来看,亚哈也的确是一个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者,堪称反生态的恶魔。但这并不表明小说的主题就是反生态的,我们绝不能因为一部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位疯狂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就说它是反生态的,只能说这部作品的某个人物是反生态的;就如同一部描写战争残酷的小说就一定是反和平的作品一样,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至于什么是反生态文学,笔者尚未发现学界有明确定义。但根据人们对反生态文学的批判,反生态文学应该指:从正面宣扬人类与自然对立、歌颂人类对自然进行掠夺与征服的艺术作品;它体现了作家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宰,凌驾于万物之上;人与自然是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关系;人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终极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按照以上对反生态文学的理解,要判断《白鲸》是否反生态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作者对于捕鲸业的态度,也即对于人类捕杀鲸的行为是批判还是赞赏?(二)作者对于被捕杀的鲸的态度:是同情还是冷漠?(三)作者对亚哈这个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态度:是肯定歌颂还是否定批判?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应该是评判《白鲸》是生态还是反生态文学的关键之所在。关于第三点,笔者另有专文进行了论述:“虽然《白鲸》这部小说的主题纷繁复杂,亚哈这一人物形象也是多重而相互矛盾的,然而从整体上来看,麦尔维尔对亚哈疯狂追击白鲸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亚哈是其批评和解构的对象。”〔6〕所以本文仅就上述一、二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二、麦尔维尔对捕鲸业的批判
《白鲸》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正是美国工业蓬勃发展、经济日益强大,文化上也逐渐脱离英国母体而获得独立的时代;另一方面,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19世纪的美国人过于自负,在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的影响下,“个人主义”被推崇到了极致,对财富的拥有成为了衡量成功的尺度。19世纪的美国从而成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和金钱崇拜的时代。人们肆意开疆拓土,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裴廓德号”捕鲸船正是美国时代的缩影,堪称“美国之舟的复制品”〔7〕。
在《白鲸》中,麦尔维尔首先对捕鲸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没有石油及天然气的19世纪,欧、美市场对鲸油的需求不断增长,鲸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加油壶”〔8〕。在捕鲸船上,金钱、权力高于一切,“裴廓德号”的前任船长、老股东比勒达就是这样一个爱财如命的人物。他虽然随时都拿着一本《圣经》,但却认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一回事,而这个现实的世界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第72页)所以他一面劝说水手们在主日里不要捕杀得太多,可是一面又告诫他们别错过任何机会,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第75页)。在小说中,麦尔维尔对他的描写虽然用墨不多,但对他这种嗜财如命的性格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斯达巴克身上得到了最好体现。作为“裴廓德号”捕鲸船大副的斯达巴克虽然多次力劝亚哈放弃对白鲸的追击,但他对白鲸的态度和以实玛利不同,他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实用理性主义经济至上的思想。斯达巴克真正关心的只是鲸油,他出海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当他第一次反对亚哈追击白鲸时,就旗帜鲜明地说:“我是到这里来捕鲸的,不是来为我的上司报仇的。就算你捉到了它,你报这个仇能产生几桶油呀,亚哈船长?”(第156页)所以他总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在“裴廓德号”第一次放下小艇追击鲸时,他再一次表明了这种态度:“前边就是大量的鲸油,斯塔布先生,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呀。”(第209页)由此可见,他劝说亚哈不要追击白鲸并非像以实玛利一样是出于对莫比·迪克的敬畏,而是出于对所得利益和承担风险的理性权衡与取舍。斯达巴克这个人物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功利主义的缩影。
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人的生命也变得用金钱来衡量。当胆小的水手比普第一次落水被救起后,二副斯塔布就警告他说不要离开小艇:“我们不能为了你这样的人而白白牺牲一条大鲸。一条大鲸……卖起来可比你的身价高出三十倍呢。”(第392页)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可怜的比普再一次因为惊恐而落入海中后,斯塔布和其他水手果真弃他不顾,径直去追击比他“身价高出三十倍”的大鲸了,结果独自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比普被吓疯了。对此麦尔维尔这样评论道:“人类虽然爱他的伙伴,然而,人类毕竟是种孳孳为利的动物,这种癖好往往要跟他的仁爱心发生冲突。”(第392页)人类已经堕落到了嗜钱成癖的程度了,多么辛辣的嘲讽!由此可见,在金钱至上的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背后是情感沙漠和道德荒原。
19世纪美国的捕鲸业也象征着人类对海洋大自然的掠夺与征服。当时正值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地进行领土扩张的西进运动。而《白鲸》里“裴廓德号”的航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精神向海洋的延伸。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就曾指出,“亚哈船长是美国征服世界的化身”〔9〕。对于为了巨大经济利润而在海洋上进行疯狂追捕与血腥杀戮的捕鲸行径,麦尔维尔充满了厌恶和愤怒:“这只牙骨的‘裴廓德号’已经变成个屠宰场了,每个水手都是屠夫。”(第290页)即使对《白鲸》持批判态度的布依尔也坦言,《白鲸》“的确多次描写了捕鲸者的邪恶:不仅将亚哈描绘成偏执狂,而且把整个捕鲸描绘成‘一种屠宰业’,捕鲸者则是‘屠夫’,而裴廓德号的日常捕杀则成为了像要去耶路撒冷进行圣战的十字军,沿途所进行的‘入室行窃’的勾当。”〔10〕不仅如此,麦尔维尔还将捕鲸者同拿破仑的侵略与鲨鱼的贪婪并置:“我们都是海上陆上的凶手,包括大鲨鱼和拿破仑在内。”(第135页)在《斯塔布的晚餐》一章中,麦尔维尔直接将在船上吃着鲸排的斯塔布和在海中抢食大鲸尸体的鲨鱼等同起来:那天晚上,大尝鲸肉筵席的不仅只是斯塔布,同斯塔布自己的咀嚼声交混在一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鲨鱼在巴嗒巴嗒地饱尝它的肥肉。(第279页)这段描写一针见血地讽刺了人类的贪婪无情,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这一残忍行为的厌恶和批判。
麦尔维尔还从鲸的视角对人的兽性进行了嘲讽与批判。在小说中,当描写一群被捕鲸者包围了的鲸的恐慌时,麦尔维尔这样评论道:“看到我们面前这些古怪的‘吓怕了’的大鲸,就毋须大惊小怪,因为普天之下的野兽决不会痴心妄想,认为人类在疯性大发的时候,不会把它们大批杀害。”(第364页)其对人类兽性的讽刺批判溢于言表。在小说中,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贪欲与残忍有时甚至超过了动物。在《白鲸》的结局中,连凶狠的鲨鱼和残酷的海鸟也都变得温顺了,唯一不能控制自己贪得无厌本性的就是人类。
而在以实玛利眼里,捕鲸船就是人间地狱:这艘载着野人,烧着鲸尸向前奔赶的“裴廓德号”,似乎就是患偏热症的亚哈船长心灵的具体复本……“那时虽然被包裹在黑暗里,然而却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人的红彤彤、疯狂而可怕的面孔。我看到的尽是不绝如缕的幢幢鬼影,在浓烟里,在烈火里半隐半现。”(第401页)在这些文字中,麦尔维尔对于捕鲸业的批判、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谴责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经济学家戴利断言:“贪得无厌的人类已经堕落了,只因受到其永不能满足的物质贪欲的诱惑。撒旦唆使道:把石头变成面包!现代人就照着做了,甚至到了制定某种能量集约计划以将地球上的岩石全部碾成面包原料的地步——妄图吃掉地球方舟本身。”〔11〕在小说《白鲸》中,以亚哈为首的捕鲸者正是这样一群“妄图吃掉地球方舟”的疯狂之徒。他们历时三年,环球世界,只为了满足自己征服白鲸、报仇雪恨的欲望。麦尔维尔对像亚哈一样疯狂追击白鲸、肆意践踏海洋的行径发出这样的忠告:无论幼稚的人类如何夸耀自己的科学和技艺,直到末日审判,海洋终将粉碎人类所能制造的最宏伟、最坚固的航船,因为“人类已经忘记了本来就应该对海洋做出的充分的敬畏”(第262页)。
在对捕鲸业进行批判的同时,麦尔维尔对于遭受人类屠杀的大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要求人们向大鲸学习,礼赞大鲸。
三、麦尔维尔对鲸的同情与礼赞
麦尔维尔在批判捕鲸者的无情和残忍时,对于鲸因人类的杀戮所受到的灾难和痛苦充满了同情。这种情感在对“裴廓德号”捕杀第一头鲸时的描绘中得到具体的表现。当鲸被刺中后,在血海中垂死挣扎时,麦尔维尔用了“痛苦地滚动”“煞是怕人”等词汇来描写鲸中枪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从而将一头垂死的鲸转化成了一个正在受苦难流血的人,深切体会到大鲸的痛苦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因为麦尔维尔深信,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
这种对于鲸之苦难的怜悯之心和对于人类凶残行为的自责之情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在描绘那些被捕鲸者追赶、中了标枪的鲸所遭受的苦难时,“痛苦”“可怜”的词句随处可见:一只因为捕鲸者的围追而惊恐失措的鲸,好像“给人施上了魔法似的”,它除了从喷水孔里喷出来的那阵闷气,一点声响都没有,使人“顿生一阵难以言状的怜悯心了”(第337页);垂死挣扎的大鲸最后那阵将了未了的喷水,“煞是可怜”(第341页);而被捕鲸铲击中的大鲸则因“痛得发狂”(第369页)而在水里翻腾;一只老鲸的眼里暴出的两只大泡泡,“教人看了非常可怜”(第340页)。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白鲸所受痛苦的悲悯之情,也激发了人们对于捕鲸者荼毒生灵的深切痛恶,迫使读者意识到人类应该成为白鲸苦难与毁灭的代理人,从而消除了人鲸之间的二元对立。
不但对鲸所遭受的痛苦给予深厚的同情,麦尔维尔在小说中还热情礼赞鲸的智慧与壮美。麦尔维尔曾说:“除非你承认了大鲸的价值,否则,在真理方面,你就不过是个思想狭隘者。”(第322页)而这正是当代生态批评家所倡导的理念,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一切生命。在麦尔维尔笔下,大抹香鲸的额头“又高耸又威严”,一如神灵的仪表,它那种赫赫威仪,就会教人不由自主地对它那无限的尊严“心悦诚服”;而当鲸快速游动时,那种迅疾而又非常和缓安静的游姿,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而且,鲸和人一样,既有肺又有热血,可是,它竟能终生活在寒冷的北极,这说明鲸具有比人类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人类“你应该礼赞鲸,以鲸作为你的楷模!”(第294页)麦尔维尔甚至说,在写作关于鲸的文章时,需要大手笔、大气魄:“请给我一只秃鹰的羽管笔!给我把维苏威的喷火口拿来作墨水缸吧!……这就是这么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广袤无垠的题材的特点!我们要把它写得跟它身体一般巨大。”(第432页)这种对鲸由衷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麦尔维尔所创作的《白鲸》的确是一部包罗万象、气势恢宏的巨著。英国作家劳伦斯就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麦尔维尔那样,满怀激情地去感知非人类生活的浩瀚与神秘。他非常执着地想要超越我们视野。”〔12〕
麦尔维尔不仅从正面讴歌了鲸之宏伟与壮美,它们对于同类的友爱与援助也堪称人类的楷模:
最近抹香鲸因为遭到四面八方不断地追击,所以它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小群游动,而是成群结队了。当鲸发现有捕鲸艇追击它们时,虽然相距还有一英里之遥,它们就迅速聚拢来,“列成紧密的队伍,所以它们的喷水完全像是一片闪光的枪林弹雨,以加倍的速力奋勇向前。”(第364页)正如安德鲁·德尔班科所指出的:“抹香鲸的确为了相互的保护而聚集在一起,而当鲸群被鲨鱼或者别的食肉动物攻击时,单独的鲸就会将自己暴露给攻击者,通过自己的身体护卫受伤的鲸并将它们带回到保护圈里。”〔13〕
鲸不仅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进行自卫,而且还为了同类的安全而不惜冒着危险挺身而出,麦尔维尔还在小说中描绘了莫比·迪克英勇救援其同胞的场景:有一天,当“撒母耳·恩德比号”的水手放下小艇去追击一群鲸,并且已经把其中的一条拴住了的时候,突然海底里竟蹦出一条大白鲸来,“泡沫飞溅地奔进了鱼群,开始凶狠狠地咬起我的捕鲸索了,而其它那些鲸却都给侥幸地望风逃脱了。”(第416页)白鲸的这种勇敢拯救同类的行为,比起为了金钱而置自己同伴生死于不顾的人类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堪称动物世界中精诚团结、见义勇为的楷模。“《白鲸》是一首献给鲸的这种神秘天性的赞美诗——它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团结互助的精神,麦尔维尔几乎以一种虔诚的敬畏来描绘这种神奇的动物。”〔14〕
人类对鲸的疯狂捕杀,也令作家对这个物种的存亡而担忧。在小说中,麦尔维尔直接使用《鲸的庞大身躯会缩小么?——它会灭亡吗?》(第105章)这样的标题来表明这一主题。由于捕鲸者借助现代技术和机器工具来疯狂地捕杀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鲸,麦尔维尔担心鲸最后是否会从海里消亡:“那条最后的鲸,是否会像最后的一个人那样,抽完最后一筒烟后,连他自己也在最后一口烟里烟消雾散了呢。”(第437页)麦尔维尔认为,作为个体的鲸虽然会有死亡,但作为一个神圣的物种,“我们还是应该把鲸类看作是一种不朽的动物”(第439页),即使人类都在“最后一口烟里”绝迹了,鲸却还将生存在波涛汪洋的大海中。由此可见,麦尔维尔将鲸的生死同人类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认为鲸将会比人类生存得更为久远一些。
麦尔维尔不仅表现出对鲸存亡的极大关切,而且这种关心也扩大到其它动物。在《白鲸》中,麦尔维尔还描写了美洲野牛急剧减少的现状:“这些野牛群,三四十年前,成千成万地曼衍在伊利诺斯和密苏里的大草原上……伊利诺斯的野牛数目,就超过了现在伦敦的人口。”但到了现在,人们在那个地区“已经找不出它们的一只角或者一只蹄”,而这种神速的灭种“主要是人类的刀枪所造成的”(第437页)。在小说《皮埃尔》(1852年)中,麦尔维尔也描绘了对于因为人类捕杀而致使许多物种逐渐灭绝的担忧:“地球上这些凶猛的动物不是每天、每小时地走向灭绝吗?英国的野狼去哪儿了呢?在维吉尼亚,现在又要去哪寻找黑豹呢?”〔15〕通过这样的描写,不难读出19世纪的麦尔维尔在对动物命运的关切和担忧中所折射出来的生态意识。麦尔维尔的这种超前的生态意识在《做菜的鲸》一章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达:
毫无疑问,第一个把牛杀死的人,总是被人家看作是个谋杀犯;说不定还要送他上绞架;而且如果把他送到牛群里去审判的话,他准会给绞死;也一定会像任何一个谋杀犯一样罪有应得。请你在礼拜六晚上到肉市场上去走一趟,去看看一群群的两脚动物,在瞪眼紧瞅着一长排一长排的被杀死了的四脚动物吧。那景致可不像是从吃人生番的嘴里拔掉一只牙齿一般么?吃人生番么?谁不是吃人生番?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斐济人,为了防备那即将到来的饥荒,把一个瘦骨嶙峋的传道师拿去腌在他的地窖里,那倒是比较情有可原的;我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斐济人将比你,比你这个开通文明的老饕,把一些活鹅钉死在地上,拿它们的肝去做你的肥鹅肝饼而大嚼一顿的,更会获得宽恕呢。(第287页)
以上这段文字里面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思想:
首先是众生平等的观念。在麦尔维尔看来,牛和人类一样拥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力,如果让牛来审判人的话,那么人类一定会被送上绞架,因为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屠杀了许多牛的兄弟。这种生命平等观在《白鲸》小说中还在很多地方得到了体现,比如他把吃鲸排的二副斯塔布同抢食鲸肉的鲨鱼等同起来;而在幼鲸的眼里,“我们这些人似乎只是一些马尾藻而已”(第367页)。此外,对于以实玛利同食人生番魁魁格友谊的描写也体现了作者这种众生平等的观点。不管是人类还是其它动物,在麦尔维尔的笔下都能看到这种平等博爱的人性主义光芒!在这里,看不到人类唯我独尊的骄横与霸道,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与狂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这些非人类生命的手足之情,折射出他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之心,从而彻底远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
此外,在这段文字里,麦尔维尔还表达了一种辩证的生态观:即一切生物都依赖于其他生物而生存,这其实就是朴素的达尔文生物链的思想。世界上的一种生物都是以另一种生物为食物而得以生存,而且反过来自己又为另一种生物提供食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吃人生番”。然而在麦尔维尔看来,一个活吃鹅肝的人比一个因为饥饿而吃人的人更应该进地狱,这正是一种生态正义观的体现。人们倡导生态,但决不会置人类的基本生存于不顾;但我们却反对为了自己的贪欲和享受,而涂炭生灵。或许麦尔维尔的这种观点应该得到当今主流生态家的赞赏。人应该像其他生物一样,有保障自己生存的权利。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认为,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了生存所需而猎杀动物不仅“不意味着不尊重生命”,而是“尊重了那个生态系统”〔16〕,因为这是整个大生物链得以延续的必要环节。而即使是最高级的人类,死后的尸体也成了其他生命摄取食物的对象。
四、结 语
当然在剖析《白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当今的生态价值观来看,该作品中的确也存在着少许非生态的描写。例如,在第24章《辩护士》中,麦尔维尔虽然一方面承认捕鲸业就是“一种屠宰业”,捕鲸手就是“屠夫”,但另一方面却为美国捕鲸业的兴起与强大流露出赞美之情:我们美国的捕鲸者的数目现在怎样会超过世界所有捕鲸者的总数,捕鲸队的船只多达七百艘,人数多达一万八千人,每年有高达七百万美元的收获输进我们的港口。(第103页)而捕鲸业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令他颇感自豪,鲸油不但是许多制造业的重要原料,也成为了普通百姓日常照明的必需品:“差不多一切照耀整个地球的,以及照耀在那许多圣殿之前的大小灯烛,都得归于我们的功劳!”(第103页)从这些字里行间,读者不难发现麦尔维尔对于美国捕鲸业的兴旺发达所产生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此外在第82章《捕鲸业的荣耀与辉煌》中更是追述到了替天行道的柏修斯、圣乔治、约拿等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最后麦尔维尔还十分豪迈地说:“这样,在我们团体的全部成员中,就不仅有英雄、圣人、神明和预言家了。”(第345页)由此可见,麦尔维尔对于捕鲸这一行业的情感是复杂而多重的,他一方面批判了捕鲸业的残忍与血腥,也同情捕鲸水手的非人生活,他们不但每天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甚至有时还要为此丢掉性命,所以他对世人疾呼:“千万请你节省灯油和蜡烛!你每烧一加仑油,里面至少有人为它流过一滴血”(第197页);但另一方面又为捕鲸业给美国带来的繁荣与发展而深感自豪。
虽然《白鲸》小说中有某些非生态的描写,但就整个作品的主体来说,麦尔维尔通过抒写对鲸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通过批判并解构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了保护动物、尊重自然的生态情怀;而以亚哈为代表的“裴廓德号”的覆没及以实玛利得到救赎的结局,更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伦理取向:尊重自然,敬畏一切生命,才是身处灾难深渊的现代人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这对当前的生态危机无疑具有超前的警示意义。因而可以说,《白鲸》的主体是倡导生态的,是一曲惩恶扬善的生态正义之歌。
注释:
〔1〕Buell,Lawrence.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
〔2〕〔10〕Buell,Lawrence.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8,214.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王诺:《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1页;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
〔4〕乌热尔图:《麦尔维尔的1851》,《民族文学》2007年第5期,第122页。
〔5〕于秋颖等:《生态批评的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以〈白鲸〉和〈老人与海〉为例》,《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第154页;胡铁生:《生态批评的理论焦点与实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5期,第84页;尹雪梅:《生态文学:西方批判文学的新范式》,《求索》2008年第6期,第184页。
〔6〕央泉:《英雄还是恶魔:〈白鲸〉主人公亚哈形象新解》,《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10页。
〔7〕〔13〕〔14〕Delbanco,Andrew.Melville:His World and Work.London:Picador,2005,pp.158,168,169.
〔8〕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后文中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做注。
〔9〕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412页。
〔11〕赫尔曼·E.戴利:《珍惜地球》,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9页。
〔12〕Lawrence,D.H.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124.
〔15〕Melville,Herman.Pierre or The Ambiguities,eds.,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 Newberry Press,1971,p.34.
〔16〕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