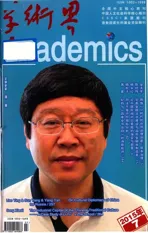《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2015-02-25姚小鸥孟祥笑
○姚小鸥,孟祥笑
(1.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2.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于放流中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而作《天问》。相关论述如下: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1〕
上引文“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呵)而问之”,言及《天问》的创作过程,此即“呵壁”说之由来。〔2〕唐宋诸儒所论承此,明代始有异议,至今争而未决,成为屈骚研究史上的重要学案。
“呵壁”说首先涉及到“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与其中的壁画问题。在关于《天问》创作缘起的讨论中,人们的关注点最早集中在这里。
古代制度,宗庙建于都中。〔3〕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楚国都城先后有多处。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楚居》篇的记载,楚都称“郢”者,先后有十几处之多。〔4〕这为屈原放流中可能到过多处楚王都提供了依据。〔5〕关于“公卿祠堂”,王逸说,《天问》中“白蜺婴茀,胡为此堂”,“盖屈原所见祠堂也”。〔6〕孙作云虽然赞成《天问》创作缘起于壁画,但否认这一问题涉及“公卿祠堂”。〔7〕有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包括楚墓建筑遗存指出:“商、西周时期的人们已在墓上建筑了封土,并设立了用于祭祀先祖的‘享堂’。”〔8〕这说明先秦时期确实有与“公卿祠堂”性质相类的建筑。
“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多有壁画。《吕氏春秋·谕大》篇说:“《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9〕王逸之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系据汉鲁恭王灵光殿壁画而作,赋作的内容与《天问》所述颇有相似之处。〔10〕由汉代发达的壁画艺术与出土楚地帛画等美术实物可知,《天问》所描写的天地开辟、人类降生、忠臣孝子、贤愚成败等神话故事以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包括壁画在内的古代图画经常表现的内容。
“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确有壁画,屈原也确实见到过这些壁画,是否就可以判定《天问》系叩壁而问的题画诗呢?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篇中的某些抽象内容,如“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等,很难见诸图画。而且正如质疑者所言,《天问》所述内容极为丰富,任何一座建筑的壁画难以将其一一呈现。〔11〕
那么,壁画与《天问》创作契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学术史上讨论《天问》的创作时,学者们已经考虑到了屈原的个人修养和知识储备。〔12〕各种资料显示,屈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哲人。《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末觉浪道盛的《三子会宗论》将屈子与孟子、庄子相提并论,具视为战国时代精神的代表。〔13〕从其全部作品来看,屈原对楚地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掌故都非常熟悉。所以,《天问》中的许多内容本不待其偶遇壁画而获知。见壁画而呵问云云,只能说是屈原创作《天问》动机的获得而已。〔14〕
更为重要的是,《天问》形式上的特点与“呵壁”说颇相参差。任何事物皆须依托其形式而存在,事物的形式又由其内在与外显两个方面组成。自其内部观之,则如王夫之《楚辞通释》所言,《天问》“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固原自所合缀以成章者。逸谓书壁而问,非其实矣。”〔15〕《楚辞通释》的上述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了《〈天问章句〉序》所言“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与《天问》文章本身存在的矛盾。
《楚辞通释》对《天问》内在文理的分析,及其与“呵壁”说矛盾之处的论述虽颇为精当,在《楚辞》学史上却未成定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氏此说缺乏对《天问》外显形式的分析。《天问》的文体综合反映了屈原作品外在形式与内在文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正是破解《天问》创作之谜的枢机。我们曾经指出,《天问》是史诗式的哲理诗。〔16〕文体性质决定它的创作必然经过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远非“呵壁”说所能涵盖。
回顾学术史,关于《天问》的文体,先后有“四言诗”“哲理诗”“史诗”“咏史诗”“抒情诗”诸说。这些说法分别照顾到了《天问》形式和内容的某些方面,但说者拘泥于诗篇之个别要素,皆未能参透《天问》内容、形式与其创作过程之间的密切关联。故难以对“呵壁”说进行周严的解释。“史诗式的哲理诗”说,汲取了以上各种观点的合理之处,使《天问》的本质特征得以显现。沿波讨源,可由此窥得《天问》创作之奥窔。
“史诗式的哲理诗”含有两个关键词,即“史诗”与“哲理诗”。就形式而言,《天问》首先为史诗之属,此即“史诗式”之由来。下面就此逐一进行讨论。
首先谈《天问》的句式。学者早就注意到,《天问》的四言句式在屈骚中具有独特性,“四言诗”说即由此产生。〔17〕按照王逸《〈天问章句〉序》所言,《天问》类乎“题赞诗”。古代的题赞诗大多为四言体。宋代王回《古列女传序》曾总结说:“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18〕孙作云先生继此分析说:“《天问》是根据壁画,或基本上根据壁画而作的,壁画上有人像,像旁有像赞,而像赞是四言诗,所以《天问》也采用了四言诗的形式。”〔19〕
前人讨论《天问》与图赞诗四言句式的关联时,多依据汉代文献材料。事实上,《天问》的四言句式有更早的来源,它与我国古代图文结合的史诗传统关系密切。〔20〕《文心雕龙·辨骚》篇指出,《楚辞》之作深受《诗经》影响。〔21〕《诗经·大雅》中的《大明》《绵》《皇矣》《公刘》《生民》诸篇,一般被认为是周族史诗。〔22〕有学者认为,上述周族史诗为“宗庙壁图上祖先人物及其业绩的述赞之辞”。〔2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周公之琴舞》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说明战国时期《诗经》及其他《诗经》类文献在楚地曾十分流行。这使得《天问》四言形式与《诗经》以来史诗传统的关联,得到文献学方面的进一步证明。
文学作品的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素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天问》对传统文学样式的继承和发展,与屈原早年接受的教育有关。楚国贵族教育的内容与中原诸国相类。《国语·楚语》载申叔时谈论贵族教育时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4〕
由《楚语》可知,楚地贵族教育的内容涉及到周代礼乐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诗”与“史”占据重要地位。在屈原的早期学习经历中,必然接触到各种经典文献样式,这为《天问》文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王国维说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25〕《天问》与《诗经》所代表的北方文学的关系,显示了其诗学精神的渊源所在。
四言句式本身,尚不能充分证明《天问》的史诗性质。统领全篇、铁证其为史诗形式的是开篇所用“曰”字。
《天问》开篇的“曰”字十分醒目,曾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游国恩《天问纂义》关于“曰”字的“按语”说:“此曰字,自是发端叩问之辞,其上当省一问字。”〔26〕游氏按语“发端叩问之辞”一语显系由“呵壁”说派生,它并未阐明“曰”字与《天问》整体结构的关系。近代有学者指出《天问》开篇“曰”字的使用与“呵壁”说不契合,但未作进一步的说明。〔27〕
“曰”字置于篇首,具有重要的文体标志意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包括楚地简帛文献,多有以“曰”字开篇者,兹举要如下:
《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
《尚书·皋陶谟》:“曰若稽古皋陶……”〔28〕
《史墙盘》:“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
《楚帛书》:“曰故(古)﹝黄﹞熊包戏……〔30〕
李学勤先生首先发现“曰”字的这种特殊用法。他指出,这是“古人追述往史的常用体裁”。〔32〕以“曰”字统领全篇,说明屈原在《天问》的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采用史诗的形式。它的使用,是屈原结构《天问》全篇的自觉选择。
《天问》是韵文的问句体裁。与前引《尚书》《史墙盘》《楚帛书》等叙事文体不同,世界各民族流传下来的早期历史文献,很多采用的都是问句体。饶宗颐先生《〈天问〉文体的源流》指出,《梨俱吠陀》《火教经》《圣经旧约》等域外文献采用的都是问句体。类似文献还有巴基斯坦联邦直辖北部地区的巴尔蒂斯坦流传的《索玛莱克》。这首对话体的创世歌,包括150个问题及回答。其开头部分的内容,和世界许多民族的史诗一样,有关宇宙的起源。《天问》采用问句的表达方式,曾使一些学者误认为它的主要目的是对宇宙万物的怀疑甚至否定。但从《天问》的内容来看,诗人对篇中的提问并非不知答案。有些问句之间,本身就互含答案。由此可见,作者“问”非求答,而是借助提问,通过隐喻的方式引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33〕
从形式上来说,《天问》的艺术创造在于,它将以“曰”字开篇的先秦史传、原始民族问句体史诗和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传统史诗三种文体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屈骚中别具一格的文体样式。《〈天问章句〉序》所言楚人裒集屈原零星题壁诗句辑成《天问》的说法,显然与此龃龉。
从内容来看,《天问》与一般史诗有所区别。屈原创造性地将上古神话传说和孔子笔削《春秋》以来以史为鉴的史家传统相接续,大至宇宙、细至鸟兽的自然万物与天地开辟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作者思考探索的对象。由此看来,《天问》虽具有史诗的形式,却不宜简单地称作史诗。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首探索宇宙、社会与人生奥秘的哲理诗。
《天问》全篇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屈原对有关天地万物、宇宙自然产生发展的神话传说,皆持严肃的怀疑态度;对社会历史、善恶是非等问题,也以深刻的理性思索待之。”〔34〕《天问》对天地万物等自然现象和历代兴亡等历史教训的描述和体察,与古代相关专门著作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往往深刻得多。〔35〕对哲理的阐发,屈原往往通过素材的捡选和安排来实现。篇中有关禹的记述,很具有代表性。
先秦文献所记述的禹有三种形象。在《天问》中,屈原分别在两处描述了禹的创世神和半神英雄形象,借以表达不同的历史哲学内涵。《离骚》所极力推崇的禹的先圣王形象,在《天问》中则未有述及。这种选择和安排,服从于《天问》历史和哲学的思辨,显示了大匠调动细节的非凡功力。〔36〕
在对传统文献样式的利用和改造方面,《天问》是一则经典的成功范例。《文心雕龙·辨骚》篇言:屈骚诸篇“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37〕《天问》这篇皇皇巨作为屈原精心构筑,绝非作者临时起意的涂壁之作,更不可能由他人裒辑零句拼凑而成。
《天问》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为古人所许。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38〕太史公的惺惺之意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理解。钱钟书《管锥编》认为,《天问》煞尾部分“冷淡零星,与《离骚》《九歌》之‘伤情’、‘哀志’,未许并日而语”。他又说,“苟马迁只读《天问》,恐未必遽‘悲’耳”。〔39〕钱氏此说,似未注意到屈骚诸篇系通过不同的文体形式,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从不同层面来表达相类的意愿与志趣。《离骚》为抒情诗,情感充沛而表达外显。《招魂》作为屈原首创的赋体作品,奇伟谲诡而寄意深广。《哀郢》等篇则于纪行叙事中杂以愤懑的抒发。《天问》是史诗式的哲理诗,在这篇作品中,深刻的哲理和强烈的情感通过史诗的外在形式,寄寓了作者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
有关《楚辞章句》的学术传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40〕据此可知,王逸对《楚辞》文本的训释及各篇本事的索隐皆可能承有前人旧说。然《楚辞章句》于词语的训释方面虽然相对可靠,对诸篇本事的推断则疑问较多。就《天问》创作而言,屈原至宗庙而“因书其壁”,或有其实。但楚人“因共论述”,纂成全部之说,显然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学者探索屈骚诸篇本事与屈原事迹之间的关联时,多注目于作品的内容,本文进一步证明了,对诸篇形式的分析是屈骚创作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切入点。〔41〕
注释:
〔1〕〔6〕〔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第85、101 页。
〔2〕高秋凤:《〈天问〉研究》,收入《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四辑,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3〕《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春秋左传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2页。
〔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80-182页。
〔5〕关于屈原在放流中可能到过的楚国都城,前人曾多有讨论。孙作云认为,屈原所见先王之庙在楚昭王十二年所迁鄀都。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林庚、路百占持论与之相类。林庚:《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路百占:《〈天问〉发微》,《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陈子展说楚国有三处旧都。陈子展:《〈天问〉解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徐英认为在怀王之前先后有四处楚都。徐英:《楚辞札记》,钟山书局,1935年,第85-87页。
〔7〕〔19〕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 年,第54、36页。
〔8〕王从礼:《楚墓建筑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2页。
〔9〕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9年,第304页。
〔10〕徐英:《楚辞札记》,钟山书局,1935年,第85页。
〔11〕黄文焕:《楚辞听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崇祯十六年刻清顺治十四年增修本,第678页。
〔12〕潘啸龙:《〈天问〉的渊源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13〕杨雪:《重估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李学勤先生谈清华简的学术意义及对于历史文化再认识的作用》,《人民政协报》2013年5月20日。
〔14〕毛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5〕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页。
〔16〕〔33〕〔35〕姚小鸥:《〈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原》,《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17〕王世贞说“《天问》虽属《离骚》,自是四言之韵。”王世贞著:《艺苑卮言校注》,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第68页。
〔18〕〔4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517、1267页。
〔20〕吴成国、彭忠德:《屈原〈天问〉的史学价值论析》,《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
〔21〕〔37〕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
〔22〕傅道彬认为,曾在楚地流传的《诗经》中之《大武》亦具有史诗的性质。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中华书局,2010年,第71-72页。
〔23〕李山:《〈诗·大雅〉若干诗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24〕徐元诰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483-486页。
〔25〕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26〕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27〕苏雪林:《天问正简·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8〕《尚书正义》,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18、138 页。
〔29〕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154、12页。
〔30〕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第64页。
〔3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第167页。
〔32〕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34〕郭杰:《论屈原艺术想象的独创性》,《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36〕姚小鸥、孟祥笑:《“文义次序”与〈天问〉中的禹》,《山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38〕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3页。
〔39〕钱钟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929页。
〔41〕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姚小鸥、孟祥笑:《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学术界》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