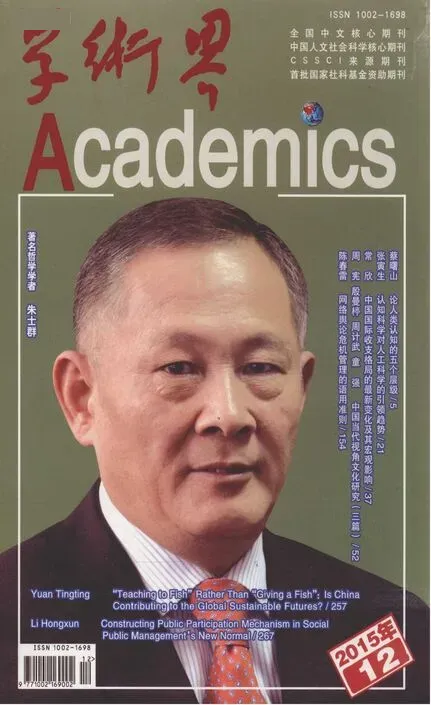艾略特精神求索的两重性〔*〕
2015-02-25刘孝梅
○刘孝梅
(安徽大学 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艾略特曾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的方式。”〔1〕《荒原》中,艾略特以非凡的“敏感和意识”、创新的表现方式表达了其独特的“感受性”。《荒原》当然不可能仅是诗人对个人生活的琐碎发泄,这些“有节奏的牢骚”背后的真意值得探究。
一、从诗歌内在神话结构视角看:死亡与重生交错
《荒原》(1922)发表以后,所受争议颇多、褒贬不一,支持者赞扬它是现代主义的模本,反对者则斥其为一场巨大的灾难,对其“浮夸的博学展示及缺乏统一的内在结构”〔2〕甚为恼怒。但《荒原》结构的破碎、语言的凌乱却恰是诗人刻意苦心经营的结果,诗人大量运用拼贴、隐喻及象征等诗歌技巧,对现实进行分解、扭曲和再重组,以反映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此外,诗人还以不同的诗歌媒介来表达意义,从而使“许多印象和经验以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3〕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下称《情歌》)中,布朗宁的戏剧独白作为媒介,似“一盏幻灯”将普鲁弗洛克优柔寡断的“神经变成图案投射在屏幕上”。〔4〕《荒原》中,艾略特以乔伊斯发明的“神话方法”代替叙述的方法,“用神话,在现代和远古之间巧妙地达成一个持续的平行状态……,这是对现代历史的虚无及混乱的一种控制、安排,并赋予其形态和意义”。〔5〕这种神话方法也是诗人“历史意识”的体现,“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6〕大量人类学、神学和神话原型等远古意识作为诗歌的隐形结构使古今相融,诗歌人物得以在重叠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四处奔走、上下求索,诗歌所表达的主旨更具历史的普遍性,而神话结构所蕴含的“死亡与再生”的信仰,则反映了精神信仰求索的双重性。此外,《荒原》还融入了来自于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宗教故事,它们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如评论家所言的“宗教拯救”,这些宗教故事同样也蕴含“死亡与再生”的信仰。借耶稣“死后再生”、圣杯传说以及远古繁殖神话中的生死辩证,人类精神救赎的困惑、矛盾及渴望得以客观呈现。
《荒原》题辞以先知西比尔对死亡的渴盼奠定了全诗“死亡与再生”的基调,结合耶稣“死后再生”、圣杯传说等,基督教的原罪——灵魂的赎罪——死亡再生的信仰模式被作为隐形线索植入诗歌,人类精神求索的感性与理性的交织在生与死的循环往复中体现,贯穿于诗歌的五个章节。如“他过去活着的现在已经死亡”,〔7〕影射耶稣的被捕及遇害情节,以耶稣之死暗示灵魂的赎罪和净化,为荒原人的重生埋下了伏笔。但在“去往以马忤斯旅程”一节,已经复活的耶稣“戴着兜帽悄悄行走”在世人身旁却没被认出,彰显出荒原人对道德传统的背离和信仰追索之路的渺茫。除了传统的基督教,艾略特还将东方佛教及宗教文化中的不死鸟传说、涅槃及轮回等引入诗歌以表达主题。如《火诫》中,一系列有欲无爱的男女情爱,如同“一只充塞着形形色色邪恶的性爱的大锅”,荒原人有可能脱离这无尽的欲海获得精神的救赎吗?佛教《火诫》中佛陀对门徒的布道“燃烧吧,燃烧吧”〔8〕似乎指明了一条拯救之途:只有用圣火烧毁感官的欲望,现代人才能脱离轮回达到精神的涅槃。但丁炼狱中的灵魂为了洗罪主动接受苦难,而已经抛弃了西方核心基督教文化的现代人,却在无尽的欲望中沉沦挣扎,惧怕净化的烈火,靠其自身的自律去获得灵魂的拯救令人生疑。此外,艾略特还从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中再觅出路,雷霆的布道“给予、同情和克制”的智慧能否拯救人们?荒原人却只能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的降落。总之,诗人以三大宗教文化所蕴含的生死辩证作为其思想表达的手段,在死亡与重生的交错中表现了现代人信仰缺失的苦痛,拯救希望的渺茫及重建基督教文明的期望。
维斯顿的《从祭仪式到传奇》中的圣杯传说和弗雷泽《金枝》中的繁殖神话记录了古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死亡与再生意识同样反映了人类精神信仰的上下求索。圣杯传说讲述了渔王因病致使国家变成不毛之地,渔王与荒原的拯救完全依赖于一名骑士历经艰辛前往神秘的教堂索取圣杯。与渔王传说平行并置,艾略特在诗中也描绘了一幅地旱树枯、空虚死寂的现代荒原以及一群虽生犹死的现代渔王。圣杯传说的结尾,抵达教堂象征着与死神的邂逅,是“一场超自然力量和邪恶力量交锋的冒险”,〔9〕帕西法尔骑士历经磨难最终到达教堂并获得了圣杯,而《荒原》中,骑士看到的教堂却空无一物,“只是风的家”,〔10〕寻杯旅程的高潮就这样以绝望告终。背对荒原孑然“垂钓”的渔王不禁自问——“我是否至少该把我的国家整顿好?”,〔11〕“至少”二字透露出对精神救赎既畏葸不前又心存希冀的矛盾心理。此外,人类学著作《金枝》中所包含的繁殖神话中,古繁殖神的死亡和再生与植物的荣枯、土地的肥瘠密切相关,所以人们每年会把繁殖神吊死、埋葬或投于水,以期来年复活泽披大地。“去年你栽在你花园里的那具尸体,/开始发芽了没有?今年会开花吗?”〔12〕在死亡的漩涡中挣扎的荒原人,必须像繁殖神一样经死方生,然而“狗”和突降的“霜冻”却令荒原人再生的希望又被延宕。通过在诗歌中多处影射“死后再生”的繁殖神,如“被吊死的人”、腓尼基水手弗莱巴斯等,艾略特意在以死亡与再生的循环呈现人类自古以来的这种“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的艰难求索,《荒原》反映了“一种人生的状态”。〔13〕
神话宗教故事中的生死循环作为诗歌骨架,连接起现实生活与历史传统,虚实结合,使诗歌无序中潜存秩序,赋予现代人的荒原求索以历史意义,突破了前期诗歌的局限,使得精神求索的主旨上升到了普遍性的高度。
二、从意象语言营造视角看:绝望与希望并存
依托诗歌的内在神话框架,诗人在古今自由驰骋、剪接碎片,使得诗歌语言碎片化呈现。诗人曾明确表明要“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14〕即为了表现无序的现实,诗歌语言必须更加隐晦、精练,更具暗示力,而这些碎片通过暗喻、对比和衬托等技巧融入诗人的哲思成为其“客观对应物”的主要来源,有力地表现了人类精神求索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矛盾情感。在《哈姆雷特及其问题》(1919)一文中诗人首次提出“客观对应物”理念,“以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就是找到传达那种特定情感的一组物体,一个场景,一串事件;要做到感官体验中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相应的情感即刻被激发”。〔15〕该理论继承了17世纪玄学派诗歌、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等传统及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庞德将意象定义为“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16〕艾略特认为意象能激发起的“相应的情感”指的就是庞德的“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但他对庞德的意象定义也有推进,即他明确定义了意象是什么——一组物体,一个场景,一串事件,是存在于感官体验中的外部事实。“客观对应物”论也与诗人的“非个性化”诗歌理念紧密关联,即诗人认为诗歌的目的“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17〕但是,艾略特所要表达的“非个性”并不是世人所理解的逃避个人感情,而是如何将个人的情感提升到非个人化的高度予以表现,“客观对应物”即是诗人用来实现诗歌情感普遍化的工具。《荒原》中,各种自然意象、城市意象、人物意象和典象等突兀并置、堆叠穿插,在艾略特独具匠心的意象语言的多重组合下,实现了激发“相应的情感”的目标,表达了人类精神求索的矛盾冲突。
从诗歌的整体意象思维而言,《荒原》突出的成就是采用多重叠象,如意象并置、叠加、对比以及辐射式意象等将过去现在、真实虚幻糅合,使远古神话中的荒原重新脱胎。诗歌以“荒原”为主导意象,其它众多的意象围绕它扩展,且诗的五个章节又分别有其中心意象,每一个诗章再以中心意象为轴,辐射出众多的意象,构成一个结构复杂统一的意象整体。这一系列意象以死之绝望和生之希望为主线,集中展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格异化的现代人精神求索的空间,而生死并存的空间又体现了人的生存状态。诗中的意象组合最突出体现为完全不加解释的意象并置,比如,“紧紧拉直长发的女人”“向黑墙俯冲的蝙蝠”“空中翻滚的高塔”“缅怀往昔的报时钟声”和“空虚的水池和枯竭的井低唱出的歌声”几个意象的粘贴表面互不相容,但却营造出神秘忧伤、怪异惊悚的氛围,凸显出现代人的空虚异化、生活秩序的丧失,但绝望中又隐隐透出冲破阻碍恢复往昔的憧憬。此外诗人还采用意象叠加——以一个或多个意象去衬托、复现需着力表现的中心思想,如对于雷霆的“给予、同情和克制”的抽象布道,诗人以一系列蕴含生与死的意象叠加予以客观呈现,将讣告和墓志铭上的蛛网叠加来表达若舍弃了道德信仰,人们将至死也无法寻回;监狱和钥匙的叠加则体现了唯有“同情”这把钥匙才能开启每个现代人的心狱;船儿与划桨的手的欢快应和表达了只有克制无尽的欲望,生命之舟才能迎风前进。总之,以死亡与再生为主线,诗人将各种场景、事件、典故和引语等意象语言有机组合,使形而上的人类精神的上下求索得以具体化、客观化。
对比性意象的悖论统一也是《荒原》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如人物意象间、动物意象间以及凸显主题的生与死、水与火的对比等。此外,诗人还从宗教神话及但丁《神曲》、莎翁戏剧等作品中大量撷取典故与现代经验相叠合以形成典象,增强了意象的多义性和表现力,隐喻了精神求索衰微与希望并存的矛盾冲突。
与前期诗歌受意象派和玄学派影响意象多清晰硬朗、神秘拼贴相比,《荒原》中,艾略特旁征博引,在组象上更偏重于艺术技巧的拓展,构建了更为宏阔、极具包容性的“客观对应物”,除各种事件、戏剧化场景、典故和引语等外,典象的大量运用,使得诗歌意象呈现丰富的象征内涵。此外,艾略特继承象征主义的暗示和隐喻特征,在意象语言表现方式上堆叠、拼贴、交叉和辐射等,有效反映了现代经验的混乱无序和纷繁复杂,在意象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启了现代主义诗歌的新特征。
三、从诗歌的叙说视角看:黑暗与光明交织
在《诗歌的三种声音》(1953)一文中,艾略特指出诗歌有三种声音:第一种是诗人对自己或不针对任何对象说话;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说话;第三种是诗歌的声音或诗剧的声音,即诗人通过不同的诗中人物来发声。《荒原》正是诗人这一批评理论的实践,诗中有纷繁驳杂的人物声音,还有诗人的或诗歌的抒情声音,也有非人类的夜莺、雷霆以及来自于文学作品的声音,各种声音突兀转折,飘忽来去,引领读者步入《荒原》却又迷失其中,这些声音正是了解本诗主题的重要途径。艾略特早期接受了英国理想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的唯我论,即从“我”出发来看待世界,《荒原》中,他选择的“我”是泰瑞西士。“泰瑞西士虽然仅是一个旁观者,不是戏中‘角色’,却是本诗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贯穿其它所有人物”。〔18〕的确如诗人所言,自称“跳动在两个性别之间”〔19〕的泰瑞西士作为中心叙事者,集合了诗中所有人物的特征,连接起诗歌的叙述结构,串联起一系列凌乱无序、突兀交织的声音并赋予其意义。此外,泰瑞西士还是预言者,他“所见到的,也就是本诗的内容实质”。〔20〕因此,泰瑞西士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串联诗歌的叙事上,还体现在他身份的两面性。一方面,所有的人物都是泰瑞西士,“他们的作用不在于表现自己,而是表现客观状态”,〔21〕所以《荒原》中的衰败堕落不是个体的悲哀,而是普遍的人性。虽然“早已经经受过”荒原人的一切苦痛,但像其他个体求索者如渔王、诗人等一样,泰瑞西士却无从解救。另一方面,泰瑞西士又肩负起预言者的使命,尤其在诗章最后与雷霆融合,以预言者的身份将人不能言说的,通过预言者的警示之声来表达,如“人之子”“我,泰瑞西士”及“请细思弗莱巴斯”等。泰瑞西士角色的两重性反映了人类精神求索的两面性,感性使人沉沦于无尽的欲望,理性又试图冲破泥淖,分裂为人、神的泰瑞西士是人类精神救赎的人格化,是诗歌主题思想的隐喻者。
从诗歌第四章《死于水》开始,诗歌的叙述从激进中平静下来,表达了对死亡和黑暗的平和接受,先知的预言不再是我们必将归于尘土的“一把尘土中的恐惧”,只是语气平和、不动声色地规劝警醒世人戒除贪欲。随着诗歌的推进,泰瑞西士在最后一个诗章与先知雷霆合而为一。《雷霆的话》是艾略特自认为写得“最好的部分,而且是唯一验证全诗的部分”,〔22〕错综复杂的语言碎片减少,叙述也不再假借各种假面(persona),仅以雷霆形象及其话语去“验证全诗”。诗人将耶稣复活、圣杯传说、东欧衰败与雷霆话语组合,再次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杂糅并置以供抉择。艾略特自己甚为满意的“水滴之歌”应是诗歌的声音或诗人的声音,遍地岩石、滴水全无的荒漠之旅中,一个诗歌的声音反复念叨盘桓着生命之水,从岩石想到岩石中的水洼,到“水的滴答声”,直至幻听到松树上画眉的歌唱,最终,“但是没有水”,〔23〕一语成谶,本节生动再现了心灵求索的饥渴和绝望。但是耶稣毕竟已经复活,骑士也已到达了教堂,所有人物的徒劳抗争结束,雷霆顺理成章开口布道,以其隆隆之音最终统一了先前扭曲混乱的声音,包括人格分裂的泰瑞西士在内,弱化了诗歌中黑暗阴郁的氛围,但轰轰雷响之后,却未见渴盼已久的降雨。领悟雷霆的“给予、同情和克制”的布道,荒原会起死回生、光明会重回大地吗?诗歌末尾,诗人从人物的面具后走出直接发声,自比为拥有巨大信念的阿基坦王子,渴望似燕子般自由发声,但须臾又变成装疯的希罗尼摩,无法完成意义的追寻,也许正如诗人在《四首四重奏》中所言之“向下的黑暗”才是光明。
《荒原》开拓了诗歌的叙述视角,以泰瑞西士为全能叙述,通过他的意识流动使时空流转,最大限度地超脱了时空对人的视角的局限,在诗歌文本中融汇了各种角色、各种声音,展开了一幅现代荒原的全景,无论是作为现代荒原上的集体求索者或神话传说中的个体求索者,他的精神求索历程都以痛苦失败告终。整首诗以泰瑞西士的意识流动完成了一段对生命意义探索的历程,诗歌精神信仰的求索主题达到了客观性和非个人化。但贯穿全诗的先知的声音总是在死亡萦绕的诗行若隐若现,于绝望混乱中透出一丝希望,泰瑞西士的生命状态就是人类精神求索本质的客观化体现,即永远徘徊在堕入黑暗和追求光明的循环往复中。艾略特曾说《神曲》使“人类情感在深度和高度上达到了极限”,〔24〕《荒原》以叙述方式的革新也潜入了我们心灵深处很少探寻的层面。
注释:
〔1〕〔4〕〔7〕〔8〕〔10〕〔11〕〔12〕〔18〕〔19〕〔23〕陆建德主编:《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导言首页,第8、98、96、101、103、83、108、91、99页。
〔2〕Grant,Michael.T.S.Eliot: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1.London:Routedge & Kegan Paul,1982,p.151.
〔3〕James Olney.T.S.Eliot.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88,p.146.
〔5〕Jewel Spears Brooker.Mastery and Escaply.University of Massachussetts Press,1994,p.142.
〔6〕〔17〕〔24〕陆建德主编:《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诗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11、343页。
〔9〕James E.Miller,Jr.T.S.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Exorcism of the Demons,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124.
〔13〕李俊清:《艾略特与〈荒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14〕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15〕Eliot,T.S.“Hamlet and His Problems”.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Ed.Hazard Adam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1992,p.766.
〔16〕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20〕James E.Miller,Jr.T.S.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Exorcism of the Demons.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118.
〔21〕郑敏:《从〈荒原〉看艾略特的诗艺》,《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第18页。
〔22〕James E.Miller,Jr.T.S.Eliot’s Personal Waste Land,Exorcism of the Demons.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