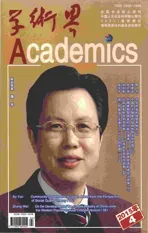文人画的“逸品”意识——中国古代画的庄禅意蕴
2015-02-25孙延利
○ 孙延利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中国古代画史中,自晚唐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逸品”意识,与此前的“写形”传统一并发展,经宋至元,经过米芾、倪瓒等人的实践,黄休复、邓椿等人的理论总结,“逸品”终成一独特意识,与“写形”传统双峰并置。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论者谈论的多是逸品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对逸品意识的探讨并不多。本文从“逸”的内涵入手,着重探讨逸品意识形成、发展及其背后的原因,以考察古代绘画史是如何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逸品意识。
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逸品只存在于文人画中,在画工画中是无所谓逸品的。逸品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画论中,始于晚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但这个概念的形成,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先秦典籍中已出现“逸”字。《国语·晋语五》说:“马逸不能止,三军从之”。〔1〕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逸”的解释是:“逸,失也;从辵兔,兔谩訑善逃也”。〔2〕《国语》中的“逸”是其本义,逃跑、逃逸的意思。段注对“逸”作注:“亡逸者,本义也。引申之为逸游、为暇逸”。〔3〕逸游、暇逸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个方面是说逸乐之游,指闲适、安逸的享受,此引申义多贬义,《战国策·楚四》说:“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4〕另一个方面是指摆脱世俗羁绊后的清闲,有隐逸、隐退的意思,此引申义多为褒义,《论语·微子》有:“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5〕何晏《集解》说:“逸民者,节行超逸者”,〔6〕“逸”又增加了一个引申义,即超逸、超绝的意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7〕在论者眼中,“逸”褒义居多,典型的例子是徐复观,他结合《论语·微子》和何晏《集解》所说的“超逸”,认为“逸”有高逸、清逸和超逸的意思。〔8〕逸品中的“逸”字,也取其褒义,大致有逃离世俗、安闲、隐退、超绝之意。
从六朝开始,“逸”字逐渐用在文艺批评之中,作为审美鉴赏的一个标准,如《梁书·武帝本纪》所说的“六艺备闲,棋登逸品”,〔9〕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说的“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10〕到唐初李嗣真《书后品》中,第一次将“逸品”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敻绝终古,无复继作。”〔11〕《书后品》是相对于南朝梁代庾肩吾的《书品》来命名的,《书品》将书法家按成就高低分为九品,《书后品》则在九品之上,另列逸品,登逸品者共五人:李斯、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对照《书品》,没有李斯,王献之列上中品(即第二品),其他三人均列上上品(即第一品),这样看来,李嗣真基本上沿袭了庾肩吾的看法,只是为了突出二王等人成就高出一般书法家,才单列逸品。朱景玄作《唐朝名画录》时,便吸收了李嗣真的“逸品”,将其放在神、妙、能三品之后,作为神、妙、能系统之外的一个类别:“以……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优劣也。”〔12〕并将王墨、李灵省、张志和三人列为逸品。朱景玄虽然没有明说逸品与神、妙、能三品之间的优劣关系,但显然还是比较推崇不拘常法的逸品。
朱景玄之后,画论中对逸品的论述逐渐多起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北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他首次对逸、神、妙、能四个概念做了明确说明,并将逸品(逸格)置于神品(神格)之上:
逸格: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形具简,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神格: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13〕
从黄休复的论述看,“神格”是在“应物象形”范围内的“妙合化权”,“逸格”则超出了“应物象形”的范围,不求形似,只用简笔勾勒传达出画者心中的自然之情,由于侧重画者内心而不注重外物的形似,所以“出于意表”。黄休复的观点经过苏轼、苏辙兄弟的推崇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轼首次区分了文人画(士人画)和画工画(院体画),他发起的文人画运动影响了很多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旨趣和画法不同:一追求意趣,侧重写意;一追求物趣,侧重写形。侧重写意的文人画似乎天然地与逸品有内在契合之处。苏轼本人也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14〕之类的话。苏辙则在宣扬黄休复观点的同时,明确指出逸品在画中的品格最高:“予昔游成都,唐代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有四格,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15〕经过苏氏兄弟的推崇后,逸品的地位得以确立,这给宋代文人画乃至整个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文人画的审美趣味。
逸品地位确立以后,以前由于重视写形而轻视的一些画作,又得到了重视。沈括所说的“淡墨轻岚为一体”〔16〕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情况。“淡墨轻岚为一体”说的是五代南唐人董源和巨然的绘画特点,二人在五代和宋初,地位并不高,但沈括说他们“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17〕米芾也说董源“格高无与比……皆得天真”。〔18〕沈括所说的话与黄休复对逸品的界定如出一辙,都强调简笔,都强调出于意表。米芾本人就是大画家,被公认为逸品的两大画家之一(另一个是元代的倪瓒),画作的显著特点则是墨戏云山,这和董源的画很像,所以有人说沈括所评论的董源的画,其实是米芾“托古改制”的产物。〔19〕不论情况如何,至少说明米芾对逸品的追求有一种自觉意识。正是由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提倡和坚持,逸品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为一种审美趣味,文人画才得以蓬勃发展。
逸品的另一大家倪瓒既师法董源,又吸收了赵孟頫的笔法,在披麻皴的基础上,自创“折带皴”,将董源的平淡风格变为寂寥和枯瘦。和米芾墨戏云山的点染不同,折带皴需要以较高的书法造诣为基础,皴法的笔墨是书法性的笔墨。倪瓒对逸品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逸笔”说和“逸气”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20〕“写胸中逸气”是他作画的技法及追求。由于倪瓒的贡献,逸品在文人画乃至中国画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
二
逸品是一种“品”,《说文解字》对“品”的解释是:“众也”,〔21〕由此引申为种类、品格、等级(名词)之义,又有品评、品藻(动词)之义。逸品的形成,与人物品藻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有“举孝廉”,品人以德为首;东汉末年曹操则推行“唯才是举”,用人以才为首;三国时刘劭则强调“人物之本,出乎情性”,〔22〕转而以精神面貌来论人。重德、重才、重精神面貌,都是人物品藻的不同标准。《汉书》则开启了“九品论人”的先河。《汉书·叙传》说:“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23〕将经书中的人物分为九等,以古喻今。曹丕则在州县中设中正官,按才能将士人分为九等,作为朝廷用人之参照,这种“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南北朝。由于以品论人在三国时就已成为一种制度,到南北朝时由于清谈的盛行,更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于社会风气的浸染,人物品藻对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艺术门类都青睐于以品论艺,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品”论画,用“六法”来品评画家的优劣,画家由此被分为六品;南梁钟嵘的《诗品》以“品”论诗,用上、中、下三品来品评诗人的优劣;南梁庾肩吾《书品》以“品”论书,用上、中、下三等中分别又区分出上、中、下三品,共九品来品评书法家的优劣。
就画论而言,谢赫的《古画品录》的以“六法”品评画家,首推“气韵生动”,并没有用“逸”来立品。画论中以“逸”立品始自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朝流行的是用张怀瓘的“神、妙、能”体系来品画,到晚唐时出现了不少水墨山水画,朱景玄觉得这些画难以纳入“神、妙、能”体系之中,于是另立“逸品”,作为“格外”之“不拘常法”。从他的论述看,逸品不完全是就画作本身而言的,还涉及到画家的人品。他所列的逸品有三人:王墨、李灵省、张志和。王墨“多游江湖间……性多疏野,好酒……醺酣之后,即以墨泼……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王墨的泼墨作画,与他的好酒有关,他的好酒与他的性格“疏野”有关,与他的“多游江湖间”的经历有关。李灵省“落托不拘检……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重……一点一抹……得非常之体,符造化之功”。李灵省的点抹作画,与他的傲然自得的个性有关。张志和“常钓于洞庭湖……高节”,能依文赋象,“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24〕从朱景玄的表述看,王墨、李灵省、张志和的共同特点是不拘礼法、不与世俗为伍,而这些特点似乎正是导致他们的画作成为与众不同的“逸品”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逸品在朱景玄这里,是只定品性不分品第,朱景玄的贡献是在画论史上开启了以“逸”品画的先河,很多论者由此形成了一种明确的“逸品”意识,同时,这种意识不再是只定品性不分品第,而是有明确的品第观念。黄休复推崇逸品姑且不说,即使是推崇法度、重视形似的宋徽宗赵佶,也有明确的“逸品”意识。他确立的品第次序是“神、逸、妙、能”,和黄休复的“逸、神、妙、能”的差别仅在于神品和逸品孰优孰劣,逸品仍是他心目中仅次于神品的品第。南宋邓椿作《画继》,竭力推崇苏轼等人的文人画,对唐宋以来的“逸品”流变加以考察,并以“狂”的程度为标准,将“逸品”本身分为逸格之极(狂怪)、逸格之可(狂肆)、逸格之卑(无所忌惮)三个等级,逸品绘画艺术观得以确立,并产生持续影响。到明代董其昌,更将文人画比作禅宗之“南宗”,奉逸品为画品之首。
“逸品”意识不仅存在于画论中,在画家心中,同样也有一种“逸品”意识。当然,很多画论家同时也是画家。画论家侧重理论的梳理和总结,画家侧重作画时的意趣和技法。赵佶本人即是绘画高手,他虽然不推崇逸品,但推崇逸品的画家却大有人在。苏轼以“墨戏”作画,引领了以写意为宗的文人画的潮流,使得“墨戏”一度成为“逸品”的代名词。与王墨等人相似,苏轼也喜欢酒后作画,米芾《画史》记载,元丰五年,“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25〕苏轼酒后作画,与其逸品意识有关。黄庭坚《东坡居士墨戏赋》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筿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夫惟天才逸群,心法无轨,笔与心机,释冰为水。立之南荣,视其心中,无有畦畛,八窗玲珑者也。”〔26〕所谓“天才逸群”“无有畦畛”等等,是说苏轼有超绝世俗、不因贬谪而抑郁的清逸之气,正是这清逸之气才使他形成“心法无轨,笔与心机”的逸品意识。元四大家之一的黄公望虽然一度以卖画为生,但非常强调画作品位,有清高之气。他的《富春山居图》乃水墨杰作,画中山石以枯笔勾勒,远山用淡墨抹出,林壑蜿蜒中见开阔境界和博大胸怀,全无一点俗气。去俗可说是黄公望的自觉意识,他在《写山水诀》中引《辍耕录》之语:“作画大要,去邪、甜、俗、赖四个字”。〔27〕正是依靠自身的清高之气,使黄公望形成了“去俗”的逸品意识。
综上所言,可得出如下结论:就逸品意识的形成而言,最初是王墨等人创作出逸品,但这些画家并没有明确的逸品意识;作为画论家的朱景玄在总结王墨等人画作的基础上,提出了“逸品”这一概念。此后的画家和画论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阐发,或是通过创作使“逸品”在形象上具体化,或是通过阐发使“逸品”在理论上明晰化。换言之,是论者先有此意识,而后画者才有此意识。逸品意识的形成,既离不开画家的实践,也离不开画论家的归纳,正是在画家和画论家的共同努力下,逸品意识才得以形成并逐渐成为文人画的主流意识。
三
逸品不仅仅是画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画的品第问题,它背后涉及到的是画者的心态问题,如果没有一种超绝世俗的清逸精神,没有一种“逸品”意识,很难画出逸品的画。逸品意识的形成,直接的原因是画家的文人情怀和时代的审美风尚。
文人情怀有很多种,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但逸品意识的形成,与这些积极入世的文人理想无关,而是与文人的审美情怀有关。审美,既关乎现实又超乎现实,所以逸品画作中虽然能看到现实的影子,但看到更多的则是影子背后的心灵世界。正是由于对画家人品和精神世界的关注,画论家才用“逸品”来定位画作的审美品格。通过逸品,可以看出画家的文人情怀。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隐逸。最先用逸品来品画的朱景玄,认为逸品有三家:王墨、李灵省、张志和。这三家中,王墨和张志和都有隐逸之举,王墨并不是他的真名,只是由于他善于“泼墨画山水”而得此名,他“多游江湖间”;张志和则退隐洞庭,“号烟波子”,常常自得其乐地在洞庭湖钓鱼。由于他们多少有些避世,因而行为有些异常。《宣和画谱》卷十说王洽(即王墨)作画,“必待沉醉之后,解衣磐礴,吟啸鼓跃,先以墨泼图幛之上……”〔28〕《新唐书·张志和传》谓其“善图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成”。〔29〕张志和的举动一般人或许可以接受,只是有点异常而已,王墨的举动在一般人看来只能是怪诞了。异常或怪诞,都是由于他们有隐逸的心态,不需要考虑世俗的眼光能否接受自己。正是由于这种心态,他们可以不拘常法,画出朱景玄所说的逸品。黄公望在因张闾案入狱之后,息却入仕之心,也在富春江边隐居起来,闲云野鹤,才能画出《富春山居图》那样的逸品。
二是旷达。旷达不需要隐逸,旷达之士仍生活在世俗之中,但心胸开阔,不为俗事所困扰,通达而悠然。苏轼是典型的例子。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形成了他旷达的情怀。在院体画盛行的时候,他提倡文人画,通过对文与可画竹的分析,指出超越“常形”达到“常理”的途径,提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30〕之说,强调真性情对画作的重要性。一个在官场上跌打滚爬的人,如果没有旷达的情怀,很难不被主流的院体画观念所束缚,但苏轼能跳出这一流行的观念,在前人逸品理论的基础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文人画运动。运动声势浩大,并不是他积极策划的结果,而是由于他在文坛和画坛的影响以及他的人格魅力而引发的结果。对他本人来说,他只是以旷达之情来对待一切。院体画于他而言,无可无不可,只要能传神就好,而传神又与主体性情有关,他因而提倡注重主体性情的文人画。他自己的画作虽然不是很多,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追求与他的旷达一起,使他的画作有一股超逸之气。
三是孤独。孤独和隐逸、旷达均不同,隐逸者未必孤独,他可以以山水为伴,旷达者无需孤独,他可以生活在尘世中。孤独者即使不隐逸,但由于清高而不愿与世俗为伍,又由于孤僻而知音难觅。倪瓒在50岁左右,对世事倍感失望,产生了深沉的孤独感,加上他有严重的洁癖,养成了孤僻狷介的性格,53岁时,更散尽家财,发出“壮心千里马,归梦五湖波”〔31〕的感慨,隐入太湖深处。正是这种孤独冷寂的情怀,使他的画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冷峻的“逸气”,《松林亭子图》《容膝斋图》等名作,共同的特点是:笔墨简约,几棵枯树,一个茅亭,空灵中带有寂寞,沉静中带有孤独,给人一种地老天荒式的清冷之感,折射出画家的孤独和无奈。这种孤独和无奈,使画作呈现出一种孤高的清逸品格。
隐逸、旷达、孤独的文人情怀,使逸品画家具有超越凡俗的“高”和与众不同的“逸”,成为一般人眼中的“高人逸士”。但“高人逸士”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唐时逸品的出现以及宋、元时期涌现出大量的逸品画家,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有直接关系。
唐代绘画总体上讲究“真”,因而“不拘常法”的逸品地位并不高,逸品画家也不多。《唐朝名画录》录画家124人,列逸品者只3人,且放在最后。唐朝是绘画艺术繁荣的时期,唐人对绘画艺术不断探索,除了对吴道子以来的“笔法”进行全面探索外,还有一个突破性的创造:即墨法的运用,从水晕墨染到泼墨,逐渐形成作画的方式。王墨的逸品显然就是在墨法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就绘画的审美风貌看,唐人重视“以形传神”,神虽然是针对“写形”画而言的,但重视画作之神,很容易让人接受画家主体之神,这就涉及到画家的精神境界,这样看来,“‘格外逸品’虽不合法,但在深层意义上却更合‘理’;虽不斤斤于‘形似’,但却更讲究‘神意’;乃至虽不突出‘技术’,但却更能见其‘人格’——这是处于‘格外’之‘逸品’所以成立之观念依据”。〔32〕逸品代表了唐人新的审美风气。
到宋代,逸品观念已经确立,由于沈括、米芾等人推崇董源、巨然的“淡墨轻岚为一体”,也由于“淡墨轻岚”符合士人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山水画逐渐形成了以“逸”为主的审美倾向。在这种倾向下,以“写意”为特征的“徐熙野逸”的花鸟画也打破了此前以写生为特征的“黄家富贵”的花鸟画的垄断地位,徐熙的花鸟画重笔墨,不重形似,与黄筌写生传神、富贵气十足的花鸟画形成鲜明对照。随着受徐熙影响的崔白等人入主皇家画院,“徐熙野逸”显露头角,花鸟画也逐渐形成以“逸”为主的审美倾向。人物画方面,出现了梁楷的简笔写意人物画,和此前的“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以及“周家样”仕女人物画相比,写意人物画显然受到逸品观念的影响,人物画领域也出现了以“逸”为主的审美倾向。需要说明的是,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的“逸品”意识,与苏轼发起的文人画运动都有关系,由于文人画的兴盛,才使得符合士大夫审美情趣的逸品得以盛行。
元代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重视佛、道而轻视儒学,甚至废除科举,让很多文人士子报国无门,倍感压抑,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这给文人士子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无法解脱的苦恼和困扰,二是悠然自得的闲散心态。前者使他们趋于归隐,或隐于闹市,或遁迹山林;后者使他们寄情书画,自娱自乐。元四大家可为代表。黄公望早年热衷于功名,失意后专意于画,并隐居富春山;吴镇禀性孤耿,终生不仕,家虽殷富,却以卖卜为生,且有渔父情结;王蒙虽混迹官场,也弃官隐居黄鹤山,纠结于出仕与退隐之间,画了很多隐居图;倪瓒如上文所说,曾隐居太湖。就元四家画作来看,除王蒙不够超脱之外,其他三家均高洁雅致,很少烟火气息,以倪瓒为最。王蒙虽然不够超脱,但他创造的“水晕墨章”,走的也是“写意”的路子。看来,四大家的共同特点是不求形似,以表现画家主观精神为主,这其实是在彰显一种以“逸”为主的审美风尚。由于元代很多文人画家有元四家一样的审美趣味,逸品画在元代被看作是中国画的最高品。
四
逸品意识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文人情怀和时代审美风尚,文人情怀和审美风尚的背后,还有个大的文化背景问题。具体说来,是庄禅文化的影响导致了逸品意识的产生和盛行。
庄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逍遥游精神。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指出逍遥游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33〕的忘我之游,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4〕的自在之游。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必须要无所凭藉地悠游于天地自然之中。这样看来,逍遥游主要是“游心”:“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35〕(《人间世》)、“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6〕(《应帝王》)、“知游心于无穷”〔37〕(《则阳》)等都反复强调“游心”的重要性。要达到“游心”的境界,大致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无欲,二是心斋,三是超越。画家能画出逸品,其心灵世界一般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只是不同的画家各有偏重而已。
无欲是说摆脱了现实的功名利禄之心,这是很多逸品画家的共同特点。当然,这种摆脱,有被动和主动之分。黄公望蒙冤入狱,让他看透世事,出狱后便隐居富春山,寄情山水,加入道教全真派,以出家来表示自己已看破红尘,无欲无求。在这种心态之中,他的《富春山居图》,多用披麻皴,干笔皴擦,疏朗简秀,清爽潇洒,整个画面给人一种仙风道骨之感。吴镇似乎天生地排斥世俗功名利禄,他曾说:“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回拜相,两度封侯,采菊篱边,种瓜圃内,都只到邙山一土丘。”〔38〕这几乎是庄子“游心”思想的诗意表达。吴镇自号“梅花道人”,基本上独来独往,自画自题,甚至很少从俗卖画,宁愿以卖卜维持生计,既体现出他对艺术的虔诚之心,也体现出他对世俗利益的鄙夷之心。
心斋说的是一种内心修炼的状态,一种达到无功利的审美途径,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心境。只有在“心斋”状态下,才能排除外物和内心的干扰。“心斋”与老子的“虚静”一脉相承,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39〕指出虚静通过修炼才能达到,庄子通过“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40〕进一步指出通过“心斋”才能进入修炼状态。倪瓒晚年,似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心斋”过程。由于家庭变故,他内心烦闷,只能自我修炼,经常寄居在寺庙里,“篝灯木榻,萧然晏坐”,〔41〕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发出了“白云终不染缁尘”〔42〕的飘然出世般的感慨。正是这种“白云终不染缁尘”的情怀,形成了他自己所说的“逸气”,使他的画作显得空灵无碍,“纤尘不染,平易中有精贵,简略中有精彩”,〔43〕成为逸品的代表。
超越是说超越世俗和自身的羁绊,达到一种自由无碍、随心所欲的精神境界。要做到逍遥游,超越不可少,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4〕(《逍遥游》),字面上看,是说修养高的人忘掉自己,物我不分;精神世界能超脱物外的人已经没有功利之心;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人已经不立名了。显然,庄子的超越不仅是物质上的超越,更是精神上的超越。逸品画家当然没有达到庄子所说的“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但他们一般都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超越。上文所说的吴镇和倪瓒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庄子的逍遥游区分出无欲、心斋、超越三个阶段,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其实三者基本上是裹杂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划分并不明显。无欲、心斋、超越使庄子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出世、不与世俗为伍的特立独行的色彩。逸品画家总体上也倾向于隐逸,倾向于我行我素。总体而言,庄子的超脱情怀在后世文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隐逸文化,很多文人画家在这种隐逸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避世情结,在避世中又不忘自己的人格理想,从而形成逸品画。
如果说庄子思想对逸品意识的形成是一种深层次的影响,禅宗则为逸品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契机和途径。禅宗的超越规矩、讲究顿悟与逸品意识的形成都有内在相通之处。
和传统佛教重视苦行、戒律不同,禅宗则超越了这些规矩和法度,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修行方式,强调佛在心中,追求一种“即心即佛”的境界,认为佛并不是高远缥缈的,佛就存在于平常的生活之中。逸品画家的“不拘常法”和禅宗的超越规矩如出一辙,也是打破了此前的框框条条而从心所欲。正是禅宗,给这种讲究本心、自然适意的画法提供了理论上的契机。很多逸品画家都与佛禅结下了不解之缘。五代宋初的石恪有《二祖调心图》,逸笔草草,水墨淋漓,表现出高僧玄妙深邃的禅境;南宋的梁楷参禅,《泼墨仙人图》等画作禅意浓郁;元代的吴镇晚年向佛,经常在慈云寺等地与僧人谈佛论经;晚明的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墨色层次分明,意境幽深,并以禅宗论画;明末清初的朱耷则干脆一度落发为僧,是著名的“画僧”。
禅宗的一大特点是讲究顿悟,讲究刹那间的心灵感悟,在一念之中看通问题,达到永恒,这种感悟如此奇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与传统的坐禅不同,坐禅强调的是主体意识、文化修养、思想境界的修炼和提高,顿悟强调的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在感性之中突然获得某种超越,达到妙悟的境界。逸品在两方面深受这种顿悟的影响,一是绘画观念上的影响:绘画不再是描绘客观世界,而是表达画家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突然在某个时刻洞察到了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由于对妙悟的推崇,绘画推崇写意风格,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逸品形成的根本原因,已有论者指出:“重‘妙悟’轻‘人工’的艺术趣尚是这一艺术转换的直接推动力。”〔45〕二是画家思想上的转变:当文人画家看透社会的纷纷扰扰和利益纠纷之后,突然间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开始抛弃世俗的种种诱惑,潜心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庄禅思想有相通之处,都强调逃离尘世,回归本真之心,这正是文人落拓潦倒又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倪瓒的“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46〕可说是很多逸品画家的写照。由于庄禅思想对中国文化和文人的深远影响,逸品意识在元代成为画坛的主流意识、逸品画被尊为最高品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总之,由于逸品追求的清逸、超绝之气与文人的精神追求有内在的契合性,使得逸品逐渐成为文人画的最高品,逸品意识也成为中国古代画论的独特贡献,为世界画史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注释:
〔1〕《国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2 页。
〔2〕〔2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3、267 页。
〔3〕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72页。
〔4〕《战国策》(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55页。
〔5〕〔6〕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1279、1283 页。
〔7〕陈寿撰:《三国志》(四),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0页。
〔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9〕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
〔10〕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宋刻本,第160页。
〔11〕陈思:《书苑菁华》卷四《唐李嗣真书后品》,宋刻本,第29页。
〔12〕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68页。
〔13〕黄休复等撰:《益州名画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14〕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轼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1页。
〔15〕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陈宏夫、高秀芳点校正:《苏辙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6页。
〔16〕沈括:《图画歌》,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17〕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18〕米芾:《海岳论山水画》,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19〕童书业:《五代的董源、巨然和米元章眼里的董源、巨然》,见《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2页。
〔20〕倪瓒:《清閟阁遗稿》卷十三《答张藻仲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700页。
〔22〕刘劭:《人物志》,王水校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9页。
〔23〕班固:《汉书》(十二),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1页。
〔24〕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87-88页。
〔25〕于玉安编:《中国历代美术典籍汇编》(卷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26〕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27〕黄公望:《写山水诀》,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703页。
〔28〕潘云吉主编:《宣和画谱》,岳任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2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09页。
〔30〕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苏轼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31〕倪瓒:《清閟阁遗稿》卷三《题画赠张玄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03页。
〔32〕胡新群:《逸品嬗变》,南京艺术学院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1-92页。
〔33〕〔34〕〔35〕〔36〕〔40〕〔44〕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17、28、60、294、147、17 页。
〔37〕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92页。
〔38〕吴镇:《梅花道人遗墨》卷下《题画骷髅 调寄沁园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
〔39〕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4页。
〔41〕倪瓒:《清閟阁遗稿》卷十四之《诗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703页。
〔42〕倪瓒:《清閟阁遗稿》卷八之《顺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集部·元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672页。
〔43〕王原祁:《雨窗漫笔》,清光绪翠琅玕馆丛书本,第2页。
〔45〕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
〔46〕转引自马鸿增:《“逸品”论的文化内涵》,《美术研究》1990年第1期,第3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