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中的性别秩序*
——基于对山东Q市某乡农村集市的个案研究
2015-02-24管田欣
管田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中的性别秩序*
——基于对山东Q市某乡农村集市的个案研究
管田欣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北京100872)
性别化社会转型;市场化;乡村集市女;性别秩序
集市经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农民补充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规范,传统集市基本是男性主导的场域。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的乡村集市中买主和卖主却往往都是妇女,集市变成了女性化的场域。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集市女出现了代际更替的现象。文章通过分析山东Q市某乡三代农村集市女的不同经历,探究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性别体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转型利用并再生产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及权力结构。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转型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政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集体经济模式开始解体,“户”重新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1](P131)。笔者对Q市某乡农村的调查发现,改革三十余年间,以户为单位的农村经济模式经历过多次调整,具有
明显的性别化劳动分工的特点。Q市农村妇女的集市经商正是农户为应对社会经济变迁而采取的家庭生存策略,并体现了明显的性别化分工。
集市经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农民补充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传统集市是男性主导的场域:一则“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劳动分工模式让家户外的集市经商成为男性化的劳动;二则女性居家的传统性别规范使集市购物也变成男性化的活动。但是,中国1978年改革之后的乡村集市变成女性化的场域——买主和卖主往往都是妇女。并且,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集市女出现了代际更替现象,尽管同一时期集市中可能同时存在几代人。以笔者调查的Q市某乡农村集市为例,第一代集市女出现在改革之初,也是国家颁布恢复农村集市的政策之初,集市经商作为家庭副业由妇女承担起来。第二代集市女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加速时期,农民迫切需要更多的现金收入平衡家庭支出,家庭主妇到集市贩卖商品成为贴补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进入21世纪,大量耕地变成企业厂房,进不去厂的家庭妇女再次进入了门槛更低的乡村集市以获取现金收入贴补家用。
妇女集市经商并非偶然现象,埃斯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的调研发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以妇女为主要经商者的集市[2]。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妇女集市经商且出现代际更替现象也比较普遍,至少在山东的青岛、临沂,安徽省的淮北、蚌埠,河南的开封等地①笔者访问了来自临沂、淮北、蚌埠和开封的多位受访者,他们都提起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大量农村妇女涌入集市经商,90年代人数又有增加,并且有多位受访者的母亲或其他女性亲属曾经在集市摆摊经商。,都存在这样的乡村集市经商女。集市经商成为农村妇女普遍选择的劳动模式,改变了集市的性别。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对农民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有何影响?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问,笔者于2011年1月到2015年2月期间,对山东Q市某乡的11个乡村集市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对包括集市经商女、周边村民和市场管理人员在内的对象进行访谈,并且在2011年2月同当地两位做海鲜生意的集市女一起生活、摆摊,开展参与式观察研究。调查访谈集市女共计82人,按照笔者划分的三代集市女标准将其归类:第一代集市女22人,年龄基本在60岁以上,多为文盲或半文盲;第二代集市女47人,年龄在45-60岁,39人具有小学文化水平,占到总数的83%;第三代集市女13人,年龄基本在45岁以下,4人小学学历,9人初中学历。其中已婚者69人,未婚8人,离婚5人。访问周边村落农民(包括集市女的家人和普通村民)共计67人,男性38人,女性29人,其中儿童6人。本文希望通过展现三代集市女的经历,探索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性别秩序的变与不变。
一、第一代集市女:公/私领域分离与农村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户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单位。国家肯定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各地试行,两个文件对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做了进一步强调。1979年9月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肯定“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参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载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989页。[3](PP967-968),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③比如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草案)》提出允许农民对完成交售任务后剩余的农产品进行加工和销售、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农民私人也可以进行经营、扶持农民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服务业等,还提出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此外1983年1月《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2月《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3月《关于发展成向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等,都对农村发展个体工商业提出了政策支持和改革指导。[4],其中包括明确规定并肯定集市贸易性质的《城乡集市
贸易管理办法》[5](P973)。Q市农民用一句俗语概括对当时国家政策的记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乡镇企业(包括村办企业)和沿海渔业在此时发展起来,集市贸易开始复苏。少量男性农民进入乡镇企业④调查地20世纪80年代有大量乡镇企业,如窑厂、砖厂、水泥厂、木材厂等,在农村有很大影响力,被农民视为最好的就业去向。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农民(男性占绝大部分)成为农村最早一批工人。,更多的男性选择“靠海吃海”,合伙打鱼或就近打工。农村妇女承担起日常家务与农活,并不约而同地选择集市经商:渔民的妻子主要将海产品(蛤蜊、鱼等)卖给个人,其他妇女在自家菜园种植时令蔬菜,主要卖给乡镇企业的食堂。由此,Q市农村家庭经济策略的调整初步完成,家户内的劳动模式和性别分工模式也逐渐定型。
农村改革之后,户成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单位。离开生产大队回到家中的农民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农业劳动工具不全,需要重新定制;劳动力不足,特别是孩子尚小的家户,往往需要夫妻两人承担多重劳动责任:晚上干农活,白天外出打工或赶集。“户”成为国家管理农村的基本单位(如纳税)。对于农民来说,“户”不仅是划分家庭内外的概念,而且是农民建立个人身份的基础。因此,包产到户的政策契合了农民以家庭为重的传统,使贫穷的农民愿意为了提高家庭收入、改善家人生活而勤恳地劳动。
为应对家庭外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农户必须调整家庭生存策略,户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模式便是重要的体现。集体经济解体后,回归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并没有回归传统家庭妇女的性别角色,除了照顾老幼、承担家务的传统性别分工责任,还必须承担家外劳动责任——家庭大部分的农活以及到集市经商赚钱补贴家用。这种性别分工模式完成得如此自然,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农村家户内性别分工模式的延续。集体主义时期,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指导下,广泛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性的生产劳动,妇女劳动的空间和内容大大拓展了。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时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策略,尽管生产方式实行公有制,妇女也参加家庭外的集体生产劳动,但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的照料责任也一直是“妇女职事”,这一点从未被真正地挑战过[6]。所以,在集体主义时期,国家在动员妇女参加家外社会劳动的同时,保留了“户”的结构和妇女传统的家内责任,父系家庭制度并没有被打破。正因如此,农村经济改革后,妇女自然地担负起家内家外的双重责任。集市经商赚取现金补贴家用就是农村妇女新的家外责任。
但是,类似于集体主义时期的性别劳动分工模式背后,是不同的性别秩序运作模式。不同于集体主义时期国家对妇女家外劳动价值的高度肯定,公/私领域分离后,农妇的家外劳动(农活、集市经商)被视为“户”这个私领域内的劳动。于是,评估妇女劳动价值的决定权回到家庭中。在这个过程中,丈夫充分利用了妇女家外劳动性质的“私化”结果,维护着家庭内部的性别等级秩序。
首先,妇女在集市经商被丈夫界定为轻松的家内劳动。第一代集市的女丈夫普遍认为集市经商是“家里的轻快儿活”,自己“在外面出大力”⑤管大爷,1929年生,韩婆婆的丈夫,访谈时间:2013年2月11日。王大爷,1942年生,赵婆婆的丈夫,访谈时间:2012年8月8日。对其他第一代集市女丈夫的访谈都得到了类似的说法。,隐含的意思就是,妻子做的都是轻松的工作,这些轻松的工作都是妻子应该做的家内劳动。妻子们(特别是渔民的妻子)并不认同丈夫将集市经商视为轻快活。韩婆婆是一位渔民的妻子,她往往要凌晨三点起床做好饭,给丈夫和孩子放在锅中温着,然后推着独轮小推车步行三十余里去海滩上找到丈夫的船,把海货卸船装车,再推到早市卖掉。
我去海滩上推着这二百来斤蛤蜊往集上走,叫他快点回家吃两口饭好再出海。我就看着那个车子歪呦歪呦的,一个轮子,我不会推那种车,我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是二小姐,(所以)我推起来很吃累。好不容易推到集上赶紧卸下来卖,卖不出去就臭了,就得扔。你得吆喝着卖,还得能说会道,我都不会⑥韩婆婆,1928年生,访谈时间:2014年4月29日。。
于婆婆回忆道:
(我)天不明去前海沿上收海蛎子,挑着满满两担得有180多斤,一路小跑赶快回家剥出蛎子肉,挎着篮子跑去王台集卖,那可是40里路啊!真是一路跑,这东西不赶紧卖出去,拿回来就得扔。有时候去晚了,没卖出去,往家走的路上嚎(大哭)啊。(回)家去看看仨孩子,大的(孩子)背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等食吃,都不知道我心里的滋味⑦于婆婆,1938年生,访谈时间:2014年4月27日。。
虽然集市女都否认这是个“轻快活”,但她们赞同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家内劳动。在农活和菜园被划归妇女家内责任时,卖农副产品便被视为家内责任的延伸;渔民负责将海货带回陆地就算完成了工作,至于将海货推到集市卖掉的工作则是妻子的分内之事。这种将家外劳动的性别分工类比家户内性别分工的说法在第一代集市女及其丈夫的表述中很普遍。甚至更极端的,有集市女提到除了丈夫家外的工作,其余的都该由妻子做。她们很少将自己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与丈夫相比,甚至不止一次地强调家里的顶梁柱、养家人始终是丈夫,自己赚的只是零花钱而已。笔者询问“零花钱”的用处时,集市女的回答恰恰说明,尽管丈夫的收入是家庭重头开支(如“盖屋”)的主要来源,但集市女的收入绝非可有可无,而是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如薛婆婆称:
盖屋这样的大钱还是靠俺家里(丈夫),他挣得钱平日里不花。可是平常不得买个火柴、线头什么的用用?挣个块儿八毛的,供家里头平常日里的开销⑧薛婆婆,1931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8月20日。。
丈夫是认可妻子的经济贡献的,但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内性别等级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总会否定集市经商的性质和妻子的劳动能力。比如丈夫称“集上摆摊算不上正经营生”“你看集上有几个男的?能干活的在家里?叫人家笑话!”⑨管大爷,1929年生,韩婆婆的丈夫,访谈时间:2013年2月11日。丈夫眼中的集市摆摊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男性不屑于从事的工作⑩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认为集市经商不是正经营生,而是“耍活”的人很多,比如H镇W村王大爷说:“什么是庄户人家的正经营生?早年是种地,现如今加上个出去干活。男人当然都出去(打工)了,能出去谁留在家里赚着这一毛两毛的钱?”王大爷将集市经商称为“耍活”,这是当时农民的一种主流看法,集市经商并不是农民获得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王大爷,1933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8月。,自己从事的乡镇企业工作或者打鱼是需要技术的工作,是比妻子所从事的农活、家务、集市摆摊等都要高级的工作。不仅如此,丈夫往往强调自己的扶助对妻子集市经商的重要性,妻子集市经商的工作是比丈夫低级的工作,只能为家庭赚取“零花钱”,且这笔“零花钱”里还有丈夫大部分的功劳。妻子大都认可这种说法。以现金收入衡量劳动能力的经济体制打造了家户内部的劳动等级,从事“高级”劳动的丈夫与从事“低级”劳动的妻子构成了家户内部的性别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彼时农户的经济支柱依然是农业,但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农活对家庭的贡献却常被忽视,更不必谈家务和照顾老幼这样的“妇女天职”了。集市经商不仅被视为农妇普遍从事的分内工作,而且也是家户经济中可有可无的女性化工作,妻子劳动对家庭的贡献被再次淡化。例如,当赵婆婆自豪地提起曾用集市摆摊赚的钱为孩子交学费时,受到丈夫最严厉的反驳和压制。
王:那时候家里都穷,人家都去她也要去,我就叫她去了。她也能挣几块零花钱哩。
赵:一个月能赶六趟H集,少说一次挣三块钱,一个月还挣十八块钱哩!有时候我还挑着扁担去D集市、L集市、Z集市赶集哩!俺家小的(孩子)刚上学那会,他爹钱没拿回来,孩子交学费谁拿的?(自豪地笑了)
王:你就拿了一回。
赵:一次就不算了?
王:你出了多大力,我出了多大力?⑪赵婆婆,1946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2月17日。赵婆婆是比较勤劳并会做生意的集市女,村子附近的H集市每逢二、七是开集日,即农历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初七、十七、二十七是集日,如果每次集都去的话,每集都赚三块钱,每个月的收入也就十八元。但由于农活、家务或天气等原因,她们通常不能每集都去,且并不总能卖得好,所以她们平均一个月靠赶集一般能赚到十块钱左右,而这通常连丈夫工资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段对话后,是妻子长长的沉默。
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他认为妻子的话是对其户主权威地位的挑战。笔者在对第一代集市女进行访谈时,常遇到谈话过程被集市女的丈夫控制主动权的情况,声音高昂的丈夫和轻声低语的妻子多少也显示出第一代集市女家中的性别秩序。这种性别秩序也使第一代集市女不断贬低自己在集市劳动对于家庭经济的作用和价值。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性别秩序的重构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整体过程。国家的改革政策分离了公/私领域,将妇女为家庭增收而进行的家外劳动私化,父权文化使丈夫获得了评估家庭成员劳动价值的决定权。妇女集市经商的工作被视为轻松、低级、“算不上正经营生”的家内劳动,与传统家内劳动(如家务、照顾老幼等)一起成为妇女的分内之事,而这些家内劳动都被界定为低价值的劳动方式。因此,为了实现家庭增收,妇女虽然不断累加生产劳动的责任,但始终无法以此撼动家内的性别秩序,反之,她们默认了这种性别秩序。农村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与其说是包产到户政策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直接结果⑫黄宗智用“过密化”的概念分析中国农业长期所处的状态,农业不兴非劳动力投入不足。老田指出,改革初期农业迅速增产是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大量使用化肥等)的结果。参见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与现在》,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老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重点转移”与“林润生-林毅夫假设》,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8][9],不如说是基于这个性别秩序的性别化转型⑬宋少鹏在《“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中首次提出“性别化的社会转型”的分析视角,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性别化的过程,转型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性别化的社会结构。[7]。事实上,依赖国家短时间内密集投入所带来的农业增产很快遭遇困难⑭从1978年到1995年,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总投资的1/4,失去国家支持的农村面临资源枯竭的状况,基础设施不足,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农业科研技术资源浪费,等等。[10][11]。农村妇女承担起从家务、照顾老幼到农活、集市经商的更多劳动责任,任劳任怨地支撑着农户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她们承担的“家内劳动”越多,其丈夫便越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以男性为主的农民工就是这样诞生的。
二、第二代集市女: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后的性别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启动了全面的市场化转型,对农民来说,一方面生活(即家庭内部的消费)更加依赖市场,急需调整家庭经济方式弥补农业收入的欠缺⑮农产品收购价格低导致农民积极性受挫,包产到户小农经济的弊端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显现出来1984年粮食丰收后出现卖粮难的问题,次年粮食、棉花产量纷纷下降,农民农业收入大幅下降,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平均增长只有1.7%,其中1990年为负的0.7%。参见郭书田:《农村改革30年,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事实上,大部分地区农民非农收入在这一时期超过了农业收入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9月末,中国农民整体的非农业收入859.95元超过农业收入732.76元,而此前已有大部分省市超过。。另一方面是再生产职能私人化,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都被取消,不得不由私人化的家庭通过性别化分工(妻子承担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和代际分工(分担照料责任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来承担。在对Q市的调研中,笔者发现生活压力往往迫使农家夫妇共同承担“养家”责任:男性通常做建筑工人或成为外资/合资企业的工人⑰就本文的调查地周边镇子的情况来看,1989年到1996年有多家外资企业注册进驻,包括台资的玻璃厂(1993)、韩资的玻璃制品厂(1989)与工艺品加工厂(1996)、日资的电机制造厂(1992)等。数据来自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http://www. qdaic.gov.cn/qdaic/,于2014年4月28日访问。,大部分妻子在兼顾家务等传统家内责任的同时,成为女建筑工、工厂女工或集市女以赚取更多的现金来弥补丈夫收入的不足。进入工厂至少需要初中学历,赚钱较多的建筑工地劳动强度大,且离家较远,不利于妇女兼顾家内的多重责任,因此,大部分妇女被“留”在村里。农民生活所需和国家政策对市场的青睐[14](P522)催生了乡村地区大量的中小
型集市⑱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乡村集市迅速繁荣起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的发展尤其迅速。以山东省为例,据统计1987年底全省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达到5737处,比1980年的3899处增加了1838处。,由于离家近、门槛低,它们成为大多数农村妇女的就业选择,造就了数量最多的第二代集市女。她们的经商性质和模式都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改变。集市不再是本地渔民和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而变成了城市向农村倾销工业品的集散地,因此驾驶三轮车奔波于批发市场和集市之间的集市女成为兼业商人,被称为“贩子”。
乡村集市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性质的转变,由农产品交易市场转变为以工业品为主的交易市场;另一个是集市主要参与者性别的转变,集市彻底变成了女性化的场域。集市转变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正是农村社会市场化转型的一个缩影。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集市依然是嵌入在乡土社会结构中的熟人社会,但不同于80年代集市主要还是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此时农村的集市已转化成主要是工业品倾销市场,卖家已然不是生产者,而成为赚取中间差价的商人。市场结构的变化遭遇到熟人社会里的交易规则,往往伴着卖者的无奈:卖给熟人不盈利,甚至要亏本。张阿姨说:
你拿这件45(元)的褂子来说,上货37(元),乡里乡亲的,真是不赚钱。刚才俺村的仨老太咬定给35块钱。(她们)一口一个“谁谁谁家的(老婆)”叫我,我卖我就亏本,我不卖,她们回去碰到俺爹娘(指公婆)还不挖苦我?⑲张阿姨,1967年生,访谈时间:2013年2月11日。
市场化的乡村集市与熟人社会的磨合并不顺利,盈利困难使第二代集市女的流动性很大。那些善于经商的集市女大声叫卖、讨价还价、尽可能多挣点钱,成了农民眼里狡猾的贩子,这看法背后一方面是对赚到金钱的能力的羡慕,另一方面是对“女贩子”的鄙夷。Q市的农民认为极少有男人会为了一毛半分钱在集上讨价还价,这是不体面的事,但都认为在工地议工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跟外头人不一样”。传统农村社会的关系纽带是通过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建立起来的,男性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核心,从夫居的妇女依附丈夫结成自己的关系网络。男人认为在集市中讨价还价不体面,却可以在工地上这么做,究其原因是集市是熟人社会,工地却不是。这不仅反映了男性给自身划定的内外界限,也提供给我们一个观测农村社会市场化的窗口。传统熟人社会中家户内外的事务也是由男性主管和操作,而市场化让使用金钱处理熟人社会的事务成为当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1](P145),集市交易就是明显的代表。但男人们却巧妙地撤出了金钱与伦理道德的纠缠,将讨价还价的集市交易(包括买和卖)建构成女性化的劳动,因为妇女被认为是“允许犯错误的人”⑳笔者访谈中至少有11位男性受访人提到涉及日常金钱收支的事情要交给老婆来做,一来因为金钱敏感,作为户主的男性一旦出面,结果就定了,但是女人可以反悔。。如果妇女(多是作为卖方的集市女)在集市交易中的行为不当(比如要价太高或者货物质量有问题),熟人常会找到妇女的丈夫或公婆抱怨,再由他们训诫妇女。如此,不仅不妨碍集市女为家庭赚钱,也不妨碍作为家族男性的“体面”,用“老婆懂什么?!”这样训诫妻子的话,丈夫常可以轻松地反悔妻子做出的决定或行为(有些是丈夫授意但后来认为不妥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社会,追求赢利的现代商业规则与传统社会中熟人间的互助规则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利用性别等级/性别差异去化解和调整,以适应逐渐市场化的农村社会。基于家庭整体的利益,集市女在家外不能挑战这种性别等级。
不可否认,能够与丈夫一起“养家糊口”的第二代集市女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她们渴望自己为家庭所做出的经济贡献能得到丈夫和家庭的承认,提升家内地位。访谈中,如若丈夫在场,集市女在介绍自己工作给家庭带来的贡献时总是要轻声问一句丈夫的态度。丈夫虽然肯定妻子的贡献,但常有丈夫在访谈中扮演妻子的代言人,甚至帮助妻子回答集市摆摊的感受,妻子这时总会安静地在一边倾听。这种对话模式显示出丈夫仍努力扮演着一家之主的角色,而妻子很大程度上也仍承认这种家庭内的权力结
构。此外,集市女和丈夫普遍提到的两件事情引起笔者的注意。第一,家中两部账本,夫妻两人的收入分开记。在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现金收入往往是衡量家庭贡献的标准,大部分集市女在家庭账本中的收入总是低于丈夫(丈夫是建筑工人时情况更突出)。收入更多的“养家人”理所当然的是“当家人”,丈夫继续居于家内权力秩序中的支配地位。第二,不少集市女家中出现了阶级之分:作为企业工人的丈夫和身份认同模糊的妻子。第一代集市女的工作是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其身份仍然是农村家庭妇女。但是第二代集市女却随着集市性质和经商模式的改变,逐渐模糊了身份认同。深受市场化逻辑影响的她们,认为现金收入是唯一能帮助自己确立家内地位的依据。但是,当集市女用收入超过丈夫的事实要求丈夫承认自己的养家人地位时,丈夫往往用工厂工作的稳定性来维护自己的家内地位。于阿姨和丈夫(姓周,台企工人)的一段对话非常形象生动。
周:叫我说,啥也没有家里整齐重要,为了家里和孩子,扔了买卖也不可惜。
于:扔了买卖行不行,咱都明白得很。都多少年了,你还开一千来块钱,吃啥?我挣得比你这大工人多吧?我白日里赶集,晚上上人家小区门口摆摊,活儿不比你少吧?你每天四点下班,家里营生干一点不算多!
周:你看,她就是这样的急脾气,弄点事儿就吵吵起来了。我也嫌钱少,光我这样?在F厂子的人不都这样?不过那些双职工的还能比俺家里强点,好歹厂里还能投保。唉,普普通通的家庭,咱辛苦点没事。
于沉默了。
于阿姨试图用自己赚钱多和劳动强度大来反驳丈夫对于自己贡献的贬低,突破丈夫划定的劳动等级标准,并提出家务也是丈夫应当分担的责任,体现了她想改变家内权力关系的要求。尽管整体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在市场化过程中下降了,但拥有稳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工人群体,相比于“无组织”管理、生计更不稳定的农民的现状仍占优势。用另一位集市女丈夫的话说“不管咋说(我)还是有组织的,生病有医保卡,退休还能继续开钱。她有时候是挣得多,能挣一辈子吗?”㉑管叔叔(隋阿姨的丈夫),1963年生,访谈时间:2013年2月18日。
Q市的农民大都入了保险,工人在工作单位投保,大部分妇女是缴纳“自谋职业”的保险。每年的保险金缴纳需一次性交齐,集市女的现金收入不定,且都用于家庭日用,因此保险金往往需要从丈夫的工资卡或银行卡里取,建立起丈夫为妻子购买保险、保障妻子晚年的表象。这一现象的另一面被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妻子无酬的家内劳动保障了丈夫在劳动力市场相对的优势地位;集市女以独立的经济收入分担养家责任缓解了丈夫低工资换社保的压力。
第二代集市女体验着市场逻辑如何无孔不入地改变农村社会,也经历着社会性别秩序的变与不变——她们必须能够“养家糊口”却不挑战丈夫权威。这种性别秩序既是农民家庭对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适应策略,也是男性农民巩固其在家内权威地位的策略。同时,这种性别秩序反过来也深刻影响了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转型——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思想观念的全面市场化,使之成为一场性别化的转型。农民日常生活逐渐依赖市场与货币,农村熟人社会关系遭遇市场逻辑带来的伦理危机、社会保障体系外部化之后给农村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等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都借由性别劳动分工和性别秩序得以暂时化解。因此,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造就了更利于资本的性别秩序,反过来,这种性别秩序成为农村社会进一步市场化的重要支撑。
三、第三代集市女: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迷失了身份的妇女
Q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招商引资中建立了多个劳动密集型工厂,吸纳了周边农村的男女青壮劳动力进厂工作。然而,女工走进婚姻后,往往不得不离开工厂。一方面,生儿育女后的妇女要担负“农家妻”的多重责任,另一方面,工厂不愿承担工人再生产的责任,女工难以重返工厂。2008年前后,经济危机使Q市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出现大量再就业困难的女工。但是,这些妇女所处的现实却是大部分农户已经没有耕地,或者农业收入可忽略不计,农村生活全面依赖市场。丈夫在周边工厂打工,妻子集市经商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模式。第三代集
市女经商的动机,一方面为家庭增收,另一方面是为寻找和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
进入2000年后,房地产热造成Q市农村的大量耕地被圈后搁置,而不是变成厂房,农民没有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征地事件本身却成为农村社会性别秩序重构的外部条件。征地赔偿款全部直接打入男性户主的银行账户,这笔数额可观的现金被农民称为“大钱”,由丈夫来管理。妇女婚后从嫁入村庄分得的个人口粮田也变成“大钱”的一部分交到丈夫手里,竟有多位妻子不知道账户密码,她们真正成了“失地农妇”㉒目前学界关于失地妇女的探讨集中在农村女性的生存和发展(参见金一虹:《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村妇女》,《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妇女地位、身份或角色的转化和财产权益保障(参见刘继华、王晓:《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障的法律规制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顾栋、羌怡芳:《统筹城乡妇女就业的主要障碍与对策思考》,《兰州学刊》2005年第3期)以及失地妇女就业(参见孙良媛、李琴、林相森:《城镇化进程中失业农村妇女就业及其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为基础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等。学者们都欲为失地农妇找到更利于其发展的出路,然而却都没有厘清“失地”的制度性原因(有则只关注到婚姻迁移的因素),如新的父权制度,这还待研究。。“大钱”连同男人的工资银行卡都由丈夫管理,于是农民家中普遍出现了男人不但当家,而且理家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再生产职能私人化后,农村家庭也不得不求助于暂时性的扩展家庭模式来适应市场化就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年轻夫妻将孩子交给父母照顾。表面看来,农村妇女的家内责任大大减轻了,父母和丈夫不同程度上分担了她们的家内责任。实际上,她们进入了比任何时候都迷茫的时期:用什么证明对于家庭的价值?用什么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似乎只剩下通过参加家外劳动获得经济收入这一条途径,在紧张的就业形势下,不少妇女选择到集市经商作为暂时性的工作,“好过闲在家里”。
第三代集市女通常从事的都是服装、内衣或者小包装零食买卖,一般一个人摆摊,从事集市经商时间较短,说话声音小。和第二代集市女不同,她们对自己集市经商感到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工在集市相遇时。“她们工人到点下班,到日子发钱,俺是出大力的命,根本没法比”㉓陈姐,1975年生,访谈时间:2013年2月18日。。虽然也有集市女表示自己并不羡慕女工,因为女工赚钱不一定更多,但她们都认可工人是更有社会地位和更受人尊重的高级身份。女工与集市女的身份等级凸显的是现代性观念——工农、城乡等级——对于农村社会以及农民思维的影响,形成另一种圈地运动——精神圈地[16]。第三代集市女并没有在与女工的等级落差中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没有将自己与其他集市女视为一个身份群体。
1.我还在找别的活,找到了我就立即走。你知道吧?我好歹也是上完了初中的。
2.我来(集市经商)当然是为挣钱,可是挣不着,闲着不好看,我才天天赶集。
3.谁还在集上买东西?俺孩子吃的零食都是超市买的。俺妹夫说D区有个厂招保洁的,我以前嫌弃,觉得年纪轻轻干这个不好意思,现在倒觉得能给投个保(保险)也中。下一集,我就不来了㉔引语分别来自1.赵姐,1971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7月12日;2.陈姐,1975年生,访谈时间:2013年2月18日;3.管姐,1974年生,访谈时间:2013年2月18日。。
市场制度下女性的社会身份是根据职业确立的,已经是职业商人的集市女为何无法建立身份认同呢?一个原因是,集市女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于集市经商这种工作的认知。在市场化和城镇化加速的进程中,与集市功能相似的超市全面进入农村社会,以其声称的“品牌、清洁、卫生、廉价”等特点迅速占领了农村市场[17]。农村集市岌岌可危的地位造成了集市经商女不确定的身份认同。另一个原因,是她们的家人对集市经商存有偏见,认为是“收入不稳定、工作不体面”的工作。她们几乎都提到自己失业后在家内地位的下降,突出的表现就是丈夫和公婆把曾承担的大部分家务“还”给了集市女,理由就是“她现在不上班了”㉕笔者在访谈多位集市女都提到曾经被丈夫和公婆分担的家务和菜园农活“重返”的情况,笔者访谈了四位集市女的丈夫,和三位集市女的婆婆,他们在解释这种做法的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提到“她不上班了嘛!”,似乎上班才是为
家庭挣钱,集市经商却不算。比如贩卖蔬菜的冯姐:
冯:ZY厂倒了以后,我来(回)了家,一开始没怎么,后来慢慢地都不管了。菜园里种几垄葱,提前跟我说好,叫我第二天赶完集去种。家里来了客,从我这里拿菜,打电话叫我拿着菜回家做饭招待客。都觉得我是闲人吗?我不是在给家里挣钱吗?
笔:你跟丈夫或者婆婆说过你的想法吗?
冯:当我觉得好像是不平等了,我就更加使劲地干活,我相信多劳多得、相信平等㉖冯姐,1976年生,访谈时间:2012年2月13日。。
冯姐口中的“平等”是典型的市场社会逻辑,现金收入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于是她认为可以“多劳多得”,获得家内地位的提升。笔者在2011年2月与两位集市女一起摆摊时也有这样的感触,当年她们虽然抱怨从事了集市经商这种低等的工作,却相信加倍工作会有回报。难以获得夫家支持的第三代集市女越来越倾向于从娘家“借钱”作为集市经商的运转资金,也倾向与娘家的亲戚或朋友合伙经商。于是,Q市出现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娘家倾斜的现象。但是集市惨淡的前途和集市经商较低的社会地位,通常使集市女的“多劳”空付,纷纷离开集市。笔者2015年初再去集市时,之前访谈的十余位第三代集市女只剩了一位,集市里多了新的妇女面孔。
笔者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了曾经做内衣生意的徐姐,她在集市旁的道路边开了家内衣店;曾经做海鲜生意的张姐在家,偶尔去村子水厂做临时工。徐姐透露店面是属于娘家兄弟的,不需要交房租,获得这样的待遇是因为娘家拆迁赔偿的时候,徐姐没有分到楼房。她说生意勉强,但她满意的是,女儿可以放学后来店里吃午饭和午休,晚上放了学还能在店里写会儿作业。“我接受俺大哥这安排就是他一句话说动了我,有个地方叫孩子放学来,当娘的不就为了孩子吗?”
笔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三代集市女都在集市短暂就业,越来越差的集市行情、不断加重的精神压力,迫使她们重新审视“赚钱”和“家务”的意义:与其抛头露面从事出力不赚钱也不赚尊重的工作,不如专心照顾好家内老幼。于是她们主动“要回”被公婆和丈夫分担的家内责任,换得一份心安。妇女回归家庭重新履行传统的“妻职”与“母职”已经在农村社会中普遍化。但是,生活全面依赖市场的农民生活又不能让她们安心待在家里,选择一个能兼顾家庭内外工作且比集市经商体面的工作提上日程。因为其年龄和学历相比第二代集市女的优势,她们大多会以保洁员、临时工等身份“重返”工厂,只是这需要丈夫去村委会或者厂里的熟人“找关系”,从夫居的婚居模式使已婚农村女性的社会资本主要还是依赖丈夫家庭。当经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越来越市场化,农村妇女沦为最低等的劳动力被资本碾压,社会将其归因为妇女自身的“没文化”时,却看不到加诸妇女身上的制度性因素:正是因为妇女承担了再生产的职能,才使家中的男人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获得资本青睐,才使转型期的农民可以通过非农业收入支撑家庭生活;也正是因为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使无力通过购买市场服务来转移再生产职能的农村妇女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底层。未婚进厂-生育离厂-集市经商-回归家庭-再进厂,透过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将劳动力等级化处理,使得这些农村妇女更坦然地接受了集市经商前不能接受的工作,比如做保洁员。但是这份工作能帮助农村妇女获得比集市经商更高的家庭地位吗?
在国家的推手之下,资本迅速改变着中国的农村社会。招商引资而来的工厂拒绝承担女工的再生产职能,传统父权文化却让妇女不得不肩负农家妻母职责,造就了离厂女工。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给勉强留厂的女工带来的是厂主不负责任的逃脱,再就业一筹莫展。历经改革20年的集市贸易繁荣起来,为这些妇女提供了一条就业途径,但资本主导的超市下乡摧毁了小商户个体经济、也重塑了农民的意识,集市经商的劳动进一步贬值。当家务、照料孩子的责任被公婆和丈夫分担,无法通过家外劳动获得足够收入和社会尊重的集市女“主动”选择回到家中重操“旧业”以确立自己迷失的身份认同。但农村生活全面市场化之后,丈夫一个人的劳动已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妻子家外劳动收入对于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在她们“回家”后显示出来,于是,妻子只好再次进入
市场。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第三代集市女似乎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回归家庭,做职业主妇,家庭难以维持生活,她们既无法通过工作获取社会身份,也不能提供收入以获得家庭认可。走出家庭,传统家内责任使其只能成为低级劳动力,她们无法通过“体面”的劳动获得独立的社会身份,更难获得社会认同。可以说,农村妇女的不利处境是结构性的,与农村社会性别化转型息息相关。
四、结论:性别化的转型与转型中的性别秩序
三代乡村集市女跌宕的命运是中国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转型的一个缩影。朱爱岚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1]、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18]、宋少鹏的《“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19]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性别秩序的变与不变。但笔者对三代集市女的分析发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与性别化不是谁制造谁的关系,中国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转型本身就是性别化的,总结有三点原因:
第一,农村的经济转型是性别化的。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政策分离了公私领域,也重新建立了男性户主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户主独占性的经济控制权在土改时期受到挑战,一直延续到集体化时代。包产到户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返还到丈夫手中,也将评估家庭成员劳动价值的权柄交到了父权制家庭的丈夫手中。因此,在农村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民生活逐渐全面依赖市场的背景下,丈夫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外部转移增加收入,从而巩固家内的权威地位;妻子却只能通过不断累积被贬低的劳动责任,争取获得家庭的认可。但是,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没有妻子逐渐累加的劳动责任,丈夫便难以成为廉价劳动力,作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农村家庭将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内在的因果关系却被集市女的丈夫以及她们自身忽视了。这种权力秩序和性别分工在三代集市女的经历中延续并不断调整巩固,使农村家庭足以承受和适应全面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农村的经济转型是性别化的。
第二,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转型是性别化的。首先,市场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逐渐全面依赖市场,极大地突出了现金收入的重要性。集市女越来越难通过经商获得可观的收入,但丈夫因为经常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成为“养家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家人”。其次,市场化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实现了类似潘毅讲的“精神圈地”。当超市和商场消费变成农民试图弥合城乡差距而接近现代化生活的方式,集市女的工作同时被视为落后职业。集市女的身份随着集市命运的跌宕而迷失了,而因为她承担多重劳动责任而成为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丈夫,却因为有明晰的工人身份(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工资、社保等工人待遇),成为家庭中更有话语权的人。最后,正因为这样的性别秩序,使市场逻辑遭遇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和伦理道德时,有了性别化的解决方式——女性处理熟人社会的金钱关系,男性负责展演伦理角色。这种方式既能保证家庭在熟人社会中的经济收入,也勉强维系着金钱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伦理关系。因此,农村社会的全面市场化转型是性别化的。
第三,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结果是性别化的。大规模的资本下乡击垮了个体经济,改变着农民的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当集市女既不能通过集市经商获得更多的收入,也不能通过这一工作赢得家人和社会尊重时,她们一度回到家庭重履传统的妻职与母职,找回身份认同。但是,无论社会舆论如何讴歌母职,也无法抹去这样的现实:丈夫一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开支,妻子必须有收入。于是,集市女回到家庭又走出家庭,从事起集市经商前拒绝的“低级工作”(如保洁),成为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三代集市女的经历证明,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转型的结果对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错综复杂,既为妇女带来机会,更提出挑战,甚至使一些妇女处于困境,需要深入研究相关难点并发展对策,以便男女能够平等拥有机会和利益。
[1][加]朱爱岚著,胡玉坤译.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丹]埃丝特·博斯拉普著,陈慧平译.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节录)[A].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1998)[G].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A].商业部办公厅.商业政策的法规汇编[G].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
[6]宋少鹏.公中之私——关于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1949-1966)[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1,(19).
[7]宋少鹏.“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J].妇女研究论丛,2015,(2).
[8]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与现在[J].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9]老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重点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J].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厦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10]刘舰.从农业投入看农村经济的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9,(5).
[11]宋巨盛.试论我国的农业投入问题[J].农业经济,2003,(10).
[12]郭书田.农村改革30年,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N].农民日报,2008-11-21.
[13]宋少鹏.结构性压迫和个人美德:“女德馆”能否救赎现代妇女的焦虑[J].文化纵横,2015,(1).
[14]山东省经济研究中心.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1988-2000[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15]进一步搞活管好城乡集市[N].人民日报,1983-02-24.
[16]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
[17]T.Readon and A.Gulat.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The Rise of Supermarke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2008[EB/OL].www.ifpri.org/pubs/dp/ifpridp00752.pdf(last accessed Novermber 2012).
[18]潘毅著,任焰译.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19]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妇女研究论丛,2011,(4).
责任编辑:玉静
GUAN Tian-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CCP,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gendered social transformation;marketization;rural women;gender rule
Trading in rural fair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ese farmers to supplement family income.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der norms,rural fairs had always been dominated by men.But this situation has changed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in 1978,and since then trading in rural fair has gradually become rural women's business.Three generations of women have grown chronologically together with ur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ral China and changes in gender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wome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working in rural fair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rocess of full-scale marketization in rural China to a large extent is based on the utiliz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gender order in rural families.
C913.68
:A
:1004-2563(2015)05-000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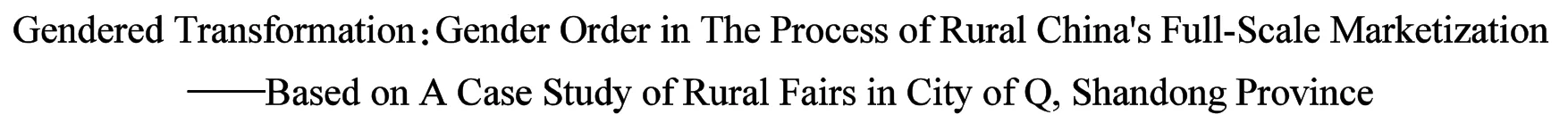
管田欣(1991-),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妇女史。
*感谢宋少鹏老师在此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给予笔者精神上的鼓励,学术上的耐心指导!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