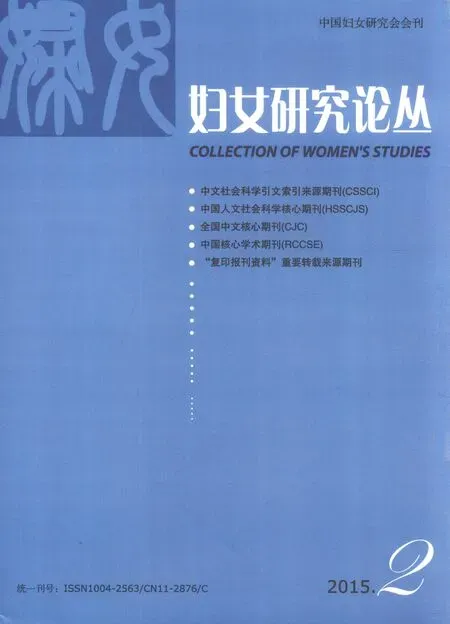从性别表演到文化批判:*论朱迪斯·巴特勒的政治伦理批评
2015-02-24王楠
王楠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从性别表演到文化批判:*论朱迪斯·巴特勒的政治伦理批评
王楠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伦理;文化;犹太性
20世纪最后10年,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自然性”的质疑之辩改变了我们思考性别、普适伦理和言语行为的方式。文章以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点,侧重考察性别表演理论之后,她在性别与伦理、伦理与政治之间所进行的理论介入与文化批判的努力。笔者认为,巴特勒质疑女性主义、重构主体的再生产意义和建构美国犹太文化“它者”生存策略是对美国女性主义政治的伦理式演进。尽管巴特勒在世纪之交倡导回归伦理,但她希望保持“伦理两难”的思考状态,让阅读生发更多的问题而非提供思考的结果。她的思考照见了西方人文主义研究中关于人学的一个盲点——人的脆弱性,这或许也是巴特勒无法回避的“伦理两难”的境遇。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师从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开始接触黑格尔(Hegel)和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80年代初,她回到美国,在耶鲁期间,研读黑格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等理论家的著说,并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欲望的主体:20世纪法国哲学对黑格尔的接受》(1987年出版)①国内学界对此书关注不够。此书初成于1984年。作为博士论文,最初只是讨论黑格尔哲学在法国20世纪30-40年代的接受情况。受福柯启发,或者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结构主义转向之后,巴特勒对此书做了修改,增加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欲望、主体和承认的述评。这篇博士论文最后出版于1987年,即现在的版本。虽然出版之初,并未受到关注,巴特勒也在此书再版之际(1999)表达了“遗憾”,但无疑这是理解巴特勒思想的关键文本,可以说为她后来创建的性别伦理准备了理论资源,作者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反复围绕欲望与承认是何关系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探索”[1](Pviii),以及“主体的构成到底需要与异他性(alterity)保持何种激进且富有建设性的关系?”[1](Pxiv)她把未竟之志著录在第二本专著《性别麻烦》(1990)中,该书很快成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肇始之作,至今依然影响深远。。这本书成为她识别和拆解女性主义主体的稳定性的哲学出发点②巴特勒考察黑格尔的关于主体和欲望的哲学思想在20世纪法国的转化与创新。从让·伊波利特(Jean Hippolyte)到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再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勒在关注这些思想家改写黑格尔的主体与欲望概念的批判轨迹中,提出了性别政治,尤其关注少数性别团体的承认的政治学。对于“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的精彩论述,参见巴特勒著作《性别麻烦》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主体(subject)、欲望(desire)、承认(recognition)、异他性(alterity)这些关键概念的黑格尔式问题始终贯穿在巴特勒的著说之中。虽然她无意梳理黑格尔哲学接受的思想史,但她关注以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在主体间建构政治话语的内部关联以及消解主体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方式[1](P15)。在前期理论阅读的铺陈以及诸多先驱学者思想的影响下,巴特勒在博士后工作期间将批判探索延伸至女性主义。她重新诠释了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并在甄别无法规约的他者——双性人、同性恋者、有色人种、跨性别者、劳工——基础上提出了性别表演论(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表演论成为巴特勒的理论标签,也成为90年代消解性别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与批判诉求。巴特勒的质疑构成了对女性主义理论挑衅性的“介入”,她所识别的性别化的生活揭示了充斥着性别假定的二元框架的思考惯性,并进一步质疑性别得以形成的规诫权力。正如她在《性别麻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主体的政治建构是以某些合法性以及排除为基础,并被政治话语以‘自然化’为由有效地遮掩了。”[2](P3)性别从此成了“问题”。
21世纪初,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声音之一,巴特勒开始关注跨国家政治和犹太族裔的流散性问题,在解构主义留下的“断裂”与“褶曲”中,辨识文化政治理论的伦理危机③关于性别与伦理的哲学话语和理论背景的晚近理论,参见王楠:《性别与伦理:重写差异、身体与语言》,《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6期,第80-86页。。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她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和阿多诺的道德主体入手,梳理当代文化和智识传统的伦理缺憾。本文以巴特勒晚近的著说为基点,考察性别表演理论之后她如何在性别和伦理之间找寻理论的契合面,以及她在性别与伦理、伦理与政治之间所进行的批判努力。笔者认为,巴特勒在解构思潮中消解性别差异、重构主体的再生产意义、建构美国犹太文化生存策略是对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伦理式推进。本文的第一部分说明女性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考察巴特勒在解放的性别伦理批判中的标杆意义。第二部分探讨她的性别表演论的伦理批判指向和女性主义政治立场。第三部分考察巴特勒建构的它者,论述作为两性规范伦理例外的它者的伦理诉求。第四部分探讨作为犹太裔的巴特勒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它者的承认问题。巴特勒的政治伦理转向并非简单地表明她从反人文主义到人文主义的哲学性回归,而是探讨解构主义理论中有关性别思考背后人的主体性的重构和由此生发的语言和伦理的“情感功能”。
一、作为性别伦理的女性主义
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自己。人类自我承担着揭示关于共有人性的终极善的责任。在人类面向终极善、趋近终极善的各种行为中,“人何以为人”的有关人类共有的伦理思考在人类的平等欲求与现实的伦理实践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尤其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作为伦理的批判工具,有关性别的伦理思考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论证。与三次妇女运动并行,女性主义提出了平等、差异和解放的性别伦理主张。平等伦理关注女性与男性共同人性的参与平等;差异伦理强调女性和男性平衡与互补间重构标准的诉求;解放伦理试图冲出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约束和范畴,在消解性别后重塑人性所获得的自由。从平等伦理到差异伦理再到解放伦理,伦理所试图解放的是社会建构范围之外的有关人性的一个维度,正是人类自我这个维度。作为性别伦理的女性主义在重新获得人性的共同之处的意义上,彰显“超越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规约和范式的新的生活方式”[3](P40)。巴特勒正是在解放伦理形式中展示了她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标杆作用。她反思性别的范畴和权力建构问题,指向预设的伦理学主体——男性本性,以求获得关于人性思考的某种改变,书写更完善的人性。
差异女性主义者划定女性这个范畴,是用来强调被忽视的具有女性性征的妇女权利,例如要求避孕权、堕胎权、对孩子的绝对监护权等政治主张。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用妇女作为“铁板一块”的集体“询唤”(interpellation)策略形成了女性共同体。在当时女性主义所维系的一系列性别政治主张,如改变从属地位的等级要求和拒绝因给定的身体特质而强加给女性的生育和家庭义务,对团结全球妇女发出整一的性别政治诉求、维系妇女共同体的利益起到了积极意义。但是,到了80年代末,这种单一的妇女范畴使得女性对父权制规范中自身的从属地位有所觉悟的同时,又充当了彰显性别差异、维护二元对立的异性恋霸权的同谋。同父权制一样,女性主义通过不断重复其主张和宣扬其合法性,奠定了认同的基础和确立了自身的合法领地。
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提出的差异性别建构说就是遭此诟病的例子之一。一般认为波伏娃在为女性谋取权利而辩。但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分析模式中,把生理性别描述为一种前话语领域,是无法选择的先于话语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这种在生理性别上分化的身体所承担的意义只能在它与另一个对立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里存在。身体是一种“情境”,铭刻了身体差异、语言差异、身份差异。这种解剖学意义上区分的身体在波伏娃看来是一个严格的文化律法建构中的被动接受者。我们只能用一套对身体具有规诫作用的律法系统来理解社会性别所建构的“文化”,如此“变成女人”的过程实际上命定的不是生理,而是文化[2](P11)④这里对《性别麻烦》的引用页码是中文译本的页码,笔者对译文做了改动。建议读者参看英语原作。。对波伏娃来说,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学事实使得主体只能用“给定的”性别进行二元文化诠释。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矩阵中,“主体”只有一个,即男性,男性即普遍性,女性即他者,外在于普遍性,具身为肉体,被化约为身体物质的存在。男性/主体则是抽象的,甚至超越社会规范所做的标记,成为自由意志,而女性则因受贬低的身体,等同于这个性别。身体附属于灵魂(意识/精神),女性亚于男性,女性是第二性⑤见笔者《性别与伦理:重写差异、身体与语言》一文中有关身体的论述。。波伏娃似乎还是囿于萨特式的身/心二元区分,因为对二元结构的复制实际上依旧维持着性别等级,并进一步使其合法化。
不同于波伏娃,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认为,女性这个性别不是“单一的”,女人不能被认定为他者,因为主体与他者两者都是用来支持封闭的菲勒斯中心意指系统。波伏娃强调女人是男人的反面,是缺乏,因此要标注女性,用社会建构的关系来重新定义女性。伊利格瑞则认为,女性这个性别从未在场过,是语法中无法表述的一个存在(substance),因为对性别关系的描述只能依赖于对二元关系的描述,这个描述不仅预设了男和女、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两性差异化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这个关系的结果——异性恋情欲的合法性。伊利格瑞引入对女性身份的批判,把被女性这个范畴排除和拒绝的一切可能性都包含进来,从而建构多元女性。伊利
格瑞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解读就是一例。作为血亲混乱的结果⑥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的母亲所生之女。,伊利格瑞认为安提戈涅在二元对立的伦理体制中无法标注自我,只能沦为“共同体永恒的讽刺”[4](PP277-295)。这个被排除在二元对立体制外的“准主体”永远不能等同于主体/男性,只能作为主体的“重影”或“内衬”,在为男性绝对效劳(埋葬她的哥哥)的份内之职中寻找自我。[4](P273)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莫妮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则认为性别范畴一直是女性的,因为男性从来不用标记,从来都是与普遍性等同,消除异性恋霸权是性别问题的关键。
巴特勒继伊利格瑞和维蒂格之后,进一步厘清了性别范畴的划归问题。实际上划归问题是一场性别的权力圈地运动,“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但它也不是一组流动的属性,因为性别的实际效果是有关性别的一连串管控性实践,通过表演生产而强制形成的”[2](P34)。巴特勒的矛头指向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概念以及划定妇女范畴的“被代表”的问题。“主体”问题对于巴特勒的女性主义伦理政治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主体的政治建构必然朝着合理化、自然化和排他的目标发展。如同律法的建构,权力形成并确立之时,也意味着承认某种虚构的主体的普遍存在。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在假定妇女这个主体的同时,虚构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一个单一的形式,也强化了女性主义所宣称的“代表性”的表象。女性主义在范畴上生产出的这个稳定的能指,实际上强化了女性共同体的屈从的集体经验,也掩盖了妇女共同体的多重身份样态。巴特勒主张“并非扩大‘妇女’范畴或是呈现其复杂性的多元自我”,而是解放并“永远延宕”性别这个伦理联合体,因为“它最终的整体形式在任何时间点上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2](P22)。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了解构思想的启发,如同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对于西方哲学这个形而上学体系提出的解构主义挑战,巴特勒让性别向未来开放,因为“保持问题的开放性比预先知道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共性更有价值”[5](P35)。
二、性别表演背后的伦理预设
《性别麻烦》(1990)和《消解性别》(2003)成为巴特勒追踪“性别”、打破“妇女”普遍意义上的性别标签的伦理预设的理论批判力作。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从规范之外的某些性实践中质疑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稳定性,试图证明规范的性取向强化了规范的性别取向。在这个矩阵中,巴特勒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是女性,不是自然地接受她的女性性征继而成为女孩,重要的是这个人通过对异性恋规制中有关女性的性/性欲规范的“引用”成为符合某一规范的主体。对规范和权威的“引用”使所有语言符号置于引号之中,性别身份在对这些符号的引用、嫁接、重述过程中,循环往复地被征引,在征引中松动、瓦解而丧失稳固性。例如,扮装这个范例。如果一个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通过穿衣打扮这个明喻修辞法引入你的认知作为认定性别的依据,其实,这个性别判定不具真实性。因为这是自然化的认知,它是建立在一系列“共识的”(intelligible)文化伦理推论基础之上的,如果把扮装换成变形,衣服遮掩下的生理性别则无从判断,用以表达身体的衣着无法推断出稳定的解剖学的判断。
性别的范畴界线变得模糊,我们习得的稳固的、惯常的文化认知不足以应对面前这个人,当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性别成为“问题”的时候,对人的二元形态的划分、异性恋的身体、“正确”的男/女身体特质等有关伦理的范畴受到拷问时,关于范畴的思考、关于“正确”性别的伦理文化表达、关于“共识”的文化规制的批判就浮出了地表。
于是,性别成为“一场行动”[2](P183)。在厘清了性别范畴的排他性后,巴特勒继续哲学式消解性别的伦理正义行动。行动的革命性在于揭示划分性别的脆弱本质以及用规制外的性别实践对抗异性恋规范所施行的暴力。这类洞见使得巴特勒看到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表演的结果,性别不再被理解为自我的身份被建构的基础,而是作为言语行为表演的结果。
在什么意义上性别是一场行动呢?在文化实践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足以解释扮装或易装等性别被戏仿的事实。性别实质上是一种给定的身体风格,性别化的主体通过社会集体协议,共同表演、生产和维护这个二元形态的文化伦理预设,这个预
设的文化期待由此生产和积淀了一系列性别特质。同其他仪式性的社会习俗一样,性别的行动需要不断重复的表演,表演的结果使得性别获得一个临时表象,这个表象如同扮装,有时“表里不一”,这个不连贯的行动构建一个由操练得来的偶然状态,重复的性别行动只能趋近一种实在的身体理想,有关身体的理想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以政治建构为目的的戏仿而已。最终,性别表演的结果就是没有恒久的性别身份,因为“真实的性别身份的预设只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2](P185)。
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并不是要为主体寻找那个原初的、前文化的同一的位置,正如美国伦理学家苏珊·弗兰克·帕森斯(Susan Frank Parsons)所说“她了解这种做法只是将法律政权推向形而上学的思考”[3](P164)。巴特勒深知这样做不能跳出律法和规范所圈定的二元思考范式和界线。女性主义性别政治只是为性别问题取得了一个安身的可能,而对二元对立范畴的吸纳反倒验证了律法对精神的管控,如同福柯在《规诫与惩罚》中所批判的那个“渴望承认、服从的个体”⑦福柯认为主体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对于规范和服从的欲望”的产生、创立、内化和外化的精神生活完成的。而精神的服从正是标志着服从的一个具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规范,因此,“这种规范的精神实施得自预先的社会运作”。[6](PP16-20)。那么,“法门之外”⑧《法门之外》是卡夫卡的一则寓言式短篇小说。巴特勒在看到德里达对这则寓言的解构阐释之后,着手写作《性别麻烦》一书,重新思考性别。的那个人何处安身?那些没能符合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规范的某些“性别身份”何处安身?正是在揭露这个男/女“文化规范矩阵范畴”的局限过程中,巴特勒打开了性别无序的另类伦理矩阵,并开放了某些性别身份的伦理边界,使得性别多元伦理身份得以持续存在并增衍。
三、伦理主体的再生产
如果说巴特勒80年代专攻黑格尔的思想在法国的接受,90年代转向后结构主义理论,揭示女性主体在父权制话语系统中被建构和塑形的过程,那么21世纪,她则关注伦理学对主体的公平和平等的表征,致力于表达被赋权者获得权力的政治伦理意义。以往巴特勒力图说明性别范畴是一种前身份,是文化分配的结果,揭示性别表演背后的话语权力运作机制,可以说她更多地注重反思社会规制的管控系统。新千年以来,巴特勒把注意力转向伦理批判的效力和能动力。简言之,巴特勒认为权力不仅仅支配和压抑主体,并且生产主体,主体在寻找外在于自己的存在的认同,欲望的主体为了存在只能选择服从,并在对权力/律法或社会规范反复地吸纳和引用过程中,被生产出一个屈从的主体。这个主体在服从的范围内,接受规范对主体精神的管控运作,成为“忧郁的性别”[6](P130)。
巴特勒将她的思考深入地写进了《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这本哲学专著中。书中福柯对巴特勒的影响不言而喻。可以说,正是由于福柯,巴特勒转向政治伦理批判。早年她在阅读福柯《性经验史》和《规诫与惩罚》时,就开始“寻找性别的起源、欲望主体的内在原理以及压抑所阻止的真实或真正的性别身份”[2](P8)⑨也正是受到福柯《性经验史》中对身体的谱系学考察的启发,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就已经开始了对性别范畴的谱系学研究。她不是简单地动摇这些范畴,而是力图思考作为铭记性别差异的身体对性别的引用的理论意义上的暗喻。。福柯在《性经验史》的第一卷《知识意志》中悉数权力的渗透和效力。权力把个体塑造成知识的主体,规训身体,使其臣服和吸纳社会规范。在福柯的性秩序中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压抑性的。福柯对17世纪以来有关性在宗教中的形成以及在现代语境中如何演变成规训和治疗的技术进行了研究。在第二、三卷中福柯一改批判和反思的路数,转为论述伦理学和自我的技术,即个体是如何通过一套伦理学和自我塑造的技术来创造自己的主体。对于巴特勒来说,福柯的这本未竟其志的著作给了她思考走出女性主义困顿态势的伦理批判启示。巴特勒推进权力生成主体的界说,把规范中的“禁律”转化为主体回望自我时所获得的具有能动性的内在伦理驱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一个抵抗的支点,而是力图超越那个被压抑的为了生存而存在的伦理主体。主体在回望那个服从的自我中寻找具有拯救希望的哲学话语,生成面向未来并具有共同人性的、开放的伦理主体,延续“人何以为人”的性别伦
理思考。
在消解/拆解性别之后,巴特勒为续写性别伦理政治提出了“生成中的性别主体”的观点,让性别“保持移动”[6](P155)。“生成自我”不是简单地挑衅和反对主体的位置,而是将“我”暂时悬置,在不稳定的重复和危险的身体实践中,在社会存在的边界上保持移动,反抗预设的性别伦理“暴力”。这也是巴特勒借助主体在回望那个“服从的自我”时表达拯救希望的可能,在重新生产主体的过程中重构性别伦理主体的意义[6](P156)。正如历史上父权制对女性的整体忽略和压迫,对避孕权、堕胎权和对孩子的绝对监护权的要求实质上预设了某种类型的女性伦理主体,如女性气质、母亲和异性恋。那么,那些不一致或不连续的性别化存在——看起来是人但不符合人所定义的文化共识系统里的人,如何用两性伦理归类?又怎能被“代表”?
巴特勒在文学虚构作品中对“非人”(less than human)的甄别正是回望“人”这个主体的文学伦理批评实践。借助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⑩有关安提戈涅的论述,参见笔者论文《性别与伦理间的安提戈涅:黑格尔之后》,《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8-153页。、卡夫卡的奥德拉德克(Odradek)⑪卡夫卡笔下虚构的非人。奥德拉德克,某种造物,一个线轴,一颗星星,滚动在房屋的楼梯上或楼梯下或楼梯附近,唯一让主人公感到不安的是它将活得更久。这种东西已不是动物,也不是生物,充斥着“种”的变异和无规定性以及无法归类性。,巴特勒把“非人”的状态作为伦理批判的参照物,开发能够照见人类并不完美的断裂之处,这个断裂之处正是人类在划界时忽略的处于边缘和底层的“非人”渴望被承认的政治伦理诉求。巴特勒以自身拒绝划定身份的政治姿态为例,在文学批评领域,这个没有终极意义甚至激发误读和错读的可能场域,为“非人”正名。
作为福柯和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追随者,巴特勒为现实中的“非人”也发出了同样的生命权力诉求。一方面,巴特勒认为对于生命的管控和实施见诸对赤裸生命的暴力,比如关塔那摩的囚犯、艾滋病患者、医学意义上的实验生命、性别“酷儿”等。巴特勒看到作为权力的他们,无论是否意识到,都在以主权的名义统治着我们,这正是看不见的主权。另一方面,主权/法的构成也依赖于例外状态下的“非人”。巴特勒认为辨识“非人”的努力,不是为了解放这些“赤裸生命”,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如何让“赤裸生命”在文化共识(cultural intelligibility)意义上得到承认的问题。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考察了欲望的形成机制时所论,受规训的主体由压制性法律所产生,是法律权力通过规训实践在历史中所制造出来的。对福柯来说不存在被压抑的主体需要解放,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具有压制性,也具有解放效力。这就是说,解放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或者一种话语取代另一话语,存在的只是转变而非对权力的超越。若想成为在文化上得以承认的主体,我们必须首先依附于法,这就是臣服(subjection),而后我们才能获得能动性(agency)。权力塑造主体,但是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可以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能动性。正如她自己,作为权力再生产的主体,巴特勒要以反对她自己的面目出现,坚持自我的欲望,坚持异他性(alterity)⑫巴特勒有关异他性(alterity)的观点受到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思想的影响。列维纳斯的他者是针对自我提出的概念,巴特勒在此基础上从异己出发,在政治与伦理间建构“我”和“非我”之间的关联,“它”处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中间性”(in-betweeness)。这个中间性正是巴特勒需要用来描述超越二元对立关系、处于过程中的状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是一例。而巴特勒和列维纳斯都是犹太裔学者,他们对犹太人的“异他性”问题有共识。见本文第三部分详述。。她的坚持至少表明,她在思考叙述的自我和阅读的他者之间的美学和伦理的指向问题。因为自我和他者需要“成为互相认同的人类”[8](PP29-30)。新世纪新人文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提供给人类表达权利和价值的潜力和空间。面对日趋被同化的美国犹太人的身份问题,巴特勒表达了对犹太性的政治学关切。她认为,被同化的犹太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被抛入历史的夹缝中,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是无法获得自身意义的它者(not-me/non-Jews)。承认的框架的边界究竟划归在哪里?
四、建构它者伦理:向未来开放
正是在回归列维纳斯他者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巴特勒提出了“它者”“文化共识”的概念。其实,早
在《性别麻烦》的结尾处,巴特勒就提出性别是一项关于“文化共识”问题的工程⑬“文化共识”不仅要求性别表演的个体有义务浮出异性恋矩阵中的权力/知识框架,而且提示主体应该认识到“我成为性别化的我是为了生存,而性别化了的我与异性恋合谋共同建构了这个主导的性别体系”[2](P139)。。“9·11”事件之后,美国少数族裔的流散性和性别文化身份如何重新被认定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5](PP35-36)。这个“认定”问题引发了一个伦理问题:以美国的犹太人的归属问题为例,我们如何面对因差异而带来的对“人”的重新表达和定义?我们如何学会接纳它者(not-me)被排除在西方理性主义思考模式之外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伦理观?作为道德的主体如何使人——不同人群、族群——的生命可活(live a livable life)?如何为共同的人类未来负责?
巴特勒在她的最新力作《十字路口:犹太性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2012)中,论述了列维纳斯、阿多诺、赛义德有关犹太性的理论,并理顺一条关于“他者”的美学——自我意识的自足性需要一个他者的在场。这个自足的自我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种伦理他者、一个大写的他者(Other),并非一个小写他者(other)。小写的他者表明自我依赖他者,是被我所吸收和同化的对象,大写的他者乃是因为“异他性”而不能被具身化的东西。
巴特勒回溯到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伦理学并获得灵感,在颠覆传统哲学引以为自豪的主体概念上,从他者出发,进行了一系列重构、拯救伦理主体的工作。但是,巴特勒的它者(not-me)有别于列维纳斯的他者。列维纳斯的他者是确定的他者,需要借助语言或某种媒介提出主张。正如盲人需要语音引导去完成被指称的询唤结构。但是,这种询唤结构通常依赖已知的存在的某种语言、习惯或媒介,这个被询唤的结构被划定的边界总有未被命名和指称的空隙,在有误的询唤和个人的错位感之间的窘境找到“我们”这个称呼的意指和“我们”所处的临时性(temporality)。不同于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巴特勒的它者存在于政治与伦理间的“相关性”(relationality)上。通过它者的“介入”[7](P253),伦理“不再被理解为根植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或行为方式。而是为了回应来自于主体之外的责任而进行的一系列相关性实践,挑战主体和本体论的关于自我身份的言说”[8](P9),实际上,它者伦理指向那些“我‘不是我’的空间中的行为”[8](P9)。伦理的核心问题在巴特勒看来,应该是“如何、是否和以何种方式‘让位于’它者”,有关这些问题的伦理反思,并不是回归主体她或他,而是可以理解为保持移动的相关性上。对于被驱逐出领地和国家的犹太人来说,要用超越自我的越界表现回击那些固有的偏见和言论,以便去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并重新定义超越民族主义的有关社会和政治的义务”[8](P10)。
作为在美国的犹太裔学者,巴特勒以自身的“犹太性”为“介入”的切入点,把犹太传统作为她的哲学思想素材加以改编和重新塑形,与鼓吹犹太复国和重建以色列国家的思潮分裂。她把自身放进有关人种的思考之中。正如她在“消解性别”时秉承的解构单一性范畴的精神,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她把有关人的概念放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坐标中,用“文化翻译”的策略重新定义文化身份。这里讲的翻译不是“两种封闭的、相异的、自成一体的语言之间的翻译。这个翻译会迫使每种语言发生改变,以理解另一种语言,而这种理解发生于熟悉的、具体范畴内的以及已知事物的边缘,并将成为伦理和社会转化的发生场所。会造成失序和迷乱状况,但同时也会更新这个范畴”[4](P38)。巴特勒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预先确定正确的文化共识的方向,会导致文化翻译的工作吸纳“规范”(norm),“规范”则无法使生命过上“可过的生活”(livable life)。
巴特勒用“我注六经”式的政治策略,对《塔木德》、《古兰经》等犹太素材在非犹太语境中开展“文化翻译”工作。她认为“只有通过从一个空间临时的矩阵中移位、挪用才能使得某种传统在‘非我’的领域与它者性接合”[8](P12)。翻译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接合的断裂之处起作用,并成为辨识两者的相关性的工具,目的在于让“文化政治变得民主”。虽然民主不可能和谐地表达,但对不同人群的划界问题保持开放态度,则是让多种生命形式得以生存的可能路线。
巴特勒为了使这种文化翻译工作不至于被美国的大熔炉“同化”或“吸收”,她提出文化翻译中的权
力问题。这个观点显然受到德里达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的影响。翻译的政治和伦理任务是德里达论述翻译的两个重要命题。翻译是政治的,因为翻译依赖语境,而语境则受制于句法、语法、语用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非自然因素。正因为语境具有这些不确定性,任何语境都是不能完全封闭的,在缝隙和裂痕之处,它者得以介入,“既然一个语境是在翻译活动中向它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个语境的开放,于是便产生相互的责任问题、负债问题和履行职责的问题”[9](P39)⑭参见陈永国:《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外国文学》2005年第5期。论文中就斯皮瓦克的翻译政治的哲学来源和在后殖民批评和女性批评中的拓展和延伸进行了翔实和透彻的分析。。斯皮瓦克则紧随德里达,将翻译的政治带入对印度属下妇女的性别伦理的考究中。翻译的过程不仅仅是“词语的换置和意义的传输”,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穿梭更多包括因为语言的修辞性和沉默而生发的“偶然性”、“任意性”和“不规整性”。在恰当的语境和位置上,挪用和重置词语的修辞性以便完成对历史的书写。巴特勒受到启发,在西方智识传统链条中寻找“未解决的”和“没有授权的”知识“缝隙”和“裂痕”。从违反常规、偶然的偏离轨迹中考察传统的认识论框架。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上演一出与任何已有学科的认识局限的遭遇战。将这个学科带入一种危机,一种使用任何策略都无法同化和消融差异的危机”[8](P13)。
巴特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犹太教的话语文本素材“译成”公共话语,“意在抵消宗教话语,支持公共话语转码”[8](P16)。这个隐含的意义表明“宗教是一种特殊主义⑮“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两个概念,在文化、政治、文艺、宗教、法律等领域都有所应用。在哲学上,这两个概念分别是指知识或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知识是事实判断,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与反相对主义之争,涉及有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的问题;价值观是价值判断,在道德领域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涉及有没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观的问题。、部落制或是社群主义,必须‘译成’(原文加引号)通用和理性的语言确保公共生活中的合法和受限区域”[8](PP13-14)。巴特勒超越了德里达和斯皮瓦克的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的语言转换实践,将有关犹太性的历史“流放”译成或者说建构成当下的“流散”意义,“做一个犹太人就需要背离自己,走近非犹太人(non-Jews)的世界,这注定要在无法逆转的霸权主义秩序内开启一条伦理和政治之路”[8](P15)。这也是对斯皮瓦克“翻译是权力的领域”的当下思考⑯转引自Judith Butler,Parting Way.P 12.原文出自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More Thought on Cultural Translation,Http://eipcp.net/transversal/0608.spivak/en.。或者,如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⑰阿萨德采用尼采所开创、在福柯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谱系学方法讨论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性问题。所说,文化翻译的实践“不可避免陷入权力之争”[10](P15)。
巴特勒并非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借助犹太人的文化特性,进一步延伸她的“它者”伦理理论在文化研究上的可能性,这也是巴特勒对政治伦理批评的贡献。因为她在谈论犹太人的文化共识问题时,所把握的正是人的政治、文化以及日常活动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并指向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的关系。就犹太性的文化共识问题,巴特勒认为犹太人和宗祖国当地人共生的问题不应是文化同一性问题,而是文化多元主义造就的结果之一。面对“9·11”事件之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呼声的高涨现象,巴特勒提出了从自我赞扬式的“犹太精英主义”(Jewish Exceptionalism)思潮转到“非犹太人”的建构设想。这个设想的实质是在美国的宗教和文化多元性的大背景下,为建立杂居共生的诉求寻找素材。因此对犹太素材、《塔木德》、《古兰经》等文本进行非犹太语境下的“文化翻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巴特勒并非批判犹太复国主义,而是提倡超越绝对的犹太性以便在激进民主主义国家内构设犹太人与宗主国人民共荣的更广泛和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理想。关于犹太性的政治伦理,巴特勒的主张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解决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倾向的可能。
结语:行动的巴特勒
巴特勒把因性别而起的世纪末的理论论战看作一个哲学“问题”。在哲学论述中,什么构成了“人的主体”是个永恒命题。在有关性别的伦理思考中,性别如何形成又如何区分?人是如何通过生理性别、社
会性别或性别取向等稳定的概念确立自身的性别“身份”?这个“身份”又是如何支配主体并认同“文化共识”的规范?那些规制之外的“不一致的”或“不连续的”幽魂如何存在?这些都是巴特勒消解性别和重构主体的最初疑惑,也是她把性别作为“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建构解放的性别伦理的出发点。
作为介入的它者,巴特勒在当代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所进行的有意义的“差异”重建工作留给当代知识分子很多思考[11](P239)。巴特勒从后现代哲学思想家那里获得思考的灵感,从社会边缘人身上汲取思想的活力,关注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问题、关注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利,自觉担负起“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提出知识版图中遗留的“非正义”的政治—伦理诉求。她的“它者单语”发声系统正是留给目前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克服学院派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脱节现象的启示。文化批判的责任之一应当是让自己的学术论战参与当下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活保持相关性,对未来文化研究的走向保持前瞻性。正像巴特勒,对文化研究中不同人群保持“介入”的政治自觉性,这也是关乎人类自身的伦理正义事业。
[1]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20 Century France(with a new prefac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1999.
[2][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三联书店,2009.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with a new preface)[M].New York:Routledge,(1990)1999.
[3][美]苏珊·弗兰克·帕森斯著,史军译.性别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法]露丝·伊利格瑞著,屈雅君等译.他者女人的窥镜[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2013.
[5][美]朱迪斯·巴特勒著,郭劼译.消解性别[M].上海:三联书店,2009.
[6][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张生译.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黄晓武译.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8][美]Judith Butler.Parting Ways: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M].Cambrid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
[9]陈永国.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J].外国文学,2005,(5).
[10]Talal Asad.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A].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1]肖巍.飞往自由的心灵:性别与哲学的女性主义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含章
WANG 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Judith Butler;gender;ethics;culture;Jewishness
In 1990s,Judith Bulter's intervened questioning on the presumption of the essentialist gender dichotomy has changed our oppositional beliefs on gender formation,universal ethics and speech-act of daily life.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discusses Butler’s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especially after she proposed the theory of“Gender Performativity”.It argues that Butler’s contribution,interrogating feminism,reforming the productive meaning of ag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rvival for Jewish Americans,make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dealing with contemporary gender impasse.It would be fair to say that Butler’s ongoing critical endeavor has unveiled a possible correlation that intertwines between gender and ethics.Instead of providing an immediat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atic of gender trouble,Butler prefers to stay in the"becoming"state of gender“in-betweeness”.Her political and ethical probe has lightened up the blind spot of western humanistic tradition:the vulnerability of human beings.The exclusion of“non-human”beings and the neglecting of multi-forms of life still remain unsolvable ethical problem in regards to recognizing their claims of“living a livable life”.
C913.68
:A
:1004-2563(2015)02-0081-09

王楠(1975-),女,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2011-2012)。研究方向:性别理论、美国文学、20世纪西方文论。
This project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Beatrice Bain Research Group,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本文是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朱迪斯·巴特勒与女性主义伦理批评”(项目编号:13YJC752024)、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2014)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