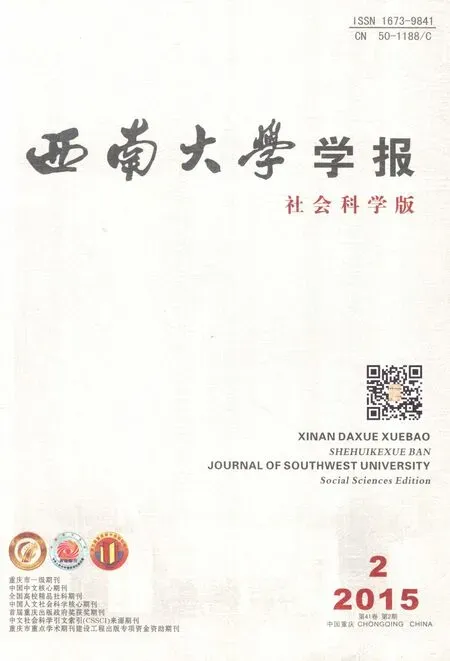从混沌中苏醒: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
2015-02-24许祖华
杨 程,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从混沌中苏醒: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
杨 程,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的涌入,中国传统的身心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思想界逐步形成了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思想,让身体由“虚”入“实”,成为有血有肉的物质实体。而尚武、人种改良、新民运动等思潮,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造个人身体来改造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完善国家制度来解放身体,以此形成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身体刚从封建礼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
身体;清末民初;身心一元论;国家;个人;尚武
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1],然而,身体本身却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物质的身体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点正好与身体转向要求身体本身凝固下来以便身体话语能够依附在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上相吻合;另一方面,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则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流动的。身体话语如何在这种稳定与流动之间寻求到合理的平衡点以便发起真正有效的反击?”[2]这是身体史与文化史上一个长期纠结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身”一直作为“心”的附属,牢牢地被“心”所贬抑和控制着。鸦片战争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保种之道,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国门,对西方国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受启蒙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许多思想家对身体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主张身体平等和身体解放,希望通过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传统的身心观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身”从“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一、身心一元论与身体实体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题。且不论杨朱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3]的极端贵身思想,其他先秦哲学家也大多主张身心一元论,对身体较为重视,《道德经》中有“故贵身于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4]之语,庄子提出了“无情”[5]的观点,试图摆脱思想对身体的束缚。老、庄都希望身体回到“赤子”的原始状态,唯此才是最合于“道”的,才能“逍遥游”,这也就是身体的本体论。不过,老庄思想中已经存在着将身体虚化的苗头,他们所谈的身体并不是以骨骼、血管、肌肉、皮肤组成的物质实体,而更像是与山川、草木乃至宇宙本体在本质上相通的概念化的身体。孔子也是主张身心合一的,《论语》中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6]之语。到了孟子,身、心二者有了显著分野,身成了阻碍心的发展所需要克服的东西:“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7]就是将身摆在了心的对立面,在身体的痛苦中才能“益”其心。后世思想家既接受了孟子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同时又发展了老庄将“身”虚化的理论,使实体的“身”虚化成了“心”的附庸,修身只是克服欲望、保持健康的一种途径,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不断自觉地对身体进行规训来“修心”,由此便导致了身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缺席。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随着西方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引入,传统的身心观逐步向一元论与实体化的方向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彻底的、一蹴而就的,许多思想家还在身心之辨中犹疑与挣扎,这正是晚清五四时期的特点所在。
(一)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的形成
以身为本位就是要尚独、尚私,重情、重欲,重视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传统身心观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身为本位的观念觉醒于戊戌维新时期,当时受西方影响更大的改良派思想家们开始关注并肯定身体的欲望,以康有为《大同书》最具代表性。它虽然成书较晚,但其基本思想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乃至更早,其核心观点是“去苦求乐”,主张重视并满足身体的快乐:“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8]7人生在世全为快乐,“居处”“饮食”“舟车”“衣服”“器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去苦界至极乐”,男女之间快乐即合,不快乐则分。康有为这种以身体为本位、以快乐为目标的“大同”理想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惊世骇俗。然而,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带有个案性,当时许多思想家还秉承以“心”为主导或者身心兼顾的理念,严复就认为:“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9]10
以身体为本位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渐成规模。在这一时期,身体的欲望与意志力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尚独尚私的思想蔚然成风。“以知识为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10]“有英人洛克者,谓健全之心意,宿于健全之身体,以此为教育之大眼目。”[11]这也就是“心”宿于“身”、“身”决定“心”的“身本位”思想的雏形。王国维“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即意志之入于知力之形式中者也”[12]的身心一体思想,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身本位的思想还衍生出了对“独”和“私”的尊重,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的极端贵身思想也不再是受到批判的对象:“今夫杨子为我之旨,不过曰个人独立,不求当世之名位货利,于不侵人自由之范围内,纵一己之欲。此不可斥之为无君明矣。”[13]“且夫无国与无家孰急,则必曰家急;无家与无身孰急,则必曰身急。诚以国与家较,家其亲切焉者也;家与身较,身其尤亲切焉者也。”[14]269这种将一身之利置于国家之利之上的理念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但在这一时期,许多革命家从现实需要的角度仍然坚守着“心”为本位的理念,孙中山就曾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15]
到五四运动前后,以身为本位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尊劳主义和推崇物质文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与重“心”轻“身”的身体观一脉相承。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人阶级地位提升,纯粹的体力劳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16]141不仅如此,劳动还成了人生的乐趣,成了痛苦时的消遣:“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17]187劳动是创造社会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由尊劳主义生发出对物质文明的重视:“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16]246胡适也认为“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所以才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18]5,然而“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18]9鉴于此,胡适对西方工业文明、机器文明是极为推崇的,他认为机器不仅可以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训练人的感官:过马路倘不耳聪目明,就会有危险,“这便是摩托车文明的训练”[19]。然而,工业文明既是对人类身体的解放又是对人类身体的压制,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认识得非常深刻:“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16]177这种不是人统治物而是物统治人的异化现象,是“烂熟”的资本主义文明难以避免的,不过,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当时的思想家对异化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表层上,深入的认识还要等到1930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经济独立对身体独立的决定性作用。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诸多思想家提出了禁止妇女缠足、冲破家庭限制等身体解放的理想,然而怎样将这种理想变为现实,他们大多语焉不详。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意识到了真正的个人解放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身体独立要从经济独立开始。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说:“女子丧失人格,完全是经济的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16]190鲁迅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20]人最要紧的事无疑是生存,如果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那么一切身体解放、个性解放便都是空谈,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正是如此。而一旦有了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个人特别是女性才能不依赖于父兄,不依赖于家庭,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自立”的人生观[21]。
(二)身体由“虚”入“实”的过程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身”虚化,否定身体的实体价值。而在清末民初,“传统的‘修、齐、治、平’之道和‘穷独’、‘达济’之论已经失去实效”,当时的知识分子“似乎只能找到‘身体’这一最切近、最方便,当然也很模糊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各自对民族国家危亡的焦虑”[22]。在这种情况下,一度被忽视的作为物质实体的身体也重新进入了思想家们的视野,而身体的实体化过程也就成了“身体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就开始从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审视身体,“心”被他们拉下了神坛,由与“道”相通的主宰还原为具体的身体器官:“至心之为用,不过能由大小血管送血以通于脑,以充于周身,而身之百骸活焉,而脑之精气足焉。”[23]115郑观应在比较之后提出了中医不如西医的五个方面,对重解剖、科学、实证,“明脏腑、血脉之奥”而“无虚设、无假借”[24]166的西医极为赞赏。这可视为清末民初之际身体实体化之滥觞。不过,对中医的信服和对西医的怀疑难以在短时期内骤然改变,薛福成认为:“余谓西医之精者,其治外症固十得七八,但于治内症之法,则得于实处者多,得于虚处者少。”[23]98
在其后的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理论的大量译介特别是《天演论》的出版,使中国知识分子更自觉地运用自然科学原理来审视身体。较有代表性的是“有机体”“质点”及“以太说”。唐才常认为身体是由“质点”构成的,组成人体的各类元素也组成了自然界的其他物质,故而人能与天地万物相通:“是为地天、人天、天天,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质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与。”[25]52这是将西方原子学说与佛教“宇宙全息”的思想融合了起来。谭嗣同的观点与唐才常颇为相似,提出了“以太说”。“以太”本是西方科学家假想出的光传播介质,谭嗣同借用来阐明自己的哲学理念,将“以太”视为一切物质组成的本源,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类似于中国传统的“道”,人体死亡后,以太又将重新“粘合”成新人。不过,以太说只是谭嗣同为中国传统身心观披上的一件洋外衣,骨子里仍旧秉承重“心”轻“身”的观点,不生不灭的以太只是将佛家轮回与性空理论换了种说法而已。在《仁学》中,谭嗣同一再表示:“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26]5“乃中国之谈因果,亦辄推本前人,皆泥于体魄,转使灵魂之义晦昧而不彰,过矣!失盖与西人同耳。”[26]34“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26]96不得不说,谭嗣同将个人身体视为毫不足惜之物的身心观和他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行为有着必然关联。总体说来,唐才常和谭嗣同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依旧强大,试图在西方理论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对接点,用自然科学理论对佛教和儒家的某些理念进行全新阐释。比唐、谭二人走得更远的是严复,他率先用“有机”二字翻译了英文的“organism”,将人体视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各部分协调运作的“有机体”:“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9]197这就不仅将身体视为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并特别强调了身体“物”之本性,也就是将身体看作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实体,直到今天我们仍常常将“有机体”作为身体的代名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推崇以及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历史而不单单局限于生物学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建立之后。
到辛亥革命时期,很多思想家已经接受了西方关于物质组成的“原子说”并将其本土化。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人们进一步重视遗传学说,对细胞内的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主张优生优育以改良人种,并已意识到中国只重父系血缘而忽视母系血缘所导致的姑表亲、两姨亲等近亲结婚之弊端。章太炎说:“核丝之远近,蕃萎系焉。(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善。)故父党母党七世以内,皆当禁其相婚,以血缘太近故也。”[27]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宏观上的泛泛而论,而是深入至细胞、染色体等微观层面,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时期,身体的实体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人的身体早已不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依附于“心”的存在。
二、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身体
清末民初之际,随着人们对身体的再发现、再认识,种种身体解放、身体平等的理论不绝于耳。然而,追求身体解放和身体平等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解放自己还是为了拯救国家?大多数思想家给出的答案都是后者。在那个危机深重的年代里,改造个人身体是与强国保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一项政治任务,其中又包含着自下而上试图通过改造个人身体来拯救国家和自上而下依靠改变国家制度来解放个人身体这两个部分。这种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身体的纠缠,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到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身体更是每每成为社会的焦点,并多被放大成为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对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应有作用。”[28]
(一)从个人到国家——尚武、练兵与人种改良
长期以来,中国美男子的标准是“白面有须”,中国人欣赏的是谦谦君子的潇洒飘逸,而非赳赳武夫的雄壮威武,长此以往便导致了中国人身体的文弱。中国第一位公使郭嵩焘在出使西洋时看到洋人体格强健,能用额头和手掌击碎核桃,同时又“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不禁感叹:“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29]
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很多人甚至有吸食鸦片的恶习,以至于身体羸弱。鉴于此,他们开始呼吁“习武”“练兵”,试图扭转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思想,打造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才。薛福成认为:“宋明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23]96郑观应说:“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24]90这说明当时的思想家意识到,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已经成为避免亡国灭种厄运的必要途径之一。
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还是从提升军力的角度来倡导身体训练的话,那么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是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提倡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改变“中国者,固病夫也”[9]18的现状。同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也意识到家国天下并不是属于君主一人的,而是由无数人的身体乃至无数身体上的器官组成的:“世界一耳目心腹之所积也。积耳目心腹而成人,积人而成家,积家而成邻,积邻而成里,积里而成乡,积乡而成党,积党而成都邑,积都邑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25]79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30]10如此一来,个人的身体素质就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鉴于此,严复主张“开民力”,并将“民力”与“民智”“民德”一起视为“生民之大要”。可以说,对中国人体质病弱的忧虑和对尚武、尚动、开民力的提倡,成了戊戌维新时期及后世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基点,对身体的改造升华为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改造。“倡言‘新民’、‘公民’,都是意欲使‘国’与‘民’的结合更加紧密,使个人由家族依附转向为国奉献。”[31]
同样是受进化论的影响,戊戌时期的思想家们逐步明确了人种的概念,认识到各个人种都处在进化之中,要想不被其他人种所淘汰,中国人就必须通种、保种、进种。唐才常著有《通种说》,严复提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主张。由于当时欧美国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唐才常、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皆认为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体现出了白种崇拜的倾向。梁启超说:“白人之优于他种人者,何也?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30]13当时的思想家均认为保种是要务,要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立足就要通种、进种,让中国人向白种人靠拢。由此观之,中国长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落后,渐渐演变成了对中华民族乃至黄种人本身的不自信,文化、制度上的劣势导致了中国人在身体上的自卑。此外,在个人与种族关系方面,许多思想家主张,当个人利益与种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于整个人种的利益,甚至要为种族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存权,这就是严复所说的:“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9]25
自此之后,通过尚武、练兵、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来强国保种的理念就蔚然成风。“20世纪初叶的中国确实对身体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与坚持。从康、梁一辈开始,知识分子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努力于推动各种的身体改造运动,营造一个有关身体‘应然’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32]191902年由沈心工作词的一首学堂乐歌就颇能体现这种风尚:“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冬冬冬冬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不仅尚武练兵、强国保种的身体改造工程直接与国家利益相连,即便是身体解放运动,也割不断与国家利益的联系。比如,康有为《大同书》一方面推崇男女身体平等:“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8]147,“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8]148,“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8]178;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堕胎:“为全地人种之故而思保全之,则禁堕胎乃第一要义矣”[8]241,“夫大同之道,虽以乐生为义,然人为天生,为公养,妇女代天生之,为公孕之,必当尽心以事天,尽力以报公,乃其责任,妇女有胎,则其身已属于公,故公养之,不可再纵私乐以负公任也;若纵私乐以负公任,与奉官而旷职受赃同科矣”[8]233,这又分明是打着公家的幌子将妇女的身体视为生育之工具,让妇女的身体刚从男性和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旋即又落入了“公”的魔爪。辛亥革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妇女解放、禁止早婚,试图让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工作、参与社会活动,其思想的本质与目的和康有为相通:“那就是将身体的‘殖民’权利由家庭和礼教体系转移到国家的手上。”[32]23“‘国’在清末正逐渐取代‘家’的地位成为身体的新统治者。”[32]113妇女的解放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解放了妇女就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禁止早婚又可以改良人种,这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将个人身体与国家直接挂钩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更是与中国传统观念合流,发展出了新型的“舍生取义”思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他们无不主张牺牲个人、共赴国难:“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33]“故我劝列位撞着可死的机会,这死一定不要怕。……泰西的大儒有两句格言:‘牺牲个人(指把一个人的利益不要)以为社会(指为公众谋利益);牺牲现在(指把现在的眷恋丢了)以为将来(指替后人造福)。’这两句话,我愿大家常常讽诵。”[34]“‘身’和政治紧密地结合着,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革命’作为非常态的政治手段,它既以身体(改造、消灭、新生)为目标,也以身体为工具”[35]。孙中山、陈天华和邹容舍生取义的理想,就带有鲜明的将身体工具化的倾向。而严复所翻译的“有机体”一词正来自希腊表示工具的词汇[36]。其他重视个人身体的思想家,也无不同时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联系,个人对民族应尽的义务,重视杨朱利身思想的同时不忘墨子的博爱。“自我身、我家、我国以至于我民族,皆与我有绝大之关系,皆我私也。自我身、我家、我国以至于我民族,若有迫不得已之事,皆我私事也。”[14]270“墨子兼爱之旨,不过曰欲人之爱利吾亲,必先爱利乎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13]这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自私与博爱完全对等同一化的说法难免牵强,但却鲜明地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个人至上与民族至上之间的摇摆、犹疑。一方面是冲破封建束缚的启蒙主义,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国家主义,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下,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折中、调和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到了高扬启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五四时期,不为国家牺牲个人的思想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37]“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6]104特别是针对自杀行为,许多思想家都有委婉的批评:“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16]40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38]然而,中国自古便把身体当作是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附属物,“舍生取义”的行为总是被当作美德传诵千古,以对身体的抛弃来达到所谓的名垂青史,这实际上是对生命和身体的漠视,是死后的名分对活着的身体的压制:“在历史上,只有孝女,贤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却没有一个‘女人’!”[39]五四时期这种对个人的解放、对虚伪的民族大义的反抗、对个体权益的提倡,恰恰是对身体的重新认识与发现,正如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17]205
(二)从国家到个人——破除礼教钳制,维护身体权利
清末民初之际的思想家们一方面极为重视自下而上由个人到国家的身体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自上而下调整国家的法律、制度,破坏钳制身体的封建礼教来达到身体的平等与解放。
在古代中国,受儒家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中国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秩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40]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体权利往往由身份决定,甚至犯罪量刑也是如此。比如子杀父与父杀子,同是对他人生命权的剥夺,但由于父与子在封建身份等级上的不同,子杀父即为十恶不赦之罪,定当处死,而父杀子却可酌情减免量刑。“男子杀妻,罪不至死。女子杀夫,则有凌迟之刑。男子停妻再娶,不过笞杖,女子背夫改嫁,罪至缳首。(曰停曰背,轻重可见。)”[41]259所以,要打破身份对身体的钳制,就要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维护身体平等,使中国社会“由伦理法走向权利法,或者说,由家族本位走向个人本位的身体权利演变”[32]92。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资政新篇》就提出了一些维护人的基本身体权利的举措,如:开设医院;兴办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废除酷刑、禁止溺婴、缠足、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婢等。到洋务运动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对西方法治社会人人平等、赏罚不以身份差别而异的现象已有了初步认识,薛福成就注意到:“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23]99特别是他们发现西方人对妇女较为尊重,有女士优先的传统,与中国压抑、束缚妇女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君民平等、男女平等的观念。王韬提出一夫一妻制思想:“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42]11郑观应《女教》极力反对缠足这种残害女性身体的行为:“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24]121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女子才力不输男子的言论在当时也是极有震撼力的。何启、胡礼垣认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43]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自主力,不受控于君、父、夫。另外,身体的平等不仅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也体现在华洋之间。当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犯罪亦不由中国审理,由此就导致了洋人犯罪每每量刑过轻,洋人与华人在身体权益上极不平等。对此,郑观应主张:“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无分畛域。”[24]215
在刑罚方面,中国古代历来重“刑”(主要是肉刑)轻“罚”,审讯当中经常严刑拷打,乃至屈打成招。郑观应、王韬等人认为残忍的肉刑绝不能起到怀柔惩戒、改过自新之功效,不如外国刑罚那样“宽严有制”,故而必须予以革除。如王韬认为西洋犯法者“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狱制之善,三代以来所未有也”,而“国中所定死罪,岁不过二三人,刑止于绞而从无枭示”[42]157。郑观应认为:“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24]214与反对妇女缠足类似,郑观应也反对阉割这种残酷的肉刑,在《阉宦》一文中,他认为阉割乃是“极弊之政,为合地球所共无者”[24]200,“是故古今异势,治乱异法,古虽有之,今亦宜绝”[24]201。这些取消肉刑的呼吁,使刑罚从对身体的迫害转移到对身体的拘禁上来;从对肉体的粗暴惩罚以及对这种惩罚过程的丑陋展示转移到限制肉体自由的规训上来,这无疑是更合于人道,是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除了刑罚之外,中国古代的礼仪规范也是建立在身体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举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无怪乎相习而成风也”[44]。因为不平等,所以身份地位较低微的臣、子、妇就要在拥有更高地位的君、父、夫面前表现出身体姿态上的驯服——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等等。这种等级差异不仅体现在身体姿态上,也体现在服制上:“男子丧妻,持服仅及期年,等于父母之丧子女。女子丧夫,乃有三年之服,等于子女之丧父母,且有终身不释者。”[41]258-259“人们可以从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之中发现,儒家学说对于人体的规范训练几乎面面俱到;这种训练显然从属于‘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于统治机构说来,人体不是某种单纯的物理存在,人体必须充当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45]要达到身体的平等与解放,让身体获得独立性,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就必然要破除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当时很多学者更是认为要破除封建的“三纲五常”就必须破家、毁家,打破父母、兄弟、翁姑、丈夫对妇女身体的暴政:“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矣。”[46]正所谓不破不立,如果不能自上而下从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社会的礼仪、规范、习俗等方面加以改革,那么身体的平等与解放永远都只能是一纸空谈。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身体意识的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身体平等与身体解放的理念也日渐深入人心。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身体刚从封建礼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如果说传统中国人的身体是隶属于家庭的,那么清末民初大多数思想家们理想中的身体就应该是隶属于国家的。换句话说,他们试图让身体完成从伦理化的到政治经济化的转型,让身体成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基点,用规训的方式,针对“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进行“安排和征服”,因为“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47]。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个人与国家的互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国家不单是代替家庭控制身体、制约身体的压迫性力量,很多时候它还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推动着身体平等、身体解放。而身体到底应该属于个人,还是应该属于国家,这个命题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3.
[2]赵淳.身体话语:诉求、突破、抵抗[J].外国语文,2013(3):1-4.
[3]王先慎.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8:353.
[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50.
[5]陈鼓应.庄子今注全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93.
[6]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76.
[7]焦循.孟子正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6:576.
[8]康有为.大同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9]胡伟希,编.论世变之亟——严复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0]章太炎.菌说[M]//章太炎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
[11]刘显志.论中国教育之主义[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32.
[12]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M]//王国维文集:下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191.
[13]吴虞.辩孟子辟杨、墨之非[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36.
[14]剑男.私心说[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5]孙中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自序[M]//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
[16]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7]高瑞泉,编选.向着新的思想社会——李大钊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18]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M]//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9]胡适.漫游的感想[M]//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
[2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7.
[21]胡适.美国的妇人[M]//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44.
[22]程亚丽.新身体·新民·新国家——论晚清民族危机中现代身体话语的生成[J].社会科学辑刊,2010(6):226-230.
[23]薛福成.筹洋刍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4]郑观应.盛世危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5]郑大华,任菁,选注.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6]加润国,编.仁学——谭嗣同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7]章太炎.族制第二十[M]//訄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01.
[28]程亚丽.“脚”上的政治:晚清“废缠足”小说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74-178.
[29]陆玉林,编.使西纪程——郭嵩焘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1.
[30]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1]郭继宁,郑丽丽.“疾病”与“治疗”——对清末新小说中一对隐喻的考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49-151.
[32]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3]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M]//朱正,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71.
[34]郅志,编.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63-64.
[35]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0.
[36]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5.
[37]蔡元培.《国民杂志》序[M]//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255.
[38]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
[39]胡适.女子问题[M]//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20.
[4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38.
[41]愤民.论道德[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3]郑大华,编.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53.
[44]佚名.箴奴隶[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80.
[45]南帆.文学、革命与性[J].文艺争鸣,2000(5):22-32.
[46]汉一.毁家论[G]//胡伟希,编选.民声:辛亥时论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39-140.
[4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7-28.
责任编辑 韩云波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揆诸明代史的演进历程,正统“己巳之变”而导致的一时政治危机,却因名臣于谦的挺身而出,从而使危机化为乌有,且历经成化、弘治两朝的善治,更使社会暂趋稳定,甚或享有盛世之誉。武宗继位,沉溺游逸而无心治国,因绝嗣而国无储君,又一次使明代陷于危机之中。正德末年,看似简单的皇位传承,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政治史信息,却颇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加以重新审视。如何解读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乃至社会危机?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显然已经作了较有建设性的解读。田澍所撰之文,通过广征博引的史实考辨,证明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处理绝嗣危机时的种种失策之举,不失为一种让人耳目一新之论;陈旭所撰之文,虽仅以论证林俊与“大礼议”的关系为主旨,然“大礼议”实为正德、嘉靖之际政治危机的主要表征。就此而论,两文实则互相呼应,对于解读正德、嘉靖之际的这段历史颇有裨益。当然,正德、嘉靖之际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诸如因《嘉靖事例》与《嘉靖新例》的出现而导致制度性的变革,或因“大礼议”而导致的士风变化,无不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课题。
I206.5
A
1673-9841(2015)02-0131-08
10.13718/j.cnki.xdsk.2015.02.017
2014-05-01
杨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