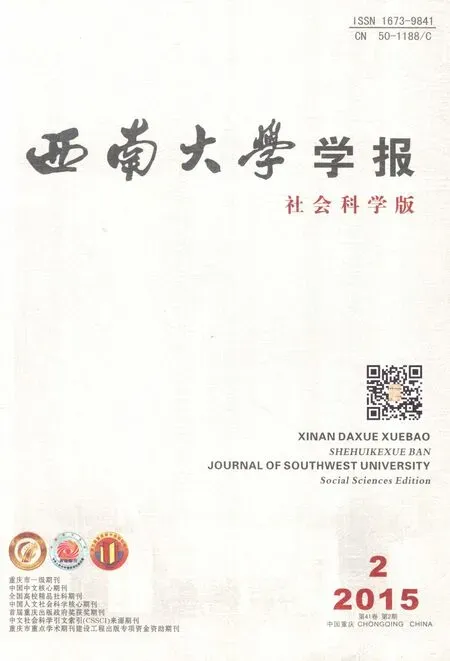经典文本也有分裂与解构性∗
——以卡夫卡《城堡》为例
2015-02-24高玉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经典文本也有分裂与解构性∗
——以卡夫卡《城堡》为例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文学作品必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作品各内在因素必须“一致”“统一”“和谐”,这一观点并没有充分的哲学根据和文学史根据。传统的经典作品也可能具有后现代性。《城堡》是一个分裂和解构的文本,具体表现为:不具有风格上的统一、内容上的统一、结构上的统一,不是内在的有机统一,故事和情节都缺乏清晰的描写与交代,情绪、情调、思想、表述、手法等通常都不一致。没有传统小说的那种“主题”,描写和叙述有很大的跳跃性,描写与描写之间、叙述与叙述之间缺乏主体上的逻辑性,缺乏事件上的前因后果。小说到处相互矛盾,比如时间上的矛盾、人物性格上的矛盾、叙述人称上的矛盾等。卡夫卡把“矛盾”正常化了。
《城堡》;卡夫卡;矛盾;解构
一、经典作品与后现代手法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作品的主题是中心,所以“主题”也被称为“中心思想”,而作品的其他因素诸如创作方法、结构、体裁、故事、写作技巧等都是为了表达中心思想。具体到主题和结构、表现手法等,也是高度统一的,各自构成有机整体。所谓“统一”,并不是单一,故事也好,情节也好,内容也好,可以多样,但多样不是散乱、冲突、矛盾的,而是要求和谐、一致,具有某种共同性。散文讲究“形散而神不散”,小说讲究“收放自如”、“大开大合”。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强调因果关系,强调集中,强调内在逻辑等。传统写作特别强调把可有可无的东西删去,如可有可无的人物、情节、词句等。传统的文学作品也有冲突和矛盾,也有前后不一致,但这被认为是写作的不成熟或失误,是作品的硬伤,是作品层次低的表现,传统观念中的优秀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首先,从理论上说,要求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不矛盾、不冲突、不分裂,这实际上是没有哲学根据的,也从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论证,恰恰相反,后现代主义倒是论证了文学作品分裂和解构的合理性、合法性。其次,经典作品并不是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都是有机统一体,都精致得没有矛盾和冲突。一旦我们不再接受“一致”“统一”“和谐”“有机”的文学观念,就会发现很多经典作品并不精致,矛盾、分裂、冲突和解构也是经典作品的重要特性,很多经典作品的“一致”和“有机”等特征其实是被“解释”出来的,很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也具有后现代性。其中卡夫卡的《城堡》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分裂和解构特征的经典作品。
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今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思潮,但它却并不是在“后现代主义”话语和言说方式产生之后才产生的。盛宁说:“‘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衔接关系,无非就是‘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的概念之后,‘后现代’这个概念是建立在‘现代’这个概念基础之上。”[1]也就是说,“现代”和“后现代”仅仅在概念上具有先后和承接关系,而作为现象不分先后。或者说,“后现代”是性质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作为一种精神品质,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它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高宣扬说:“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后现代’,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只要它符合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后现代,曾经零星地,因而是偶然地和无规则地发生于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及其后。”[2]20王钦峰则把文学史上早期的这种后现代现象称为“前现代主义时期的后现代主义”[3]。所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作为文学现象和文学因素并不是有了“后现代”这个概念之后才有的,它早就存在于文学史之中,“在世界文学史上和艺术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往往都熟练地采用和运用上述后现代特殊的表达方式,尽管他们并不属于后现代主义者”[2]76。卡夫卡就是这种熟练地运用后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伟大文学家。
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它适用于所有的文学现象研究。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很多传统经典文本也具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或因素,只是过去我们视而不见罢了。美国文学理论家米勒曾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分析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他的结论是,《呼啸山庄》不具有统一的、具有逻辑连贯性的、单一的意义,它存在着多种潜在的意义,这些意义互不相容[4]。这可以说是从后现代视角研究经典作品的成功范例。
卡夫卡的作品非常复杂,他本人并没有“现代”与“后现代”意识,但我认为,他不仅是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既有非常标准的现代主义作品如《变形记》等,也有非常标准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如《城堡》等。卡夫卡生前长期处于可怕的孤独之中,这既是指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更是指他与文学史的关系,他的作品因为与传统格格不入而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余华说:“卡夫卡没有诞生在文学生生不息的长河之中,他的出现不是因为后面的波浪在推动,他像一个岸边的行走者逆水而来。很多迹象都在表明,卡夫卡是从外面走进了我们的文学。于是他的身份就像是《城堡》里K的身份那样尴尬,他们都是唐突的外来者。”[5]我认为,卡夫卡《城堡》①本文主要依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卡夫卡全集》(第4卷)本《城堡》,译者赵蓉恒,本文中所引作品文字均据此本,仅在引文后面用括号注明页码。同时参照汤永宽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高年生译本,《卡夫卡文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版;英文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李小宛译本,《卡夫卡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米尚志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王印宝、张小川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主人公为“K.”,赵译本沿用,但这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也是为了简洁,本文一律用“K”而不是“K.”。的“异质性”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后现代主义。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文学上有什么特征?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大致说来,后现代主义有这样一些明显的特点: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矛盾性、解构、反本质主义、多元论、去中心、解元叙事、非同一性、无主体等。具体到各个领域,情况又有所不同,其问题和对象各有侧重。文学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反叛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的主题、情节、结构、体裁、叙事等方面的解构上,解构本身以及文学的个体性决定了很难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传统方式的归纳。但根据文学史实践来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意义悬置、模糊性、中心消解,从而具有不确定性、主题不确定、形象不确定、情节不确定等特点;修辞和意义处于不稳定状态,断裂和开放性等;平面化、零散化,拼贴、游戏、即兴式、反主体或者无主体性、小叙事或微观叙事;反讽、戏拟、对形式的颠覆、对真实性的颠覆;黑色幽默、元小说、反逻辑、魔幻等。任何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包含所有这些特点,《城堡》同样也是这样,但仔细阅读《城堡》,却可以发现这部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因素竟然如此丰富,其后现代主义的综合性大大超过了后来的很多作品。
为什么说《城堡》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或者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文本,它有什么特点?下面笔者将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从分裂和解构的角度对《城堡》进行研究,以《城堡》为例来说明很多经典作品都具有的内在紧张、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分裂和解构性。
二、没有主题和事件的碎片化
传统小说不管怎么创新,作品的整体性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表现为主题集中、风格一致、线索明确、结构清晰、脉络清楚、人物形象鲜明以及具有深层次的环境基础、情节完整、事件安排井井有条、逻辑严密、具有强烈的因果性等特征。优秀的传统小说,在思想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每一处细节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围绕着主题展开,否则就被认为是多余的。对于传统小说,主题越集中紧凑就越富于匠心、越精致,因而也就越容易成为经典。但《城堡》显然不是按照传统小说方式来写,很多人读了之后都惊叹“小说竟然能这样写”,这说明了《城堡》在写作上的反传统性。整个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在这些方面充满了分裂性,表现为:没有主题,思想的矛盾与冲突和缺乏方向感;人物没有性格或者说多种性格;情节的散漫和事件的碎片化、不连贯等。
《城堡》没有传统小说的那种“主题”,它的题旨是多方面的。小说的很多叙事都有紧张感,有很大的跳跃性,描写与描写之间、叙述与叙述之间缺乏主体上的逻辑性,缺乏事件上的前因后果。
卡夫卡喜欢写故事片断,今天整理出来的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的所谓“小说”、随笔、日记,很多都是故事片断:主要是场面描写,没有原因与结果;细节上非常具体,但思想上却非常抽象,具有箴言性。卡夫卡已经发表的许多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城堡》虽然写作时间相对集中、完整,但本质上仍然具有箴言性。故事缺乏背景,事件发生突兀,没有任何预兆,不符合常规,该交代的不交代,比如K为什么不能进城堡?进城堡为什么不能被谈论?能够看到城堡,没有任何人阻拦他,他为什么不直接走进去?巴纳巴斯经常进入城堡,K为什么不能像巴纳巴斯一样直接走进去?巴纳巴斯为什么拒绝带K进入城堡?是否城堡当局下达了某种命令?克拉姆为什么拒绝会见K?这些都是读小说的人能够简单地想到的问题,但卡夫卡就是不交代。小说第13章讲汉斯的故事,对小男孩有一段描写:“对某些紧急的问题似乎犯犟脾气根本不愿回答,只是一声不吭,而且表情没有一点窘态,这是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6]157其实,整个小说都是这种风格,套用这段话,作者“对某些紧急的问题似乎犯犟脾气根本不愿写”,“支支吾吾”,“而且表情没有一点窘态”,这是一般作家“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
小说第3章写K和弗丽达一见钟情,这是K到达村庄的第二天晚上,这种爱情来得实在是太突然。另外,佩碧和奥尔珈都是一见到K就爱上了他,同样没有交代,让人不能理解。小说写K第一次见弗丽达,感觉“有着一双忧伤眼睛”,“可是她的目光却令人吃惊,那是一种特别高傲的目光。当它落在K身上时,K觉得它似乎已经把所有与他有关的事情统统解决了,他本人现在还一点不知道这些事情,然而这目光却使他坚信这些事情的存在”[6]40。初读这段文字,不论从句法、手法还是从现实性上,都不好理解,而且这段话还是反因果关系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这么具体而复杂的目光,它不过是K主观上的感受或想象,是作者的一种表达方式。所谓“事情”,和前面的“战斗”[6]28一样,虽然我们可以从写作技巧上把它看成是一种伏笔或暗示,但小说实际上后来并没有什么“事情”和“战斗”,有的只是想象“事情”的氛围,或者说因为想象“事件”和“战斗”而发生的一些事情。
《城堡》的突兀性、不连贯性、碎片性尤其表现在人物对话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往往缺乏“对话”性,对话似乎不是在交流思想,而是各自表达什么,人物的语言缺乏语境基础和情节前提,有些话初读起来莫名其妙而只有读完小说之后才明白,有些话完全不能理解而简直就是语无伦次,说得突然,也没有任何后续解释,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并不是人物性格和情节故事的合理延伸。比如第1章写K在乡村遇到小学老师,两人有一段关于城堡的对话,K问老师是否认识伯爵,老师回答说不认识,K又问为什么,老师回答:“我怎么会认识他?”“老师低声说,然后便用法语大声补充道:‘请您考虑一下这里有这么些天真无知的孩子在旁边。’”[6]12不认识伯爵是很正常和坦然的,为什么要低声回答?为什么要回避孩子?难道是丑事?“儿童不宜”?按照常理,K应该进一步追问,从而解开这个谜,也是向读者交代,但K却转移了话题:“老师,我可以拜访拜访您吗?”轻轻地把这个回答回避掉并消解了。K的问话也可以说有承接性,这似乎可以解释为:既然当着孩子的面谈话不方便,那么我改天去拜访您,私下里谈谈这个问题。但认识与不认识伯爵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成为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话题呢?读完小说,我们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团,小说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说不了了之。
整部小说充满了不可理解性。第4章和第6章写K和老板娘两次长谈,谈得越多,让人越觉得糊涂。老板娘本来准备和K谈弗丽达,但却转移到K能否见克拉姆。K要求见克拉姆,老板娘认为这是“异想天开”[6]53,K问为什么,老板娘说“这个我会给您解释的”[6]54,但直到谈话结束也没有给出一个解释。整个谈话似乎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K为什么要见克拉姆?“究竟想跟克拉姆老爷谈什么呢?”面对老板娘的提问,K的回答是:“当然是谈弗丽达。”[6]56有必要和克拉姆谈弗丽达吗?有什么可谈的?而且,K在认识弗丽达之前就要见克拉姆,难道那时也是要谈弗丽达?后来老板娘再次提出这个问题,K的回答是:“我想亲眼见见他,再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另外还想知道他对我和弗丽达结婚抱什么态度。”[6]94这些对于K来说难道有意义吗?难道值得他去苦苦追求吗?另一方面,克拉姆为什么不能见K呢?读完小说我们也不知道。K和老板娘的对话不仅没有解决读者的疑惑,反而增添了更多的疑惑。
小说在情节发展上充满了随意性。小说的情节看不出经过精心安排,人物及故事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作者除了似乎坚守K无法进入城堡以及始终不讲原因这一信念以外,其他一切似乎都很偶然,读者根本无法预测。小说情节缺乏发展的方向,小说以K的行动为线索,但K就像风中漂浮的尘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皆不得而知。K意外闯入村庄,初来乍到,对村庄完全陌生,他在村庄短短6天的行为就像在黑夜中乱窜,究竟会碰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难以预料和把握。小说的情节也像K的乱窜一样漫无目标,作者似乎完全不遵照“伏笔”和“照应”的传统情节规则。有些故事,前面有了很多铺垫,似乎应该写下去,但实际上却不了了之,比如鞋匠勃伦斯威克一家的故事,特别是汉斯母亲的故事,K在小说开头时闯进了他的家,描写非常神秘,留下很多伏笔,后来通过汉斯的讲述知道了一些,但却留下更多的悬念,似乎故事仅仅只是开了个头。再比如村长一家的故事,特别是村长老婆,似乎留有故事,但也只是留下悬疑和神秘。
有些故事则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冒出来,没有缘由。明显是作者的突发奇想,比如佩碧的故事。佩碧开初出场时,读者不过是把她当作一个道具,不过是因为弗丽达走后不能有空缺。但到了小说快结束时,她却突然成了故事的主角,让读者对弗丽达有了意外的收获。而弗丽达究竟有多少故事则不得而知,小说虽然写了很多,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冰山一角,也许还应该有一个她自己讲的故事,包括她和克拉姆的故事、她的生平的故事、她和助手的故事、她和老板娘的故事等,而这些在小说中都是谜团。在佩碧讲述之前,弗丽达的老谋深算可以说没有一点迹象。
传统小说一般较严格地根据逻辑构思来写作,是非常理性的,即使违背构思,比如人物在特定情形下会自己行动等,也要有充分的逻辑根据。传统小说也会设置很多悬念,也有很多矛盾,但多在结束时一并解决。一部小说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发生、发展和结局。但《城堡》却是不断设置悬念,不断出故事,旧的故事还没有结果或不了了之,新的故事又产生了,故事不断旁逸滑动,所以讲述越多则小说的迷局就越多、故事就更多,讲述不是解决了读者的困惑而是制造了更多的困惑。故事越写越复杂,头绪越来越多,这种写作方式永远不可能有结局。《城堡》的故事没有方向感,K后来怎么样了,故事如何收场,都是不可预测的。据说卡夫卡对于结局曾经有一个意向,但可以肯定,他如果有机会继续写下去,他未必会遵守这一意向。
三、K作为人物的内在分裂性与无形象性
小说到处都是前后矛盾,比如时间上的矛盾、性格上的矛盾、叙述人称上的矛盾、逻辑上的矛盾等。诺伊曼说:“谈不上通常意义的逻辑连贯性。思路一会儿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否定所打断,一会儿被一种意义相反的转折排出自己的轨道,一会儿被纳入到一种突然逆转的基本关系中。”[7]544又说:“卡夫卡运用反复的立与破、正与反、肯定与否定,试图排除一切解释动机的、从而歪曲认识的思维程式。这一系列的反论造成的结果,是读者迷惑不解和对所有通常的思维法则的扬弃:这一系列反论引出了某种通过其它思维途径不可能认识到的东西。”[7]574作者对现象的描述非常准确,但我不赞同作者通过“曲解”的方式把“矛盾”往“合理”的方向解释,我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解构”,也就是说,卡夫卡追求的是“矛盾”。
传统小说中也有很多矛盾,即前后不一致,但那是构思和写作不够严密造成的。按照传统的小说观念,它是漏洞、硬伤,属于失败。《城堡》中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但卡夫卡是把“矛盾”正常化,也就是说,它是《城堡》重要的表达或表现方式。“矛盾”正是《城堡》在艺术上的一种尝试,现在看来非常成功,开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先河。没有这些矛盾,《城堡》就不再是《城堡》,其艺术性将大打折扣。其丰富的意义以及寓言性与这种“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比如K的身份就充满了前后矛盾。
几乎没有哪一个读者不对K感到迷惑。我认为,迷惑的原因除了作者有意支吾其词、有意模糊其身份之外,还与有关K身份的信息互相矛盾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根据小说的描述勾勒出K的确切身份。在小说中,K被称为土地测量员,还有两个助手跟着他,但实际上,K没有任何测量土地的工具,他自己不会测量土地,两个助手也不会测量土地,他在城堡的6天时间里根本没有从事与土地测量有关的任何工作。小说提到K“曾经服役”[6]20,“正好有一点医学知识,更有用的是他还有看病的经验。有些连医生都没有办法的病他也给人治好了。在家乡,因为他有这妙手回春的本领,还得了个‘苦口良药’的绰号呢”[6]159。但小说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学过土地测量以及从事过这种工作。K的确有两个助手,但这两个助手从哪里来都是疑问,与其说是他被聘为土地测量员的证据,还不如说是解构他土地测量员身份的证据。
K因为迷路闯进了村子,因为没有留宿的许可证所以被“城堡主事”的儿子施瓦尔策盘查,K底气十足地说:“现在请您听清楚: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6]4单就这个回答来看,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似乎确凿无疑,而且,第二天真的有两个助手到来,这似乎更增加了他被聘任的可信性。第15章当奥尔嘉说到索尔替尼时,K以为是索尔蒂尼,曾说到这样一句话:“聘任我的官员中就有他。”[6]206从这句话看,似乎城堡真的聘请过他。而且,K到达村庄的第二天就收到由巴纳巴斯送来的“第十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的信,信上说:“非常尊敬的先生!如您所知,您已被聘任为大人供职。您的直接上司是村长,他还将告知您有关您的工作及薪俸的一切细节。……递送此信的巴纳巴斯将不时向您询问以了解您的愿望。”[6]26这里明确讲城堡已经聘请了K,并且还有非常具体的内容。
小说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身份进行解构。当施瓦尔策打电话到城堡询问得到确认时,K却相当意外,“吃了一惊”,“K听了这些话精神为之一振。这么说,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6]7。这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他的自我介绍,但至少使他的话变得可疑。第14章叙述来到城堡及身份问题,K有非常详细的心理活动,K恼恨施瓦尔策,认为正是他第一天晚上的盘查造成他后来的诸多不顺。他本来可以悄悄住下来,然后被“当成一名漫游工匠”在“某一家当上雇工而住下来”,“第二天办公时间内去求见村长,老老实实地按照规矩报上自己的外来漫游工匠身分,声明自己已在某一村民家有了住处,很可能明天就继续上路”,可能的结果是“在此地找到了活干而留下来,当然只留几天,因为他决不想在这里多待”[6]181-182。也就是说,K并不是接到聘任邀请来到村庄的,闯入村庄之后他本来准备做一个漫游工匠,呆几天就走人。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声称是伯爵聘请来的土地测量员,可能是为了住宿而随口胡编的。有学者指出:“‘土地测量员’的称呼只是他为了在城堡下属的村庄客栈里留宿过夜时,由于一个好事者的逼问,他误打误撞地临时捡得的一个头衔。”[8]这是一种可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胡编在城堡官僚主义的体制中竟然也能得以通过。
到底城堡是否聘请过K为土地测量员,小说始终是矛盾的,信息相互否定。第5章K专门去拜访村长,主要就是谈他的工作问题,村长的开场白却是:“整个这件事情我是早就知道了的,我之所以还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第一是因为我生病,另外就是您很久没有来,我已经在想您大概已经放弃这工作了。……如您所说,您已经被录取为土地测量员;但是遗憾得很,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6]66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话,不仅K是迷惑的,无所适从,读者也是迷惑的,同样无所适从,正如K最后所总结的:“我们谈话的惟一结果就是,除了轰我走这一点很明确外,别的什么都是一团乱麻,一笔糊涂账了。”[6]81原来,好久以前,那时村长还年青,刚当上村长,城堡曾经发了一个公函说要聘请一位土地测量员,但被聘的那个人并不是K。这似乎是对聘任K的否定,但接着村长又对K说:“聘用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6]69似乎又是对他被聘的肯定。读者不禁要问:既然聘用了K,那就应该有聘书或相关通知,对此,村长的回答同样相互矛盾:“我不知道在您的事情上是否也发出过一个这样的决定——有迹象说明发出过,也有迹象说明没有发出过——;假如已经发出,那么聘任书就可能早已寄给了您,然后您就会长途跋涉到此地来。”[6]76似乎是K接到了聘书才来的,但实际上K是迷路闯进来的。K从来没有提到过聘书,也拿不出聘书。在最需要回答、最需要直接面对的地方,作者有意回避或者说绕过去了,因而对于K的身份,读者充满了不解。但从艺术手法上来说,这其实是作者为自己解构写作模式留置空间。
克拉姆给K的信似乎是K被聘的确证,但实际上,这封信也可以解构。最早对这封信进行解构的是村长。村长认为:这封信除了克拉姆的签名以外,其他都是可疑的,他鉴定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对于已经聘任K的事,他的解读是:“说您被聘只是‘如您所知’,就是说您已被聘这一点要由您自己来证明。”[6]78“这封信只能说明克拉姆在一个条件下打算亲自过问您的事,那就是:如果您被聘为大人供职。”[6]79这是一个悖论,但说明K并没有被聘用。而以后是否被聘用,村长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聘任您作土地测量员。”[6]77村长通过重新解读信件的方式即理论的方式把K的被聘给解构了。第15章奥尔嘉的讲述则是通过事实的方式把克拉姆的信以及信上的内容彻底解构了。原来巴纳巴斯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差,这封信也不是克拉姆交办的,而是秘书从一大堆“毫无价值的信中胡乱抽出来[6]202的”,“是一封已经在那里搁了很久的、很旧很旧的信”[6]196,是一封早已过时的没有意义的信。奥尔嘉不仅把信解构了,把巴纳巴斯的信差意义解构了,也把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以及他在村庄里的各种努力解构了。
与此相关,K究竟准备在村庄长住还是短住,小说前后也是矛盾的,小说开头K说他自己迷了路,闯进了村庄。但第13章他对弗丽达却说:“我可不能离开这里”,“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留在这里。我一定要留在这里”,“要不是有留在这里的强烈愿望,还有什么能把我吸引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6]150还说“不是为了过体面、平静的生活才到这里来的呵”[6]167。第14章K最初想“明天就继续上路”,“只留几天,因为他绝不想在这里多待”,但第15章却是要“成为村里正式的一员”[6]219。
四、两个助手身份之不可解
K的两个助手虽然很难说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也是较重要的人物。K显然是异乡人,两个助手究竟是他自己带来的还是城堡派来的,小说中充满了矛盾。下面按小说的叙述顺序,把两个助手的一些重要信息摘录出来并作简要分析。
“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6]4从这句话看,助手应该是K自己带来的,但这里附带性地把“迷路闯进村庄”给解构了。
“我的助手们很快就要到了。”[6]8似乎K和助手们早就有约定,说明助手是K带来的。但K第一次见到两个助手并不认识他们,两个助手也不认识他[6]16。这说明两个助手是城堡派来的,而同时把小说开头所说的“几个助手”“带着各种器件”“乘车”等给解构了。
第二次见面,两个助手向K行军礼,K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回答是:“您的助手。”于是K和两个助手有一段对话:
K问:“你们就是我那两个老助手,就是我让你们随后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的那两个人吗?”两人点头称是。“很好,”片刻之后K说道,“你们来了很好。”“不过”,又过了片刻,K说,“你们迟到得太多了,你们太拖拉了。”“路很远呵。”一个说。“路是很远”,K重复说,“可是你们从城堡来时我碰上你们了。”“对。”他们说,没有更多的解释。“仪器你们都放在哪儿了?”K问道。“我们没有仪器。”他们说。“就是我交给你们保管的那些仪器。”K说。“我们没有。”他们又重复一遍。“唉,你们是怎么搞的!”K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土地测量?”“不懂。”他们说。“如果你们是我的老助手,那么你们就必须懂这个。”[6]20-21
真是匪夷所思的对话,完全不能按常理来理解。这里包含了很多他们本来就认识的因素,也包含了他们并不认识的因素,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互相解构的奇妙景观。既然是老助手就应该认识,但事实上不认识。既然曾经交给他们仪器就应该认识,但事实上不认识。既然是土地测量员的老助手就应该懂得土地测量,但实际上不懂。这里有多重解构,K的问话中包含着自我解构,两个助手的回答对K的问话又是一种解构。这可称得上是经典的解构叙事。
“既然你们是我的老助手,那你们也就是外来的。”[6]22“外来的”本应是事实,但却是根据“老助手”推理出来的。K给城堡打电话假称自己是助手,有这样一段对话同样精彩:
“他们是新来的助手。”K说。“不,他们是老助手。”“他们是新的助手,我才是老助手,是今天比土地测量员先生晚一步到这里来的。”“不对!”那边大叫起来了。“那么我是谁呢?”K问道,一直保持着冷静。[6]24
K说两个助手是新来的助手,和前面“老助手”相矛盾。“我是谁呢?”这是最荒谬的问题。有趣的是,卡夫卡还特别补充一句,说K一直保持着冷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反话或捣乱,没有头脑发热,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对于K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对于小说来说同样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K心里仍很清楚,那是两个严密监视他的人。”[6]50这说明两个助手是城堡派来的。村长对K说:“其实我认识他们,我们是老相识了。”[6]68说明他们不是K带来的,不是老助手。“他们是我到此地后才跑到我身边来的。”“好吧,就算是派来的吧。”[6]69K似乎承认两个助手不是他自己带来的,而是派来的。
两个助手“刚刚脱离城堡的严格管教,这是初次被指派为外来客人服务”[6]137-138,“据她所知,是K自己要他们来的”[6]138,说明两个助手是城堡派来的,并且是根据K的意愿派给他的。
“我是耶里米亚,你的老助手呀。”[6]258“加拉特派我们到身边来。”[6]259助手的话自相矛盾,既承认是K的老助手,又承认是城堡派来的。也可以说明是K带来的,也可以说明是城堡派来的。
“我们是小时候常在一块儿玩的伙伴——那时我们一块儿在城堡的山坡上玩。”[6]277助手和弗丽达原来是“青梅竹马”,这说明他不是K带来的。
两个助手“是通天的,是从城堡里腾云驾雾而来的”[6]280,又说明他们是城堡派来的。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两个助手究竟是老助手还是新助手,究竟是K自己带来的还是城堡派来的,小说前后显然是矛盾的,甚至在同一句话里也包含矛盾。这绝不是疏忽,而是作者有意为之,是一种有意识的解构叙事。
上面详细分析了K的身份和两个助手的矛盾叙述,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比如小说一开头,老板“愿意让他在店堂里一个装稻草的口袋上睡觉”[6]3,草袋就在店堂里但K却是“自己去阁楼上把草袋搬下来”[6]3,明明是睡在草袋上但随后却“拉过被子盖在身上”[6]4。弗丽达离开贵宾楼之后,她的位置由佩碧接替,第4天K到贵宾楼求见克拉姆,克拉姆就在贵宾楼,佩碧亲口对K说:“他马上就要乘车离开这里,雪橇已经在院里等着了。”[6]110但到后来佩碧自我讲述时,却是克拉姆在她当班这段时间“没有到下面贵宾专用室来”[6]336,也没有到贵宾楼来[6]337。开头施瓦尔策给城堡打电话是正常的对话,而且施瓦尔策是“城守”的儿子,他应该知道对话的实际意义。后来K给城堡打电话,虽然对话很诡异,但对话本身还是正常的。而到了和村长谈话时才知道,“我们这里的电话所能传达的惟一正确可信的东西,也就是这种沙沙声和歌唱声,别的信息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最初的两次通话“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是官员疲劳了,“放松一下消遣消遣”[6]80,从而把最初两次一本正经的电话及其意义解构了。K曾经收到克拉姆的两封信,这对于他在城堡的生存至关重要,甚至是他行动的依赖和保障。两封信都是巴纳巴斯送的,信的内容、送信的方式等最初都是正常的,但在奥尔嘉的讲述中,巴纳巴斯作为信使是可疑的,信的内容是毫无意义的,信本身也是毫无价值的。不仅把巴纳巴斯作为信使解构了,把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解构了,而且把K到达村庄之后的一切努力都解构了。
五、叙事和表达的矛盾
卡夫卡的箴言和他的小说一样非常有名,不妨摘录一段:
人类的主罪有二,其他罪恶均由此而来:急躁和懒散。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懒散,由于懒散他们被驱逐,由于懒散他们回不去。[9]
这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箴言,前后矛盾或互为否定:前面说主罪有二,后面又说主罪只有一个;前面说是由于急躁被驱逐,后面又说是由于懒散被驱逐。但这种矛盾和传统的二元对立又有本质区别,它主要是通过模糊、置换概念的意义、不同层次地表达现实中的不同状况等,使“矛盾”哲理化、常态化,展示现实中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把矛盾正常化,后现代主义称之为解构。事实上,这种解构式的语言在《城堡》中非常多,前引“有迹象说明发出过,也有迹象说明没有发出过”[6]76就是如此,下面再摘录一些并具体分析:
可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是手工工匠的事,是市场的事,要城堡大大小小事无巨细一概都管,可能吗?当然实际上城堡也无事不管……[6]234
前面说城堡不可能大小事情都管,马上又说城堡“无事不管”,既然“无事不管”,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就要管。这里,“无事不管”就构成了对不可能“大大小小事无巨细一概都管”的解构。
我的上司克拉姆老爷最近几天心情烦躁不安,至少我们这些生活在他左右的人,我们这些在他左右揣摩他的每句话、力求体会他每句话的意图的人感觉是如此。我们的感觉如此,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如此,就是真的烦躁不安——烦躁不安怎么可能同他沾边?而是说我们自身烦躁不安,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烦躁不安,并且工作时无法在他面前掩饰。[6]410
克拉姆的心情这几天究竟是烦躁不安还是不烦躁不安?读完这段话我们无从判断。开始时明确讲克拉姆这几天心情烦躁不安,这是结论;然后又说这是我们的感觉,从而使克拉姆心情烦躁不安变成了只是一种可能,这是过渡;最后这种可能也被否定了,变成了是我们的烦躁不安,克拉姆不仅没有烦躁不安,而且根本不可能烦躁不安。经过两次“滑动”性的转换和阐释之后,就把最初的结论解构掉了。
“你这些话说得多对,总结多好啊,真让人佩服。你的头脑多清楚呀”“不”,奥尔嘉说,“你这个印象错了。”[6]199
这是《城堡》中经常采用的叙述方式,也可以说是典型的解构叙事。又如:“你对阿玛莉娅的看法完全错了。”[6]228其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人讲述或表达,另外一个人予以否定,然后进行另外一种讲述和表达,但究竟谁是正确的,作者并没有立场。所以有学者说:“读者的最大困难是无法判断谁的谈话是可信的。也许这些话至少对这个说话的人来说是真实的。而叙事者声音的隐退已使读者无从判断这种真实性。”[10]叙事者的声音隐退当然是读者无从判断的重要因素,但意义相互解构则是无从判断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告诉你吧,女人同官员的关系是很难说清楚的,或者恰恰相反,很容易说清楚。[6]217
那么,女人和官员的关系究竟是难以说清楚还是容易说清楚呢?也许,难以说清楚是一个角度和层面,容易说清楚则是另一个角度和层面。这样,矛盾和解构恰恰表达了一种复杂的现实状况,也可以说是富于哲理的。从下文看,也可以认为女人和官员的关系是简单和清楚的,也可以认为是复杂和不清楚的。在这一意义上矛盾和解构实际上迎合了所有的读者,我们可以随意选择。
在四天的时间里,由于佩碧努力,人们可以说差不多快忘记弗丽达了,但是终究还不能完全忘记;如果弗丽达没有制造那桩丑闻使自己继续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那么她兴许还能被人忘得快些,只是出了那件丑事之后,她在人们心中又火起来。[6]334
结论是“差不多快忘记”了,但事实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在人们心中又火起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中间相隔的只是一个分号,完全相反的观念被并置在一起:
这里谁都不困,或者恰恰相反,人人都犯困意而且老是犯困,然而这种困倦并不影响人家的工作;唔,看来它反而对工作有促进作用。[6]303
这里的人究竟是犯困还是不犯困呢?下文经过一番曲解之后,似乎自圆其说了,但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回避其实也是一种解构。
以致于那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的任何一点无足轻重的变动,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干扰。[6]301
既然是“无足轻重”,且是“无足轻重”中的“无足轻重”,如何能“造成严重的干扰”呢?不仅仅只是“矛盾”,而且是“矛盾”中的“尖锐矛盾”:
你认为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出现吧?您想得对,这种情况确实根本不会出现。可是某一天夜里——谁能对什么事都开保票?——这种事真的发生了。[6]296
在观念上是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却是这种事真的发生了,或者说结论是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证据却是这种事真的发生了。究竟是观念和结论的错误还是事实和证据的问题呢?
“那个非常罕见、几乎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能究竟在哪儿呢?”[6]296“他这人很灵活,这正是他那愚蠢的一种表现。”[6]7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认为,这是《城堡》在意义上复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相反的观念并置,相反的讲述并置,相反的意象并置,相反的意义并置,从而造成相反的理解和解读。每一种解读即使是完全相反的解读,都能从小说中找到充分的根据。这正是解构的效果。
六、结构和叙述的解构性
上文谈的是句子内部的自我解构,是直接的解构。《城堡》的解构性还表现在叙述结构上,这是更隐匿的解构。第15章奥尔嘉讲故事,采用的就是解构模式。讲述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主观上,奥尔嘉对她的家人包括她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持批评态度,叙述以否定方式前行,她和她的家人清楚地知道她们的努力不论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是错误的,都是徒劳;但在客观上,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在故事本身却又以肯定方式向前,她和她的家人严肃认真地做傻事,明知故犯地做错事,越陷越深。主观上,奥尔嘉和她的家人是清醒的,思想具有逻辑性;客观上,她们的行为却非常荒谬,不可理喻,一家人前仆后继走向深渊。主观的否定和故事本身的肯定以奇妙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二元消解叙事。
奥尔嘉一家人的灾难,最初的原因是阿玛莉娅拒绝了城堡官员索尔替尼侮辱性的求欢,阿玛莉娅本来是正义的行为却遭到了莫名的惩罚且连累全家,使奥尔嘉一家人陷入深重的灾难。最初的灾难是村里人都疏远奥尔嘉全家,原因很简单:“人家之所以同我们断绝往来,除了害怕以外,主要的原因就是事情本身令人感到尴尬,人们回避我们,主要是为了不再听到那件事,不必谈到、不必想到、不必以任何方式同那事沾边。”[6]229解决的办法按说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甩开……”[6]229但事实却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我真不知道那时我们究竟在等什么。”[6]229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解性叙事,思想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往思想的反方向走,采取错误的行动,这样,思想和行动就构成了悖反,思想是一个方向,行动则是相反的方向,从而构成了互相解构。
“四处求情”,整个故事和叙述就是这个模式。“在那段时间里,后来我们又干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事,我们让人瞧不起。”[6]233这就是父亲向城堡求情,请求宽恕。但自己又没有犯错误,城堡从来也没有明确说奥尔嘉一家有什么错误,那请求城堡宽恕什么呢?“由于没能查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也就无法进一步通过官方途径达到请求宽恕的目的,于是他最终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到处去求情上,私下里到处去找当官的求情。”[6]237具体的措施是到城堡附近大路上官员们乘车总要经过的地方去站着,一有机会赶紧抓住。后来变成在大门附近的一块菜地上等:“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坐在满是雨水的、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又坐在雪地里。”[6]240“我们有多少次看到两位老人背靠背地瘫在那块巴掌大的石头基座上,缩成一团,披着一块不能将两人完全裏严实的薄薄的毯子,包围着他们的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雪花和雾气,方圆几里内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和一辆马车。”[6]240直到最后完全瘫倒下来为止。这已经不再是为了求情和宽恕,也不再是解救苦难,而是制造苦难,是自我沉沦、自我放逐和自我毁灭,所以,奥尔嘉一家的灾难与其说是城堡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自己造成的:思想是理智的,行为则是非理智的;思想是正常的,行为则是反常的。
这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后悔式”叙事有着根本区别。现实主义的“后悔式”叙事通常是:过去由于思想错误,或者由于环境限制等因素制约因而失误,犯了错误,现在非常后悔。但《城堡》的二元消解叙事完全不是这样,它可以概括为:思想正确但行为错误,从而思想与行为分裂,最终是行为对思想进行了解构。对于奥尔嘉父亲的种种计划以及具体的行为,奥尔嘉姐妹知道他的错误,父亲也知道其错误:“什么同情啦,怜悯啦,这类事情是根本不会有的,不论我们多么年轻,多么没有经验,可这一点还是知道的,父亲当然也知道。”[6]237“这事连初小学生都懂得是绝对不可能的。”[6]238“他已经不抱希望能在那里使自己的事情哪怕只得到一点点进展。”[6]240但父亲就是不可理喻地做这些连小学生都知道是错误的事情。奥尔嘉用了“精神虚弱”(英语)一词来描写其父亲的思想状况,但“精神虚弱”不是糊涂和没有理性,这一点就使父亲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犯糊涂具有质的区别。
“奥尔嘉的计划”在叙述上更是这样。奥尔嘉的“救命稻草”是向当时送信给阿玛莉娅的那个信差道歉,这同样是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奥尔嘉就是这样行动的。为了打听到这个信差,奥尔嘉每天晚上到贵宾楼和粗野“无耻到了极点”的仆人们在一起,“两年多来我最少每星期两次整夜同那些仆人一起待在马厩里”[6]243,实际上是沦为了妓女,这是更可怕的灾难。奥尔嘉自己清楚,虽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对事情来说其实无补,她说:“如果我现在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点不后悔,你可别看不起我。也许你会想,天晓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同城堡的联系哟。你想得对,那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联系。”[6]244且不说奥尔嘉所说的“联系”是否是真联系,即便是真联系又有什么用呢?奥尔嘉的计划,不论是她自己去贵宾楼当妓女,还是巴纳巴斯去城堡应聘信差,对于拯救她的家庭来说都毫无用处,南辕北辙,深陷泥淖,是往火坑里跳,最终毁了她自己和巴纳巴斯。奥尔嘉看得清楚,巴纳巴斯看得清楚,父亲和阿玛莉娅也看得清楚,但他们就是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他们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但他们就是做错误的事,“一点不后悔”。主观思想和实际行动背道而驰,从现实角度看难以理解,但这就是卡夫卡,人物似乎都是理性的,但人物的行为却是荒谬的,思想的理性与行为的荒谬构成了严重分裂和对抗的解构。
相比较而言,在整部《城堡》中,第15章的故事是最连贯的,逻辑是最清晰的,最接近现实主义,读起来也很顺畅,相对较好理解,但骨子里仍是现代主义的,具有深层的二元对立的解构性。表面上具有逻辑性,深层次反逻辑。解决问题的方案从一开始就是荒诞的,每一种手段都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手段不断地被当成目的,请求宽恕本来是为了被接纳而后来却成了目的,求见官员本来是为了反映问题而后来却成了目的,当信差本来是为了有机会为家人争取点什么而后来却成了目的,这实际上是不断地解构目标。
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和贡献,学术界讨论较多,笔者认为,卡夫卡更大的贡献是在小说形式上的开创,他对世界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小说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为小说的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小说之父。与传统小说相比,《城堡》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具有全新的特点:破碎、分裂、残缺、矛盾、模糊、无中心、无主体、不可捉摸、含混不清、偶然性等。《城堡》不具有风格上、内容上和结构上的统一,不是内在的有机统一,故事和情节都缺乏清晰的描写与交代,情绪、情调、思想、表述、手法等通常连方向都不一致,更不要说和谐了。内容经常滑动、转移,没有目标,整个小说没法结束。小说充满了不能理解的混乱,诸如时间上的混乱、空间上的混乱、非生活化、非逻辑化等。卡夫卡最大的本领就是把荒诞讲得头头是道,把荒诞讲得非常富有故事性,充满了细节、悬念和紧张,当然也充满了喜剧感和幽默。城堡可以说是“幻象”,但与一般的虚构不同,传统小说的虚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把“谎话说圆”,但卡夫卡恰恰相反,他把现实讲成谎言,描写成“幻象”。保罗·德曼曾描述后现代文本说:“不在文本结构中突出寻求语音上、语意上和语句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而是特意寻求文本中各种不可化约和不可重复的矛盾性、含糊性和吊诡性。”[2]61《城堡》就是这样的后现代文本,具有分裂性和解构性。
通过详细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到,《城堡》文本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统一性、有机性,它是一个分裂和解构的文本。由此至少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没有矛盾和冲突,并不只是后现代作品才具有后现代性,传统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作品也具有后现代性,分裂和解构也可以是经典作品的重要特性。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同样具有这一特性,比如关于他的《美国》,有评论指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是一个陌生、混沌、充满了挣扎与妥协的国度,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放逐与排挤的无奈中,体验着无尽苦旅的人生大舞台”[11],这是与《城堡》异曲同工的。
[1]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7.
[2]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
[4](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第3章.
[5]余华.卡夫卡和K[M]//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94.
[6](奥)卡夫卡.城堡[M]//卡夫卡全集:第4卷.赵蓉恒,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匈)诺伊曼.倒转与转移——论弗兰茨·卡夫卡的“滑动反动”[G]//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07.
[9](奥)卡夫卡.随笔[M]//卡夫卡全集:第5卷.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
[10]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5.
[11]张赟.美国作为“文学化空间”——德语文学中的美国图景[J].外国语文,2013(4):26-2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I106.4
A
1673-9841(2015)02-0100-11
10.13718/j.cnki.xdsk.2015.02.014
2014-10-09
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