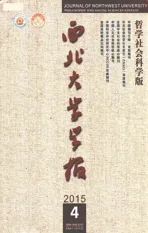从“学为圣人”到“敦本善俗”——论张载的教化思想
2015-02-23周后燕
周后燕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张锡勤教授对儒家的教化作出了界定:“所谓‘教化’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教道民’‘以教化民’,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转移世间的人心风俗。”[1]“道德教育”是儒家教化的内容,通过“感化”的方式,达至“转移世间人心风俗”的目标,这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张载作为关学的创始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非常重视从实践层面落实儒家的教化思想。但学界对于张载的教化思想多从哲学角度讨论,而对于其实践层面的论述相对薄弱。本文在重视理论层面的同时,着重对张载教化思想实践予以论述。
一
张载自小就有经邦济世的胸怀。《宋史·张载传》:“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2](P12723)张载经历了整个仁宗时期(1022—1063),而此时的政府内外交困:边境战争屡败,被迫以缴纳金银、绢茶等方式向西夏与辽求和;而国内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民不聊生,儒家伦常遭到极大的破坏。居于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的张载对于西北边境战祸有着直观的认识与深切的体会。怀着深切的家国忧患意识和经世情怀的张载欲投身于“攘外”这一事业以求解决国家的“外患”问题。由此,青年张载给当时被贬为陕西招讨使的范仲淹写信表明自己的志向。但范仲淹并不赞同张载的从戎志向,而劝勉其把重心放在名教上,并劝其读《中庸》,从而促发了张载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转向,即由重“攘外”转为重“安内”以解决“内忧”问题。虽然对《中庸》进行了长期的阅读与思考,但张载并没有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办法。此后他又出入佛老,求诸六经,提出了一条治国理民之策即“渐复三代之治”。他认为建立由“井田”“封建”“宗法”三位一体的治国方略,可以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一政治理想为张载的教化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思想上说,佛道的昌盛与儒学的衰弱形成鲜明的对比。儒家学者认为,儒家“道统”不明是造成世风日下的原因。所以,复兴儒学、重整纲常成为他们的共同理想。此外,自唐中叶以来思想领域出现的疑经思想和怀疑创新精神使得思想家们纷纷回到先秦经典当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对经典予以重新认识,以建立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体系。这是张载教化思想产生的学术文化背景。
《大学》为儒家教化奠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修身”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也是基点,而治理天下的法则是由“齐家”衍生而来。这种由个人的修养推展到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儒家血缘宗法伦理的必然逻辑,也是儒家“家国同构”思想的体现。由此张载提出个体层面的“学为圣人”与社会层面的“敦本善俗”内外结合的教化思想。
二
(一)变化气质
人性论是儒家教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孟子以人性善为根基,强调涵养本心,通过扩充仁、义、礼、智四端的方式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荀子隆礼重法、化性起伪的教化思想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点上。孟子和荀子虽然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存在差异,但以人性问题作为教化思想的出发点则是相同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基础,但他们都未能彻底解决善与恶的根本问题。孟子的性善论无法解释社会中恶的存在,也无法说明后天的环境何以能够磨灭人固有的善性。荀子无法解释人性既然为恶那么向善的可能性源于何处,也无法解释既然圣人与凡人具有相同的本性,又为何圣人具有能力制定出礼仪制度而凡人不能。人性善恶这一问题至张载才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哲学层面上,张载从气本论出发,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解决人性善恶问题。他认为万物皆由气聚而成,气在而存,气散而亡。在气凝聚之前天地之间充塞着本然纯善的太虚之气即天地之性;当气凝聚形成具体的万物之时,会造成气禀的偏差从而形成兼有善恶的气质之性。如此,人在本源上皆善,没有圣凡之分,这为个体理想人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在气凝聚形成具体的万物时,因有气禀的偏差所以又有恶的存在,圣人与凡人气禀的差异为“以礼为教”提供了依据。如此既能解释为何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又能解释现实世界中恶存在的原因。在人性二分的基础上,张载展开了个体层面教化的论述。
“成圣”是个体层面教化的目标。张载反复强调“学必如圣人”,为学者要以圣人为目标,“常以圣人之规模为己任,久于其道,则须化而至圣人”[3](P77)。实现这一目标须经过内在的“变化气质”与实践中的“行礼”这两个内外结合的修养途径。如何变化气质即如何消除因气禀之偏差而产生的恶的存在?张载认为变化气质应从“为学”开始,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学习的能力。虽然人的气质之性的美恶、贵贱、夭寿都是先天形成的,但通过“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摒除气质之恶而复归于本然之善。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善者是因为他们主观上不学习、不去改变的缘故:“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3](P266)为学的路径有两条:“自明诚”与“自诚明”。“自诚明”是从“尽性”到“穷理”,“自明诚”是从“穷理”到“尽性”,前者是从上向下的路线,后者是从下往上的路线。张载认为两者皆有优长,但他更偏重于“自明诚”这一为学方法,因为后者更具有可操作性。
“礼”是学习的内容。为何习“礼”?原因有四:其一学礼可以消除过去形成的陋习;其二学礼可以使人立定志向;其三学礼可以培养人的德性,使人能有立足之处;其四学礼可以守住仁德,使人的举止皆有依据。所以张载说“人必礼以立”[3](P192)“成就其身者须在礼”[3](P266)。“为学”须与“虚心”相结合才能变化气质:“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3](P274)心能做到虚则能公平,能公平则能分清是非,进而能知当为与不当为。“虚心”需要消除“意、必、固、我”四种弊端即主观臆断、独断偏至、拘泥固执、自以为是,因为四者有其一就无法回归本然之善。
在虚心的基础上使用“善反”的方法使天地之性得以保存即“成性”。保存“天地之性”即能实现人本然的善性,能实现人本然的善性则能消除气禀之恶,最终实现与天合一。“成”在张载的思想中含有两层意思:其一,真实无妄;其二,成就与实现。他说:“诚,成也,诚为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3](P192)“虚心”与“善反”这两种方法是从主体内在层面而言;成性还需要实践层面的“行礼”,只有将礼落实于人伦日常当中才能产生教化的作用。
(二)行礼
“宋代开始,中国步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与这种变化相对应,思想家们在礼论方面的探讨,将重点转移到了礼与维系道德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上。”[4](P132)张载对“礼”与“道德秩序”“社会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有深刻认识。礼的本质在于分别亲疏远近,通过行礼将这种等级秩序内化于人心,落实于人的人伦日用中,从而稳固封建统治秩序。“行礼”首先需要克己,因为克己能化去习俗之恶。“礼”不能停留在外在的礼节仪式上,它须与诚意兼行:“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3](P330)“诚”就是真实,只有当人对别人行礼时心里是真实的情况下,才具有与此礼相副的意义,只有心里对别人存有真切的尊重之心而行礼才叫做“礼”,无此诚敬则礼不称其为礼。张载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敬”与“礼”的关系:“‘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3](P36)“敬”是礼的载体,没有“敬”则礼无处安放。
张载指出:行礼应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处着手,从基本的生活礼节出发,然后由小的层面扩展到大的层面,即由洒扫、应对延伸至制度文章。不能忽视“洒扫应对”中的基本礼节,因为它们是行礼的入手处。对行礼的培养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小及大的长时间的积累与实践的过程。张载还批评社会上一些不合“礼”的行为,如在古代妇人行跪拜之礼时常把头低至地,双膝弯曲,那是因为庄严的缘故;而今天妇人在行跪拜之礼时,仅屈膝,还直着背,如此便失去了跪拜之礼的根本意义,因为心无敬意。
张载以恢复三代之礼为己任,所以非常重视古礼,并希望能将古礼作为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他说:“古之人,在乡闾之中,其师长朋友相教训,则自然贤者多。”[3](P266)古人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所以贤者多,从一个侧面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3](P355)在古代儿童都能很好地侍奉长辈,当长辈需要搀扶时,则知用双手,问答时则知掩口回答。做事稍有不敬则容易流于不忠不信,所以对于幼儿的教育,要强调内在层面的重要性,让他们做到“安详恭敬”即安静、细心、谦恭、敬重。“古人耕且学则能之,后人耕且学则为奔迫,反动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箪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则多欲,故难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难,故以为贵。”[3](P266)后人常被过多的欲望牵绊,所以学礼须修心。
张载继承儒家的身教胜于言教的思想,在治家接物的过程中严格要求自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感化时人。当他实行某一礼俗时如果得不到赞同,不会苛责别人而是反躬自省,检查自己是否有错误,在确定自己无误的情况下,则以“安行而无悔”的态度坚持下去。他的坚持对当时的社会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因为其师对礼俗的倡导,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并且跟从者甚多:“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重,皆先生倡之。”[3](P383)张载亦严格要求其家人:“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3](P383)幼儿需要学习洒扫应对之礼节,侍奉长者;未嫁之女必须亲自参加祭祀,完成荐酒水等祭祀礼节。
三
(一)圣人以“礼”为教
1.“理”即“礼”“礼”的本质是“别”。别亲疏别贵贱以论证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将“礼”这种外在的约束与人内在心理相结合,提出“仁”这一概念,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礼”的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孟子深化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为礼是人心天然具有的本然善性之一。荀子继承这一思路,将礼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提高到“天道”的高度,强调礼治是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保障。大致来说,孟子从主体心性层面论证了“礼”的必要性,荀子则从社会层面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张载继承孟荀关于“礼”的思想,提出“礼即理”的教化思想。
“以礼为教”是张载关学的特色。他说“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3](P264)“礼”的本质是“理”,张载说:“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3](P326)如果不以“穷理”为先,即不认识天道运行的规律,就难以“制礼”。张载强调知“礼之意”才能“观礼”,“礼之意”即“礼”是圣人依据“理”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全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法规。而“理”指的就是气的变化规律。万物皆由气构成,人与物皆遵循气的变化即“理”。“理不在人皆在物”,所以说“礼”虽是“圣人之成法”,但并非圣人随意而制。“礼”源于自然的尊卑大小,等级秩序,圣人只是“顺之而已”。对于礼的客观性,张载认为人类社会所遵循之礼源于自然宇宙,它先于人类而存在,换言之,人类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到礼存在的客观性,这样就强化了礼的至上性与权威性。张载显然继承了《周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5](P156)之说亦即将自然伦理化的思想。
张载通过“理”这一范畴,将“礼”提升到自然本体的高度,为“礼”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礼”亦是气化的一种展现,人源于气,所以在本质上“礼”与“人”是一致的:“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3](P264)如此礼与人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得以结合,从而为儒家的礼找到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这推进了儒家礼教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品格。
2.圣人之教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圣人既是理想的道德人格又是聪明睿智之人。圣人具有至真、至善之性,因此不但能弘道还能推己及人,博施而济众。圣人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P320)。圣人如天但又异于天,因为天无情而圣人有情,圣人之情在于教人。圣人之“教”源于天道自然:“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通聚结,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3](P13)气的运动与变化形成万物,而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皆显示的是自然之教:“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圣人之动,无非至德,夫何言哉!”[3](P13)即圣人之教的思想与模式均源于自然天道,所以张载借用天道运行的规律以阐明神道设教的作用。他将“天”与“圣人”并举,将“自然秩序”与“天下服”并举。圣人在本质上与天同一,天虽不言但自然万物运行有序,同此,圣人借用神道设教亦能使天下归服从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所以圣人必先认识自然大化的规律,依据万事万物运动的规律制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以教化大众。张载将《周易》中的思维模式引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将自然本体与伦理道德本体相结合,从而为自己的教化思想找到了有力依据。
圣人通过“感”的方式以施行教化,从而形成诚于此而动于彼的效果。圣人何以能“感”,因为圣人能通天下之志:“有两则须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圣人则能用感,何谓用感?凡教化设施,皆是用感也,作于此化于彼者,皆感之道。”[3](P107)阴阳二气相感使万物得以化生,圣人以“道”感人心而使天下和平,有圣人之感才有凡人之化,有凡人之化才能成就凡人的理想人格。圣人之教强调“时”的重要性。张载借用《蒙》卦之意,强调施教必须把握时的重要性,使施教达到“时雨之化”的效果。因时引导使受教者不失其正,这就是教化者的功劳。由此,不同的年龄阶段,应有不同的教化内容。礼教必须从小培养,古人就非常重视幼儿的礼教。但仁宗时期的社会状况却异于古,其时的人们非但不重视幼儿的礼教,反而对幼儿十分娇惯放纵,致使其形成诸多不良的行为习惯。
六经与四书是教化的文本依据:“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3](P255)所以学者观书要以六经为重,反复阅读到每次翻阅都有新的收获,则学必有进益。“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3](P277)张载尤其重视《论语》与《孟子》两书,认为两书囊括了天地自然之义理,所以为学者只需认真体会反复思考,即可体认天理自然。
此外还必须注重施教的秩序:“教人当以次,守得定,不妄施。”[3](P84)施教者必须知道为学的秩序与难易程度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在幼年应学习的内容不能等到成年之后才学,这样的教育不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引起受教者的反感。对于初学者不能以“大道教之”,因为这有悖于为学的秩序。张载吸收《庄子》“庖丁解牛”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教化思想中以深化儒家因材施教的教化理念:“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圣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余地,无全牛矣。”[3](P335)教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必须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与应对,在受教者需要并能理解的时候才告其所以然,如此才能使受教者学有所获。正如庖丁解牛之技之所以如此精湛,就是因为对牛非常熟悉,从而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二)重建宗法
自唐代后期以降,旧有门阀地主势力被削弱。伴随土地关系的变化,人们的宗法血缘观念也逐渐趋于淡薄,至宋此种情况变得愈发严重。与此同时北宋封建租佃关系有了新发展,使得中小地主势力日益强大,他们迫切要求重新修订宗法制,以期在政治与精神文化领域保护其既得利益。北宋边境战祸不断,身处西北的张载对这一切都有切身的体会。如何建立稳固的政治秩序是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是张载日夜所思的问题。成年之后的张载一改早年为国杀敌之心,在儒家有家才有国、家稳才能国固思想的指导下,认为重建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更为根本。再者唐宋佛教的兴盛对儒家的社会伦理纲常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张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强调重建宗法以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企图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提供内在的保障。
张载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论述了宗法制的社会功能。从积极方面说宗法制能“摄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能使人不忘本并理清谱系及世族之间的关系,进而能立宗子法。宗法最大的作用是稳定社会秩序。立宗子法不但能保障朝廷世臣的地位,还能保障崛起于贫贱之中的中小地主的利益。宗法立,人人各知来处,如此则家稳,忠义有依托,进而有助于朝廷的稳固。从消极方面言,废弃宗法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良:人们的血缘关系松弛,世风日下,人心浇漓;宗法废、谱牒又废导致人不知其宗族,虽是至亲之间其情亦淡薄,如此家难保,就更无法论及保国了。总之,宗法既能凝聚家族力量形成稳定的家庭结构,又能保障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稳固。
张载所倡言的宗法制是对庶族地主利益的肯定和维护,具有北宋时期特定的历史内涵。他把宗子法上升到天理的神圣的本体地位,认为它与天子君统同出一源:“‘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于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则本自是须低摧。又譬之于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泾流泛滥,则自然后河身转而随泾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3](P259-260)固本强宗、稳定大宗的封建等级秩序是根本的立国之法。张载期望通过强化儒家伦理的现实性以抵抗佛道的虚无,进而强化儒家的地位。韩愈建立“道统说”以明儒家的谱系;李翱从本体层面建立了儒家的心性论;张载则从礼制出发为儒家建立了一套社会层面的保障设想。
何为“宗法”?“宗”即以自己的旁亲兄弟来宗己,强调“宗”的主导地位是人来宗己而非己宗于人。张载解释“宗子”:“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3](P259)首先肯定传统宗法的可行性,即认为实行大宗、小宗之法均可,但更倾向于以政治地位较高者为宗子,如果嫡长子地位微贱,其他数子中有地位较高者,则不问长少,须由地位高者为宗子继承一家的祭祀,并且次臣之家也要照此实行。这就肯定了北宋时期新兴庶族地主的合法地位,而政治地位高于血缘也确实是宗法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趋势。
张载亦肯定宗子的道德素质的重要性,认为“宗子不善”则须别立贤者。宗子在整个家族中拥有至高的地位: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和祭祀祖先的特权;此外还有专设“教授”的特权,若宗子有所失,责任不在宗子而在“教授”。而诸子不能单独祭祀祖先,更不能别立一庙。祖庙必立于宗子之家,这样才能“严宗庙,合族属”。
祭祀礼俗是宗法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的教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3](P293)通过祭祀,生者与死者得以连接,等级制度得以延续,从而稳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张载对祭祀有大量的论述,从不同的祭礼到不同的祭祀者再到祭祀的具体细节,他都有详尽的说明。他对祭祀礼俗的重视,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P25)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息息相关:“自周衰礼坏,秦暴学灭,天下不知鬼神之诚,继孝之厚,致丧失节,报享失虔,犹尚浮屠可耻之为,杂信流俗无稽之论。”[3](P365)周朝衰亡致使礼崩乐坏,而秦朝统治更恶化了这一趋向,使得天下百姓不知鬼神之诚,更不知孝之厚,加之佛教对儒家礼俗的冲击,丧祭变得更加没有章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载对各种礼俗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整体而言,张载以三代之礼为今礼之标准,时常将古人与今人对举以说明古礼之善与今礼之不足不善:从态度上说,古人非常重视祭祀,会慎重准备饮食礼乐以会宾客;而今人对待祭祀却非常马虎,以事生之礼事祭,仅呈物而未尽心;从具体的细节而言,今人之礼亦有许多错误,在古代,吉礼所戴帽用缩缝,丧礼所戴帽用衡缝,今人反之;古人重礼之实质,心存敬畏,今人常流于形式,毫无敬义可言。所以张载感慨:“祭祀之礼,所总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数犹不足,又安能达圣人致祭之义?”[3](P294)
张载以古礼为准绳,对于不符合古礼的礼俗提出批评。比如认为,五更时进行祭祀活动不符合礼制;对于“八蜡”亦提出异议,认为昆虫不应该成为祭祀对象,因为昆虫于农业无益;此外对于通过看风水来安葬死者,亦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毫无义理的做法,完全不足取。
张载遵循古人对祭祀礼俗的划分,从祭祀主体上分为统治者与庶民,从祭祀对象上分为山川之祀与祖先之祀。不同的祭祀主体有不同的祭祀对象与祭祀仪式,通过具体的祭祀仪式将不同的身份等级落实于现实层面。所以他十分强调祭祀者的身份,认为祭者必须是正统相承即嫡系,祭礼正则整个宗族才会有统属。他非常重视血缘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撰有大量专门论述祭祖的文字。对于祭祖的时间、场所,祭祀者的身份、服饰、饮食、居处、祭品、祭器等都有详细的说明。祭祖对于合宗族有最直接的作用,所以张载强调亲人之忌日这一祭礼,并加入了新的内容。在古代亲人的忌日是不需要告庙的,但张载认为凡忌日必告庙,即将其他祖先的牌位迎出庙与忌日之祖先合祭,以此加强整个宗族的联系。此外,对于没有固定日期的祭礼如孟月之祭、仲月之荐等则需要提前占卜日期,以免其他各家所选日期相同,导致无法合祭,影响整个宗族的凝聚力。
四
张载以“家的模式”将自然伦理化,然后以之指导人类社会。他将天地比作父母,万物比作天地的子女,天地与万物组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他将人类社会的等级关系投射于自然万物之中,又用此种自然的等级秩序为人类的贵贱尊卑作论证。将自然天道与人道相结合设论,从而继承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个体经过“变化”气质以恢复本然的善性,为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人性论基础;而圣人的以礼为教又为整个社会教化提供理论支撑。宗法制的重建,将社会等级秩序落实于具体的实践当中。他对祭祀礼俗的强调与论述,增强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之间的联系。如此,张载将封建等级秩序植根于社会各个层面当中,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化思想。
张载的教化思想在北宋时期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对古礼的倡导起初不被更多人接受,久之则从之者甚众。他的以身作则与严格要求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人,乃至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他的高足吕大临制定的《吕氏乡约》直接受到了他的启发,此约在中国社会教化史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张载创造性地提出的人性二分说成功地容纳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宋明理学时期的人性论基础;他对宗法的阐释与重建使得教化思想深入到民间,促进了民间教化习俗的发展与繁荣。
[1]张锡勤.试论儒家的“教化”思想[J].齐鲁学刊,1998(2).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章锡琛点校.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陈其泰,郭伟川.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