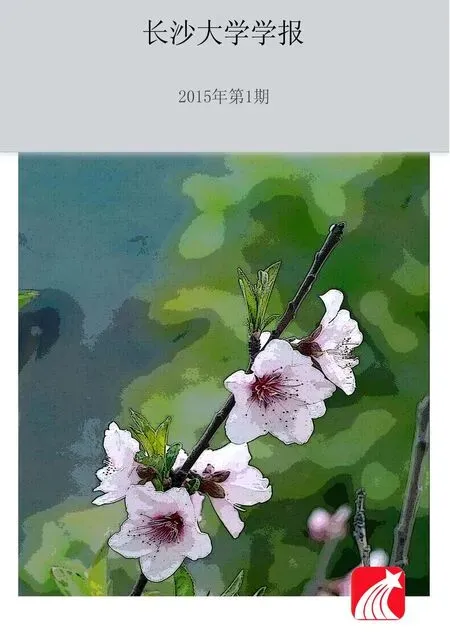男旦乐伎对清代中前期文学的影响
2015-02-22程宇昂
男旦乐伎对清代中前期文学的影响
程宇昂
(韶关学院中文系,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清代中前期是伎乐转型的关键期,男旦成为公共乐伎的主导力量。这一转变使得男旦对文人生态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男旦;乐伎;清代中前期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15)01-0078-04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男旦与明清文化”,编号:10YJAZH013。
作者简介:程宇昂(1968— ),男,安徽桐城人,韶关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戏曲史论。
Abstract:It was the key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music performer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when female impersonators became the leading force of public music performers. Female impersonators influenced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 literati depending on but also literary works.

女性一直是中国伎乐的主导力量。明代,朱元璋开始改变这一格局:弃置女乐,禁止官员宿娼。女乐在清雍正时做到令行禁止,藉伎乐而生的妓女不再受到律条保护,从此,中国城市剧场几乎见不到一位女伶。年轻貌美的男性以女性面目柔声缓步于剧场、酒庄和茶楼之间,成为娱乐宠儿。男旦,本是以男身而装扮女性的演剧唱曲者,明清两朝渐成台上唱戏、席间唱曲侑酒、台下陪睡的全能娱乐客体,即乐伎。
乐伎是文人重要的人文生态。文人宴饮,伎人度曲,诗词因而昭彰。唐之乐伎影响唐诗如此,宋元乐伎影响词曲如此,明清男旦影响诗词小说亦不例外。男旦作为乐伎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关键时刻在清代中前期:顺治至乾隆时期。这一时期,男旦演员更自觉认同女伎身份,文人更自然地视男旦如女伎,新的伎乐环境正式形成。文人与男旦交往,首先影响的是诗词,其次为文章与小说,以下分而述之。
一男旦题材入诗词
一如苏轼以诗为缠头赠女伎可以“与汝作诗传不朽”[1],题赠男旦亦如此,演员常乞诗于文人。文人出于结交名旦等目的,亦愿意酬以诗词。文人与男旦交往时因而产生大量诗词。乾隆间名旦王湘兰善墨兰,“一时同人庚和,以志韵事”[2]。“娄东十子”之一的王揆有《广陵赠歌者》诗二首,其一曰:“才看何家傅粉郎,忽疑神女下高唐。销魂最是三更后,不作闺妆作道妆(时演《玉簪》)”[3]。这样的即兴之作虽为欢场戏言,却常常于戏谑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男旦演员的生活状况。
词亦为欢场良媒。宋琬有《采桑子·赠歌者陈郎并柬西樵》词二阕:
樱桃时节樱桃郑,改作崔徽,夺得鸾鎞。轻燕翩翩掌上飞。红牙按罢黄金缕,卸却罗衣,一段娇痴。羞杀西楼穆素辉。
灯前倦倚娇无力,臂作空床,重理清商。一串骊珠绕画梁。暮云朝雨今宵梦,错赋催妆,何物王郎。醉里温柔(是日演《西楼》传奇)更有乡。[4]
西樵乃王士禛长兄王士禄,宋琬与之善。综合二词可知,词为宋、王同观袁于令的《西楼记》而作。穆素徽,词中作穆素辉,陈郎饰演。陈郎演技高超堪比王紫稼,貌美远胜穆素徽。两首词均强调陈郎乃床上尤物。由词题可知,宋琬打趣王士禄,或许试图怂恿王士禄尝尝男风妙处,或许对王氏钟情于陈郎心领神会?
题旦诗词一般为即兴拈来的短制,戏谑或褒奖意味浓郁,更具娱乐色彩。题旦诗词之外,是借男旦抒情言志的篇章。屈复《变竹枝词》云:“刘郎复周郎,能增文武价。昆弟皆贵人,感赐风流骂。”作者自注曰:“刘郎,富华班旦色,例监考州同知。周郎,苏州小优儿,来试武举。一时达官以受二优毒骂为荣。又有翰林结为昆弟。”[5]诗中携有康乾间男旦走红、世风转变的感慨。此类诗中,令人瞩目者为长篇歌行,如名诗人为名旦写的巨制:吴梅村为王紫稼作《王郎曲》、陈维崧为徐紫云作《徐郎曲》、袁枚为李桂官作《李郎歌》、赵翼为李桂官作《李郎曲》,戴晟有《沈郎行》,毕沅有《陆郎曲为童梧冈作》等。上述作品均长达数百字,在当事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较高地位。与长篇歌行同样有分量的是组诗。査慎行与乔莱友善,乔侍读家有旦色管六郎,査氏作《乔侍读席上赠歌者六郎》诗。乔逝去,査氏哭之。康熙三十四年前后,査慎行再次见到六郎时,六郎已经名擅京都梨园,贵胄公子争相一见。査氏不快,“口占四绝句示同席诸君”,感叹“自琢新词自裁扇,教成歌舞为何人”[6]。文人动辄吟诗一组的例子颇为常见,甚且一唱多和,文情荡漾。
中下层文人亦不甘寂寞,竹枝词纪旦诗多为其所为。《中华竹枝词》中存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如李声振《花档儿》诗描写康熙中期小唱卖艺生涯:“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怆神。却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7]花档小唱也是以男妆女,与一般男旦的区别在于:年龄更小,歌舞体制短小。
清人以旦入诗状况也体现在诗集编纂中。徐釚《本事诗》乃诗话体诗集,集中有涉旦诗近百首,诗人十二家以上。是书“略例”将女伎与男伎平行列出:“青楼狭邪之倡色艺双绝……歌童人宠自霍氏家奴,以下栉比而生。讵谓世无秦青,鄂君绣被竟令香消耶,余故录之,仿佛见郑樱桃与歌板青尊之下。”[8]编者将涉旦诗篇独立成类,足见当时此类创作之旺盛,也足见学人之看重。《本事诗》经王士禛删定方付梓,当时诗坛宗主的态度耐人寻味。
此处以吴伟业《王郎曲》为例,大致瞭望咏旦作品的文学高度。其诗内容约略如下:王紫稼为吴人,十五岁的他,漆黑乌亮的头发与白皙的面庞互相映衬,婀娜的舞姿和嘹呖的歌喉令人生怜。如今,昔日的主人家相继败落,流落京城的他已至而立之年。王郎颜色如故,风采依旧,豪门子弟为其痴狂。然而,王紫稼因耻于做一名乞食的戏曲演员,放弃了教戏授徒的工作,拟返回江南老家。尽管人们以在京都才能博得盛名相劝,王郎不改初衷。从内容看,诗非简单游戏之作。作者臣服于时代美少男,倾力歌咏之,肯定其耻作伎的人生态度,对其执意离去无限惋惜又无可奈何。从形式看,它是典型的梅村体,“摹写生动,几于色飞眉舞”[9],“气格恢宏,开阖变化”[10]。《王郎曲》乃吴伟业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清诗的名篇之一。它从容真切地从男性的视角歌唱男性色艺之美,一唱三叹,是一段时代风情至为清晰的文学记忆,影响深远,张际亮等多有仿制之作。
总之,清代中前期,男旦题材诗作的质与量远胜明代。数量上,类似作品数量多得难于统计。就诗人论,仅吴长元在《燕兰小谱》中就留诗240首,词3阕;就男旦演员论,仅《紫云出浴图》就存有76人吟咏徐紫云的诗162首,词1阕,断句1。质量上,诗体多样化,作品品味高,为人津津乐道的咏旦名作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清代中后期,涉旦诗数量更大,但由于作者多为中下层狎旦者,诗作的文学价值有限。
二男旦题材入文章
这一时期,关乎男旦的文章主要有三类:笔记、诗话与人物传记。
笔记。笔记记录男旦生活,有荒诞不经者,有于史可征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旦在当时的生存状况,有史学意义亦兼具文学价值。如和邦额《夜谭随录》记录了耿精忠少子的同性恋故事,同性恋对象就是男旦演员:“有贴旦名珍儿者,尤姣媚。耿少子与结断袖之契。”[11]
清代笔记蔚为大观,中前期的笔记中言及男旦者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书目:《研堂见闻杂记》、《谐铎》、《丹午笔记》、《援鹑堂笔记》、《不下带编》、《坚瓠集》、《觚剩》、《池北偶谈》、《艮斋杂说》、《锡金识小录》、《子不语》等。这些作品或叙述与男旦相关的传闻,或如实记录亲身经历,对男旦文化的态度褒贬不一。
诗话。诗话言及男旦,除前文所述徐釚《本事诗》外,尚有《莲子居词话》、《莲坡诗话》、《随园诗话》等。王紫稼、徐紫云等名伶与文人热络的风流韵事,不仅散布于笔记,也被吴衡照、査为仁、袁枚等在其诗话中津津乐道。笔记为随笔记录文字,旨在留存历史细节,但流于志怪传奇;诗话亦为随笔,多记录诗坛轶事,旨在补述事实。两类文体中出现大量记录男旦的文字,说明文人群体以不同心态关注着正在出现的时尚。
人物传记。为旦色立传主要有两种形式:花谱小传与典型的人物传记。
品评人物肇端于《论语》。魏晋时品题的主要对象为名士,唐以后妓女继之。男旦艺术是伎乐的延续,品题男旦如期而至。品评乐伎主要有三种方式:题咏乐伎、评定花榜和制作花谱。评定花榜主要为甲乙人物,因较少文字参与而并无直接的文学意义。题咏乐伎的文学成品为诗词。制作花谱可能诞生韵文文学与散文文学的双胞胎,花谱体制并不统一,最常见的方式是为乐伎立传并以诗词称颂其色艺。花谱都是对众多乐伎的品评介绍,故传记大多较短,本文名之为“花谱小传”。
清代中前期的花谱留存下来的有成于乾隆五十年的《燕兰小谱》。该书评介安乐山樵十余年间所知京师名旦,含六十四篇传记。传记一般百字上下,典型形制是:
王桂官(萃庆部),名桂山,即湘云也,湖北沔阳州人。身材彷佛银儿,横波流睇,柔媚动人,一时声誉与之相埒。余谓银儿如芍药,桂儿似海棠,其丰韵嫣然,常有出于浓艳凝香之外,此中难索解人也。为少施氏所赏,赠书画玩好千有余金,故矫矫自爱,屡欲脱屣尘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12]
体制虽较小,与明人同类作品相比,却要舒展很多。潘之恒《乐技》记郝可成班演员:“徐翩父,以旦色名。善妖,其当夕之价,倍于姬姜,而兼秦宫一生之活。二女翩翩、亭亭皆能,尤似之矣。”[13]短短的38字品评徐翩父女三人,文字近似春秋笔法,非真正意义上的传记。《燕兰小谱》的小传综合运用说明、记叙、描写、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是合格的人物传记。花谱作者先点明人物姓字、出身,更多的文字用于突出其色艺品质。其篇幅与《世说新语》接近,写作模式与元明清时代品妓之作类似。
真正称得上传记的是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左右的《秦云撷英小谱》。其书乃秦中名伶传记,传主几为旦脚。共七篇,字数三百至两千不等,平均七八百字。该书较《燕兰小谱》更具文学性,是纯粹的纪传体,叙述传主的人生际遇与人格品质,真情实感潜流于文字间。如《三寿》篇,800余字,在简略介绍作者与三寿的三次相见后,回顾三寿从四川德阳到西安的艰辛,及其在陕西时对母亲的惦记。至此,作者怜爱与敬意并生,突然又笔锋一转:
三寿每至余斋,依依不舍去,捧书拂纸,执役如僮仆状。偶酬以金,辄辞,问所欲,则曰:“吾母在德阳,而吾随人至此,欲归既不能,习为伶,实非愿也。且人方以吾渔利,而又虐以求之,吾何以堪?计可脱吾于苦海者,惟主人耳。倘蒙主人恩许,相随至京,虽死无憾。”言已,泪岑然下。余婉言慰之……余自度力不足以致三寿,恐终虚其愿,而又不欲没其意也,为记其实如此。[14]
三寿希望借作者之力脱离苦海,未能如愿。作者诚恳憾之,亦将感叹唏嘘留给读者。《秦云撷英小谱》与《燕兰小谱》的区别,就像侯方域《李姬传》、陆次云《圆圆传》、徐仲光《柳夫人小传》、冒襄《影梅庵忆语》区别于《青楼集》等。
《秦云撷英小谱》之外,文人文集中偶见此类文字,如厉鹗《书项生事》。
传记“志属信史”,这一文体关注男旦,意味着男旦受到高规格的文学礼遇,文人开始对他们郑重释放前所未有的尊重。
在《秦云撷英小谱》、《燕兰小谱》拓宽品评男旦的河流之后,清代中后期,花谱制作进入狂热时代。
三男旦题材入小说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都有男旦的身影,《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野叟曝言》即是。《红楼梦》写到的蒋玉菡即琪官就是男旦演员,小说第二十八回、三十三回、三十四回、八十六回、九十回、九十三回、一百零二回写到了他。他本受忠顺王府王爷宠爱,又与贾宝玉有情感纠葛。“优伶有福”的蒋玉菡最终娶了“公子无缘”的袭人为妻。蒋玉菡虽是小人物,却是小说刻意表现的人物,亦是名中含“玉”、映衬宝玉的形象之一,宝玉挨打的直接原因是亲近他。《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十一、五十三回等有男旦出场,其中第三十回写著名的莫愁湖大会。杜慎卿突发奇想,组织小旦比赛,参赛选手有六七十位,观众闻风而来。比赛的结果是:
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与的大老官来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买了酒在酒店里吃酒庆贺的。这个吃了酒,那个又来吃,足吃了三四天的贺酒。[15]
描写男旦较多的是明清之交的《梼杌闲评》。该书的中心人物是魏忠贤。小说交待魏氏出身时,用了十多回的篇幅介绍其父、小旦魏云卿与其母侯一娘相爱,并生下他的经过。魏云卿/男旦为小说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
《绣榻野史》、《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有与男旦属于同一文化现象的小唱现身。小唱也是男扮女装的演员,与戏曲男旦不同的是,小唱主要唱曲而不登台演戏。
值得注意的是,章回小说对男旦的褒贬在清代中前期出现了较大变化。明中后期的《金瓶梅》和明清之交的《梼杌闲评》对男旦明显缺乏好感,成书于乾隆间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转变态度,开始为男旦正名,二书为深情描写男旦的长篇巨著《品花宝鉴》的到来作着精心的铺垫。
中短篇小说的男旦题材多见于笔记体小说集,如《子不语》、《续子不语》、《谐铎》、《萤窗异草》、《觚剩》、《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小说属稗史性质,或实或虚的记录了很多男旦演员的事迹,如《阅微草堂笔记》就以搜奇夸异的心态记录了乾隆间名旦方俊官的故事。
男旦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题材上,也表现在审美风格上。凡是对男旦抱同情甚至欣赏态度的小说,多少会偏爱男性的阴柔之美。《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有这种倾向,贾宝玉从面容、服饰、性格到心理,都充满着阴柔气质。
总之,清代中前期是伎乐转型的关键期,公共妓女失去歌舞呈伎的高雅修饰而现形为低俗的性工作者,缙绅名流整体衰落后残存的家乐女伎不过如覆巢之完卵。女伎凋落既是量变,也是质变。与之相消长,男旦在娱乐圈中取得绝对优势,成为公共乐伎的主导力量。伎乐转型的关键期也是男旦文化影响古典文学的关键期。清代中前期,男旦演员全面而深入地走进文学诸体,成为文学史中独特的艺术形象。这一时期一流的作家大多积极面对男旦走红的现实,染指男旦题材,描写旦脚伶人的生存状况,借全新的题材反映全新的社会生活。文学诸体记录男旦生活的频次并不均衡,诗词明显高于散文与小说。究其原因,诗、乐有天然的伴生关系,诗词为短制,乐酒之余信手拈来。文章小说并不能如此快捷地反映全新的文化现象,不过,它们描写男旦生活的深度一点也不逊色于诗词,这样的文字常常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戏剧文学中罕见男旦题材,但男旦对戏曲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唐以前诗为歌诗,唐以下词、曲为歌诗;男旦的乐伎身份使他们成为剧曲最为重要的公共传媒,男旦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即是传媒对歌曲生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景星.宋诗别裁集(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2]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3][8]徐釚.本事诗[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宋琬.安雅堂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屈复.弱水集[A].中华竹枝词全编[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6]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雷梦水.中华竹枝词(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9]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0]靳荣藩.吴诗集览[A].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01396)[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和邦额.夜谭随录(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汪效倚.潘之恒曲话(上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14]叶德辉.双梅影闇丛书[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8.
[15]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On the General Effects of Female Impersonators as Music Performers
o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CHENG Yu’ang
(Facul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Guangdong 512005, China)
Key Words:female impersonators; music performers; the literature of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effects
(责任编校:余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