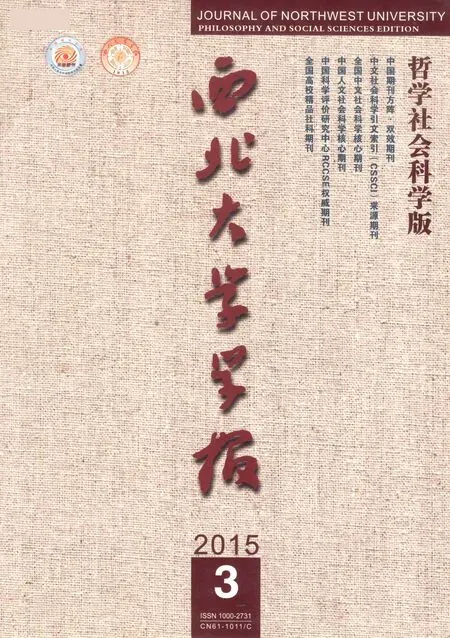非道之德:历史境遇中的实践智慧境界
2015-02-21李建森
李建森,徐 茜
(1.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经法学院,陕西西安 710129;2.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3.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中西圣哲很早就发觉从思想向行为的一越,是不无惊险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可以从理智和德性两个方面加以诠释。从理智方面看,普全知识高于经验直观,行易知难。因此,让具有“下愚”特质的民众把握行为的抽象而复杂的理论基础和根据是不现实的。从德性方面看,孔子儒学思想也是用来牧民的,是治理之术,因此,让具有“流氓”特质的民众明白行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背后的形上运思是不理智的。可是,这些思维机巧所暗示的对于普通民众实践智慧的不屑一顾,实际上是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根据的。就一般意义来说,作为高等动物,人的理性思维不可能和实践分裂开来;就历史发展而言,人在历史中对行为和思想的互相作用的自觉意识,日益强烈。事实上,普遍思想要求和特殊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张力,历来存在,而且随着文化多样性的演进,越来越发紧张[1]。在当代社会,随着不确定的“流动性”的日益肆虐[2](P1),不仅仅“下愚”,而且,“上智”在整体和具体境遇两个维面也都出现了在将普遍原则生活化能力上的拙雅区别,即,社会行为之实践智慧属性的量阶分野。
一、历史的实践智慧
有关“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哲学言说,在西方思想史上,一般被看作是发轫甚至奠基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道德哲学的。亚里士多德语义下的实践智慧具有以下基本规定性。第一,实践智慧就是趋善避恶的能力。“实践智慧是一种与正确计划相联系并坚持正当行为的践行能力,而这种践行的对象是那些对人善与不善的事物”[3](P125)。第二,实践智慧本身就是其自身的目的。实践智慧和技术不同,技术还有别的目的,而实践智慧本身就是目的。他说:“因为制作在自身之外尚有别的目的,但践行却不是这样,因为良好的践行本身就是目的。”[3](P125)第三,实践智慧指向一种整体的善。他说:“所谓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就是能正确考虑对自身的善或有益的事,但这不是就部分意义而言的……而是就整个意义而言。”[3](P124)这里的“整体”具有个人和共同体两方面的意义,是对于“大全”,即包括主客体所有因素在内而无需分别主客对立的全部情境的把握。第四,实践智慧是在面对特殊的个别事物时所表现出来的生活能力。他说:“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东西的知识,它更应当通晓个别事物,因为它的本质是践行,而践行必须与个别事物打交道。”[3](P128)第五,实践智慧只能经由经验而不能通过学习和传授获得。他说:“心智方面的美德的产生和发展是大体上归功于教育(因为它需要经验和时间),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果。”[4](P322)他还说:“人们总是择善而行而非习规”[5](P80)。第六,实践智慧是实现生活善的必要条件。他说:“像伯里克利(Pericles)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因为他能明察什么事对自己和别人是善的。”[3](P125)
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关于实践智慧服从于理论智慧的基本理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实践智慧是知识和德性的统一,“德性就是理性(logos)”。简言之,实践智慧就是德性的知识或知识的德性[6]。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实践智慧从属于理论智慧,相反,是理论智慧从属于实践智慧。但是,关于实践智慧的这种亚里士多德界定在康德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康德看来,实践智慧只是仅能提供劝告和建议的自爱准则的假言判断[7](P48-49),而不像道德法则那样属于提供道德绝对命令的定言判断。因此,它与道德无关[8](P67-70)。以规范伦理学为主流的现代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原则是彰显普遍性的义务和规则,而以德性伦理学为主流的古代道德哲学的基本理念则是人的具体生活方式和品格。在此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道德观念史上充斥着对于生活的实践智慧的一片讨伐之声,实践智慧的道德呐喊日渐式微,并且从德性之首最后沦落为道德弃儿[9]。
马克思是现代实践哲学转向的开拓者之一。正如萨特(Jean Paul Sartre)所说:“自马克思以后,哲学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活动,一种介入。”[10](P4)马克思看到了实践智慧在哲学实践史上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对于有思想的感性社会生活的世俗意义。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1](P54)“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P57)这充分说明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上非常重视“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强调彰显着普遍性意义的革命的原则必须与体现着生活情境特殊性表象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近的具体化境遇中,更有必要充分发挥实践智慧。
二、实践对象的历史性
反思在时间中以经验形式存在的“我们”和“对象”显然是分析实践智慧的最基本前提。“我们”和“对象”之间鸿沟的离析和聚拢及其后果是构成实践过程的最为基本的内容。
在文化系统的自我叙述和表达中,“显白”的和“隐微”的“我们”,是一个最为核心的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如此的独断,甚至是对于复杂而多变的自在对象的暴力或暴政式样的屠宰。“我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作为海德格尔所讲的“凝视”[12](P72),都是对于自在存在的终结、冻结、静态化。“我们”是什么?“我们”何以可能?这里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反思:“我”、“们”以及“我”和“们”是如何联结的①我们可以借用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显白隐微论”概念来分析“我们”这个语言行为里最为常见的关于叙述主体的说辞。“我们”关于主体和对象的表述或写作都包含着从“私人语言”向“公共语言”过渡的种种不连续或断裂。这种断裂,可能出于认知的局限,也可能出于机巧或奸诈。如列奥·斯特劳斯说:“有的时候,我从来不把我的信念说出来,我也从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如果有时候我意识到,我说了真话,那么我就把它隐蔽在大量的假话之中,使它很难被发现到。”([美]列奥·斯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首先,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种对于“自我”的偏执是十分可笑的。“自我”的身份,个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从来都是文化赋予的。这可能才是“现实的自我”。纯粹的自我、以“在”的形式存在的自我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是对于这种“现实的自我”的有限出轨。这种有限性规定,一方面是说保留了逃离“现实的自我”的浪漫激情和美好理想,另一方面使得那种将自我彻底从“现实的自我”独立出去的虚无主义不至于毁灭不得不进行的言说和叙述的可能性。总之,没有纯粹的“我”。其次,“们”是一个具有强烈类型学思维特质的表达方式。在这里,共性的假设出场了。“们”显然不是一个个体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整体主义、共同体主义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群主义色彩的概念。再次,当“我”和“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我”的视角有限性和“们”的类型武断性,都清楚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的言说,意味着演讲者将自己看作是某一个共同体的典型部分,并隐含着自己的事实主张和价值主张具有某种代表性、具有某种语言权力的意蕴。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谦词,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契约型授权,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浮夸的修辞性的语词,那么,它就是一种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不自觉的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僭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来好像不太慎思“我们”,然后在“我们”的现实化过程中,背离实践智慧。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难题。“濠梁之辩”和“美诺悖论”似乎更多地从知识论角度讨论对象性的客观性问题[13]。柏拉图的观点在今天似乎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柏拉图不屑于这种“诡辩派论证”,他说,“我们应该去探索,(这)比起陷于那种认为不存在认识活动,没有必要去求知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的懒汉幻想……将使我们善良一些,勇敢一些,不那么束手无策一些。”[4](P190)如何看待对象的客观性,如何规定人的认识和实践适恰的可能性?似乎有一条中间的道路是可以尝试的。也许它具有较好的解释性。第一,在人和对象之间能够达到一种相对的统一。第二,这种统一性具有现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既要看到这种统一的相对性,又要看到这种统一的客观性。这有别于柏拉图主义和休谟主义。总之,这种统一是历史的,而不是决定论的或非决定论的。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又说:“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14](P324)显然,人和对象处于彼此相互设定的关系中。如果人是历史的,那么,这种“设定”也就应该是历史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②马克思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可以看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在历史生活的统一性和复杂性两种主张中保持了某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巻,人民出版,2009,第470页).,但是,“历史也有惊人的相异之处”。“相似之处”提供了从理论向实践飞跃的可能性,“相异之处”则显现了理性的有限性以及实践智慧的艰难性和必要性。就实践哲学的对象而言,尽管“设定”的统一性力量十分巨大,可是,对象的“非决定论”存在不会因此消失。历史的实践面对普遍的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欲求、机遇以及所有与变幻无常高度相关所造成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得生活世界深陷不可预知性。“审慎的理论家总是强调审慎的分析就开始于结构性断言的终结之处”[15]。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指涉的是那些不能被普遍必然性所决定的非典型性的历史行为。[3](P124)历史的实践面对多元性存在。对于行为抉择而言,常常置身于复杂的实践情境中,与形而上学的理想的或者先验的主体不同,现实的实践主体每每具有相互冲突的异质性价值需求,不同的主体之间,同一主体的不同时空境遇之间,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之间,都要求一种恰当的具体性、境遇性的平衡或结合。因此,实践智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被看作是潜在不可通约的、复杂交错的各种视角的交融。也就是说,能够关照并最后超越历史性、情境性的不确定性存在的实践智慧,就是一种对各个内在的相互竞争的决定性变量的调适过程。而且,它还不能被“概括”为种种内蕴着普遍性迷失危险可能性的理智或德性具体规范[3](P129)。
三、历史实践的自由境界
历史实践的自由境界因此显然是同人们对于规范的异变和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历史实践的自由境界就是对于理性和规范的“辩证的否定”。我们所讲的“辩证的否定”就是以彰显人的存在和历史情境的意义为特征的通过对于诸规范的中道从容而展开的生活适切现实。它就是辩证的否定的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最基本内核。
在哲学史上,从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到后现代哲学家,关于规范的过度强制性,已经受到长时间的批判。尽管虚无主义的主张是矫枉过正的,但是,历史实践的经验进程似乎还是说明了,对于规范的康德主义式绝对化主张的可操作性都是乏善可陈的。或者说政治和道德生活史证明,如何从规范的理想性着床于生活的丰富性,就是生活本身,文化生活本身要比“文化哲学”真实得多。德行要比“道”真实得多。如果道德行为是以现实的形式存在的道德认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就是对于“道”的扬弃和否定。“有德”就是“非道之德”。就道德发展史而言,最基本的且源远流长的实践智慧就是对于已有的社会规范的扬弃,这才是善。在此,包括政治和道德生活在内的个人或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必须符合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最为普遍的善。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实践智慧就是“把握真理,体现理性,关涉着对人类来说有善恶意义的行为。”[3](P125)即实践智慧是在善恶层面上对于“真理”、“理性”的扬弃。实践智慧意味着趋向合目的性,而且它还是一个嵌合着德性旨趣和知性慎思的双重评价和践履过程,道德主体,包括个体和集体,正是通过这个慎思过程决定何以趋善避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规范性取向实践智慧与更具形式性的智识模式判若云泥。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实践智慧的这种对规范的德性主义之“非”,不是“拒绝”和“排斥”,而是“生活化”、“具体化”、“条件-情境化”,也就是实践化。“中道”的合适只是在个人具体的食物需求中才可能是恰当的,是具备实践智慧的。这就是《尼各马克伦理学》的实践智慧的特色。由于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马基雅维利(Nicolo Maachiavelli)等人的进一步强化,这种“促理性就善行”的意志,渐渐被看成实践智慧的基本界定。这意味着,实践智慧被看作是政治和道德生活语境中的政治思维和道德推理。这种实践智慧,具有如下的历史表征:在治郅之世,即,“邦有道”,它与理想主义相契合;而当庸俗的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时,即“邦无道”时,则灰飞烟灭,难觅行踪。这也许就是德性伦理学中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传统的保守政治家而言,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让人们具备这种对于规范的伦理反思精神是危险的。但是,非规范的实践智慧并不局限于此。实践智慧的非规范性精神所面临的偶然性对象和多元性观念是异常复杂的。所以,可以把实践智慧理解为协调诸善间紧张关系的伦理调适,或者说是对于诸善间之恰当平衡点的生活安排。实践智慧是一种疑窦四伏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困难重重的行为方式,它力图最大限度地实现那些常常彼此相互排斥的多重目标。非规范的实践智慧是人们深陷诸如民主与自由、人权与发展、效率与公平、平等与正义等冲突和困境时,所作出的“知-行”具体恰当。正如I·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马基雅维利言说的实践智慧正确地“揭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各种同样终极、同样神圣的目的可能相互冲突,如果没有可能得到合理的公断,完整的价值体系可能陷入纷争”[15]。面对这些政治和道德选择困境,实践智慧表现为审慎地对于规范的反思和对于诸种善的恰当平衡,并把恶限定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质言之,实践智慧就是当人们不得不有效排解诸善之矛盾性以及规范之多元性、有限性等困局时所展现的那种因缺憾而美的生活过程和样态。这里拒绝乌托邦式自由。
一般认为,预防性的实践智慧理念是马基雅维利提出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对此有过比较明确的区分。他说:“实践的智慧,不仅仅以一般的命题为事,也必须追求关于特殊事实的知识;因为实践的智识总是实践的,而实践乃与特殊事实联系在一起。”[16](P319)也就是说,实践智慧趋向于通达任何设定的目标。这种看法成为西方近现代政治道德哲学关于预防性的实践智慧的一种叙述范式。就以一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而言,人们应该格外关注对大量潜伏的变数做出有效预测,并以此作为智慧选择的前提之一。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需要普遍知识,也需要就处身之情境是如何发生演变的诸多特殊知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行动的,所以需要有关于一般的和特殊事实的两方面的真理和知识,特别更需要关于后者的知识。”[16](P319)遗憾的是,这种特殊知识总是相对的。而且,人们的任何个性行为选择都会孕育并创造许多新可能。进而,“失败行为”驱使竞争者创造新的意外,而所谓“成功行为”则导致竞争者排除原本必然的“偶然”东西的正常存在或产生。“失败”和“成功”都在进一步孵化进而倍增着新的意外或偶然。有鉴于此,合格的政治家往往被要求“既可审视台前亦可洞悉幕后的眼力”,以便他化解源源不断的意外[15]。预防性的实践智慧能够合理评价各种不利和有利因素,从而为各种特殊性行动提供正确预见。这就是“施宜”政治和道德情境之经验偶然性困局的智慧方式①道家思想包含丰富的实践智慧内容。这种智慧,体现在充分关照诸多经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超越性思维和自由行为的两个方面。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法”,层层递进,亦层层否定,直到“自然”。可是,这“自然”实际上就是“无”,就是“否定”和“非”。但是,这种“非”不是抽象而空洞的寂灭,而是一种超越。正如文子所讲:“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文子·道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今天,预防性实践智慧不再被蔑视为一种经验哲学个性化极端的冒险精神,也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意识哲学客观性理想非自由的机械性反应。相反,预防性的实践智慧被看作是文明加速发展的标志[17](P1)。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不断犯错误的历史的开端。每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18](P426)因此,如果看不到历史情境的这种不断滋生的新的不确定性,并在政治行为和道德实践中保持一种对于未来的警觉态度,即使行为业已取得成功,它也仍然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消极自由。
看来,在当今的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得不学会坦然面对现在和行将出现的各种“流动性”、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显然,人们只有在对这些“变数”的境遇性应对和未来性把握中,才可能找到一种像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否定性的“积极”自由——一种具体的自由[16](P93)。如果能够游刃有余于其间进而安心于这种自由,并且“知道”自己所做,那就是达到了自由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在对于“心”和“矩”的超越中②如果我们按照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一般性理解,即,它就是既合乎主观意愿,同时又和社会的“道”要求相一致,那么,按照本文的观点,“从心所欲,不逾矩”并没有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因为它并没有对“心”的特殊性和“矩”的一般要求所经常遭遇的不确定性进行批判。,即对于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的双重实践批判中所获得的一种自由,是一种基于否定性力量的自觉。正所谓,“人啊,如果你知道自己所做的,你是有福的;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你要遭谴责,就是一个违法者。”[19](P8)可以说,基于普遍知识的先验原则指引的理性主义“撞大运”式成功生活是不优雅的。
[1]王南湜.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3,(6).
[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洪汉鼎.论实践智慧[J].北京社会科学,1997,(3).
[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刘宇.当代西方“实践智慧”问题研究的四种进路[J].现代哲学,2010,(4).
[10]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傅金霞,张作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13]童世骏.“美诺悖论”的认识论分析[J].哲学研究,1985,(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罗伯特·哈里曼.实践智慧在二十一世纪(上)[J].刘宇,译.现代哲学,2007,(1).
[16]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的法则[M].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坎伯·摩根.路加福音[M].钟越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