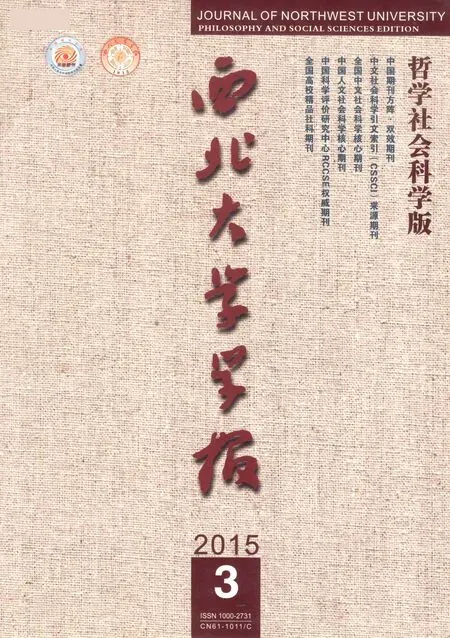“比较电影”视野下华语电影融合汇流的历史进程分析
2015-02-21余雅琴
郭 越,余雅琴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两岸三地电影本出一源,系同一民族文化母体衍生出的三支脉络,却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电影生态格局。这一独特的电影生态格局形成于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又因应了三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形成了同中有异的电影创作风貌。若从同的角度审视,三地的电影均源自上海电影传统,如果从异的方面来看,1949年后的三地电影在生产传播和美学经验上已形成较为明显的分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电影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然昭示出未来华语电影互融、互汇的美学演进态势,并且在文化整合的层面上塑造着华语电影的“大中华”的形象。
一、“前融合时期”: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初步融合与合拍探索
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7年,两岸三地电影的融合与发展渐次展开,三地影业汇流的此一时段可称之为“前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内地、香港电影界开启了初步合作制片的尝试,香港电影工业体制和美学经验也开始影响内地电影,同时台湾电影也尝试以香港电影为中介,拉开了与内地电影融合的历史帷幕。
上世纪80年代,三地电影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内地和香港浅层次的合作制片活动的展开。这一阶段,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香港、内地电影的互动交流较为有限,主要以香港制片方为主导,内地制片厂协拍并参与制作的合拍片形式进行初步的融合探索。80年代末,随着台湾电影管理政策的逐步调整,两岸电影界也开始了初步的交流与互动。自此,三地电影的发展与融合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大陆、台湾电影意识形态对抗的缓冲地带,香港影业曾较长时期作为三地影业合作交流的重要场域。1983年,香港新昆仑影业率先在内地拍摄了影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两地观众中均产生了巨大反响。而张鑫炎执导的《少林寺》更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永恒的经典。之后,香港影人借各种方式来内地拍片日渐增多,且日益发展为常态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香港、内地电影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入,加之中外电影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内地影人的眼界也得到了持续更新,表现为创作观念的积极转型。从那时开始,内地影人对电影的商品属性的认知开始深化。纵观90年代,香港、内地电影制片领域的合作、交流模式也开始了新的探索。随着1993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对电影制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新的合拍模式被催生出来:香港影业投入资金,内地制片厂提供劳务设备和场地,但是影片发行后参与利润分成,这一新的合拍模式和之前的分配方式两种并存[1](P16)。《大话西游》和《东邪西毒》便是这一政策出台后的代表作品,两片的投资与主创人员均来自香港,内地的合作方负责提供拍摄场地和人力,两片在商业、艺术上的成就可谓是这一合拍模式成功运作的范例。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海峡两岸电影界的文化交流也渐进展开。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1989年,台湾通过《现阶段大众传播事业赴大陆地区采访、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规定》,单向开放台湾大众传播人士进入大陆从事活动。自此,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也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局面。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来大陆拍片的影人中代表性的导演有朱延平等人。朱延平是“解严”后最早赴大陆拍片的台湾导演,他的一部《傻龙出海》踏踏实实地迈出了两岸电影交流共进的第一步,该片也成为台湾真正意义上第一部赴大陆拍摄外景的电影。朱延平由此也成为两岸合拍片导演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其后更有多部合拍片在大陆拍摄。1990年,陈朱煌导演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大陆市场卖座火爆,大大激发了台湾影业对大陆市场的信心和兴趣,此后开始有更多的台湾影人纷纷赴大陆谋求合拍片的机会,并且日益衍生出“以大陆地区版权换取大陆方面劳务投资”的新合作模式[2](P216)。1990—1994年间,两岸合拍片中代表作品有《滚滚红尘》《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上海假期》《活着》《画魂》等。这一时期,两岸合拍片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台湾投全资或台湾背景的香港公司投全资(或担当最大投资方)的合拍片居多,而导演或主演却往往聘请大陆的优秀人才参与。随着两岸电影界的交流的日益加深,资本、技术、影人各个层面也渐进趋向融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三地影业的发展与融合还衍生出台湾的资金、香港的技术、内地的人力和以大陆地区版权交换中方劳务投资的合作模式。对此,李天铎曾指出,“90年代台湾电影与香港、大陆的汇流,与其说是一种恋母式的对中原文化母体的回归与探触,倒不如说是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企求生路的结果。”[3](P216)李天铎的观点对从产业操作层面透视三地电影的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可以说,在“前融合时期”,两岸三地电影界在制片领域的合作、交流,既有力促进了三地电影各自的发展,又大力推动了三地电影渐进融合与汇流的态势,为三地电影业的深层次的融合、汇流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中融合时期”: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交流共进与整合发展
1997年至2010年,两岸三地电影业的融合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称之为“中融合时期”。这一时期,三地电影业跨越了“前融合时期”浅层次的合作制片模式,渐趋迈入融合、汇流的新阶段。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后,大批香港影人“北上”,两地电影在资金、人才和美学、文化等层面有了更深层次的融汇,从而开启了华语电影合作的新篇章。这一融合汇流的新态势,既表现为香港电影的商业美学经验对内地电影创作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即内地电影人在创作上更为重视观众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并大力推动了多元类型影片的摄制,又表现为海峡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及合作制片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自此,两岸三地影业的渐进融合、汇流的趋向也进一步加深。
CEPA签署之后,香港、内地电影在产业和美学两个层面的汇流进入新的阶段,两地创作资源的互动也进一步增多。这一时期,大批香港导演“北上”并主动融入到内地华语影片的创作中。香港影人的“北上”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资源,而且带来了商业电影的美学经验,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华语电影与国际主流电影接轨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内地华语片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并进一步推动了三地电影融合汇流的新发展。“北上”导演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徐克、吴宇森、陈可辛、尔东升等人。有着香港“新浪潮”旗手之称的徐克,较早融入到内地华语片的创作中。作为第一部“北上”合拍的华语片,《七剑》从容拉开了香港导演群体“北上”的帷幕。应该说,香港导演的“北上”,对于三地电影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纵观香港导演“北上”后的作品,一方面不论是《七剑》《如果·爱》,抑或是《赤壁》等片多少都呈现出一种“水土不服”的症状:即影片品质无法与该导演的香港时期的作品比肩,商业上的回报也无法与内地导演的作品相比。少数像《赤壁》这样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影片,导演吴宇森也几乎舍弃了自己标志性的“港片风格”。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电影也难以在大陆市场获得成功,这体现在影片上映档期的滞后,制度原因造成的陆港版本的不同等诸多方面。但总体而言,虽然香港电影人面对大陆市场的陌生环境一时难以适应,但是他们对于三地电影融合与汇流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同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电影渐进融合的趋向也进一步加快。尽管此前两岸电影界的合作交流一直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以致于很长时间以来台湾资金尚不能直接在大陆直接投拍电影。但随着两岸电影政策的调整,两岸电影业融合发展的进程开始加快,资本、技术与创作资源上的融汇交流也进一步深化。纵观这一时期两岸的合拍片,大陆不同电影机构作为第一投资方的影片制作占有重要的比重,而合作也不仅仅是在两岸老牌的大电影企业或公司间展开,新兴的电影公司尤其活跃并积极参与到合拍片的投资制作之中。在此阶段,两岸合拍片中台湾导演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群体亮相,其中除了王童、徐小明这样的资深导演,更有不少年轻导演崭露头角,如王毓雅、李云婵等,《空手道少女组》《基因决定我爱你》的合作摄制便是明证。不仅如此,此阶段两岸合拍片的类型和题材也进一步多元,既有李安的《色·戒》这样扬名国际的艺术电影,也有像《南京大屠杀》和《云水谣》这样具有主旋律色彩的电影,更有朱延平的《大灌篮》这样的商业类型影片。
三、“后融合时期”: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美学交汇与创新融合
2010年,大陆和台湾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电影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合态势超越了此前的融合态势而进入“后融合时期”。此时期三地电影尤其海峡两岸电影的合作交流,不仅推动了华语影业深层次融合汇流的进程,也对未来华语电影美学品质的整体提升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在此时期,三地电影制片汇流向更深层次迈进,创作资源的整合重组更为华语影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北上”导演创作策略的调整,香港、内地电影的融合汇流进程进一步加深。“后融合时期”的华语片以全新的影像品质展现了两地电影深度融合后产业、美学层面的互融、互补态势,并有力昭示着未来新华语电影创新发展的多元可能。
作为“北上”导演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陈可辛近年来的创作成就尤引人注目。《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两部影片的叙事策略,映现出陈可辛对于“后融合时期”华语电影创新发展策略的积极探索。《中国合伙人》的成功本源于陈可辛创作观念的更新变化,表现为对内地励志人生故事题材的敏锐捕捉及对内地观众审美文化心理的自觉迎合。在这部讲述1980年代中国青年创业传奇的影片中,陈可辛以流畅的影像语言,纯大陆的演员班底较好地实现了与大陆观众的审美对接。该片的中国气息使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内地观众倍感亲切和熟悉,影片故事主角们的传奇人生经历及创业奋斗历程更是感动了亿万观众,加之该片较小规模的商业投资,终于在商业上收获了巨大成功。《亲爱的》一片题材上更选取了真实动人的“寻子”故事,敏锐聚焦近年来大陆的社会热点,采用传统中国电影的“苦情戏”模式,又一次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成功。
杜琪峰是“北上”导演群体中另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作为昔日香港影坛极具“作者”风格的类型片导演,杜琪峰“北上”后也积极调整创作策略,一方面重拾起早年的爱情喜剧类型,快手拍摄了颇受内地市场欢迎的爱情喜剧影片,如《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即在内地收获了尚佳的票房业绩;另一方面,他还将自已原先擅长的类型片进行了去“港味”的美学革新。《毒战》一片成功将成熟的香港警匪类型片范式巧妙植入内地公安题材的缉毒故事中,从而在新华语片创作中延续了杜氏的“作者”风格印记,较好地实现了与内地观众的审美对接。该片在内地票房超过1.6亿元人民币,成为“后融合时期”华语电影合拍历程中获得票房、口碑成功的又一范例。
作为香港导演“北上”后的重要代表人物,陈可辛、杜琪峰的成功基于他们对内地市场与观众趣味的深度考察,其创作路径的革新探索为“后融合时期”华语影人创作策略的调整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参照。
ECFA签署后,台湾和大陆电影的合作交流由民间转为官方,开启了包括合作制片在内的全方位融合的强劲势头。自此,大陆和台湾影业的资源整合的态势也进一步加深。在“后融合时期”,内地、香港合拍片曾有力推动了台湾电影商业化的进程。2010年以来,内地、香港合拍片进入台湾市场后,开始将商业元素与类型意识注入台湾影业。从这一意义上审视,香港、内地合拍片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电影商业化的进程,也使台湾影片的商业元素开始彰显,并显现出由原先较为单一的文艺片向动作片、警匪片、爱情片等多元类型发展的新趋向,甚至出现了《赛德克·巴莱》这样既有较强商业性又兼具深度思想内涵的史诗性动作大片。由此观之,内地、香港合拍片对于台湾电影产业水平的整体攀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2012年,台湾本土影片生产总量已达50部,其中《阵头》一片更以3.17亿新台币刷新了本土影片此前的票房纪录。
也是在“后融合时期”,海峡两岸的合拍片也开始增多。海峡两岸合拍片的探索从更深层面上彰显着华语影业的互融、互补、互汇的发展态势,并以美学上的深层交汇有力地推动着华语电影在类型创建、叙事策略、艺术品质等方面日趋多元的变化。如2012年,两岸电影公司联合出品的合拍片就有多部,《LOVE》《饮食男女2:好近又好远》《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新天生一对》《宝岛双雄》《台北飘雪》等片的出现即有力昭示着未来新华语电影深度融合时代的到来。
四、结 论
新世纪以来,如何凝聚两岸三地电影的优势创作与产业资源,合力摄制优质的新华语片已成为当前华语电影发展必须直面的实践课题。对此,早有学者指出:“由于分享共同的书写文字及某种形式的文化传统,大陆、港台的电影生产及消费行为有其内在的向心律动,特别是在主题的开展、资金的运用、人力的支援及发行的网络等方面,两岸三地的华文电影相互学习、合作、竞争、指涉,让这些地区内外的华人及非华人社群了解了海峡两岸三地的文化差异及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命共同体’文化经验。”[4](P1)事实上,两岸三地影界同仁正是在各自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共识,并相互推动、促进,不断深化对于华语电影共同体的认知。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华语电影共同体的构建,将全面推动新华语电影品牌的创新与发展。
当前,两岸三地电影正处于“后融合时期”的全新历史阶段,融合走势中的华语电影已充分显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未来两岸三地电影在创作与市场两个端点上的融合将会不断得到深化,三地电影的整合发展也将进一步彰显全球视野下华语意义上多地电影文化的深度交融。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两岸三地影界正合力探寻着一种全新的汇流模式,以超越此前传统的的合作模式,从而探索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融合策略,即在产业、文化的深度交融中充分保持各自原有的核心优势,并积极适应新媒体时代观影群体审美趣味的复杂变化,最终合力打造出更具文化影响力的新华语电影。
[1]肖丽娜.香港内地合拍片的商业美学嬗变(1979—2009)[D].河北大学,2010.
[2]梁良.论两岸三地电影[M].台北:茂林出版社1998.
[3]李天铎.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M].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7.
[4]廖炳惠.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媒体、消费大众、跨国公共领域[M]//郑树森.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