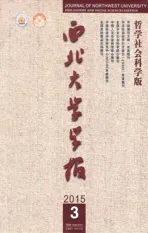作为虚构文本的梦叙述
2015-02-21方小莉
方小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从古至今,梦之于人类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在东西方的各类典籍中均有关于梦的记录。梦本身神秘莫测,光怪陆离,似乎是在人类社会的逻辑、伦理、秩序之外建构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但是梦同时又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因此人类一直钟情于探索梦的奥秘与作用。
古代的详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梦境来了解神的旨意,同时梦还可以预知未来,甚至到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人相信梦可卜吉凶。从心理学上来讲,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某种愿望幻想式的满足,它是通过幻觉式的满足来排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一种经历”[1](P115)。也就是说,人类压抑的各种欲望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刺激从而影响人类的睡眠,而梦则通过幻觉体验的方式满足了人类的某些欲望,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睡眠不受干扰。从叙述学上来讲,龙迪勇认为梦是一种为了抗拒遗忘,追寻失去的时间,并确认自己身份,证知自己存在的叙述行为[2](P22)。而赵毅衡则主张“人类十多万年的进化中之所以没有淘汰梦是因为梦有力地加强了人的叙述能力,帮助人类成为一个能靠讲故事整理经验,并且能够用幻想超越庸常的动物”[3](P56)。
从心理学方面来研究梦,自弗洛伊德开始历经一个多世纪,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从叙述学角度来研究梦却一直未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梦作为叙述的合法性问题,即梦是否是叙述。普林斯(Gerald Prince)认为梦不具备叙述的特征,完全否认梦是叙述[4];吉尔罗(Patricia Kilroe)一方面主张“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另一方面他认为不是所有的梦文本都是叙述[5]。梦叙述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长期被忽略,早期关注梦叙述的仅有龙迪勇的《梦:时间与叙述》,他认为“梦实质上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一种叙事行为”,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讨论了梦文本所具备的叙述特征:梦叙述包含了叙述所应有的基本元素:“人物、事件、空间、开端、发展、突变、结局”,从而肯定梦是一种为了抗拒遗忘,寻找时间的叙述行为。龙迪勇在国内率先肯定了梦作为叙述这个命题,但遗憾的是他研究的对象已经是被再次媒介化,通过某人讲述的梦,仅剩下了梦的部分内容,而失去了梦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研究的并不是此时此刻的梦本身。
梦叙述的研究一度陷入僵局,直到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的诞生,才让梦叙述名正言顺地回到了叙述学的怀抱,他把梦看成是“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6](P5)。赵毅衡认为“梦是媒介化(心像)的符号文本再现,而不是直接经验;其次它们大都卷入有人物参与的情节,梦者本人就直接卷入情节。因此梦是叙述文本”[3](P47)。梦叙述满足叙述的底线定义。在《广义叙述学》中,赵毅衡集中检查讨论梦本身的文本性与叙述性,不仅为梦之为叙述提供了有力证据,同时也从叙述学的角度探讨了梦的形成、作用及意义等重大问题,从而为梦叙述的研究打开方便之门。然而该书尚未对梦作为叙述文本的各要素系统展开讨论。本文详细分析了梦叙述作为叙述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并试图探讨梦叙述自身的特殊性,针对过去被学界忽略的梦叙述的隐含作者与叙述可靠性问题,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梦叙述的(文本)虚构世界与(文本外)经验世界
梦叙述与小说、戏剧等叙述形式同属于虚构型体裁。正在做的梦并非是经验,因为“经验面对的是世界,而梦者面对的是被心像再现的世界”,同时梦叙述“很难是纪实型的,接受者无权将文本与实在世界对证”[3](P48-50)。任何一个虚构型叙述文本都通过叙述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文本内虚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虽然独立于经验世界,却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可以无限地靠近经验世界,却永远无法与之重合。弗洛伊德认为,“睡眠中我们将自我同整个外部世界隔离开来”[1](P121)。做梦的人入睡隔断清醒思想,从而进入叙述的二度区隔[3](P78)。也就是说我们的梦世界与外部世界是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梦的内容却又与真实世界分不开。无论梦是真实世界人类本能欲望的满足还是只对个人过去经历、记忆的重新组织,可以肯定的是梦跟所有虚构型叙述一样锚定于经验世界。我们可以通过梦世界去建构各种可能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经验世界。
当然梦叙述与其他虚构型叙述相比又具不同的特点。梦叙述似演示类叙述一般,总是此时此刻感知当场发生的事件。但梦叙述作为心像叙述又无法被分享,一旦分享就改变了媒介,破坏了梦的此刻性,从而“此梦”也就不同“彼梦”了。梦被转述使梦的媒介由心像转为文字,使梦的时态由此时此刻变为过去时。梦的无法分享不仅是体现在形式被破坏,事实上梦的内容被再次分享时,也无法完整保留。
首先,叙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没有一个人能够事无巨细地将梦中发生的一切完完全全再现。
其次,“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觉形象,对梦进行再叙述时,部分困难在于我们将用语言描述这些形象”[1](P71)。也就是说当梦者醒时,心像媒介发生了变化,梦已经变为过去时。而梦者在对梦进行转述时也需要将图像文字化,这使得媒介又一次发生变化。
第三,从心理学上来讲,梦的审查机制,使得我们在清醒后,在记忆梦中发生的一切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不明确的成分,让梦者无法记起梦中的一切,当然也许是梦的该部分内容无法通过“审查”进入人的意识层面,所以当我们清醒时梦中的某些细节早已忘记。
最后,如果梦真是本能欲望的满足,没有任何人可以坦然地分享自己的所有梦的一切细节。也许梦叙述所构筑的世界是一个比任何一类虚构叙述更丰富,更具有想象力的世界,因为它是个人的、私下的,可以充满各种奇思妙想、荒诞不经,各种逻辑混乱,甚至是各种有违伦理纲常……这个梦的世界无需向任何他人负责,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就算是醒来以后的自己如何觉得厌恶、羞愧或是震惊……那也是经验世界的事了。
从梦叙述与其他虚构叙述的对比可以看出梦叙述以及其所建构的虚构世界的特殊性。构成梦叙述的各个基本要素一方面具有各种虚构叙述中各要素的共同特点,同时也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二、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合一
本文将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放在一起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三个因素在任何叙述文本中都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叙述文本都是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而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3](P7)。叙述的底线定义中所说的“主体”即叙述者,“接收者”即受述者,可见任何一个满足叙述的底线定义的叙述都必须包含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与其他的虚构叙述文本相比,梦叙述文本中的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之间有着更为特殊而密切的关系,三者可以说是统一于同一个整体。
“任何叙述都是一个主体把文本传送给另一个主体”[3](P52)。在虚构叙述中,虚构世界的叙述者将一个有人物卷入的故事讲给受述者听。叙述者可以是虚构世界的人物,也可以隐藏于叙述框架之后,而受述者在虚构世界中可显身作为虚构世界的人物,也可以完全隐身。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通的虚构叙述中叙述者与受述者必然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两者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受述者对叙述者可以产生影响,受述者会对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方法、讲述的内容等产生影响,甚至是可以人为地打断或叫停叙述。事实上在一些叙事文本中也出现了对受述者重要性的强调,例如在《一千零一夜》中,受述者才是终极意义的阐释者。受述者对叙述者的影响在一些现场表演、即兴表演中更为明显,如相声艺术中的“现挂”。
然而在梦叙述中情况却有所不同,梦者并不是梦叙述的叙述者而是受述者。梦者在梦中犹如看电影一样被动地接收着梦。梦叙述的叙述者与受述者是同一个主体分裂后的产物。梦叙述是“主体的一部分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3](P52)。即是说大脑分裂出了两个部分:孕育梦的部分和接收梦的部分。梦叙述就是人体孕育梦的部分向接收梦的部分讲述故事。在这个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梦叙述的叙述者永远躲在叙述框架背后不显身,但却掌控着整个叙述;而梦叙述的受述者永远显身,却“无主体性,仅是梦叙述的被动接收者”[3](P52)。受述者只能“观看”“经历”梦中的一切,既不能影响叙述者讲故事的方式,也对故事无力叫停,更没有选择不听的自由,即使是经历噩梦也只能被动等着被惊醒。在梦叙述中受述者永远显身,同时“观看”和“经历”着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因而成为了梦世界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梦者作为梦的接收者,也同时作为人物被卷入了梦世界。
作为叙述者那部分的“我”讲述了梦却没有看到梦,而作为受述者那一部分的“我”看到了梦,却大多数情况下,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在虚构叙述中,虽然经验世界中的读者明白该叙述为虚构叙述,但虚构世界中的叙述者、人物和受述者却不会认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虚假的。虚构世界自成体系,虚构世界中的叙述者、受述者及各个人物按照虚构世界中的逻辑与规约来行事。弗洛伊德认为“梦常常是无意义的,混乱的和荒唐,但是有些梦也有意义,符合实际以及合理”[1](P77)。龙迪勇认为“梦里活跃着一系列难以用理性和逻辑去框定的事件”[2](P29)。而大多数人也都认为“梦的情节光怪陆离,神秘莫测,不符合人类文明生活的逻辑与常识”[3](P4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的来源都是来自“清醒”后经验世界的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论断是因为我们用经验世界的逻辑去对证梦的虚构世界。事实上梦世界与任何的虚构世界一样自成一体。对于经验世界的人来说,梦世界是虚构的,而且大都是非逻辑的。然而对于梦世界内的叙述者、受述者和人物来说,所有被经验世界认为离奇的、非逻辑的一切却自成逻辑。正如前文所说,梦者并不知自己在做梦,梦中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正在体验和看见的,都是真实的。在梦中的“我”即使觉得梦境离奇,也极少质疑它的真实性。只有清醒过来,回到经验世界后,“我”才发现梦中的一切不符合经验世界的逻辑和标准。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从心理学上来讲,梦者(受述者)并不能完全获悉叙述者的所有信息。弗洛伊德认为梦具有显意和隐意。梦的显意会清晰地呈现给梦者,而梦的隐意却只有通过梦者的联想才能得到[1](P102)。从叙述学上来讲,弗洛伊德所说的获得梦的显意的“梦者”其实就是梦世界的受述者,而能够展开联想去获得梦的隐意的“做梦者”却属于经验世界。由此可见,在梦世界里的受述者只能获得梦叙述的显意,而梦叙述文本的隐意(隐含作者的意图)只能是文本的“理想读者”才能够获得。论文将在接下来的部分对梦叙述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进行系统讨论。
三、隐含作者、隐含读者与梦叙述的阐释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是一对构想出的概念,在文本内无实体可依托。再加上梦叙述本身的特殊性,因此这一对概念至今无人问津。热奈特认为隐含作者是“作者在文本中的一个形象”[7](P141),查特曼也认为隐含作者是“文本意图的体现”[8](P104)。申丹同意布斯的观点,指出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他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可见隐含作者代表了文本中真实作者的某种立场与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与立场又要依靠读者的解码来完成,因此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9](P73)。那么在讨论梦叙述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时,梦叙述的作者和读者似乎也是无法规避的问题。与一切虚构文本一样,梦叙述的作者和读者也理应属于经验世界。然而与其他虚构文本不同的是,梦叙述的作者和读者也合而为一:做梦前清醒的我与梦醒后清醒的我。经验世界的清醒的“我”,入睡后分裂出一部分来讲述故事,又分裂出另一部分来接受故事和经历故事。因此入睡后不清醒的我就犹如虚构文本的执行作者,而这一作者在梦中通过叙述要表达自己的某个立场,即梦的隐意。然而他的这个立场并不是直接显示给接收者,而是经过各种伪装变形,只让受述者接收到显意。而他的隐意则需要清醒过后,再次回到经验世界的读者“我”通过对梦进行阐释才有可能获得。
任何叙述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梦叙述的叙述者也不例外。构成梦世界的材料极为丰富,不可能一一进入梦叙述。梦叙述的叙述者则需要根据自己要传达的隐意来筛选组成梦世界的材料。为了让受述者能够有效接收到梦文本的信息,叙述者则需要选择受述者所熟悉并能理解的材料。因此梦叙述“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个人过去经历的记忆,特别是最近的,最显著的材料相对优先”[3](P51)。这些材料都是梦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共享的材料。另一方面,梦本身所具有的审查机制也使得梦叙述者在讲述某些故事时,为了让梦文本的意义能够传达到梦者那里而不得不采取特殊的策略,进行隐喻式的叙述。由于受到某种刺激,如本能欲望被压抑,遭遇某种压力或紧张情绪等,叙述者通过对相关素材的高度筛选,再结合自己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作为受述者的梦者听,一方面通过叙述可以获得幻想式的满足或是释放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也通过显梦的展示,将梦叙述的意图传达给梦者。
关于梦叙述的意图,即隐含作者的立场,并非是任何一个处于清醒状态的“读者”都能够获得,而只有“理想读者”,即梦的隐含读者才能读取。笔者认为梦叙述的理想读者很难成立,若有可能,也只能是那位经验世界的梦者本人。一方面是因为,梦的材料来源几乎都与梦者以往的记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梦的无法分享性。梦的隐意大都需要通过专业的精神分析才能获得,然而即使是具有精神分析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自我梦的阐释时,也会遇到下面两个难题:
首先,梦是作为一个复杂结构进入意识层的,这个结构由许多元素混合而成,而各个元素间的连接是无意识的。我们对梦进行阐释是借助于意识对比去想象无意识,然而并不是梦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可认识的性质,都能从它推论出意识的特征[10](P61-62)。梦是无意识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内容均复杂多变。而无意识依然是人类尚未完全认知的领域。这个领域有自己的标准和逻辑,而清醒后的梦者只能处于意识层面,也就是只能用意识(经验)世界的逻辑去理解、想象无意识世界,这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障碍。然而处于梦中的梦者虽具备无意识逻辑,但却苦于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因此无法展开梦的阐释活动。因此我们的意识层面不仅无法在此时此刻分享我们无意识层面的梦境,同时用意识层面的逻辑也并非能够认识无意识或是潜意识的全部内涵。梦世界让我们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也相信另一种逻辑的可能。
其次,梦的审查作用时常通过修饰、暗示和影射来伪装并替代真正的表达。梦者在醒来过后记忆可能会出现模糊不清的状况,这些无法通过审查的梦的成分根本到达不了意识层面。梦者甚至都无法忆起构成梦的显意的一切内容。如若梦者无法记起梦的内容,要通过分析梦的显意来获得梦的隐意就更是难上加难,那么也就是,梦叙述的隐含作者的意图也相应难于确认。
梦叙述的隐含作者与其他叙述中的隐含作者相比也有一个突出的不同点。赵毅衡认为所有叙述的隐含作者原则上都比作者本人要高尚,但笔者认为梦叙述却是个特例。“叙述大多是一种‘社群文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群责任,要让听者得出伦理结论,遵从社群的规范与期待”[3](P54)。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识,所以一方面作者在写作时要对群体负责,建构一个高尚的隐含作者,否则该书可能无法通过审查与监管,从读者方面来看,读者在阐释时也会相应地根据社会的规范与期待来解读出一个高尚的隐含作者。梦叙述则不然,首先梦叙述完全是个人的,无法分享,也无需共享,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群体责任,梦者即使在梦中烧杀抢掠也与人无尤,梦者无需担责。梦世界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逻辑,它不受到经验世界的管辖,因此无需尊崇经验世界的规范与期待,那么隐含作者就不一定需要比作者高尚。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梦叙述的隐含作者甚至是比作者品质更为底下,因为我们的梦都是“本能欲望的满足”[11](P12)。而从我们的文化规约来看,我们的本能是比我们的自我要品德低下的。
由于梦叙述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特殊性,也使得梦叙述文本的意义阐释具有特殊性。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符号的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意义,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三者常不一致,梦叙述尤为如是。梦叙述的符号发送者(孕育梦的那部分头脑)的意图是要发送梦的隐意,即是隐含作者的意图,梦叙述文本(梦境)包含了显意和隐意,但梦的接收者(梦者)在梦中只能看到显梦。要获得梦的隐意,则需要梦者醒后对梦境进行分析。然而醒来后的梦者已经回到经验世界,梦境的媒介已发生改变,内容也无法完全还原,因此即使是梦者自己也已经无法完全分享接收梦时自己所看到的显梦。当然也正是由于梦叙述的特殊性,使得人类对该类叙述的阐释相对自由。首先,由于梦叙述是纯粹私下,无需向公众问责的特殊叙述,那么在阐释梦叙述时也无需拘泥于要读出一个“高尚”的隐含作者。其次梦境是由人类潜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活动构成,它的世界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方式,并不受人类意识层面的控制。因此我们在对梦文本进行阐释时,需要打破我们的逻辑常规,自由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而对拥有不一样逻辑的梦文本的认识,也可以启发我们打破陈规,重新认识和建构我们的现实世界。
四、梦叙述的叙述可靠性
讨论隐含作者必然要涉及到叙述的可靠性问题,因为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中很关键的问题,学界对该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然而有关梦叙述的可靠性问题至今无人提及。在讨论了梦叙述中的隐含作者问题后,本文也尝试探讨梦叙述中的叙述可靠性问题。叙述可靠性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之间的距离问题。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一致时,叙述判定为可靠,反之则判定为不可靠。
在虚构叙述中,叙述可能是可靠也可能是不可靠。当虚构型文本中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不一致时,叙述就会不可靠。而在纪实性叙述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重合,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无距离,价值观一致,因此纪实性叙述中叙述绝对可靠。叙述是否可靠是一个文本内的形式问题,我们所考察的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间的关系。而是否可信却是跳出了文本,是读者对作者的质疑。虚构叙述可以可靠,也可以不可靠,只有纪实性叙述才绝对可靠。那么也就是说理论上作为虚构叙述的梦叙述也会出现有的文本中叙述可靠,有的文本叙述不可靠的现象,但是作为虚构性叙述的梦叙述却是绝对可靠的叙述。在梦叙述中,孕育梦的那一部分头脑就是梦叙述的叙述者。孕育梦的那一部分主体的意图是要向接收梦的那一部分主体传达人本能的或是潜意识的欲望、需求及想法等。梦的叙述者则通过高度的选择,将这个意图经过变形,以显梦的方式发送给梦者,以期待梦者能够通过显梦获得隐梦的意义。因此梦叙述中叙述者与主体中发出梦信息的那一部分人格合一,梦叙述者的价值观等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纪实性叙述一样,梦叙述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之间无距离,是叙述者绝对隐身的可靠叙述。
本文通过对梦叙述的各要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梦叙述作为虚构型,演示类叙述的文类特点。梦叙述与其他虚构型文本具有共通的特点,但由于构成梦叙述的主要成分,叙述者、受述者与人物的特殊性,梦叙述又展现出了自己不同的特征。本文在讨论构成梦叙述的基本要素的同时,也试图对梦叙述的隐含作者、叙述可靠性等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学者能够加入对梦叙述的研究。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C].周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2]龙迪勇.梦:时间与叙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2,(8).
[3]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4]PRINCE G.Forty-One Questions o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J].Style,2000,34.
[5]KILROE P.The Dream as Text,The Dream as Narrative[J].Dreaming,2000,(3).
[6]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第9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7]GENETT G.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8]SEYMOUR C.Coming to Terms: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9]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荣格.性与梦: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M].梁绿琪,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C].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