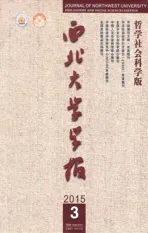“仁爱”与“神爱”:《论语》与《圣经》核心价值差异比较
2015-02-21刘炜评
郑 荣,刘炜评
(1.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 710061;2.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 710069)
《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通行本共20卷,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间或有叙述体。全书摘要录存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主要涉及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原则等方面,其文化关键词是“仁”“礼”“义”“中庸”“君子”等,集中体现了孔子学派的价值取向。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人的《圣经》”云云,皆就其地位崇高与影响深广而言。
《圣经》(拉丁语Biblia,希腊语Ββλο,英语Bible,本意为莎草纸)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经典。犹太教的经典指《塔纳赫》(或称《希伯来圣经》),基督教的经典则指《旧约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圣经》(《新约全书》)两部分。基督教《圣经》思想文化信息丰富,素称“打开西方精神世界的钥匙”“唯一的书”“书中之书”等,是全世界译制版本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论语》和《圣经》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教育方式、道德观念承变、行为规范引领等方面分别都对东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两部经典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依然涵溶于东西方人的思想血液之中。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读解、分析《论语》与《圣经》的义理异同,对于理解东西方历史的来龙去脉,增进东西方国家与人民的相互了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孟子曾无比敬仰地赞美孔子为中国上古文化之“集大成”者,并强调孔子学说达到了“理”“圣”兼具的深度与高度:“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1](P672)移“集大成”之说于《圣经》,亦足称名实相副。《圣经》66卷,创作时间至少跨越千年以上,作者40多位,身处不同时代,而全书的“条理”相贯是始终的。《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编撰者为孔门众徒,全书“条理”的相贯更是始终的。自《论语》《圣经》问世迄今,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它们的释解、研究代代延续、汗牛充栋。《圣经》传入中国和《论语》传入西方以后①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至初唐传入的“景教”,为基督教分支之一。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出土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自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遭禁。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第一期。第二期为元朝,流行于西亚的景教重新传入,同时罗马的天主教并传入,时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第三期为明末清初,时称天主教(旧教)。第四期为近代,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者数量大增。159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取名为《中国四书》(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是为《论语》等儒家典籍西译之始,但未能正式出版。最早刊印于欧洲的《论语》西文版本,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由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主持编译。大体来说,从17世纪开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较多传入欧洲,思想家笛卡尔、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等,都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有很多研究。参见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版;杨平《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中外学者对于两部经典的异同也给予注意,从宗教、伦理、文学、语言、翻译等角度陆续展开对比研究。明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自西徂东的传教士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向阐释者的角色。著名者如利玛窦(Matteo Ricci)、艾儒略(Jules Aleni)、贺清泰(Louis Poirot,1735-1814)、马士曼(Joshua Marshman)、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在《圣经》汉译和《论语》英译的过程中,大都采取了“调和耶儒、以耶补儒”的归化翻译策略和弹性传教方式。19世纪后期以来,中外学者如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 (Arthur Waley)、安乐哲 (Roger T.Ames)、辜鸿铭、刘殿爵等的《论语》西译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无不潜在地体现着他们对中西文化背景的对比与理解。熊十力、杜维明、唐君毅、余英时等新儒学派在定位和理解“儒家是宗教的还是伦理”的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以《圣经》这一建制性的宗教范式为显性或隐性的比照对象和标准。李泽厚的《论语今读》[2]在参考朱熹《四书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刘宝楠《论语正义》、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等注解的基础上,不时以《圣经》比较《论语》,提出了《论语》“半是宗教半是哲学;论语非圣经,中国仍需‘德先生赛先生’”的观点。近20多年来,从教育、伦理、社会影响等方面对《论语》《圣经》进行的对比研究,较诸以往更为深入,成果甚多。举其要者,专著有何世明著《从基督教看中国孝道》(基督教文化出版社,1999),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儒释道与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第4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姚新中著《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论文集有傅有德主编《跨宗教对话: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罗秉祥、谢文郁主编《耶儒对谈:问题在哪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等;论文有夏志丽的系列成果《〈圣经〉的上帝观与〈论语〉的天神观》《天道人性显于语言——〈圣经〉与〈论语〉语言观的对比》《〈圣经〉〈论语〉人性论之比较》《〈圣经〉〈论语〉知识论之比较》②依次见《孔子研究》2004年第6期;《齐鲁学刊》2006年第3期;《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齐鲁学刊》2009年第5期。,刘清平《佛教与基督宗教普爱观之比较——析普世爱人与宗教仇恨的悖论》③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林滨《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④见《哲学动态》2011年第5期。等。
本文在借鉴前贤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通过比照对读《论语》与《圣经》文本,讨论两者的核心价值——“神爱”与“仁爱”的义理差异,并由兹涉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些方面。至于孟子及后世诸贤著作中对“仁爱”的阐发,不在本文述论范围之内。
一、“爱”的内涵与本原之差异
《论语》和《圣经》都宣传一种理想的道德理念——“爱”。《论语》提倡“仁爱”,即“爱亲人和爱众人”[3](P60)。《圣经》倡导“神爱”,即“爱上帝和爱邻人”。虽然它们都主张“爱”,但对于“爱”之来源的理解与“爱”之本质的确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言之,儒家“仁爱”思想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最后落实在‘亲亲’‘敬长’”[4](P23)上的伦理差序之“爱”,其特点是由人及人,在人际关系上强调爱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等差性。而基督教的“神爱”坚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其特点是由神及人,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上帝之下所有人爱的平等性;认为爱的本质与根源是上帝的先在和永在,如果没有上帝的权威、恩赐和帮助,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
(一)《论语》的“仁爱”:由人及人
从概念内涵上看,“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就是这种差等思想的体现。首先,血缘家庭的亲情之爱是“仁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仁爱”的最内圈层。爱人首先要爱自己身边的亲人,《论语·学而》载有若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P48)也就是说,“孝悌之爱”是“仁”的根基。其次,亲情之爱只是“仁爱”的出发点,它还要求推己及人,把对父母兄弟子女的爱推广到爱一切人,即孔子主张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5](P49)。“泛爱众”是“仁爱”的中间圈层。第三,“仁爱”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一家,即子夏劝导司马牛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论语·颜渊》)[5](P135)第四,由爱人推及天地万物,达到与天地万物谐和相安的境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5](P99),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一方面作为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取食于自然物;另一方面作为有善性和有理智的人类,对自然物须持爱而惜之的态度。北宋张载《西铭》中的“民胞物与”说,则是对儒家由爱人到爱物传统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可见“仁爱”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先爱自己的亲人,再层层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地扩展到他人以至天地万物,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现代人常说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四个方面关系的措理[6](P99)。
从思想根源上看,“仁爱”始于人性,在人性中表现为美德。首先,“仁爱”是一种人人都应该拥有的普遍的道德品质;其次,“仁爱”是一种人类追求善与崇高的特殊德行;再次,“仁爱”是完美且最高的美德的具体表现;最后,“仁爱”是人类所有德行的基础,具有道德的奠基意义。当人的潜能得以实现时,“仁爱”的内涵就有了具体的外现,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1](P86)“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1](P891)等等。
从功能意义上看,“仁爱”的落脚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良化。在人类生存活动中,“仁”不仅指的是人的存在形式,还指人的超越品性。所以,既需要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阐释人性,更需要在社会伦理的层面上控导人性。“仁爱”立足“主体间性”的社会关系规定人际伦理准则,包括人的自律与他律:要求具有理性自觉能力的人,必须接受主体自定的伦理法则(“克己”)并通过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获得“自由”(“从心所欲”),而要保证这种个体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并存,就应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5](P92)的准则为人处世。所谓“存心”“养性”“事天”云云,既是“仁爱”所设定的准则,也是人性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代价。
(二)《圣经》的“神爱”:由神及人
“神爱”的基本内容是“爱上帝及爱邻人”。“人神之爱”和“人人之爱”是“神爱”的本质属性。这两种形式的爱既有区别,又不能相互割裂。这种由回应神之爱而强调的人与人之爱,实际上是一种泛爱主义。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就明确指出:“爱邻人”中的“邻人”,就是指每个人或一切人[7](P26)。在基督教文化中,爱上帝与爱邻人是“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2∶31。第15页)①引自中译本《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刊印,南京,2004年版。本条及其后引自《圣经》的语料,皆出此书,拙文只标注引文在该版本中的章节和页码。。“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2∶37-40。第28-29页)但就相对关系看,爱上帝是第一位的、至高无上的,爱邻人则是第二位的、从属的。爱上帝之于爱邻人,不仅具有本原性、先决性的意义,而且始终占据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8](P26)。只有上帝对人的爱,才有可能生发出人对上帝的爱和人对人的爱。上帝之爱构成爱的本体论基础,人之爱上帝与人之爱人是对爱的本体的积极回应。
“神爱”强调博爱精神和宽恕品德。“爱人如己”的诫命,就是要求毫无差等地博爱众生,盖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3∶4-8。第194页)。首先,无条件性、无差别性、非选择性是“神爱”的突出特征:“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3∶34-35。第123页)其次,神爱还宣扬无所不在的宽恕之爱,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它不但强调亲情之爱,还主张“要爱你们的仇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5∶44。第6页),要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然饶恕你们的过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6∶14-15。第7页)这是一种极端之爱,更是一种普遍之爱,超越了世俗的男女之间的自然爱欲和亲朋之间的伦常之爱,进而超越了地域的、种族的、民族的局限。
“神爱”本质上揭示的是神与人的关系。基督教倡导平等之爱、无私之爱,具体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神学的爱,二是宗教的爱,三是伦理的爱。但三者不是平行的,而是一种因果关系。首先“神爱人”是因,是先于后两者而存在的[9]:“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圣经·新约·约翰一书》4∶7-8。第270页)又明确指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0∶34-37。第12页)在基督教的神人关系中,神是主宰者和主动者,人是执行者和被动者;给予→接受、恩典→承纳、启示→信仰是神人关系的呈现方式。神人之划界,实质上揭示了上帝的绝对性和神圣性。
二、“爱”的超越方式之差异
《论语》强调的“仁爱”与《圣经》强调的“神爱”都非常关注“爱”的自觉、自为与超越,要求人类将“爱”的理念既能“内化于心”,又能“外化于行”,从而实现从外向内灌输、确立和从内向外践行、超越两个过程的统一。但在探索超越的途径时,“仁爱”将超越转向了美德,而“神爱”将超越转向了响应。“仁爱”主张通过修身养性、道德反省实现超越;“神爱”提倡通过原罪忏悔、灵魂反诉实现超越。
(一)《论语》的“仁爱”:自我升华与实践准则
《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P79)朱熹解释“性与天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性即性命,亦称命,天道亦称天命。孔子不轻易谈论性命与天道,不等于不承认它们。事实上,孔子生前也曾提及性或天道。如“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5](P176)“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5](P173)“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5](P196)不过在孔子看来,“天道”固然是外在于人类的客观实体,但其之于人类的意义,却非外在而是内在于“人道”之中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5](P181)意谓“天道”“天理”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天以“无言”的方式,既滋育着世间百物,彰显着“仁”的本质,又昭示着人类:人的生命自持力可以直接变成“仁”的德行,所以“仁”乃诸多美德如义、孝、礼、智、信等的根源和基础。而人要把“仁”这一普遍原则内化成为自己的特殊美德,就必须通过积极地入世实践来完善与提升道德修养,进而实现“仁”的内化与超越。“克己复礼”便是修养自我以达到“仁”的要求的手段和方法。孔子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5](P61)“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5](P133)“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5](P100)说明人是“仁”达成的物质载体,要实现“仁”就要发挥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仁”德的获得,重在发自内心情感,诉诸心理原则,将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10]。人能不能成仁,不在于能力大小,关键在于自觉地追求和持续地践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5](P70)“仁”需要通过“修身”“养心”“躬行”等途径方能实现,所以“仁爱”的超越实质是一种反省内求活动,是一条可通过自力修养而抵达的成德成贤以至近圣之路。
“仁爱”的超越,是伦理方式的超越。它倡导以人为中心来超越生命的有限,认为实现超越的责任主要在人自身而不是人之外的神与物。超越的境界和人的世界是不可分离的,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自身的道德完善来实现人际、天人之际的和谐、圆融。所以,超越在本质上是人的事情,只有人才能为此负责;对于人而言,超越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一个人的善良本性。“人性可以通过道德的自我修养而获得超越,超越的实现也就是仁的实现,仁的实现也就是伦理的实现。”[11](P217)
(二)《圣经》的“神爱”:神的使命与上帝的宽恕
对超越的追求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但“神爱”的超越主要来自神的谕示。对绝大多数基督教徒而言,超越就是要生活在基督的圣灵之中,参与到基督的生命中去。不是人间物事的启发、帮助而是上帝的怜悯宽恕,才能使人生实现超越,而所谓终极实现,也只存在于上帝的神爱之中。所以积极响应上帝召唤,将身心归属于上帝,才是超越的根本途径。生而有罪、感悟有限等这些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人必须依靠“他者”的神圣力量亦即在上帝的恩典与启示下,通过信仰、忏悔而实现超越与重生;人性与神性是可以交往的,而爱是神性的表现,只要让“神”进驻到人心中,消除原有的“罪性”,爱才能表现出来[12]。不仅如此,人要得到神的爱怜,还必须要对神的要求或命令给予回应。爱必须由神性灌注到人心,才能在人那里获得自己的表现形式。没有这种把“客观”命令主观化为内心要求的过程,人类的爱就不会成为现实的存在。所以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道德成长的源泉是上帝。
从“神爱”的超越方式来看,其运动的起始和终点都不在人性之内,超越过程由神之爱激活,从中汲取力量,最终目标还是融入神之爱中。人的内心信仰、神的外在救赎构成“神爱”超越的两面,只有在神的启示和人的信仰发挥合力作用以后,人才会获得恩典而浴火重生。所以,“神爱”具有附身性和给予性,“神爱”的超越是对上帝的信仰和追随,超越的根本意义是将人从“罪性”中拯救出来,使人回归“原善”及与上帝的关联性之中。
三、“爱”的宗教与伦理之差异
《论语》的“仁爱”体现的是人本主义精神,其基本特征是原则的包容性。在“仁爱”中,宗教与伦理并没有什么不同,超越只被看成是伦理的至善,在此意义上“仁爱”便具有了世俗性;“仁爱”将道德看作是仁之人性的反映;在伦理的实现机制上,“仁爱”主张修身成仁在己,因而重视道德践履;在道德目标上,“仁爱”注重伦理的现世性,重视“内圣外王”的达成[13]。
《圣经》的“神爱”体现的是神本主义精神,其基本特征是原则的排他性。在“神爱”中,宗教与伦理有着严格的界限,伦理从属并服务于宗教,在此意义上“神爱”就具有了神圣性;“神爱”把道德归之为神性的表达;在伦理的实现路径上,“神爱”强调拯救的他力性,指出救赎之路在神;在价值目标上,“神爱”重视伦理的彼岸性,关注“天堂永生”的实现。
(一)《论语》的“仁爱”: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以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依据理性原则确认社会价值并据此衡量社会意识和个人行为,因而其价值尺度具有现实性、现世性和世俗性。“仁爱”在多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取向。
首先,在伦理道德观上,仁爱强调道德是人性之仁的反映,认为人有自由选择向善的本质力量。仁在人性,仁在人心,人只要真心、决心向仁,就可以通过修仁践仁而实现自我超越。发掘人的善良本性,鼓励人的道德修养,重视人的实践活动,无不体现了“仁爱”以人为本的特征。
其次,在修行方式上,“仁爱”关注的是人的责任担当。它认为仁与人性浑然一体,所以实现“仁德”的基本修养方式,就是人的反省内求;引导“善性”、推行“仁道”和践行“仁德”,是人应有的担当。“仁爱”重视爱的自身性和给予性,把人的道德超越看作人的自我完善途径,坚持人性与超越的一致性。
再次,在价值追求上,“仁爱”将人作为价值主体,以寻求人的道德自觉、确立德性的主体性为根本目标,积极唤醒人的自我觉醒意识,力求释放人的自我道德正能量,促成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并崇尚人法天地的人文精神,鲜明地体现出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为终极目标的热忱。
最后,在人格塑造上,“仁爱”追求君子品格和圣人之境。将仁道所塑形的人性具化为一种理想的人格,那就是“君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5](P163)。君子何以能临危而毫无惧色?因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5](P71),“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5](P166)。仁与义充盈身心、统领行止,乃是君子必备的品德和行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5](P70)。君子要有“修己、爱人”的品德,修己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人,爱人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二)《圣经》的“神爱”:神本主义精神
“神爱”将爱归于神性,认为人的道德品性必须通过信仰上帝才能养成,人生的终极目标、价值意义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所依归,这正是强调“神性”“神权”“天理”和“教条”[14]的神本主义的表征。
首先,“神爱”强调“神性”,将爱之源归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罗马书》第五章指出,神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经·新约·罗马书》5∶5。第172页)。因为邪恶贯穿于人的全部生存状态,所以人必须靠上帝的恩典才能爱。使信徒获得上帝之爱并藉此恢复人性的原善,是耶稣与教父的主要职责。
其次,“神爱”强调“神权”,执著于伦理道德的信仰性。按照基督教教义,全人类作为上帝的造物,应该绝对服从上帝旨意。只有那些承认上帝的权威和仁慈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爱的对象,也只有那些充分理解耶稣牺牲之意义和价值的人才能接受爱。这种排他性的神本主义原则,贯穿于基督教的一切诫命之中。因此,信仰上帝的伦理价值,便远远高于人们的其他一切善行,甚至是一切善德的终极根源。
再次,“神爱”强调“天理”和“教条”,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神爱”强调人的意志力的无能,将善的判断与立法者归于上帝,并从人类的原罪引出上帝出场的必然性。因此,在“神爱”的概念架构内,人深陷于“罪性”,加之良知有限,无力从堕落中自拔,因此需要神圣的他力救赎,需要绝对的“神爱”的终极审判和矫正。中国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倒颇像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余 论
作为影响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两部经典著作,《论语》和《圣经》两种文本之间的文化差别是显著的。《论语》彰显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儒家伦理范式,而《圣经》突出的是以神为中心的犹太伦理范式;《圣经》系统地使用着超自然的和比喻性的语言,而《论语》使用着日常经验的和理性的语言;《圣经》的经久性,源于古代地中海文明神话学传统的持续影响力,而《论语》的经久性,源于孔子学派和其承继者共同崇尚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尽管如此,《论语》和《圣经》中仍然存在着相通或相似的人文精髓。如孔子对弟子谈事亲既强调侍养尽力:“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更强调从内心深处尊崇爱父母:“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5](P55)。这与《圣经》“能养、尊亲、不辱”的事亲训诫不无相合。其他方面如对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阐发等,亦有不少辉光相映之论。正是这种相通性,才使它们的对话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否则两者就只能是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的独白。
[1]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3]刘夏.孔子仁爱思想内涵及现实意义[J].传承,2008(11).
[4]杨宝安.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思想比较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1.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韩星.仁者爱人——儒家仁爱思想及其普世价值[J].梧州学院学报,2013(4).
[7]AURELIUS A.On Christian Doctrine[M]∥In Dods,Marcus(ed.).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e,Vol.9.Edinburgh:T.& T.Clark Co.,1873.
[8]刘清平.佛教与基督宗教普爱观之比较——析普世爱人与宗教仇恨的悖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9]孙文娟.儒教之仁与基督教之爱[J].绥化学院学报,2005(3).
[10]赵春霞,李坤英.《论语》仁爱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与忠恕之道[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11]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赵艳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关静.神本主义之爱[J].天中学刊,2009(6).
[13]林滨.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比较[J].哲学动态,2011(5).
[14]席云舒.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中国精神现象学”的视角与当代社会转型[J].文艺争鸣,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