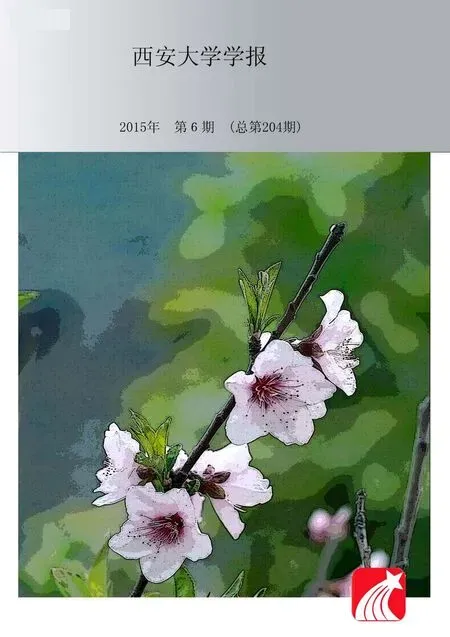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2015-02-21高进
高 进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政治人格是政治人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内涵着相应的政治道德特质及其价值构成,形成了模式化的人格表征[1]35。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政治人格主要通过其政治言行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关键重要事件中的行为选择,能够深刻揭示政治人内在的道德特质和价值追求。“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的谢迁就是典型个案。谢迁,浙江余姚人,历仕明代宪宗、孝宗、武宗及世宗四朝,官至内阁大学士。但是,宦海浮沉,在与刘瑾等阉党斗争的过程中,在选官荐举时却发生了针对谢迁的“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此事以圣旨形式颁布,而且“著为令”。“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本身只是宦海长河中的一朵涟漪,但是,事件却是谢迁的政治人际生态角力的结果。谢迁人际生态中的敌友双方对峙形成的张力,在政治道德价值层面,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因此,本文旨在以“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切入点,揭示事件背后隐藏的谢迁政治人际生态,探求以谢迁为代表的明代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以期抛砖引玉。
一、力的支点:“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
谢迁,秉节直亮、见事明敏,与刘健、李东阳同在内阁辅政孝宗,天下称之“贤相”[2]卷181,《谢迁列传》,p4819。武宗嗣位,宦官刘瑾等“八虎”当道,谢迁与刘健等奏请诛瑾不成,“见几勇退”[3]卷6,《四十二世祖丕行状》,遂同致仕。但是,刘瑾等阉党“憾不已”[2]卷181,《刘健列传》,p4817,“因遣侦卒四出伺察迁事,竟无所得”[4]卷49,《谢迁》,p929。此前,正德二年(1507)三月,诏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既而,“(正德)四年二月,以浙江应诏所举怀才抱德士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皆迁同乡,而草诏由健,欲因此为二人罪。”[2]卷181,《谢迁列传》,p4819刘瑾以此为借口,欲加其罪,“遂矫旨谓:天下至大,岂无可应诏者,何余姚隐士之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之弊。遂下礼等镇抚司鞠问”。吏部尚书刘宇为攀附刘瑾,阿从瑾意,参劾布政史林符、邵宝、李赞,参政伍符,参议尚卫、马辂,知府刘麟,推官谌聪,知县汪度访举失实。大施淫威,打击异己。而镇抚司领会瑾意,借机示好,狱辞连及健、迁。于是,刘瑾以此为证,必欲逮捕刘健、谢迁,施以并坐,且要籍没其家。大学士李东阳徐为劝解,“瑾意稍释”。但是,焦芳在旁落井下石,抗声曰:“纵轻处罪,亦当除名”[5]卷47,正德四年二月丙戌,p1073-1074。于是颁旨,刘健、谢迁被贬为民。周礼等皆谪戍边。尚卫、林符等各罚米三百石,谌聪、汪度罢职。而且下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2]卷181,《谢迁列传》,p4819。
从客观上看,“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存在着特定的促成因素。
其一,“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与明代选官荐举制度变化有关。明初,荐举制度广为用于选官,“洎科举复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永乐之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宣德虽有鼓励,但是,“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正统以降,“荐举者益稀矣”[2]卷71,《选举志三》,p1714。在荐举日稀人情共厌的情况下,周礼等应诏行荐举之途,“所司未纳,四人屡奏求用”[5]卷47,正德四年二月丙戌,p1073-1074。周礼等人是“因荐举而得祸”[2]卷71,《选举志三》,p1715。周礼“生而颖异,十岁能诗文,弱冠补邑弟子员,博极群书,淹贯经史”,但“累科不第”,著有《续编纲目发明》一书,“进奏孝庙”,由礼部进呈,谢迁为之作序,刊行天下,“援例赐其冠带荣身”[6]卷18,《隐居静轩》。恰逢“诏访举怀材抱德之士”,浙江以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四人应诏。既是应诏,何罪之有?
其二,“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还源于余姚的人文地域文化。余姚以文献、科举著称。“余姚以文献称久矣”[7]卷2,《赠邑宰丘君以义被召之京序》,好学诗书遍及乡里,“好学、笃志、尊师、择友,诵弦之声相闻,下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其子弟,自农工商贾鲜不知章句者”[8]卷5,《舆地志》,p117。而且,“姚士之盛于乡,犹其乡也,其试于春宫成进士,则海内以为前茅矣”[8]卷14,《选举志下》,p291。故此,出现以谢迁为代表的一大批进士科举人才和未中科举却志于科举的怀才抱德之士,是明代铨选官员的重要来源,以致刘瑾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抱怨“何余姚隐士之多如此”。同时,余姚地少人多,余姚人士多愿通过科第入仕等渠道外出谋得生路。“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9]卷8,《史四》,p72因为,“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10]卷4,《江南诸省》,p45。于是,余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外出谋生顺理成章。“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的周礼、徐子元、许龙及徐文彪参与荐举自然无可厚非。
从主观上看,刘瑾利用此事主要基于两种可能:
一种是应试言语触怒刘瑾。《浙江通志》载:“(徐文彪),字望之,上虞人。正德间,举贤良,以母老辞。有司敦趣,乃行。是时,逆瑾方专恣,而谢文正迁以忤瑾,谢事去。文彪至京,试吏部,用萧傅‘恭显’语,瑾览策,以为文正乡人,怒甚,下之狱,榜掠几死,械戍镇番。镇番,接壤流沙,在中国万里外。”[11]卷188另有《甘肃通志》载:“徐文彪,上虞人,武庙时以布衣征。值瑾乱政,即于廷中指为‘弘恭石显’,极诋其恶。瑾怒,下狱,廷杖,谪戍镇番卫。”[12]卷40,《流寓》清人毛奇龄记载:“会诏举怀才抱德,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应诏,同试吏部。中有文用‘恭显’语者,瑾大怒,诏狱榜掠刺,械之戍镇番。而以四人者,迁乡人,其草荐举诏,则健为之,矫旨黜健、迁为民。”[13]卷74,《明少傅谨身殿大学士文正谢公传》
另一种是刘瑾故意找借口屈打成招。陈洪谟《继世纪闻》载:“浙江绍兴府勘报明经修行者四人,内余姚三人。逆瑾以为谢阁老迁所私,执送锦衣卫镇卫司问。其一人妄招,词连谢,因及洛阳。刘瑾以为奇货可耽宿忿。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谢于边戍,赖李阁老曲为辨析,令其为民。”[14]卷3,p86查继佐《罪惟录》载:“时有经明行修之举,内余姚三人,指为臣谢廷(当为迁)所私,送锦衣卫打问,硬招,连谢边戍,免为民。”[15]卷29,《刘瑾本传》
无论是周礼等人言语触怒刘瑾,还是刘瑾屈打成招寻隙谢迁,都成为刘瑾打击谢迁的有力工具。如若周礼等人不是浙江人氏,未必引起刘瑾注意,至多不为叙用。如若周礼等人考举科举之途,刘瑾等阉党也难寻其隙。但是,四人皆为谢迁同乡,而且“事在谢当国时”[16]卷28,《太傅王文恪公传》,又由刘健草诏,这为刘瑾以谢迁“私其乡人”为借口,既能打击谢迁,又能连及刘健,实乃一举两得的机会,刘瑾焉能放过。
刘瑾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主要目的是打击刘健、谢迁等异己力量,周礼等人只是斗争的牺牲品,荐举制度在刘瑾等人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凭由乡党的关系,臆测徇私的“莫须有”,实乃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并且,由此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这是刘瑾等阉党专权的肮脏苛政,也是明代政治发展中丑陋的闹剧。
二、力的形成:谢迁的政治人际生态
“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虽然是不同理念支配下的政治人物以制度为工具的政治斗争,但是却反映了明代正德初年的政治人际生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例事件背后隐藏着围绕谢迁的政治人际关系而表现出的政治矛盾。但是,无论是政治矛盾还是政治合作,都折射出明代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
一方面,刘瑾、焦芳及刘宇等人与谢迁矛盾关系的根源,不仅是政见的分歧,而且蕴涵着个人恩怨,这种政治矛盾叠加积累而表现为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刘瑾之所以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不断打击谢迁,主要是因为谢迁参与正德初年谋诛刘瑾等“八虎”阉党之事。刘瑾等宦官日导武宗游戏荒政,刘健、谢迁等人连章请诛之。刘瑾等环泣帝前,武宗不满刘健、谢迁等顾命老臣的束缚,对刘瑾等皆宥不问,恩准刘健、谢迁等致仕。刘瑾逃过此劫,但是,谢迁“词甚厉”[2]卷181,《李东阳列传》,p4822的态度和“欲遂诛之”[2]卷181,《刘健列传》,p4817的决心,让刘瑾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这既是刘瑾与谢迁的政争之仇,又是明代内宦与阁臣党争的缩影。
焦芳之所以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对谢迁等落井下石,除了个人的政治品德与秉性之外,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为了攀附刘瑾。焦芳“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奏章,一阿瑾意”。其二是与谢迁的个人恩怨。焦芳“又上言御边四事以希进用,为谢迁所抑,尤憾迁。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詈”[2]卷360,《焦芳列传》,p7835。同时,焦芳“亦憾迁尝举王鏊、吴宽自代,不及已”[2]卷181,《谢迁列传》,p4819。其三是南北党争之故。“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国进瑾。”[2]卷360,《焦芳列传》,p7836而谢迁乃余姚人,正是焦芳所深恶之人。这既是焦芳与谢迁的政治矛盾,又反映明代阁臣之间的党争。
刘宇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参与打击谢迁,并非与谢迁存有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攀附刘瑾。刘宇通过焦芳介绍,极力巴结刘瑾。刘宇为刘瑾打击台谏御史,刘瑾“以为贤”;刘宇行贿刘瑾万金,刘瑾“大喜”[2]卷360,《刘宇列传》,p7838。对于刘瑾的政敌,刘宇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刘瑾欢喜的机会。刘宇与大学士刘健不仅是同乡,而且早期受过刘健的栽培、推荐和提拔,但是,当刘瑾得势、刘健失势之时,刘宇对刘健恩将仇报、落井下石。政治人格扭曲的刘宇对恩人况且如此,何况谢迁乎?
另一方面,刘健、李东阳及王鏊等人与谢迁的友好交往,既是源于同僚的关照,也是政见的志同道合,这种政治结合表现为合作性的政治行为。
刘健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与谢迁同命相连。刘健与谢迁在弘治、正德初年同为阁臣,合作很好。根据谢迁《归田稿》的记载,刘健作为内阁首辅,对谢迁“诚意交孚、委任无二”;谢迁作为辅臣,对刘健是“忝从公后、协力同志”。在孝宗弥留之际,“榻前末命,同受重寄”;在同辅武宗时,面对刘瑾恣乱,“权奸恣肆,守正不同,横罹谗忌,我时从公,引身退避”[7]卷3,《祭晦庵老先生文》。可谓共同用行、共同舍藏。二人退隐后,一个在河南洛阳,一个在浙江余姚,相隔千里,二者虽少通有无,但是,交情依然,可谓:“望穷云树驰情远,谊重金兰入梦频”。此后,谢迁回想当年与刘健同命相连之事,慨叹“榻前末命从公后,追想当时泪满巾”[7]卷7,《哭晦庵先生诗》。
李东阳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上全力救助谢迁。李东阳与谢迁皆少年得志,同为翰林,多有交游唱和。而且,同入内阁,与刘健齐心协力同辅孝宗,“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2]卷181,《谢迁列传》,p4819,时称贤相。对于谋诛刘瑾等阉党之事,李东阳亦有参合,但是,态度、言辞“少缓”[2]卷181,《李东阳列传》,p4822,而在刘健、谢迁被勒令致仕时,独留内阁。李东阳泣别刘健、谢迁二公,并赋诗二首送别谢迁:“十年黄阁掌丝纶,共作先朝顾命臣。天外冥鸿君得志,池边蹲凤我何人。官曹入梦还如昨,世路论交半是新,仄柁欹帆何日定,茫茫尘海正无津”。“暂从中秘辍丝纶,同是羔羊退食臣。偶为庭花留坐客,岂知宫树管离人。杯尽尚觉情难尽,棋罢惊看局又新。极目春明门外路,扁舟明日定天津。”[17]567-568“蹲凤”、“羔羊”,已言东阳之心境。但是,此后在谢迁遭受刘瑾等不断打击、“几得危祸”之时,“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2]卷181,《李东阳列传》,p4823。而且,李东阳与谢迁虽遥隔万里,李东阳却通过书信与谢迁“音问不绝”[7]卷3,《祭西涯先生文》,“长笺短札劳频寄,海角天涯慰远思”[7]卷7,《哭李西涯》,二人交情可谓:“谷兰香远尚同心”[7]卷7,《寄寿李西涯七十用雪湖韵》。所以,李东阳对谢迁施以援手,情理之中。
王鏊对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力救得免”[2]卷181,《王鏊列传》,p4826。刘健、谢迁致仕,内阁只剩李东阳,廷议补缺,刘瑾“欲引家宰焦芳,众议推鳌,瑾虽中忌,而外难公论”[18]卷29,《吏部左右侍郎行实》,p176,由此,王鏊入阁。王鏊刚正不阿,与刘瑾、焦芳等人政见不一,面对刘瑾作恶多端,认为应该“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19]卷上,《官制》,p16。王鏊特别赞赏谢迁的耿直与不畏强权,对谢迁所做所为“深以为是”,认为谢迁“十余年间,号能持正,不失为贤相”[20]卷下,《吴宽、谢迁》,p26。而且,从私人交往角度,谢迁与王鏊同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谢迁是状元,王鏊是探花,交情颇深,谢迁在以灾异求退之时,“举公与吴文定自代”[21]卷16,《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赠太傅谥文恪王公墓志铭》,认同与推荐之情殷殷。所以,在刘瑾追究谢迁“私其乡人、摭以为罪”之时,“以公言得释”[16]卷28,《太傅王文恪公传》。后来,嘉靖帝亦对王鏊此举大为赞赏,评曰:“志切匡救”[18]卷12,《内阁行实》,p820。王阳明论曰:“世所谓完人,若震泽先生王公非之耶!”[22]卷25,《太傅王文恪公传》
明代的党争是明代政治人际生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只是一个个案载体,展现出以谢迁为中心的政治人际生态格局,演绎着明代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多元力量进行角逐博弈的政治轨迹。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中,以谢迁为代表的一方,虽然处于战略守势,但是,毕竟他们肩负着维护圣学和国家利益的重任,是政治人际生态中的积极力量,经过积聚与酝酿之后,实现政治人际生态的自我调试。
三、力的呈象: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
“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反映了谢迁特定的政治人格。这种政治人格不仅是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孕育的成果,而且是传统士大夫价值选择的折射与反映。
其一,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君子与小人具有各自独特的内在价值构成,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是衡量君子小人的基本标准,君子崇义,小人逐利,在这种价值选择和追求的过程中,逐步演化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谢迁在儒家义利观的熏陶下,以践行君子礼义为标准,言行如一,始终如一。“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体现了谢迁人格的道德恒定性,展现出君子的“无私”与“无我”。余姚人的荐举,并非谢迁的私心所为,更非谢迁的私利所系,可谓“无私”;面对刘瑾利用“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打击报复的险恶境遇,谢迁亦能处之泰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体现出传统士大夫正气凛然的气节和精神,可谓“无我”。面对刘瑾、焦芳等人的污蔑与打击,“人皆危之”,但是,谢迁却“若不知有忧患者”[23]卷3,《太傅谢文正公迁》,p416,依然将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对于家人与亲友的担心,谢迁应对说:“天佑皇明,计当无他,不见刘元成事乎?”[24]卷27,《宰相中谢文正公迁》谢迁所言刘元成,是指北宋谏官刘安世,其“正色立朝,扶持公道”,有“殿上虎”之称。为章惇、蔡京等排挤,先后七次贬谪。谢迁所言“刘元成事”,是指刘安世因受“同文馆狱”牵连,蔡京欲诛杀其灭口,刘安世得知此息,“色不动,对客饮酒谈笑”[25]卷345,《刘安世传》,p10954,视死如归。谢迁所处境遇与刘安世相似,自然以不变应万变为良策,正气的信仰与坚守支撑着谢迁不屈的意志。于是,谢迁“处之裕如,日与客围棋赋诗以自娱”[24]卷27,《宰相中谢文正公迁》,p49-50,心地坦然无界,气节昭然可见。正因为“无私”,方能“无我”。这种政治人格是惯常的行为模式,并非刻意掩饰即可成行,亦非朝夕之间自能可为。真可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其二,在道统与政统之间。在“余姚人毋选京官”的事件中,谢迁之所以受到诬陷及连累,刘瑾之所以能够无事生非、肆意报复,左右这个不平衡政治格局的力量是明武宗的态度。但是,究其根源是谢迁以什么态度侍奉顽劣而偏信宦佞的武宗的问题,即在道统与君主之间需要抉择。谢迁奉行传统儒家道统原则,以道事君,以天下为己任。对于孝宗,忠诚无私,恪尽职守,信守孝宗遗命,精心辅佐武宗,殚精竭虑,对武宗的顽劣行为进行劝谏无效。在道统与君主意志产生分歧时,谢迁奉行道统与君主的分离,选择了“从道不从君”。因此,武宗允许谢迁等人致仕,也就意味着武宗对“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的态度。谢迁在道统与君主之间选择了道统,也就意味着谢迁放弃了对君主无道的苟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谢迁奉行道统,维护圣学,坚信道高于君,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谢迁的政治人格决定了其政治行为的方向。“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只是一个个案载体,蕴含的却是士人政治人格的价值选择。以谢迁为代表的士人,在位时,见事明敏、精心辅佐;去位后,“奉身而退,始终一节,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3]卷6,《四十二世祖迁墓志铭》。个人的政治人格,体现了士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命价值,更彰显出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
[1] 葛荃 .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谢嗣庚 .四门谢氏二房谱[M].1918年木活字本 .
[4] 过庭训 .明分省人物考[M].台北:明文书局,1992.
[5] 明武宗实录[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
[6] 皇明人文[M].明代建阳书坊刻本.
[7] 谢迁 .归田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 (万历)新修余姚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84.
[9]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 王士性 .广志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1] 浙江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 甘肃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 毛奇龄 .西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4] 陈洪谟 .继世纪闻[M].中华书局,1997.
[15] 查继佐 .罪惟录[M].四部丛刊影印本 .
[16] 文征明 .甫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7] 李东阳 .李东阳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8] 雷礼 .国朝列卿记[M].台北:明文书局印行,1991.
[19] 王鏊 .震泽长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0] 王鏊 .震泽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1] 邵宝 .容春堂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2] 王阳明 .王文成全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 刘廷元 .国朝名臣言行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24] 张萱 .西园闻见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25] 脱脱 .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