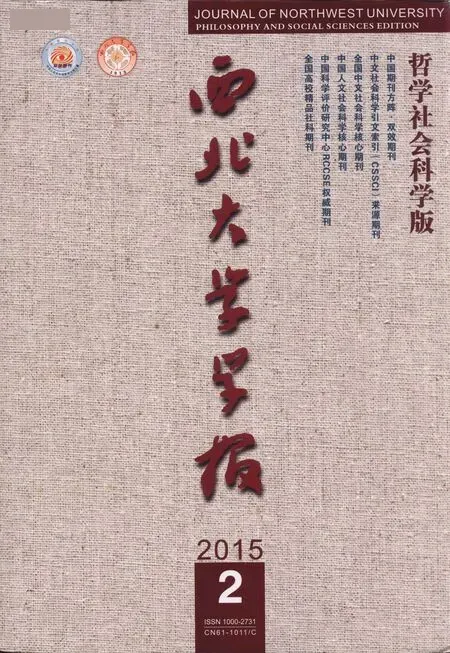符号的底线:始于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讨论
2015-02-21彭佳
彭 佳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41)
“符号调节着解释项符号及其对象。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论及符号,它的解释项不一定是符号。当然,任何概念都是符号;奥卡姆、霍布斯和莱布尼兹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把符号放在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解释项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种行为或经验,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将符号的意义扩展至,认为它的解释项仅仅是感觉的一种质。”[1](8.332)
1868年,在对符号的三元关系进行了数年的思考之后,新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皮尔斯在手稿中,首次用“符号”(sign)一词代替了之前使用的术语“再现”(representation)。他写道:“如此地,一个符号有三项指称:首先,对于解释它的某种思想来说,它是一个符号;其次,对这一思想中它所等同的某个对象而言,它是一个符号;再者,在将它和对象关联起来的某个方面和品质而言,它是一个符号。”[1](5.283)在皮尔斯繁杂而漫长的符号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这一有关符号三元关系论述的正式出现,宣告了符号定义向开放体系的重要转变:无怪乎后世的符号学者为之雀跃。奥斯曼(Carl R.Hausman)认为,这是皮尔斯早期思想中最为明确的对符号过程的解释,它确立了符号学充分发展的基础[2](P66)。这一论述打破了符号是“一物代一物”的传统定义,由此开启了广义符号学的广阔天地。
然而,在符号的开放定义提出后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对于符号的底线是什么,符号是否是人类所独有,国内学界仍然存疑。就连皮尔斯本人的论述似乎也前后矛盾:从本文开篇的引文看来,他似乎认为其解释项产生效果(这种效果可以是行为、经验和感觉到的品质)的再现体就是符号,如此说来,我们可以推论出,生物反应和信号能够被视为基本的符号;但另一方面,皮尔斯又明确说,“符号是一个携带着心灵解释项(mental interpretant)的再现体。也许可能存在一些非符号的再现体,比如,向日葵总是跟着太阳的运动方向转动;凭借这个动作,向日葵在没有别的条件下,完全有能力再次以同样精确的对应方式朝向太阳,并且获得一种再生产的能力可以重复做到这一动作,由此,向日葵就会成为阳光的再现体。”[1](2.274)照此看来,皮尔斯本人似乎并不认为生物反应是符号。然而,当代的生物符号学家们却几乎一致认为,皮尔斯提出的开放体系正是将生物信号纳入到符号范畴的重要理论支撑。皮尔斯的论述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他的符号学思想又是如何为生物符号学提供理论可能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到皮尔斯”,回到他“寻找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方法”[3](P7)的三分式之上,去寻找答案。
一、解释项是否是符号?
三分法是皮尔斯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模式: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他对符号的定义及分类,都是建立在三分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最初的三分项之下可以用这一模式继续进行三分,由此形成一个向下不断分叉扩展的体系。这种开放性,是“任何追寻智慧的科学研究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特征”[4](P49)。本文将紧扣皮尔斯的“解释项”这一概念来进行讨论,因此,笔者在第一部分,将对皮尔斯提出基本解释项三分式的过程进行粗略的梳理。
皮尔斯认为,解释项不仅仅是一种指涉,它更像是符号的效果或者说“效力”(effect),他在此认知之上对解释项进行的分类。就符号过程而言,解释项可以分为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tion)、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tion)和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tion)。皮尔斯是在1902年讨论指示符(index)时,第一次提到“直接解释项”这个概念的:“尽管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肯定是一个指示符,但既然它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单独的(单个的)规约符的对象,那么,这个指示符的非直接解释项(indirect interpretation)就可能是规约符。”[1](2.294)从这段论述可看出,皮尔斯在对解释项进行考查时,注意到了符号引起的“效果”:所谓“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肯定是一个指示符”,即符号主体在对指示符进行解读时,第一步的解释是,这个符号在自身的意义认知体系中指出了什么方向,自己如何对其作出反应。而后续的“非直接解释项”之所以可能是规约符,是因为符号主体已经走到了意义的下一步,对这一指示符可能包含的规约关系进行了理解。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此进行证明。当人们在夜间行车的时候,看到反光的紧急路障标志,第一反应往往是“有物体在那儿,危险!”从而即刻采取避让措施。紧急路障标志在这里首先是作为一个指示符出现的,它的直接解释项是另一个指示符:“这里有个危险的东西!”在相当的速度之下,符号主体(即驾驶者)往往并不能判断这个符号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这个指示符表现的是对象的一种相关质性,即物体的存在。通常是在避让之后,符号主体才意识到,这个反光的图案代表的是一个规约性的紧急路障,他/她此时的理解已经进行到了皮尔斯所说的第二步,即“非直接解释项”。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04年,皮尔斯用“动态解释项”代替了“非直接解释项”。此后,在1905年,他提出了解释项的基础三分式。他写道:“第一,直接解释项;它之所以为解释项,是因为它在有关符号自身的正确理解之中显示出来(revealed);它通常被称作‘符号的意义’;第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动力解释项,它是符号作为符号而真正造成的实际效力(actual effect)。最后,还有一种解释项,我暂时将其命名为最终解释项,它指的是一种方式(manner),而符号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再现来与其对象有关。”[1](4.536)这一三分式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最终解释项”的提出,使得我们可以将对符号的认出、反应和对符号关系的理解相区分,意义过程更为细化。就上文的例子而言,对于夜间的反光紧急路障标志,符号主体的直接解释项是“这里有个东西”,它之于符号主体的意义是“有危险!”它的动态解释项是“我必须即刻避开”,符号主体由此采取了避让措施,这是符号起到的实际效果。而最终解释项则是“原来这是个发光的紧急路障,而路障意味着我需要避让”,这是对符号再现方式、或者说规则的理解,具有规约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皮尔斯曾在1908年时考虑将其称为“规则解释项”(normal interpretation)的原因。
当然,以上三个步骤在实际中可能是几乎同步完成的,无法截然分开;并且,这里所说的“最终解释项”只是就一个完整的意义过程而言,而逻辑上(或者说理论上),最终解释项在无限衍义的过程中可以到达真相本身。但无论如何,从本文所举的例子来看,反光的紧急路障标志这一指示符的直接解释项,即符号主体辨认出“这里有个东西”,它已经如皮尔斯所说的,是一个指示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这是符号主体对符号的即刻感知,是一种对相关质性的感觉,它已经是符号。那么,既然皮尔斯承认了这种作为感觉的、最初级的解释项已经是指示符(他在1908年曾经把“直接解释项”称为“感觉解释项”felt interpretation),他又为什么会认为解释项不一定是符号,因为它“仅仅是感觉的一种质”?如果说人类对符号的感觉和认出可以是符号,为什么对于其他生命体则不然?诚然,皮尔斯在世时,他的理论著作未能得到出版,因此手稿中有不少混乱之处,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矛盾的存在,主要在于另一个和解释项相关的概念的转变历程,即皮尔斯对符号过程的考察,从“心灵”(mind)转向了“准心灵”(quasimind)。
二、从“心灵”到“准心灵”:皮尔斯符号理论的进一步敞开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心灵”与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讨论的重点之一。他认为,符号必然和心灵相关,和符号的接收者相关:“符号是在心灵上被某种东西所代替的某种东西。”[5](1873:380)由此可以看到,皮尔斯并不是绝对反对“符号是一物代一物”的传统符号学思想,只不过他在此基础上进了一步,将解释符号意义的权利交到了符号的接收者一方。不仅如此,“心灵”的存在是符号得以存在的前提之一。皮尔斯在1873年讨论符号的存在条件时指出,除了品格(character)和与对象的因果关系之外,符号要存在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符号存在的第三个条件是,符号自身必须可以与心灵对话。符号不仅仅与它的对象存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非常必要,因为它可以把人的思想也带入到与对象的关系之中,也即让思想知道对象之所在。换句话说,符号不仅必然与它的对象存在联系,而且也必须让思想知道它们之间存在这种关系。符号可以直接与思想对话,或者通过把其翻译为其他符号的方式与思想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符号必须具备可解释的能力。……毫无疑问,心灵的本质(nature of mind)就是这些普遍规律的根源。”[5](1873:380)
在这里,皮尔斯明确地把心灵和人类思想相等同,也就是说,只有人类所认知、解释和使用的符号,才是符号:符号是某一对象在人类思想中的再现,这种再现是否忠实,与对象本身是否对应,并不是符号学所关心的问题;它是如何与对象相关并产生意义,才是符号学的重要议题。在皮尔斯看来,心灵,即人的思维,是对象能够被作为符号来认知的基本前提:“一个符号之所能成为符号,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符号必须被心灵认作是一个符号,因为只有符号才能使心灵能够进行思考;如果某物对任何心灵来说都不是符号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符号。……符号使得心灵产生了某种观念——一个有关所指称之事物的符号的观念;而观念本身就是符号,因为观念是一个对象,它代替着另一个对象。”[6](P10)照此而言,思想本身就是符号,符号是人类所有意义活动的载体,作为再现体的符号是和人类思维密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皮尔斯也指出,解释项除了是思想之外,还可以只是行为或经验,或者是“感觉到的一种质”,它甚至可以和人类活动无关。如上文所说,皮尔斯认为存在着“非符号的再现体”,比如,由于向日葵茎顶的向光生长性,它可以成为阳光的再现体。皮尔斯认为这种再现体不是符号,因为这一时期(1902年)的皮尔斯还把符号活动牢牢地限定在人类的范畴中,四年之后,也就是1906年,皮尔斯才写出一段被当今符号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关于“准心灵”的论述。
李斯卡(James Jakob Liszka)是如此评价皮尔斯关于“准心灵”的看法的:“解释项是与皮尔斯所谓的‘准心灵’结合在一起的,而并非是与那种完全意义上的心灵捆绑在一起;并且显然地,这种准心灵并不仅仅局限在人脑皮质(human cortex)之上。生性(natural disposition)界定了符号过程的这种三元特性。动物的交流及其对符号的运用是这类符号过程的典型,尽管这类符号过程也存在于人类符号过程的某些层面中。这种过程所产生的符号不是纯符号(genuine),而是广义上的符号。在这里,符号的解释并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变化的;它会发展,并且会展示出它校正(之后的结果)。尽管如此,解释还是具有它自己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存在于其自然且稳固的习性中,而不是那种有意的自我控制(selfcontrol)之中。正如皮尔斯所述:‘思想并非必然与一个大脑相连。它出现在蜜蜂的活动之中,出现在结晶体的活动之中,并且贯穿在整个纯粹的物理世界之中……’”[6](P165)
很显然,从李斯卡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皮尔斯的“准心灵”概念是和习性(habit)有关,也就是说,“准心灵”其实是皮尔斯在发展他的实验主义思想时,对符号学理论作出的修正。接下来,这段著名的论述指出:“思想不仅存在于有机世界中,还在有机世界中得以发展。然而,正如没有例证就没有一般法则一样,没有符号,也就也没有思想。毫无疑问,我们要赋予‘符号’一个相当宽泛的意义,但不能宽泛到超越它的定义。承认符号必须和准心灵相关,我们就可能进一步宣称,没有孤立的符号。而且,符号要求有两个准心灵,一个准发送者(quasi-utter)和一个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尽管在符号本身中这两者是一体(即是一个心灵)的,它们仍然是有区别的。”[1](4.551)皮尔斯的这段文字对于生物符号学意义重大,它打开了将符号主体从人到其他生物扩展的可能。首先,皮尔斯不再认为“思想”是人类心灵所独有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其实是符号主体经历的意义过程,即对对象的感受和认出,以及随后的比较、理解:这是生命体的符号能力逐步积累和发展的阶段,比如,库尔(Kalevi Kull)就指出,从感受到比较、再到理解,其实是植物、动物和人类符号能力的对应发展[7](P8-27)。而皮尔斯明确提出,“思想”是在有机世界中存在和发展的,这就为符号边界的重新界定确立了一个大致的范畴。这个范畴,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科学性的:由此可见,皮尔斯的思想的确超越了当时的理论界整整百年有余。其次,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需要两个“准心灵”,即一个“准发送者”和一个“准解释者”,这就为当代符号学家对生物交流、尤其是种际交流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塔尔图的符号学家就研究过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试图在不同的“准发送者”和“准解释者”中寻找生物语言翻译的规律[8](P17-26)。符号在交流中产生,在作为符号主体的不同生物(即“准心灵”)之间产生,这样的观点,也是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得以确立的基石。
李斯卡认为解释项和“准心灵”相关,也就是说,解释项可以是由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体得出的,是作为符号主体的生命体的理解、行为或感受,与习性紧密相联。“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习性可能是情绪的、行为的或认知的。对动物而言,树枝断裂的声音可能是一个让它们警惕或害怕的信号,这样的信号开启了它们的逃跑模式。”[9](P18)如此说来,动物对这一信号的感知、判断(警示或危险),以及随后的逃跑行为,就是树枝断裂声这个信号的解释项;而后文会说到,信号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动物意识到“此处有危险而需要逃跑”,这个解释项和上文提到的夜间行车的司机对反光路障的反应相似(此处危险需要避开),是一个之于“准心灵”的指示符,本文第一部分的疑问就可以得到回答:解释项确实是符号。并且,本文开篇提到的皮尔斯论述中的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当皮尔斯用“准心灵”代替“心灵”,对符号过程进行解释时,他其实已经开始考虑给符号一个更宽广的范畴,开启了将生物信号纳入到符号中的可能。这种可能,在当今的符号学界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由此大大拓展了符号的底线。
三、符号的底线:生物信号
生物信号是最低限度的符号,对此,国内符号学界已有论述。赵毅衡就指出,“信号是一种特殊的不完整符号:它不需要接受者的解释努力。信号的特点是:(1)它是一个由符号载体的意义发送。(2)它不要求解释,却要求接收者的行动反应。”[10](P53)而他对符号的定义是,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10](P27)。既然生物信号过程中有符号主体对其进行接收和感知,且它本身携带着意义,那么,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符号。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指出,赵毅衡文中所说的,信号不要求解释,是指生物主体在接收这一符号的过程中,不需要试推式的解释,而并不是说信号没有解释项。既然解释项可以是情绪、行为、感受和理解,那么,“接收者的行动反应”就是符号主体对这种特殊符号的解释项,符号的三元关系在这里依然成立。赵毅衡的符号定义是宽泛式的,它可以将信号包括在其中,应当说,这是国内符号学界提出的最能和国际符号学前沿相“对接”的一个定义。
当然,对这种“广义符号”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声:譬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坚持把符号学研究限定在人类文化的范畴之内。有趣的是,卡西尔的手书整理稿题目为《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这里的“Symbol”一词可用于表示仅仅是人类才能使用的规约性符号,而并非更为广义的“Sign”。如果符号学只能讨论规约符,将指示符、像似符都排除在外,那么,它无疑就自我窄化、自我切割式地和符号过程的起源完全割裂,并且这种割裂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言。
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对信号的符号性进行过讨论,他们认为,信号的解释项是一种“辨别性解释项”(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也就是生命体对信号进行的辨认反应。“信号是符号性程度最低的符号……从这点看,‘信号’暗示某种不同于符号的东西;‘信号’似可作为表示最低程度的符号性的更为恰当的术语。从信号性来说,信号处于解释的最底层——辨别层。在以前的著作中,我们曾提议,与信号或信号性相关的解释项可以叫作‘辨别性解释项’。在所有符号中,辨别性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呈现的是单一意义关系;这种关系预先由符码决定,类似于信号中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的关系。”[11](P2)
由于信号的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是预先决定的符码关系,因此,就如赵毅衡所说,它需要的并非符号主体的解释努力,而是需要其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亦或说效果,就是信号的辨别性解释项,而其他更高层次的符号的解释项,则被庞齐奥称为“应答理解性解释项”(inter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sion)。如此,生物信号和更为高级的语言符号,都成为了渐次展开的符号网络中相互联接的部分。
在由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所主编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中,这种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认:“符号首先是一个解释项,一种反应,开始于从它之中,某种东西被当作一个符号并且成为其被解释者,而且进一步地,能够生成其他符号。符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声部和单声部。信号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单声部符号,或者更好地,定位成一个具有最低程度的多声部的符号。”[12](P404)信号被认为是符号,而且,作为反应和经验的解释项都被视为符号,这进一步地解决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即解释项一定是符号,符号主体可以是人之外的生命体。
事实上,晚年的皮尔斯已经开始寻找生物物理学中具有决定习性的细胞质机制,在塔尔图的生物符号学家看来,这意味着皮尔斯想要为生物的习性建立符号学模型。卡莱维·库尔就指出:“我建议大家读一读皮尔斯的《人的透彻本质》一文……我们从本文可以看到:第一,皮尔斯倾向于相信,细胞质的、特别的分子构造决定着符号过程。”[8](P64)尽管皮尔斯最终未能成功地建立这一模型,但他“将符号过程视为过程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这种观点使他的方法适用于生物符号学,并具有相当的生产力。”[8](P62)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之于生物符号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可以让生物符号学家进行重新的阐释和发展。
如皮尔斯所说,符号意义过程确实是在有机界、即生命界内发展的,但这种发展并不是跳跃式,而是渐进式的。事实上,对于猿人是否已经具有初步的语言符号能力,生物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语言符号显然是最典型的规约符。因此,符号发展的阶段其实是渐变式的光谱,而非界限鲜明的色块。这并不意味着符号学不能对人类的符号行为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和文化艺术符号的考察,至今是符号学体系中最为丰富和有趣的部分,但由此而拒绝将其他生命体视为符号主体,拒绝承认生物信号是符号的底线,是一种狭隘而过时的观点。
符号学界能够“重新发现”皮尔斯,生物符号学的奠基者西比奥克(T.A.Sebeok)功不可没,而哈佛大学整理出版的、长达八卷本、厚达近三千页的《皮尔斯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ierce),就是由西比奥克的得意门生、美国符号学家迪利(John Deely)撰写的编者导言。西比奥克将皮尔斯提出的“符号过程”(semiosis)和生命过程相比较,认为符号科学(sign science)和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可以相互融合[13](PP.151-58):符号过程与生命过程的一致性,已经是生物符号学的基本观点。本文对皮尔斯符号思想在解释想和“准心灵”问题上的探索,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皮尔斯丰繁浩荡的理论系统中,还有更多的符号学遗产有待我们发掘,在进一步建立符号学体系、尤其是生物符号学体系的过程中,这些符号学遗产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1]PEIRCE C S.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1-8[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
[2]HAUSMAN C R,CHARLES S.Peirce'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2014,(9).
[4]PIETARINEN A V,DAI Wei-wei,ZHAO Xing-zhi.Extensions of Charles S.Peirce:An Interview with Anti-Veikko Pietarinen[J].符号与传媒,2014,(9).
[5]ROBIN R S ed.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Peirce[C].Massachusetts: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67.
[6]查尔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C].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7]KULL K.Vegetative,Animal,and Cultural Semiosis:The semiotic threshold zones[J].Cognitive Semiotics,2009,(4).
[8]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C].彭佳,汤黎,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9]LISZKA J J.Some Reflections on Peirce’s Semiotics: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Anniversary of His Death[J].符号与传媒,2014,(9).
[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PETRILLI S,PONZIO A.Semiotics Unbounded:Interpretive Routes in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M].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2005.
[12]保罗·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M].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3]SEBEOK T A.A Sign Is Just A Sign[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