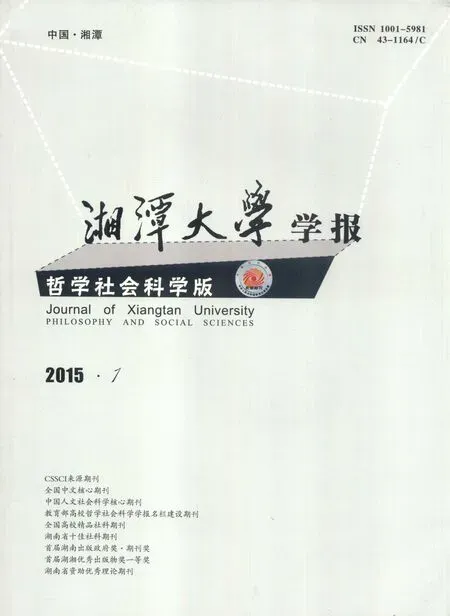从他者到本位:中西生态文学伦理的现代转型*
2015-02-21龙其林
龙其林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从他者到本位:中西生态文学伦理的现代转型*
龙其林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随着生态危机的降临和生态意识的勃兴,生态伦理逐渐为更多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并成为中西生态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生态伦理的迅速发展相比较,中国的生态伦理观念进展较为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制约与影响。思考中西生态文学中的伦理叙事,比单纯地观察人类之于自然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单一伦理维度具有更大的发掘空间,也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伦理体验。当前仍有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偏重于人间的伦理道德规范,缺乏一种超越世俗伦理的意识和探索未知文学领域的精神。
生态文学;本位;文学伦理;发展史
一
随着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和世界范围内生态意识的勃兴,生态伦理成为环境保护的理论依据和生态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西生态文学对于伦理叙事的重视已在众多作品中得到了证明,但是关于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问题迄今并非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恰恰相反,生态文学中的伦理叙事一直是个富于争议的话题。
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萌生于18世纪后期,历经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演绎和发展,于20世纪初叶至中期得以确立,出现了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学说、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等影响广泛的生态理念。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生态伦理学说形成了两大流派,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都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在两大流派之外,还衍生出了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学说。在这些生态伦理学说中,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最具影响。它们分别以人类的共同利益、自然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立场,可谓泾渭分明。其差别在于,“在一般方法上,人类中心论总是维护传统伦理的‘公理’即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道德只存在人与人之间,因而只对传统伦理学作延伸和拓展,自然中心论则力图修正原有的‘理论硬核’,突破‘公理’,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和研究范式的转换”[1]3。
自然中心论颠覆了传统伦理以人类为中心的惯性,凸显了自然作为伦理主体的诉求,认为自然拥有不依赖人类存在的固有价值,人类应对自然承担一定的义务。但自然中心论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例如过于强调返回自然,刻意渲染荒野意识,由此导致个人主体性的模糊与丧失。在自然中心论的这些缺陷中,最招致非议的或许还是其中涉及的生态伦理。自然中心论以自然价值和权利为预设,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否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而真正实现对自然中心价值和权利的体认及实践?在批评者看来,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不要求人类为了保持环境的完整而牺牲人类的利益和经济发展。甚至有人更为尖锐地提出:病毒也有生存权,艾滋病毒的生命也值得尊重,那么人们是否也会为了保持艾滋病毒的生存环境——人体——而牺牲自己的生存权?生态作家与学者们倡导敬畏生命而拒绝肉食,主张以素食代替。但时常令他们陷入窘境的是,反对者总是提出一个极其尖刻的问题:既然生命需要敬畏,那么植物也有生命和知觉,素食主义者为何不敬畏植物的生命呢?
虽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并不普遍,但却从根本上使人类处于生态伦理上的困境。正是由于自然中心论或生物中心论、动物解放权利论等学说存在着类似的伦理缺陷和实践盲区,很容易遭到人类中心主义论的理论狙击。在反对者看来,伦理道德只局限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非人类的动植物也可以成为人类伦理道德的覆盖范畴,但必须符合人类的利益和情感。基于此,人类中心主义者也认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性,但坚持从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出发,而非没有限度地遗弃人类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自然环境的开发程度,是与社会物质文明的进程大致同步的。只有当人类的基本生存得到了满足之后,生态保护才成为可能;否则,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物质极度匮乏、食不果腹的阶段,这时谈论生态保护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无权要求尚处于生存奋斗中的人们为了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而放弃生存的努力。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类本来就归属于自然,需要向自然索取生存的物质资料。作为对自然中心主义论忽视人类自身利益诉求的反拨,人类中心主义论则提出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具有一定的限度:“环保不代表绝对的正义,环保是有底线的,越过了这个底线,环保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这个底线就是:不能脱离现实,要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惟有这样,环保才是现实的,也才是道德的。环保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坚持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绿色环保主义者所努力达到的目标和为之奋斗的原则理念。”[2]60
与西方生态伦理的不断发展相比较,中国的生态伦理观念进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制约与影响。依据通常的划分,我们可以将西方文化称为宗教文化,而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伦理文化。中国是一个早熟的、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而且在历史上建构了一系列的中国伦理精神。中国的伦理思想由人伦、人道和人性三个部分组成,但其着眼点均在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由于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宗教精神的牵引,中国传统文化也缺少一种强烈的向前追求的欲望……专注于现世道德修养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协调的现实精神,既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该为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承担主要的责任。”[3]12中国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上,“中国人性论是在人兽之分的意义上定义人性,把人性看成是人之异于、贵于禽兽者,把道德性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4]226,因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被排除在伦理道德的观照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伦理与政治长期纠葛不清,“伦理政治化了,政治也伦理化了。一方面,政治的等级尊卑从血缘亲疏中引申出来,具有神圣的、天经地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政治的道德价值与伦理机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成为‘伦理政治’的基础,因此,传统伦理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某种准宗教的作用。”[4]225传统伦理观念对于社会的辐射,为中国强韧的家国一体社会结构提供了伦理支撑,因而传统伦理观念至今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注重人伦、人道和人性的伦理,一方面固然维系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的伦理观念具有超乎寻常的顽固,不利于新的伦理观念的引入与进化。在这种情形下,生态伦理虽然也得到了中国学人的有意识倡导,但就整个伦理文化氛围而言无疑仍是传统的人伦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中国的伦理观念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无论是反对虐待动物草案的提出还是人们对于加强生态保护的认识,都反映了生态危机对于中国人伦理观念转变强有力的影响。
生态伦理转变的目的,乃在于切实有效地应对威胁全球的生态危机,使生态系统的规律内化为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信条。阿尔贝特·施韦泽毕生都在为人类伦理朝生态方向进化而努力,在他看来人们应该从有限的伦理向无限的、生态的伦理发展,创立一种凸显人与自然统一的现代新型伦理。利奥波德则倡导没有疆界的大地伦理,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能将过去作为自己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自然视为大地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这个共同体及成员都享有其尊严。
从中西生态伦理观念的转变来看,他们的设想正在缓慢地为人们所认可、接受。
生态保护中的伦理矛盾和悖论,体现了不同伦理观念的差异和生态伦理的应用困境。伦理观念一方面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集中表现,但它同时又具有独立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之外的恒久价值。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对于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和普及是有着不同效用的。我们应当看到,由于伦理观念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并非总是一致,社会与现实生活对于伦理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双重性,伦理观念一方面顺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功利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着超越这些功利内容的诉求。这些超越功利的方面,正是作家值得关注和用力之处。人类或许永远无法真正地、绝对地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立场,而只能朝着自然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无限努力,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生态本位对于伦理道德的影响。文学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的生态危机和生态伦理,而且还应该朝着人类目前无法完全解决的伦理困惑、精神症结持续用力。
相较于西方作家而言,中国作家习惯于以传统伦理、日常道德标准进入作品,在超越现实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方面常常心怀畏惧。在面对生态伦理这一全新的书写领域时,中国作家们的伦理局限和思想狭隘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表现人类对于环境的保护时,总是努力与既有的、世俗的伦理观念趋同。在一些对于生态理论和环境伦理有着较为自觉的学习、认识的学者和作家那里,现实人间伦理的影子依然紧随其后。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由于过于贴近现实伦理,更由于缺乏伦理思想观念的生态激活,不少生态文学作品在审视生态伦理问题时往往秉持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准则,从而使原本无限丰富的伦理境遇和精神冲突简单化、机械化。“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伦理叙事和话语道德。”[5]4
与具有超前意识的生态伦理相比,日常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道德观念往往更为保守。当生态伦理常常为普通民众所漠视时,生态文学应当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普遍认同的生态伦理在文学世界里获得巨大的表现空间。不难发现,人间的伦理道德也即世俗的伦理道德具有超强的稳固性,具有较为明晰、具体的指向,但也往往导致自身的滞后性和保守性。而文学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则超出了世俗的、现实的界限,它并不局限于伦理的现实指向和具体目标,而在于探索伦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若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世俗道德即现世道德作为一个庞大且积淀深厚的体系,必然面临更新或增补其缺陷的过程,生态伦理即是其中一个亟需更新发展的部分。这种更新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换言之,生态伦理与现世伦理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从长远来看二者面临着整合与发展的必然性;但就短时间而言,生态伦理较之现世、世俗伦理无疑显得更为激进,其与现世伦理道德无法重合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文学关注和表现的绝佳空间。
二
纵观中西生态文学不难发现,尽管出现了一些超越现实伦理、聚焦生态伦理叙事的佳作,但也有相当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偏重于人间的伦理道德规范,而缺乏一种超越世俗伦理的意识和探索未知文学领域的精神。思考生态文学中的伦理叙事,比单纯地观察人类之于自然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单一伦理维度具有更大的发掘空间,也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伦理深处的回音。但是,不少中西生态文学却拘囿于人伦、人道和人性的框架中,习惯性地褒扬环保人士、批判生态破坏者,并对二者的争斗有着极强的兴趣。充满丰富开拓空间和语意符码的生态伦理,在一些作家笔下被简化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被定型为一部分人与大多数人的斗争,生态伦理意义的开掘蜕变为法律意义、社会意义和个人品性的博弈,人类伦理可能遭遇的困境、质疑被轻易地规避了。因此,为数众多的中西生态文学的伦理指向,往往停留在国家、社会的层面,潴留于公正正义、英雄主义的人伦境界,而无法进入艺术化的生态书写自由,作家无法真正深入到生态环境问题的内核——人的伦理世界的矛盾与较量之中。
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被誉为是前苏联文学史上第一部鸿篇巨制的生态文学作品,出版之后曾获得了1957年度的列宁文学奖。评论家十分看重这部作品,认为“它标志着以关爱大自然和保护大自然为特色的普里什文文学派经过数十年的沉寂之后再一次崛起”,“也标志着苏联生态小说和生态哲学第一次获得了苏联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官方的正式认同。”[6]102但若探究作品中的生态伦理叙事,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因为过于贴近现实伦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了作品可能具有的伦理深度。小说主要围绕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茨基两位林学家关于如何对待俄罗斯森林问题的尖锐冲突进行展开,并穿插了许多往事,将前苏联建国以来对于森林生态的思想分歧展现了出来。在作品中,作家着力刻画了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茨基对于俄罗斯森林的不同见解:维赫罗夫从小熟悉森林,对于森林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林务官,维赫罗夫厉声呼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渐渐短缺的俄罗斯森林资源,即便在工业化建设的紧张阶段仍然冒着风险提出了削减木材采伐量,坚持宣传森林生态自然的保护公式。由于招致各方面的打击,维赫罗夫的家庭分崩离析,他却不改初衷,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与维赫罗夫针锋相对的是格拉齐安茨基,他原本是一个混迹于学术圈的庸俗市民,不顾森林资源日渐萎缩的现状,反而极力鼓吹无限度地砍伐森林,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在这部小说中,维赫罗夫和格拉齐安茨基无疑是作者塑造的两个生态伦理角色的典型,一个坚持生态伦理,另一个则扮演着反生态伦理的角色。但是问题是,不同伦理观念之间关于生态问题的争执被简化为正义与邪恶、正直与钻营的两极模式。小说围绕着两位林学家的矛盾冲突展开叙述,这种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的较量贯穿小说首尾,却始终无法深入到生态伦理层面的内心战栗与不安之中,而是将笔墨放在不同路线的斗争的表象上。“这两种思想的冲突更多地体现了苏联公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诠释,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6]112,这仍然徘徊于现实伦理的层面。即便是维赫罗夫在当时提出了森林生态文化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将自然生态保护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也并未超脱政治、现实的维度。生态文学的伦理叙事应该是对于人类伦理的审视与超越,是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精神发现,而不是对于政治冲突、世俗道德的生态演绎。生态文学的伦理叙事应该超越狭隘的现实伦理规范,朝着伦理叙事中的生态情境与精神细节不断用力。
在生态伦理思想尚未普及的20世纪中叶,作家们显然无法自觉地意识到伦理的生态维度具有深入探究的可能和必要。这种情况在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也留下了痕迹。这部小说以母狼阿克巴拉及其家族的毁灭性遭遇为线索,讲述了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任意破坏及其给予人类带来的后果。母狼阿克巴拉的几窝狼崽的毁灭都与人类的肆意破坏相关,或是围猎,或是火燹、端窝。出于丧子的悲痛,阿克巴拉最终对人类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并叼走了波士顿的爱子。波士顿追赶母狼时,在用猎枪打死阿克巴拉的同时也误杀了孩子。这原本是一个充满巨大生态伦理阐释空间的文本,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人类行为的伦理规范、生态失范后的人类伦理境遇等都大有刻画的空间。但作者并未朝着这些方向努力,而是回到了另外两种思考路径:一种是阿弗季对于宗教之于人心拯救的思考,一种是人类开发自然对于母狼家族的巨大冲击。应该承认的是,这部小说仍然为生态伦理叙事保留了一份空间:母狼阿克巴拉对于孩子的疼爱以及失去孩子之后于深夜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哀嚎,都触及到了动物伦理这个层面。这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胡作非为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从而向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发出厉声的控诉。但问题是,作家仍然坚持从现实的、世俗的生活而非精神的冲突、伦理的困惑、内心的战栗入手,作品始终无法洞悉人类伦理的局限与可能。因此,这部作品固然能够写出阿弗季的“神会”这样具有精神拷问的深度,却无法对生态伦理进行深入的开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也很大程度地存在着重现实冲突与伦理规范、轻生态伦理与灵魂审问的问题。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曾有过一针见血的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的传统重人情、重义气,但这种看重义气的传统往往忽视或逾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而西方文明的正义精神强调是非善恶的分辨,强调社会的秩序和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质,这是我们所应大力借鉴的。”[7]4在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司马炎的《麻雀梦》、姜戎的《狼图腾》、刘心武的《青箬溪之恋》等作品中,作家虽然也批判了破坏自然生态、屠杀动物、匮乏生态责任的现象,但是作家们依然没有意识到生态伦理叙事具有的灵魂挣扎,而是转向于政治批判、道德斥责的末梢。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描写了人类由了解、开发可可西里到大肆猎杀野生动物、破坏自然生态的过程。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迫捕食野生动物,无意中掀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小说开始便鲜明地刻画了“我”、王勇刚、李石柱、石技术员等不同人物的性格,王勇刚的莽撞、暴戾和自私,李石柱的憨厚与正直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些老兵之后纷纷退伍,其中王勇刚借助州经委的名义成立了开发公司,勾结境内外走私团伙疯狂猎杀珍稀动物牟取暴利。李石柱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甘愿在保护站默默工作,最后在阻止盗猎团伙时英勇牺牲。作品着重考察的是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搏斗,李石柱和王勇刚分别代表了“善”、“恶”两种势力,而且这种善恶的本性早在小说开头人物的性格刻画中已经定型。也就是说,善良与邪恶都已经注定,围绕着可可西里发生的盗猎与保护的斗争不过是演绎着两种不同的人物斗争。可可西里的自然条件和野生动物在作者眼中更多地扮演的是“资源”的角色,动物们的生命体验、盗猎者的伦理压力、保护者的伦理良知都为激烈的斗争所抹杀。即便如李石柱这般为阻止盗猎团伙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也只是停留在语言和行动的层次,作品无法深入到其内心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遑论人类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冲突、整合。在李石柱牺牲前,他曾说道:“我早就考虑过了,可可西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需要我们用生命和鲜血来唤醒政府和社会保卫可可西里的意识。要是我真的被盗猎分子打死了,情况反映到省上,反映到中央,让全中国全世界人都知道,可可西里或许就有救了!”[8]6-54在这洋溢着英雄主义豪情的壮语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李石柱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口号,却无法看到其内心伦理世界的颤音,也就无法理解其长年坚守在动物保护站的精神动力与生态思想、伦理观念的变迁。而这也恰恰是这部小说最致命的弱点,重事而轻人,重斗争而轻伦理,小说固然能够以题材、情节吸引读者,却缺乏足够的伦理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司马炎的《麻雀梦》中的“我”梦见自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麻雀,亲历极“左”时期麻雀被当作害虫为人们所消灭的生物悲剧。作为麻雀的“我”,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发达的思维、人类的知识,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就作品体现的伦理叙事而言,虽然也涉及保护麻雀、爱惜生命的内容,但更主要的是对极“左”年代疯狂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反思,其立意并不在生态伦理本身。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了富于政治鼓动力的句子,如“宣传员作报告,给算了一笔细账:全国大体有多少只麻雀,每只雀一年约吃掉多少粮食,全年被麻雀吃掉的粮总共有多少?我的天,那可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为了把农业搞上去,不灭掉麻雀这个大祸害行吗?”[9]264因此这部小说虽然也以动物保护为题材,但在伦理层面仍然是将动物视为人类的“益鸟”,而不是从动物的生命、尊严和伦理入手。因此,在文本中我们看不到现实伦理与生态伦理的冲突,无法体会到消灭麻雀这一突然行动在人的内心可能引发的悸动、疑惑,因而也就无法体验到政治化运动对于动物生命的践踏所引起的悲剧意味。
生态文学的伦理叙事,既是对于生态问题的观察、反思,又是对于伦理问题的深究与探讨。因此,生态文学在涉及伦理问题时不应仅局限于现实伦理,更不应以现实伦理规范小说伦理叙事,从而使具有多层次阐释的生态伦理问题浅层化。生态书写的一个更高的境界便在于超越现实伦理和具体道德的束缚,而以一种穿越性的视野审视人类的情感和伦理世界,聆听最敏感的内心颤音。在施韦泽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没有限度、直抵人心的伦理观念,它不仅说明了生态伦理的根本精神和原则,而且超越具象、建构起了以爱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对于生态伦理由于扩展其施行范围至一切自然生命和事物而可能导致的理论与现实困境,伦理学家和作家显然是有着自己的觉察的。若非如此,我们的伦理学仍然将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立场上,而对非人类的生命与事物则视而不见。在施韦泽看来,“在我们生存的每一瞬间都被意识到的基本事实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我的生命意志的神秘在于,我感受到有必要,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我之外的所有生命意志。善的本质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从而,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我给予任何生物的所有善意,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帮助,即使它有益于得以保存和促进其生存的帮助。”[10]92施韦泽的伦理学综合了人与自然的整体伦理诉求,以一种道德信念的方式提出了伦理的本体论原则,抛弃了现实伦理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模糊认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动植物和其他存在物之于自然整体的伦理关系。伦理学试图停留在人伦范畴,而文学恰恰具备了伦理冒险和精神探索的性质,它在被现实束缚得紧张的地方切入,向我们展示了文学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先锋性。“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像。”[5]4推崇生态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扩展了人类的道德责任和活动的领域,不仅强化了人类的自然道德意识,而且强调生态整体系统内的平衡原则和自我的伦理完善。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本位,促使人们将思考的触觉提升至世俗伦理道德之上,站在全球整体生态的角度思考生态危机与人类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在对更高生态文化理想的追求中实现人类伦理道德进步和自然生态的重趋和谐,创造出有益于自然整体生态的文化精神和伦理成果。
三
西方生态文学受惠于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的学说,本着保存生命、促进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的使命而努力,同时又不讳言和回避恶的存在,在生命的毁灭和伤害中朝着生态伦理的绝对境界驶近。这种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成为生态文学超越世俗伦理、剥离现实道德的助推器,帮助作家形成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伦理叙事。
在法利·莫厄特的《被捕杀的困鲸》中,我们看到了围绕一头鲸鱼而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伦理观念之间的交锋,它不是呼应现实伦理规范,而是从现实的伦理处境中寻找到了新型生态伦理的发生。当长须鲸被困在小海湾时,爱好打猎的人们和以莫厄特为首的生态支持者们各自采取行动,其目标都在鲸鱼上。但作者并没有将猎鲸与护鲸的斗争情节化,而是揭示了不同人群的内心伦理观念及其细微变化:捕鲸者为了猎杀困鲸,驾船冲撞、枪支捕杀、汽笛骚扰等伎俩无所不用,他们在鲸鱼的痛苦和死亡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变态的满足:男人和男孩们手举刀斧大声嚎叫,跳进没膝的浅水,蜂拥而至地屠杀困鲸,“活像传说中的报丧妖精。”[11]57人们渴望在对鲸鱼的大屠杀中插上一手,却无人顾及血从鲸鱼伤口中喷涌而出,仿佛落雨一般溅在人们头上。“人们扬起面孔,抹一把脸上的血,大笑着,嚎叫着,为参加了夺取生命的罪行而欣喜若狂。”[11]57人性的嗜杀弱点与伦理道德的盲点,在这一群体屠杀的场景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但是作者又不局限于对于参与屠杀人们的简单批判,而是从伦理角度写到了他们对于违背自然生态行为的良知谴责和内心不安。当“我”向人们说明这是条雌鲸,或许怀了孕,这么欺负它太残忍,太野蛮,太卑鄙了。在“我”的控诉下,人们突然离去。当时人们仿佛谁都没有交谈,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还故意躲开“我”的目光。“我”终于体会到,自己的言行刺激了人们心底的生命意识和道德观念,他们对于自己的罪过感到羞愧。“事后,许多人为当时的情景感到可耻。除了直接射击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无意加害那条鲸。人们看到射击场面只是觉得好奇,后来,许多人觉得难过。他们很难描绘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那天都感到心烦意乱……”[11]102作家从生态伦理视野切入,而不是将人类伦理完全定型,从而写出了一幅屠杀发生前后人们内心的伦理触动和生态原罪意识,使作品具有了拷问人性和反思人类伦理的双重功效。
人们在谈到生态文学时,习惯简单地认为这是由“文学”加“生态”组合而成的样式,或者认为以生态理论来观照文学创作,而忽视了生态文学所应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伦理意蕴。生态文学固然应当表现自然生态,反思危机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放弃了对于伦理叙事的探究。生态环境的现实也许无比严峻,现实伦理道德的疆域仍然关隘重重,但是生态文学的精神触角并不应由此而受到限制,相反它更应该凸显自己的精神窥探力和想象超前性,敏锐地发现冷漠现实表象下的精神战栗。因为从根本上而言,文学本身即是一种审美的文化形态,丧失精神的超越性,生态文学便走入了画地为牢的窘境。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叙事,一方面以生态的自觉性反映生态问题,反思环境危机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则遵循文学伦理叙事的基本规律:“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嘘气——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12]4文学创作虽然要来源于生活,但同时更需要超越于具体的现实的生活,转而进行伦理道德、精神价值的开拓,为人们提供多层面的、富含精神价值的阐释空间和艺术积淀,从而为人们重新认识、发现世界提供思想文化养料。生态文学对于伦理叙事的聚焦,正在逐渐地突破文学创作与世俗伦理之间的隐性关联,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叙事,并通过优秀作品向人们昭示生态文学可能达到的伦理深度和精神锋芒。只有坚持生态伦理叙事的方向,生态文学才能超越现世观念、世俗伦理和狭隘视野的束缚,真正开掘文学叙事的多样和深度,走向生态伦理叙事的新境界。
生态问题从其社会根源上看其实是人性、人格的问题。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最大幅度地张扬了人类意志之后这种环境问题愈加严重。扭转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改变人类所习惯的以人类自己作为中心来看待生命、自然和世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复活‘大地‘观念’,树立‘大地伦理’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性建构和生成的又一次根本性转折和重大飞跃。”[13]332只有真正实现由人类中心主义向自然生态主义的转变,将自然视为它物、肆无忌惮对其进行掠夺的生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对于习惯了唯我独尊的人类来说,要让人类平等地看待其他非人类生命和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过程必然是曲折艰难而且惊心动魄的。然而,也只有经历过这次痛苦的蜕变,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主义观念才能落到实处。
[1]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2]海斯.环保主义的“底线” [J].绿叶, 2006(1).
[3]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4]张岱年,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谢有顺.中国小说的伦理叙事[M]//此时的事物.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6]谢南斗.苏联文学生态环境主题 [M].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唐凯麟.序 [M]//唐凯麟, 舒远招, 向玉乔, 聂文军.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杜光辉.哦,我的可可西里 [J].小说界, 2001(1).
[9]司马言.麻雀梦[M]//张力军,主编.碧蓝绿文丛第1辑小说卷·放生.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10][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 [M].汉斯瓦尔特贝尔,编.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11][加]法拉·莫厄特.被捕杀的困鲸 [M].贾文渊,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8.
[1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13]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万莲姣
From the Otherness to Its Own Departmen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y
LONG Qi-lin
(CenterfortheStudyofLiteraryThought,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006,China;DepartmentofChines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ecological ethics i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ogical literature which absorbs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to accept. Compar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logical ethics,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ecological ethics is slow which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constraints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Thinking about the ethics of narrativ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ogical literature is better to arouse people's emotions, ethical experience than the single ethical dimens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nimal protection, which has more space to be explored. There are still many ecological literature emphasis on the human code of ethics, lack of awareness and explore the unknown spirit of literature beyond secular ethics.
ecological literature; based; literary ethic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2014-07-24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文学博士(后),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3FZW051);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广州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博士学术团队项目“生态灾害与中国当代文学书写”(201404XSTD)
I0-03;I0-02
A
1001-5981(2015)01-00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