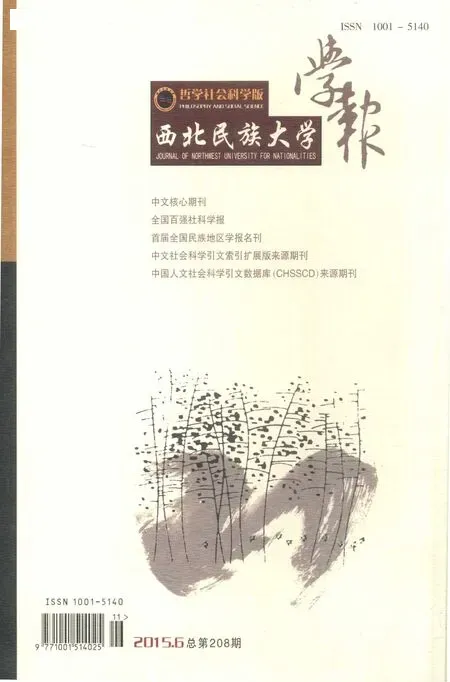岷州茶马司建立原因探微
2015-02-20闵文义
闵文义,王 丹
(1.北方民族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基地,宁夏 银川750021;2.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茶马互市主要是指我国北部与西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它产生于唐代,盛行于两宋、明、清,长达千余年。”[1]明代更是吸取宋、元经验,始终坚持以和平的“茶马贸易”为主的经济手段对藏区实行羁縻统治,“以茶驭番”的政策指导思想贯穿明朝始终,因而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制度最为系统、完整,较历代最为繁荣。万历二十五年前后中央政府于岷州地区增设岷州茶马司,本文拟对岷州茶马司建立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分析岷州茶马司建立的原因。
一、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
明朝初期明政府主导控制下的官营茶马贸易从总体上来说是兴盛、高效的,基本上实现了茶马贸易的最初目标:从茶马贸易中获得马匹数额巨大,军马来源稳定;藏族地区及西北边境较为稳定;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密切;河湟岷洮地区汉藏民族关系和谐有序等。
但自永乐后期始,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开始走下坡路,由盛转衰。官营茶马贸易的政策实行、官茶的运输、官茶的茶源和茶马司茶叶储量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官营茶马贸易规模日渐萎缩。明政府从茶马贸易中获得的马匹日渐减少,军马的不足削弱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严重影响到明朝西北和北方边境的防卫质量;明朝政府从茶马贸易中收取的赋税也越来越少,而内地茶农的生计更是困顿不堪。到了嘉、万时期官营茶马贸易的问题进一步迸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诸茶马司茶叶积压情况十分严重。嘉靖二十五年,由于洮州、西宁、河州三茶马司陈茶过多,明政府不得不降价三分之二,将茶叶贱卖,清理库存。另一方面由于官府所售茶叶都是陈茶,质量低劣,藏族不愿意用马匹与之交换,明政府从茶马贸易中获得的马匹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堪敷用,这又反过来使官茶进一步积压。如此往复,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明政府大受其害。官营茶马贸易衰落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能说明其窘困境地的便是以商茶为代表的民营茶马贸易和以私茶为代表的走私茶马贸易的兴盛。
(一)嘉、万时期商茶逐步崛起
明初规定商茶不能运至边境,不许商人介入茶马贸易,实行严格的完全的茶叶官方专卖,茶马贸易完全由明政府垄断。商茶合法参与茶马贸易始于明代中叶弘治时期,面对官营茶马贸易中存在的严重运输困难,明政府开始在西北茶马贸易中实行“招商中茶”,自此拉开了明中后期商茶合法参与茶马贸易的帷幕。“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於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馀者始令货卖,可得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数足而止’从之。”[2]商人到巡茶御史处开具茶引,然后凭茶引到产茶地方收买茶叶,再自行运到西北各茶马司,政府从中抽取四成茶叶,剩余六成商人自行售卖。
弘治时,明政府并没有打算永久实行“招商中茶”政策,仅仅将其视作一种临时性的应急举措。明政府认为商人的参与会产生严重的私茶问题,这将会影响到政府垄断的官营茶马贸易。弘治十二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王宪言:国家于河州等处收茶以易番马,大得制御之道,比来抚臣建议从权开中粮茶,遂令私茶难禁而易马不利,未见其益,只见其弊,请自今停粮茶之例”。这样,实行了近十年的“招商中茶”就被废止了。
然而到弘治末期,西北地区无论是马政还是茶法都已经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单纯的依靠官营茶马贸易已经无法解决西北地区马政茶法之困。“自宣德、正统以来,为因边地多事,运粮为急,势不能行,茶马停止,六十年来,莫之能复。”[3]“谨饲秣各房马不过三千六百七十余匹,瘦病者不可胜数。”[4]这种情况下杨一清以都察院副都御使的身份督理陕西马政,开始主持对西北茶法马政的整顿改革。其采取的主要做法便是恢复之前所停止的“招商买茶”法,“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一清复议开中,言:招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帝从所请”[5]。再次开中后,明政府从商茶中抽取的茶叶份额从四成降低至三分之一,明政府对于商茶的压制较之前有所松动,给予商人更多的利润空间,鼓励更多的商人参与茶马贸易。
杨一清在西北重启“开商中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商人参与茶马贸易为明廷解决了茶马贸易中茶叶运输问题,诸茶马司茶叶储存量少的问题也基本解决,随着边境茶叶存量的增加,茶马贸易有所恢复,官方抽取的茶叶份额后又提高至与商对半。“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6]凭借政府的垄断,“开中法”使得明朝政府在茶马贸易中既不用负担茶叶的运输问题,又不需要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茶叶和商税。“招商中茶”在经历时举时废的尴尬境地后,最终为明朝中央所采纳,“遂著为例永行焉”[7],商茶被明政府认可,官营茶马贸易在明代茶马贸易活动中一家独大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到嘉、万时期,商茶已经在茶马贸易中站稳脚跟,贸易量与日俱增。“嘉靖十九年,除正额茶九十万斤易马外,仍开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俟边储稍给,遵照旧额专备易马,诏从部议”;“嘉靖二十六年,令陕西开中茶一百万斤。”[8]以至于频繁出现明廷中央每逢开中之时需特别要求“开中”不得太滥的记录,以限制商茶过多。“嘉靖十三年,令陕西金西等五州县,又限各处开中茶斤之数不许太滥;嘉靖十三年,奏准今后开茶之期,商人报中每岁至八十万斤而止,不许开中太滥。”[9]到嘉靖朝后期,每岁开中茶叶已由初期的五六十万斤猛增到一百万斤,甚至有个别年份达到四五百万斤[10]。①有“(弘治)十四年以榆林环庆固原粮饷缺乏将洮河西宁发卖茶斤,量开四五百万斤召商”的记载。综合史料来看,嘉靖时期每年“中茶”量大抵在一百万斤上下浮动,商茶迅速成为茶马贸易中茶叶的主要来源。动辄百万斤的商茶量使得明朝边境茶市上的茶叶存货量猛增,这对明廷的茶叶专卖制度和茶马贸易政策构成了极大威胁,明廷不得不减少中茶的数额。“嘉靖四十三年,兵部覆御史潘一柱条陈茶马事:召商中茶,近增至百万,滞矣,止,宜岁中五、六十万招商,以百五十人为率。”[11]明廷还控制茶引,减少茶商的数量,以期将商茶的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到万历年间商茶已然在茶马贸易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招商中茶”使商人得以参与茶马贸易的各个环节,巨大的利润驱动大量的商人参与其中,市场的贸易主体开始多元化,官营茶马贸易不得不与以“商茶”为代表的民营茶马贸易竞争,原先凭借政府完全垄断市场的官营茶马贸易逐渐失去了在茶马贸易中一家独大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嘉、万时期私茶愈加泛滥
私茶问题始终是明代官营茶马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明朝在实行茶马贸易政策之始就注意到私茶问题并且加以严厉打击,为此制定、颁布了许多茶禁制度和法令。《明太祖实录》卷90载:“山园茶主将茶卖与无引、由客兴贩者,初犯答三十,仍追原价没官;再犯答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价人官。”《明史·食货志》卷80载:“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贩私茶者,与私盐同罪。”梁材《议茶马事宜疏》载:“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载:“洪武三十年又规定:“把守人员若不严守,纵放私茶出境,处以极刑,家迁化外;说事人同罪;贩茶人处斩,妻小人官。”
在严格绵密的私茶查禁政策下,明初的茶叶走私仅仅局限在一小部分贵族和边境官员中,如洪武年间驸马欧阳仑就因为涉及私茶而“坐死”[12]。整个明朝前期茶禁政策随着明朝中央政治的风云变幻略有疏漏起伏,但私茶问题总体上来说还是可控的,并没有对官营茶马贸易构成根本上的挑战。
私茶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明朝政府罔顾茶马贸易应当是基于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也有茶马交易中“茶贵马贱”的不平等交易是对藏族事实上的经济剥削,导致了藏族不愿意以马易茶;更有官方一味垄断不予民利的因素。然而明朝中后期私茶泛滥,无法查禁,这也是与“招商中茶”政策的实行有极大关系的。
“开中”法由过去官茶官运改为商茶商运,商人从政府买来“茶引”,到产茶处买茶,继而由商人自己运输到边境,运输到边境的茶一部分交予边境茶司用于易马,其余部分由商人自己贩卖。到嘉、万年间商人除了不能在边境用茶叶和藏民直接交换马匹外,可以充分参与到茶叶的采买、运输和部分合法售卖的环节中去(在边境的规定地区)。明廷认为只要把商人排除在以茶易马的最后一个环节外就可以尽享“开中”之利,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情况来看,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恰恰自“开中法”实施后凡是有商人参与的环节无不出现了“私茶”泛滥的情况,就连严格禁止商人直接“以茶易马”的环节也形同虚设。
商人交予边境诸茶司的茶由弘治初的五分之二上升到三分之一,再到嘉、万时期的五成,比例在逐渐扩大。似乎商茶自卖部分越来越少,其实不然。因为到嘉、万时期每年“中茶”的总量与弘治、正德时相比是不断增长的,所以自卖部分商茶量也是增长的。“令自卖”并不是彻底放开边境茶叶市场,允许商人在边境地区随意贩卖茶叶,而是在指定的地区贩卖,是“内销”而不是“外销”,运输到边境的“自卖”茶叶是绝对不允许与少数民族直接“以茶易马”,参与易马贸易的。
“招商中茶”导致私茶问题进一步突出的原因也是多重的。首先,“召中法”使商茶量不断增加,商人将大量的茶叶运输到边境地区,但边境的市场是有限的,又加上诸多限制,必然会导致商人手上的茶叶积压,贩卖不畅。商人大受损失,又经历正德荣幸番僧导致杨一清整顿后的茶法崩坏,“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13]。到嘉、万时期,茶法已是形同虚设。加之茶马交易中的惊天利润,商人必然铤而走险,将手中积压的茶叶私自贩卖,大量的商茶逐渐转变为私茶。
其次,“召中法”商人在茶叶运输环节是主要的承担者,这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商人的“夹带”行为所带来的大量私茶——除了正常“引”“由帖”规定的茶叶运输量之外商人额外夹带的茶叶。许多茶商“假以附茶为由,任意夹带,悠情短贩,甚至汉中盘过有二三年不到茶司者,巩昌招中有十数年不销原引者”[14]。夹带的私茶已经到了“动至数万,赊寄居民,家租户蓄,塞户充栋”[15]的地步。
而伴随茶马贸易之始就一直存在的茶叶走私现象到嘉、万时期不仅没少反而是变本加厉。如边疆官吏参与茶叶走私问题,由个别现象发展到普遍存在,自将领以下,很少有边境军人的家人不参与茶叶走私,“军积自将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当通番”[16]。这与明后期边关军人生存艰难也是有关系的,但也可以看出私茶禁法名存实亡;而普通茶叶走私贩更是气焰嚣张,明火执仗的走私,“今之贩者,横行态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积聚如丘,外境夷方,载行如蚁”[17]。视查禁为无物,甚至武装走私,官府亦不敢抓捕,“各执兵器,昼止夜行,群聚势凶,莫之敢捕”[18]。
私茶的极度泛滥以及私茶茶马贸易的强势崛起使得积弊重重的官营茶马贸易雪上加霜,就当时的实际情形来说,私茶和商茶的贸易规模实际上已经和官茶大致相当了。到嘉、万年间,明朝西北茶马贸易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二、岷州地区是茶叶运输的主要节点
在西北地区私茶日益泛滥甚至无地不私茶的局面下,岷州地区也无例外。探究其各种原因我们会发现,明代岷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西北地区茶马贸易茶叶运输的主要节点,这也是私茶贸易在岷州地区兴盛的重要原因。
明代在岷州地区设岷州卫管辖此地。洪武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平定河州后,在岷州筑城,后升河州岷州千户所为岷州卫,驻军镇守。岷州卫位于甘肃西南部,辖西固(舟曲)、阶州(武都)、岷州(岷县)、迭州(迭部)、宕州(宕昌)等地。“东至巩昌府漳县一百八十里,西至临洮一百二十里,南至阶州三百七十里,北至临洮府三百七十里,东南至秦州礼县四百三十里,东北至巩昌府二百四十里,西南至境外叠州天生寨生番界一百里,至北京四千一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九百里。”[19]明代岷州地区实则是甘青藏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地,是西北三大茶马司茶运途径的十字路口,与西宁、河州、洮州等明代最主要的茶马司均接壤,同时又与南方四川等地的藏区相邻,“西亘青海之塞,南临白马之氐,东连熙巩,北并洮叠,内则屏翰蜀门,外则控制番境,百二疆场实有赖焉”[20]。所以,岷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重要。
明代西北诸茶马司以茶易马的茶叶主要来源于陕西和四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明代中期,陕西汉中等地茶叶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明代陕西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的汉阴(今陕西汉阴)、汉中府(今陕西汉中)、西乡(今陕西西乡)、金州(今陕西安康)、石泉(今陕西石泉)、诸府州县。“陕西汉中府金州、西乡、石泉、汉阴,具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廓、新里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黄册,又增加一里,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逸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已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具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21]这样在陕西的产茶地区和诸茶马司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条运茶通道,即“茶马古道”。其中“自汉中府到徽州,过连运栈,俱由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方偏僻,原无衙门,添设置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11站,每处设茶夫110名,巩昌府至三茶马司,变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计30站,每处设茶夫30名”[22]。后由于官茶的运输由商运替代官运,各地茶运所裁撤,西北运茶路线又有了新的变化。据《甘肃通志·茶马卷》记载:“中茶易马,惟保宁、汉中”;“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一路经勉县、略阳、徽县、西河到达洮州、岷州为‘汉洮道’。”[23]西北诸茶马司的茶叶另一大来源则是川茶。与陕茶的情况一样,在川茶的运输路线中岷州也是必经之地。“其达、巴三州之茶,自汉中运至秦州,道远难致,人力多困,若令就汉中收贮,渐次运至秦州。”[24]川茶西运的路线之一是溯白水江(今白龙江),运至徽州(天水),再由徽州运往诸茶马司。
无论是川茶北运还是陕茶西运,两条茶马古道皆经过岷州地区。这也给岷州地区的私茶贸易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便利。梁材《议茶马事宜疏》中明确提出,岷州是私茶偷运到藏区的主要途径,“夫茶聚于茶司,则通番之弊易滋,茶严于内郡则私贩之弊难究,何也,盖陕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阶岷;一曰临洮;一曰兰州;三路严守则茶企能飞入番境哉?”岷州地区属地又多山路小道,私茶流通更加隐蔽难以防范,因此,岷州地区是明政府查禁私茶的重点区域。
而从明朝历代中央给各地下达的禁茶律令以及地方督抚的茶禁条陈来看,四川松潘、建昌等地的川茶走私往往有岷州等川、甘交界地方军民的参与。杨一清在《为申明事例禁约越境贩茶通番事疏》就向明朝中央呈报,岷州私茶走私贩聂子太等人在得知“四川保宁府通江、巴县并利州卫等处私茶不禁”[25]的情况后,前往上述等地买茶私藏在家,后卖与本地藏族一事,并且建议明廷加强在川、甘交界地方私茶查禁力度。嘉、万年间为了治理川地私茶流往西北以及商茶“夹带”等问题,多次申饬严令管辖洮、岷地区的“洮岷参将、巩昌兵备道”等职能部门,加强稽查边路小道和茶叶运输的“印钤截角”工作以防私茶[26]。
另一方面,藏族很多的部落栖息于岷山的山沟密林中,明朝岷州卫管辖境内番族被称之为“岷州番”“西固城(今甘肃舟曲)番”等不下151族”[27]。此地藏族要想纳马易茶必须要翻越深山险水到相隔甚远的洮州、河州地区,这显然给当地藏族带来了极大不便。岷州这些独特而又重要的特点,使得明朝中央单纯依靠查禁去解决岷州地区的私茶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在岷州增开茶马司无疑是一种可供明廷选择的最佳方式。
三、隔断蒙藏联系以保障洮岷地区稳定
面对蒙古族与藏族,明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统治方略,明朝统治者视雄踞北方草原上的蒙古诸部为自己的头号战略威胁,明朝的诸多国防战略都以此为出发点,始终视其为最大敌人。对藏族则认为其威胁较小,主要采取怀柔羁縻的较为柔和的统治政策。同时为防止蒙古与藏族联合,明朝初期在边境防卫体系的设置上十分注意切断蒙藏之间的联系。在河、湟、洮、岷地区设置卫所,屯兵驻扎。明初一百余年间,蒙古势力始终在北方没有进入西北地区,河、湟、洮、岷等地较为稳定,刀兵少起。
但是不到百年,明朝政治腐败,边防废弛,土木堡之变也改变了明朝与蒙古的战略态势,蒙古诸部频繁入侵中原内地,并开始往西逐渐进入青海地区。正德五年,蒙古亦卜剌部在与达延汗的战争中失利,被迫西逃,首先入青海。“明年,北部亦卜剌与小王子仇杀,亦卜剌窜西海,阿尔秃厮与合,逼胁洮西属番,屡入寇,渐深入,边人苦之,八年夏,拥众来川,令远徙,亦卜剌遂西掠乌斯藏,据之,自是洮、岷、松潘无宁岁。”[28]
自此蒙古开始长期驻牧青海,到嘉靖中期随着蒙古俺答汗部崛起,明朝整个北方和西北方向的边境处处烽火。青海蒙古诸部不仅仅侵扰明朝边境,而且对散居甘青、实力分散的藏族同样劫掠,藏民不堪其扰。“自青海为寇所据,番不堪剽夺,私馈皮币曰手信,岁时加馈曰添吧。”[29]“番族受其害者,烧帐房,掠羊马,掠妇女,杀壮丁,番皆畏之。”[30]“(隆庆二年三月壬戌)先是中虏三千余骑驻红城子、石棚沟等处,由庄浪飞石崖入犯西宁河州界,掠熟番灵藏宗刺等族,寻引还。”[31]“(万历十八年正月乙丑)巡抚甘肃李廷仪奏言:十月十二日套虏吉囊纠合火落赤等指抢生番,两路并进,侵犯射死居民,抢掠牲畜,乞敕兵部查议。”[32]俺答汗死后,青海蒙古诸部进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嘉靖、隆庆两朝着力安抚俺答汗和其部众想实现青海蒙古与中原和平相处的局面,然而期望落空,失去俺答汗的青海蒙古诸部与明朝的关系更加恶化。蒙汉、蒙藏民族关系空前紧张。明朝开始改变对青海蒙古诸部的安抚策略,变抚为剿。
万历初期,青海蒙古诸部势力逐渐由青海湖向周边扩张,向南渡过黄河,占据莽刺川(青海贵德以南)、捏工川(青海同仁),进入河曲地带,河、湟、洮、岷地区直接面对青海蒙古,原先较为稳定的岷洮“番地”开始动荡不安,情势很是严峻。“永邵卜遂统领部落,掠番聚丑,负海称雄,而火真等酋遂渡河南牧,营成三窟。”[33]“以故,两河东西无处不虏,无地无市,要挟不遂,无日不抢,甚则犯西宁,继犯洮州,三犯洮河。”[34]而青海蒙古诸部每次入侵几乎都会裹挟甘青藏族加入,一部分藏族部落也趁机参与劫掠。“万历间,夷犯内地,驱番为导引前锋,番既获利,危害河湟胜于夷矣。”[35]“自青海为寇所据,番或反为向导,交通无忌。”[36]明朝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所谓“南番北虏”联合在一起。西北边境的局势越加复杂。
更有甚者,青海蒙古频繁袭扰河曲地带,明朝西北诸卫疲于应对,岷州地区的千哈、劄哈、咱细、日雾四族趁机攻打、劫掠阶、文两县城。“(万历三年二月庚午朔),先是,陕西河、洮、阶、文等处数有番警,去秋九月攻陷麻山关,去冬复出抢介州。”[37]“(万历三年八月)先是,逆番千哈,劄哈,咱细,日雾四族展抢阶、文等处。”[38]至此青海蒙古所引起的乱事已然祸及岷州地区,明政府面临着空前的边境军事政治压力。
明廷任命郑洛经略陕西以征“西虏”。明朝在对“两川”蒙古着手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很快认识到要实现对青海蒙古的战略优势一定要先稳定河、湟、洮、岷地区以及该地区的藏族诸部落,必须分化、争取夹在汉蒙之间的甘青藏族。对于那些被裹挟、压迫以及摇摆不定的藏族部落,明朝中央政府则多管齐下,既威之以武力又加强汉藏贸易往来,茶叶这一藏族生活必需品以及茶马贸易被视为与青海蒙古争夺甘青藏族、打击青海蒙古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和有效武器。
为此在郑雒的主持下,明朝西北边疆官吏在临近莽、捏两川的临巩道等地陆续“收番”[39],以切断青海蒙古和洮岷等地藏族之间的联系,加强明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万历年间“两川之战”前后,“收番”行动效果空前,万历十九年八月,仅临巩兵备道“收生、熟番人部落二万一千三百余名”[40]。而据经略陕西尚书郑雒在其《收复番族疏》中则记载更为详细,“临巩道呈称会同总兵官收过生熟番人共八十七族部落,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名”,除了原先“纳马熟番六十三族”又新招“生番共二十四族”。这是在河东收服的藏族,在濒临青海湖的西宁卫等河西地区同样“收番”较多,“西宁分巡肃州等道报招熟番八万二百(千)七十(百)余名”。万历十九年十月,按察使石槚等新收番族工巴等124族(名)[41]。万历二十一年,“番族头目板日,因招率众来归,至二百余帐”[42]。“收番”之后在如何安置这些“东附”藏族部落的问题上,明政府再次运用起茶叶和茶马贸易的杠杆,对于这些脱离青海蒙古投向明朝的藏族部落,明廷多采取“安插原驻牧地方,中马领茶”[43]的方法,但凡站在明朝一边的藏族就可以被纳入到明朝的官营茶马贸易中。
明朝中央政府还意识到青海蒙古也在用茶叶来诱使部分藏族部落随其东侵。“番以茶为命,若虏得,借以制番,番必转而从虏,遗患匪细。”[44]而有的私茶走私贩不仅将茶叶走私到藏区,更有甚者直接将茶叶偷运到青海湖附近,贩卖给驻牧其地的蒙古族。“有一种奸商,私挟茶篦,深入番地,利其货值。又有一种奸吏,私载茶篦,远抵虏穴。”[45]私茶流入青海为青海蒙古所得,“借以制番”的事实给明朝中央经略“番虏”带来了极大困难,为此明朝中央必须加强对河、湟、洮、岷地区茶马贸易的监督和整顿,加强官营茶马贸易对该地区茶马贸易的控制,严禁私茶流入青海地区。
青海为蒙古所据,使得原先向明朝“纳马”或者参与茶马贸易的许多藏族部落迫于蒙古威胁被动或主动的与明朝为敌,不再向明朝“纳马”、以马易茶。“自青海为寇所据,番不堪剽夺,而中国市马亦鲜至。”[46]明朝的马源受到极大限制,严重威胁明朝的军事准备。“诸番分纳各夷添巴,不纳中国,茶马已判然为夷属。”[47]大量藏族部落或主动或被动脱离明政府转而依附蒙古诸部的事实,更是让明政府如坐针毡。
明中叶“招商中茶”的政策实施后,在政府许可的部分境内地区,合法商人和地方政府可以散铺行卖。由于岷州临近藏族地区,一直实行茶叶禁卖。嘉靖时,明世宗采纳了巡察御史刘良卿的建议,“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万历年间。岷州地区的藏族要想从正规渠道获得茶叶,必须到西宁、河州等茶马司以马换茶,多有不便。
如此,在局势不稳的河、湟、洮、岷地区严厉打击私茶贸易,整顿河、洮等茶马司并且加开岷州、庄浪等茶马司成为明朝中央的必然选择。明朝中央政府充分利用茶马贸易的经济杠杆作用争取甘青藏族,隔绝蒙藏贸易;填补明朝巨大战马需求缺口;削弱青海蒙古,进而稳定西北边境。
[1]白振声.茶马贸易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3).
[2][4][5][7][12][13]张廷玉.明史·卷80·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0,1951,1951,1951,1942,1942.
[3][14][15][16][17][18]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115·杨石淙文集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78.
[6][21][25]杨一清.杨一清集(上)[M].唐景绅,谢玉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64,67,89.
[8]明世宗实录·卷164·嘉靖十三年六月乙卯[Z].3630-3631.
[9][10]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287卷·食货典·茶部[M].北京:中华书局,1988.85001,85004.
[11]明世宗实录·卷532·嘉靖四十三年三月戊申[Z].8659.
[19][20]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岷州志校注[Z].1987.2,59.
[22]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120·杨石淙文集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88.
[23]李刚,李薇.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J].西北大学学报,2011,(4).
[24]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辛巳[Z].1499.
[26]申时行.明会典·卷37·茶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54.
[27]王继光.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2002,(4).
[28]张廷玉.明史·卷367·鞑靼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478.
[29][36]张廷玉.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西番诸卫[M].北京:中华书局,1974.8549,8549.
[30][35]梁份.秦边纪略·卷六[Z].赵盛世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31]穆宗实录·卷18·隆庆二年三月壬戌[Z].1568.
[32]神宗实录·卷219·万历十八年正月乙丑[Z].1590.
[33][34]神宗实录·卷294·万历二十四年二月乙亥[Z].1596.
[37]神宗实录·卷35·万历三年二月庚午朔[Z].803.
[38]神宗实录·卷41·万历三年八月辛巳[Z].938.
[39]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郑经略奏疏一·收复番族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7.
[40][43]顾祖成.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二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173,1176.
[41]神宗实录·卷241·万历十九年十月壬寅[Z].1591.
[42]神宗实录·卷263·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庚寅[Z].1593.
[44]神宗实录·卷67·万历五年九月乙未[Z].1577.
[45]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郑经略奏疏二·类报四镇虏情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0.
[46][47]神宗实录·卷70·万历五年十二月甲午[Z].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