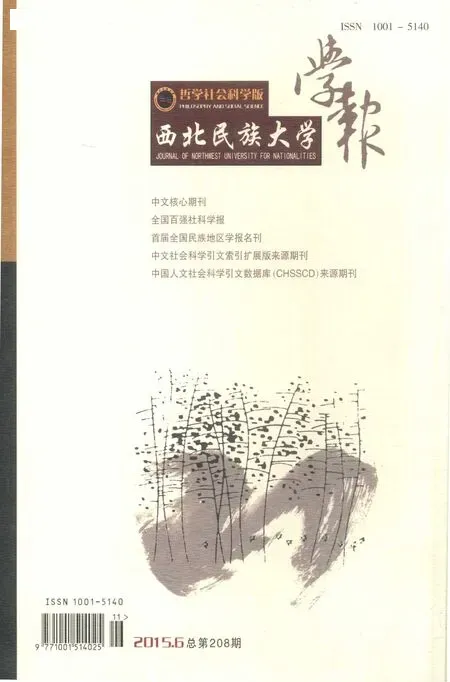甘英出使大秦:研究述评与再审视
2015-02-20颜世明刘兰芬
颜世明,刘兰芬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2.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273100)
东汉和帝时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是中外关系史与中外交通史上的壮举,《后汉书》《晋书》《梁书》《旧唐书》均载其事。核心史料的匮乏、史籍记载的歧义及各家对史书解读的不同,致使历史公案产生与聚讼不已。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广觅史料,以全新的方法、不同的视角抒发己见。在激烈的辩驳中扬弃庸俗的观点,在深入的研究中涌现新颖的见解。百余年来众家之研究纵然存在分歧,但在某些方面已达成共识。本文以甘英出使大秦的目的与无功而返的原因及出使路线为纲,将前贤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扼要举出,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简要评析,以图推动研究层次的再深入与研究视野的再拓展。
一、出使目的与无果而返的原因
史籍缺载甘英出使大秦目的与任务,中外学者纷呈己见以补其憾。少数西方学者荒谬地认为甘英受班超指派入侵大秦,1885年德国学者夏德在《中国及罗马东边地》(China and the Rome Orient,朱杰勤先生另译作《大秦国全录》)已直斥其非[1]。1944年龚骏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考》中提出班超欲探听大秦虚实之说[2],后之学者长泽和俊、余太山先生认同之[3]。长泽和俊先生又认为当另有探明中国丝绸制品在安息交易情况之目的。莫任南先生则认为中国丝绸在大秦畅销不滞,安息从中坐收垄断之利,出于探寻与大秦经济贸易商道之目的。且亦可招徕外臣,宣扬汉威[4]。姚胜先生认为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践行重农抑商之策,商业附属农业为末业,东汉官员焉会主动探寻商道,莫先生第一说不符合东汉国情。而宣扬国威或有可能,但绝非根本目的。姚先生结合东汉与匈奴的关系、班超个人因素、甘英出使路线,认为东汉班超时代两次大败匈奴,匈奴仍是与汉争夺西域的劲敌,班超欲稳固汉在西域的统治必须寻求政治盟友,大秦国则是理想之选[5]。
纵观东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东汉始终秉持消极、被动的态度,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支出远逊前汉。西域既受匈奴势力威胁,亦时常受西域大国控制。班超欲镇服西域、稳定西陲,而又不劳中国,必须依赖西域诸国之力,即班超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实际上班超确曾数次联合西域盟国诛伐叛逆,如建初三年(78年)亲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四国胜兵万人攻姑墨,又上书言西域远国月氏、乌孙、康居愿归附汉[6]。即班超既努力争取葱岭之东西域诸国支持,同时又注意结交葱岭之外的强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初九年(84年)班超攻疏勒王忠,康居遣精兵援忠。时康居与月氏联姻,超遣使持锦帛厚赠月氏王,令其规劝康居王罢兵,结果康居收兵而还。正是巧妙地利用康居与月氏的姻亲关系,班超不费兵卒收服疏勒失地。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亦当出于结交大秦、寻求盟友的目的,即笔者之意与姚胜先生相同。
《后汉书》《晋书》二史载甘英抵达安息西界,临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若遇善风则需时三月,遇迟风则需时两年,且海中存在着令人思土恋慕之物,“英闻之乃止”[7]。安息西界船人向甘英讲述海中善使人思恋之物,应即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塞壬(Sirenes)。塞壬善以妖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其如痴如醉[8]。后人根据本条史料揣测甘英出使大秦无功而返的原因,归纳起来计有两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观方面是甘英缺乏冒险精神,畏惧困难,如康有为[9]、范文澜[10]、余太山[11]先生持是说;客观方面如海洋阻隔[12],安息船人为垄断中西贸易而从中阻挠[13,14,15]。
袁宏《后汉纪》成书时间较范晔《后汉书》至少要早五十年,书中保存了东汉时期若干原始史料。其中《孝殇皇帝纪》亦载录安息西界船人所讲女妖塞壬之事,甘英闻听之后止步不前,“俱问其土风俗”,下文叙述大秦国风土民情、物产状况,文与《后汉书》中“大秦国传记”行文基本相同,袁纪又云:
其长老或传言:“其国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相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惊,而有猛虎、狮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赍兵器,辄害之,不得过。”又言:“旁国渡海飞桥数百里。”[16]
《后汉书》《晋书》仅节录安息西界船人讲述的海妖塞壬之事,删削其叙述大秦国状况之事。由《孝殇皇帝纪》或可还原本事的原委:安息长老(《后汉书》、《晋书》则作“安息西界船人”)述说海妖塞壬之事后,甘英又向其询问大秦国情况,安息长老将其所知风土民情如实相告,其中提到从安息陆路绕过西海也可以到达大秦。即安息长老向甘英提供海道与陆路两条通往大秦的路线,显见安息长老诚恳待英,倾己之力助其行。安息船人述说珍奇怪事,是甘英西使见闻中的插曲,并非令甘英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前哲所言海洋阻隔、安息船人阻挠之说不可立。
《后汉书》曰:“(甘英历)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17]甘英历尽险难方抵安息,焉会再次临危退缩,前贤所讲甘英胆怯、畏惧困难之说不可信。笔者以为甘英出使无果的原因与出使目的相关,前揭甘英出使大秦目的是寻求政治盟友,自安息到大秦快则三月、慢则两年,毋言自塔里木盆地到安息的行程时间,汉与之结盟、抗衡外敌可望而不可即。
二、出使大秦路线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序言概括汉代丝绸之路中段南北两道路线:南道从莎车逾葱岭可达大月氏、安息,北道由疏勒逾葱岭可至大宛、康居、奄蔡。同时正文中又插叙南道支线(即皮山到安息路线),自安息到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路线以及由莎车经蒲犁、无雷到大月氏的交通线。范晔在《西域传》序言中指明全传皆是“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史料所及未见班勇出使域外之载,甘英又奉勇父班超之命出使,许多学者推测范书《西域传》中通往域外的路线当是甘英出使路线,他们或糅合序言与正文中这两条路线,或撷取正文路线以作甘英出使路线。如龚骏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考》中认为甘英出使路线当自南道始发、北道返归:皮山—乌秅—悬度—乌戈—条支—安息—大月氏—无雷—蒲犁—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焉耆。理由有二:其一,范书《西域传》正文路线按照由南至北顺时针回转,通往域外的路线有始有终,或是甘英西使路线;其二,正文中葱岭之西的诸国传记(如天竺、大秦)内容空泛,当是甘英旁听而来。而罽宾、乌戈、条支、安息、大月氏五国传记叙述翔实,且囊含行程时间与诸国间距离,当是甘英躬履其地而得[18]。
莫任南先生在《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中指出龚文以东汉都护府驻地在焉耆实误,又认为永元九年(97年)班超并未驻守在南道,龚骏先生自南道出发之说缺乏根据,又提出自北道出发、由南道返回的路线:龟兹—疏勒—莎车—蒲犁—无雷—大月氏—木鹿—和椟—阿蛮—斯宾—条支(于罗)—乌戈山离—罽宾—悬度—乌秅—皮山—龟兹。其路线根据如下:其一,永元三年(91年)班超升任西域都护,而西域都护府治地在龟兹它乾城,永元九年(97年)甘英既受班超之遣出使,当自龟兹出发;其二,范书《西域传》载莎车国西经蒲犁、无雷到大月氏的路线以及大月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的行程时间。这条路线、时间当是东汉某使者的行程日志,东汉史籍中仅载甘英曾西逾葱岭,故当是甘英路线;其三,范书《西域传》又载安息到洛阳25 000里,安息东界的木鹿到洛阳20 000里,故安息到木鹿5 000里。木鹿即安息东界马尔吉亚那·安条克(Margiana Antiochia),向西越过赫开尼阿群山到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即安息都城和椟城),其距离约合古代西方历史学者所言5 000“视距离”,与《西域传》安息到木鹿的距离相符。同理《后汉书》安息(和椟城)、阿蛮(Acbatana,阿巴塔那)、斯宾(Ktesiphon,泰西封)、于罗(Hira,希拉)之间的距离,与西方历史学家所载诸地之间的“视距离”大体趋同。同时范书《西域传》大月氏到安息路线与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相合,东西方学者记载路线不谋而合,表明确实存在着自大月氏到安息的交通路线。范书《西域传》大月氏以西路线、道里精确无误,必是甘英亲身经历而得;其四,范书《西域传》又载皮山到安息的路线,可将其途经地颠置成安息到皮山的路线,当是甘英返回路线[19]。
莫文出入中西史书之载,论证过程貌似严谨不苟,时为中国学者认同。但其文与龚文相同,未有强有力的史料支撑。甚至援引论据存在着疏漏,如东汉时班超亦曾逾葱岭(见下文),莫文言东汉时惟甘英西逾葱岭过于武断。2000年杨共乐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甘英出使大秦路线新探》[20],对莫任南先生考证的甘英西使路线提出质疑:其一,托勒密《地理志》提到从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到巴克特利亚(Bactria)路线,是为计算经度及有人居住的世界长度需要,未言本路线是通向中国的惟一交通路线;其二,《后汉纪》具载甘英出使大秦路线:“甘英逾悬度、乌戈山离,抵条支”[21],即甘英循丝绸之路南道路线至安息,并非莫文所讲的北道。杨文又指出《后汉书》亦载类似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至乌戈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特。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22]袁纪与范书路线途经地如此吻合,范书《西域传》又系班超少子班勇所记,史料所及班勇政治活动区域局限在葱岭之东,基于甘英、班超、班勇之间的关系,可以断定《后汉书》皮山到安息的路线当是甘英出使大秦的完整路线。
《后汉纪》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即悬度—乌戈山离—条支)过于简略,然其史料可靠性毋庸置疑,前引《后汉书》“(甘英历)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可佐证。“沙度”,《后汉书》又别作“悬度”,亦即《汉书》“县度”,《汉书》曰:“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23]其地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达地斯坦(Dardistan)的达丽尔(Darel)与吉尔吉特(Gigit)之间的印度河上游地带。
《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曰:“(皮山)西南当罽宾、乌戈山离道”,西汉成帝时杜钦劝说大将军王凤,云以前汉使自皮山送还罽宾使者归国,需要经历不属汉的四五国及县度,道路艰险、盗贼横行,今后护送罽宾使者至皮山即可[24]。即循南道去往罽宾、乌戈山离的捷径当由皮山出发,且经过县度方可到罽宾。《后汉书》曰:“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25]综合上文可将《后汉纪》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扩展为:皮山—悬度—罽宾—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补充之后甘英路线与前引《后汉书》皮山到安息路线途经地基本相同,惟详略有别,杨共乐先生指出《后汉书》皮山至安息路线当是甘英出使路线深有见地。《后汉纪》又载甘英自安息的返回路线:“(甘英抵条支临大海)西南极矣,山离还,自条支东北通乌戈山离,可百余日行。”[26]即甘英自从南道出发,又从南道沿原路返归,杨文并未指出,甚憾。
笔者曾撰文《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 —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27],在杨共乐先生考证甘英出使路线基础上,结合两汉书《西域传》路线进一步补充、完善,并与实地相印证:甘英西使大秦由它乾城出发行至姑墨(今阿克苏),复沿阿克苏河、和田河南下达至于阗(今和田),西北过皮山(今皮山县附近)到达今叶城县,顺着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即西夜、子合地)西南行,至叶尔羌河上游支流马尔洋河(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马尔洋乡境内),往西直行可达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或帕米尔高原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沿洪扎河(即乌秅国,今罕萨地区)到吉尔吉特(即难兜国),再南下沿印度河支流至罽宾国(今阿富汗塔克西拉与白沙瓦临近地区),复由阿富汗南部洛拉河、赫尔曼德河至乌戈山离,再由伊朗萨尔哈德高原重镇哈什南行,进入伊朗东南角、阿曼湾沿岸冲积平原,沿波斯湾沿岸低洼平原西行可至条支,又东北过两河流域至安息王治泰西封(Ctesiphon,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其后由原路归返。
笔者刚踏入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加之材料搜集不够充分,拙文中穿越伊朗高原的路线(伊朗萨尔哈德高原至条支路线)依据条支地望在安息西南及甘英由条支到达安息两个方面推测,并未顾及古代伊朗高原交通路线。笔者又研读西史,知拙文路线实误。甘英行至伊朗境内克尔曼(Kerman)、法尔斯(Fars),后傍伊朗高原扎格罗斯山南麓进入两河流域。笔者已在《浅析〈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西域史料价值》修正[28],因文章主旨与篇幅限制,文中并未开列原因,现将其罗列如下:
其一,锡斯坦—克尔曼—法尔斯交通线在历史上通畅不绝,如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建立者居鲁士(公元前558—公元前529)东征曾另遣一军由克尔曼地区的帕塞波利斯(Persepolis)向东进入锡斯坦,复溯赫尔曼德河抵印度河上游。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退兵路线则由锡斯坦、克尔曼进入法尔斯。
其二,伊朗高原横亘着西北—东南方向的扎格罗斯山,在安息都城泰西封之北,其南脉纵跨法尔斯境内。甘英自乌戈山离(即今以塞斯坦与坎大哈为中心的阿富汗南部地区)向西南进发抵条支,其行程路线只能是越过伊朗境内萨尔哈德高原到达法尔斯。自踏入萨尔哈德高原即进入安息领土(安息辖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甘英路线由条支转北而东到安息,说明此处安息当指安息都城泰西封,条支位于泰西封西南方向。抵法尔斯之后,如果先西南抵条支、后由条支东北行至泰西封,只能循法尔斯境内的扎格罗斯山脉南麓至条支,然后沿底格里斯河到泰西封。此路线是考证东汉时期条支国地望的依据,亦是否定后文宫崎市定条支即塞琉西亚说的重要论据。
永元七年(95年)汉和帝下诏嘉褒西域都护班超,诏书中云:“超遂逾葱岭,迄县度。”[29]即班超曾翻越葱岭亲至县度,而甘英出使大秦亦“逾悬度”,知甘英择取出使路线或出自班超之意。甘英出使大秦部分路线保存在袁宏《后汉纪》中,而《后汉纪》又以《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诸郡耆旧先贤传为基础删削而成[30],九种史籍辑本中惟《东观汉记》、司马彪《续汉书》立有《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或取自《东观汉记·西域传》、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袁宏《后汉纪》甘英出使路线亦或采自二书。其中《后汉书》李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甘英,司马彪《续汉书》作‘甘菟’”[31],司马彪在《续汉书》中必然提到甘英出使之事,司马彪《西域传》辑本又与《后汉书·西域传》行文相近,故袁纪甘英路线出自其书的可能性较大。
与袁宏同时代释法显在《法显传》中言:
其(陁历国)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縆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32]
陁历国即今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河北岸的达丽尔,又即《汉书》“县度”,《后汉书》“沙度”、“悬度”。法显南下印度朝见佛陀,曾攀爬悬梯横渡达丽尔地区印度河。萧梁时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记述释智猛路经达丽尔时亦云:
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縆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汉之张骞、甘英所不至也。[33]
释法显、释僧祐均言甘英未曾到达悬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直引法显之言而不加辨正[34],事实上甘英亲历其地。可见南北朝时期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已经鲜有人知。南朝宋时范晔萃取众家《后汉书》之说,将甘英出使大秦的完整路线辑入《后汉书》,文中并未指明实乃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范晔《后汉书》面世后,唐章怀太子李贤又为其作注,以致范书盛行于世,众家《后汉书》流行式微、乃至亡佚。至后治史者研究东汉史独尊《后汉书》,忽视《后汉纪》史学价值,致使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在《后汉纪》中尘封千年之久。
三、余论
综上所举,中外学者利用《汉书》《后汉书》《后汉纪》西域史料,结合东汉西域政治形势、西域古国地望的研究成果,对甘英出使大秦目的、无果而返原因与出使路线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经历由主观臆测到客观推证,佐证史料由删减众家《后汉书》而成的《后汉书》,到较范书成书时间要早五十年、保存更多原始史料《后汉纪》的过程。以上哲贤之研究深度挖掘隐含史料,考证缜密,成果突出。
甘英出使大秦研究除却涉及上述三个方面外,另有若干课题研究始终停滞在表面甚至极少涉及,如出使时间,司马彪《续汉书》“甘英”异名“甘菟”,甘英闻见录,出使大秦路线与条支、西海地望结合考证。笔者不揣浅陋拟将之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学者加入讨论。
(一)出使时间
甘英出使大秦的时间,《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序言曰:“(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35]即永元九年(97年)当是甘英出使大秦的返回时间。《西域传》又云:“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36]永元九年(97年)又是甘英抵达条支的时间。《后汉纪》将甘英临海而返的时间系于和帝永元中[37],言辞含糊不足为据。
《汉书》与甘英出使大秦路线中包含途经各国的大略时间:姑墨(东与龟兹接)南至于阗(西接皮山)马行十五日,皮山到乌戈山离六十余日行,又马行百余日到条支,再马行六十余日到安息。即自姑墨到安息国约需二百三十五日,八个月左右。既然永元九年(97年)是甘英自龟兹出发抵条支的时间,又是自安息返回龟兹它乾城的时间,则当亦是甘英自条支前往安息的时间。可选取甘英由条支抵安息、又自安息返归龟兹这两个时间段进行逆推,按由安息返回龟兹需时八个月,则甘英返归龟兹的时间至晚当在永元九年(97年)十二月,其由安息启程的时间应不晚于永元九年(97年)四月。而条支到安息行程时间两个月,其由条支去往安息的时间当在永元九年(97年)二月左右。由上可推甘英当在永元八年(96年)六、七月出发,经历六个月行程后,在永元九年(97)元月到二月间至条支。又在两个月后到安息,时在永元九年(97年)三、四月间。又自安息按原路返归,历经八个月后即永元九年(97年)十一、十二月间返回。以往之研究,均以永元九年(97)作为甘英出使的始发时间(如翦伯赞《中国史纲》、白寿彝《中国通史》[38]),实误将回返时间以作始发时间。
(二)甘英与甘菟
甘英,《后汉书·西域传》李贤注曰:“《续汉书》‘甘英’作‘甘菟’”[39]。即唐时存在《后汉书》甘英、《续汉书》甘菟两种写法,均指同一人。“英”在上古音中为平声阳部影纽,拟音[iɑη]。“菟”在上古音中为平声鱼部透纽,拟音[tɑ]。阳部与鱼部可相对转,影纽属喉音,透纽属舌音,发音部位完全不同,“英”与“菟”古音不同,并非语音假借关系。二字字形相近,或是在书籍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与《后汉书》《晋书》《梁书》《旧唐书》相同,袁宏《后汉纪》亦作“甘英”。前揭《后汉纪》西域史料或取自《东观汉记·西域传》、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即最初《东观汉记·西域传》、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均作“甘英”,流传至唐《续汉书》已讹作“甘菟”。
甘英之职务,某些初高等历史教材、历史词典、历史普及读物作“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既有副使,则必另有正使。副使既然是甘英,正使又指何人?事实上史籍中确载甘英的职务,如《后汉书》曰:“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40],《后汉纪》云:“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41]。“掾”是汉代官府秩禄百石的小吏,即甘英职当西域都护班超的属吏,并非副使。
除了干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药师可以建议患者转诊到指定呼吸科医师或更有经验的医师处就诊,以调整药师自己不能确定的治疗方案。
(三)班超《西域风土记》与《西域图》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序言、论赞曰: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
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42]
据上文之意,甘英出使大秦归来曾将所见所闻汇编成文,内容包括经历诸国自然地理、风俗民情、珍奇异物诸事。清人姚振宗依据范晔之言判定当有甘英闻见录流传后世,并将之归于班超名下,拟名《西域风土记》[43]。范晔《后汉书》西域诸国传文转袭“班勇所记”,史籍未见班勇出使葱岭外之载,或可揣测范书《西域传》葱岭之外的罽宾、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诸国之间交通路线与相关诸国传记出自甘英之述。前引《后汉纪》以甘英与安息长老问答的形式叙述大秦国状况以及讲述善使人思慕的海妖塞壬,当是甘英“备其风土,传其珍怪”中的一则。可见甘英闻见录当包含两部分:①出使大秦路线,②经历诸国见闻,既有亲历西域诸国历史地理状况,又有他人之述。
魏末晋初鱼豢曾撰《魏略》,内立《西戎传》。原书现已散佚,部分佚文收录在《三国志》裴松之注文中,鱼书转引《西域旧图》罽宾、条支、大秦三国物产[44]。按鱼豢生活时代主要在曹魏,迨晋代魏后又以曹魏遗臣自居、耻于仕晋。《西域旧图》既冠“旧”字,《西域图》当是其本名,属东汉之书。东汉时历罽宾、抵条支、闻大秦者惟有甘英,且《西域图》大秦国物产与范晔《西域传》大秦国物产基本相同,前者物产数量大于后者,说明后者或节自前者之文,笔者曾据此推测《西域图》当是甘英闻见录(见拙文《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第131页)。仔细斟酌其中当有欠妥之处:前揭甘英见闻纳含在“班勇所记”(即今之范书《西域传》)中,而“班勇所记”或有专名,故《西域图》亦有可能是“班勇所记”书名。即使并非二书之名,其史料当采自二书。
(四)条支与西海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将躬历西域四国(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与传闻中西域六国(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历史地理情况呈报武帝。其中述及条支国在安息西数千里,濒临西海。气候湿润,种植水稻。出产大鸟,卵大如甕。置有小君长,隶属于安息[45]。《汉书》全袭《史记》条支国史料,未添增其他史料[46]。《后汉书》因袭《史记》中临西海、大鸟史料,又增加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海水环绕其国南与东北,惟有西北可通陆路史料[47]。范晔又在《西域传》序言、正文、论赞中三次提到甘英抵达条支,临大海。条支、西海与甘英出使密切关联。
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综合《史记》《后汉书》条支国地理、物产特征及“条支”对音,推证条支国与西海的地望,岑仲勉先生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胪列十余家之说[48]。其中影响最大、现今认可度最高的当属夏德主张西海即波斯湾,条支位于今两河流域卡尔提阿半岛希拉(Hira)[49]。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主张西海即地中海,条支即塞琉古王国都城安条克(Antiocha,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外港塞琉西亚(Seleucia)之说亦具有一定影响力[50],研究中国西域史的著名学者余太山先生即认同是说[51]。
宫崎市定考证方法是假定大秦位于地中海某处,又将四项条件中第二项条件(即位于连接安息与大秦交通线上)具体化,自认为汉时从中国抵地中海的交通路线有三条:①陆路,由中亚进入伊朗高原北部至叙利亚;②海路,自中国南方某处海港出发,经马来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由埃及到地中海;③中间路线,由海路到波斯湾头,再上溯幼发拉底河后转陆路到叙利亚。三条交通路线中第一条路线(即陆路)是由中国前往地中海地区最为便捷、经常使用的路线,夏德、白鸟库吉、藤田丰八条支说并非位于这条路线上,故可将之全部否定。波斯湾位于两河流域地区之南,以西海称之不妥,惟地中海可当西海之称。
宫崎市定提出条支是塞琉古王国或塞琉西亚之音译,塞琉西亚建筑在绝壁山上,西临地中海,与史书条支城的地理特征相符。塞琉古王国全盛时辖有西自埃及、东到印度河流域的地区,这个广阔地域内的气候与出产的动植物与史籍条支国气候、物产相合。塞琉西亚与条支国亦有不合之处,如条支国“海水曲环其南与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而塞琉西亚城地形特征则是海水并未环绕其城东、南、北三方,城东、城西深谷与海面限制东南西三方与外界交通,仅在东北角有条小路可通。二者之不合,宫崎市定认为条支国或根据传闻而录,与实际情形当有误差。
简言之,宫崎市定以中国到地中海的陆路交通线否定前人观点,又以塞琉西亚与条支大体相符断定塞琉西亚当为条支。笔者以为其论证方法的确新颖,论证过程又有欠虑之处:
其一,除宫崎市定列举三条交通路线外,另有一条与条支国地望联系密切的路线,即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前揭东汉时期条支位于安息都城泰西封的西南方向,宫崎市定主张条支国在塞琉西亚,则远在两河流域西北,藤田丰八主张法尔斯则在两河流域东南,二人之说值得商榷,夏德、白鸟库吉考证的条支地望具有一定合理性。
其二,公元前64年罗马帝国攻陷塞琉古王国(时仅辖叙利亚地区,都城安条克亦在叙利亚地区),直到公元640年叙利亚地区一直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汉纪》《后汉书》均提到和帝永元年间(97年)甘英亲抵条支,倘若如宫崎市定之言(条支即安条克外港塞琉西亚),则甘英到达大秦领地,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后汉纪》《后汉书》均载安息船人讲述自安息西界乘船到大秦善风则需三月、迟风则需二年,“英闻之乃止”,“具闻其土风俗”,可见甘英并未到达大秦国。
笔者以为条支国史料应分作两类:①《史记》条支国史料系张骞闻听之言,《汉书》全袭之,二书条支国史料归作第一类;②《后汉书》条支国史料增加地理特征及乌戈山离、条支、安息三国之间路线,当是甘英亲临而获,可归作第二类(不含转抄《史记》气候、物产史料)。即条支国史料来源过程经历西汉时传闻、东汉时亲获两个阶段,其地望因时代不同、史料来源方式不同可能分指两个地区(亦不排除指同一地区):西汉时条支地望笔者不敢臆断,东汉时条支当在两河流域南部某地。考证条支地望,不妨先将《史记》《汉书》条支国史料与两河流域印证。若二者相符可证两汉条支国地望相同,二者不合可求诸于其他地区。条支地望既明,西海指何处则昭然若揭。
[1][13][14][49]夏德.大秦国全录[M].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5,964,30,20-21.
[2]龚骏.甘英出使大秦考[J].东方杂志,1944,(8):23.
[3]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论甘英之西使[M].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434.
[4][15][19]莫任南.甘英出使大秦的路线及其贡献[J].世界历史,1982,(2):14,17-18,15-17.
[5]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J].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1):82-86.
[6]班梁列传[A].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C].北京:中华书局,2006.1575,2917,2931.
[7][22][25]西域传[A].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C].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张绪山.〈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段希腊神话[N].光明日报,2006-03-21.
[9]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1.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9.
[11]余太山.关于甘英西使[A].国际汉学(第3辑)[C].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257-263,
[12]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A].饮冰室合集(第六册)[C].北京:中华书局,2008.14.
[16][21][26]孝殇皇帝纪[A].袁宏.后汉纪(卷十五)[C].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302,301,302.
[17][31][35][36][39][40][42][47]西域传[A].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C].北京:中华书局,2006.2931,2910,2910,2918,2910,2910,2931,2918.
[18]龚骏.甘英出使大秦考[J].东方杂志,1944,(8):21.
[20]杨共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新探[N].光明日报,2000-10-13.
[23][24][46]西域传[A].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C].北京:中华书局,2013.3882,3882,3888.
[27]颜世明,高健.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 —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29-130.
[28]颜世明,高健.浅析〈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西域史料价值[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82.
[29]班梁列传[A].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C].北京:中华书局,2006.1582.
[30]袁宏.后汉纪·序[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
[32]释法显.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6.
[33]智猛法师传第九[A].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C].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579.
[34]河水[A].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卷一)[C].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4.
[37][41]孝殇皇帝纪[A].袁宏.后汉纪(卷十五)[C].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300,300.
[38]秦汉史[A].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1.
[43]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M].马小方整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97.
[44]乌丸鲜卑东夷传[A].陈寿.三国志(卷三十)[C].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861.
[45]大宛列传[A].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2010.3163.
[48]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9-203.
[50]宫崎市定.条支和大秦和西海[A].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民族交通[C].北京:中华书局,1993.385-413.
[51]余太山.条支、黎轩、大秦和有关的西域地理[J].中国史研究,1985.5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