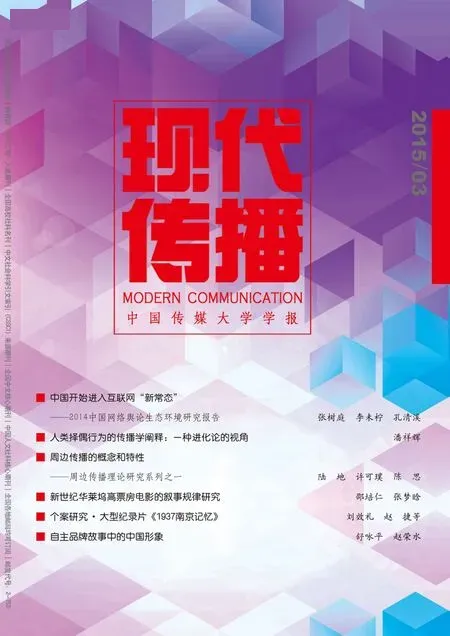《个人影响》对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应用研究
2015-02-20严功军
■严功军
《个人影响》对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应用研究
■严功军
传播学经典文本《个人影响》关于群体对传播效果影响的理论解释资源,实际上是对芝加哥学派首属群体理论的借用。这种被称为再发现的借用,由于研究范式不同造成了严重的理论误读,体现出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的固有缺陷,同时也反映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首属群体;再发现;误读;重构;芝加哥学派
“迪凯特研究”与《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MassCommunications,1955)作为哥伦比亚学派传播学经典研究和经典文本,一直被学界广泛关注。学者米尔斯在其享有盛誉的《社会学的想像力》第三章,深刻评述了以《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等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2006年11月,《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刊》专门推出题为“政治、社会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重读《个人影响》”专刊,21名学者从多个角度评析《个人影响》的学术地位和研究路径。本文从《个人影响》的理论解释资源入手,讨论其对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应用,指出该研究借用库利提出并由希尔斯给予深刻阐释的首属群体理论,揭示了其在信息流动与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实际上是对该理论的误用。这种误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哥伦比亚学派行政功利性的控制研究立场。应该看到,就当代中国传播研究而言,承载亲密关系的首属群体较之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首属群体阐释更具启示意义。在社会流动和多元化网络社会时代,中国传播研究需要对芝加哥学派价值取向与社会立场重新认识。探索以首属群体亲密关系为模型,建构“伟大共同体”的社会传播学路径,成为重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价值的重要维度。
一、《个人影响》研究与出版的复杂历程
“迪凯特研究”自1942年开始酝酿,1945年进行调查和资料收集,直到1955年才以《个人影响》为题得以出版,成果来之不易。在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面临三个问题:一是经费问题。战争年代经济发展动荡,靠外来资金援助的应用社会研究所运转困难。“用下一个研究的资助支付上一个研究的赤字,成为研究所生存的方式”,①项目资金筹措难度可见一斑;其次是人员组成的问题。由于经费困难、社会发展不稳定以及研究视角分歧等原因,许多参与迪凯特项目的合作者经常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②项目聘请学生来完成调查也遭到质疑,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项目的进程;最后,影响出版更重要的因素是项目研究满足资金赞助者商业利益要求与体现学术理论价值的矛盾问题。“由于研究所费不菲,其实践者往往使其研究涉及商业与科层管理的应用……,重视研究方法,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理论和原则来指导如何选择研究主题。”③米尔斯上述对抽象经验主义不留情面的批判,集中反映了各个研究项目面临的这一突出矛盾。迪凯特研究是由麦克法登出版公司资助3万美金完成的,意味着研究结果也必须为该公司服务,其在“测量方法”方面的成熟同样不能克服其理论断裂的固有缺陷。
正是因为对迪凯特项目理论依据矛盾问题的分歧,使得项目成果的作者选择变得十分复杂,也使成果出版耗时10年。迪凯特研究最早由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主持实地调查,并撰写了长达300页的报告初稿,但这个报告因没被拉扎斯菲尔德接受而最终丢失。之后,还有包括默顿在内的多人都试图为迪凯特研究撰写结果报告,但都没被认可。④《个人影响》作者选择之谜折射出拉扎斯菲尔德工具性研究路径所引起的广泛争议,特别是他与米尔斯的冲突问题。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把米尔斯在做迪凯特研究时,关注并搜集自己感兴趣的社区领袖权力问题的资料,忽略对于调查样本进行技术监督作为其最终被解雇的原因,但更为强调的却是二者在学术视野冲突方面的因素。⑤作为一个批判社会学家,无论是基于米尔斯反权威的倾向或者其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他和拉扎斯菲尔德“重方法、重实用与重政府、工会、公司利益维护”的研究旨趣有着根本区别。他不能作为作者,其写的调查报告不被接受也在情理之中。
二、再发现:《个人影响》研究理论依据问题的解决
当然,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经验研究者们,不会无视社会学界对他们研究路径的争议和批评,这也使得为经验研究成果写几章序言(或者称之为“文献综述”),作为调查报告意义构建基础成为趋势。⑥10年成稿,拉扎斯菲尔德一直致力于思考和寻找《个人影响》的理论依据。他和他的合作者卡茨,最终找到了“首属群体”这一经典社会学理论,并在成果出版前两年,花了近半时间来进行小群体与大众媒介和个人影响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个人影响》第一部分内容。他们把这一理论的应用称为首属群体理论的“再发现”。⑦
根据学者杰弗逊·普利(Jefferson Pooley)的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对首属群体理论的再发现,一方面受其负责的多个关于有限效果实证项目研究的启发,但主要是受到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关于首属群体研究的影响。1948年希尔斯所著的《美国社会学之当下形势》,已经对首属群体研究进行了讨论。1951年,希尔斯撰写《关于首属群体的研究》论文,系统地论述了首属群体理论作为本土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再发现问题。⑧
同时,关于首属群体理论再发现的应用研究,希尔斯与贾诺维茨1948年合著的《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团结与分化》一文,成为战后“传播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⑨该文提出为什么纳粹德国军队在战略和军备都比盟军要差的条件下,乃至最后德军被击溃,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却总能保持高度一致的组织纪律性和较强战斗力的问题。并指出,人力、装备缺乏,运输不畅,包括战略失误,都是影响战斗力的有限原因,军人政治信仰影响也不大,反而是其所属的小群体能否给军人提供基本需求,群体领导是否得到认可,群体成员是否相互支持、信赖等成为确保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士兵为群体的整体性而战,为群体内其他军人而战。⑩这些振聋发聩的结论无疑会对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拉扎斯菲尔德受到希尔斯影响的有力证据是他1948年在奥斯陆举行讲座所谈的内容。这场并不起眼的讲座聚焦小群体,内容主要来自希尔斯《美国社会学之当下形势》和“纳粹德国国防军”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在讲座中把希尔斯关于纳粹德国国防军的群体研究作为经典案例引证,明确指出社会学家发展了小群体理论。在《个人影响》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首属群体“再发现”时,也以注释的方式申明受到了希尔斯论述的影响。(11)而在1975年,希尔斯在回忆中也明确表示,《个人影响》借用了他的研究假设。(12)
众所周知,首属群体理论是库利提出的美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传统经典理论。而希尔斯作为当代美国有影响的社会学家,正是受聘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做研究助手后,才从此成为著名的社会学教员的。他与芝加哥学派学者学术师承关系,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和教授社会学的数十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在小群体研究、“传统研究”等领域体现出的理论与人文探索精神,对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的历史承继性、多元性、复杂性充分认识的学术研究旨趣等(13),都使他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因此,拉扎斯菲尔德对希尔斯学术研究的再发现,虽然“巧妙”地解决了《个人影响》理论依据的问题,但也使自己的研究与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发生了联系,变成了对“业已衰落”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应用。《个人影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凭着其对传播人际影响与有限效果论的精到叙述而深入人心,成为传播研究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
三、作为解释资源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及其误读
首属群体理论实现了《个人影响》把“枯燥的调查数据转换成具有原创洞察力观点”(14)的目的,为其带来了广泛的学术声誉。然而,拉扎斯菲尔德对首属群体理论的应用,其主要的内涵阐释却与该理论本身有较大偏离,其路径也是经验性和操作主义式的。
《个人影响》对群体理论的应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强调共享规范的问题。通过互动、讨论(人际传播)形成群体规范,对个体产生群体压力,促使其做出相似选择;同时,群体规范也是一种动力,推动合意选择的形成,制约外来信息劝服效果。个体是否参加群体、接触频次、以及群体联系的紧密程度,都会影响个体选择行为。第二是存在人际传播网络及其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不同群体结构、群体氛围、群体共识与凝聚力,人际传播发挥的作用不同。群体信息主要由低层向高层流动,个体层次越高,会有更多的人寻求与之交流,高层个体也倾向于对群体发言。不难看出,《个人影响》对这两方面的详细阐述,主要还是服务迪凯特实证研究,服务两级传播与意见领袖理论,最终证明大众传媒有限效果结论。这种机械地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赋予其意义”的努力(15),很容易造成对理论本身内涵和作用的“炮制”应用和误读。
第一,芝加哥学派的首属群体理论,把该群体当作社会系统的最基本子系统和结构组成。这种“通过亲密的面对面的联系与合作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微观上是自我形成和人社会化的基础,从宏观上则是传统社会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16)体现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部落式发展形态,并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内涵和作用的变化。因此,芝加哥学派的首属群体理论,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发展的进程,从社会整体角度思考这一群体对个体和社会本质影响,体现社会学理论建构和应用的历史延续性。而《个人影响》的群体理论,则是脱离了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对“群体规范的影响作用”以及“群体中人际传播与意见领袖作用”预设式、个案式、断裂式的应用,根本谈不上理论建构。
第二,就传播与群体的关系理解而言,芝加哥学派始终强调传播对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长期的巨大作用。人的自我离不开传播,传播先于自我的形成;社会的本质是交流互动,传播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传播技术变迁影响社会文明发展。即便是关于首属群体弱化的问题,库利也把它归因于交流方式的革命(17)。也就是说,传播是自我、群体和社会形成与变化的前提,从历史延续与宏观整体上看作用无可替代。而在《个人影响》中,传播与群体关系却被简单地因果倒置。在迪凯特以及其他诸多被应用的实验个案中,群体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被多次“科学”地验证,大众传播的效果变得有限的结论也应运而生,成为普适性的规律。显然,这种强调短期与个案效果影响的研究理念与芝加哥学派始终坚持传播巨大社会作用的思想是相悖的,其结论的科学性也是饱受质疑的。
第三,从传播的特征来看,芝加哥学派始终强调群体与社会中的传播是多次互动和长期进行的,自我、意见或态度都是在互动中逐渐生成的,不是一次完成,且非常注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互动中微妙、复杂的心理过程,注重个体对群体和社会的建构作用。而《个人影响》群体中的传播则是机械的、分层的、被动的、简单的,是可以设计和科学计量的。个体是被测量和劝服的对象,是刺激反应模式中对他人的遵从和从众。在这种观点下,作为首属群体概念里主体参与传播过程的意义完全消失了,群体传播的多元性、复杂性、变化性也被解构了,变成了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简单量化因素。
第四,从群体的特征看,不同群体结构和功能不同,有不同的类别。芝加哥学派的首属群体类别特征十分鲜明,强调这一群体是“小群体、面对面传播、角色多元互动、突出个性、难以替代、交流富于感情、整合程度高”等等。而迪凯特研究调研妇女关于“购物、时尚、看电影、公共事务意见”四个方面的内容,其所涉群体的范围是模糊的,只是笼统地描述个人会受到群体压力影响,至于受到什么样特征群体的影响均未说明。虽然《个人影响》把迪凯特研究调查的对象解释为小群体/首属群体,但我们却很难感觉到这个群体有像首属群体一样具有那种特有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心理。首属群体的基本要素在《个人影响》中忽略不见,足以说明其对该理论应用的简单、机械,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粗暴的。
总之,分析表明《个人影响》对芝加哥学派群体传播理论的应用,是典型的误读。这也使得《个人影响》主要以其定量研究方法获得学术地位,其借用并再发现的群体理论,根本不能产生任何理论范式固有的历史与现实启发价值。而首属群体作为经典社会学理论,其理论本质内涵固定,又兼具延伸性、启发性。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代社会,都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促使我们反思不同社会语境下这一群体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作用和功能的变化,并由此采取不同的社会应对策略。
比如帕克、沃斯等进行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关注都市化进程所导致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造成社会异质和首属群体功能弱化等问题,都和首属群体理论有紧密联系。而在当前移动传播时代,传媒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途径,首属群体以何种形式存在,其作用和价值如何体现?兼具人际、群体、大众传播特征的微信传播,构建了什么样的群体形式,将对社会群体构成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我们都可以从首属群体理论得到启发,去深入思考并开拓出新的理论阐释空间。
四、价值重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现实应用
《个人影响》对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误读,体现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在传播研究范式上的根本不同。客观地说,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通过个案调查统计分析得出了系列具有一般规律性的、影响传播效果的结论,直接体现了传播研究对政府、组织机构和企业的应用价值,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其重要价值和合理性。但是,就人类悠久的传播历史、丰富的传播形式和内容而言,哥伦比亚学派大大窄化了传播的研究领域,以致贝雷尔森1959年就提出“传播学已死”的断言,揭示了这种不断重复的量化研究的危害性。同时,抽象的量化研究,并不能真正反映经验世界的本质,不能阐释个体、社会、传播三者之间复杂、多元、变化的本质关系是其更加致命的弱点。它所反映出来的冷冰冰的科学研究范式,与充满人文精神甚至生命哲学体验的人类传播显得格格不入。
反之,芝加哥学派致力于探讨传播与人的本质、传播与社会变迁等根本性问题,注重动态的、长期观察式的经验研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知识传统中,首属群体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分析单位,更重要的是,它因血缘、地缘因素的面对面传播亲密关系而具有深刻的规范意义。首属群体作为一种人类联结方式,在根本上区别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多元化、去中心化,其自身具有抵制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疏离、社会共识涣散等社会问题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杜威、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或哲学思考才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将空间广大、内涵异质的现代社会改造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也即如何在这种社会中重建某种接近于首属群体亲密关系的现代社区。哥伦比亚学派学者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观念的流动,需要了解这种流动的社会反应,进而在一定的时空之间实现对公众的态度、行为控制,芝加哥学派学者则认为传播是交谈、对话和对共同生活的参与,是大范围里“类首属群体”关系的重建。
为此,我们认为,芝加哥学派传播理论始终保持着创新的生命力与研究的想象力,更接近人类传播的本质内涵,更契合传播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分析《个人影响》曲折出版原因,厘清其理论来源,指出其误用首属群体理论,并批判认识哥伦比亚与芝加哥两个学派传播思想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研究价值,以关照新的传播问题,拓宽传播研究与应用的领域。
比如在大数据传播时代,当所有传播都变得可以量化,所有传播研究都因数据分析而日趋科学化,传播控制似乎变得轻而易举让许多人欣喜若狂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传播虚无与焦虑,应该如何实现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平等对话与反思“现代社区与公共领域”重建等问题。比如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传播形式急剧变革,使得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基本命题受众、效果等概念,越来越因为用户参与性增强、媒介中心崩塌而失去了落脚点;全媒体用户的交往、生活方式与关系模式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影响问题等。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范式,其知识传统不仅仅有着其作为解释性资源的功能性意义,它本身就是理解和研究当代传播问题的必要途径,这对于探寻中国社会传播问题解决的科学策略,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大科研项目“芝加哥学派新闻传播思想研究”〔项目编号:SISUZD201201〕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⑤[美]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29-330页。
②⑦(11)Katz,Elihu,and Paul Lazarsfeld.Personal Influence: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Glencoe,Illi:Free Press,1955,p.7,p.34,p.37。
③⑥(15)[美]C·怀特·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9-71、69、69页。
④Simonson,Peter.“Personal Influence:The Book and Its Peopl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608,2006,p.15;Pooley,Jefferson.“Fifteen Pages that Shook the Field:Personal Influence,Edward Shils,and the Remembered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08,2006,p.149.
⑧⑨(12)(14)Pooley,Jefferson.“Fifteen Pages that Shook the Field:Personal Influence,Edward Shils,and the Remembered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608,2006,p.139,p.134,pp.140-141,p.145.
⑩Shils,Edward,amd Morris Janowitz.“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Public Opinion Quarerly 12,1948,pp.280-315.
(13)希尔斯作为芝加哥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研究教授,其学术师承和学术研究旨趣,可从他的研究成果,如“Some Academics,Mainly in Chicago”“Some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The Study of the Primary Group”《论传统》等概括得出。
(16)Cooley,Charles H.Social Organization,Glencoe,Illi.:Free Press,1962,pp.23-30.
(17)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3页。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