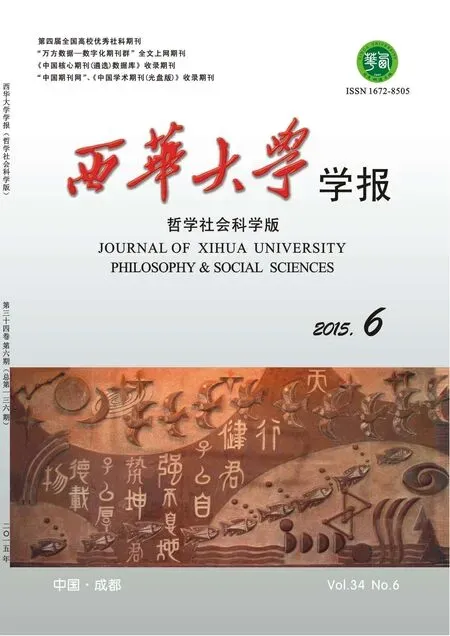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2015-02-20袁宝龙
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方统治思想——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于诸子争鸣时代发展成熟,成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秦汉之际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革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机遇。统一政权的出现催生了对统一意识形态的理论需求,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也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几经变迁,最终于汉武帝之世成为封建王朝的官方统治思想。本文拟就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求正于方家。
一、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制濒临崩溃。在这样的动荡年代,思想的碰撞却格外精彩,春秋时期的乱世也因此成为儒、法、道、阴阳等多种理论体系孕育成长的肥沃土壤。儒家学派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基本完成于春秋时期。
《周礼·大宰》载“儒,以道德民”,贾公彦疏称:“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1]40指明儒者是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班固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2]1728也指出儒学源于王官之学。儒家思想具体的源流以及产生的时间已不可考,不过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建以及儒家思想的体系化无疑完成于春秋之际,在此过程中,孔子的发起、首创之功无可替代。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周游列国,却终其一生未能如愿。不过他广收门徒,桃李满天下,此后儒家学派代有传人,故儒家思想得以代代传承,历春秋战国之世迄未中衰。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次则为“礼”,两者互相依存,支撑起儒学理论的整个体系。有关儒学的精义,自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的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还原儒学在秦汉时期不同阶段的地位变迁。
儒学在秦汉以后的影响力远超诸子之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仅是普通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已,其时代影响力远不能与当时的法、墨等学派相比。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从孔、孟两圣的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先后到达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但均未能找寻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他曾对老子说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3]450其中七十二君的说法当属夸张,但是在孔子之世,儒学未能引致诸国当政者的赏识却是事实。与孔子相隔百年的亚圣孟子,同样在学成之后周游列国,历至梁、齐、宋、滕、鲁等国,不过与孔子一样,孟子的政治理念也始终未获明君赏识,最后负憾而终。
史载齐景公悦孔子节财之政,欲封以尼溪田,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4]1911
孟子的遭遇与此类似。孟子周游列国“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4]2343。后人也曾作诗讽刺孟子之学唯重空论,不切实际:“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5]538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作为诸子之学的一个流派,从未被列国当政者采纳成为一国之内的官方统治思想。
孔孟的遭遇表明了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尴尬境遇,同时也揭示了儒学遇冷的内在原因。韩非子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6]1092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群雄争长,列国都在追寻富国强兵之术,而面对这种功利性需求,儒家思想显得陈旧迂腐且不合时宜。孔子问礼于老子之际,老子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4]2140而在孔子感慨自己的理论思想不为世上国君所赏识时,老子说道:“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3]450-451在传统礼制崩毁、诸国争雄的历史语境之下,仁义智辩殊非持国之道,所以孔孟二人均无机缘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儒家思想迄未能成为某一国邦的治国理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家之学历孔孟之后,在先秦时代的尾声,荀子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儒学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至为深远。对于荀子其人,清人汪中称:“盖自七十子之徒即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7]78他把荀子与周公、孔子并称,足见对其赞誉之高。郭沫若称:“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8]218如郭氏所述,荀子对传统儒学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创新改造,试图以伦理道德准绳为工具来完成现实社会中的国家构建,从这个角度来说,荀子的思想与孔孟之学并无二致。但是荀子以此为基础的诸多发展,却使儒学产生了从纯粹的理论层面向现实靠拢的趋向。比如荀子议兵、讲刑政等等,均与孔孟的传统儒学理念有异,却使儒学成为现实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荀子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建了万物轮回的循环宇宙观。荀子称:“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9]482这种宇宙观反映到春秋战国的现实社会,即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9]306-307。与孔子怀念远古的周公时代不同,荀子以轮回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承认王朝更替的合理性,儒学的政治倾向由因循守旧转为革故鼎新,这使儒学成为新兴王朝官方政治哲学的机率大增。这种转变的一个现实表现是荀子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西入秦面见昭王。秦昭王称:“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答道:“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9]117-120具体谈到儒学对人国之益,荀子认为,启用儒者可使“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9]121。
综而言之,荀子的儒家思想,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创建了万物轮回的宇宙观;二是从传统的理论教化转向讲现实功用性。这种变化极大地完善了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故而使儒家之学从普通的诸子之学成为影响力日著的时代显学。
李泽厚先生对此总结道: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处于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进程中。先秦诸子之学,或逐渐衰颓而至消亡,或始终活跃终于绵延而强大,名、墨属于前者,而儒、道、法、阴阳则属后者。儒家思想在历经曲折之后,日益融合其他三家,其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凌驾于其他三家之上[10]136。
二、秦国、秦朝的儒学发展情况
史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4]685,这表明了早期秦国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却在客观上使秦人易于摆脱旧法传统的困扰,通过彻底的变法而完成一统之业,这一点想来非六国之人所能预料。
秦穆公时,戎王使由余使秦,穆公与谈天下大事,问之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以为,中国之乱缘于黄帝以后之君“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而戎夷之治在于“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4]192-193。穆公以之为圣人,“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4]194。
西周亡于戎,而秦穆公灭戎,故秦国的地位在当时列国之中得到了极大提升。由余的思想近于儒家,只是未能如孔孟之学一样系统化和理论化。秦国能成就霸业,与由余的影响密不可分,这表明了秦国具备如下两个特点:对外来文化易于吸收;同时对于异文化的选择取舍具有极强的功利性。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故富国强兵之术,在秦国极易获得成功。
不过穆公之后,秦国的地位再度回落。“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至孝公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故孝公下令求贤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4]202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始有商鞅变法之事。
从孝公求贤诏中可见秦国君臣对富国强兵的渴望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式态度。商鞅变法确立了秦国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商鞅对儒学的看法自然也在影响着秦国官方对于儒学的态度,进而决定了儒学在秦国的地位高低。
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军国之路。尽管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身死,不过通过商鞅变法建立起来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却被秦国统治者世代延续。秦惠文王十年,以魏人张仪为相,由此引领了此后秦国以客入仕的历史高潮。据考证,自张仪入相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共计二十二位国相,仅一人明确为秦人[11]44。这一方面表明秦国法制化建设的深入,传统的世官制已经被摧毁殆尽;另一方面则表明秦国对于贤才能人的追逐起用早已摈弃了国别的偏见。后者固然与秦的传统有关,同时也表明了秦的文化政策具有兼容并包、功利色彩浓重的特点。
秦昭王时代,春秋战国之际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入秦,两人的对话前文已述,最终秦昭王对荀子之论颇加赞赏,这同样也在表明着前述秦文化政策的特征。不过当时,秦国以法而致强盛,这与荀子的儒家之学仍然存在极大差异。故荀子虽然称“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以此来肯定秦国的强兵之策,但是同时又称其“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认为“故招近募选,隆执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9]274-275,而以最强大的军队也不能敌“汤武之仁义”。
不过秦昭王善荀子之论,却表明了秦国对于儒家思想至少持不排斥的官方态度,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国理念其实是法制思想的深化。无论如何,在秦国统一前夕,秦国统治者与儒学的首度接触,势必影响着秦统一之后的治国理念。
实际上,秦昭王与荀子之会,固然是由于荀子主动西去,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以秦昭王为代表的秦国统治集团对于法家之外的理论思想主动求索的态度。当时秦国的发展已经领先于东方六国,历史底蕴不足的秦国欲在传统礼制崩溃的时代实现其帝国霸业,需要重新构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考虑到秦国以法而强,故这套理论体系必然以法家思想为根基,佐以他说,杂糅而成。
著名的《吕氏春秋》完成于秦国统一前夕,而这部著作对于统一后秦王朝的政治哲学取舍有着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集门客之力写就。关于其写作目的,元人陈澔如是说道:“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12]148也就是说,《吕氏春秋》的一个重大使命是为统一之后的秦国提供新的统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也表明了秦统治者对于新的政治哲学的求索追逐。换言之,《吕氏春秋》试图通过把诸家之学熔于一炉,创造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以之治国理戎,同时完成思想的统一,而后者更是秦国至秦王朝一直追求的目标。李泽厚先生指出,《吕氏春秋》自觉地企图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写作《吕氏春秋》的现实基础应该是在秦国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家传统的长久实践,但这个治国大方略中却保留了许多儒家思想。不过,《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与原始儒学相比,实则大有区别。前者具有服务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着法家精神。二者貌同而实异,正好标志着在新社会条件下新的统治阶级对原始儒家思想所作的具体改造和利用[10]136-138。
也就是说,在秦国统一前夕,无论从儒学本身抑或秦国统治者来说,两者均有通过对儒学思想的改造来提高其与现实社会契合度的需求,双方相向而动,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相距最遥远的两个对象走得越发接近。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力不高的儒家之学即将通过自我改造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秦的统一,则成为儒学地位徒然提升的历史机遇。
史称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4]238。关于他尚法之偏好,已属公论,本文无须赘述。在此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秦始皇的统治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辅以儒学、阴阳学等各种思想流派的新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和意旨与《吕氏春秋》极其神似。也就是说,秦始皇依旧信奉法家,但同时又吸纳了其余诸子之学中可为其所用的理论思想,比如引入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神仙家的神仙、方术之学等等,儒家思想由此首次被应用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之中,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命运因秦始皇而得以改变。
《史记·礼书》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4]1159这表明了秦朝在礼制方面的继承与革新。而早期秦国的情况却殊非如是,当时“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4]1857。从与戎翟同俗到整合六国礼仪,创建起文明国家的雏形,这都显示出儒学在秦朝政治生活中不断深化渗透的过程。
秦始皇至迟在统一之后建立了博士制度,“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4]1366。对此《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2]726尽管方士、儒生曾指责秦始皇“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4]248。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博士制度依然在秦王朝的国家决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议定统一后国君的名号问题,李斯、博士共与其事,又与儒生议刻石颂德、封禅山川之事等等。而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3年),咸阳宫会上,博士淳于越请“师古”[4]255。陈胜起山东,秦二世如博士诸儒生问应对之策,博士诸生始请发兵击之,二世不悦。叔孙通时为待诏博士,应以谀词,二世称善。而其余博士儒生中言反、盗者或下吏,或被罢[4]2720-2721。不考虑以上事件的最终结果,儒学之士在当时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是绝无疑义的。
由此可见,秦始皇在统一之后,首次使儒家学说上升为国家政治哲学的一部分,这是儒学地位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秦始皇努力开创全新的兼容式政治哲学;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士与儒学均表露出了为与政治结合而改变自身的意愿并且付诸行动。而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致其蒙上反儒的恶名,但实际上,他对于儒学的首度提携之功却往往被学界习惯性忽略。梁启超曾云:“盖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于儒教矣。然则学术统一与政治统一,同在一时,秦皇亦儒教第二功臣也。”[13]54-55
而儒学未能在秦代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一方面与秦尚法的历史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处于转变初期的儒学理念仍然与秦初集权思想有矛盾之处,两者的深度融合有待于双方做出更高层次的转变,这一任务则在数十年之后交由汉武帝来完成。
三、汉代儒学的发展
秦的统一局面仅维持了十五年。秦亡汉兴,以刘邦为首的汉室君臣也要面临新的政治哲学的选择。
前文已述,商鞅变法之所以彻底,与秦国宗法势力较弱有直接关系,这种现状也使得秦国统治者能够大开大阖地寻找新的政治哲学与统治思想而无所羁绊。《吕氏春秋》的问世表明了秦始皇对于一套庞大政治理论体系的求索,并使改良升级后的儒学首次上升到国家官方思想层面,只不过其地位远远不能与法家相比拟。
汉室则以布衣卿相开国,这种情况比此前的秦国更为特殊。刘邦出身市井,刘汉天下全无任何文化底蕴可言,所以其对政治哲学的选择上,视野必然更为开阔。对于汉初君臣而言,最直接的教训是,尚法的官僚制秦帝国二世而亡,这让目睹秦亡汉兴的汉室君臣印象极其深刻。
汉王朝对于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范围广阔,也做出了许多尝试。史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陆贾造《新语》。”[2]81刘邦的此种安排,即体现了对多种理念的开放原则,不过汉初在政治哲学的选取上更多地追求一种功利性,即能够在客观上使汉王朝的统治更为稳定。
实际上,真正可供选择的对象依然是儒、法二家。秦统一后地位显著上升的儒家思想,在此时地位继续有所提升,个中的原因在于,作为秦朝政治哲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家思想被认为是秦亡主因,那么理念与之相左的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自然因此得到肯定。
秦汉之际的大儒陆贾成为这一时期儒学的主要宣扬者。他对高帝刘邦总结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4]2699其所著《新语》称:“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14]17这体现出明显的抑法兴儒态度。
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层面的体现首先表现为汉初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选择上,汉初实行了与秦朝郡县制迥异的分封制,其目的是惩于秦以孤立无援而亡的教训。吕思勉先生指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于是有汉初之封建。”[15]50-51汉初分封其实是试图真正回到周朝的分封时代。关于分封制,学界有人指出,其实汉所继承的是楚制而非周制,不过至少从其思想上来说,这种分封制的理念更符合早期的孔孟之学,具有一定的儒学倾向。
但这种复古之举的失败结局也已注定。其失败不仅仅是由于集权帝国与郡国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重行周制,引发了对于汉代统治者皇权合理性的思考和质疑。叔孙通制礼,是儒家思想在现实功用上的又一次体现,它在形式上使刘邦具备了天子权威,但仍然未在理论上合理地解释刘汉皇权的合理性。出身市井的刘氏有何权威像当年的周天子一样分封诸国?这种思考自然会引发对刘汉皇权的质疑,以至于汉昭帝时,眭弘以天有异象而请汉帝行禅让之制[2]3153-3154。
不过总体而言,汉室江山的社会秩序当时已经初步建立,尽管皇权合理性的问题未能迅速解决,但是当时天下方经大乱,百废待兴,即便不认可刘汉皇权之人也无精力和能力进行实质性的质疑指责。
汉惩亡秦之弊,表现出一定亲儒远法的倾向,不过在汉初官方统治思想的取舍上,儒家之学依然让位于法家,其中原因大致如下。首先,尽管叔孙通自称儒家之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4]2722,可是汉初百废待兴,从国家治理与管理的实际效果来看,法家理念无疑更胜一筹;其次,尽管儒学在秦时上升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但其影响力仍远不及法家,故秦时法家人才之盛远胜儒家,经历秦末战乱后,具有法家背景的人才成为汉初官吏的重要来源。
以汉相萧何为例,有学者指出:萧何身上有着明显的法治倾向。作为秦王朝一名精明能干的县吏,他精于秦的法律条文,他所秉承的思想准则,正是秦的法治思想,是他作为前朝一名“文无害”的县主吏习之有素的法治精神。而萧何作为标志性人物,表明汉初在统治精神上,继承了秦朝尚法的传统[16]。
以上两点原因决定了儒家无法在汉初的儒法之争中获取先机,但纯粹的法家之盛也仅如昙花一现。萧何死后,曹参为相,标志着汉代的统治思想进入了黄老之学时代。黄老之学与法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黄老之学时代,法家并非真正式微,而是隐藏于黄老学说的外壳之内。“萧规曹随”,表明曹参肯定了萧何时期以法家为主的理念,只不过曹参时期纯法家的地位进一步衰退,变种后的黄老之学则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黄老之学在当时成为汉朝的统治思想,有其历史因素:一方面,黄老清静无为的意旨表明了统治集团休养生息的决心,希望籍此恢复国力;另外一方面,作为统一的集权国家,依然要依赖法家思想进行管理运转。所以兼具以上两个特征的黄老之学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黄老之学注定只是历史中的过客而已,原因在于,汉初百废待举只是短期内存在的事实,黄老之学更像是处于两种政治哲学的中间过渡状态。
黄老之术除了有利于恢复国力,也为学术思想的争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2]90,这标志着各种思潮可以自由发展,诸子之学开始了复苏的势头,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也使儒家之学有机会在与其他思想的交融中进一步完善自身。
汉朝的国力逐渐恢复,国家统治渐入正轨,关于皇权合理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于完整的国家政治哲学的需求问题也日渐开始凸显。文景年间爆发了七王之乱,暴乱的表面原因在于王国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刘汉皇权的合理性未得到圆满的解释,即便刘氏宗族内部也认为人人可为天子,更遑论他人。
汉武帝是汉代少见的有为之君,他征讨四方,建功立业。一方面,他需要提高对于帝国管理的行政效率,这是黄老之学的温柔法家所无法实现的;另外一方面,他需要进一步确认刘邦一系血脉皇权的正统性,这是即便传统法家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这就给当时的学术思想提出了时代命题,《淮南鸿烈》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淮南鸿烈》筹备于文景之际,于武帝即位次年完成。淮南王刘安集数千宾客,共撰此书,其目的“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17]700-707。《淮南鸿烈》以黄老之学为基础,把儒、法、阴阳诸家之学尽纳其中,试图重造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无论从成书方式以及成书理念,其都与《吕氏春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治史者也往往把二者并论。
武帝之世,汉朝的国力已经达于巅峰,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何从制度和思想层面予以巩固成为当务之急。王国势力被逐渐削除后,整个国家的管理权力终端尽归中央,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然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是亡秦的先例已经表明,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一元制指导思想无法支撑起帝国的后续发展。在以法家搭建的框架之内,必须要实以一种新的精神内涵,通过体用结合的形式,来达成目的。
一方面,强汉对于新兴政治哲学的需求日渐旺盛;另外一方面,汉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进一步的转化转变之中。在秦时能够作为官方的辅助思想,表明了儒学自我转化的成功,同时也在激励着儒学的进一步转化。
元光元年,大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面圣,这次君臣会晤无疑对于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2523
儒家思想即将因此而晋级为官方统治思想,这样的地位向为孔、孟、荀子以下儒者孜孜以求,直至董仲舒时代始能实现。而董仲舒的儒学理论则受前述《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精神的影响极其明显,两者均试图构建一种超越权术理论的思想,可以付诸当时实践的政治经济措施,为建构统一帝国的上层建筑提供理论体系。如果说《吕氏春秋》是建构这种体系的第一步,那么从逻辑上而言,《淮南鸿烈》则是第二个里程碑,董仲舒则在精神实质上承继了《吕氏春秋》开拓的方向,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最明确地把儒家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10]141-146。
董仲舒时期的儒学,比之先秦、秦代、汉初的儒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通过对诸子之学的吸纳,其理论体系相当庞大,而其对现实的关注也在深入。关于董仲舒的具体理论框架学人已经多有论述,此不赘言。在此我们强调的是董仲舒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理念,强调君权神授以及国家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高度统一,这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对于政治哲学的一切需求,通过君权神授解决了汉朝统治者皇权合法性的问题,通过对大一统理念的强化有效地实现了对民众精神层面的控制约束。纵然,汉武帝其实霸王道杂用之,法家思想依然在帝国的管理运转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已经升级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从而完成了从普通的诸子之学到官方统治思想的历史变迁。
四、结论
儒家之学源远流长,其在春秋诸子争鸣的时代迎来了首个黄金时期。不过,与当时风靡一时的法、墨诸学相比,儒学偏保守的理念无法在诸雄争胜的时代为竞逐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孔孟二人的失意是儒学不能与时世相适应的必然结局。功利色彩更浓、富国强兵效果更强的法学则在商鞅变法之后,成为秦国的官方思想。战国晚期的荀子推进了儒学的现实改造,使其与社会现实的结合渐趋紧密。秦始皇统一六国,成为儒学地位上升的历史机遇。在秦统一之后,儒家思想首度与国家政治生活实践相结合,儒学的地位比之当年普通的诸子之学有了飞跃性的提升。秦亡汉兴,在汉初学术复苏的风潮中,黄老之学营造的宽松学术氛围成为儒学吸纳自强的优质土壤。在度过漫长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朝统治者对于王朝政治哲学的需求愈加强烈,董仲舒的儒学则完美地解决了其所有需求,这要获益于自先秦以来,儒者出于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的强烈意愿而对自己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使其与国家的政治思想需求逐渐契合,进而使儒家之学在先秦、秦汉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与政治地位,并最终成为汉朝统一帝国的官方思想。而秦汉时期儒家思想这种历史地位变迁的影响却远不止于秦汉,而是持续于整个封建时代,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6]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 (清)汪中.述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8]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12] 陈澔.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
[1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 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 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5):79-85.
[17]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