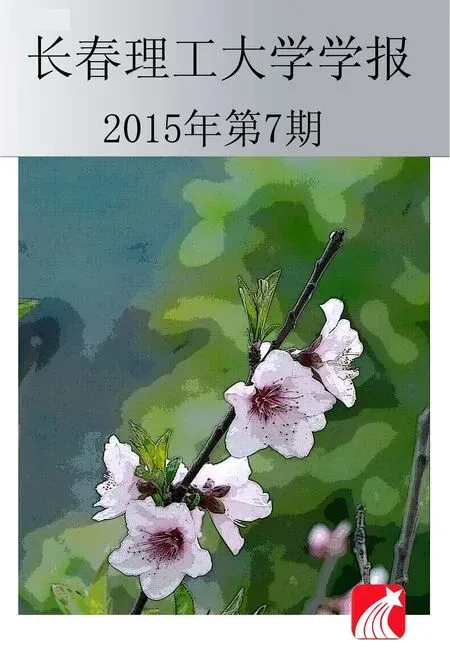废名小说“韵味”建构之管见
2015-02-20刘侃如
刘侃如
(吉林省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说,废名亦或当时的整个“苦雨斋”都是另类的,他们偏离战火、忧患,自觉阻隔哀痛,偏居一隅谈学养、畅文艺。在多数人看来,他们因避世是应被讥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苦雨斋”也臧否人物,偶涉时事,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时候沉浸在精神的宁静与淡漠中。作为“苦雨斋”的代表人物,废名自然承袭了知堂先生的“清淡朴讷”,但却又有所持行,其作品被后来多数论者称为“田园式”。他的作品里流露的是对乡土田园浓浓的眷恋,对宗法农村深深的体认。
废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影响,爱好魏晋文章,并多次表示:“愿学则学六朝文”。他偏爱陶渊明、庚信、杜甫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对李商隐诗、温庭筠词的理解颇具独到。废名中西合璧,在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剥离着对“诗化”的执着和“真实”的探究,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诗化小说”。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生生的字词,而是一幅幅充满了生气的诗画。有人曾说:想要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找本有趣的来打发时间,最不应选的就是废名小说。当然,他的大部分作品因为用字的精炼与构造的用心,难免造成晦涩、难懂之感。但正是因为如此,附和其文章中那未经斧凿的天真,才真正生成了属于废名的“韵外之致”。
一、以“纯粹”试探文明
废名对乡土田园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笔下到处可见宗法社会那淳良质朴的乡民,无不充斥着和谐的乡土风情,融合着温情的人性美。废名的叙述正是构建在这片充满着“原生态”意味的沃野之上的,尤其是在当时激进主义迸发的年代里,这倒显得较为难得。《柚子》中的表妹柚子稚气朴实,《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纯洁善良,《淀衣母》中的李妈慈祥仁爱——李妈疼爱着所有的孩子,村里的孩子也都喜爱有事没事往“茅草房”跑。而这份“疼爱”又是那么的“原始”,李妈恼了驼背姑娘,用力把剪刀朝地上一摔:“不知事的丫头!”责骂的直接,背后却是于命运的挣扎无力与对子女未来无望的叹息。《桥》中“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的“史家庄”集合了主人公所有的成长记忆,也融合着宗法乡村里人们的天真、和谐、温情与善良。其后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刻画了一段出离尘寰般的生活,缺少了诗的意味,倒存了些深沉的思索,所有的叙事都是围绕着那个叫“金家寨”的小村庄,“金家寨”虽然不及以往叙事中的村落超然,但它仍然承袭了废名一贯的创作风格,保有传统乡村的宁和、朴质……
“爱本来就不是由某一特定对象所‘引起的’外在的东西,而是隐含在人内心的一种缠绵之情,某一特定的‘对象’只是使它现实化而已。”爱应是长久积淀在主体内在“无意识”中的,“积淀”自然是指它的形成除了人体机制外,与一系列外在客体也有一定的关联,在某一特定时机借由能够激发的特定对象表现出来。黄梅给了废名以钟毓,而激进的现实则给了他“创造”黄梅最好的借口。或许很多时候废名创作之时正是处于一种所谓“成熟”的“无意识”,当然,这种“成熟”的“无意识”非等同于动物和婴儿的无意识。这种由内而外的对乡土田园的爱是无邪、纯粹的,在“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作用下,描绘着宗法乡村的一切文明与不文明。
《四火》中的王二嫂是个收生婆,“谁家的毛头生下地三天了,她又去,去把毛头洗得干干净净,拜天地、拜祖先。未拜之先,干净了以后,王二嫂一手握了两个鸡蛋:‘滚滚头,头戴顶;滚滚脚,脚穿靴。’这个毛头当然不是丫头。”《竹林的故事》于“送路灯”一段中讲说着:“‘送路灯’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连三天晚上,所有你的亲戚朋友都提着灯笼来,然后一人裹一白头巾——穿‘孝衣’那就现得你更阔绰,点起灯笼排成队伍走,走到你所属那一‘村’的村庙,烧了香,回头喝酒而散。”面对着生与死,废名并没有用浓重的笔墨来渲染温情热烈与沉重悲凉,而是纯粹而平淡地将其化作仪礼展现在读者面前任大家“观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在废名笔下也不少见:《桥》中小林与琴儿的婚姻是琴奶奶找媒人到小林家说的媒;《我的邻居》中么娃与细女是父母在两人还是孩童时就定了婚;《柚子》中“我”与妻子因为外祖母的媒介在襁褓中便把婚约定了;《阿妹》中阿妹出生后外祖母一听说是女孩就急忙跑来,说着已经托付别人探听了一个木匠家要抱养孩子做媳妇的话……封建婚姻在废名笔下没有过多的渲染,只是默默地流淌。《河上柳》中的陈老爹随口就唱“木头戏”、《桥》中南城脚下小伙伴们喜爱的“家家坟”、《阿妹》中给死去的阿妹“送乳”……废名就像是一个生性单纯、充满了好奇的孩子,用着一双干净的眼睛还原着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毫无顾念,将一切的文明与不文明都构筑的如此自然,于纯粹中构建田园之韵。
二、以“内倾”指示叙述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情感”始终渗透其中,即使作家极力撇清,采用所谓的“冷血”叙述。作家往往采用艺术的语言,对其情感的生理反应做出具体的刻画与描述,这就说明了在艺术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创作主体的个体因素。正因个体“情感”的不同,艺术作品则自然各异。朱光潜曾评论冯文炳“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内倾于自我,在创作中时常沉湎于自我想象。当然,这种自我想象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无论内倾型或是外倾型都是必要的。但不同的是,内倾型按照荣格所说:“主体是而且一直是一切兴趣的中心”,内倾者在同样的艺术创作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阻挠客体的影响,使个体、主意识与思维成为吸引一切的“磁石”,并使其以特殊的状态呈现出来。《柚子》在回忆中叙述着“我”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柚子之间那淡淡的道不明的情愫,随着儿时时光的流逝,因着祖母为我另缔婚约,两个人的关系便慢慢淡薄了。在“我”对柚子的回忆中,那一声声的“炎哥”无论是出自于柚子还是他人口中,都是使“我”沉迷的所在。我们在了解着废名的成长生活(或是幻想中的)时,于第一人称叙述中又感受着他的细腻、他默默于婚姻不自主的怨怼。《阿妹》中记述了“我”那短命的“阿妹”从生到死短短几个年头里所遭受的世事。因叙述着阿妹,“我”自然成为了叙述对象之一,而在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与《柚子》类似,情节的展开几乎都围绕着叙述者“我”的意愿为中心,于叙述者、被叙述者身上低吟着文章的“主旨意向”。
在非第一人称叙述中废名并没有规避作品中出现“作者的影子”,反而让读者深深地感受着作者就在其中,在参与或是见证着作品的发展。《桥》中虽然写的是“小林”和“琴子”的故事,但作者却偶尔跳出来晃一下:“我记得我从外方回乡的时候……我举头而看,伸手而摸,芭茅擦着我的衣袖,又好像说我忘记了它,招引我”“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走路,你的耳朵里仿佛有千人之诺诺”“我们有她在天禄山过生日的笔记可考了。”“我慢慢在那里画画,细竹今天格外打扮的好看”……,在“你”、“我”、“他”人称的变换游戏中叙述主体变得模糊,作品在时间与空间上有了一定的喘息,给了读者从其他角度审视作品的机会,而这种不顾忌语法的叙事策略不论精心与否,倒的确表现了作者“随意”的内倾。
废名多随内心感受行文,即使是现实确定的材料,他也会拿了来重新回炉提炼,随创作思绪的走向构造自己的“梦”,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在真实的“黄梅”感受相同的气息,却无法找寻到他作品中的任何行走痕迹。废名在《桥》中说过:“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有了梦才有了轮廓,画到哪里就以哪里为止”。他的作品中常表现人物非睡梦状态下内心思想及意识的自然流动。根据意识流作家和理论家的说法,人的知觉、情感、思维过程的某些方面总有不能用确定的语言来表达清楚的部分,作家只能把这些因素转换成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替代品”,以期能够尽量准确无误地表现这种意识状态。这样一来,没有了时空的正常秩序,传统的叙事也多少被颠覆了。当然,废名这种中国式意识流写法与西方现代意识流是不甚相同的,但他作品中人物语言的跳跃性倒初显了对这种手法的认可。
三、以“诗意”执着行文
语言本身没有形象,却具有描述外物形象、唤起形象感的功能。废名的小说漠视情节、语言跳跃,无论长短篇,皆以其“如诗如画”著称。“诗化”的背后是从人与物到景与情的转化,从“象”与“意”到“象外”与“意外”的渗合,是对小说意境创造的执着。废名的小说用字是节省的,这种用写绝句的方法来写文章的方式造就了小说意境的丰富。作为中国诗歌理论的核心概念,意境起于诗并兴于诗。但是随着文艺理论的发展,这一概念也逐渐地被应用在阐释除诗歌外其他文学样式中。“不是诗歌的小说并不存在”,即使在应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仍然讲求意境的开拓。
以宇宙人生为具体观照对象,主情于美的“意境”因不同地域之各因素表现不尽相同。中国之意境论旨在强调主体内在,强调主体的张扬、注重审美的领悟,抒写方面较为重视情感的体验,在漠视审美客体自然属性的前提下产生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融理与景、物于一身,使读者如临其境,并有所感。致力于和周作人一样写美文的废名于其作品中描述了诸多景物:翠绿的菜园、竹林旁的茅屋、桃园、红花、城墙、沙滩、万寿宫、洗手塔、城陛庙、五祖寺……组合出了一幅幅秀美的乡土田园画卷,于精致之中透露着他的执着:
《桃园》以王老大和他的女儿阿毛为中心,描写了园中的景色:墙砖上阴阴的青苔、园中叶子吹落了不少的桃树、月下的那三间比桃叶还要清冷的草房……组合出一种凄凉的氛围。桃树茂盛,却是来年,而今阿毛已渐消瘦;当初因爸爸酗酒而与他打架的妈妈已长眠于地下了;晚上月色很好,半个月亮对着大地倾盆而注,但却是让人打着冷噤的秋夜;这种凄婉的情调附和情境的发展:阿毛因病吃不下睡不着,只得张着眼睛,心里空空的,回着爸爸要吃桃子。王老大应着阿毛,拿了铜子换了瓶子,又用瓶子换了桃子,笑着回走却被玩耍的孩子撞到了将手里的桃子摔在了地上——碎了。原来,是个玻璃做的,这玻璃做的桃子的碎去,却也连着父女两个人的心儿碎了。在这样情与景的融合下,更加重了那凄清、哀婉的情调。
《菱荡》中菱荡圩上的陶家村有着优美的风景,有着古朴的民风,有着带神话色彩的历史……“落上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戏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它是那样的优美、富有诗意。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到参禅打坐,从斗士到隐士的生涯中,废名将对禅学的感悟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于诗意中塑造超脱。在那如宋元山水画般的陶家村里,陈聋子的塑造无疑将诗意推到极致。陈聋子遇见讨要萝卜吃完却说不好的,只是笑笑;见着得体的石家姑娘“牙齿都笑出来了”;陈聋子吃烟竿,二老爹因了他的聋而不啰嗦他……这一系列情节的发生看起来好似没有太大关联,直到文末,洗完衣服的两个女人对话着“张大嫂好大奶”,“我道是谁——聋子。”聋子看着水,自语着“聋子!”这种震惊,似在告知读者一直追究的答案,又似在低低陈述着一个既定的事实。将文章推到了更高的审美意蕴上。“无念”、“无相”、“无住”,恰是陈聋子的超然。在鲁迅等人看来,废名的作品“有意低徊,孤影自怜”。当人的外在物质生活一旦在社会上受到挤压或排斥,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要么放弃,废名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而已。选择于“纯粹”、“内倾”、“诗意”的路上默默流淌着自己的“韵”。
[1] 吴中杰.废名·田园小说[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 北京鲁迅博物馆.苦雨斋文丛·废名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5]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 埃里希·弗罗姆.周洪林校.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