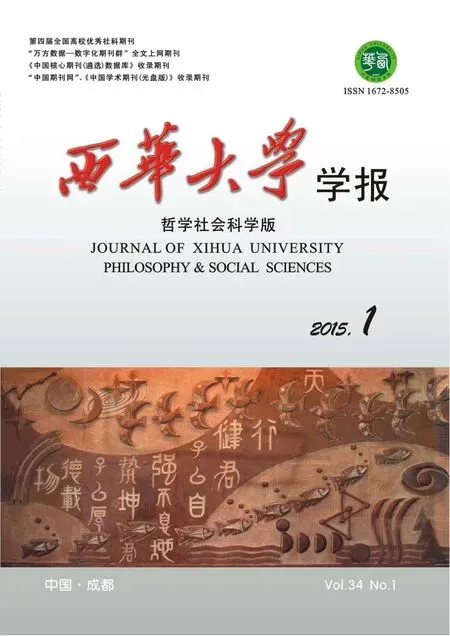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
——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2015-02-20谢桃坊
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四川成都 610071)
·中国文化·
文化现象的逼视与衡量
——论李安宅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开拓
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四川成都610071)
在中国近世人类学发展史上,前辈学者李安宅引入了英国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其著述涉及社会学、意义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广阔的领域,但他是借助各学科知识去透视、分析和衡量人类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他译介和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以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以及他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成就,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他的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现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尚有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李安宅;马林诺夫斯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实地研究
文化人类学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新兴的学科,它与社会学和民族学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部分的交叉;它们均注重实地工作方法,然而它们又各自保持着独特的学科性质。前辈学者李安宅(1900—1985)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又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两性社会学》,学界遂以为他是社会学家。他于194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边疆社会工作》,又于1941年完成《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学界则以他为民族学家或藏学家。因此他的学术定位被认为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和藏学的开拓者之一”[1]序,1。纵观李安宅的全部著述,其治学范围虽然涉及社会学、宗教学、意义学、语言学、美学等学科,但它们构成一个系统,其基本理论、对象和方法则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自1934年《意义学》与《美学》出版之后,李安宅自述:“作者是更钻研了人类文化学,且于内地与边地进行了比较长期的实地工作,结果可以说,对《意义学》与《美学》的背后条件—情感语言与思想语言的社会学,比较多了一点心得。”[2]这表明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意义学和美学的文化深层背景的,而且此后进一步研究文化人类学了。李安宅的著述及译著均对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开拓之功,可惜学术界在回顾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概况时,仅谈到“李安宅译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36)”[3]。兹试就李安宅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的逼视,及其实地研究成就略作述评,以期重新评价他在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中的历史意义。
一
李安宅的学术思想受到二十世纪初年英国两位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吕嘉慈的重大影响。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984—1942)是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为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倡实地调查,将一切社会现象置于整个人类生活系统,以考察其文化作用。李安宅于1926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留校工作,于1928年将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著作《野蛮社会里的性及抑窒》改名为《两性社会学》译毕,次年又将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译出一部分。剑桥大学教授吕嘉慈(I.R.Richards)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均有成就。他于1930年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讲授文艺批评,此年秋为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讲语义学与文艺批评。李安宅根据吕嘉慈的语义学和美学著作,和吕氏指定有关参考书,著成《意义学》与《美学》于1934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出版。李安宅在燕京大学期间学习和翻译马林诺夫斯基与吕嘉慈的著作,并吸收了近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人类学理论。
关于人类学学科的兴起,自然可以追溯到西方希腊时代,但真正的渊源是文艺复兴时期。这时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新大陆发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向外殖民,学术界开始关注殖民地落后的异质文化。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ie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发表,其进化论成为现代人类学的科学基础。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异质文化的关注而进行科学的考察与研究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然而在西方诸多人类学著作中基本上避开了其历史背景的本质性的论述,例如1979年美国出版的《社会科学新辞典》对人类学的解释是:“它深信有可能存在一门在生物、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综和研究人类的科学。从整体来看,人类学的范围是无限广大的;从时间上讲,它的研究要从人类最初出现在地球上开始;从共时的角度讲,它要从各方面来研究一切社会,特别是研究在习惯了归类为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的社会。人类学继承并保持了欧洲人在文艺复兴后的意识,对最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的起源及意义展开研究。”[4]这里提到的人类学重点是研究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及新发现的各种民族,已暗示了此学科兴起的历史背景,其性质和研究对象已区别于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国学者林惠祥于1934年谈到人类学的兴起说:“近代则因航海术进步,地理学上的‘大发现时代’开始,世界交通大为繁盛,各民族间接触的机会甚多,种族间的关系日密;于是先进的民族希望知晓异族的状况——特别是野蛮民族的状况——以为应付。经过无数次调查探险的结果,发现世界上种族的复杂与风俗习惯的歧异:东方与西方的不同,野蛮的与文明的更有异。……这些问题很能影响于实际的种族关系以及现代文化的进退,因此很被近代的人所注意而欲求其解答,于是人类学的研究遂应运而兴了。”[5]这也是对殖民性质的淡化处理。1935年李安宅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译者序里简明而精深地对人类学阐释说:
人类学在历史发展上,一面与考古有关,一面与殖民经验有关。英、法、美各国所以发展了人类学,便是因为各有各底殖民问题。因为殖民地底实际要求而有异种文化底研究,这异种文化又偏是经济落后的,所以这种研究便是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原始社会的科学,而原始社会便是经济落后的社会,并没有旁的意思。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一切经济落后的社会,是再对不过的。[6]译者序,3
此应是关于人类学的定义,揭示了其真实的性质。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而形成了许多分支,如种族人类学、体质构成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物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人类学等等。李安宅吸收西方学界的意见,从研究对象将人类学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他说:“体质人类学有人体测量一部,因为测量可有数字可记,似乎有科学的尊严,所以一般人听见的人类学不是考古就是人体测量。……体质人类学乃是以群或型为单位的生理学,前途虽无限量,可是专门得非一般人所可理解——非生物学专家且兼具人类趣味者不能理解,所以现在一提到人类学,与以前相反,不是体质人类学,而是文化人类学。我们心目中所要提倡的人类学,便是文化人类学。”[6]译者序,3-4在文化人类学中又分为两派,即进化学派和功能学派。进化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美国摩尔根(Lewis H.Morgan,1818—1881),是此派代表人物,其《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他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属于此派。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清末已有译本,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在1949年前已有两种译本,因此进化人类学派在中国学术界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此学派在西方受到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的批评,力图否定其社会发展阶段论。李安宅是崇尚功能学派的,他也批评说:“恩格尔(斯)一派则为一般左倾思想家所宗守。他们所宗守的典籍是恩氏底《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884年)。这本书则根据莫尔根(摩尔根)底《古代社会》(1887年)。莫氏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发现家底变迁也合乎演化论,于是给十九世纪的文明供给了理论的根据。这一派的失当处,乃在误认特殊过程为普遍的演化阶段。马林懦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所批评者尚不止此。”[7]注四a,7李安宅接受功能派的学说,特别将马林诺夫斯基的两种著作译介入中国,这显然意在与进化论派抗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安宅在中国人类学史上被忽略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被公认为功能主义这一理论方面的重要人物。他的一条功能主义的原理是:文化的各个部分不仅是联系的,而且是整合为一个相连贯的文化体系。”[8]李安宅译介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里的性及抑窒》入中国,他认为:“中国是个父权社会,且是比西洋更严格的父权社会。在现在这种家庭形式正在转变的当儿,亟有将这本著作介绍到中文读者底面前的需要。”[7]译者序,5他译介《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目的则是:“因为这本书是在直接提倡(实地工作)这种方法。著者在西洋的学术界已是大声疾呼,在素来不重实学、不重实地经验的中国,更有加紧提倡的必要。”[6]译者序,5此两著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李安宅希望因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中国文化。他说:“人类学所关心的比较,不但中国本身人群众多,文化复杂,是极丰富的园地;而且中国已成了各文化底聚会地,在这里考察文化接触的现象,适应的过程,变迁的辙迹,推陈出新的可能,在在都是启发……人类学所关心的功能,在中国这样处处需要重新估价的时候,正是要问功能所在,而用不着徒事中外新旧等空名之争辩。”[6]译者序,4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价值衡量与文化选择,在长期的争辩中并未使诸多矛盾关系得以解决。李安宅试图从文化功能的观点对中国文化进行逼视,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
二
在译著的序言和注释以及专著和实地考察的报告里,我们可以见到李安宅以文化功能为标准来逼视、分析和衡量“中国本位文化”。因他观察中国文化的观点与方法的不同,其许多文化批评的意见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将世界的其他不同民族称为“野蛮人”,而以自己高级社会的“文明人”,这是“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摩尔根曾在《古代社会·序言》里说:“我们想要知道:人类是怎样度过已往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时代的?蒙昧人是怎样以慢得几乎觉察不出的步伐前进,而达到野蛮社会的高级状态的?野蛮人又是怎样经过类似的渐进而最后达到文明社会的?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别的部落和民族在进步的竞争中成了落伍者——有些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些停留在野蛮社会,而另一些则停留在蒙昧社会?想知道这些问题的愿望不仅很自然,而且也很正当。”[9]他正是按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这显然是由本族中心主义发展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功能派的人类学家是持文化相对论的,以为每一种文化必须以该文化的立场来理解,各种文化只存在不同,而无优劣之分。中国封建王朝对周边的邻国,中原汉族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均存在本族中心主义的态变。李安宅是持文化相对论的,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族文化至上论”,以为:“在‘本族文化至上论’的社会看来,只有他们可以代表文物制度,他们是天朝,是中土,其它一切都是蛮夷,都是外邦。……这种不客观,而以我执为蔽的办法,当然是不会齐物等观的。多亏了心理学与人类学底进步,我们才知道蔽而不明的情形是到处一样的,谁也瞧不起谁,谁都是惟我独尊的。”[6]59本族文化至上论是由狭隘的文化观念所造成的蔽障所致,它不是对文化客观的态度。在中国进行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必须抛弃这种本族文化至上的观念,否则难以进行实地工作的。由本族文化至上观念,必然产生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分,即中原与边疆之分。关于中国边疆的界定,李安宅说:“我国正统文化为以农立国之文化,惟因地理之限制或人工之未尽而未至农工阶段者,其区域吾人率以‘边疆’目之。故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牧畜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因此,我国之东北、西南、西北各方面在文化与国界双重意义之下,共可称为边疆之区域殊多。”[10]151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观念,所以他深感:“对于边疆,我们已经有的,与其说是认识,毋宁说是误解,是偏见。”[10]153中国的思想方式是灵活而不精密的,例如“气”、“性”、“道”等基本概念难以确切的解释,但它们却成为某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某种学说更缺乏逻辑的系统。李安宅说:“中国一切思想,不管是伦理的、艺术的、巫术的,都非有玄学上的根据不可。不重分析,不易彼此传递知识在此;容易弄得不可捉摸,以致混混沌沌,吃亏处在此;然在会心所及,想得通,走得圆,大而无当,小而无间,妙处也在此。”[6]63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具有一些神秘的色彩,李安宅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
儒家经典《仪礼》和《礼记》是关于古代礼制和礼教的著作,它们为秦汉时期的儒者所著。在儒家学说中“礼”是理论的核心,他们以礼来区分社会的尊卑、贵贱、上下的关系,以礼教来维持社会的伦理。儒家的政治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懂得繁琐的礼制、礼仪,以为通过礼教便可实现宏伟的政治目的。正是因为这极有利于统治阶段的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固,所以儒学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李安宅不从儒学的角度来研究《仪礼》和《礼记》,而是将它们视为社会学的材料,以考察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民俗并建构一个文化体系,将它们由“圣人的天启”降到“社会的产物”,剥去它们的神秘性。李安宅虽然对《仪礼》和《礼记》作社会学的研究,但中国的“礼”,包括“民风”、“民仪”、“制度”、“仪式”、“政令”等,它们又是社会学所不能包括的,因而只有从文化的视野去理解。他认为:“礼书既已影响了中国社会这么多年,而其将死的游魂依然附在少数‘国粹保存家’身上,我们很应该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是装的什么药。而且文化这东西,不是截然中止的,现在的文化一定是旧文化的产物,为欲了解现在起见,也该研究研究旧有文化之‘上层建筑物’的这一小部分。”[11]1-2因此他实际上对中国礼书是作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的‘礼’既包括人常所需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那么,虽然以前没人说过,我们也可以说,‘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11]5从人类学的观点看来,在每个民族里,他们以自己的礼教(民仪)是最高的东西,是不可违反的,是属于禁忌的,以它为是非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异端。若是有人违反禁忌则恐殃及族群,坚守本族的礼教是一种崇高的责任。这样关于礼的研究便进入人类学的领域了。在儒家观念里,礼是文明人的标志,社会的人是分为若干等级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关系中均须按礼的规定区分尊卑高下,处理好相互的关系,尽到各自的义务,如《礼记·礼运》所说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样社会秩序井然,便可达到德治的效应了。中国古代的礼制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它不是圣人为后世制作的,而是因民俗、民仪对社会的作用而加以肯定的,这与政令化的礼不同。当礼成为群众或社会现象时,并且能锦延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有社会生活条件为基础的。因此当社会生活条件发生根本变化时,旧的礼制民仪也就必然为新的礼制礼俗所代替了。李安宅研究中国礼书,却并不主张恢复古礼,他从社会变革的视角认为:“许多改革运动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未求其本而求其末,未求生活条件上的改变而求建筑在旧有生活条件上的东西的改变。不过生活条件虽已改变,旧的风俗制度尚且因为沿用已久而变僵固,作为进化的障碍,所以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加以破坏,那就是革命。到这时候,不管国粹不国粹,非要廓而清之不可。近来所通常诅咒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变成沉积的废物在那里作怪,阻障社会的演进”。[11]3这表现出李安宅关于礼制的认识已由进化论的观点发展为革命的观点,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国粹残余势力的批判。他表明:“现代的国粹家活在现代,死不肯脱去古时死壳,硬要将些死壳加在活人身上,那就未免缺德,所以我免不了要辞而辟之。”[11]8由此我们可见李安宅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礼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了。
原始社会的巫术是愚昧与迷信的产物,但在文明社会仍有种种迷信存在。马林诺夫斯基谈到巫术时说:“我们站得高高在上,站在文明进步的“象牙之塔”一无忧百无虑的,自然容易看着巫术是多么粗浅而无关紧要呵!然而倘无巫术,原始人便不会胜过实际困难象他已经作得那样,而且人类也不会进步到高级的文化。”[6]77李安宅翻译这段话时,联系到中国的实际而深有感慨。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力破除迷信,而它仍象乌烟瘴气一样存在?当民众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若没有一点迷信作为精神的支撑便只有悲观地死去,所以要破除迷信便得改变民众的生活条件。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基础甚低,大体上是‘迷信救国’的社会。少数人也很难超然自拔的。这样,即使不为大众计,专为造就出天才来,也非得改善大众底一般生活条件不可。”[6]78破除迷信自然首先要改变民众的生活条件,但同时要发展科学以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当时中国不仅存在巫术和迷信,并有许多陋俗,重男轻女便是普遍的现象。这与西方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李安宅分析说:“中国人以儿子为自己底继身,对于女儿的态度,似不这样。富贵阶级的父亲,以女儿底美善,得到荣耀底满足原因不似‘自已在女形里的化身’(马林诺夫斯基语),而似自己能力和财富底炫耀。第二个原因,女儿有时要优待,因为女儿不被看作自家人,多少有些客气。第三个原因,因为男女有别,父亲对于女儿也就有些回避,不似对儿子那样密接过甚。至于贫苦阶级,则女儿较儿子多受虐待,因为她是‘陪钱货’。”[7]注六,41这样的分析是很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无论道德、制度和习俗,它们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马林诺夫斯基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殖民地的情形说:“晚近以来,古代的道德和制度既在虚伪的基督教的道德之下渐形崩毁,白人所谓法律和制度一被输入,便将部落传统所已抑窒的热情,更猛烈地公开地透露出来了。”[7]94李安宅对此段话加上按语:“中国自与西洋接触以来,何尝不是这样情形?”[7]注三,99此则按语足令我们深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便显示出它与现代文明的不适应,而人们迅即从旧的道德制度下抑窒的热情更猛烈地表现出来。我们从李安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见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而采取批判态度的。
三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主张实地研究,或曰田野调查,它以记录和观察为主要特点,而且强调纪录另一种文化的唯一方法是生活于其中,学习并理解它。马林诺夫斯基于1914—1918年在南太平洋初步兰岛的调查,对一个单一文化的研究,将该部落生活的复杂情形充分地描述出来。他的调查及系列著作使实地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本族文化的基本方法。李安宅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说:
这几年,社会科学在中国总算很流行了。一个青年在书肆所找到的,五花八门,议论纷纭。特别是大学里读到的课本与由市上所买到的流行译本,显然是各不相容。于是大学里的只能当学分,市场上的只能充时髦:时髦加上革命的引力,学分戴上学者底面具。于是两者底不相容视为固然,各走各的,谁也不理谁。不理还是小事,甚至两面都是气烘烘的,好像有甚么深仇。其实这样气烘烘的学者与读者都只是“读书”,都只是读读旁人的东西,便以感情底适与不适对于作家投了信任票或不任任票,谁也不曾实地调查过。[7]译者按,259
李安宅之所以译介马林诺夫斯基的两种文化人类学著作,旨在提倡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他说:“译者特别关心的,自然不只是读了人类学的文字而有的可能贡献。最大的可能贡献乃在人类学底严格训练教我们所作的实地研究。”[6]2在李安宅的治学过程中,实地研究是很重要的部分。1934—1936年李安宅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进修社会学。他于1935年6月15日至9月16日在美国东部新墨西哥州的祖尼(Zuni)人居住地进行实地研究。他住在一个祖尼人家中,融入他们的生活,身临其境观察,还参加祖尼人的跳祈雨舞的仪式与活动。此后他完成了《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12]的英文论文,于1937年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第39卷第1期。他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对一个异族文化进行文化透视,并学习美国人类学的实地工作方法。关于祖尼人的研究,西方学者已有许多论述,但李安宅以为有些论断是由于以孤立的文化特征为依据,或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作出的,或是基于异族文化模式的相对性作出的。这些论者忽略将一个民族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例如关于祖尼人的宗教问题,李安宅说:“外人觉得稀奇的东西对处于该文化有机体内的所有人来说,因为有着完整的背景,可能是毫不足怪的。脱离原有背景单将某特质引入另一个文化中去,的确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12]82他经过实地研究,在关于祖尼人的宗教、首领、教养、丈夫和妻子等方面,发掘了新资料,并辨析了西方学者的误解。这成为一篇典型的以批评为特点的文化人类学论文。
1938年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在兰州主持中英庚款西北教育委员会,4月至8月到渭源、陇西、漳县、岷县、临潭、卓尼、黑错、夏河(拉卜楞)、临夏、永靖、和政、宁定、洮河及西宁等边疆地区考察教育情况。这一带是蒙、藏、回、汉民族杂居地区,经常发生民族或部落的矛盾,顾颉刚在考察后以为这是因交通闭塞,人们只记得近邻的恩怨,又为野心家利用而造成寻仇生衅;要改变此地区民众的这种心理,应当发展交通,配合社会教育[13]。此年为了“抗战建国”,李安宅与妻子于式玉接受陶孟和与顾颉刚的建议,自北平赴甘肃兰州,进入藏族地区拉卜楞考察。李安宅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藏族宗教,于式玉则义务创办拉卜楞女子小学。他们学习藏文藏语,辛勤地工作三年。在拉卜楞考察后,李安宅完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部专著介绍了藏族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概况,继而论述了藏族的原始信仰及藏族佛教的各派,对格鲁派寺院——拉卜楞寺作了重点的详细的考述,最后描述了拉卜楞地区的地理、寺院、民俗、生活等情况:由此辨清了关于藏族宗教的种种误解。李安宅比较藏族宗教与内地佛教,使西藏宗教的特征更为突出。他说:“喇嘛教与内地佛教均来源于印度,但内地佛教已无密宗,……藏族宗教与内地教育颇类似。他们既出家,与内地出外读书差不多,由识字到深造,既可分,又不可分。信仰宗教的人们,是出力维持寺院的人们,也是被寺院统治的人们。寺院既是求学的地方,受人崇拜的地方,也是为群众进行娱乐的地方,更不用说活佛的统治,既有专制的特点,又无专制出于私人家庭世袭的短处。所以寺院所在之处,与贵族统治相比,寺院日盛,而贵族一代比一代衰落。”[1]1李氏此著完整地论述了藏族的宗教问题,成为填补历史的空白之作。
以人类学来研究一切经济落后的社会是恰当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因此以人类学来研究中国农村是很合适的。李安宅在边疆地区考察后,感到这工作是急切的,他认为:
国内深山远境未甚通化的初民正合乎人类学底对象,要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不必说了;即国内一切经济落后的农村社会与垦殖过程中的边疆社会,也都不是一般抄袭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社会学所可容易下手。我们不希望对于自己底社会基础——农村——有科学的认识则已,不希望对于边疆社会加以开发与巩固则已,如其希望,则必要脚踏实地的细大不遗的社会学,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为背景的社会学,不以西洋工业化的大量生产的农村为背景的社会学,便是译者心目中的人类学。[6]译者序,2
以人类学对中国农村和边疆进行的实地研究是一种新的待开发的学术园地,但怎样进行实地研究,这在当时国内尚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李安宅深感此工作的重要,因有了实地研究的经验,于是对边疆实地调查方法作了理论的探讨。为什么要提倡实地研究,李安宅说:“我们可以肯定一条原则:学问之道,在有直接经验的。不过,要有脱颖而出,比较经验、整理经验的机会;在有传闻或书本经验的人,则要有破除故障,实地研究,获得直接经验的要求与实践。虚而复实,实而复虚,抽象而具体,具体而抽象,循环相济,以致即虚即实,即抽象即具体的境界。”[10]152-153实地研究的最好方法,是将研究,服务、宣传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对象是自然、人、文化,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新的治学方向。李安宅说:“中国过去的习惯,多偏重在文字,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满腹经纶’,反每易闭门造车,即纸上谈兵是。‘巧妇难做无米炊’,没有客观界的材料,势不能产生利用厚生的学术,当属明显的事。所谓‘到自然界(客观界)去’,是世界文艺复兴的基本发动点与指南针。吾国新文化运动只解放了学术工具,即:由过去少数人使用的文言,走到了适于大多数人的口语。至于学术本身,则要另一种新的运动,将自然、人、文化三者加以实地的研究。”[14]155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对实地研究对象提出一个纲要:一、对于自然界的适应:土垠、气候、水利、动植物、职业、舟车、渔猎、饮食、居所、家具、耕种、纺织、皮草、烟、陶器、盐、酒、医药、金属制作;二、对于同道的适应:民风、民仪、制度、社区、节俗、家庭、宗教;三、对于自己心理生理的适应:文身、补牙、耳环、发饰、佩物、服装、体格、毛发、眼口、颔、头、表情;四、对于超自然的适应:信仰、节仪、禁忌、寺庙、教堂、僧伽、教会;五、适应工具:语言文字、劳动工具。这样全面的调查宜于组织一个文化考察团,由社会科学家与人类学家、医学家、地质学家、工业技术家、语言学家等组成,作综合的考察。对经济落后的社会和边疆地区之所以需要进行人类学的考察,是因为这可从某一文化的立场及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以见到其各种文化——宗教、民俗、语言、社会、节仪、婚姻、家庭等在此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功能。李安宅在美国祖尼和中国边疆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正是如此的。他希望全国学术风气“都走入实事求是的一途”,这样必将带来学术的丰收——“满地尽黄金,能拾取者有之!”[14]161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克·T·斯瓦兹和大卫·K·乔丹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的展望》对人类学的定义是:“人类学试图描述和阐释人类从最早的人前时代的先祖到现代所有历史时期和社会的生活状况和方式。人类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科学。它涉猎范围广泛而且它关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并从实际研究中区分他们。它以‘文化’的概念作为依据的基础并用交参文化比较来区别研究它们间各种类的不同。”[15]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理解李安宅著作及译著所涉及的社会学、意义学、语言学、美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广阔的范围,但均是借助这些学科知识去逼视、分析和衡量人类学的文化现象,自成一个文化人类学系统的。他译介并阐发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人类学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和他在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成就,以及他对实地研究方法的提倡,这些都在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开拓的作用。他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对我们尚有启发和指导的意义。
[1]雷洁琼.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序[M]//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2]李安宅.意义学[M].重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8.
[3]庄锡易,孙志民.人类文化学的理论构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93-294.
[4]王海龙.人类学入门[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5.
[5]林惠祥. 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
[6][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7][英]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M].李安宅,译.影印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8][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M].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01.
[9][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2.
[10]李安宅.边民社区实地研究·实地研究与边疆[M]//《仪札》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附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李安宅.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讨论[M]// 《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附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64-165.
[14]李安宅.实地研究纳要[M]//《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附录三·边民社区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王海龙.人类学入门——文化学理论的深层结构[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3.
[责任编辑李秀燕]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Cultural Phenomena: Li Anzhai,A Pioneering Figure in Chin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XIE Tao-fang
(InstituteofLiteratureResearch,Sichu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Chengdu,Sichuan, 610071,China)
Malinowski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unctional school of British cultural anthropology. His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forerunner scholar Li Anzhai into Chines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Mr Li’s works covered various fields like sociology,semantics,aesthetics,folklore, religious study, ethnology. He used knowledge of these subjects to perceive, analyze and evaluate human cultural phenomena, forming a system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His translation and explication of theori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his critic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his field research are all pioneering efforts to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His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still instructive and insightful for today’s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Li Anzhai;Malinowski;cultural anthropology;sociology;field research
2014-10-20
谢桃坊(1935—),男,研究员,主要从事词学、国学研究。
I206<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
1672-8505(2015)01-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