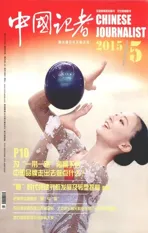“移动端还有巨大想象空间”
——对话新京报传媒公司副总裁、北京热火朝天科技有限公司CEO刘炳路
2015-02-15万小广
□ 文/本刊记者 万小广 程 征
“移动端还有巨大想象空间”
——对话新京报传媒公司副总裁、北京热火朝天科技有限公司CEO刘炳路
□ 文/本刊记者 万小广 程 征
·对话新媒体·
编者按:2014年12月,消息称《新京报》原副总编辑刘炳路转型创业。今年4月,他在产品上线前夕接受《中国记者》专访,详谈转型创业的缘由,以及对移动互联网发展机遇、媒体人转型创业潮等话题的思考。
本刊从2012年第8期起开辟“对话新媒体”栏目,已有多位新媒体领军者接受访谈。今后,这种特色访谈还将继续,以期从另一个角度为探索转型的媒体人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刘炳路新京报传媒公司副总裁、北京热火朝天科技有限公司CEO
【刘炳路简介】:2001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曾先后供职于《燕赵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擅长调查报道,曾担任《新京报》副总编辑。
传统媒体的“内部创业”
中国记者:有消息称你去年12月转型创业,报道还起了个标题称“连刘炳路都转型创业了”,怎么理解那个“连”字?你原来是《新京报》最年轻的副总编辑,转型创业好像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能否谈谈这一选择背后的考虑?
刘炳路:可能我的机会成本最低吧。我一直做新闻,做得还算可以,很快就有了比较高的平台,在很多人看来有很好的前途,放弃了好像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学经济的,做企业一直是我心底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甚至很困惑,觉得内容做得越好距离初始的梦想越远,我就越恐惧,担心自己被定格在某个领域。
我在《新京报》开始做深度报道,后来做了管理工作,从主编到编委、副总编,很常规的路子。那么,问题来了,尽管我们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领域出了很多作品,也确立了江湖地位和行业标尺,但是思维也固化了,很难突破常规报道模式,触到了天花板。早在2012年底,我就萌生了转型的想法,想探索新事物。
中国记者:你在《新京报》分管过新媒体业务,应该说也是在寻找传统媒体转型的出路。为什么后来还是独立出来做新媒体?
刘炳路:2014年初《新京报》成立全媒体编辑部,整合新媒体业务,让我负责分管这一块,主要做微博、微信、客户端以及网站等新媒体业务。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你知道,在传统媒体,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新媒体都还无法取代原来业务成为主业。当时没人愿意和我去搞新媒体,重点谈了几位年轻人,都是90年左右生人,告诉他们要顺势而为,搞清楚“势”在哪里,努力才更有成效,互联网就是现在的“势”。苦口婆心几番周折,虽然强压了几个年轻人过去,但是还是有几位回去了。
到后来,我们新媒体业务发展迅速,即时新闻(非报纸内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常被重要客户端推送,也因此大幅提高版权价格,针对门户的版权收入增长了50%。同时推出动新闻,以3D动画形式展现新闻,动起来的新闻更精彩,并针对企业、政府做了很多商业定制动漫视频,增加了收入。
后来,报社和腾讯合作的京津冀区域门户网站“大燕网”,选了新媒体这边一名副总监担任总编辑,就是因为他有新媒体工作经验。这时,整个形势都发生变化,很多主编争抢着要搞新媒体。
但是,在传统媒体体系内做新媒体业务,还是受到很多制约,比如报道空间、技术水平、所有制形式、产品意识、服务理念等等都有束缚;再一个,移动互联网让门户也成了传统媒体,大家突然又在同一起跑线上,移动端还有巨大想象空间。所以,我想更加自主地去做点新东西,也给年轻人腾出位置。
我很感谢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允许我全身心投入这个新公司新项目中去。严格来说,这仍然是传统媒体另立门户的“内部创业”,但我们已经非常激动了,也都做好壮士断腕准备。除了我还保留新京报传媒公司副总裁头衔,其他几位核心创始人和报社都没关系了。
做面向年轻人的内容类移动APP
中国记者:创业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方向、钱和人”,你的创业方向是如何确定的?资金从哪里来?又有哪些创业伙伴?
刘炳路:公司名叫“北京热火朝天科技有限公司”,三胞集团和新京报社是两大股东,创业团队持有一定比例股份,并设计了期权制度。
关于创业方向,我们目前主要做的产品是一款内容类ĀPP,叫“热门话题”。2.0版本正在内测,调整得比较大,定位于新闻的另类解读,正在做上线推广准备。
合作伙伴很重要,创业一定得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内容团队主要来自新京报新媒体、深度报道团队;产品技术团队来自互联网公司,负责产品和技术的马金男、技术总监刘强等,都曾在百度、新浪工作过,也有过创办乐淘、占座网的经验。
中国记者:之前你说“创业方向基于移动互联网,跟内容相关,但跟新闻关系不大”,可否详细介绍下这款“热门话题”APP在产品定位与功能设计上有哪些特色?背后又有哪些思考?
刘炳路:像“热门话题”这个名字显示的,这是一款强互动产品。新闻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不愿意做纯新闻,会有更多知识、娱乐类内容,所以不是新闻客户端而是话题性内容类产品。
具体来说是“不三不四”,“不三”是,“无延展不新闻、无分享不热门、无互动不话题”。“无延展不新闻”是指新闻的标题制作、角度选择、导语提炼、所配图片,都是新闻本身的深度延展;另外,也会选取有趣、新颖、另类的角度,进行盘点整合,延展新闻的厚度和广度。“无分享不热门”是指一定要选取那些大家有分享冲动的内容提供给用户。“无互动不话题”则是指有讨论、有争议的,才是话题。每条新闻后面,我们都会精选集纳附上网友对此新闻的精妙点评、观点吐槽,同时用户也可以跟帖进行讨论。
“不四”呢,1.不乏味——有趣;2.不浪费——有用,向用户提供贴心的资讯,不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既紧跟形势,又多“涨”姿势;3.不肤浅——有料,针对热点的深入浅出的话题讨论和妙趣横生的解析;4.不冷血——有温度。
目标用户主要是20岁到35岁的社会中坚力量,希望能影响这些有影响力的青年人。为什么把目标定位他们身上呢?有这么一件事触动我。当年我在《新京报》负责采编时,大家都用“高大上”的MSN,很多用QQ的年轻记者被我们改变了习惯。若干年过去,MSN完蛋了而QQ成为主流,无非是用QQ的年轻人长大了,他们成为潮流的界定者。同样,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习惯从手机上看新闻和浏览内容,
只有赢得年轻人,才能赢得未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款Āpp能够关注这些青年力量的喜好和关注点,适合他们的口味,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让人们关注应该关注的“硬新闻”。全部是精致内容,又与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这跟“今日头条”这种纯技术平台不一样。未来还会增加原创,但不会像“澎湃”“界面”那样铺开摊子,不会做突发事件新闻采编,更多是做话题讨论的组织者、延展者。消息留给他们,延伸我们来做。
中国记者:看你一直在强调在移动端做内容要接地气,要有趣味,而你原来一直在做非常严肃的深度报道。为什么有这种转变?
刘炳路:做一篇6000字的深度报道,得辛辛苦苦核实每一句话,形成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搞了新媒体后发现,常常一篇好报道放到网上的点击量可能还不如一张低俗图片。那么,是不是深度内容就没有意义了吗?恰恰相反,在这信息泛滥时代深度内容更有价值,但要改变呈现形式。比如,这篇6000字的稿子可不可以拆成6篇1000字的稿子,或者1000字加一幅图,再或者干脆用一段3分钟短视频、用图表、用演说的形式来呈现?只要我们能想到的方式,技术都能实现。
我认为,传统媒体的一些冷酷、呆板的东西已受到移动互联网冲击。而移动互联网技术会给内容带来更好的呈现方式,即使现在没有找到,但这一定是趋势。所以,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一种新的内容生产与表现形式的标准,像《新京报》当年做深度报道的生态系统一样,做出一个移动端的内容生态系统。
中国记者:你担任过传统媒体高管,现在又负责新媒体公司的运营管理,你感觉在运营管理上有没有明显差异?
刘炳路:传统媒体很容易在业内树立权威,一般是领导或者写出过优秀作品的业务骨干,都容易成为权威,其他人也都信服这些权威。但在互联网公司你会发现权威被打破了,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由主观到客观,由主编个人喜好到数据说话。
像“热门话题”这样的内容产品,如果是传统媒体做,肯定是做内容的领导说了算。但在互联网公司,是由产品经理决定,一个产品是由基础功能、内容运营、用户体验、数据分析等多方面构成的,内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当然需要双方很好地沟通。移动互联网的组织模式也更加扁平化、去中心化,责、权、利更加明晰,也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团队的创造力。比如,一个普通编辑可以协调、调动其它部门主任、甚至我,因为这项事务是他负责,这在一些传统媒体是做不到的。
中国记者:你长期从事纸媒报道,现在又做移动端的内容生产,你觉得在做内容的方式和目标上有哪些不同?
刘炳路:传统媒体人做新闻其实是比较主观的,虽然有读者写信、打电话,但总的来说,从选题到写作,基本上都是编辑和领导靠经验决定的;做完之后,也不知道读者是男是女、停留多长时间、有什么意见;稿件的评价、反馈也来自少数人,主要是领导和同行觉得好,你这稿子就好。在移动互联网公司,稿子写完,工作才刚刚开始,要考虑用户的特征,以及阅读、评论、分享等行为数据,来调整选题的内容与形式。当然,这些也有主观成分,但至少有这些客观数据来帮助我们分析。我刚好是学统计的,更喜欢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感受,传统媒体比较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倾向于理想主义,可以不计回报去做事,因为觉得这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互联网公司,则比较关注利益回报。一开始我还不太习惯这种变化。互联网公司当然也有理想,但不是宏大的抽象的,而是具体如何搭建一个平台、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更多人,给用户创造价值,怎么让用户“爽”起来,获得收获和满足。一篇报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产品则可能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行为习惯。
刘炳路采访手记
热火朝天科技公司在宣武门SOGO旁边一幢不起眼的小灰楼里。傍晚六点,楼里的公司几乎都已经关灯下班,只有顶楼的热火朝天公司仍然灯火通明。在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创业后的刘炳路。黝黑的皮肤,厚嘴唇、国字脸,头发略带自然卷,再加上一副大眼镜,给人的感觉是憨厚朴实、随和亲切。
刘炳路告诉我们,自己的憨厚外表具有较强的迷惑性,让他做调查报道的时候一路“骗”过很多人,甚至能混进警局拿到一手材料。凭借在深度报道领域的赫赫战功,70后刘炳路在《新京报》创下诸多“之最”。
刘炳路认为这些成绩归功于自己天赋不够而下的“笨功夫”。实际上,从他的经历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勤奋,更是那股生猛的闯劲,以及不断挑战自我、追逐潮流的胆识。
刘炳路大学学的是经济统计,毕业后被分到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燕赵都市报》,“误打误撞当了记者”。当时常有机会和省市领导一起下乡,“时常在电视上出现”,对来自农村的他来说已经“光宗耀祖”。但刘炳路觉得,“看到报社五十多岁同事时,觉得人生一眼望到了头”。于是,半年后提出辞职。当时《河北日报》的总编辑非常惊讶,说他是第一个“炒”掉《河北日报》的。
辞职后,刘炳路去了同事口中常常提起的《南方都市报》。然后,跟着南都人马北上创办《新京报》。本来,他跑的是时政口,但听说深度报道最能体现水平,于是就想“转型”去做深度报道。
但当时的报社领导不同意,觉得他“文字太差。”刘炳路不服气,自己去找深度报道部的负责人软磨硬泡,得到一个选题,即杨新海特大杀人案,他成功突破层层信息封锁,采写了1万余字的独家报道《杨新海特大系列杀人案调查》,先声夺人,引起轰动。
凭着这股闯劲和胆识,刘炳路最终如愿以偿进入深度报道部,并很快在深度报道领域奠定“江湖”地位,很快又走上管理岗位。做了十多年的深度报道,刘炳路觉得“做内容已经到了天花板”,并酝酿新的“转型”。
恰逢《新京报》为开拓新媒体业务成立全媒体部,刘炳路受命分管和组建这个新板块。他上任后开拓即时新闻供稿、商业视频等新业务,很快就把这块做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刘炳路愈发觉得独立运作、贴近市场的重要性。
于是,他决定又一次转型,彻底投身移动互联网。这个消息又让很多人意外,觉得他在体制内前途可期、放弃挺可惜的。但外界不知道的是,学经济的刘炳路一直怀有独立创业和从事商业经营的梦想,他甚至有点小得意地告诉我们,其实他一直炒股票,而且“还炒得不错”。
创业后的刘炳路很忙。虽然公司目前只有20多个人,但与以前相比责任更大,因为作为创业者又是职业经理人,不仅要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也要对老东家《新京报》的声誉负责。他开玩笑说,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了,压力比较大。
他已辞去编委、副总编辑职位,彻底断了走回头路的可能。这种决绝,被他解释为自己脸皮薄,“干得好的话,不用回报社;干不好的话,也没脸回去”。尽管离开传统媒体采编岗位,刘炳路骨子里仍然带有传统媒体人的情怀。比如“热门话题”的愿景是既有深度,又接地气,希望影响那些已有一些价值判断的年轻人。
“从报社副总编转型为创业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当我们抛出这个问题时,刘炳路略一沉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自己身上的T恤衫说,“你看,以前我不可能穿成这样”。
那件T恤确实是他现在状态的写照:长袖翻领、面料顺滑,没有西装紧绷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自由舒展的空间,可《新京报》鲜红的火炬LOGO,依然印在胸口。
媒体人转型创业潮的冷思考
中国记者:你认识的新闻同行转型创业的多吗?无论是内部创业还是外部创业,媒体人创业是否已经形成一股潮流?为什么?
刘炳路:我朋友圈里转型创业的媒体人还是比较多。现在聚到一起,大家谈论的都是谁谁谁创业了,谁谁谁融资多少钱。即便没出来创业的,也有很多人有想法。很多人还没有出来,只是没有机会。可以说媒体人创业是个普遍现象。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行业来看,传统媒体这几年不景气,经营收入在下滑,广告和发行量、广播电视的观众数量都在下降,趋势不可逆。但这些传统媒体又承担了很高的税负,比如报纸是25%,而互联网公司才15%。
从媒体人自身来说,首先他们对时代变化趋势比较敏感,而传媒业恰恰是受互联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其次,新闻人的职业训练,让他们善于学习新知识,善于应变;第三,媒体人大都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创业有一定基础。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他们相对容易选择转型。
中国记者:这种媒体人转型创业潮流对于行业有什么影响?你怎么看媒体人转型创业?
刘炳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本质上是颠覆垄断,并形成新的垄断。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BĀ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只要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就有空隙,那条空隙可能就是创业机会。
过去,传统媒体人纷纷向门户网站跳槽,都是香饽饽,现在门户也成传统媒体了,很多都在裁员。现在是互联网+融媒体时代,传媒行业需要大跨度改革,就需要既懂内容又懂移动互联网的人去主导这种变革,所以媒体人的转型都会作用和加速到传媒改革上,对于行业来讲有积极作用。
再一个,都市报都已经有20年了,不仅读者慢慢老化,从业者也老了。上次碰到一位都市报朋友,得知这家都市报员工平均年龄都40多岁了。而当年我在都市报工作时平均年龄才20多岁,这种现象可能带有普遍性。当年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升到中高层了,车也有了,房也有了,也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地位了,做新闻也很难跳出原有的惯性和套路。你很难想象让40多岁的人像20多岁的年轻人那样去做服务,所以很多人也在力求转型。
整体上,互联网制造了很多一夜暴富的创业神话,把新闻业的氛围变得比较浮躁,对原来兢兢业业做好内容的人来说构成一种干扰。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说,还是需要有一批人沉静下来做好内容。
转载本刊文章,请务必注明转载自《中国记者》期数、作者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