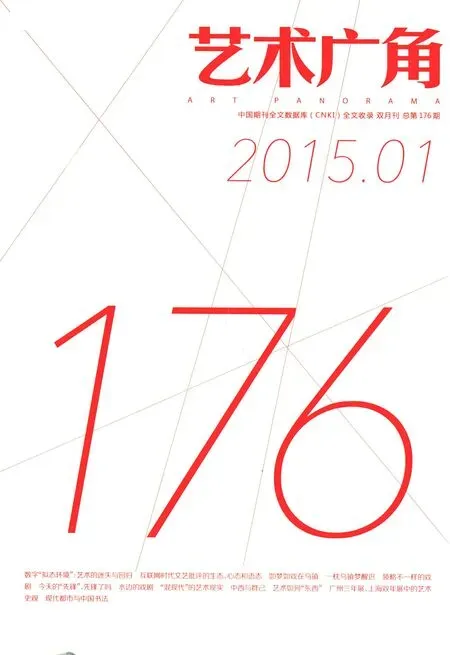数字“拟态环境”:艺术的迷失与回归
2015-02-14陈秀云
陈秀云
数字“拟态环境”:艺术的迷失与回归
陈秀云
陈秀云: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媒介与文学关系研究。
人类正不知不觉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是数字媒介。媒介一旦数字化,意味着超强的信息传播力,也就是传播空间的无限扩张和传播速度的无限增长。我们发现从数字电视、数字电影、数字杂志、数字报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到手机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介,多种多样的数字媒介势不可挡,在短时间之内就实现了对人类生存时空的占领。这种占领不是来势汹汹的攻城掠地,而是静静悄悄的信息扩张。这种扩张仿佛一场夜雾的悄然光临,使第二天清晨睁开惺忪睡眼的人们看到的世界如幻如梦,美丽朦胧,这就是数字迷雾下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插入我们与世界之间,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着作为我们生命投射的艺术。艺术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面对?正如哈姆雷特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一样,在数字“拟态环境”的大考前,艺术如何选择,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
“模仿”的模仿
“拟态环境”是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其经典名著《舆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传播组织为了各自目标,依据不同标准,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和加工,通过象征符号形成一个取向芜杂的信息环境,这个环境不是现实世界“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一个由于人为加工而与现实有着较大距离的虚拟世界,所以李普曼把它称之为“拟态环境”或“假环境”。在李普曼时代,造就“拟态环境”的,是以报纸为主体的纸质媒介,文字符号的模糊性使现实世界很难得到直观反映,决定了当时的“拟态环境”只是人类生活的有限模拟。
如今数字媒介的出现,使文字、声音、图形和影像等诸多符号共同发力,现实世界可以得到生动、直观的再现: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从国计民生到鸡毛蒜皮尽收眼底,无论是卧榻之近还是天涯之遥,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信息。数字空间仿佛藏有一个心想事成的魔方,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然而正如李普曼发现的那样,任何媒介信息都是人为选择的产物。在数字空间里,无论新闻、广告还是艺术,都是重重审核后的结果,而重重审核就意味着大量的不符合媒体需要的信息被过滤掉,媒介对于世界的反映依旧只能是管中窥豹,即便专业化的媒介机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具体信息的真实客观,由于排除了大量其他的信息,也根本无法做到对复杂客观世界的全面再现;而私人化自媒介传播虽然不如组织传播那样目标明确,但是也没有任何人会事无巨细“晒”出自己,而是选择那些能够展示个人魅力的信息。可以说,如今的数字“拟态环境”和此前相比显得更加真实,但仍是主观选择的真实,与客观世界依旧相距甚远。然而,当下很多人就是安然地在这样的“拟态环境”中游历,乐此不疲,“新技术对人的注意力来说犹如催眠曲,新技术的形态关闭了判断和感知的大门。”[1]如今高仿真的“拟态环境”比以往任何媒介环境都更具麻醉性,人们不知不觉中正在按照这个环境提供给我们的模板去框定生活,从时尚衣装到流行发式,从高大上到小而全,无不来源于这个环境的塑造。
艺术家也在这样的数字“拟态环境”中生存,被这个无边无际的“假环境”所包围,如果心安理得地按照这个“假环境”去构造艺术世界,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对“拟态环境”的模仿,便成了问题。近年来,真正能够捕捉现实、刻画出“国人灵魂”的艺术作品着实罕见。文艺界曾进行“想象力”的讨论,认为一些艺术家失去了想象力,才使作品失去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品质。这种讨论发现了问题却没能找到真正原因——想象力的缺乏除一些社会原因外,还与“拟态环境”的影响有关。“拟态环境”往往看起来很美,比自然和现实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经过人为选择后,那戏剧性的冲突、离奇的故事、古怪的人物和令人震惊的变迁,虽然碎片化,但更具娱乐性、话题性和观赏性,这些对于艺术家具有很强的诱惑,更何况它是如此的经济便捷,如果考虑投入与产出,依据“拟态环境”资源进行“创作”的确最划算;更何况数字“拟态环境”汇聚了新闻、广告、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剧、真人秀等等五花八门不同形态的信息,仿佛一个无限宽广的“秀场”,艺术与其他形态信息同台竞技,海量的新闻和各类纯娱乐的火爆让艺术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要以如此微小的身躯引人注意,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很多艺术开始向身边的浅俗信息“模仿”,或千奇百怪,或千姿百态,或千娇百媚,归根结底是千方百计吸引眼球博出位。
构造数字“拟态环境”的信息无论多么栩栩如生,也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加工和模仿,艺术家依据这些信息的创作自然就成了“模仿”的模仿。当下一些小说像微信八卦,电视剧像网络游戏,玄幻、惊悚、滥情的作品和社会新闻难以区分……模仿的结果是雷同,雷同的效果是虚假:标榜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缺乏知识含量,号称反映农村生活的小品没有泥土气息,历史剧找不到历史依据,科幻电影不合科学逻辑;自以为在塑造英雄,进入人眼的却是流氓,自称为生民立命,最后却流于为个人谋利,本来要描写奋斗和理想,最后呈现的是争斗和虚妄……而一些艺术家对此并不自知,安然生活在数字化的“拟态环境”之中,甚至养成依赖“拟态环境”的创作习惯,不停重复着“模仿”的模仿,“想象”的想象,让“失真”成为无法复元的伤。
“平均化”的审美取向
营造“拟态环境”的数字媒介把人类信息传播速度以几何级数不断刷新,从2G、3G到4G……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传播速度不断提升,眨眼间一条信息就可以到达城市、到达乡村、到达全中国、到达地球上的任意角落,超强覆盖力意味着超大受众群,意味着高票房、高收视率、高收听率、高阅读率和高点击率……日益攀高的数字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所有数字的获得,要求媒介能够提供满足不同品位、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各色人等共同需求的内容,这样,就出现了比尔·麦克本在《丢失的信息时代》中所发现的那种景象:“地球村村民们今天将共同分享的,不是有意义的信息资源,而是豪饮可口可乐、吃汉堡包、穿利维牛仔裤的图像。”[2]
媒介环境学者尼尔·波兹曼明确指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3]数字媒介的超强覆盖力偏好的自然是能够适应其受众群的内容,也就是像可乐、汉堡这样全球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符合人的共同需要的产品。当下,这样的标准化主宰着数字“拟态环境”的文化。正如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跨界互联互通需要“IP协议”一样,那些被人广泛传播与接受的信息,实际上也都在自觉进行标准生产,这个标准就是不同信息需求的平均数,是人的共性。具有差异化、独特性的信息在数字拟态环境中很难生存。数字“拟态环境”是依靠传播标准存在的环境,程式化和平均化成为数字“拟态环境”中的文化通律。这一定律制约下,是文化产品的无限重复不断循环,“拟态环境”中的文化貌似丰富多彩、发达兴旺,但所有热闹的背后却是自我增殖、自我膨胀,以“平均化”的信息培养着世人“平均化”的审美取向。
作为文化主要生产者的艺术家,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就会被裹挟其中,磨掉自己的棱角,放弃自己的个性,以牺牲艺术的独特属性换取传播的辉煌。当下许多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遵循易传播、易接受的“平均化”逻辑,其相关的艺术生产就带有这样的特点:影视剧的制作,被奉为圭臬的是“性”“暴力”和“大场面”等所谓的创作元素,一部作品的完成,不像是创作,而如儿童拼图一样,只要把几个元素依照不同的方式放到不同的位置,则会拼出不同作品;文学畅销书的打造,常常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故事和人物,不是高富帅就是白富美,丑小鸭总是会变成白天鹅,青蛙终归是王子,白雪公主毕竟是公主,恶毒王后永远恶毒……无论是穿越回一千年还是奔向未来一万年,故事还是那个故事,没添也没减;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号称为文学的作品数不胜数,但内容却是大同小异,翻来覆去,不过是编造些商场、官场和情场的是是非非,一些所谓新作似乎只是在固定模板里玩替换人物姓名的游戏而已。大量的作品就这样失去了独创性,作家成为写手,作品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以量的累积制造着“拟态环境”中艺术的虚假繁荣。
“变动不安”中的沉沦
媒介环境学的先驱、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与传播学者伊尼斯,通过对媒介史的研究,深刻揭示了传媒的时间与空间两种偏向。时间偏向的媒介主要指石头、金属等易于保存的笨重媒介,这些媒介有利于宗教信仰等内容的传播与保存,人类形而上的精神往往依赖于时间偏向媒介存在;空间偏向的媒介则是像莎草纸那样轻薄、易于运输、不宜保存的媒介,这些媒介有利于国家实力的炫耀与文化影响的扩张。理想的传媒生态是两种偏向媒介共同生长,这样有利于形成人们感知的平衡,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够有恒久的信仰,以维系内在的宁静。
但是,进入大众化传播时代以来,高度发达的是空间媒介,随之而来的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而人类曾经的信仰和价值在物质的冲击下迅速败退。当下造就“拟态环境”的数字媒介恰恰把空间偏向推到了极致,时间一维受到无限冲击,人类的感知严重失衡,我们发现“拟态环境”像个无底洞,源源不断的信息滚滚而入,却又转眼而逝,这种不停的制造与消逝使“拟态环境”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不安感,所有的事物都变得昙花一现。在“上传”“下载”“刷新”这些动作的变换中,没有人敢保证一条信息会留存到下一秒,“删除”“更改”与“替换”成为“拟态环境”的常态,从兴旺到衰败,从热恋到抛弃,从朋友到仇敌,转换只需一键,这是变动不居、光怪陆离的环境,这是高唱“只要曾经拥有”、不敢预约“天长地久”的环境。这个环境里的一切都可能被压缩成“快捷方式”,以瞬间的图像变动代替漫漫的历炼过程。
数字“拟态环境”的变动速度正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升,没有止境的加速度,使人类犹如被技术这条鞭子不停抽打的陀螺,在不由自主的运转中,感到的是迷失的恐惧,人们不再能够安然闲适,冲淡从容,而是患上了严重的时间紧迫症,仓促与匆忙、焦虑与浮躁成为流行的社会心态。人们开始重视即时效应、眼前利益,重物质轻精神,重展示轻内省。数字“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平铺,它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历史的深度。我们看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空间里,有人恶搞,有人山寨,有人“挖坑”,有人“灌水”,有人骂,有人赞,有人喊,有人打,有人捧……各种表演,各种宣泄,各种表达,不一而足,但在一片喧嚣中,除了有关衣食住行的实用信息外,大量传播的是那些轻松的、反常的、有趣的娱乐,文章出轨、王菲离婚成为跟贴最多的信息,《鬼吹灯》系列被当作最具“价值”的网络文学经典……而那些平凡的、沉重的、深度的信息却比较少见。崇高消解,俗性高扬,不思未来和永恒,眼前利益、瞬间快感、当下享乐就是一切,欲望蒙蔽心灵,千载沧桑在指尖完成。
在这样的数字“拟态环境”生活,一些艺术家也沾染上了浮躁之气。为了赢得公众,甚至一些坚持品质制作的艺术作品也采取商业化的宣传路线,用似是而非的“性”等信息为诱饵,争取在海量的信息中引起注意。而更多的所谓艺术则直接屈服,舍弃自由的价值探索、意义寻觅,以感官化的叙事、欲望化的表达、快感的张扬加入到“拟态环境”的建构中。这样的作品可以展示,不可深思,消减深度,淡化意义,摆脱责任,选择轻松,纯艺术向伪艺术靠拢,一些艺术创作正在失去发现世界、干预生活、探寻生命的能力,成为远离现实、回避思考的符号的自我增殖。在社会普遍的短期效应、眼前利益的追求中,艺术曾经高昂的价值与意义的精魂正在一点一点被腐蚀被浸染,在一片充满快感的喊叫声中迅速沉沦。
“闲定”中的回归
当下的数字“拟态环境”给艺术带来了诸多问题,从模仿到消泯个性再到失掉意义,这些问题正在由局部向更多的艺术家、更多的艺术领域蔓延,形成越来越大、越来越厚的包围圈,艺术家如何从充满诱惑的“拟态环境”突围,向真正的现实回归,是当务之急。
鲁迅说:“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4],“闲”是有“余裕心”,既不是被生存所迫的四处漂泊,也不是为名利所诱的“秀场”竞演,而是给自己保留观察和思考的时间,这样才可能有所体悟、有所发现;“定”是在喧哗中的淡定,是忙乱中的从容,是不为流俗所动的泰然,只有“定”才可能在大潮涌动中把握自己的方向。这种“闲定”正是“拟态环境”中的艺术家必备的一种心态。事实上,那些得到公众普遍认可的艺术家,向来不是刻意制造“拟态环境”中的轰动,通过种种出格言行增加粉丝的数量,不是有了一点名气就立刻让名气变现获利,而是秉承对艺术的尊重,在世事纷繁中坚持自己的个性、保有自己的天地,如著名演员陈道明一年通常只接一部戏,拍戏时做到全心投入、人戏合一;拍戏之余则推应酬、远热闹、习书法、做手工、调琴弄画,不囿于名利忘记自己。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在“拟态环境”中依旧坚持个体精神的高度独立,以超拔的姿态、强大的定力对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保持应有的审视距离,在众声喧哗中拥有一份宁静的理性,在气定神闲的淡泊中坚守对艺术的基本尊重。
气定神闲不是放弃参与社会和生活的消极退避,不是关进象牙塔中的清高,而是让自己回归,回归到自然,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生命本身。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个性化体验传达生命的意义。个性化的体验应该是艺术家亲身感知、感悟、感受的精神结晶,而不是对于别人感受的模仿。经验可以借鉴,而体验必须独有,只有独一无二的体验才可能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即便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事物,当时过境迁,体验也会完全不同。作家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彼时彼地彼种体验的写照,正如流离失所、人到中年的李易安再也不可能写出“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天真少女情怀一样,在艺术的世界里独一无二的体验是个绝对值,即便自己也无法模仿自己,更何况模仿他人。如果李白像一些“宅男”“宅女”那样整天与电脑、手机面面相觑,就不可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唱。构成“拟态环境”的信息恰恰都是他人的体验,如果艺术家仅依据当下的数字“拟态环境”进行创作,其致命缺陷就在于体验的“二手性”。失却了独特体验的艺术品,就失去了生命。
气定神闲也并不意味着远离和放弃数字传媒,而是学会借助“拟态环境”提供的条件丰富创作、完善自己。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已经与数字媒介融为一体,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拟态环境”单独存在。艺术家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可以把“拟态环境”当作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从中发现生活的某种变化;另一方面还可以把“拟态环境”中的信息当作创作的线索,为进一步深入生活做准备。当然无论怎样利用这个“拟态环境”,艺术家都需要保持理性的判断,保持对信息的分辨能力,“拟态环境”无论看起来如何真实,其本质不过是诸多信息的汇聚,总会造成对现实的扭曲。它以最快捷的方式提供信息,但它没有义务把生活的全部展现给你。“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艺术家要想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需要的是从“拟态环境”的迷雾中突围的勇气、踏实的努力和坚持的毅力。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传播技术的进步已是大势所趋。数字“拟态环境”的扩张还在继续。虽然它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诸多便利,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数字“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存在遥远的距离,哪怕有一天这个拟态环境“真实”到色香味俱全,人的五官感受都可以从中得到满足,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份清醒,那就是信息终归是信息,虚拟不过就是虚拟,那高高的山、潺潺的水、蓝蓝的天和我们脚下的大地永远无法代替,而艺术的根就在那里。
注释:
[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9页。
[2]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8-99页。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4]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