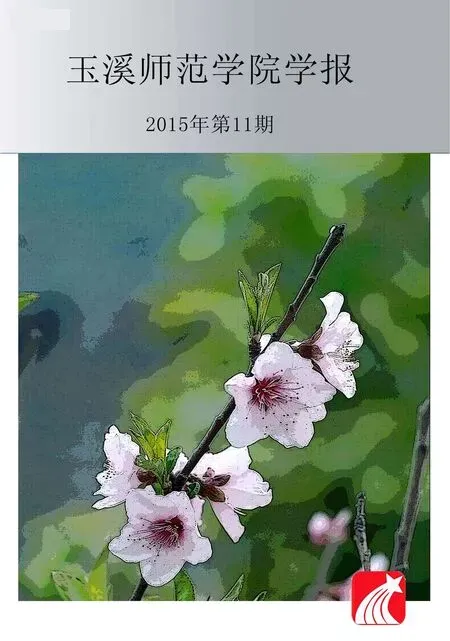复仇无聊与无聊的复仇:重读《复仇》
2015-02-14朱崇科
朱崇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
复仇无聊与无聊的复仇:重读《复仇》
朱崇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东广州510275)
鲁迅;《复仇》;看客;劣根性;无聊复仇
鲁迅先生在《复仇》中其实有其精心创制:他设计了精妙的复仇策略,以鲜活加以诱引,以干枯进行对抗,对比的手法、诗性的张力批判其间的劣根性,尤其是看客们的内在文化质地。同时,在此文中,鲁迅也呈现出其常见的复仇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文本中也暗含了复仇的无聊性,也即裸体男女的路人之间有劣根的共通性,而其自我干枯至死亦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乃至缺憾。
毫无疑问,复仇思想乃至哲学是贯穿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追求和行动实践,它绝非简单“有爱才有恨”的浮浅辩证或拙劣注脚,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多元立体的伴随性存在。而且,在鲁迅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文体创造中都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和特征:简单说来,如:为追求国富民强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向帝国主义复仇的南京读书及留学日本时期;作为个人“无治主义者”/启蒙者的向愚昧的庸众的复仇,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是《呐喊》《彷徨》时期;而作为国民劣根性批判者,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坚守者,向传统中国文化糟粕及其代理人的复仇,如《故事新编》及后期杂文时期。毋庸讳言,上述复仇内容是相对犬牙参差的,互相渗透与勾连。《野草》中的《复仇》大致属于鲁迅的彷徨时期。
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对此文的解读颇多说明,如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就有明确的说明,“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而后在1934年5月16日给郑振铎的通信中提及,“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相较而言,后世的论述和解读多受此影响,也多围绕此点。
简单而言,有关《复仇》的研究观点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种,复仇看客/旁观者/庸众。有关此问题亦有争议,比如早期(1981年)的孙玉石就认为,这是鲁迅的历史局限,“鲁迅是自己时代的‘人之子’,而不是超越历史的‘神之子’。他无法摆脱时代和世界观给他的带来的历史局限。鲁迅没有掩盖这些思想的阴影。”而陈安湖则认为,这种批判亦有其意义,“作者批判群众与批判反对统治者不同,目的是促使群众去掉落后性,在思想精神上‘即于诚善美强力敢为之域’,成为强国兴邦的主力。”而后来(1999)的孙玉石却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鲁迅长期以来的精神批判,也是沉思很久的生命哲学,并认为他的复仇观和尼采与阿尔志跋绥夫不无关联。
第二种,和复仇结合的婚恋关涉。如李天明就认为这是鲁迅不和谐婚恋的反映,因为《复仇》中有些原本可以和谐的形象之间具有不和谐和冲突,“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形象之间的情感冲突是鲁迅自己不和谐情感生活的形象化,《复仇》是这种冲突达到顶峰时最惊人地诉诸感官和情绪的表达。”而胡尹强则认为这是鲁迅剑指爱情的偷窥者,“《复仇》里的旁观者,不是一般的旁观者,而是刺探、窥伺诗人恋爱隐私,以便过后津津乐道、到处传播的旁观者”。
第三种,认为这是指向先觉者的双刃剑。如李玉明指出,“在鲁迅的观念中,现实异己力量又以一种庞大而凝固的面目出现,因此,有时候,他又痛感这种韧性的战斗无异于一场无限无尽的精神消耗战,穷于应付,不见战绩”,“‘复仇’在鲁迅这里是一种‘自残式’选择,呈现着其内心深处巨大的矛盾和怀疑。”
上述种种,固然可以新人耳目,但其间同样亦有可继续探究的空间。在我看来,《复仇》中既呈现出鲁迅对无聊(看客)的复仇,同时却又呈现出复仇的无聊,前者相对彰显,而后者却相对潜隐。而恰恰是后者,却很幽微的呈现出鲁迅特色的复仇及其问题(当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与否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探勘。
一、复仇无聊
和鲁迅《野草》其他篇章的精雕细琢、独出机杼类似,《复仇》同样也显出鲁迅的匠心独具。即使在大家熟知的复仇看客/旁观者主题上,他也采取了相当精彩的策略。
1.如何复仇?
在复仇无聊中,鲁迅呈现出双重的复仇技艺/策略:既引蛇出洞,又冷静虐杀。
以鲜活引诱 面对无聊的庸众和相对沉寂的存在,鲁迅首先书写出令人血脉贲张的裸体,这其中自然有躯体的活力、温热,“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同样,这躯体之间的姿态又引人遐想,“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而这里的“大欢喜”首先呈现为生命的酣畅存在、活力四射。
其次,鲁迅继续推进身体的诱惑力,虽然依旧以幻想的形式:(1)用利刃刺破皮肤,血溅/血洒杀戮者,“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2)鲁迅继续利用大欢喜隐喻这种酣畅淋漓,“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种是奔向轰轰烈烈的死亡,另一种则是杀戮中的喜悦和释放,杀戮者亦有所得,可谓生与死各得其所。
这种幻想仿佛亦是为旁观者的一种预设性演出,旷野中的两具裸体坦诚相对,“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往往会有论者将此对裸体视为爱人,这更多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有三个层次,如范美忠所言:(1)鲁迅分别与朱安、许广平、周作人之间的爱恨情仇;(2)恋人之间的相互吸引、爱恋温暖又相互排斥;(3)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爱恨纠缠。
不必讳言,二人之间的关系更该是志同道合者,他们颇具活力,无论肉体还是内涵,又颇具张力,本该如常人所料,或拥抱,或杀戮,但最终只是沉静相对,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像是唱双簧的搭档,既相互贬损、争锋吃醋,又惺惺相惜、心照不宣。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鲜活的还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诗性书写,无论是大欢喜的神采飞扬、重复性强调、层层递进,还是具体文字的诗性细描,都令人怦然心动,如人所论,“《复仇》中有人物,有动作,叙事性因素很强。但作者不是用叙事的笔墨展示一幅清晰明了的画面,而是用诗笔创造出诗的意象,辅之以起伏交错、回旋呼应的旋律配置,使作品具有诗的鼓惑力和音乐的感化力,将‘复仇’的诗思深沉含蓄而又强烈动人地表达出来。”
以干枯对抗 不必多说,看到对抗的两具裸体的好事的旁观者蜂拥而至,“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他们颇有期待,希望裸体的二人制造更大刺激,来抚慰他们被挑起的浮浅窥探欲望,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易言之,两具裸体把自己站成了塑像,只供人民瞻仰,却不用来满足闲人们浮泛的期望,于是人们开始无聊,无聊之后互相传染,等看到“圆活”变成“将干枯”时,再也无法忍受索然无味,只好离去,“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而文本的结尾令人拍案而惊讶,“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裸体的他们以干枯消解无聊,同时又以死人的眼光鉴赏路人们的干枯,得到复仇的“大欢喜”。这里的大欢喜其实是复仇成功、哪怕生命老去同归于尽的喜悦。如张洁宇所言,“这个‘大欢喜’不仅仅是生或死本身的大欢喜,更带有一种快意绝望的抗战之后的非常彻底的大欢喜”,那是一种“决绝的、清醒的、悲壮的快意”。
2.无聊看客
毋庸讳言,文本中的复仇对象就是一群看客,这是鲁迅在其系列创作中精心炮制的文化群体图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精彩创制与描述之一。在其小说中亦屡有提及,如《示众》中的不断游移的猥琐群像,《阿Q正传》结尾里阿Q被杀头前游街时感受到的看客们的冷漠与吃人本质;《药》中深夜里看夏瑜被杀头而仿若被捏着脖子的鸭子描述中呈现出的无聊又愚昧无知,甚至到了《呐喊·自序》中鲁迅把幻灯片事件浓墨重彩、郑重其事加以反思,不光是剑指当事的中国人、看客,甚至带入了观片的自我,震惊、愤怒、绝望之余明了和强调改造思想和灵魂的重要性。
焦点模糊 需要强调的是,看客/路人们往往是一群脑袋空空、无聊空虚的行尸走肉,“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可以反证出他们一如芦苇浮躁、夸饰,却腹中空空,他们没有自我、没有知识,因此也往往很容易让琐事变成自己关注的焦点。鲁迅在文本中设置了两个对站的裸体,这当然是极有吸引力的焦点之一,于是“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
但同时因为他们的期待落空,迟迟得不到新刺激的确认和回应,同时又因为缺乏明确焦点和成熟的自我,他们其实亦没有耐性、毅力和恒心,于是只好无聊的走散,意兴阑珊。鲁迅这两处书写都极具诗性色彩:一个是他们的群体盲动性,貌似强大多元其实枯燥无味、杂乱无章,而另一个则是书写他们之间互相传染无聊、无知甚至某种程度的无耻,把无形的无聊写得有形/有型,极其传神。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行尸走肉自然缺乏真正的焦点、兴趣,更遑论建构主体性?鲁迅对此早有精辟论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复仇》中间对路人们穷极无聊的书写不过是一种实际的再度验证罢了。
脑残嗜血 或者是由于统治阶层的长期奴化专制所致,这些路人们往往奴性十足,但同时却又在“无特操”的懦弱卑怯之余相当嗜血。相较而言,作为羸弱动物性的存在,他们的脑海中更多只剩下性与死,也就是鲁迅设计的拥抱或杀戮。一方面是性本能,文化上的传宗接代,也要为统治阶层提供新的生产力,但在性方面却往往显得猥琐不堪,如鲁迅在1927年9月24日撰写的《小杂感》(后收入《而已集》)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另一方面,正因为无聊懦弱,不敢自己杀人或激烈反抗,他们却偏偏期待杀戮,这样既可以满足自身的好奇心,同时又借强者的精彩表现实现精神穿越或逆袭,践行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奇怪逻辑。当然,能够躲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看别人被杀或互相残杀恰恰也是他们吻合,乃至迎合统治阶层暴力、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
整体而言,鲁迅采取了以鲜活加以诱引,却又以干枯进行对抗的双重策略复仇无聊,甚至觉得大快人心,这自然也是一种对症下药,如人所论,“《复仇》以仇恨的方式宣泄了鲁迅自我对‘看客’的感受和情绪,形成了‘复仇’话语。其中‘路人们’的热衷、觊觎和‘青年男女’的憎恶无动的对立,是‘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看客’对拥抱杀戮的赏玩嗜好,及其被‘复仇者’的使其无戏可看倒是疗救的‘复仇’,显示出鲁迅对改革思考的独特与深刻。”
二、无聊的复仇
《复仇》中的复仇风格颇具鲁迅特色,但其中似乎亦有值得继续探勘的其他可能性,或者说这种复仇的效果似乎仍有可斟酌之处。
1.鲁迅式复仇
考察《复仇》文本内外的鲁迅风格和实质,它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复仇者和被复仇者之间的“肉搏性”。这样的结果如果细究原因亦会很复杂,但简单而言,亦可最少分成三个层面:
鲁迅自身的自反性(self-reflectivity) 如从创作上看的话,从一开始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狂人在反省封建制度/文化“吃人”的本质时亦未忘记自己的吃人血统/原罪,而到了和《野草》同时期(或交叉)的《铸剑》时,小说中作为复仇之神的黑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最终变成了一锅煮三头的鏖战狂欢,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复仇主体与复仇对象同归于尽了。
繁复强大的旧阵营与“中间物”的启蒙者/复仇者之间的角力 这个似乎无需太多解释,一方面是旧文化阵营依旧相当强大,尤其是数千年的文化/糟粕传承往往根深蒂固,随手拈来,鲁迅对此往往具有深刻和犀利的认知,“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复仇者的“中间物”特征,他们是来自旧阵营的反叛者,但因此也不得不带着镣铐舞蹈。
鲁迅式复仇的牺牲精神与承担感 某种意义上说,在鲁迅的《野草》文本中,复仇者往往既具有战斗的韧性,但同时亦勇敢刚猛:从《影的告别》中的没入黑暗中独自吞没黑暗的“影”,《死火》中宁愿烧完的“死火”,到《秋夜》中遍体鳞伤却依旧指向天空不屈作战的枣树等等,诸多意象无不具有这种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气质。
《复仇》自然亦不例外。某种意义上说,如前所述,鲁迅的复仇自有其机智策略,既以鲜活诱引,又以干枯对抗和消解,但同时,如有论者研究“复”[復]“仇”[雠]的字源学含义后指出,鲁迅原本想在路人与“包孕了二龙交合腾飞趋向的裸体男女”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但因为不对等而失败,并解释道,“作品从爱出发,本欲沟通现代子民与他们的民族雄魄的联系。然而,当陷入一种龙种与跳蚤的巨大逆差的情境之中的时候,这种爱就转化为恨。到了这里,就与作者的解释相通了。”
但似乎惟其有深爱才同时有大恨,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回答许广平问询如何面对“歧路”的时候曾写道,“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鲁迅的刚硬与柔韧并存特征,但从和老虎的关系处理上鲁迅复仇的硬气也因此彰显。为此,他在《复仇》中似乎刻意强调“大欢喜”,无论是生机勃勃、圆活孔武,还是酣畅淋漓、神采飞扬,无论是痛快杀戮,还是痛揍无聊,都有一种决绝,乃至凄绝之美。
有论者指出,裸体男女与路人作为两种意象,不乏对立性(男女内部也有对立):一个意象诱惑,另一个则拒斥;一个是肉欲的,另一个则显得粗俗。若说第一个意象是色情的,那第二个则是反色情的。在《复仇》中,鲁迅其实一方面强调男女内部、男女和路人之间的对立,但另一方面却又呈现出复仇的“肉搏性”,乃至彻底共同灭亡。而在文本里,裸体男女最终将干枯而死,其间的关系其实又是难以彻底割裂的,甚至也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裸体男女对路人的一种独特警醒乃至拯救意识,如人所论,“这就是鲁迅式的复仇,以精神的意志反击精神的弱点,让无聊的人更加无聊,让空虚的人更加空虚,在针锋相对的抗拒中高扬‘个’的尊严与力量,映现‘众’的猥琐与可悲,从而使复仇成为一种揭示,一种唤醒式的拯救。”
2.无聊的复仇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复仇》中其实亦有复仇的无聊性存在。只是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潜行物,而绝大多数论者不愿、不能或不敢指出。
劣根的共通性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设置裸体男女对站,其实在除了大力彰显和批判国人在性与死中的虐杀和猥琐劣根性以外,亦有其相对哗众取宠/故意折腾的一面:两个裸体之间并未真正仇杀,只有对峙的张力,反倒是诱引了无数无聊的路人/看客围观,形成一种以干枯为主体风格并针对无聊看客的虐杀。这其实也反映出鲁迅内心对庸众的一种复仇心理,“作为启蒙知识分子,面对群众无从启蒙、无法启蒙而导致启蒙无效的紧张、困惑、悲观、绝望以至‘精神报复’可说是其内心深处最为沉重的淤积。”
饶有意味的是,《复仇》中的槐蚕(还有蚂蚁)意象原本是鲁迅用来嘲讽路人这群“乌合之众”的精神品格的,他们无知无聊“无特操”,但也可以残忍残暴。但在文本开头,鲁迅在书写血管里热血的密度时,却也以槐蚕作为比喻,“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仔细反思这段话,其实也隐喻了裸体男女血液中和无聊的前往窥淫的路人们之间有着的共通性,易言之,裸体男女在引诱并以干枯消解路人们的无聊时,他们本身亦有其无聊特质,这其实已经不单纯是鲁迅复仇的特色问题,而是裸体男女的“中间物”特征,或至少也是拿无聊作有趣来对抗无聊的悖谬式操作,符合鲁迅1925年3月11日给许广平心中所言的,“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
自我枯干 但同时又不免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裸体男女身上亦有劣根性,但相对而言,他们是有活力、有担当、神采飞扬的精英个体,但结果却是以自我的干枯作为复仇无聊的代价,这的确有点得不偿失。这个结果大概可以推出可能的原因:鲁迅自身的浓烈的凄惨、苦闷、彷徨感难以排解,哪怕是采取这种不平等的同归于尽的方式亦难以彻底解决,但也已经是一种宣泄和部分解脱,他将之命名为“大欢喜”,但如李何林先生所言,“作者对无聊旁观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实际情况是,原本该死得其所的路人/看客们只是觉得无聊,而因此慢慢散去,但众所周知,奴性十足、无所事事的闲人却是层出不穷、代代相传。裸体男女的自我枯死某种意义上说,更多是一种存在的象征,一种短暂的刺激,希望(部分)路人们可作一刹那的反思。从这个角度思考,其中有其苦心和救赎意义,但无论如何,从整体上说,鲜活的裸体的自我干枯是很大损失,并不太符合鲁迅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这种态度毋宁更是彷徨期鲁迅的一种激烈而飞扬的负气和豪气的自我抚慰,如人所论,“这种复仇的方式是经历了失败的改革者对于旧社会特别是对不自觉地表现出国民劣根性的群众充满了憎恶的复仇心理的表现。”
三、结 语
鲁迅先生在《复仇》中其实有其精心创制:他设计了精妙的复仇策略,以鲜活加以诱引,以干枯进行对抗,对比的手法、诗性的张力批判其间的劣根性,尤其是看客们的内在文化质地。同时,在此文中,鲁迅也呈现出其常见的复仇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文本中也暗含了复仇的无聊性,也即裸体男女的路人之间有劣根的共通性,而其自我干枯至死亦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乃至缺憾,虽然酣畅淋漓,但终究令人扼腕。不过,鲁迅毕竟是鲁迅,“如果失却了多维多重富有个性色彩的复仇言论和情绪,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他对于恶势力与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鞭挞,也就不会那么有力,解渴,解气。”
Revenge on Boredom and the Boredom of Revenge:After Re-reading Revenge
ZHU Congke
(Asia-Pacific Research Institut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
Lu Xun;Revenge;onlooker;viciousness;boredom revenge
Lu Xun’s Revenge is an elaborate story.The revenge plan is ingenious,with irresistible lure and outright confrontation,while the viciousness,particularly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onlookers,is brought under fierce criticism in sharp contrast and poetic tensions.The common features of revenge are revealed in the story.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that implied in the text is the boredom of revenge,or the shared viciousness among the onlookers,and self-dry-to-death as a helpless choice.
朱崇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文学、华文文学、鲁迅研究、文学理论。
l210.97
A
1009-9506(2015)11-0014-06
2015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