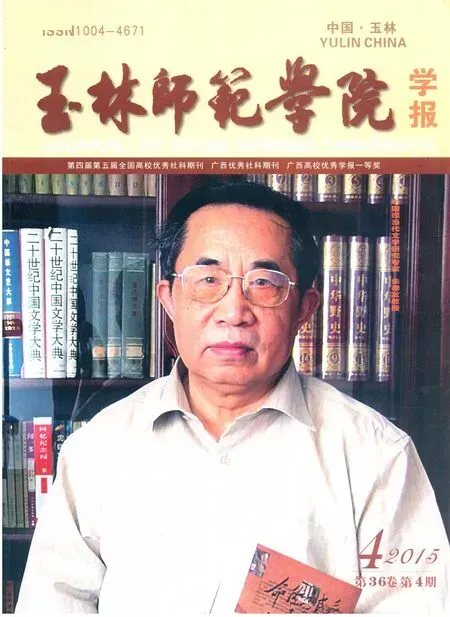论超验主义视阈下谭延桐的超验诗歌
2015-02-14罗小凤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论超验主义视阈下谭延桐的超验诗歌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谭延桐是诗坛的一个“异数”,在诗歌上有他独特的追求,其诗被称为“超验诗歌”,蕴含着丰富的超验主义色彩,在诗歌场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一格。他的诗试图建构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直觉,呼唤灵性的回归,以诗传达神秘世界的体验与感悟,构建充满童话色彩的寓言世界,提供了一批富有超验性的独特的诗歌文本。
谭延桐;超验主义;超验诗歌
无论是在广西还是在整个中国诗坛,谭延桐或许都是一个“异数”,这不仅指他为人的超拔、脱俗,具有禅风道骨,亦指他独特的诗歌追求。他的诗被他贴上“超验诗歌”的标签,蕴含着丰富的超验主义色彩,在诗歌场域里独树一帜,自成一格。
所谓超验主义,最初兴起于新英格兰,是19世纪早期在美国兴起的一场文学、政治、哲学的思潮,核心思想是强调精神,反对趋物主义;重视个体,追求自我培养、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上帝的象征,人可以通过自然达到对心灵的抚慰。在文学领域中,超验主义以爱默生、梭罗为代表,他们对超验主义进行了文学性的阐释,要求人们返回自然,返归生活本源;强调精神或“超灵”的作用,强调人性中的神性;呼唤灵性回归,主张通过构建诗人的内在宇宙空间,完成人的诗意救赎。谭延桐在其诗中实践了超验主义的这些观点与理念,正如他在谈诗时所指出的:“诗歌紧紧抓住的应该是自然性、生命性、心灵性、艺术性、独特性、超越性和惊异性。”[1]他的诗试图建构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强调直觉,呼唤灵性的回归,以诗传达神秘世界的体验与感悟,构建充满童话色彩的寓言世界,提供了一批富有超验性的独特的诗歌文本。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悟
谭延桐是一个充满博爱精神、具有儒者风度的诗人,他笔下有大量书写自然的诗,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传达人对自然的思考。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席勒曾指出,人们喜爱自然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自然世界中发现“遵循自己法则的存在,内在的必然性,自身的永恒统一”,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化身:“它们是我们理想之最圆满的表现,因而它们使我们得到高尚的感动”“它们是我们曾经是的东西,它们是我们应该重新成为的东西。我们曾经是自然,就像它们一样,而且我们的文化应该使我们在理性和自由的道路上复归于自然”。[2]而超验主义者则认为自然界万物都有象征意义,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具体体现。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便曾在《论自然》中首次阐述其超验主义观点时要求人们不是通过先辈的眼睛注视神和自然,而是自己直接跟宇宙建立联系;他在《神学院讲演》中则大力推崇人本主义,认为人就是一切,自然界的全部法则就是人自身。可见,超验主义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我合一的和谐关系。谭延桐的诗暗合了超验主义有关自然的观点。他热爱自然,在大自然中净化心灵,独自内省,体悟人生真谛。在他笔下,自然中的万物都有灵魂,人类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启示与力量,如《风是我师傅》中他将“风”视为师傅,在他笔下,“风”是无所不能的:“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水上显形/就在水上显形。想在树上显影/就在树上显影”“身怀绝技”。在《有山有水有树的地方》《我们有开不完的花》《大树藏了很多唱片》等诗中诗人在与自然的交融中顿悟,感受到宇宙万物的美好和生命的希望,诗人对自然充满敬畏。
在谭延桐笔下,自然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物我合一,而实现方式则是“移情”。他曾谈及他对“移情”的理解:“移情,就是将人的感情移植到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中,使物也有了人的感情。看见花开,心就和它一起开;看见鸟飞,心就和它一起飞;看见灯亮,心就和它一起亮;看见火灭,心就和它一起灭……再也简单不过。”[3]谭延桐由于热爱自然而移情于自然,正如里尔克所指出的:“自然界,我们操作和使用的万物,都是暂时的、脆弱的;但只要我们还在此,它们就是我们的财产和朋友,就是我们苦与乐的知情者,正如从前它们曾经是我们先辈的熟人那样。因此,不仅不要粗暴对待和贬低一切此在的东西,相反,正因为它们与我们都具有短暂性,这些现象与事物应当被我们深切地理解和转换。”[4]在谭延桐的诗歌世界里,人常为自然所感化,人与自然是同一的,如《剪刀发言》《那只喇叭》《还是那朵云》《云的事业》《另一阵风还在》等诗都将“物”移情为“人”的知觉、感觉、心理、神态,让“物”都有了生命、思想、感情甚至脾性。《我们有开不完的花》里的“我们”则已完全“物”化,诗人以“花”的身份说话,完全与“花”融为一体,“花”与“我”互喻甚至互换:“它们败了,我们继续开/开花。这不是一个开花的季节,我们也/继续开。开给喜欢花的人看/开给自己看。一朵接一朵地开,直到远方的空气/也收到了我们让风托运去的最新鲜的祝福/我们的祝福都是真实的/芬芳的”“开花,就是把我们心里的形象/都搬出来。把我们心里的颜色都拿出来/把我们心里的香气都捧出来”。
或许正是由于谭延桐对自然充满敬畏,也充满爱护,他的诗充满了生态意识。如《鸟窝》《鸟窝空着》《再次把目光投向鸟窝》《都想错了那只鸟儿既不是在替你飞也不是在替他飞》《抓一把鸟语》等诗,都抓住“鸟”这一自然界中最有生命力和灵性的生命个体展开诗思,但诗人不是抒发对鸟的感情或描摹鸟的姿态、形态或样貌,而是对鸟的生存状态显露出担心、忧虑与同情。众所周知,现代人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砍伐森林等行为严重破坏、劫掠了鸟的栖居之所,影响了鸟的生存状态,诗人敏锐地将之写入诗中,呈露出鲜明的生态意识,折射了他对自然的爱护、敬畏之心。
二、超验直觉的顿悟
超验主义认为人能够通过直觉认识真理,因而强调直觉,强调瞬间且强烈的感觉和反应。这亦是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他曾指出,人可以通过直觉(或悟力)从自然中感知上帝的神奇;直觉所感应的生命的内在法则完全同自然的外在法则相对应,而外在法则是由感官所感知的各种自然形象揭示出来的,因而自然万物皆具象征性;与自然环境直接、瞬时的交流能(长远地)作用于人的灵魂,使之逐渐得到净化和升华。这种强调直觉的观点与中国的禅宗强调“顿悟”是对应的。禅宗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种“顿悟”就是一种直觉能力,看似神秘而更内在,极端浓缩了想象所需要的时间过程,是一种超越人的感觉经验世界的主体限界而直接确认超感官的自在世界的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带有神秘性、超验性。这种直觉思维的起点是人在现实生活中所经验的感觉、思想、意志和实践,终点是超感官的自在之物,而这起点与终点之间根本不存在逻辑通道,直接从人的主体世界向客体世界跳跃,其内容不是单纯的经验材料,而是关涉哲学的基本的、本体的问题。谭延桐的诗歌注重描写人的感觉,常通过视、听、闻、嗅等各种感官所接受到的信息而获得一些新鲜体验,以此传达他对人生的体悟,创造了一个“自明的空间”[5],如《顿觉天地移动》的第一节:
那是一颗从神话里升起的太阳:年轻,健壮
火热,爽朗,生机勃勃,势不可挡。他一起身便带动了万道霞光
王的风范,一下子
全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诗人捕捉住一瞬间的感觉而展开想象与书写,他充分调动人的感官以感知意境,让人在意境的感受、领悟中获得启示。《夏天的剖面图》则以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所接收的信息而呈现立体的画面感,“干涸的河床像一柄利剑,插在/湖泊的心脏上”“他的身体像一块木炭”“他,这棵没人理会的树木,此刻/正和风守在一起,听风/述说着心中的忧伤”“我和他一样,被租给了热浪/——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各种感觉的叠合形成了强劲的冲击力。《风在诗经里睡着了》《眼白说了算》《红色株连了白色》《故事卷土重来》《从电话里搬出来了》《一个雨滴落入湖中》《石头的咒语》《书里有哗哗作响的声音》等诗都以直觉捕捉经验、体验,富有画面感。正如探花所评点的,语言富有爆发力和弹性并以此制造视觉或听觉的冲击是谭延桐的拿手好戏。
需要注意的是,谭延桐的诗歌所指向的并非止于诗中所呈现的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所呈现的图景指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只有诗人的直觉意识能够体悟,因而在他的诗歌中,他常以梦、幻觉等方式组合现实世界的片断、碎片,在他随意流动的思维、情绪间,诗人丰富的想象力组构出神秘的超验世界,最大限度地展示一种神秘的超真实感。如《进入本色文件2》完全以幻觉、梦幻的方式展开诗思,诗人纵横驰骋他的想象与联想,“我打本色文件1里出来,进入本色文件2/没人能够找到我,因为他们不知世界上有个本色文件2”“我在本色文件2里静静地待着,写诗,写歌/写完了,就像我的诗和歌跑到杂志或舞台上那样/跑到开满了寓言的旷野上,或站,或坐,或躺,或跑……/总之都是一些非常自由的姿势”“热的时候/我就进入本色文件1乘凉,冷的时候我就进入本色文件2烤火/那些上蹿下跳的烟花从此从我的诗和歌里彻底消失”,诗人简直就是在做梦,或是记录梦境的片段,但又显得那么真实,呈现出神秘性、超验性。《场景》《我曾三次遇见爱弥儿》《顿觉天地移动》等诗中诗人都是通过不同意象、场景的并置而使诗以奇特的方式联结起来,超越时空,充满一种神秘感,诗人从中获得直觉式的顿悟,浸润着原始的神秘与灵性。
神秘世界的传达
正如海子的麦地世界里充满“神秘性”一样,谭延桐的诗歌里亦流淌着一种神秘感,他多次写“风喜欢它的幽深/和神秘(还有许多说不出的内涵)”(《大树收藏了许多唱片》)、“那个神秘的花园里什么花儿都有/就是唯独没有/枯萎的花”(《替赫哲恩喂天马》)、“慢慢转化成一种有棱角的力量/(神秘的,特有的,持久的)/慢慢让力量长出一副能够让空气迅速兴奋起来的/鹰一样的翅膀”(《给倒影颁发一个棱角》),都试图呈现一种“神秘的力量”。《虽然只有二两》对这种“神秘的力量”进行了集中呈现:“只有二两,却毫不影响它在我心上的分量”“它是建在骨头里的一个神秘的博物馆/它是用神话打造的无所不能的魔棒/它,不是一个人,却比所有的人都有力量”“就连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和影响”。这种力量无时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且无所不能,显然是神秘的、超验的。
在谭延桐眼中,自然界是充满神秘的,万物皆有神性、灵性,鸟儿的羽毛“都是阳光做的”(《都想错了那只鸟儿既不是在替你飞也不是在替他飞》)、“我愿意承认,是某个仙人的灵魂/变成了那朵飞升的云”(《和云一起》)。因此他常将一些日常事物、自然存在物化成超验意象,以此传达不可言说的神秘世界,从而把读者带进一个充满神性的超验世界。他笔下有很多充满神秘超验因素的意象,如“风”“精灵”“鸟”“树”等,均指向一个不可见、不可触摸、不可言说却可以感知的超验中心或神性世界,这个世界是建基于人类而又超越于人类的,如《另一阵风还在》中的一节:
一阵风不见了(可能是疲倦了吧)
说不见就不见了。可另一阵风还在(我知道/这另一阵风不会停下来)
这另一阵风当初究竟是谁派来的
已经无关紧要
会“疲倦”“说不见就不见了”“究竟是谁派来的”等语句将“风”移情为人,使“风”成为一个带有神性、不可言说性的超验意象,内蕴只可意会的丰富寓意。《那棵树可以和精灵比》《火盆子》《在菩萨的耳朵里沉思》等诗都是如此。
在谭延桐笔下,人也是具有神性、灵性的,正如舍勒尔曾指出的:“在普遍的生命进程的巨大时间长河中,人不过是一短瞬的节庆,然而,人也意味着使神性本身的生成规定得以实现的某种东西。人的历史并非是为一位永恒完满的神性的关注者和审判者演出的一场戏,而是超升到神性本身的生成之中。”[6]人的灵性、神性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对此刘小枫曾指出,灵性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根基,是人的生命的依据,也是人类世界的依据”[7]。人的灵性其实就是一种人内在的生命感受性,是一种关涉宇宙与个体关系的生命意识,只有拥有这种灵性,人才能感知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才能体悟人作为存在体的存在本身。由于谭延桐对人的神性、灵性的认知,他对生死、灵魂等进行了诗意的探讨与思考。在《死亡:不太明白》中诗人思考了人死后“究竟都干些什么”“究竟有没有天堂/或地狱,在等着”“死究竟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别的什么颜色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方的还是圆的”等终极问题。诗人对灵魂同样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笔下,万物都有灵魂,如“即使它们的灵魂突然追了上来”(《高档餐馆》)、“我愿意承认,是某个仙人的灵魂/变成了那朵飞升的云”(《和云一起》)、“我在拾掇我的长篇的身体和灵魂,好让它更有优越感”(《为此我暂时放弃了去哲学王国考察的行程》)、“你在环绕大地的瀛海边看到了许多过去的鬼魂/每一个鬼魂都没能绊倒你的视线”(《奥德修斯》)、“每到夜晚,我的夭折的时光的魂就会发出声声啸叫/我知道,它们是在提醒我”(《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它/很轻,也很重,轻如白云,重如白云摄取的魂”(《春天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补品》)、“突然就很想念/那个冰肌玉骨冰魂素魄的冬天”(《突然很想念那个冬天》)、“把那些掐灭花魂的冰雪全都扑灭,扑灭吧”(《另一阵风还在》)。
三、童话世界的构建
超验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应而存在的,属于不可知的、彼岸的神秘世界,因而其超验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现实性而言的,而童话、寓言色彩便属于这种超验性的属性范畴。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的,作家描写的一切都是童话。谭延桐虽然已年逾五十,但他却以一种原初的眼光和赤子之心看待周围的世界,以儿童视角观察、思考世界,因而其诗充满着童话、寓言色彩,构建了一个充满童话、寓言的超验世界。他曾多次直接写到童话:“说残废/就残废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轻松松地走进/那个盼望已久的童话里了”(《抓一把鸟语》)、“我曾三次遇见爱弥儿,一次是在风里/一次是在雨里,一次是在风雨交加的童话里”(《我曾三次遇见爱弥儿》)、“那一刻,正侧着脑袋的阿方/也侧着身子,走进了一个刚刚落成的童话”(《我省略不掉那块西瓜的味道》)。
根据谭延桐的“移情”说,一切事物如花草鸟兽等都与人一样拥有鲜活的生命、真情实感、丰富的思想与语言,而这显然属于童话逻辑与儿童思维,但正是这种逻辑与思维使他笔下充满了童话色彩,如《云的事业》中云有“事业”、“月亮很忙”、“月亮也总是恋恋不舍”、太阳“一直在默默关心月亮”等都是将“云”“月亮”拟人化、童话化了;《得罪和不得罪就像香水的配方》中阳光“乐善好施”“得罪了我”,云朵“坐禅”、鸟儿“终生爱自由”等都充满童话色彩。而且,谭延桐在安置自然意象时极其善于调遣“天使”“精灵”“神仙”等带有童话色彩的意象与之形成映衬或对应,如《尘土飞扬》中的“天使”、《秋天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中的“花神和花仙”、《那棵树和精灵比》《火盆子》中的“精灵”、《还是那朵云》中的“花仙子”、《和云一起》中的“仙人”、《在菩萨的耳朵里沉思》中的“神”等,形成了谭延桐独特而充满童话色彩的意象群,构筑了一个超脱于凡俗的童话世界。
谭延桐亦擅长于想象一些富有童话色彩的场景,如“曼诺莉小姐过去一直住在管子里”(《曼诺莉小姐过去一直住在管子里》)、“每一棵大树都收藏了许多老唱片”(《大树收藏了许多唱片》)、“就连那些勇敢的月光/和星光,也受伤了,伤势很严重/地上,全是死去的火焰,以及奄奄一息的光”(《斧头相当激动》)等都是恣意驰骋想象而构造的童话情境,富有童话色彩。《火盆子》《梦见了六颗太阳在游泳》《留着自然发型的鸟儿》《剪刀发言》《抓一把鸟语》《进入本色文件2》等诗都构筑了富于童话、寓言色彩的场景,呈现了诗人以原初的眼光和赤子之心对世界的思考,富有超验性。
谭延桐还善于使用童话的语言进行书写,如《我明显地感觉到》中的“浪花经常嗑牙”“我经常/看见浪花的牙齿把掉在大海里的阳光/或月光,或星光,咬得碎碎的。那一刻/我的心也碎碎的。我明显地感觉到浪花的牙齿正在津津有味地/咬噬着我的心,啃噬着我的骨头”等诗句中“浪花”有牙齿,完全是用童话的语言进行书写;“无意中抓了一把鸟语,货真价实的/把它捧回了家,放在/饿了的音乐里,只为了,让音乐和我一起高兴起来/并抓紧荡漾。在鸟语的帮助下/完成施工已久的梦想”(《抓一把鸟语》)亦是用童话的语言进行书写,勾画了富有童话色彩的寓言世界;《那条路很长》《尘土飞扬》等诗中亦不乏这样携带童话色彩的语言。
正是在儿童视角、童话逻辑、儿童思维、童话情境与场景、童话语言等的调遣与使用中,谭延桐构建了一个充溢着童话色彩的童话世界。读谭延桐的一些诗,你会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个不沾染俗世尘土、烟火、噪声的纯净世界,那些童话逻辑下的思考、那些童话场景、那些童话般的语言都让你瞬间与现实世界拉开了一定距离。
谭延桐通过他的超验诗歌构建了一个具有超验性的诗歌世界,以此传达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批丰富而有意义的超验文本。 ■
[1]谭延桐.谭延桐谈诗(十一)[EB/OL].http://blog. sina.com.cn/tyt519.
[2]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M].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263.
[3]谭延桐.谭延桐谈移情[EB/OL].http://blog.sina.com. cn/tyt519.
[4]林笳.里尔克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62.
[5]编者.诗刊,1999(11).
[6][7] 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55,156.
【责任编辑 潘琰佩】
On Tan Yantong’s Transcendental Poetry in The Field of Transcendentalism Vision
LUO Xiao-feng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Tan Yantong is a heteromery in poetry field. He has special pursuit on poetry. His poetry is called transcendental poetry, which contains rich colour of transcendentalism, thus he has developed a school of his own. His poetry tries to build a kind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emphasizes intuition, calls for regression of intelligence, expresses the feeling of mysterious world, constructs a fable world full of fairy tales, and he created series of unique transcendental poetry.
Tan Yantong; transcendentalism; transcendental poetry
I207.2
A
1004-4671(2015)04-0109-05
2015-05-21
此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化研究”(课题编号:15XZW035)的阶段性成果。
罗小凤(1980~),湖南武冈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