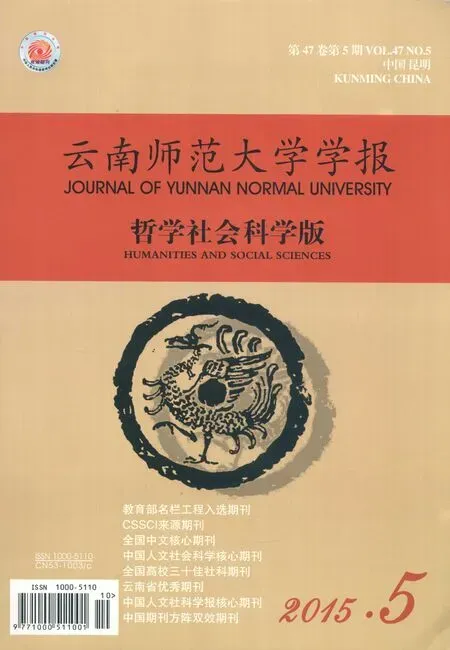国家治理背景下的公民身份及法治教育*
2015-02-14张晓燕
张晓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
国家治理背景下的公民身份及法治教育*
张晓燕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
以“法治国”和“社会国”为基本维度展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当下中国的国家公民身份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公民素养培育需求,作为服务于培育公民身份的法治教育应该对此做出回应和调试。本文试图对我国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公民身份内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以及法治教育对此可能的回应和贡献(如何培养我们需要的公民)进行探讨。
治理现代化;公民身份;法治教育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除了需要政治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更需要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塑造和促进。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发挥,有待于作为其构成主体的个体公民身份的激活。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共同体中,将个体与他的同胞联系起来的社会与政治关联,是人的本性所在,①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M].郭台辉,余慧元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57.即公民身份是深植于人性中的需要。但事实上,作为“天生自利”的个体,关切共同善的认同感以及与之相关的智慧与美德,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实践予以激活和培育。国民教育通常通过“本国语文”、“本国历史”、“本国宪法”、“法治教育”、“社会实践”等课程的规划与设计,以求对公民身份的激活与良好塑造。我国当下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所在,这就意味着作为形塑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的“法律”就不再是以单一的中立社会规范存在,而是会主动地创造出一个价值体系,形塑公民身份认知,培育公民素养。为此,法治教育不仅仅要承载,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追求的一般性的法治教育目标,即培育公民规范意识,形成公民法治信仰,而且要积极地回应法治所具体生发的国家语境中对于公民素养的要求。正如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②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14-5-5 (2).本文试图对我国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公民身份内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以及法治教育对此可能的回应和贡献(如何培养我们需要的公民)进行探讨。
一、现实与困境:好人与好公民
(一)我国法治教育的现状:以高校法治教育为视角
公民的守法精神是法治建设的文化元素,强调“主观自发性”。但是,尽管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但绝不等于说它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教育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③川岛武宣.现代化与法[M].王志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7.,将法治作为行动的基本指南,进而将其作为自身意义世界的一个部分——一种信仰来对待的前提,是要通过习得把法律变为自身掌握的一种常识,法治教育应运而生。“法治教育”属于国家推进普法工作的实施方式,但不同于其他的普法方式,其属于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自1985年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提出“法制教育”,到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法治教育”的转型,我国的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经历了“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的近30年春秋。30年的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一直都在试图通过学校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结合,给公民勾画一幅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以法治思维来确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依法办事的清晰图景。
尽管法治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依旧要面对现实抛出的难题和困境。不仅在私人领域社会成员遵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依旧不强,公共领域中官民矛盾的不断升级,尤其是社会成员对非法治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依赖,①季卫东教授曾经这样描述中国普法过程中所遭遇的窘困:“送法下乡的队伍浩浩荡荡,依法上访的队伍也浩浩荡荡,两股洪流逆向而动。”参见许章润主编.普法运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2.彰显法治教育在培育公民法治观念,塑造合格公民上存在短板。要试图弥补这一短板,就必须对当下的法治教育进行反思。作为国民教育组成部分的法治教育在当下是依循什么样的逻辑和模式开展的?这样的逻辑和模式对其回应中国问题可能存在的困境何在?法治教育(法制教育)是贯穿大中小学国民教育体系的教育,整体性地反思法治教育不是本文能力所济,鉴于高校培育对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担当角色的重要性(引领和中流砥柱),此外,高校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经历了几次有代表性的变迁,可以为本文的分析提供较为清晰的脉络,基于此,本文选择高校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所在。
总体而言,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高校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发展经历了两个有代表的阶段:
第一阶段——法律知识首次进课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的要求,学校是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阵地。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其他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设置法制教育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且把法制教育同道德品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1986年9月1日,国家教委首次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这是法律知识第一次进入大学课堂。1987年10月20日,根据新时期对思想教育提出的要求和高等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国家教委又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设置如下5门思想教育课程: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以上两门课为必修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后3门可因校制宜,有选择地开设)。②为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新形势的要求,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10月24日国家教委根据中央精神下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正式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并提出了“两课”教学新方案,一般称为“95方案”。后来为了呼应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199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全国普通高校从1998年秋季开始普遍开设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即“98方案”。无论是“95方案”还是“98方案”,对于法制教育本身没有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合并。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落实中央精神,200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把原来简称的“两课”改称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作了大的调整:四年制本科开设4门必修课,其中法制教育纳入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05”方案的调整最为直接的改变就是,将原先独立的法律基础课程与思想道德课程合并,之前的法律基础课程一般都是由高校中的法律专业院系承担,合并之后由负责公共政治课教学的部门承担。
除却在其发展过程中窥见的政治背景,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作为我国普法工作的组成部分,对其的理解不能割离“普法”这个大的背景。结合1985年~2015年6个普法的五年规划,我国当下的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作为德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我国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起源至后来的05方案提出,都被视作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教育被作为德育教育的一个部分来对待,一方面是因为,当“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国理政方式的普遍选择后,作为形塑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法律”就不再是以单一的中立社会规范存在,而是会主动地创造出一个价值体系。这就意味着法治教育一定会承载意识形态塑造的功能。事实上,不仅法治教育,任何一个现代政治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任何课程都会承载这样的功能。这在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中得以清楚地阐释。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更重要的是,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①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9.这是将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教育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的法德关系的紧密性以及“德主刑辅”的治理观念,实在法被视为是既有道德规范的宣誓,法律和道德不可分割。此外,法律一直被视为是道德调整失效的不得已使用的公器,理想的社会秩序依旧应该是建立在人民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法治教育必须以道德培育作为最根本的指向和归属,从而强调将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结合起来。
其次,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是着重“秩序维护”,强调“消极守法公民”的培育。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的内容及其教育方法选择,最终是由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目标决定的。我国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倡导的早期,一方面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恢复社会秩序,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以及“法律是统治阶级工具”的法制观,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强调培育有利于“秩序维护”的“消极守法公民”。1985年11月13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当时的司法部部长邹瑜在《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普法对于)争取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基于此,以消极守法公民培育为主要目标的我国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在内容选择上偏向刑法和民商法教育,教育手段以法条讲述和案例分析为主。尽管从“一五”普法规划到“六五”普法规划,对于普法的基本目标伴随社会变迁有所调整,如“五五”普法规划就提出,通过“四五”普法规划的实施,努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知)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行)的转变。但是,由于国家对于普法工作的重点还是强调以实现公民“遵纪守法”的消极守法教育为目标,因此“送法下乡”的思维贯穿了法治教育(法制教育)的全过程,既不强调法治教育所面对对象的特殊性(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其教育的主体是作为国家未来的青年),把法治教育建立在“法盲”的基本假设前提下,忽略教育的一体化和相互衔接对课程所提出的层次性要求,同时过分关注公民“消极守法”,忽略了公民积极行使权利的“积极守法”场域。为此,无论哪一个层次的法治教育都非常强调与公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私法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守法教育,教育内容难免重复,缺乏系统法治观念教育。尽管法治教育(法制教育)已经推行了近30年,但是讲授内容基本没有脱离“一五”普法规划所提供的模板,即讲述内容仍主要是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以私人领域规范、惩戒性规范为主的部门法。灌输教育、威慑教育在实践教育中也占据很重要的部分,宣判大会、参观监狱、惩戒法制宣传片的播放等是常见的实践教育模式。与此逻辑保持一致,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制度借助案例的讲述更容易凭借“形象化”的表达获得教学效果,因此以法条讲授为主要目标的案例教学在法治教育中占据极为核心的位置。此外,“05方案”对法律基础课程与思想道德课程实施了合并,之前的法律基础课程一般都是由高校中的法律专业院系承担,合并之后由负责公共政治课教学的部门承担。公共教学部门鲜有法律专业毕业生入职,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学教育,很难从抽象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角度开展法治教育,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支撑的部门法(民商事法律为核心的私法与日常的生活和逻辑思维最为接近,为此成为教师们比较偏好的选择)的案例讲授对其而言是更为可行的教学方式。类似教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学生能够迅速掌握一定的法律常识,但是基于该教育方法的法律知识给予是碎片化和具象化的,无助于对法律体系的整体性认知,在培育学生抽象的法律思维、观念和信仰角度容易呈现无力感。
(二)困境:亚里士多德的诘问
回顾法治教育的发展历程,法治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以“好人”为教育目标的,那么当下的“好人”培养模式(无论是基于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能否回应转型中国对“好公民”的培养要求?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一个追问:“善人(好人)的品德和良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23.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亚氏试图做出回答。首先,亚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从伦理的角度,作为一个好人的品德是什么?另一个是从城邦政治的角度,作为一个好公民的品德是什么?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但又是不同的。他先说明一个好公民的品德应该是谋求整个共同体的安全。好公民一定是回应了特定政体的治理要求的。由于政体有多种形式,适应不同的政体,显然好公民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善”的标准是唯一的,一个人之所以是好人就在于他拥有一种完满的德性。在古希腊雅典的语境下探讨这个问题,显然一个人不具有好人具有的德行,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只要其适应特定的政体需要,即好公民不一定是好人。但由于其公共领域基本上淹没了其私人领域,缺乏公私的划分,一个没有公共生活的人,无法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基本上不可能被认定为“好人”,即“好人”涵盖的伦理标准一定包括了“好公民”的标准,在此之外还包涵了宇宙间对于“善”的其他诉求,所以,好人一定是好公民。
但是,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探讨这个问题,结论就未必如此。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好人”与“好公民”问题,必须澄清两个前提:首先,当下基于公私领域的划分,强调其“公共性”的“好公民”有了独立于一般社会语境中的“好人”评价标准。德育教育致力于回答“何为好人”,但未必能够回答“何为好公民”。因为后者必须和特定的政体对于公民德性和理性的需求相联系,必须放在特定的政治国家语境之下去回答;其次,德育教育中存在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公德”关照,但基于中国社会对于“公”的特殊理解,使得我们对“好公民”的评价机制与西方话语之间存在分歧。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占据主流的“公”的观念,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中国“公”的观念中伦理色彩十分浓重,“公”是应该予以推崇的美德,而“私”是应该予以贬斥的对象,在西方概念中“公”是一个客观的空间领域描述性概念;另外,中国“公”的概念最为稳定的就是官家或者政府,为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公共事务、公共福祉更多地被视为政府责任,公民与公共领域、公共福祉本身是疏离的,积极公共责任的承担一直不被强调,这样的理念时至今日影响依旧很深远。②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A].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C].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而源自古希腊雅典的西方公民概念是和公共生活、积极创造共同善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③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对公民是否要行使积极自由、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创造公共福祉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伴随着公民政治冷漠,公共生活调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共和主义的公民观在长期蛰伏之后开始复兴。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彰显了我国德育教育培育的基本目标,尽管在《纲要》中提到了“社会公德”的基本内涵,但生发于中国传统对于“公”的特殊理解,其主要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这里除了“助人为乐”可以解释为一定的积极品德之外,其他与我们长期在德育教育中强调的以“不违法”的消极守法义务为核心的德育标准保持了一致。中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的选择性而非兼顾型德性评价标准,意味着“积极公德”在我们的公民评价语境中是不被强调的。
我国的法治教育(法制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最终是服务于德育教育的教学目标的,这样的关联以及中国特有的“公”文化理解,是否会导致法治教育本身应该承载的教育目标的陨落?法治教育除了塑造在社会生活中遵纪守法的好人,是否回应了培育“相善其群”的好公民要求?我们与西方的分歧是中国的本土化特色还是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中国当下需要什么样的好公民?当下的法治教育是否回应了这样的目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好公民必须是回应政体治理要求的,因此,以上的疑问就必须放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语境中进行讨论。
二、公民身份的语境:以法治为依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公民身份是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身份是一种伴随责任的自由身份。”①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四卷)[M].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36.这就意味着,首先,公民本身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互联系的概念;其次,公民身份的获取意味着获得特定政治国家保护的权利;此外,这种权利的获取是以公民对政治国家的忠诚和责任为条件的。②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M].郭忠华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3.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与亚里士多德的“好公民”实现了共鸣,个体需要公民身份得以彰显,权利获得保障,关键在于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责任,离开了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的参与和奉献,公民身份也就无从谈起。要回答“我们需要公民对国家什么样的参与和奉献”,就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公民所生活的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去回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好公民,公民应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首先要从中国语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解读开始。
(一)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1.社会治理——以“社会国”为依托的治理现代化
从根本上而言,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但这并不代表治理体系的选择不具备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和西方国家相似的问题,所以,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并不排斥西方治理概念的内涵。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同时包含了与西方的“共鸣”和本土化的“自语”。
与西方提出治理的背景,即进入“社会国(福利国家)”③“生存照顾”不同于传统上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强调的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资源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阶段,政府必须面对民众对其提出的与日俱增的“生存照顾”要求相似,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要面对向“社会国”转型的新命题。市场在释放个体、社会力量的同时,也造就了权利意识觉醒的“原子式”的个体,对国家的权利诉求不断扩大。伴随着与现代性相伴生的“风险社会”的到来,也使得国家治理不可能再停留在以税收权和警察权为核心的阶段,而要扩展到福利、预防等广泛的公共领域中,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剧增,急需建立新的供给体制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现代“治理”理论认为,面对日益扩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需求,只有共同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公共事务应该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相结合,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由此,与西方语境共鸣的治理现代化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将对公共行政的管理由统治向治理转变,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由国家和社会共同完成公共行政的治理任务,公共行政主体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公共行政由国家行政向社会行政和国家行政共存的局面转变。
这样的转变要求社会要恢复其活力,积极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这样的转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就得以体现。《决定》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替代了之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社会管理”,事实上就是希望在社会领域中,借力社会,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治理模式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追求公益的面向不仅仅存在于西方语境中,在中国语境下也同样成立。
2.合法性与认同——以“法治国”为依托的治理现代化
除了要面对与西方语境具有共识性的问题,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面对自身语境下特有的问题。与多数西方国家是在已经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下谈国家治理,其核心是公共事务中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不同,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承载了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即寻求政治合法性,构建公民政治认同的目标。
转型中国社会,由于利益分歧,价值多元导致缺乏共识的“碎片化”发展趋势呈现,这是当下国家治理选择法治作为根本依托的背景所在。法治对于现代公共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其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规范存在能够依靠强制力形塑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不论人们的思想如何多元,利益存在多大的分歧,由于法律的公开性、稳定性、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事实上构建了一套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共同话语体系,使不同的社会主体有了对话的可能性,多元的利益能够在法律规则的调整下实现有序共存。因此,法治成为当下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原因所在——作为整合碎片化社会手段。此外,中国社会转型要解决的一个与公民身份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当已经无法完全依靠传统的文化认同来构建当下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时,如何构建公民的政治认同这一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认同是给定的,政治认同是成员集体创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①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这种想象不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所以构建认同就应该“把民族问题转化为民主问题,通过民主参与程序将其利益需求纳入到法律框架内,通过宪法包容少数族群的基本人权;用公民身份替代民族、种族或宗教身份;把政治认同转移为宪法认同,从而抵御地方分裂主义。”②高鸿钧.宪法认同[A].许章润.宪法爱国主义[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7.即通过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实现对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来构建公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近代中国转型就意味着要把“天下观”的伦理共同体转向“权利观”的法律秩序政治共同体。从这个层面上讲,“法治”的提出是当下中国政治转型,构建公民认同的关键所在。
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事实上就是要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体系,从法律体系这一静态的规则系统建设,转向法治体系这一动态的规范系统、实施系统与价值系统建设,这意味着当下的法治建设区别于过去强调公民守法的法制建设,是以“法治国”建设为最为根本的价值依托的。“法治国”(Rechtsstaat)是一个标准的德语产物,其内涵伴随时代变迁和语境变化,学者对其有不同理解,但仍不失共识性的理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包括:(1)法律不是单纯规范个人自由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人民与国家关系定位之工具,即公共权力受法律的规范;(2)法律优先原则,强调法律统治,借助明确的法律来限制国家——特别是行政权力之范围,只要经过国会通过的法律,行政以及司法就必须完全地服从;(3)辅助性原则。即政治国家的权力范畴仅仅局限于公民及其团体无力促进的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总而言之,对于法治国的理解,一个基本的共识在于,法治国的第一要义乃在于“权力控制”,防止政府行使广泛而不受规制的裁量权力。①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8.
以建设法治国为目标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同于过去法制建设强调法治社会构建,关注公民守法,而是更关注政府守法,确保“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增强政权合法性,这就不仅仅需要公民守法观念的提升,更需要公民积极行使法律权利,参与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塑造当中。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人民是对权力最有效的监督力量和机制所在。对于权力最有效的制约和引导,力量存在于民间,存在于人民当中。为此,当围绕“法治国”建设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出后,公民如何积极地参与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塑造中就变成了中国语境下治理的关键问题。以2015年的《立法法》修改为例,本次修改赋予了除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外,其他设区的市均享有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可就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这引来了地方立法权扩大会导致地方利益泛滥的担忧。但事实上,从公共管理的有效性角度考量,地方应该拥有“因地制宜”和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进行有效立法的自治权,不能因为担忧地方滥权就从根源上拒绝地方应该享有的权力,从而因噎废食。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赋权之后有效地控制权力。事实上,除了依靠官僚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约束,如何通过人民对于立法的有效参与和监督,从而防止地方滥用立法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语境下的好公民
在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解读中我们看到,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无论是与西方语境对接的,实现多元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还是中国特殊语境下与构建认同、寻求政权合法性紧密相关的法治国家建设,都拒绝将“好公民”的面向停留在遵纪守法的消极公民层面。公民责任既包括单向的消极的守法义务的履行,也包括与国家互动地迈向公共领域,积极创造公共福祉的积极公民权利的行使。如何将自己的诉求通过合法的渠道理性化、有效地向国家表达,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构建公民政治认同和政权合法性;如何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参与公共行政,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国家行政的不足,从而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等,都成为当下中国语境下好公民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如果说法治本身是培育公民认同的一种有效方式,除了“通过权利行使实现权力监督”从而促成对权力运行正当性的认可,事实上,参与公共事务本身也有可能有效地构建公民认同。公民身份需要在面对面的地方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自我管理中才能够培养,通过在社会和地方的公共事务的商讨和参与中,逐渐培育起个体理性、合作、公益和协商等政治美德和政治能力,也才能培育起个体的政治归属感。当一个个体感受到身边的公共事务都与自己有关,并且自身能够掌控时,就会产生某种荣誉感和认同感,这种荣誉感伴随着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和提高,就能够由对小的伦理共同体的认同提升到对更大的伦理共同体的认同,即对国家的认同。
对于当下的中国治理而言,“好公民”不再局限于私人领域,不再是消极地遵纪守法就足以诠释的,而是期待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迈向公共领域,基于理性与合法性原则积极、有效地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为此,与公民紧密相连的“公共性”可以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参与”可以分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指公众参与政策的制定并影响政策设置的过程,这既是有效实施权力监督,同时也是公民权利在国家层面得以实现的有效路径以及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社会参与”则意味着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公民个体及其构建的社会不再是一个消极的被给予者,而是通过和国家的有效合作,参与到供给者队伍中,更好地满足自我需求。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在国家与公民关系上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维系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等与和谐,这有赖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合作。
三、法治教育的回应
如上所述,法治教育要承担“好公民”的培育责任,而在中国语境下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图景,从而勾勒出当下中国所需的好公民的镜像时,我们发现,以消极守法义务教育为核心的法治教育与当下我们所需要的具备公共热情和参与理性的公民培育需求之间存在对接上的缝隙。基于此,作为同时承载规范意识培育与公民培育责任的法治教育,应该做出以下的调试:
首先,关注法治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重视教育本身的知识性。法治教育从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就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教育体系中,这不仅忽略了其教授客体——法律本身是作为一门知识存在,即其本质也应该承载知识教育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划定使得法治教育陷入了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存在的误区,呈现单向性、形式主义和灌输性的特征。①张澎军.德育哲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5.作为普法教育的法治教育,属于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对象是在校学生,这些对象异于社会其他普法对象的最大特征是,作为受教育者,他们对所有的教育课程都是有着对知识的基本渴望的。也就是说,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无论其承载怎样特定的责任和目标,首先要满足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法治教育也不例外。普法的目标是树立起社会中普通成员对于法律权威的认同,从而自觉地将法治思维运用于社会生活当中。法治教育,其对象作为求知若渴的学生,这种认同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将法律解释为国家的暴力工具通过威慑的效力来实现。强大的法律帝国所构建的浩瀚的法律体系的美丽显然无法通过展示个案或者个别法规的正义之美来塑造法治图景的魅力,要塑造公民的法治理念、法治思维,首先要具备理性说服的能力,即必须通过知识教育,以理性说服、知识互动的形式实现法治知识的讲授。
其次,法治教育应该通过能够对灵魂构成征服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讲述,来完成将法律构成人们意义世界的一个部分的任务。尽管如苏力教授所言,知法并不等于守法,他也反对将普法教育建立在“人们之所以违法,之所以不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法律,或者说是没有法律的概念,法律意识不强”的基本假设之上,反对将法学的发展仅仅寄托于那种可以言说、表述的法律理论或原则的发展。②苏力.知识的分类[J].读书,1998,(3).但是,守法的前提首先还是知法,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私人领域的法律制度由于其作为“不过是日常生活规范法治化的体现”所具有的常识优势,无需法治教育就能够普遍为公众所知晓;那么由于公共生活的疏离,大量的公法规则是为公众所陌生的,而且以公权力为调整对象的公法范畴有着异于人们所熟悉的私法领域的精神和原则,不通过专门的讲授是不会成为公民所具备的常识的。对于有理性的现代人而言,确信是由证明过程决定的,承认是由说服效力决定的,个案式的法条介绍是有必要的,其叙事性的生动表达有助于人们形成对法律的生动认识,但是却存在一个弊端,即无法形成整体的法治观,无益于思维和信仰的培育,在某种程度上只完成了极为有限的规范教育的任务,而无法承载价值教育的目标,形成对法治的认同和信仰。为此,今天的法治教育需要在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介绍上注入更多的精力。
最后,法治教育应该公法与私法教育并重。如上文所分析,当下的法治教育不仅要以塑造独善其身的守法公民为目标,更要塑造相善其群的好公民,法治要求法律之治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私人生活中也要存在于公共生活中。传统的法制教育比较注重私人领域的普法宣传,如民商事法律制度、婚姻法制度等,这关切个人生活本身,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无须言说,但是伴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政治改革的深入,公民进入公共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培育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理性和美德,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必然离不开以宪法行政法、程序法为核心的公法教育。公法是以国家权力为主要调整对象的,为权力和权利的良性互动提供了规范的实体和程序指引,通过公法教育,才有可能培育公共参与所应该具备的公共理性、公共美德和公共技能,培育当下中国治理现代化所需的好公民。
事实上,法律的权威不仅来自于法律所承担的应然价值与社会成员的正义观的相互一致性的内蕴意义,同时也来自于实践意义,公民对法治的认知更多的是源于日常的法治实践,最有效的法治观念培育有赖于有效的社会环境的构建。普通民众更多地不是从法律条文,从校园的法治教育中树立对法律权威的认可,而是从亲历亲为的实践活动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和至上性。法治教育作为基础教育自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思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公民法治实践活动和国家法治实践真正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培育与国家治理需求相互匹配的公民身份。
Citizenship and leg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ZHANG Xiao-yan
(Department of Basic Social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 200433,China)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rule of the state by law and the state of welfare,which requires more virtues and skills as the qualification for citizenship.Legal education plays an essential and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qualified and good citizens.The traditional legal education which belongs to moral and ethical education has some limitations and cannot fully realize the new education target required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The paper concentrates on what kind of the citizenship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nance requires and how legal education could cultivate good citizens.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governance;citizenship;legal education
刘胜兰]
D920.0;G641
A
1000-5110(2015)05-0090-09
张晓燕,女,河北迁安人,复旦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法治教育。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研究”(14ZDC005)、上海哲社青年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公民法治观念理论内涵和培育对策研究”(2015JG002-EKS33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