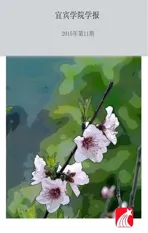被放逐的身体:作为始源的柏拉图“灵魂论”
2015-02-14钟芝红
钟芝红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被放逐的身体:作为始源的柏拉图“灵魂论”
钟芝红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多篇》和《美诺篇》提出“灵魂论”,其中灵魂不朽论与灵魂净化说探讨了身心二元论与理性的至高无上性。“身体”作为被遮蔽的存在,始终被置于与灵魂并不对等的位置上。直到西方现代“身体美学”的兴起,身体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重新建构,经过了由低级到平等的历史转向,身体不再是传统西方哲学中被忽略的部分,而是有了与灵魂相等的地位,由此有了不可或缺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身体;灵魂;不朽论;净化说
柏拉图的“灵魂论”对后世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重灵魂轻身体、灵魂身体二元论成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传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在历史书写中一直处于被放逐与遮蔽的状态。柏拉图的灵魂论,主要从“灵魂不朽论”与“灵魂净化说”出发,集中探讨了灵魂的高尚属性,而身体意义,始终作为与可知世界对立的可见世界的低级存在而被流放。
一灵魂不朽论及论证
从泰勒斯首次提出“灵魂”概念后,“灵魂”即成了古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重要话题。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柏拉图,延续亚里士多德关注灵魂的传统,对其进行过严肃的讨论。“灵魂不朽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理性、激情与欲望的灵魂
在《理想国·国家篇》,柏拉图探讨了“灵魂”,他认为灵魂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激情”与“欲望”:“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激情,亦即我们借以发怒的那个东西”[1]168。理性是用来思考的,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柏拉图灵魂不朽论的核心;作为理性的辅助者,激情处于理性与欲望的中间地带,柏拉图认为激情“在灵魂的分歧中它是非常宁愿站在理性一边的”[1]168。如果我们的灵魂存在这样的第三者激情,那么它一定是要受到理性控制的,由此得以成为理性天然的辅助者,即治理国家的手段;欲望,顺着柏拉图的思想,它则被划分为灵魂中最低等的部分,是实在的人为肉体如贪婪、饥饿及享乐等层面的满足而作出的行为。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探讨的内容,最终回归到如何治理国家的思想。他指出,灵魂的三部分划分对应城市三个阶层的结构。第三等级——即欲望,是需要被统治的,否则将会伤风败俗,国家的统治也难以为继;相反,如果理性持续地巩固在最高位置,激情辅助理性,欲望服从于理性,那么国家将会达到和谐,诗人创作的文艺必定不是邪恶、放荡、鄙俗的,每个公民也得到良好的教育,有健壮的体魄。
(二)对灵魂不朽论的论证
对灵魂不朽的进一步论证,在《斐多篇》及《国家篇》可见一斑。从柏拉图对组成灵魂三部分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柏拉图理解的灵魂不朽实际上就是理性的灵魂不朽。而归纳起来一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对立面的循环往复。不同于尼采的“永恒轮回”,柏拉图认为宇宙每个规律都存在对立面,如生与死就属于由一个方面转入另一个方面,由另一个方面转回一个方面。柏拉图的循环论显示出朴素的辩证法的思维。然而,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并不具备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在“生”与“死”的概念论证上,他预设了“灵魂”与“肉体”的对应关系,即“灵魂”代表“生”,“肉体”代表“死”,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并没有跟着消亡,而是由向世间转换的生保留下来。但显然,“生的灵魂”和“死的灵魂”而不是“生的肉体”和“死的灵魂”更符合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逻辑上错误的出发点导致该论证的苍白无力。
2.回忆说。柏拉图在《斐多篇》及《美诺篇》用回忆说论证灵魂不朽。柏拉图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学习就是回忆以前存在的记忆。理性作为灵魂固有的一部分,就是在不断回忆的行为中重新被想象的。灵魂不但不朽,还能给知识、理性提供无数个轮回,成为实现人回忆先前经验的载体。这里的知识是指对理念本身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灵魂不朽的来源,而感官知识不过是理念的影子而已。同样地,柏拉图的回忆说存在重大的瑕疵。它否定了知识来源的经验条件,从而否定了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3.灵魂的属性论证。柏拉图在《斐多篇》提出:“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自动的都是不朽的。”[2]119柏拉图把灵魂定义为自动的、不朽的东西,它具有原初的创造力而不需要借助其他生产;并且灵魂是不朽的单一体,相对应的肉体则是容易消失的复合体。
4.基于理念论的论证。从柏拉图对世界的划分发现,理念属于不可见的可知世界,它是永恒的、不朽的、单一的;肉体属于可见世界,它是暂时的、不固定的。灵魂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纽带,必然也具备理念不朽的合理性。
5.道德论论证。柏拉图在《国家篇》指出,既然“因果报应”得不到伦理上的保障,善与美德只能求助于灵魂的不朽。
在柏拉图的五个论证里,无法自圆其说的、粗糙的永生观点,从柏拉图阐释的角度出发,可以看作是为灵魂不朽性的辩护的手段。同时,尽管论证着意突出灵魂的不朽,但身体作为较灵魂低级存在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柏拉图认为的“身体”是不重要的,它无法享受“理性”的地位。从柏拉图出发,“身体”被长期视为一个低级的事件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二身体作为低级的存在
在柏拉图看来,灵魂和身体两者是割裂的,作为不朽的灵魂是持续而永久的单一体,对应的身体只是易于消亡的物体罢了。
(一)灵魂与身体二元论
柏拉图在《斐多篇》提出“身心二元论”,用当下的视域审视,已不免过时,然而,这种简单的二元论背后存在合理的语境因素。提高理性而贬低身体的地位,其实并不是柏拉图的首创,可以上溯到希腊神话与宗教世界的传统。荷马就曾描绘“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生气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奄奄一息的虚幻世界。随着自然身体的消失,“灵魂”也会从现实世界消失,变为虚幻世界的“亡灵”;古希腊第一个明确提出“灵魂说”的泰勒斯,认为“灵魂”与水一样弥漫于这个世界,万物因此蒙上灵动的韵味,这无疑提高了灵魂作为物质在场到精神在场转变的地位;而深受奥菲斯教影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表明灵魂是不朽的事物,这可以看作是“魂身二元论”的核心,灵魂只不过暂时寄居在自然身体中,它具有身体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重灵魂轻身体的直接教诲来自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反复强调的“知识即美德”,而“美德”来源于灵魂对肉体欲望的抑制。
柏拉图认为,在宇宙的生成演化中,理性作为灵魂的部分,进入形体,使后者得以成为生命。因此,宇宙由灵魂与身体组成,灵魂优于身体。身体会产生欲望,不健康的身体必然不适合国家健康。所以,更需要以理性为核心的灵魂加以引导。
首先,灵魂先行于身体。在《斐多篇》《国家篇》等,柏拉图对“灵魂作为身体的上级存在”作过论证。身体的创造是在灵魂之后的。灵魂是自动的、单一的、不朽的,它牵动着宇宙的永恒运动,是万物得以运行的条件;相反,灵魂对立面的身体不仅易于消失,还会影响灵魂的纯净。
其次,灵魂重于身体。柏拉图认为人的身体禁锢灵魂,身体成分中如先天的欲望、恐惧、懦弱、疾病、愤怒等会遮蔽了灵魂本真的面目,使人看不清对理性、知识的认知,没办法进行哲学家的思考。一切争执首当其冲的是身体的弱点。而只有当身体死去,灵魂才能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柏拉图论证过的循环说,作为世间的生保存下来。
最后,灵魂统治身体。在这点上,柏拉图灵魂身体二元论的意图昭然若揭。既然身体带着如此复杂而精确的弱点,那么,作为牵引宇宙永恒运动的纯净的灵魂,必然要将身体引向正确的道路。柏拉图在《理想国》探讨的核心观点为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维系国家的正义性是引导有益国家的方式。要完成正义的任务,灵魂——即国家统治者的理性灵魂,必须控制身体的欲望,使欲望服从于理性的管理。
柏拉图坚持的二元论肯定灵魂的高尚地位,无疑对身体造成了光芒的遮蔽。微弱的可贵之处在于,柏拉图认为美的东西是合乎比例的,那就意味着身体还能依靠自己健康的一面取得与灵魂动态的“均衡”。一个健全的人的身心,需要灵魂与身体两者的和谐去完成。因此,音乐与体育对灵魂的净化作用尤为重要。
(二)灵魂“净化”:自然身体的规训
《理想国》探讨的主要是如何建立并规范一个国家,而国家的治理主要依靠护卫者的教育。柏拉图提出:“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1]70“音乐”在柏拉图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指的是文化。音乐和体育对灵魂的净化起到必不可缺的作用,它们建构了自然身体的发展和灵魂的纯净成分。柏拉图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灵魂的净化,因此,在音乐的选择和体育的训练程度上,柏拉图无疑是严格的。灵魂净化实际上是对身体进行的严厉的规训,更强烈地将身体视为较灵魂低一级的存在形态。
在《理想国》第二卷,柏拉图抨击“首先必须痛加谴责的,是丑恶的假故事”[1]72。那么,什么是“假故事”呢?就是“赫西俄德和荷马以及其他诗人所讲的那些故事”[1]73。柏拉图要求“从词汇中剔除那些可怕的凄惨的名字”[1]388。柏拉图的目的非常明确:从一个城邦缔造者的角度来说,诗人应该服从于统治者。文艺必须对城邦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用政治标准来衡量。灵魂的“净化”,即护卫者的教育应该是有秩序勇敢的,而不是复杂多样扰乱的。情绪及附带的快感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本应压抑下去,而诗“滋养”它们,所以它不应该留在理想国。因为那些不利于培养一个正义的护卫者,反而会造成意志的软弱消沉、失去勇敢——即身体拥有的种种缺陷。
在接下来的第七卷,柏拉图还提到对哲学家的教育。数学、几何、天文都涉及到教育,而数学是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学科看来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1]291。数学能锻炼人的思考能力。对哲学家的教育首先要从数学开始,因为它们都需要依靠纯粹的理性,使人们的灵魂发生转向,到达理念世界。通过教育达到灵魂的理性,柏拉图的种种教育规定,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净化灵魂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却使自然身体更为遮蔽,几乎失去了可以出声的权利了。
体育的预设则来源于《理想国》第三卷下半部分。柏拉图认为年轻人应该从小就接受体育锻炼。这里的锻炼不仅仅指修养一个好身体,而是通过修养好的心灵和品格,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他提出护卫者应该是这样的人:“做一个自己的好的护卫者,是不是能护卫自己受的文化修养,维持那些心灵状态在他身上的谐和与真正的节奏(这样的人对国家对自己是最有用的)”。[1]129从童年、青年至成年经过考验,必须把这种人定位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护卫者。
相比教育,灵魂对体育表现出更为直接的规训。柏拉图在《理想国》反复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体育能够锻炼出健美的心灵,将孩子灵魂中的“激情”部分通过训练产生“勇敢”。通过对身体的训练,从而使灵魂自律、坚定与克制。与其说身体是辅助灵魂塑形的手段,不如说身体是通往灵魂塑形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依然以没有生命的客体形态而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理想国》第五卷的探讨,在先前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将视阈投射在男女平等及用公共体系抚育孩子。柏拉图所言的妇女与男子的智力和道德平等,“男的护卫者与女的护卫者必须担任同样的职务”[1]192,是很早的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1]196这里提出完全废除家庭制、用公共体系抚养孩子的建议。然而,这可以视为对自然身体的伤害。女性的身体并不属于自己,在疏离的时代语境中,她们的身体是为政治所建构的。
因此,对身份的体育、教育规训,归根结底都是为灵魂服务的,身体没有独立的声音。
三从客体到主体:身体的历史书写
在《理想国》第十章,柏拉图突然探讨了诗人的命运。在前面几章,柏拉图已对诗人进行过严格的约束,这里,他又提出“诗人应该是巧妙的模仿者”[1]395,悲剧诗人和真实隔着两层,因而是假的,必须将诗人和诗歌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不过,柏拉图对诗歌并没有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指出:“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1]410,这就是古老而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我们可以把这场论争看作是解读西方传统的线索。
然而,“诗与哲学之争”背后的意义来源是什么?为什么诗歌会与哲学产生竞争呢?因为诗人与哲学家信奉的神并不相同,这又是身体与灵魂对立而呈现的场域裂缝。诗人赞扬狄俄尼索斯、哲学家信奉阿波罗——人类的身体欲望奇观与理性之间呈现必然的冲突——即身体与灵魂的对抗。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背后是普遍经验的对抗,即“灵魂”作为一个完全在场的能指,成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普遍来源,对“他者”的交流进行了封闭的空间处理。古希腊时期以降,身体不得不受灵魂支配的行为也削弱了身体的话语权,古希腊及漫长的西方古典美学历史,是自然身体被长期放逐的历史。
不过,随着西方古典美学式微,一直以来被放逐的身体得到重视,并成为现代哲学家解构传统的重要武器。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就锋利地提出,理性在历史变迁中走向了它的反面,理性成为纯粹自我保存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以理性为核心的古典传统。从尼采、梅洛-庞蒂、巴塔耶、福柯、德勒兹到舒斯特曼,“身体”从客观的自然客体发展到了更多关注自身审美性与意识的主观性构造。这无疑是一场哥白尼式的激烈转型。巴塔耶拒绝“占有的欲望”“文明的禁忌”,实际上是作为对反对同一性与传统理性提出来的;拉康的“语言欲望”可以看作是对巴塔耶的回应;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对传统的重新书写,《权利意志》呼喊身体是权力意志的身体,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更直接表明他对肉体的想象:“健康的肉体,完美的、正方的肉体,说话更诚实、更纯粹:它谈说大地的意义”[3]30、“精神是给肉体报告战斗和胜利的传达者,是肉体的战友和反响”[3]30等。而“我是肉体和灵魂”[3]31将肉体置于与灵魂平等的地位,视为对二元论的解构,灵魂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意识是通过身体以物体方式的存在”[4]183-184是对传统身心论中“意识是灵魂的一部分”的彻底否定;而实用主义者将“身体”放置于更广阔的场域,视“身体训练”为柏拉图理念的对立面——与柏拉图强调身体锻炼是为培养合理优雅的灵魂不同,实用主义希望通过身体训练,从而将生活制造成审美的艺术事件——“身体”已经成为审美的方式;德勒兹认为,身体不是一个本质的概念,而是一个去本质化现象下相互交叉的力作用的一个力游戏,欲望构成身体的一个维度;在阿甘本的观念里,身体是政治的起源,“身体的出生,恰好是人权的基础”[5]25。
由此,身体逐渐进行着从低级到平等的历史转向。不仅如此,“身体”作为现代哲学家更新传统的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作用弥足珍贵。
结语
通过上述不难发现,西方哲学中“重理性、轻身体”的传统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柏拉图认为灵魂高于身体,只有坚持理性,才能“还没有葬在这个叫做身体的坟墓里,还没有束缚在肉体里,像一个蚌束缚在它的壳里一样”[2]125。以柏拉图灵魂观中的“灵魂身体二元对立论”与“净化说”为典型,柏拉图对身体作了一次立法的厘清,“身体”在柏拉图那里,是被忽视和遮蔽的。缺乏独立的身体,一切行为都指向对灵魂的顺从与规训。此后漫长的西方哲学史延续了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对身体进行了集中的放逐。直到西方现代“身体美学”的兴起,经过尼采、梅洛-庞蒂等哲学家的解构与重新建构,身体才实现从客体到主体的历史书写,这无疑对身体美学的发展产生浩瀚深远的影响。
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身体”转向是一条追溯哲学传统并发展未来的重要线索。从出现“身体转向”开始,意识的作用就不再具备蔚为壮观的绝对地位,尼采等人的努力使历史出现新的契机,那就是“身体”引起的与权力、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对话:梅洛-庞蒂直接将身体放到哲学的起源中,福柯眼中的身体是被惩罚与被规训的,实用主义的身体更多与训练联系……如今消费主义的身体奇观是文化研究的热点,比如,从封面女郎的形象变迁看社会意识的发展就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方向。因此,以发展的眼光看,“身体”不仅不再是一个被轻视的概念,从此得到了长久的哲学注视,而且它还会生出更多有趣的讨论。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露〕
The Body of Being Exiled:on Plato’s Original “Soul Theory”
ZHONG Zhihong
(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Plato put forward “soul theory” in The Republic, Phaedo, Meno and so on. “Soul immortality” and “purification of the soul” discuss the dualism of body and soul as well as the supremacy of Logos. Being shaded, “body” has always been placed in the position of non-equivalence comparing with soul. Until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modern “body aesthetics”, “body” transforms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low level to equality and carries on the historical turn from the secondary to the core. “Body” is no longer the neglected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but has the equal status with the “soul”, thus it has the indispensable exist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Body; soul; immortality; pur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72-06
作者简介:钟芝红(1991-),女,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美学、电影美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