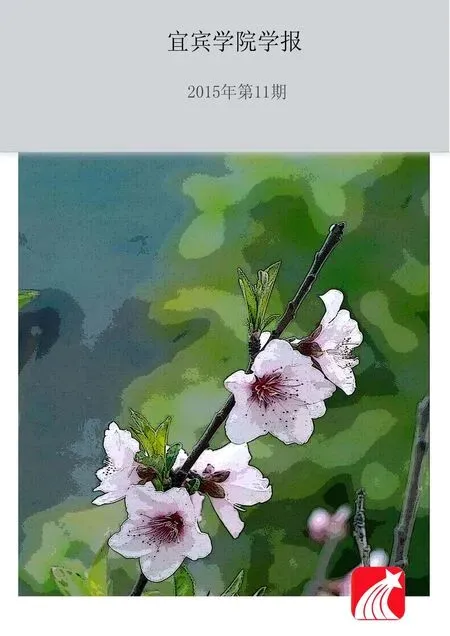唐君毅论朱子学中的“人心与道心”
2015-02-14蔡家和
蔡家和
(东海大学哲学系,台湾)
唐君毅论朱子学中的“人心与道心”
蔡家和
(东海大学哲学系,台湾)
摘要:唐君毅先生对朱子学的态度,与牟宗三先生有别,虽二者都见识到朱子学的援引外学,但牟先生判其别子为宗,而唐先生却赞朱子学的伟大。人心、道心,乃朱子《中庸章句序》所关心的问题,颇受韩国朝鲜朝学者关心,如李栗谷有“人心道心说”,韩元震曾认为朱子人心、道心之见解前后四变。而唐先生以一心、二心、三心言之,视朱子言人心道心,虽有不同的前后变化,但可以相合:一心者,“虚灵知觉一而已矣”;二心者,心之知觉于“道”与“形气之私”之不同;三心者,乃在于人心处又可分为二,一种是已成的自私之心,而另一种是人心、饮食等,能不违于道心者之心。唐先生对于朱子学的前后期看法之合会,是唐先生的圆融个性之表现,其中对于恶的产生,也有细心体会。
关键词:唐君毅;人心;道心;仁;去欲
当代新儒家,熊先生以下第二代,唐君毅、牟宗三二先生较具有形上哲学的体系建构,然二人面对朱子学,对于朱子学的评价却不大相同。牟宗三视朱子学为别子为宗,虽然牟先生评其别子为宗并不都是贬义的,也赞赏其优点,即朱子虽不同于先秦孔孟,但可以自成一大宗,而为儒家开出其他新的面貌。至于唐先生对于朱子学的态度,则不区分宋明儒学谁是正宗,谁是别宗①,唐先生虽亦见及朱子学不全同于先秦孔孟,但还是赞赏朱子学的伟大之处,二先生的个性,完全表现在对朱子的评价中。牟先生较重分析是非对错,而唐先生则圆融地涵摄,而盛赞优点。虽说牟先生的别子为宗说,对于朱子的判摄不都是贬义,但牟先生认为朱子的二元区分的认识论方式之体系,与他所谓的天道性命相通为一的道德形上学是不类的,故其判摄为以知识的方式讲道德,是一种横摄系统,而不是纵贯的天人相通为一。牟先生言:“不过世亲头脑明析,而乏理想主义之情调,大体喜作能所之分,别为对列顺取之形态,与儒家朱子相似。”[1]410此段是牟先生于《佛性与般若》论及于唯识学时,认为世亲的分解性思惟,近于朱子,而且若以此为准,而视其为顺取者,乃不是一种逆觉的本心呈现之方式,故认为其讲道德不切,反而成了知识的进路。又若与世亲相比,而认为朱子学少了理想主义,则可谓对朱子学的态度,的确有贬低的意思。在此吾人不打算对于牟先生的朱子学之判摄对错作一解说,只是用来相形于唐君毅先生对朱子学的判摄。相对而言,唐先生的态度则较为融合,而能接受朱子学。
然唐先生朱子学的文章甚多,为了题目的聚焦,吾人只谈其书中的一节,焦点放在朱子学的人心、道心之说的讨论,并对唐先生所理解朱子的人心道心说作一解析。吾人对其作品《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第十三章《朱子之理气心性论》之第八节“人心道心之开合”一文,先作一简介陈述,最后作省思。也因为该文文字多,故开为十段,并主要论及文中唐先生朱砂笔划重点之处。
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其中的“人心”该如何理解,是一个关键,在罗整庵曾对于人心道心有其体会,其言:“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凡静以制动则吉,动而迷复则凶。”[2]22整庵认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而且前者为静,后者为动,以道心为主,人心每听命之,且整庵之说视道心人心为体用,影响了韩国儒学。如此才能不失其常而不流于恶。然整庵之说与朱子相合乎?就蕺山的见解而言,已看出整庵不全同于朱子,蕺山言:“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3]1717-1818道心为性,人心为情,前者为未发,后者是已发,而且一体一用。但蕺山已看出其不同于朱子,或者说整庵早已自觉其与朱子的见解有不同。至于朱子的见解为何呢?《中庸章句序》云:“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朱子谈其道统观,于是有尧传舜,舜传禹之十六字心诀,其内容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至于人心是什么?道心是什么?在朱子的体系是如此的,心只有一心,然而知觉的对象不同,故可分为人心与道心,人心者,心之知觉于形气之私;道心者,心之知觉于性命之正。由此可知,整庵直接以性与情谈道心、人心,与朱子的意思不类,朱子是以心知觉性为道心,故还是就心与性的作用而言道心,非直指性为道心。
然而人心是否是贬义呢?这是谈论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常见的问题,也是《中庸章句序》中朱子认为“虽上智不能无人心”的意思,人心不都是贬义的。以上乃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对历来思想家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然吾人的重点是唐君毅如何解读朱子的人心道心说。以下进到内文,依原文开为十段,举重要几段以论之。
吾人对于唐先生《人心道心之开合》一文作一诠释解说,其意思指的,朱子言心,是为一心乎?一心何以又可以开为二心、三心,作一解释,合则为一心,开而为二、三心。吾人依段落顺序言之,第一段言:
朱子所谓道心,乃由人之表现其心之四德而成,亦心之天理性理,实际实现或表现于心而成。此即不同于统言人有具性理之心。此道心待于人之实克去己私,以实表现心之四德而成;则尚未去己私之心,即非道心。此非道之心,就其亦可克去己私以成道心言,或就其己私可不妨碍道心之呈现言。便又是另一意义之心。此一意义之心,如其己私足以妨碍道心之呈现,而又不能自克,更是一意义之心。于是人之一心之呈现,即可自其已实现表现其性理者,而名之为道心;就其可实现表现道,或其己私不妨碍道心之呈现者,而名为人心;就其人心之己私之足以妨碍道心之呈现者言,称其为私欲,或不善之人欲,而此心即为一具不善之人欲或私欲之心。由此一心即可开为二心或三心以说。[4]417-418
此乃唐先生对于朱子言人心、道心,到底是一心还是二心、三心作一解释,若言“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则为一心,然依形气之私与性命之正,以知觉之,则开为人心、道心;但在人心而言,又可区分为二,一者是中性之人心,此人心虽未成为道心,但可以不妨碍道心,而且不致于为恶、为私欲,则此称为人心,而私欲已成者,是为人欲,而不是人心。故在唐先生而言,把人心部分,区分为中性人心,与私欲之人欲,故一心开而为三心,一者道心,二者人心,三者人欲。这与《中庸章句序》的讲法是相合的:“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②有是形,则有是心,此是人心,乃人之饥食求温饱之心,上智之人,亦要饮食吃喝,这不到人欲的地步,人欲为贬义,但人心是中性义,否则此人有其私欲,而不为上智。故知人心与人欲可以区分开来。朱子的这种讲法,及唐先生如此诠释,在朱子《孟子集注》处也可以找到根据,朱子注“寡人好色”一段言:
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③
心若依于天理,则为道心,心若从于形气,则为私欲,故朱子认为要存天理、去人欲。但在人欲与道心之间,还有一种唐先生称之为人心者,它既不是恶,但也不能上提到道心层次者之人心,在朱子此段,以游观之乐、好色之心言之,原文孟子提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④孟子认为此“心”是不用去之的,因为人有其生理之心,生而饥食渴饮,有其传宗接代之心是正常的。此如同唐先生所言,“其可表现道,或其己私不妨碍道心之呈现者”,而为人心,即人若无身体⑤、欲求,生理已尽而死,亦不能尽道,故此人心也是道心的载体,不可无之,而朱子的用语是“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可无”。依此而言,唐先生对于朱子人心、道心之诠释,吾人认为唐先生是合于朱子的。
第二段言:
韩元震《朱书同异考》,尝谓其前后有四说……大率朱子初以“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答张敬夫书)……至于其答吕子约书,谓“操舍存亡,虽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则道心之微,便亦在此”……朱子后与郑子上书,则又谓其与蔡季通书,语尚未莹;然亦未视为非,并谓“此心之灵,觉于理也,道心也;觉于欲者,人心也。”此似为其最后之论。而其郑重作之《中庸序》,亦缘此而作;今观《语类》七十八辨《尚书》中人心道心之义,即多本于其最后之定论。[4]419-421
此段是根据韩国朝鲜朝儒者,韩元震(南塘,1682-1751)的《朱书同异考》而发言,此书还附了《朱书同异考序》,由于其所谈朱子言心四变之说,意思不显⑥;但在其南塘先生文集卷三十处,有《杂着》,其中一篇为《人心道心说》,此四变之说显著,其内容与唐先生认定者无异,即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前后四变其说⑦,内容为:
窃观朱子之言,果有前后之不同。1始则以人心为人欲。2而既而改之以为饮食男女之欲,可善可恶者,始则曰“道心为人心之理”。又曰“道心性理之发,人心形气之发”。3既而改之,以为“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其曰或生或原者,乃即其已发而立论也……4其于《禹谟》解则曰:“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谓之道心。”于形气,不下“发”字;于义理,虽下“发”字,而亦以义理字换性命字,则其义亦自不同。[5]143
此唐先生与韩南塘之说,不全同者,乃因为唐先生认为自己的说法是本着南塘引申而论之。⑧韩元震的讲法认为朱子始以人心为人欲,第二说,改人心为饮食男女之欲而可善可恶。第三说是《中庸章句序》之说,第四说是对《尚书·大禹谟》之解,其中以生于形气之私为人心,发于义理之公者为道心。此重点在于,于义理处才可言“发”,形气者不言发。
然而唐先生四变其说的内容:第一,以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第二,由人心之操存,即见道心之微,人心不全是私欲;第三,人心之形气之发,未尽不善,然其不清明而隔于理,亦不是道心;第四,《中庸章句序》的讲法。然而唐先生虽言朱子对于人心、道心的考察,四变其说,第一说较不通莹外,其他三说,其实都可相合而为一,故朱子的人心、道心说,大致而言,去除第一说外,前后都可相通而为一致,这也是唐先生之所以认为一心可以开而为三心的说法,故有道心、人心、人欲的三种说法。
接下来,唐先生对于人心作一说明:
人既自知其有知觉运动,便不能不说是有一心,然此心又明异于自觉的依仁义礼智之性理或道,而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或朱子所谓具爱恭宜别之情之心……因此由知觉运动,以自求生、延生之心,依朱子之形上学言,即亦同依于太极之生生之理、生生之道而有。[4]421
唐先生在此谈三心中的人心,不是人欲,此是中性之心,亦不可去之,如同朱子言“上智不能无人心”,又如其认为好色、好货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所不可无。而唐先生强调,依于太极之生生之理,动植物能生生不已,同样的人亦不可离于此饮食男女之情,此血气之心,亦不可无,如人的饥寒痛痒者,皆为人心。而此人心尚未至于私欲之境。如同朱子训“生之谓性”时,以知觉训之,知觉之心亦为中性,不至于到道心,亦不一定流为恶,故上智人亦有之。
第六段言:
而此人欲之正式表现,首即表现为人之只从其形气之私起念,而对其他人物之生,漠然无感;于其他人物之生与己之生,同本于一天之生道而生,更无所知;乃不能自觉此生道,即我之性理所在,并自觉的求尽此性理,以爱人利物为事。于是其于其他人物,虽亦未尝无知觉,亦未尝不对之运动,然此所知觉者,与对之运动者,亦唯是他人之形气之外面的表现,实未尝知觉他人之形气之内在的生命;而亦未尝对此生命之存在,真有所感知。由此而再进一步,则其对他人物之形气,皆欲取之为我之用,而视之同于其他一切可为足我之欲之一只具形气之工具;于是玩物丧志,玩人丧德,无所不至。此即人之灭天理而穷人欲,而人之无穷罪恶所自生……故此人欲之罪恶所根,不可说只在人与禽兽同之食色之欲,而实亦在此人与禽兽异之人心……然道心中除此一部分外,尚有所知觉之道或天理之内在于其中。而此人心中,则无此道之内在于其中;而只有一出于形气之私之欲,如自后面来推动指挥主宰此知觉,以及营为谋虑等之进行。[4]423-425
唐先生认为道心自天、自人观之为善,因道心依性命之正而行,性命之正为性善,不待言也;至于人心,自天观之为善,因有气则有理,此理亦是仁义之理,故自天言为善;但人心自人观之,则为可善可恶,不必是恶,因为不到人欲层次,可以为善,因为有食色之欲,满足生理需求,形色天性,有此载体始可行善。
而朱子言或依于形气之私而言人心,此形气之私为何?这里的私,似可以恶言之,因为自私,然朱子所言者为人心,此人心初可分为人心与人欲,若未到人欲层次,则亦不私心,这里的私,就个体的生命而言,人容易只照顾自家生命,而忽略了他人的生命,不知他人与我同一根源天理而发,而无一体之感。故此形气之私若能依于道心而行,则固善,如同我们的小体听命于大体,此上智者所不免,即圣人亦要饮食,然其饮食得体,而不损人利己以吃喝,故还是善。但是,此形气之私却容易流而为私欲,而一往下流,因为虽能知欲他人他物,而有所攻取,攻取而悖于天理,这是可能的,即不能有体会他人之心,而只想成全自己之私欲,无法照顾到普遍性的生生之要求,而流为人欲之始。此人欲之始,乃对于他人之生,漠然无感,而天地生物之泛爱众的生生之理,亦无所知,只觉察己之生道,而不知他人亦有生道。对此理一分殊是无感的,天理生生不已,要自己生,也希望他人能生,此生理,落在自己身上,也落于他人身上,故朱子《仁说》中,认为以爱人利物为心,此为天心。然若能依于天之生理,则为道心。如今唐先生所言,不只不是人心,因为人心不必违于善,而是流为人欲之心,以其自身的计较心,此心知能知他人,但只是表面之知,知其有人、有物,但无所感通;亦对其运动、攻取,但只是进取而为我所享用,损人以利己,把对象视之为工具而非目的,对人物的不尊重,只因重我而损人。此则所谓的灭天理而穷人欲,玩物丧志。
于此中,唐先生对于人之流于恶的可能,从其开始到正式之恶始成的描述,非常贴切,有其实感,此乃唐先生的人生哲学,唐先生写有《人生之体验》及《人生之体验续编》二书,可谓对道德之善的感触,及人之可哀性,人的流于恶之负面等,都真有其生命的实感之启发。而且唐先生认为人心为下堕而流为人欲,此固必待于人心,此与禽兽之心又不同,因为此计较营为设计等人为活动,禽兽虽亦有,但不像人之精细,此不从人与禽兽同之食色之欲来,而其实人心与兽心亦异。在此朱子似乎于其人心、道心处,并未如此细谈,此人心兽心之异者,反而有取于船山之说影响。船山言:“人之自身而心,自内而外,自体而用,自甘食悦色,人甘刍豢,牛甘蒿刍;毛嫱、西施,鱼见之深藏,鸟见之高飞。即食色亦自迥异。以至于五达道、三达德之用,那一件不异于禽兽,而何但于心?”⑨船山批评朱子后学,因其后学常谈人禽之同,而船山认为孟子所言者,人禽之异,甚至,食色之心亦不相同。船山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不只是道德性而已,人与兽,身心处都有不同之处。而于此唐先生认为人心与兽心亦不全同,兽心亦有计较心机,但不同于人之谋虑计划之激烈。而此人心一旦不为道心主宰,只是一私心欲求所推动指挥而离于道。而动物之私心,亦比不上人之计较心,而有区别。唐先生之所以对于恶的问题言之深切,与他对孔子之仁的理解有关。他对于孔子的仁道有如此定义之:“乃将此诸意综摄而说孔子言仁之旨,更开之为对人之自己之内在的感通、对他人之感通、及对天命鬼神之感通之三方面。皆以通情成感,以感应成通。”[6]78仁为感通,而麻木不仁则不能感通,而觉自己之重要,不顾他人之存活,而自私自利,流而为恶。
而文中,唐先生的意思,人心之为中性,而可上讲与下讲,一旦上讲,则以人心依道心而行而为善;下讲人心依形气之私而流为自私而为恶,故说一心而三分、二分皆可。在此一段中,唐先生把人心上讲或下讲,而如同孟子言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人心在此则不再表现为中性,而开为二,上讲为道心,下讲流为人欲,故分为二心亦可。
第八段谈到:
不善之人欲,无人心则无所自生,人心无虚灵知觉,亦不成人心。然人心既有虚灵知觉,又可超私欲而存其道心。此即同于谓有不善之人欲者,即必然能有道心。有道心而使道心常为主,又必能去一切不善之人欲,此即又同于谓:有不善之人欲者,必能自去此不善之人欲。再即同于谓:此不善之人欲之自身,原自有其可去之理,或由存在以归于不存在之理。此理之实现,即天理之流行,不善之人欲之净尽也。[4]427
此段可谓对朱子“道心为主,人心每听命之”一段的诠释,人心有形气之私,亦是正常,人有感性,人有七情六欲,都是自然而成的,亦不能去之。吾人要去者,乃是已成之恶的自私,麻木于其自己之私欲,而不通他人之情。故总使道心为主,人心听命之,心之虚灵而觉于道,则从其大体,而小者不能夺之。心之虚灵知觉,能虚才能觉,虽有物欲之蔽,而一觉即醒,如同孟子的求放心之说,直觉于天理,而人心之私则无其定然之必然,可化掉,复回归于天理之流行,可感通自他人我天地,而化除人欲。此乃劝人积极向善之说,复其初,则能回到天理本善之层次。
第九段言:
在董子以阴阳之气言性,而不知以理与道言性,道家重道,而魏晋玄学言玄理与名理,皆不知扣紧理或道以言性,此以理或道言性之流,乃宋儒自周张二程来所开,朱子之所承,而大进于魏晋两汉学者之处,固非董子之所及。董子亦不知以虚灵知觉言心,更不知人之不善之情欲,亦由人对此虚灵知觉之一种运用而成。[4]428
此段中乃属唐先生《原性篇》中第十三章《朱子之理气心性论》之总结,乃唐先生对于董仲舒之言“性”的形态与朱子的形态之比较,其认为二人有异同处:相同而言,董子以阴气言人欲,而朱子视之为人心;董子以阳气之言善,而似于朱子所言之道心。然二人还是有所不同,董子以气化言善恶,而到气之层次,不从道、理处谈,此乃与朱子之大异,也属汉宋之争。程朱为理学,乃一转汉魏以来对性的见解。⑩由于唐先生此文是套在他的《原性篇》而言,故其所言人心道心,特就道心之依于性而言,在程朱而言性即理,在汉儒有性是善恶混,到了魏晋玄学,所言的人物志、才性与玄理等,还是就才性而言,而不是就根源于天地之性善一性,程朱面对于前人之说,可谓耳目之新,一改前人之言性之说,而根源于天命之性,此性与孟子之性善可相承。此也是程朱的创新。
除了性之认定不同外,董子与朱子对于心与情的认定亦不相同。朱子的心性情三分,而先秦性情常连言,甚至情字与朱子认定的情感亦不同,常指实情。至于心,董子亦无虚灵知觉之心的意思。然朱子所言的虚灵知觉之心从何而来呢?《论语》言心处少,约五、六处,大致不从虚灵知觉处言心,孟子言心是恻隐、羞恶等心,而要人尽其心,此即性言心,亦未明言虚灵之心。下段唐先生指出朱子“心”义近于荀子的“虚一而静”之心,下段详之。
唐先生于此段所要发挥的重点,即此心之虚灵知觉,必不昧于理,虽人心可蔽,但道心总在,故下愚不能无道心,而可不隔于天理,道心终不可昧,人欲之必能尽,此必能尽是劝善而要人实践之,现实上,人不尽之,亦可能,但在理想上、可能上,是可以做成的。故可言二心,亦可言一心,二心是就人欲与道心而言,一心就虚灵知觉而言,而以道心为主,人心每听命焉,故为一心,以道心为主之心。
第十段言:
按此心为虚灵知觉之一义,初导源于庄子、荀子,而魏晋思想之言体无致虚,与佛家之言空,以及圭峰之以灵昭不昧之知言心,皆在义理上为一线索之思想……然朱子之言此心所具之性,则要在承二程性即生生之理之义。此性之见于情,为此理之表现于气。朱子之重人物之气质之差别,则又实上接汉儒之以气言性之旨……呜呼伟矣。[4]428-429
唐先生认为,朱子之虚灵不昧之心,乃“初导源于庄子、荀子,而魏晋思想之言之言体无虚致,与佛家之言空,以及圭峰之以灵昭不昧之知言心”。唐先生认为这一理路为同一脉络。如此言之,则朱子言心,乃借自于佛老,也借自于儒家的荀子,然荀子却不是宋明理学之所宗者。虽然朱子的体系都是以孟子为正,而不以荀子为正。但在心之说处,却近于荀子的“虚一而静”之说,亦近于庄子的灵台之心。而心之所以虚者,与魏晋之宗于老子的“致虚守柔”而言心相近,而佛学如圭峰宗密言灵昭不昧之心,此乃朱子吸收佛老之长处,故朱子本程子而言“佛氏本心,圣人本天”,圣人所本者,天理,此性即理,而不是心,佛家可以言昭昭灵灵之心,而儒家亦可。但儒家的实性,则佛家不言。
此段可谓对第十三章的总结,总结朱子的理气心性论。而朱子言心具性,乃从程子而来,心如谷种,性是心之生生之理。而朱子言人性、物性之不同,以气质言之,故人性可同于物性,亦可别于物性,人性与物性都是同一天理而来,理一分殊,人性不同于物性在于物之气质不佳,而不容易表现理。此乃于韩国儒学之所以有湖洛论争,而论议人性、物性之异同。其中一原因,乃在于朱子创造性的诠释,以至在孟子言人物性异,而朱子注《中庸·首章》,于率性之谓道处则言率人物之性,此人、物性之同。而朱子之所以有此灵感,乃因着气质之性而来,此乃张子、程子已注意之,而上溯之,则有魏晋之重才性,汉儒之以气言性。
然唐先生最后对朱子的总结,以呜呼伟矣赞朱子,其大致亦如牟先生一般,发现朱子的见解,不全同于先秦孔孟,但还是以伟大称之,而牟先生则以别子为宗称之,唐先生则不如此。由此看出唐先生的圆融。然牟先生的别子为宗亦不都为贬义,而有一义是指,能自成一家而为大宗,亦是可贵。朱子的确伟大,而唐先生亦能阐发之,而为可贵。
结语
综上,就唐先生对朱子的人心道心之看法,其对朱子学的理解是准确的,也知朱子的学问之建构,其中的心义,与孔孟不类,倒像荀子、庄子、佛教之说,这看法亦是准的。唐先生于此文的贡献在于,对于恶的产生,人心之所以成为人欲,其可能性,作出说明,这也是唐先生长年所关心者。他对于心的定义,可开为一心,所谓虚灵知觉之心,或是人心之本于道心,此可合会于一心;亦可开为二心,即人心之往上发展为道心,或人心之向下,而流为人欲,此与仁与不仁的二分;至于三心者,道心,人欲之外,还有人心,此人心为中性,但在人为中性,在天之理的层次,人心之有欲望生理,是正常之理,亦不可去之,亦可以为善。
而唐先生所一再强调者,善之有根,乃天理,而为“理一分殊”,根源之同的认知,才可不致自私;至于恶无根,故人总有冲破欲望,而回到天理复其初之时。而唐先生之诠释的特别处,他早已看出朱子的人心道心说之四变,这是从韩儒韩南塘而来,表示唐先生的研究甚广,很早就研究了东亚韩国之学,而为先驱。又他认为人心与兽心的不同,亦有其新颖之处,这一点,吾人认为多少与船山的影响是相关的,众所皆知,唐先生的船山学是功力很深的。人心一旦为恶之时,其计较性、心机性,比于动物来得更恶,这反而是动物所无,而人心所执者。又其对于人心之善的讲法,亦有其新处。其认为人心之为善,纵使未及于道心之时,人心还是可以为善,此善乃就天理要人有心、有知觉者,此为善,人有好色好货之心,是天理所有、所容,而在天理肯认定,此存在为善,可以让人有此形色之心,形色之知觉,而能行善,此乃形上天理性,而唐先生之发挥亦相当到位。
注释:
①“宋明理学中,我们通常分为程朱陆王二派,而实则张横渠乃自成一派,程朱一派之中心概念是理。陆王一派之中心概念是心。张横渠之中心概念是气……‘理’之观念在其系统中,乃第二义以下之概念。”参见唐君毅:《哲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219页。在此唐先生举三系说,亦未以谁人为正统。三系都接纳。
②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4页。
③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19页。
④参见《孟子·梁惠王下》。
⑤唐先生释孟子的性善,认为身体亦善。不只是精神、人心为善。此近溪有相同的见解,其于孟子,亦非无所本,孟子有形色天性也,形色是我们的天性,善性,则形色亦善。恶是人心之不依理而行所造成的。
⑥《朱子言论同异考》一书,其中与心有关者,有“心”一条,及中庸处谈人心道心。在中庸处言:“论中和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而未发者常行乎已发者,初说也……未发为性之分,已发为情之分,心则贯乎未发已发而主乎情者,后说也。(见大全)……旧说中亦多言与前见不不同,此书〔答张敬夫论中和大化之中一书〕亦其例耳。”见《宋子别集丛刊·朱子言论同异考》(韩国:奎章阁,2008),42页。此意思指朱子言心不只是分中和旧说与新说,于旧说亦常有更动。若如此,则至少朱子言心有三变其说。
⑦其实不只朱子四变其说,韩南塘所宗之栗谷,也对人心道心的理解有变化,原因之一乃因为整庵学传入中国,加上朱子的前后看法改变,而使得栗谷的人心道心的见解有不同。可参见栗谷之说:“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善。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参见李栗谷:《栗谷先生全书:卷九》中《答成浩原:壬申》,122页。
⑧“兹本其言,更加以引申而论之。”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419页。
⑨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六)》,1023页。
⑩其实在周子言性,亦是气性,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周子的义理是理学,这是朱子所做成的诠释,不一定是周子本意。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佛性与般若:第1册[M].台北:学生书局,1982.
[2]罗整庵.困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
[5]韩元震.南塘先生文集[M]//韩国文集丛刊:第202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7.
[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责任编辑:李青〕
Tang Junyi’s Investigation on “Human Mind and Mind of
Tao” in Zhuzi’s Theory
CAI Jiahe
(DepartmentofPhilosophy,TunghaiUniversity,Taiwan,China)
Abstract:Tang Jun-yi’s attitude towards Zhuzi’s theory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ou Zong-san. Although they both were aware of the citation of non-Buddhist studies in Zhuzi’s theory, Mou criticized the misuse of its origin, while Tang praised its greatness. Human mind and mind of Tao were the focuses of Zhong Yong Zhang Ju Xu,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Korea. For example, Li Li-gu wrote “The Studies of Human Mind and Mind of Tao”, Han Yuan-zhen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four changes in Zhu Xi’s perspectives of human mind and mind of Tao. Tang investigated Zhuzi’s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e mind, two minds, and three minds, and suggested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changes in Zhu Xi’s perspectives of human mind and mind of Tao in early period and late period, such changes were compatible to one another. Those with one mind could only “perceive false spirit”; those with two minds could percei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o” and “selfish desire”; those with three minds could divide human mind into two parts - existing selfish mind and human mind and diet, without violating mind of Tao. Tang ’s consistency of opinions on Zhuzi’s theory from early period to late period showed his tactful personality. He also carefully interpreted the development of evil.
Key words:Tang Jun-yi; human mind; mind of Tao; benevolence; elimination of desire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01-08
作者简介:蔡家和(1968-),男,福建惠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