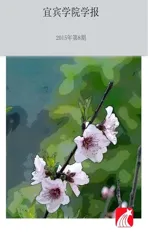废名小说叙事时间与禅宗——从《桥》到《莫须有先生传》
2015-02-13王雨佳
废名小说叙事时间与禅宗
——从《桥》到《莫须有先生传》
王雨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桥》和《莫须有先生传》都属于叙述节奏缓慢、故事时间跨度却很大的文本。两部小说在时间大幅度流转上有明显和暗含的不同,在文本结束时呈开合或封闭的不同,这种同中有异的叙事时间与禅宗“观心看净”“识心见性”的思想内涵紧密联系。废名的创作深受禅宗的“凡有所相,皆是及虚妄”“自性迷,佛即众生”等思想及“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叙事时距;禅宗;黄昏意象;《桥》;《莫须有先生传》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王雨佳(1990-),男, 湖北浠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饶新冬说:“废名,中国新文学史上一座神秘莫测的艺术迷宫”。[1]这句话既道出了废名艺术作品的深奥晦涩不易理解,也表明其艺术作品犹如迷宫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进出。因此对于废名作品的理解,学者众说纷纭各有特色,但似乎都不能完全体现出废名小说的艺术美。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去确证废名小说中所蕴含的禅宗思想。这是一种以叙事学的批评方法为基础,且同时关注文本与其外在文化关联的研究。
热奈特说:“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连接顺序。”[2]14这里区分出两种时间顺序,一种是叙事时序:文本展开叙事的先后顺序,是叙事者讲述故事的时序;还有一种是故事时序:被讲述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故事时序当然是固定不能变的,叙事时序则可以变化不定。对比两种不同的叙述顺序是发现作者的时间意识、叙事目的以及叙事意义等的有效方法。但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观照废名的小说却是一件复杂且困难的事情。
《桥》最初大部分先后刊于《语丝》和《华北日报副刊》,后厘定上篇各章刊于《骆驼草》,之后成书的顺序又和最初在报刊上刊登的有所不同,并且其中大部分章节较简短,故事较松散,所描绘的重点在于日常生活的片段,因此成书的顺序不那么受限。于是这样的小说形式对于观照废名小说的叙事时间造成巨大的困难。又如《莫须有先生传》,按常理传记应该有比较严格的时间记录以及人物行动的轨迹,这样有助于展示人物成长的过程,让读者能更好更深入了解被展示人物的方方面面,但《莫须有先生传》则反其道而行:“山上的岁月同我们的不一样,而《莫须有先生传》又不是信史,而我有许多又都是从莫须有先生的日记上抄下来的,那一本糊涂日记,有的有了日子没有年月,有的又连日子都没有,有许多我翻来翻去竟是同一个号码,所以《莫须有先生传》也只好四时不循序,万事随人意,说什么是什么了。”[3]677文本叙述者自己站出来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不可考,叙事时序的发展只能万事随人意,说什么是什么了,叙事者对于叙述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因此很难通过对比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去观照废名小说的时间意识,继而探究这种时间意识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既然文本叙事者对于叙事有着强烈的控制欲,那么我们不妨从已经形成的文本出发观照叙事时距的变化。从《桥》到《莫须有先生传》,它们的叙事时距有一致的地方,但一致中又有鲜明的区别,在这同中有异的形式中笔者发现其与禅宗思想相联系的部分。
一同中有异的叙事时距:缓慢前进与极速流转
所谓时距,就是指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在衡量时距的变化时,热奈特提出应以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关系为基准,例如由分、时、日、月、年计量的故事长度与以行、页计量的文本长度进行比较,即故事时间长,叙事篇幅短则为快;故事时间短,叙事篇幅长则为慢,这种快慢构成叙事文本的节奏。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叙事文本的节奏是相似的,都是在缓慢前进和急速流转之间转换,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由于废名小说抒写的形式趋于诗化,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又很晦涩,读者更多注意的是小说表现的形式,因而几乎察觉不到其叙述中时间的变化,只是偶尔从叙述场景的转移和小说少量时间词汇的运用中感知时间的变化。又由于纯粹的场景描写不多并且在其中总会夹杂一些其他叙述手段,因此叙事篇幅更长,故事时间就会显得更短,于是对于时间变动的感知更为缓慢甚至停滞。但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叙述者却以或明显或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时间的极速流转,之后两部小说的结尾在处理时间问题上又显现了不同的特点,从而我们才能发现在相似的叙事文本节奏下《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的深刻不同。
在《桥》的上下篇中,我们无法确认叙事者叙述故事时间跨度的长度,这不仅因为文本能追溯的时间词语缺乏,更是因为上下两篇文本的结尾故事时间呈现开放姿态,仿佛戛然而止又似未终结,能够清晰了解的只有故事发生的大概时间,分别是“初夏”和“春天”以及行动者在不同场景停留的大致时间。《桥》上篇的故事几乎就在史家庄、小林家、小林的学堂之间来回摆动,跟随叙述地点的转移我们大约能了解故事发生的时长。例如开篇小林去史家庄玩,故事时间大约为几个小时,即从下午始到落日终,但叙事时间却发展了五个章节,分别是《金银花》《史家庄》《井》《落日》《洲》。场景描写所包含的容量和故事发生所包含的时间量之间出现的反差就是小说时间缓慢前进的关键因素。这五个章节的叙述又主要通过场景和停顿两种叙述手段的交错使用使时间发展的更为缓慢。场景即叙述故事的实况,如对话和场面的记录。场景可以说是戏剧原则在叙述中最充分的应用,它由人物对话和简略的外部动作描写基本构成,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致相等,但总会夹杂一些其他叙述手段使整个文本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而停顿则是对事件、环境、背景描写的竭力延长,描写时故事时间暂时停顿,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比值为无限大。例如《洲》这一节,一开篇叙述就“停顿”在对“城外”景色的描写之中,其中还通过一段概要(文本中把一段特定的故事时间压缩为表现其主要特征的较短的句子)讲述小林对“城外”的留恋,叙述者甚至进入文本叙述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即用一首小诗确证“城外”小河存在的真实性,继而叙述者通过一段“场面”描写使故事时间又继续发展,但在叙述者使用完这些叙述手段之后叙事篇幅早已远远大于故事时间了。
《桥》的上下篇都很明显体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段,但在《桥》的下篇开头,叙述者以简短的句子做了这样一个说明:“在读者眼前,这同以前所写的只隔着一叶的空白,这个空白代表了十年的光阴。”[4]叙述者突兀地强调了一个巨大量的时间单位的流逝,使原本缓慢前进的时间状态极速流转起来,正当我们迫切想知道主人公在这十年内发生的变化时,叙述者却说:“他到了些什么地方,生活怎样,我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但这个故事不必牵扯太多,从应该讲的地方讲起。”[4]之后小说叙述节奏又缓缓变慢,时间一点一点向前爬动,在后面的叙述中停顿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偏向哲理的思索。禅宗词汇不时地出现,这些需要读者思考的过程也使得时间愈发变得缓慢。于是《桥》文本叙事的节奏可以归纳为缓慢前进——急速流转——缓慢前进(但并没有静止)。
在《莫须有先生传》中,时间的变化更是消解到莫须有先生的琐碎生活片段中,无从觅其痕迹,就像文中所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然而怎么的,吾们这个地球并没有走动,静悄悄的?”[3]在文本中季节、年月、时刻等表现时间的词语几乎不会出现,其中偶尔出现“午睡”“月亮”这样表现时间的词语大多也是场景的衬托,并且在这些故事发生的时间中叙事篇幅要远远长于它们,但我们却能从中能感受到时间在缓慢前进中是存在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首先是通过文本语境发现的——人物之间似乎彼此非常熟悉,这其中一定有相处时间长的原因,因此故事时间不是文本显性表现出来的那么短。其次这种发现是源于叙述者隐含的时间叙述,例如:“头年咱们院子里走一条长虫,哟,可了不得,扁担长,要不亏莫须有先生我就没有法子……莫须有先生连忙翻一翻日记而更正曰:‘房东太太,你这说的是去年的事,今年还没有到时候’……一年之后你又作了许多功课,这件事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3]缓慢前进的时间流就在这些不经意的对话中极速流转而过,使读者在读完文本之后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愿意去相信故事时间实际应有几年的跨度。于是《莫须有先生传》这样一部中长篇小说的容量却只显示发生了几个星期的故事含量,且得到了合理解释,又因为表现出的故事时间总量不长,叙事篇幅如此庞大,使整个文本节奏显得十分缓慢。因此《莫须有先生传》的文本节奏是这样的:缓慢前进——急速流转(暗含)——停止。为什么说《莫须有先生传》在文本结束时故事时间是停止的,我们从文本最后一段来说:“‘我生平是那么个急性子,岁今日亦何能免。为我传语于天下,《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获麟绝笔,从此一团吉祥和气,觉得此心无俗情时替人们祝福。’‘那么再见。’‘愿你平安!’‘愿你平安!’”[3]从文本可以看出在小说的最后,叙述者给了《莫须有先生传》一个闭合的结局,因此故事时间在这里也停止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桥》和《莫须有先生传》都是叙述节奏很缓慢的文本,并且故事的时间跨度都有大幅度的变化。他们的不同则在于,其一时间大幅度流转有明显和暗含的不同,其二时间在文本结束时发展的不同,一个开合一个封闭。《桥》与《莫须有先生传》在叙事方法上的同与异某种程度体现了废名思想中禅宗思想的特点。
二废名的禅宗思想:观心看净与识心见性
禅宗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也即是佛性。“自心”是众生得以禅修成佛的出发点和根据,是禅宗的理论基石。由是禅宗也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顿悟成就佛果。这也就是说禅修是心性的修持。[5]如何进行心性的修持,禅宗各派在方法、风格上各有不同,但都有同一的目的——启导心地的开悟,从而顿悟成就佛果。禅宗主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但禅学的发展很大程度又依靠文字的传承,这就如同诗学理论中言与意之辩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困境。
《桥》和《莫须有先生传》有大篇幅的场景描写和频繁使用的停顿叙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叙述者期望通过场面和思想的展示使读者“顿悟”,从而达到启发读者心地的目的。在这之间既有与读者就禅学思想进行沟通的可能,也有希望读者通过“顿悟”式的阅读达到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甚至理解作者内心真实想法的可能。就如同吴晓东所说的一样:“(废名)他还没有找到使自己私人化的心象与更多的读者理解的公共性相沟通的途径……小说中心象的营造与传达有时只能诉诸于禅宗式的顿悟,读者对意念和心象的领会也同样需要顿悟的功夫……”[6]因此对于小说场面和思想描绘篇幅占的比重就非常大,故事时间的发展则相应变得缓慢,整个文本的叙事节奏也就显得非常缓慢。这点在《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是相同的,不同的在于时间极速流转的方式以及故事结尾的方式,这种不同是与南北宗修持方式的不同息息相关。
在《桥》中,叙述者明白地告诉读者故事时间跨过了十年但不会影响小说的阅读,用这样一个大大的省略把上篇小林儿童时期的故事和下篇小林成人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其中表现出对比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说,上篇儿童小林的存在是一种接近于“佛”的存在,而下篇突然长大成人的小林则是需要通过不停的修持才能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存在。①因此这里时间的极速流转是为了突出小林儿时和成人的对比,从而显示出神秀的禅学思想(一种高度自觉的宗教理性),即成人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和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欲念中必须不断反观自身,“以宗教理性(离念不动的本觉净心)来克服、克制世俗的不净的烦恼尘劳污染”[7],这样才有可能顿悟成佛。这就是说儿童身上可能接近成佛的因素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被蒙蔽了,在这之后禅修者惟有不断地反观自身,观心看净②才能最终顿悟成佛。因为这样一种修持方式(修持者需要持续反观自身远离各种染心的妄念,这样才能恢复本觉真心、净心),所以《桥》的结局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只要修持还在进行,《桥》的故事时间就会继续延续。
反观《莫须有先生传》其暗含大幅度的故事时间的流转和闭合的故事结局则体现了六祖慧能的修行方式——识心见性③。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大致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方法、途径等都设置在活在现实之中人的心中,这种设置更显示出重视个人自我精神主体的色彩。成佛在自心中实现,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不是创造)超越的意义,现实性即超越性。这也就是把死后生命的追求转变为对内心的回归,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8]这种修持的方式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顿悟,一切全凭“本心”之意行事,在现实中“识心见性”“顿悟成佛”。因此不需要对比人身上“染心”和“净心”的区别再进行修持,而是“四时不循序万事随人意”,于是乎时间的流转也随人物之口随心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修持的方式能达到“顿悟成佛”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把《莫须有先生传》的闭合结尾和《桥》的开放结尾两相比较,可发现《莫须有先生传》与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是有联系的。
三小说的时间节奏与黄昏意象
从《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这样一种叙事节奏中(缓慢前进与极速流转的交替),笔者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时间节奏与黄昏的状态非常相似,黄昏就是这样一段看似缓慢前进然后突然急速流转到黑夜的时间段。而黄昏意象又是废名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意象,周作人早已注意到,废名小说总是笼罩在黄昏的空气里:“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1]。而黄昏意象又与禅宗思想紧紧相联系。
黄昏意象最初体现了一种漂泊感、孤独感、家归感。[1]就像《桥》黄昏一节中这样说:“有多少地方,多少人,与我同存在,而首先消灭于我?不,在于我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识,哪怕图画上的相识,我的梦灵也会牵进他来组成一个世界……史家庄呵,我是怎样同你相识!”[4]在黄昏明灭的时刻中,游子自然油生出乡愁,如此小林才会感叹与我不相识的人根本就没存在过,而史家庄则会反复在我的梦灵中萦绕。但是废名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忧愁中,这一节的最后他又说:“天上有星,地上的一切也还是有着。——试来画这么一幅图画,无边的黑而实是无量的色相。”[4]这就很鲜明地体现了禅宗思想的特点:“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和“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外部世界的所有“色相”都是虚空的,我们只能从自心、本心出发才能到达无上境界。因此不仅外部环境的景色甚至人类自身美好的情感,都只是这个世界虚妄的表象,我们只有从“无边的黑中”发现本心顿悟成佛。就像罗成琰说的:“让人物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突出黄昏时分万物瞬息即逝、刹那生灭的景象,寄寓禅宗‘凡有所相,皆是虚妄’的色空观念……其境的凄冷,情的冷寂,正是禅宗那种识破尘缘、超然世外的人生哲学和醉心于清幽寒寂的审美情趣的流露。”[9]这句话有两个层次意思,第一层是告诉那个迷恋黄昏明灭颜色的自己,惟有无边的黑即无色的颜色才是最美;第二层是告诫自己人类最重要的感情虽然是一直存在的,但我们还是要去“戒除”它们,因为我们还有更高的追求。
禅宗的某些思想甚至一些思维方式深刻烙印在废名的脑海中,使他在写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禅宗影响,从叙事方法到意象构建甚至故事的发展等。《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两者的叙事节奏和黄昏状态相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废名时间意识中一个突出的特点:生命在不自觉中疾驰而过。但对于时间以这样一种方式流逝,废名保持了一种淡泊的态度,而这正与作者倾心的禅宗有着很深的关系。
注释:
①禅宗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说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儿童的世界还是未受外界欲念所侵染的单纯的世界,他们的内心也纯然体现着人性的“自然”,因而最接近于本心、净心。禅宗强调的佛就在心中,就是说要向自己的心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儿童本就依照自己的本心而行动,不受世俗的不净的烦恼尘劳污染,因此也最容易“成佛”。
②所谓“观心”一方面是说要消除染心对净心的蒙蔽,另一方面是说要保持本觉净心。而保持本觉净心也就是要看住净心,所以也叫“看净”。
③所谓“识心”,就是直观自心,明了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生,自心就是佛;所谓“见性”,就是发现自身本有的佛性,觉知自性本来是佛,可以说,二者的境界是同一的。心性同一,也就是自心与自性同一,本心与本性同一。
参考文献:
[1]饶新冬.思索生命:废名小说意象读解[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5):4-11.
[2]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废名.废名集: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废名.废名集: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方立天.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J].哲学研究,1995(3):66-70.
[6]吴晓东.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32-42.
[7]伍先林.神秀的禅法思想[J].佛学研究,1999(8):161-167.
[8]方立天.性净自悟:慧能《坛经》的心性论[J].哲学研究,1994(5):44-50.
[9]罗成琰.废名的《桥》与禅[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1):70-81.
〔责任编辑:王露〕
Fei Ming’s Narrative Time Relationship with Zen:
From The Bridge to Biography of Mr.Fabricated
WANG Yujia
(DepartmentofLiteratur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hunan,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rhythm of The Bridge and Biography of Mr.Fabricated is slow, but the time span of these two texts are very large. In both of the novels the tim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differences lie in that the time changes significantly in one and imperceptibly in the other.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trend of the two novels is also to open and shut down in two different states.This kind of narrative t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as of Zen such as “thinking and cleaning”, “recognizing and seeing heart”. Fei Ming’s creation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Zen enlightenment, such as “everything is nothing”, “the Buddha blesses the multitude”, etc., 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Wu”.
Key words: Narrative distance; Zen; dusk images;TheBridge;BiographyofMr.Fabric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