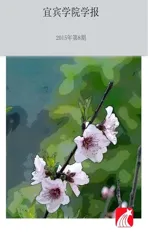心灵空间的开拓——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
2015-02-13姜玉平
心灵空间的开拓
——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
姜玉平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吕芳诗小姐》在叙事方法上别具匠心,注重叙事空间的营造。小说中作为空间意象的“红楼”“贫民楼”和“钻石城”不但对文本具有结构意义和审美功能,而且作为潜在的叙事力量在开拓人物的心灵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展现了主体突破重围向本质自我挺进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这三个空间意象形成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审美场域,深受中西文化影响,从而使小说因继承而根深叶茂,因创新而独树一帜。
关键词:空间意象;“红楼”;“贫民楼”;“钻石城”
收稿日期:2015-05-15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残雪与西方文学关系研究”(2014-qn-658)
作者简介:姜玉平(1979-),女(满族),河南南召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吕芳诗小姐》是残雪近年来最满意的作品,她认为这部作品是其创作的高峰,但国内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反应相当冷淡,相关评论文章更是寥若晨星。很多读者反映“读不懂”,或认为残雪在“搞怪”。这是因为该作品与作家其它作品均不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而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学——“新实验”文学。残雪认为这种文学是:“关于自我的文学。即拿自己做实验,看看生命力还能否爆发,看看僵硬的肉体在爆发中还有多大的能动性,是不是冲得破陈腐常规的桎梏。这样的文学具有无限宽广的前景,她摈弃了传统文学的狭隘性和幼稚性,直接就将人性、拯救自身当做最高的目标,其所达到的普遍意义确实是空前的”[1]。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创作,要求作家自觉地运用“蛮力”进入灵魂深处将自我进行分裂,使不同的自我进行扭斗、拼杀、交流,从而不断地提升精神层次;使自我摆脱世俗的阴影,让灵魂得到拯救。残雪打破常规的写作方式,将日常生活的材料进行审美转换使之成为暗示心灵的图像,并使用大量隐喻和象征。她的作品中每一个角色、意象、数字等都富含寓意,读者稍不留心就可能“陷入迷宫般的眩晕”[2],这就增加了阅读难度。
长期以来很多叙事学研究者比较重视小说中的叙事时间而轻视叙事空间,即使提到空间也总是将空间作为“惰性的容器”或者“静态的背景”而已。巴赫金在《对话想象》中开始强调空间作为活跃行为者的特征,认为时间与空间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两者互构互动。从此,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开始认识到小说中的空间对叙事发生的重要作用。比如,塞尔托在《空间故事》中认为空间是作家为叙事建立的边界,叙事与不断地划分边界有关。而弗朗哥·莫雷蒂在《欧洲小说集》中认为空间的作用不仅在于连接故事,而且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弥漫于文学领域中”[3]。残雪自创作以来就比较重视空间的建构,她说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时空也好,里面的经验也好,都是主动的。一个是把你扯着往前面去,一个是放肆动”[4]。可见,残雪与弗朗哥·莫雷蒂一样重视空间在推动小说叙事方面的积极作用,她的多部作品都以故事发生的空间命名,比如《黄泥街》《五香街》《边疆》等。事实上,残雪整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都建立在对空间的建构之上,她更注重对人物心灵空间的探索,而且她还将人物的心灵空间体验上升到艺术审美的角度探讨。她曾提到自己的审美机制“就是场外的逻各斯(理性)将‘自我极’发射到审美场内,这些‘自我极’同场内的努斯各部分纠缠在一起构成矛盾,经过扭斗与分裂形成美的艺术品”[4]16-17。审美场在作品中就是一个个的空间,这些空间是人身上的逻各斯为人物定的方位,在方位之内主体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既分裂又统一的表演,将表层的情感经验转化为深层自我,将“自我陌生化,使自我的本质显露,让人性在矛盾运动中充分展示自由之美”[4]3。在《吕芳诗小姐》中,“红楼”“贫民楼”“钻石城”,就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审美场,展现了主体自我突破重围向本质自我挺进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一“红楼”:欲望的迷宫
“红楼”是《吕芳诗小姐》中出现的第一个空间意象,是京城的一家夜总会。不过,“红楼”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娱乐场所,还是作者营造的一个让不同人物相遇、让人物的生命力得以激发的极富能动性的生存体验空间。
作家在“红楼”中安排了地毯商人曾老六与性工作者吕芳诗的相遇,并将这相遇看做是曾老六生命中的“奇遇”,因为这次相遇唤醒了曾老六沉睡已久的欲望与激情,令他精神焕发,“仿佛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5]曾老六与吕芳诗之后的交往伴随着痛苦,但曾老六依然无法放弃与她的交往,甚至在新疆遇到劫匪被绑在茅屋时,就靠着对吕芳诗的想象度过地狱般的煎熬。普通的一次相遇之所以对人物产生这么强烈的影响,是因为这次相遇对于曾老六来说属跨越界限的行为。在与吕芳诗相遇之前,曾老六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派剩男,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关注的也只有自己的生意。去“红楼”的行为揭示了曾老六告别旧我、打破清规戒律的隐秘渴望。他克服害羞心理来到“红楼”很大程度上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是他主动追寻的结果。而“吕芳诗”则似一缕散发着诱人芬芳的诗,吸引着曾老六。诗与人的欲望向来有着密切的关联,哈佛学者宇文所安认为,古典诗歌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可以唤起我们心中渴望迷失的那一部分”[6]。这渴望迷失的东西就是欲望——人心中的野兽,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受到清规戒律的压制。吕芳诗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的功能与诗歌相似,要唤醒每一个来到“红楼”顾客心中那隐秘而又受到抑制的欲望。曾老六在与吕芳诗初次相遇后不到一星期又去了“红楼”,他对自己的欲望感到害羞,但同时又觉得自豪,为自己能够跨越世俗伦理的限制、正视心中的欲望而欣喜。在此之后,曾老六越来越勇敢,有了一系列的冒险行为。可以说曾老六正是在吕芳诗的引导下踏上探险的历程,开始全新的生命体验,所以两人的相遇才能够成为奇遇。
由此可见,“红楼”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场所,其功能在于唤醒来访者心中的欲望。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讲述是残雪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她曾谈到:“从我开始创作直到今天,我写下的作品里都充满了欲望的……欲望是我创作的核心,它也是我的想象力的黑暗的母亲。”[7]不但曾老六有强烈的欲望,其他人亦是如此。琼姐、T老翁有多个情人,他们一心追求爱情的极致,琼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敢与死神共舞。残雪认为,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情感,可以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她的审美机制就是要让场外的逻各斯将人的欲望发挥到最大的限度。但人的欲望具有永不满足的根性,一旦被唤醒就会让人的心灵失去安宁,带给人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无休止的折磨。所以很多讲述欲望故事的作家最终陷入一个无望的结局,张柠在《欲望与无望——你的故事如何结尾》中谈到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诗学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是“一个黑洞,是深渊。它与死亡相连,要进入其中,必须带着火把,才能返回而不致迷路”[8]。残雪也认识到欲望的危险性质,曾老六被自己的欲望逼得发疯,他在“红楼”甚至闻到了南方墓园的气味,墓园里散发的当然是死亡的气味,这意味着“红楼”不仅带来痛苦还带来死亡,吕芳诗深有体会地说“红楼”经常发生鲜血淋漓的事情。这就是欲望带给人的矛盾体验,表面看来风光无限,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一旦真的沉迷其中,失望、折磨、痛苦接踵而来。
张柠认为“残雪就是一位出色的‘欲望叙事’的讲述者,但她最终将‘欲望’引入黑暗和死亡之中,连同肉体一起。也就是说她最终将肉体变成了‘无’。”[8]152的确,残雪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引入极为危险的状态,但最终不是要否定人的世俗欲望,而是借助人物自身的力量将危险的欲望逼进诗性的通道。她的长篇小说《五香街》《最后的爱情》都是讲述人的欲望的,其结尾都是充满希望的。小说中,无论是曾老六、吕芳诗还是其他人物都没有被自己的欲望吞没,吕芳诗最终意识到欲望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认为“红楼”的欲望冒险奠定了自己的生活基调。可以说,残雪是一个有勇气举着火把深入欲望的迷宫而又不迷路的少数作家之一,她通过创造新的空间让人物从欲望的陷阱中走出来。
二 “贫民楼”:理性之光
在“红楼”,曾老六与吕芳诗的心中潜藏已久的激情相互被唤醒,但两人的欲望始终得不到满足,反而在精神上备受折磨,自我逐渐出现分裂,于是分别在林姐和段珠(两个人的理性自我)的指引下来到“贫民楼”。“贫民楼”是作家创造的第二个重要的场所,与“红楼”相比,“贫民楼”与世俗生活的距离更为遥远,是残雪为了表现人的心灵世界运行而特意创设的艺术空间。
如果说曾老六与吕芳诗在“红楼”的相遇象征着他们与感性自我——激情、欲望——的相遇的话,那么,曾老六、吕芳诗在“贫民楼”的经历象征着他们与自己的理性自我相遇。与感性自我相比,理性自我更为冷静理智,会对人的感性自我或者说人性中世俗的一面进行冷酷无情的指责与批判。曾老六初次进入“贫民楼”时,8楼的夫人骂他是草包,15层的女子说他是懦夫,25层的男子因为曾老六不愿洗澡说他太狂妄;第二次进入时被两个穿黑衣的蒙面人痛打一顿,还被骂做内奸、贼;第三次掉到墓地里摔得半死。曾老六进入“贫民楼”的经历象征着他的理性自我对表层自我(沉溺于世俗生活的自我)的审判,也意味着他自我反省和忏悔。虽然一开始曾老六还不明白自己在反省自我,并由于身体上的伤痛而产生伤感、愤怒的情绪,但他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一出由自己主动参与的表演,其目的在于认清真实的自我,然后发展自我走向更为本质的深层次的自我。
吕芳诗在“贫民楼”也有类似的体验,她在段小姐的指引下来到“贫民楼”,在楼道里看到一名年轻女子原地踏步,这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她重复自我,没有变化与超越。接着楼下传达室的老头指责她从事着不光彩的职业,没有自我批评的习惯,惰性太重。这其实是吕芳诗的自我反思,对原有的生活状态的不满。段珠即断住,吕芳诗在她的引导下来到“贫民楼”,象征着她的理性自我对自己情感生活的钳制与批判,理性自我要求她节制自己的欲望,激发生命意志、提升自我。也正是在进入“贫民楼”之后吕芳诗认识了富翁T老爹(T者阶梯之意也),暗示她要将人生看做是一个阶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吕芳诗很快意识到T老爹是自己精神上的支撑而同他打得火热。
与理性自我的相遇使曾老六和吕芳诗能够站在一个高于感性自我的层面审视欲望以及原有的生活,增强对自我的认识形成属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漫长过程,所以曾老六和吕芳诗都要多次进入“贫民楼”,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委屈、伤感、恐惧甚至绝望的过程。因为人的理性要剥去自身在世俗生活中的一切伪装,赤身裸体面对自己的本来面目。这还是个体走出童年、走向成熟必须亲历的阶段,只有借助理性之光,个体才能从欲望的迷宫中走出来,才会主导自己的生活,变得独立、坚强、勇敢,摆脱对家人以及他人的依赖,完成自己的启蒙。
“贫民楼”艺术化地再现了人与理性自我相遇的奇景,为人物打破世俗生活的牵绊、突破生命界限提供一个绝佳的场所。“贫民楼”又是公墓,是一个让人体验死亡与虚无的地方。传达室里放着215个骨灰盒,进入这栋楼的人都要学会面对死去的幽灵。曾老六和吕芳诗进入“贫民楼”后尽管受到理性自我的严厉制裁,但由于对世俗生活的留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是继续“糜烂地生活”。吕芳诗虽然住进“贫民楼”,但总感觉厨房充斥着怀旧的气氛,卧室、小客厅里弥漫着空虚惆怅的氛围。段珠小姐指引吕芳诗认识死神,死神是不能直接谋面的,段珠也只能让吕芳诗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为了让吕芳诗更好地体验死亡,段珠在她面前表演了死亡。“精神若要穿越肉体的原始森林,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同死亡晤面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即使是从那‘关口’死里逃生之后,肉体还会转化为欲望的猛兽,横在追求者的路上,要窒息精神的发展。于是死又一次来临。”[9]6通过多次死亡体验吕芳诗克服了最初对死亡的恐惧和伤感情绪,认识到人的肉体生命是短暂的,但真正生活过的灵魂不会消失。在段珠小姐房间里自由飞翔的海鸥使她突然醒悟到:人的自由就是在死神的威胁下催生出来的,正是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人们才会更加珍惜生命,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吕芳诗不再犹豫了,开始以具体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曾老六也是在掉进墓地体验死亡后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消极等待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可以像公墓里的幽灵一样冒着生命危险骑自行车飞翔。这意味着对死亡的体验激活了曾老六的想象力,使他产生认识上的飞跃。虽然曾老六只飞到公寓的二楼,而且没飞多久就落到地面,但却是他第一次体验到的自由,这种对飞翔的体验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渴望达到的境界。
进入“贫民楼”之后,吕芳诗和曾老六对自己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体验到短暂的自由和快乐,但是不满足接踵而来。如果说在“贫民楼”人的欲望受到理性的钳制,与此同时,人的欲望却不甘心俯首称臣。理性的严酷制裁导致人的欲望的反弹,吕芳诗和曾老六的世俗欲望得到控制,但又转化为创造的欲望、对永恒的渴望,而这些欲望在“贫民楼”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吕芳诗和曾老六最终还是离开了“贫民楼”,前往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钻石城。
三“ 钻石城”:艺术的故乡
“钻石城”位于西部边疆,是小说中的第三个审美场,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场所,吕芳诗、曾老六以及“红楼”的大部分员工先后来到这里。如果说“红楼”是一片欲望狂舞的原始森林,“贫民楼”是人与理性自我谋面、灵魂展开自审的场所,那么,边疆则是一个将人的世俗欲望升华为创造的精神、将生活变为艺术的地方。
小说中小花和旅馆经理的爱情与艺术家和艺术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与经理的关系中,小花是主动的,她向经理表白了情感,但经理患有严重的健忘症,容易忘记小花是自己的情侣,这完全是种单相思。于是小花的爱情充满悖论:她和经理之间的每一次新的接触都是一次重新认识,一次不可理喻的新的恋情。再后来经理干脆从小花的生活中消失了,隐居在旅店顶层的阁楼里,小花只能凭借信念维持与经理的联系,过着一种苦熬的生活。小花与经理的关系就像卡夫卡的《城堡》中K与城堡的关系一样,体现了艺术家进入艺术故乡进行创造的心路历程。艺术家进行的是一桩“无中生有”的事业,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所谓的创造也许不过是自欺,理想中的目标总是在远处飘荡,追求者找寻不到确凿的证据,感受更多的是寒冷、空虚与晕眩无力。小说中女子常云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即便与情人跳舞她也感觉不到情人的实体,内心充满辛酸与无奈。吕芳诗来到“钻石城”不久就觉得这里是个烦恼之地,无名烦恼会一阵接一阵袭来。这里的生活像被野物日夜追逐一样极为紧迫,琼姐的老爹总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尽管如此,小花、常云等人还是无法放弃自己的爱情,反而从这种压抑的生活中看到希望,从苦熬中找到幸福与快乐。生命本身是虚无的,人无法承受虚无,冒险站出来生存,想要将虚无变为存在,但却陷入更深的虚无。邓晓芒将残雪的这种矛盾视为一种幽默,“幽默的自相矛盾就在于,每个人物既是在狂热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目标,真诚地向着更高级的生存目标挣扎,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挣扎终归无效,因而又在嘲笑或自嘲地看待自己的追求,意识到自己在地狱中如此绝望的处境,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听凭自己的生存意志去作冒险开拓,而不是看破红尘、一了百了。这就表现出生命本身的幽默本质,它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盲目乐观的,而是幽默的”[10]564。邓晓芒对残雪小说的把握是准确的,只不过随着创作的深入,残雪小说幽默的基调有所变化。残雪早期代表作《五香街》中的幽默带有喜剧的滑稽色彩,而这部作品中的幽默则有着悲剧的严肃与崇高,其境界更为纯粹。
作为更高层次的审美场,“钻石城”里的交流与“红楼”“贫民楼”相比更为隐秘复杂,所有的事情都是曲里拐弯的。比如吕芳诗与情人T老翁之间的交流就似一个难解的谜。吕芳诗在意识到T老爹是自己的精神支撑之后,追随他来到钻石城。吕芳诗只能在远处看到他、听他的咆哮声或与他的影子跳舞,却始终无法与之谋面,只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T老爹象征着吕芳诗的本质自我或者理念自我,给她的生活带来方向感,引导她不断地超越自我向灵的境界攀升。而人对自我的超越在死神到来之前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吕芳诗不能直接见到T老翁。她终于明白T老翁虽然离开她却反而将两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渴望无法满足,所以渴望才是永恒的;正因为理想无法实现,所以理想的旗帜才会永远飘扬。这个难解之谜的谜底是死亡,T老翁一到边疆就寻找自己的墓碑。只有死亡能阻断两者之间的交流,也只有死亡能实现两者之间的交流,主体自我正是在死亡阴影的催逼下从世俗生活跃入艺术的故乡的生活,用有限的生命去叩响无限之门。
四中西文化交流的审美场域
由上可知,三个空间意象在小说中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但三个空间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红楼”作为第一个审美场不是凭空产生的,按照残雪的说法是“逻各斯将‘自我极’投放到努斯里面,促成、逼迫努斯挤压分裂自身”[4]55。在小说中具体体现为吕芳诗的本质自我,由琼姐引导她到“红楼”工作,与不同的情人相遇,在情感无法满足之际,精神开始自我的分裂,此时她的肉体与灵魂、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然后进入“贫民楼”与理性自我相遇,用理性钳制自己的欲望。但理性的钳制又引发欲望的反弹,这里人的欲望不是被完全消灭反而更加强烈了,人身上的分裂加剧,吕芳诗只好来到边疆。边疆作为理念之地整合了她的不同自我。刚来到“钻石城”时吕芳诗觉得自己以前过着糜烂的生活,通过与小花及家人(本质自我)的交往,她看到自己以往生活的意义,认识到没有在“红楼”的体验她不可能进入“贫民楼”,也不可能进入“钻石城”,曾经被否定的生活在“钻石城”获得全新的理解,而人的本质自我也由抽象变为具体的现实。不但“红楼”“贫民楼”的人要去“钻石城”,“钻石城”的人也时刻关注着“红楼”与“贫民楼”的动向。小花的父亲本来是京城人,在“钻石城”定居后一直怀念家乡,时常需与每一个来自京城的人进行交流方可缓解思乡的苦痛。是“红楼”和“贫民楼”的人充实了“钻石城”人们的生活,给边疆带来生机与活力。所以,不但“钻石城”是永恒的,“红楼”也是永恒的,最后吕芳诗和曾老六都看到“红楼”高高浮在半空中,这象征着经过吕芳诗等人的努力后,世俗欲望的沉渣已经消失,升华为美、坚固与永恒。正是在三个空间的交流影响下,主体自我由混沌而分裂,由分裂而统一,生存空间不断拓展,心灵体验越来越丰富。
“红楼”“贫民楼”“钻石城”是作家为人物阶段性体验创造的边界,随着探索的深入人物不断跨越原有的边界,建立新的边界。按照塞尔托的空间理论,跨越边界需要跨文化的区域。小说中的三个空间还有文化模仿的功能,为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场域。残雪自称是阅读古典文学作品长大的,其创作自然会受到古典文化的影响。“红楼”的空间意象体现残雪对我国古典文化的模仿与继承。“红楼”本是古典文学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意象,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红楼。与《红楼梦》中的红楼一样,《吕芳诗小姐》中的红楼也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除了“红楼”这个空间意象之外,残雪还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其它意象,如玉的意象,曾老六说林姐是一块稀世宝玉。此外,琼姐的父亲在沙漠里种红柳的情景,与我国古典文化的田园牧歌理想很相似。残雪虽然在谈到自己的文学观时曾批判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她要抛弃传统文化,相反,她认为“目前的中华民族里有一个潜意识的大宝库”[1]89。
不仅如此,残雪还借鉴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其一,残雪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中肉体与灵魂、欲望与精神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小说的“红楼”部分体现了主人公欲望的觉醒,这个时期的欲望主要表现在身体层面,而“贫民楼”这一部分则体现了人的灵魂觉醒,与“红楼”形成一种矛盾关系,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对立关系。“钻石城”作为理念之地则整合了主体自身的分裂,使主体自我的不同部分形成对话关系,相互之间取得暂时的和解。当然,新一轮的矛盾还会出现,主体自我正是在分裂中走向成熟的。其二,残雪还从西方哲学中汲取营养。这部作品的内容表面看来天马行空,匪夷所思,其内里却具有严密的深层逻辑做支撑。比如该作品的结构具有辩证法的色彩,作家先通过“红楼”唤醒人的欲望、肯定人的欲望,然后通过“贫民楼”来否定人的欲望,再在“钻石城”欲望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得到肯定。还有作者把人的自我对象化,把人的自我分裂开然后让不同的自我进行对话交流,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三,残雪深受西方文学经典的影响。残雪的小说在审美机制上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所谓审美机制“就是人性机制,也是人认识自我、认识自然的机制,它还是使人的生命体验中最根本的那个部分得以实现的机制”[4]3。她认为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卡夫卡、卡尔维诺等西方大师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这种机制。残雪的这部作品就是借助人自身的主观活动和人与人之间互动交流促使作品中的人物认识自我、提升自我。
总之,残雪的这部作品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是我国文化传统同西方的理性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果实。正因为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吕芳诗小姐》显得根深叶茂、内涵丰富,能够激发喜爱读者的阅读热情。
参考文献:
[1]残雪.什么是“新实验”文学[M]//残雪文学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高玉.走向虚无的旅程:残雪小说精神机制论略[J].南方文坛,2013(2):30.
[3]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C]//James Phelan, Peter J,Rabinowitz.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残雪,邓晓芒.于天上看见深渊:新经典主义文学对话录[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5]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6]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程章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7]残雪.追求逻各斯的文学[EB/OL].(2010-02-06)[2015-03-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acfc90100h57s.html.
[8]张柠.叙事的智慧[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9]残雪.艺术复仇:残雪文学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露〕
The Development of Mind Space:
Aesthetic Function of Three Space Images in Can Xue’s Miss Lv Fangshi
JIANG Yuping
(CollegeofLiberalArts,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Henan,China)
Abstract:Miss Lv Fangshi shows ingenuity in narrative methods and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pace. The three space images“Red Chamber”“the Poor Building” and “the Diamond City”, not only have the structural and aesthetic function of the text, but also have potential narrative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mind space, which shows the subject’s self-advancing arduous journey.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three space images form different but related esthetic field, which make this novel unique because of its innovation.
Key words: Space image; Red Chamber; the Poor Building; the Diamond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