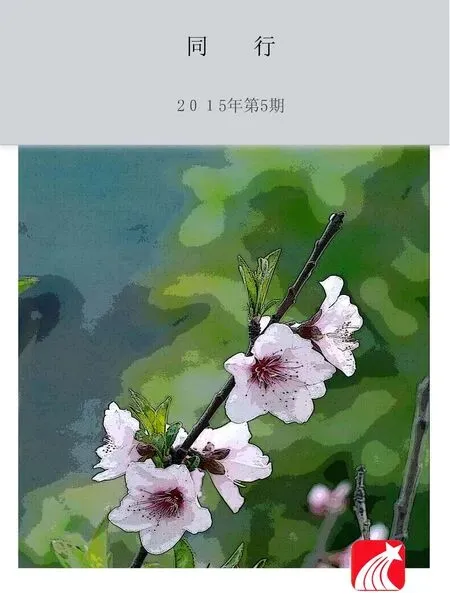扎西达娃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解读
2015-02-13高红天津财经大学
★高红(天津财经大学)
扎西达娃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解读
★高红
(天津财经大学)
【摘 要】扎西达瓦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以西藏为创作对象,在作品中运用魔幻艺术手法,即表现西藏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也展示了西藏独特文化生态的奇幻景象。他的小说将客观现实与魔幻境遇巧妙地并列、融合,同时保持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关键词】魔幻现实主义;客观现实;超自然现象
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强力影响下,很多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取法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法。在这些作家中间,扎西达娃是最成功的。扎西达瓦八十年代初对拉美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认真阅读了马尔克斯,鲁尔福等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深得其中三昧。同时作为藏族作家,他立足于以本民族生活为写作对象,在魔幻叙事创作上取得了独特的优势。西藏是孕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天然沃土。作为独具特色的地域,西藏充满了神秘奇幻的色彩。它有着神话般的历史,神奇、优雅、威严的景物,贯穿原始主义、具有刺激性冲击力的独特文化,奇异的民风民俗,陌生的宗教信仰,独有的民族思维。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而成了一种非凡的西藏意识,与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天然契合,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最好的素材。由此,扎西达娃等西藏小说家迸发了创作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极大热情。他们推出“创作西藏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口号,为魔幻文学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以现实幻化的笔触表现现实,同时保持现实主义本色的文学式样。它“把现实放到一种魔幻的环境和气氛中客观、详细地加以描写,…给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却又不损害现实的本质。”(1)(P371)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取材于日常生活,运用想象力将原始素材过滤加工,施以艺术变形,使其摆脱自然法则和逻辑关系的限制,形成超现实、超自然的事件、人物,再将其与现实元素融为一体,去曲折地反映客观现实。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现实和奇幻的巧妙结合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特性。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故乡拉丁美洲的学者、作家们,对其做出过大量评说。例如,委内瑞拉评论家罗德里克斯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来自现实生活,但并非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素材经过艺术家一番雕琢后的魔幻现实。”(2)(P202)墨西哥学者莱阿尔曾言,魔幻现实主义“不是臆造用以回避现实世界的幻想世界,而是面对现实,深刻地反映这种现实,表现存在于人类一切事物、生活和行动中的那种神秘。……具有神秘色彩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源泉。”(2)(P196)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则说:“神奇现实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现实非凡的、别具匠心的启明,是对现实状态的夸大。”(1)(P469)以上论述可谓鞭辟入里,精准到位。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问世有着明确的目的性,绝非事出偶然。其创作意图有三:第一,最有效地反映不寻常的社会现实、文化风貌、生存状态、思维方式。第二,锐利鲜活地宣示作品的主题内涵。第三,实践艺术创新,打破传统现实主义艺术局限性,构建美学形式的陌生化效果,给读者全新的审美体验。我国拉美文学专家陈众议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段…是陌生法。…变习见为新知,化平凡为神奇…一旦进入它的世界,我们似乎感到自己久已麻木的童心之弦被重重地弹拨。”(3)(P103)卡彭铁尔也言:“神奇现实…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的精神兴奋。”(1)(P470)他们的评述精确地点明了魔幻文学的艺术魅力所在。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多样化的魔幻表现策略,主要包括超自然事件、神话、传说、夸张、象征、幻觉、预示、任意时空、元小说技巧等。
扎西达娃的魔幻艺术表现了西藏经验的日常与奇幻两个方面,把史实、现实、超现实现象结合成完美的整体。其作品描述了藏民的日常经历、情感世界、行为方式、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同时“调动宗教、经籍、神话、传说、神示、巫语、鬼魂、想象、梦兆、幻化…为他的牧鞭驱使,”(4)(P211)赋予现实以荒诞奇异的外包装,但始终坚守现实主义的本质。
本文选取扎西达娃的三部代表性作品,对其魔幻现实主义艺术特征加以分析解读。
《西藏,隐秘岁月》是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小说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但内容异常丰富,堪称一部超浓缩作品。小说中,在小山村廓康,达朗与次仁吉姆是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然而,次仁吉姆长大后被迫成为尼姑,在孤独中一生侍守隐居高僧。达朗无奈另娶他人。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小说展示了一幅现当代西藏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如马丽华所言:“通过一个小村舍中几个人物的命运,反光出整个西藏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时代变迁和人事沧桑。”(4)(P210)作为“扎西达娃小说中最富历史深度的作品”(8) (P392),小说覆盖了75年的时间,涉及了世纪之交英国对西藏的入侵,五十年代解放军解放西藏,文革中的学大寨运动,及八十年代西藏的改革开放。小说生动地记录了西藏人民的实际生活,他们的婚丧习俗、宗教行为和性格特征。简言之,小说是西藏现实的忠实表现。
同时,该小说充满了浓列的魔幻气息。首先,它表现了诸多超自然现象。例如,米玛误射了菩萨雕像后,一场山崩爆发,毁掉了他生长于斯的山村;当米玛,妻子察香、女儿次仁吉姆跪拜在一个圣人所居山洞前,请求他接受次仁吉姆为尼时,一条洁白的哈达从洞内飘出,轻轻落在姑娘的脖颈上;次仁吉姆童年时,其行为显示了种种奇异迹象,表明她是诸神的化身。但外来的英国人将其冲没,使其灵性消失殆尽,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山区女孩。
其次,小说大量运用夸张手法,提取日常事件,抓住其本质特征,把它渲染到不寻常的程度以创造奇幻事象。例如:察香在七十岁时怀孕,两个月后生下了女儿;次仁吉姆在青春期身上奇痒难耐,因而产生了洗浴狂。但她穿上英国人留下的军服后,便再也不觉身痒,不想洗澡了。达朗的儿媳次仁吉姆与丈夫外出了一个时期,归家后,她对外面世界的所有记忆竟然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为了强化魔幻感,小说讲述了许多神话传说。例如:一个持密修士修练“起尸法”,用牙齿咬一具女尸的舌头。但他自己的舌头却被女尸咬掉。他当场毙命,女人却起死回生;经书中记载,当莲花生大师坐着喷吐五色火焰的飞车离开西藏去南方时,火焰给哲拉山脉留下了一个大坑,后来变成了一个碧蓝的深湖;一位修行大师的灵魂会随意地离开身体,在世间漫游。他会化身为一只鸟,或一阵风。
此外,小说多次使用梦幻手法。达朗初次见到儿媳次仁吉姆时,顿时陷入幻境。他觉得这个女孩是他所爱的次仁吉姆返老还童,一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在看望弥留之际的次仁吉姆时,达朗再次产生幻觉:他和她有情人终成眷属,举行了婚礼。而次仁吉姆在父母故去后,每当她思念他们,她都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生前说过的话。幻觉的使用模糊了真实和非真实之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魔幻意味。
由于预示手法显示冥冥中的力量预判人类命运,传递神秘的宿命感,所以也被小说所运用。例如,次仁吉姆幼年时会画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盘,会跳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神舞。而她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异秉赋,预示了她命里注定无法享受人世的爱情,只能终生事佛。
小说中,象征手法发挥了重要的魔幻化作用。象征的复合含意有实在性,又有想象性,因而有效地创造出了奇幻的意境。小说中,除老一辈外,所有的女性都叫做次仁吉姆,包括故事末尾出现的年轻女医生,而她和达朗家并无关联。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刻意设计的象征。重复的女性名字代表了藏族女性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暗示了生命(女人创造生命)重复不变的精义与周而复始的运行轨迹,进而隐喻了世事万物的反复重现,体现了一种莫名的无限感与永恒感。一位神奇老者指着不知从何处掉落的一串佛珠对女医生次仁吉姆说:“这上面每一颗珠子就是一段岁月,每一颗就是次仁吉姆,次仁吉姆就是每一个女人。”随后叙述者评论说,老人的话“一语道破了这个从不为人所知的真谛。”(5)(P46)对此马丽华指出:“对不同命运的女人们刻意使用相同名字…即表现了生命与生活的循环往复,又是对循环往复的生活之流渐进的强化审视,从中演绎出民族和人类的无穷尽的悲喜剧。精神与灵魂从中渐显。”(4)(P212)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扎西达娃的另一篇魔幻现实主义名作。它在技法上更具试验性,更加错综复杂。小说记述了朝圣者塔贝和女孩婛前往传说中的香巴拉王国的一次旅程。通过描写他们的旅程,小说详尽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西藏城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山区一家运输公司拥有德国造卡车和一家地毯厂,配有电脑。乡村生活生机勃勃,丰富多彩。大多数家庭有了拖拉机,它们的轰鸣声盖过了公鸡报晓的叫声。年轻人的生活中充满音乐和迪斯科。与现代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地人仍然保持着传统习俗。他们遇到麻烦时仍然求助于神灵指引;表达长度时,仍然伸出一只胳膊,用另一只手做出砍的动作,以表示他们所指的长度;在公路上,总有朝圣的人沿着地面爬行,满面污垢,前额因为不停地叩头而变得淤青。
同时,小说的现实生活画面又被深深地嵌入了魔幻的框架之中。小说伊始,一位97岁的活佛便向叙述者介绍了人间天堂香巴拉以及到达那里的路径;“当你翻过喀隆雪山,站在莲花生大师掌纹中间,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象。在纵横交错的掌纹里,只有一条是通往人间净土的生存之路。”(5)(P71)活佛还告诉叙述者塔贝和婛正在寻找香巴拉。关于香巴拉的神话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它对小说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男女主人公对它的寻找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通过这个神话传说,小说开篇即沉浸在迷离恍惚的意境之中。
小说同时描写了许多超自然的现象。例如,一个陌生人通过便携式计算器知道了婛的名字和年龄;一个乡村占卦人预知了塔贝和婛的到来;更神奇的是,在虚构的莲花大士掌纹地,塔贝、婛和叙述者听见了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的卫星实况转播。此外小说生动地描述了非正常的自然景物。例如莲花大士掌纹地似乎为魔力所控制。那里狂风呼啸,但人却感觉不到。空气凝固冷冽,土地如烤焦一般,寸草不生,布满上千条纵横交错的沟壑,宛若世界末日的幻景。
象征也是小说传达难以捉摸的神启意味的重要手段。小说的标题《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即呈现了小说的中心象征意象。皮绳扣代表了藏人宗教文化、宗教意识的愚顽性。荒诞不经的宗教信念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就像用坚实的皮绳结成的死扣一样,牢牢地困住了塔贝这样的宗教狂热信徒的灵魂,使其走火入魔,迷失本性。而小说显示,这一切似乎都是神意所定。
然而,小说的核心魔幻技巧是其元小说策略和非传统时间方式。首先,塔贝和婛的故事本来是叙述者(一位专业作家)很久前创作的一篇小说。他把手稿锁入皮箱,从未示人。神奇的是,活佛知道这个故事,并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给叙述者。也就是说,本小说,小说中叙述者创作的小说,及活佛讲的故事,在内容上是重合的。这种写法是一种被称为文本嵌套的元小说技巧。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使用过这种方法,其中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的羊皮纸手稿内容同小说完全相同。这种方法成功地将故事变得虚幻莫测,半真半幻。
其次,在小说结尾处,叙述者出发寻找他虚构的人物塔贝与婛。结果他在莲花大士掌纹地找到了他们。塔贝奄奄一息。叙述者试图救活他,但他还是死了,叙述者将婛带回。这里,扎西达娃应用了另一种元小说技巧:作者和人物的直接接触。这种技巧在元小说名作,如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及冯内古特的《冠军的早餐》中都出现过。此技法使叙述者,一个“现实世界的人,”卷入了香巴拉的神话中。真实的人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以及自己凭空臆造的人物的朋友。由此,小说中神话和现实,真实和杜撰浑然成为一体。
同时,小说使用了非直线型时间表达方式。自然时序被打乱,时间随着故事行动逆转闪回,往返穿梭,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混合在一起。小说中,叙述者说他在1984年写作了塔贝和婛的故事,故事就在这一年发生。也就是说,小说的主线情节要晚于这一年。所以,当叙述者去塔贝和婛的时候,他必须沿着时间回到1984年。结果,他一穿过喀隆山,时间就开始倒流。手表上的日历和指针朝着相反方向移动,比正常速度快了五倍。当叙述者与他的小说人物见面时,他的表立即停止了。然后,叙述者和婛启程回返时,时间又开始向前走。小说时间的错乱式转换移动,使时间的客观现实性变模糊,外表被神化,带来了特殊的迷宫韵味。
扎西达娃的魔幻艺术在《古宅》中呈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旧西藏社会的暗无天日、农奴的悲惨生活,与极左年代西藏农村的贫穷落后与荒谬混乱的状况。
同时,小说笼罩着浓重的魔幻气氛。其首要魔幻表现是男女主人公的传奇人生及超自然性经历。绝色美女拉姆曲珍是旧贵族,拥有一座大宅第。她被情人抛弃后,把怒火发泄到她的农奴朗钦身上,因为他与其负心人外貌相似。她让他晚间服侍她,挑逗性地向他暴露身体,又不让他触碰自己。她不许朗钦接触女人,让他在欲望中熬煎。西藏解放时,她失去了她的大宅,成为所有男人的泄欲工具。奇怪的是,每当她和男人睡觉,她的身体就散发出冰冷刺人的气息,使男人周身寒彻,像染上了大病。但朗钦是例外。他总是在阴历每月十五对她产生欲望。在那一天,她的血会变暖。岁月流逝,拉姆曲珍却青春永驻,七十岁时依然年轻美丽。然而,当她被落实政策,重回旧宅时,却一夜之间变成“垂死的老妇”。
解放后,朗钦当上人民公社社长。他47岁时还是处男。此后,他和村里所有女人睡觉,“已婚的,未婚的,美丽的,丑陋的,聪明的,愚笨的,…,”(5)(P139)这些女人一共给他生了237个女儿,这些女孩左臂都有一个红色的,眼睛形状的胎记。文革爆发后,他被打成“堕落的蜕化变质分子,”从领导位置上被免职。
小说对中心人物人生经历与性行为的夸张性、神秘化描写,尤其是对拉姆曲珍超越时空的美丽与血液温度周期性的变化,及朗钦私生女胎记的奇异性描述,产生了扑朔迷离的魔幻效应,构成了小说魔幻性的主体。
《古宅》中,象征也是重要魔幻手段。小说的核心象征是庄园古宅。通过作者隐喻式的描写,无生命的古宅似乎和人类生命息息相关,成为操控人类命运的不可知力量。拉姆曲珍与朗钦都曾是它的主人,都因为它而经历了天地之别的人生遭际。因此叙述者说:“古宅的主人都不会有好下场。”(5)(P148)
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幻觉描写。幻觉产生了迷离朦胧、真假难辨的效果。例如,朗钦弥留之际,恍然觉得身边围拢了一群女孩,她们都卷起左衣袖,向他展示她们的红色胎记。然后,出现了大自然和人类心灵的神秘交流。当临终的朗钦迷惘伤感地唱起一首深情的歌曲时,一场雪崩发生了,无边的白雾弥漫于整个天际。此外,小说中人世罕见的景色,几个世纪面貌依旧的古村,非人化的山民和从来不哭出声音的婴儿----这些高度夸张的描写都增加了小说的总体魔幻气氛。
扎西达娃小说中的魔幻元素或怪诞诡谲,或惝恍迷蒙,但都显示出了很强的可信性。这是因为扎西达瓦以高超的手法对它们做了合理化技术处理。其主要方法共有三种。
(一)适时对不可思议事物加以巧妙、不露痕迹、恰到好处的合理性解释说明,将幻象与合乎常理的因素相提并论,化为一谈。例如:察香死去时,她的脑门突然开裂,脑浆飞迸而出。叙述者就向读者解释说,这是因为察香生前积德行善,皈依三宝,戒除了女人天生的“五毒,”即贪心、忿怒、愚痴、娇矫、嫉妒,因而功德圆满,使她的灵魂飞向了天界。死人额头暴裂不可理喻,但民间认为善有善报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这一奇闻不足为怪。
(二)用陈述事实的口吻描述奇幻,语气平静、淡然、放松甚至随便,仿佛叙述最平常的事件,给读者一种印象:它们都是“真事”。例如,提及永别廓康的人下山必定连连摔倒的奇异现象时,叙述者说:“他们一行人离开廓康,米玛发现他们不停地摔跟头。米玛这才明白,凡是从廓康离开后不再回来的人下山都会摔跟头。旺美一家摔着跟头下山,他们不会再来看望老邻居了。”(5)(P10)叙述者习以为常的口气,轻描淡写的话语有效地消解了此事的超现实性质。
(三)坚持以西藏为背景。西藏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传奇王国,充满原始性、奇异性与不可捉摸性。那里奇特的文化生态,神奇的景观、古老的传说、绚烂的神话、怪诞的习俗,特殊的民族意识,这一切交汇一起,给奇异事物带来先天性可信度。读者会认为,在那里出那样的事,并不奇怪。
总之,扎西达瓦对奇迹异象不动声色的态度与沉着冷静的解说,使难以置信之事自然地融入日常经验。奇幻变得不再奇幻,而是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令人信服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
扎西达瓦的魔幻书写不是为魔幻而写魔幻,而是出于深刻的思想与艺术考量,意在表达深刻的主题寓意与追求文学的形式创新。首先,扎西达瓦的魔幻话语是鲜活如实地反映西藏地域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最直接的工具。西藏是佛化之邦,多数人都是世界上最虔诚的宗教信徒。而宗教是神秘与神奇的源泉。宗教造就了西藏奇异的人文景观与藏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例如,藏教有一家一户侍奉一位隐身修士终生的习俗,次仁吉姆尊神意终身供养一副男性骨架化石的奇事生动地演绎了这一文化怪象;藏民认为万物有灵,山水草木都是神明的化身,因此朗钦与自然界的离奇的心灵感应是实在的现实。描写这种“现实”反映了藏人的信仰。又如,上千年来藏民坚信时间,或者说生命过程,“是一种无限循环与轮回的形式。”(5)(P121)而半真实半梦幻的重复的女性名字有效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其次,通过魔幻笔法,扎西达瓦有效地表达了对西藏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的反思与批判。第一,其批判锋芒指向了宗教意识的冥顽不灵。次仁吉姆与塔贝在魔幻中演绎的人生悲剧显示了宗教痴迷对人性的摧残,也表明了宗教狂热的虚妄性。第二,扎西达瓦的魔幻艺术鞭笞了藏文化中丑陋、混乱、畸形的性习俗与性观念。在藏区,男人随意睡女人天经地义,自古使然。女人是男人当然的性工具。拉姆曲珍与朗钦魔法附身般的性特点与性行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朗钦玩弄女性被撤职查办,还认定“祖祖辈辈的历史,千百年的风俗,旧时的法典,从没说过跟女人睡觉算罪状,”并因此“悲愤欲绝”(5)(P147)。第三,扎西达瓦的魔幻笔锋还将批判矛头对准了浸透着罪恶的藏域权力文化与权力观念。在西藏,权力是绝对的,如同神力所附。而藏人对权力有着视若神明、顶礼膜拜的集体无意识心态。掌权者至高无上,可以任意支配一切,而受控者卑贱如草芥,只是主人的玩偶,毫无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可言。在围绕古宅演义的梦幻境遇般的权力更迭剧中,拉姆曲珍作主子时,无人性地虐待朗钦,待他不如一条狗,因为狗还有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自由。她用性折磨朗钦,以他的痛苦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而朗钦对她俯首贴耳,温驯地屈从于她的虐待和侮辱。当朗钦成为统治者后,也专横霸道,不可一世。拉姆曲珍与全村女人都对他卑躬屈膝,心甘情愿地作他的玩物。在扎西达瓦的魔幻文本中,虚幻与现实交错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告诉我们:西藏的权力文化孕育了无尽的罪孽、贪婪、仇恨,糜烂,变态、声色犬马,命运变迁,非人的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葬送了无辜的生命,生成了西藏沉重悲凉的历史。然而,依据藏人传统的权力文化观,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一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扎西达瓦对朗钦持同情态度。朗钦至死也根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他的这一态度是真诚、单纯、质朴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临终前他还关心、挂念着拉姆曲珍)。
他只是荒诞文化价值观的牺牲品。扎西达瓦所批判的是荒谬愚昧的藏文化,而不是为藏文化所异化的西藏人。
对此王达敏恰如其分地指出:扎西达瓦的小说,“通过魔幻描写,…蕴含了共同的思想指向:思考原始感情、意识观念与现代文明进程的关系;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进行现代审视与评价,基本持一种反省与批判的态度。”(6)(P132)
同时,扎西达瓦的魔幻文本开启并实现了当代西藏文学的一场革命。其奇幻妙绝,又真实可信的叙事方法颠覆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僵化模式,促成了藏文学观念更新,为藏文学发展开拓了新的路径,注入了新的活力。其魔幻神韵的陌生化功能构建了新的阅读视野,形成了不凡的审美穿透力;其怪诞、变形的表象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扎西达瓦的魔幻叙事标志着西藏小说艺术的进步。它促进了西藏文学的繁荣与多样化,同时对强化西藏文学独有的民族性也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扎西达瓦的魔幻作品成为了西藏文学中的一株奇葩,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也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杰出成就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王达敏指出:“新时期作家中,扎西达娃最得魔幻现实主义的真谛。他的小说被称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西藏,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小说中,我们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许多典型艺术表现方法在这里汇集。”(6)(P131)刘曾文写道:扎西达娃的作品“糅合了藏密的神性和现实的人性、混杂了民族历史与当下现实的隐秘时空。…给作品注入了真正属于本民族的深刻的西藏意识。”(7) (P60)王绯也评论说:“扎西达娃施展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几乎所有的艺术招法。在许多篇章里,都能感觉到马尔克斯或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的活泼影子”(8)(P378)
扎西达瓦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在当代中国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九十年代后,扎西达瓦式形式激进的魔幻小说完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革新的开拓者使命,逐渐淡出了中国文坛。但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文学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学,并以各种形态继续开花结果。可以断言,扎西达瓦的流风余韵必然以不凡的生命力,在今后持续不断地为文学后来者提供启迪、灵感与想象力。
参考文献:
(1)柳鸣九,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M〕花城出版社,1986年。
(3)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文学,〔M〕海南出版社,1993年。
(4)马丽华,扎西达瓦及其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2)。
(5)扎西达瓦,西藏,隐秘岁月,〔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
(6)王达敏,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性描写,〔J〕文艺评论,1997(5)。
(7)刘曾文,终极的孤寂,〔J〕文艺理论研究,1997(1)。
(8)王绯,魔幻与荒诞攥在扎西达瓦手心的西藏之西藏,隐秘岁月,〔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