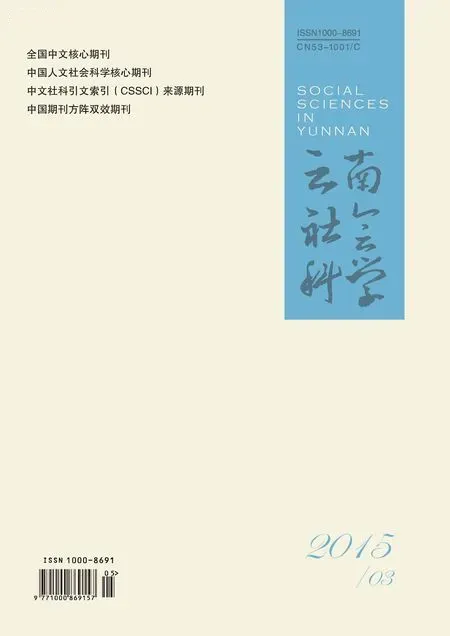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才培养制度述论(1928-1949)
2015-02-13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1948年迁往台湾,在中国大陆的20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镇,是20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人文研究机构。史语所不仅以其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享誉大陆、港澳台乃至国际学界,更为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①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何兹全序,第1页。史语所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与其成熟、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是分不开的。笔者拟在梳理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史语所档案》《傅斯年档案》等相关资料基础上,对史语所的人才培养制度作初步的考察,以发掘其中有益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人才培养的制度因素。
一、用人唯才
在史语所筹备期间,作为常务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就意识到培养后备人才的重要性。1928年5月,傅氏草拟史语所组织大纲上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其中一条“本所得设置研究生,无定额,以训练成历史学及语言学范围内共为工作之人,而谋集众工作之方便以成此等学科之进步”②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补1-2。。9月,史语所筹备完成,在颁布的章程中规定“任用助理员若干人”“设置研究生”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办事处,1928年,第34-35页。,这为聘用和培养年轻人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1928年度工作报告中,史语所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215页。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史语所是由研究人员组成,以研究工作为中心的学术机构,成立后百业待兴,未能把研究生培养工作提上日程,至1931年所务会议中才提出试设研究生办法。同年7月,在安阳殷墟实习的河南大学毕业生石璋如、刘燿(即尹达)入所为研究生,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每月津贴50元。但研究生的培养并不顺利,傅斯年谓“数年中,颇思在研究所中大招研究生,终以各种不便,未能实现,初招四名,未到所而战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起矣”①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1275。。新学术的开拓不仅需要前瞻者的登高一呼,还需后继者沿着大师指明的方向不懈努力,才能积累丰硕的成果,将新学术发扬光大,因而需要不断延揽年轻人入所。傅斯年主张“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②傅斯年:《傅斯年致蒋梦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1页。,因此,国立、私立大学文史等学科的优秀毕业生成为史语所争取的对象。
史语所汲引人才,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是由史语所新学术的开拓者们推荐优秀人才。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期间,为史语所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后备人才,如劳干、高去寻、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等。当时在各大学兼课的陈寅恪、陈垣、胡适、徐中舒等,也为史语所推荐了众多优秀人才。如陈寅恪推荐了青年才俊像于道泉、周一良等。即使在时局动荡的1948年,陈寅恪还写信给代理所长夏鼐,推荐新人。③此信中说:“作铭兄左右,周一良兄转来手示,甚感。程君(即北京大学毕业生程曦)履历附上,请于最近开院务会议时,提出通过后即求速示,并通告驻平办事处余(余逊)、陈(陈钝)诸君,如开会时需要推荐书,即请兄代弟拟就。”参见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京28-30-4。陈垣推荐陈述等人入所,胡适推荐丁声树,徐中舒推荐李广涛,李济推荐吴金鼎、李景聃等。被推荐的年轻人以后皆成长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说明推荐人在引进人才时还是坚持了很高的学术标准,称得上知人善任。
新学术的开拓者们推荐了众多人才,但史语所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如1933年,陈寅恪极力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傅氏却批示:“此事现在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然北大已竭力聘请之矣。”④陈寅恪:《致傅斯年》,《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7页。没有聘请张氏,经费固然是一面,在傅斯年回绝杨向奎重入史语所的信中兴许能找到部分理由,傅申明史语所提倡“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故近十年中,未曾增添治古史者一人”,接着说“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为本所之学风也”。⑤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148。无疑,张氏学哲学,讲博洽贯通的学术风格与史语所重史料、讲专精断代研究的学风不符,才是被拒的真正原因。⑥另有1934年,已成名的学者吴廷燮,由罗文干、汪精卫、蔡元培作为介绍人欲入史语所,但傅斯年认为其不具备“新观念”和“新工具”,“彼之所习仍为掌故一派之学问”,最终被拒。参见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78。
其二是考试录用。史语所倡导新学风,“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招考能够从事新学术青年人才。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史语所预先在南京、上海、北平等报纸上登载招聘信息,并在南京、北平等处分设考场,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吴宗济讲“一九三五年夏天,我见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招考助理员的广告,就抱着试试看的希望去报考,竟被录取了”⑦吴宗济:《我对史语所的回忆》,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史语所,1998年,第606页。。所中档案有一份关于招考助理员的通告,其中对学科、学历、证书等要求明确,规定严格,招考程序完整。为选拔出优秀的人才,采取宁缺毋滥的原则,“无合格者不取”。⑧参见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241-10。吴宗济回忆1935年史语所只招收一名助理员,却在宁、沪、平(北平)和汉口四个城市都登了报,设了四个考场,最后吴被录取。吴宗济:《我对史语所的回忆》,《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606页。若发现了优秀人才,史语所便打破成例而多录取,如1936年计划招考一名语言学助理员,因董同和与周祖谟两人非常优秀,傅斯年和赵元任商量的结果是皆被录取。通过考试入所的吴宗济、葛毅卿、吴汝康、董同和与周祖谟等人终成大器。
史语所用人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以新进者的才气与潜在学术能力为标准。1937年所务会议决定聘无学历、资质,靠自学成才但“著作精辟”的岑仲勉为专任研究员。而藉重党国要人如汪精卫、丁惟汾、褚民谊、居正等请托介绍者,皆被傅斯年拒之于门外。傅斯年的老校长、院长蔡元培经常向史语所荐人,皆被傅回绝。⑨蔡元培介绍如蔡哲夫(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89)、钟凤年(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110)、藤固(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776)、毛汶(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777)、吴廷燮(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78)等人史语所均被傅斯年回绝。毛遂自荐的严耕望,以著作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嘉许而入史语所。傅斯年致信董作宾:“今年请求入所之人,甚多。凡无著作者,弟皆谢绝了,其有著作者,现有三人,兹将其著作分打邮包寄上。其中严耕望一人似是一难得之人才……兄(董作宾)召集所务会议讨论,严耕望之工作为弟之提议,惟一切均请会中决定。”①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杂23-13-8。可见,傅斯年虽是一所之长,也不是独断专行,用人还得遵守制度,由所务会议决定。
二、严格管理,督促学问
年轻人的成长关系所中学术的未来,因而史语所非常重视对他们的管理与培养。傅斯年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管理、监督,要求他们对待研究工作具有心无旁骛和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经常有人因工作懈怠而遭受批评甚至处罚,如助理员黎光明在图书室中会客,“大防害他人工作不言可喻荒谬如此”,加上“黎君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呈请院长记大过一次。②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115-9、元115-10。所内不许研究人员在外兼职,吴宗济在昆明时因在所外担任《西南边疆》的经理兼责编,“被所里领导找去,要我放弃别干,理由是‘你既吃语言所的饭,就不许干别的’”③苏金智:《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吴宗济序,第9页。。吴虽未言明领导是谁,但在史语所有此霸气的只有傅斯年了。
傅斯年不时敲打、打磨年轻人。在四川李庄,一天“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他(傅斯年)请同屋的别位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只是不让某君出门,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称傅为“胖猫”,说“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④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台北),1951年第2卷1期。当然对年轻人的工作不只是督责亦有奖励,如1936年的一次所务会议议决,周祖谟、张政烺、傅乐焕等因在上年度“成绩优异,工作特勤,多于夜间加工赶成其著作”,“拟分别给予奖金(40至100元不等),以资鼓励”。⑤《中研院史语所人员任免迁调考绩薪给文书》,中央研究院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1675(1)。
另一方面是指导、督促学业。史语所要求新人入所后要“闭门读书”⑥全汉升:《回首来时路》,《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493页。,“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⑦王叔岷:《慕庐忆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页。。于道泉在法国认真读书未做文章,傅斯年去信称“知兄以未作文为虑,此则不必,送你去是留学,不是作文”,后又认为于在法学西藏文等科“实无多可学”,又写信提醒他“多知目录,领会语言学一般方法”。⑧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62-21、元62-34。傅斯年、陈寅恪和顾颉刚等皆主张专精的断代史研究,更是严格要求年轻人如此治学。钱穆提到“凡北大历史系毕业之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王崇武)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傅斯年)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
研究指导也因人而异。助理员黎光明政治兴趣较浓,傅斯年给赴川康地区调查民俗的黎氏写信,嘱咐“少发生政治兴味”“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千万不要在成都一带交际”,而要“细心观察”“多自己耐苦”。⑩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115-20-10。杨成志在“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傅在致杨氏的信中告诫不可自满:“若因此自负,则既与本所任执事之意不合,并恐于执事学业前途不无影响。一种专门学问,必须有严整之训练,方可取得可靠之成绩。执事上年之行,只可认为试作,如以为学业便是如此,自己已可负独立之责任,则非鄙所同仁所敢知矣。”⑪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64-11。
三、研究指导实行“师徒制”
中央研究院章程中对助理员的资格要求必须是国立、私立或国外大学本科毕业,且须对所习科目有相当研究并有成绩者。但大部分毕业生入所后还是面临研究能力不够、针对性不强、问题意识薄弱等问题,因而要求“助理员除辅助研究员研究工作之进行外得受研究员之指导自作研究”⑫《国立中央研究院设置助理员章程》,《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第10页。。上述规定为史语所实行师徒制提供了制度依据。
史语所的“师徒制”是指师生结对,助理员帮助老师借书,搜集文献,校正、核对资料,研究员指导助理员,为其研究把握方向,指导方法,培养技能。初始,有一定成绩的年轻人并不认同此制,傅斯年强调施行的原因:“助理员之成就,在其受专门之训练而能于将来独立研究。故在助理员任内,必须虚心勤勉从事,而避去一切浮动不实之趋向及新闻式之工作,及类于此者”①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64-11。。
因傅斯年等人的坚持,史语所的“师徒制”得以坚持下来。在所档以及学人的回忆录中均有提及,如历史组助理员的论文由专任研究员予以指导,傅斯年指导陈槃治《春秋》三传和李晋华治明史;傅斯年和陈寅恪指导俞大纲治唐史;②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779。语言组助理员马学良跟随李方桂治少数民族语言;考古组助理员张秉权随董作宾研习甲骨学。
“师徒制”的意义在于前辈学者能以其学力、经验与视野,指示后学者研究路径的选择,方法的指导和技能的培养,使得后学者能够快速成长。马学良回忆李方桂“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达到一丝不苟的地步,对学生要求极严。他善于启发,长于引导,极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对任何问题都要你先思考,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再解释说明,提出自己的见解”③马学良:《历史的足音》,《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69页。。
张秉权初学甲骨文时,对董作宾让其先读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非常不解,“后来,读过很多书以后,才领悟到董先生的选择,最适合于初学的人”④张秉权:《学习甲骨文的日子》,《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923页。,因郭书分类编排,条理清楚,初学的人读其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史语所迁往台湾后,“师徒制”传统得以延续,台湾学者陈昭容说:“这种‘师徒制’其实正是史语所久来的传统。”⑤李孝定口述,陈昭容记录:《我与史语所》,《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922页。许倬云在回忆录中亦肯定了史语所师徒制的积极意义,1956年许台湾大学硕士毕业入史语所为助理研究员,随陈槃、劳干和严耕望等研习上古史,“当年史语所老先生对我们满严的,但是我很感激!……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得先跟老前辈工作,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135页。)
四、定期的讲论会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现代的学术研究“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味,集众的工作渐渐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新学术的开创者们主张现代学术研究不同于个体、封闭的旧读书人,须脱离个人“孤立的制作”,强调现代学术研究的“集众”特点。⑦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410页。
为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便于“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史语所举办了定期的讲论会。讲论会开始先由主讲人报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后由同仁就观点、方法和材料等提出商榷意见,进行讨论。⑧周一良回忆:“有一次会上讨论中,傅先生对张政烺说:‘你是最critical的,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参见周一良的《史语所一年》,《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57页。王利器回忆史语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斯年)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遂遵命作了《‘家’、‘人’对文解》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好评”⑨王利器:《李庄忆旧》,《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797页。。夏鼐的日记也多有记载,如1944年1月29日王崇武讲演《明成祖靖难问题》,2月7 日高晓梅讲演《淮式铜镜之研究》。⑩夏鼐:《夏鼐日记》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5、157页。所档中亦保存着1936年上半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讲论会本学期次序表”⑪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232-8。。
讲论会方便了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论辩弥补了学人观点、方法和材料的不足,更激发出很多新观点,开阔了学人的视野,给年轻人淬炼学术提供了宝贵机会,促进了他们快速成长。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即入史语所的陈述向傅斯年报告研究心得,半年来“多聆教诲,兼得诸同事讲习。略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多重历史问题。并略知作文有高低之分,如论证确实,独有创见,假定名为教授类;如略具考订比列而成,假定名为助教类;如抄缀辑录,勘对字句,假定名为学生类”⑫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230。。陈述治学从“以书为本位”“考订比列”的补旧史之作向“重历史问题”“论证确实,独有创见”的研究论文的转变,无疑受学术环境影响所致。
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年轻人成长至关重要。李济谈到这种学术辩难的好处:“近代的学术工作大半都是集体的,每一件有益思想的发展,固然靠天才的领悟和推动,更要紧的是集体合作的实验、找证据、以及复勘。只有在这类的气氛中,现代学术才有扎根生苗的希望。”①李济:《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112页。抗战时在三台东北大学主持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金毓黻,给傅斯年写信,透露出一个研究者无书、无友的尴尬境况,因而向史语所借调陈述,“弟正苦研史颇乏良友,兹得陈君(陈述)之助,为之生色不少。我兄援手之惠,至可感也。此间地僻,颇便读书,只书少为之一病,他皆称心。古人云:恨不十年读书,兹可谓专心读书矣,不识何以教我”②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407。。
1945年,奠定董作宾学术地位的《殷历谱》出版。傅斯年为之作序,“吾见彦堂(董作宾)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倍感孤诣之苦”,因而常“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周围的朋友“知此,亦常无义而与之强辩以破寂焉”。③董作宾:《殷历谱》,史语所1945年版,傅斯年序,第2页。相互辩难的结果是大家得到学问的刺激与兴趣,正是这种辩论激发出董作宾“点”“线”“段”的方法论,不断修改完善其著作,造就了《殷历谱》的不朽。
五、学术上的高标准要求
傅斯年最初对史语所的设想是半实体化的。当时把研究员的地位设计得很高,大概等于院士,必须是各学科中的全国代表人物。④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南方都市报》2012年9月2日,第18版。1928年5月,史语所还在筹备期间,傅斯年向院长蔡元培上呈组织大纲,其中规定研究员:“须于历史学或语言学范围内各科之一有超异之贡献,为同科学者所承认,并现在仍以继续作该科之研究为业者。”⑤史语所档案:补1-2。显然傅斯年的标准过高,不得不修改原先的设想,但还是尽其所能聘请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历史学(陈寅恪等)、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考古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和民族学(凌纯声、吴定良)等各学科人才,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学术团队。
这支团队认为“无论治何种学问,都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⑥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0页。。因此,他们处处以现代西方的学术标准为范本来建设新学术,傅斯年谓“求此研究所在标准、训练、工作效能上,能适用欧洲之标准”⑦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考2-34。。在此标准下研究学术,超越西方汉学,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们相信新学术标准的建设与成就的取得“关系于国家前途者不少也”,如果开始就“建立一个较高的标准,各大学不得不奔从;若成一种讨论讲演之环境,不患不成风气”。⑧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210。
史语所的高标准处处有所体现,如在晋升上添设了练习助理员。丁文江、傅斯年、李济等人发现大学毕业生直接任用为助理员,大多面临知识储备不充分,研究能力不够的问题。于是,李济写信给傅斯年,讨论在院中助理员之前再设练习助理员一职,“此后大学新毕业之学生,应概以‘研究生’(练习助理员以研究生相称)待遇,津贴不妨略加,助理员之名义,留于大学毕业后之稍有经验者”⑨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17-4。。于是史语所在助理员之前亦添设了练习助理员。
随着人才的积聚,各项学术工作走向正规,史语所的招聘条件越来越高,更看重其专业水平和研究成果。1936年招考语言学组助理员的条件规定:“报考练习助理员者,须在大学或大学相当之专门学校毕业,对于审音特别专长或具有汉语、方言知识者。报考助理员除上述资格外,须曾在学术机关服务二年,并须有专门著作。”⑩史语所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元241-10。
1941年,史语所依据院章修正章程,在助理员与副研究员之间设置助理研究员。而后所务会议决议,在晋升资格上要求助理研究员的著作须有“德国大学之Habilitation之标准”。又因新任的助理研究员仅以大学之硕士论文及年限规定为准,所务会议认为规定“似嫌太泛”,决议新任助理研究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一)凡在大学有硕士学位,入所仍须为助理员,须于一年内完成论文一篇,合于组织通则第一条之规定,方能升为助理研究员。(二)凡在大学毕业后研究有年,著有优异论文,本所拟为助理研究员时,应预由所务会议审查,审查其资格是否合于组织通则第十一条之规定。①《中央研究院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年部分所务会议记录及其他杂项文件》,中央研究院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60。
从助理研究员升任副研究员,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同样严格。即使从伦敦大学埃及考学专业毕业回国的夏鼐博士也仅任副研究员,且“须缴纳论文”经所务会议审查合格后,才加以聘任。②夏鼐提交所务会议的论文是《古代埃及串珠》,参见《夏鼐日记》第3卷,第119页。周法高回忆所中的一次晋升,傅孟真(斯年)所长兼一组主任,要升第一组的助理研究员张苑峰(政烺)为副研究员。二组的董同和已完成了其成名作《上古音韵表稿》和论文《广韵重纽试释》,李方桂便提名他升任二组副研究员。三组主任李济之(济)也提名高晓梅(去寻)为三组副研究员,但傅斯年不同意三个人同时升副研究员,不得已“所长和主任连开了两三天的会都僵持不下,结果还是所长让步,史无前例地通过了三个人同时升副研究员”③周法高:《忆李方桂先生》,《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52-253页。。
历史组张政烺升任副研究员,同年入所的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却没能晋升。傅在致所务会议信中讲“傅乐焕君著作见《集刊》,此外未刊者尚多”,已刊的文章“堪称为重要之贡献”,按入所年限已够六年,可以评副研究员了。但在史语所能按年限顺利评上副研究员仅有语言组的丁声树一例,况且在历史组傅乐焕的学力,“非可比张君者(张政烺)”,“故今年不拟审查”傅乐焕评职称事。④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V:52。
另外,史语所对研究论文和著作出版的标准高而严格,须是积年研究所得,能经得起同行专家和时间的考验。马学良回忆,史语所“不太重视论文著作的数量,重视科研成果对本专业或本学科的创新和贡献。如丁声树先生学贯中西,当时他的著述虽不多,但每篇论文都能发前人所未发,有一鸣惊人的卓识高见,不仅为国内外学者专家所赏识,同辈学人也莫不佩服”⑤马学良:《历史的足音》,《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864-865页。研究道教的王明很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还说到“史语所研究人员很少,精兵简政,闭门著作,不轻易发表文章,登载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论文,往往引人注目。”参见王明:《王明自传》,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102页。。于道泉曾经想编一部藏汉佛教词典,但是傅斯年和陈寅恪都不同意,傅、陈认为“史语所出版的书,必须要有一定的水平”⑥王邦维:《于道泉先生小记》,《新学术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61页。,而编藏汉佛教词典,不仅要精通藏文和佛教,还要精通印度的梵文,而于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岑仲勉入史语所后,凭借优越的学术条件,阅读了大量的图书,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拓展了自己的研究。在所内工作的10年时间,是岑“做学问最努力的十年”,岑自入所后仅在《集刊》上就发表了41篇文章,出版了《元和姓纂四校记》等著作多种。如此优渥的研究环境,岑却在1948年7月辞职。从傅斯年与岑仲勉及傅与代理所长夏鼐的信中可知岑辞职的原因,傅斯年希望岑的研究领域能以史学为限,注重专精,而不要涉及其不擅长的语言学,但岑坚持己见,史语所认为其“不顾忠告,固执己见,乱发表文章,损及所方声誉”⑦傅斯年档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III:533。,考虑到人情,最终由陈槃出面劝其辞职。⑧牟润孙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感言》中对岑仲勉辞职事亦有记载:至于聘用人员,他(傅斯年)是非常严格,没有丝毫的徇情。岑仲勉他从来不认识,陈援庵先生看见岑的文章以为极难得,推荐给傅先生,傅先生也觉得好,便聘为研究员。岑到史语所果然作出了不少成绩,后来因为岑先生兴趣过泛,研究的方面太广,有时难免犯了错误。傅先生劝他少写,岑不肯听,终于胜利后不久离去。参见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7页。
六、余 论
史语所的开拓者对“少年学者”的吸纳与培养,使得史语所开创的新学术典范薪火相传,不断被发扬光大。史语所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史语所形成规范、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关系重大,从进人以新进者的才气与潜在学术能力为标准,至入所后施以严格的管理与督促,在研究上师生结对,由专任研究员指导入所不久的年轻研究人员,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所内举办定期的学术讲论会,在职称和研究著作上的高水平要求,并终成一代典章。史语所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体现了成建制的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上文对1928-1949史语所的人才培养制度略作申论,直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国学术精英如何经营与培养年轻研究人员,其成功与弊端,都将给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