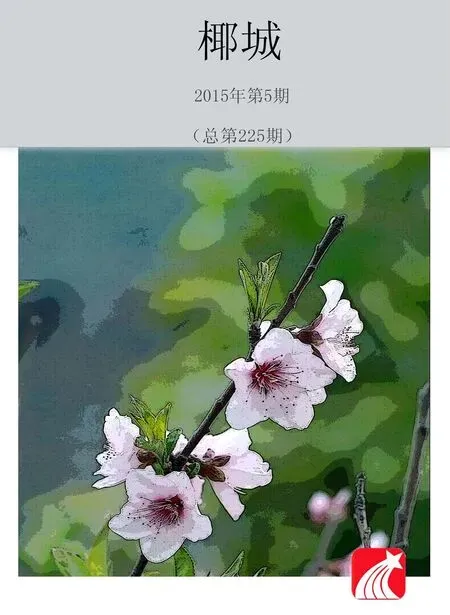散文二题
2015-02-13余芝灵
■余芝灵
散文二题
■余芝灵

日记
闲来无事,看旧日记。这已是二十年前甚至更早些年的记录。墨迹仍在,纸已发黄。
记得刚记日记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六安读中专时开始。也不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反正那时候就开始记了。或许青春伊始,是需要一些可以留存下来的影像吧;也或许只是年少时,一些心事,需要对自己诉说。当然,另一个隐秘的原因,应该是希望将来自己能写一点东西。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几乎所有的青春期的男生女生,都有一个诗人梦,或作家梦。现在想来何其幼稚,那不过是初中三年写的一些小文章,屡被语文老师好评,而催发了那个隐秘的梦罢了。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充其量不过是业余作者罢了。
记日记的习惯就这样保持了下来。中专三年无所谓秘密,并无暗恋谁,应该也没被谁暗恋。虽时有一些小小心事,也不过静水微澜,日记却从未断绝,几乎每日一篇。有心事写心事,有见闻写见闻,有感悟写感悟。什么都没有时,就写天气,写心情,写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其实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写,不过练笔与习惯而已。
及至毕业分到单位,也仍在记着。这时候的心事,开始多了忧伤与焦虑。刚出校门,一个人要开始顶天立地地在风雨里行走,再没有学校那道围墙可以保护我们脆弱的身躯了,多少有些恐惧。加之,一日三餐也是问题。单位没有食堂,要么在别的单位借吃,要么自己买炊具煮。先是在县人武部吃了一段,后来又在县委党校吃了一段。总是没有油水,总是感觉肚子里空,巨大的空,能吃一头大象的样子。也间或地自己烧点东西吃。买了个煤油炉子,无奈从小娇生惯养,烧什么不像什么。我那时脸色极差,幸而有了青春作底子,不然,真像朵秋日黄花。
有一日,与同屋女友去看电影,中途突然停电,在跟着人胡乱奔跑的当儿,没有注意到刚刚新挖的下水道,失足掉了下去,跌破嘴唇。幸亏女友有一颗善良的心,当即跟我一起去县医院缝合。记得是夏天,上衣上全是血。不单是跌破了嘴唇,牙齿也跌得稀里哗啦的,许多粒都是活动的。缝合后起码有十几日,不能吃东西,只能略略喝点流质的,比如罐头、汤呀什么的。我能吃什么?无非是天天光顾烧饼摊,每餐买一块大烧饼,回来用开水泡了吃。有位年长的女同事,见我实在可怜,煮了一碗山芋糊糊给我。我当时真是涕泪交集。缝合后的疼痛与不能吃东西,并不十分让我难过,难过的是:我已十八岁了,突然一夜之间破了相,将来可能找不到婆家了。那真是实实在在的忧虑。那是我整个青春时期最为苦闷的一段。如今想来,觉得实属多余。那一段的日记,多愁闷之音,缓慢低沉,凄凄切切,都有一点李清照晚年所作词的调子。破了的嘴唇很快就长拢了,却不可能再长回原来的样子,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于是,我和我的日记一直忧伤着。感叹着岁月漫长,也担心着可能这一世找不到自己的白马王子,那么就只能一个人孤单地过一辈子了。这么丑陋,谁会看上我,谁会完全不在意我的缺陷?况且,同事们只要一见我,就开着类似的玩笑:本来长得齐整不过的一个小姑娘,突然就破了相,怕是将来要找不着婆家了呀。他们带说带笑,我是又羞又恼。这段时期的心路历程,都忠实地作了记载。许多年后的今天再去翻阅,恍然有隔世之感。
还好,十九岁时遇上了他,我一生中命定的人,是我新调一个单位的同事。一开始是互相借书看,后来知道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就交换日记。我们是晚上各自写好日记,白天上班了彼此交换着看。看完,又还回彼此。那真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每天都为等日记等得无比忧心。当然主要是晚上,等得睡不着:不晓得他日记里又记了些什么?想看,想看,想看,想立即看。还要等到白天,太难熬了。是谁,是谁日夜敲打我窗,是谁的马蹄声日夜响在我走着的路上?这样的等待,让一个个夜晚变得扑朔迷离,让满天的星星格外的璀璨,让所有哑默着的石头也开口说话。这样的忧伤何其漫长,要等到几时是头?我又何曾希望它有个头。就这么下去吧,永远就这么下去。起初是他记他的,我记我的。无非是各自对所读书籍的感悟,对每日里所见所闻的感触。后来干脆我们的日记本子合并成一本。我们在同一个本子上记日记。这比先前的日子更难熬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把对方当作另一个自己了。我们把原先只对自己说的话,悉数说给对方,好像就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诉说,所有的,所有的想说的。越说下去,我们就越离不开了。日记写着写着,一写就是几个月,就是几年,直到儿子出生以后,我们还共同记了一段。不晓得是从哪一日起,日记就开始中断了。先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后来,连我也不记了,日记从此搁浅了,束之高阁。这是指我们共同的日记。我私人的日记,断断续续地还是记了几年,但很残缺。已不成其为日记了。或可曰:月记,甚至年记。就这样,我的日记生涯,一不小心,就走向了断桥,掉到了时间的深渊里。
日记虽然没有顺着年限记下来,但以前写过的日记本子,数了数大约有二十本之多。这也够出一本“巨著”了。精致的本子没有几本,都是些比较简单粗放的、没有特别精心的设计,但都是我精心挑选来的。许多年过去,我一直爱着这些日记本的颜色与气息。那里面,藏着我最美丽的时光,最璀璨的梦想与最年轻时候的娇憨与痴缠。以至于后来真的开始写一点东西,我还是愿意在纸上写,而不是在电脑上,皆因数年来养成的记日记的习惯。当然,最终我抛弃了在纸上写东西。如今,我已完全不记日记了。有什么心思,有什么感悟,我都在微博上、手机微信上、Q Q空间里,乱扯一通,这既没有私密性,亦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更没有留在纸张上的文字的那种袅袅的气息。
而这些日记本,将一直陪我,陪到地老天荒。假使时光能够倒流,我还是愿意回到用心记日记的年岁,那样的时候,天多蓝,鸟声多纯净,空气多清新,水多澄澈,而人心——又多么简单。
清气
日复一日跌坐于浊重的尘埃。何谈清气?然而,于浊重的尘埃之中,想得最多的二字仍然是:清气。真正认识到清气二字的意思,大约在满了四十岁以后。清气原是指干净清爽,心无尘埃。脸上干净,心上干净,身上有自然的清香,一双眼睛清澈透亮,不染俗世风尘。与身材无关,长相无关,更与身世无关。
每一个人大约小的时候,都是清气的。一开始就长得满身泥污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即使长得再丑陋的人,生来也干净清爽。我小的时候,大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像一株栀子,沐风栉雨,在大自然中摇曳。浑身散发着山野的气息、流水的气息、露珠的气息,没有受到过世俗的污染。而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大约我的清气已荡然无存,满身满心,都是俗世的烟火,每一条血脉里都浸透着尘灰与油泥——人走着走着,就慢慢地将清气弄丢了。弄丢了,再找回来,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去寻找。如果寻找与不寻找的人之间有一场对话,那么不想寻找的人,简直要将寻找的人笑死。那也真不过是一种徒然。完全的修复,是不可能的了。已经是一棵被移栽过多次的植物,怎么可能回到生命的最初,你怎么可能再找回自己的源头?
是这样么?看看那些从村庄里走出去的人,有几人会年年岁岁回到故土?有几人在夜半更深时还惦记着老家漏风漏雨的泥土屋?有几人还记得那松子从树梢上轻轻落下的声响,如亘古不变的时光?有几人还在念着溪水的清凉与甘甜?更记不得那麦子,与麦子的香味。他们的清气,在来时的路上,已慢慢消失殆尽。他们挽着异乡的月色,走在异乡的街头,在异乡的气息中,日复一日地成长,长成参天大树,却再也不认识回家的路。
看看那些在菜市场游动的人群吧,哪一个脸上不写着焦虑、俗气,甚至愤怒?清气在日复一日的烟火中,在不停地与小贩们讨价还价中,被熏得面目全非。柴米油盐,本就是打仗的。为着一张嘴,得日日里与他人争斗。争斗来争斗去,争斗得自己清气全无。
看看那些不断凸起的肚腩吧。那里面都装着世道人情,甜酸苦辣,久而久之,一切都看淡了,一切笑纳。你能否想象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满身清气?
再看看泥沙俱下的文坛。有多少篇文字,是真的蕴含着清气的?而在文字的背后,又有多少张脸,多少颗心,是真正干净,没有功利之心的?写诗写文的人千千万万,真正饱含清气能让人记住的诗文有几篇有几首?是的,如今的风,如今的雨,都没有清净之气了。总是霾,总是混沌不清。
城市的道路上,散不去的汽车尾气。城市的上空,看不见一轮完整清晰的月亮。城市的周围,没有一整块青山,更没有一大池碧水,全都是拔地而起的水泥森林,连呼吸到的空气也没有几缕是清新的,连鸟鸣也带着浊重的掘土机的声音。
总说修心。说“心远地自偏”,说“大隐隐于市”。说这些时,你会不自然地微笑。你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冒着浊气。你的生活被切割。你的阳光被抢夺。你在午夜里听到高楼上人家的狗吠。在凌晨,听到年轻的小夫妻摔碗摔盘,尖声喊叫。你总感觉到是住在一条风雨飘摇的舟子里。你能以一颗清净无尘的心,看待这一切么?你能想象到你的源头之上,那飞珠溅玉的清泉么?
但是,寻找与不寻找是不一样的,执著寻找,总能找回一些清气的,不寻找,就永远丢了。你明白这点,你热爱这浊世。你热爱在这浊世里滚爬的感觉,但你竭力地想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要保持一份自己。你总是想要让自己能有一窗飘香的月色,一泓洗涤灵魂的溪水。你一边在浊世里滚爬,一边在幻境的世界里寻觅,纵然是不能找回,但寻找清气的过程与寻找的坚持,其实就是清气的一种,所以,日子虽然也基本是就这么过去,但终归并不就这么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