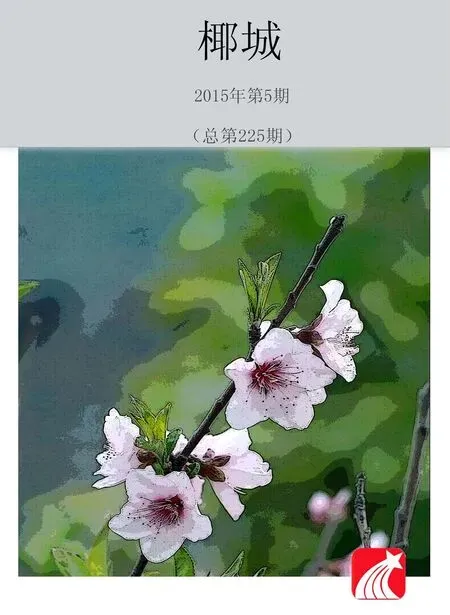梦·醒
2015-11-17宁亮
■宁亮
梦·醒
■宁亮
火车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咚咚”声把我从沉重的思绪中拯救出来,我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梦魇,睡多久了?我似乎患上了白内障,眼前的一切变得模模糊糊,脑袋又像是裹了一层布,始终被一种莫名的疼痛包围。
我的思想像一块冰那样在慢慢地解冻,苏醒的过程是痛苦的,像有一万根针在皮肉里来回进出,做拉锯状。我终于记起这次回老家其实是去奔丧,就在昨天,我外公在我众多姨妈和舅舅的呼唤声中再也没醒过来,临走时他大叫了一声,嘴巴就永远停住了,成了O型,像是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叹。
临走时我把买好的空心菜、干辣椒和肉放在案板上,我知道老四川会很感动,眼泪会顺着他皱巴巴的脸颊流到下巴上。他擦干眼泪后会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感叹般说道,这娃儿!
小刀离开我们后,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寄居,有点相依为命的味道。我给老四川写了一张纸条:“有急事回家!”他看到后会马上给我打电话,我时常会为他的关怀感到不知所措。
对于外公的去世,我还没感到一丝难过,也没来得及掉一滴眼泪。人老了,终归是要死的。这一点我看得很透。我甚至觉得这次的旅程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我外公已经病重很久了,他脑袋里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连医院也放弃了在他身上挣钱的机会,让他回家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我外公是个勇敢的人,他甚至不停地向身边的人追问:“我究竟什么时候能死呢?”他焦躁不安的情绪让人感觉他是在等一所知名大学的通知书,而不是在等死。
这座城市总是让人烦躁不安,高架、地铁以及横纵分布的道路像蜘蛛网一样呈现在你面前,你不得不一会儿变成一只掘地的鼹鼠,一会儿变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犀牛……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脑袋里像长出了一团乱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座城市寄居,它早已被许多人说得一无是处。
“火车站是一座城市最乱的地方。”老四川曾对我说:“三教九流都在这里混,你不要在火车站买任何东西,甚至连跟他们说话,都不要。”他总是像教育孩子那样跟我说话。
火车站病怏怏的,沉重的钢铁脚手架已把整个车站变得面目全非,很多人走到老的进站口才发现进错了地方,于是骂骂咧咧地往回走,沉重的行李让他们疲惫不堪,最后他们连骂的力气也没有了,只能乖乖地跟着人流往前走。好在我的行李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书,我根本没打算在家里常住。
半空中的站台通道是临时搭建的,铁板是悬空的,踩在上面咣咣地响。我忽然感觉自己的胸腔好像变薄了,心脏快要从里面蹦出来,我莫名地感到一阵痛楚,像有一把尖刀忽然向我胸口扎过来,我真怕自己会突然心肌梗塞,客死异乡,此刻,我是那么地想我的老家,我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
还好,这次我买的是下铺,卧铺车厢里不是十分干净,但比其他车厢要好些,至少不会有民工脱了袜子把脚放在你座位上的情形,我仔细地把铺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像头发之类的脏物,然后把被子叠好,枕头压在上面,半个身子倚了上去,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后,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火车要开了,乘务员不停地吹着哨子,陆续还有上来的乘客,外面天色暗了下来,夕阳懒懒的,像我老家在村前漫步的鸭子,我心里猛地难受起来,胃里的苦水像泉眼那样翻滚着,我的身体像阳光下的冰块那样开始解冻。
我对面是一个年轻人,脸很瘦,一搭眼,我就看出他的异样,他嘴唇发紫,两腮下陷,眼球狠狠地向外凸着,他行李不多,只有一个帆布包,我上车时就注意他了,我敢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无非是两种:吸毒者或是通缉犯。
我想此次旅程注定我是要提心吊胆的了,不管他是二者中的哪一个,我的生命都堪忧。他向我这边看过来了,他的目光像是电力不足的手电,距离我还有一半的时候就散掉了,生命的迹象在他身上很弱,我感到潮湿和阴冷。
果然,他很快就躺在床上开始抽搐起来,也许这不是他的第一次抽搐,他用树枝一样干巴巴的手死死地抵住下巴,一些白色的泡沫顺着他的手指缝儿流了出来,他的眼睑很薄,好像再一用力,眼球就会从里面掉出来,我站起来,冲着车厢的两边各喊了一声:警察!
几个乘务员手忙脚乱地把他抬走了,不大一会儿,广播里列车长在焦急地询问有没有医生,从列车长的口气里我感觉到,他必定是凶多吉少。
我拿起一本书挡住了我的脸,我想尽力忘掉这一切。这是一本关于命相的书,在翻修老屋时,一个瓦工在外公家房梁上发现了它,不久后这个瓦工不小心用瓦刀砍断了自己的一截手指。
这本书落在我二舅手里,起初我二舅以为这本书里藏了什么秘密,并贴身研读了它三年,后来他在一次车祸中身体被压成了两截,我外婆认为这本书是不祥之物,便把它放在床下面的一个雕花的樟木柜子中。
车开的方向应该是正北,我却偏偏以为是往南开,我时常在旅途中迷失方向,也许一会儿查票员会告诉我坐错了火车,那样也好,我似乎并不在意这次旅程的目的地,毕竟我是奔着悲伤而来。
火车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后悄悄地行驶着。我很疲倦了,眼皮耷拉着望向窗外,高压线横架在铁塔上从一片片稻田里穿过,铁塔上有不少鸟巢,正是稻子开花的季节,稻花的香气从火车车窗的缝隙里溜了进来,越聚越浓,这味道浓得像酒,稻花香酒是这里的特产,我感到一阵眩晕。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错觉,香味另有所踪,我歪头一看,果然,一个女孩拖着箱子“咕噜咕噜”地走过来,她低头看看手里刚补的票,又看了一下铺位上的号码,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娇小而精致的胸和翘起的臀恰恰是我欣赏的那种,当她向我投以求助的目光时,我愉快地起身将她的箱子放到行李架上。
“谢谢!”她的声音很柔和,只是有点沙哑。
“不客气!”我对她说。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声音太过粗犷。她优雅地坐在我的铺位上弯腰解着鞋带,我偷偷挪开书本看见她露出一截美丽的椎骨,她很瘦。我又望一眼窗外,是一个叫“埠曲”的小站,站台很简陋,人们甚至无法在站台上避雨。
火车像一只在黑暗里奔跑的野兽,不停地嘶吼着,窗外一伙男人正在追逐一群獾,獾的头领不断地带领獾群改变逃跑的方向,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形同鬼魅。
我真没想到獾们会变得那么凶猛,它猛地回过头,咬在其中一个男人的手臂上,隔着玻璃,我还是听见那个男人的惨叫声,其余的猎人看到这个情形都放弃了追逐,他们拿着弓弩和棍棒赶过来,胳膊粗的木棒呼哧呼哧地砸在它身上。
十年前在镇上,那只獾还很小,它躲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笼子里,眼屎和眼泪混在一起迷蒙了它幼小的眼睛,我想它是想妈妈了,旁边放了一小块儿玉米饼子,它根本就没吃。一个猎人在抽着旱烟等待买主,我央求着母亲,也许是那只獾的眼神打动了母亲,母亲花了不菲的价钱买了这只幼獾。
这只獾在我外公家呆了三年,它完全充当了一只狗的功能,我想它之所以会老老实实地在我外公家当狗,完全是想报答我母亲的救命之恩,后来,我二舅从南方带回一个白皙的姑娘,也就是我二舅妈,我这个舅妈来到北方的第一个冬天就得了严重的冻疮,我二舅曾经央求我母亲让他杀了那只獾取油,獾油是治疗冻疮的绝佳好药,我母亲当然拒绝了他。
后来那只獾没了踪影,现在我知道那只獾是逃走了,当年有人传言是我二舅杀了那只獾,他很恶毒地把那只忠实的獾拦腰砍成两截,当时我就怀疑这个传言的真实性,杀一只獾有很多方法,难道非要砍成两截那么残忍吗?
我怀疑这个谣言的制造者是我三舅,我二舅曾经把我三舅暴打一顿,其中的原因我母亲未详说,但从母亲讳莫如深的语言中我猜个大概,那就是我三舅觊觎过我的二舅妈。我二舅妈后来再也没犯过冻疮,而且以前的冻疮竟然没留下一点儿疤痕。
没想到我又见到了那只獾,它显然是长大了,而且变得凶猛,它死死地咬住了猎人的胳膊,嘴里的血呼呼地往外冒,它咬得太死,猎人不得不用木棒敲断它的牙,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敲断了那一截截嵌在肉里的牙齿,那些牙齿的碎屑跌落在地上像玻璃落地一样清脆,它终于死了。
猎人的皮肉像肿胀的嘴唇一样往外翻着,血洒了一地,地上的泥土像下过雨一样泥泞……我抬头看看对面的姑娘,我想和她说说话,我害怕窗外的情形会让她的神经崩溃。
大半夜了,火车也飞奔了几千里,窗外的一切变得模糊了。应该是到H省的地界了,我把脸贴到玻璃上想从外面的灯光中分辨出到了哪座城市或是小镇,也许我真是坐错车了,外面的一切使我感到陌生,这条路我经过了无数次,怎么对外面的景物一点印象都没有?起风了……
我起身穿上鞋子,女孩见我起来,说:“我拿了你的书。”我说:“没关系,你看吧!”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本想加这么一句。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只手拿着书本,一只手正把玩着一个红色的火机。看样子她一直没睡,书已经翻过了大半,这么暗的车厢,我真怀疑她是否看得清楚上面的字。
我借了她的打火机,在火车的车厢连接处抽了两支烟,洗了脸后又走了回来。我在她对面的座位坐下。
“你的火机火苗太大。”我对她说。她看得很入迷,并不想和我说话,我也不想打搅她,于是我拿出了一罐啤酒自顾喝起来。我想我已经喝了两罐了,身体已经热起来。她在哭,哭得很伤心,她轻轻地咬着嘴唇,这让我心疼起来。
“回家?”我不想让一个女人在半夜哭,我已经够伤心的了。
“是的!”她说,她“哗啦哗啦”地翻书,眼睛被泪水洗得很亮。
“照你这本书推算,我活不过十八岁。”她一边擦着从眼角渗出的眼泪,一边望着我说。
我忽然怨恨起我外公来,这本不详的书已经害死了我二舅,在深更半夜又让这么漂亮的姑娘哭哭啼啼,我只能转移她的注意力,我把书拿过来,跟她说:“这些书都是瞎诌的,你不要相信。”
她望着我说:“其实书里面讲的很多事情都很准。”我想,我应该岔开话题了。
“你还上学?”她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学生。
“嗯。”其实我不敢肯定她是说“嗯”还是“呃”。
她的冷漠让我感到悲伤起来。我又想起了我的外公,最后一次见外公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痛苦地睁开眼睛望着我,他嘴巴张得圆圆的,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飞出来似的。他向所有探望他的人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不易呀!”也许是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抬起那只像枯树枝一样的手指了指床下,我看到了那只雕花的箱子,忽然,我想起了我那只有半截身体的二舅。
一只软软的手,只是有些凉,是那个姑娘的。她把我从梦魇中拉了出来。
“你没事吧!”她好像看出我的异样。
“没事!”我说,“我外公去世了!”我不打算掩饰。
我忽然记起小时候他给过我一块钱,我用这一块钱咂了一个星期的冰棍儿。我这才发现原来我是这么爱我的外公,我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我对面的姑娘显然是动情了,她递过来一个手绢说:“节哀吧!人总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我忽然感觉到了什么,我好像和她很熟。
“你也是到北方吗?”我忽然担心起来,如果我坐错了车,我就不能见外公最后一面了,也许外公圆圆的嘴巴尚未闭合,我回去的时候从他的嘴巴里还会飘出一些久违的声音。
“哦,是的。”她说。我这下放下心来,我用她的手绢擦擦眼泪,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好像是秋天河滩上蒲草的味道。
我望着眼前的这个姑娘,半夜车厢里只留了几盏灯,她的脸很白,白得有些惨淡,我想她应该是有贫血的毛病或是这几天她身上正来着月经。
“你男朋友呢?为什么不陪你一起回去?”我问她。像这样漂亮的姑娘肯定是有男朋友的。
“我们很多年前就失散了。”她冲我笑笑说,脸上并不见得悲伤。
“失散了?你们认识很久了?”我的意思是她的年龄并不大。
“十五年。”她很平静地说。
“十五年?”她的回答让我惊讶:“十五年前你还是个孩子吧?”我这样问她。
“是的,认识他那年我才十四岁。”她说。
“中学生?”我问她,我忽然有种窥视到别人隐私的兴奋,一个姑娘肯跟你讲她的隐私其中的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对,每次下课见了,他总是盯着我看。”她说。
“后来呢?”我继续问她。
“就这样一直四年。”她说。
“难道四年你们就没说一句话?”我继续问她。
“嗯。”她说,这次她的回答很清楚。
“那后来呢?”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原委。
“后来他终于给我写了张纸条,在快毕业的时候。”她说。从她的语气里我感觉到收到纸条时她并没有吃惊。
“上面写什么了?”我很好奇地问,其实像这样的东西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没敢看,就装在衣服兜里了。”她说。她脸上终于有了血色,红扑扑的,汗毛清晰可见。
“那后来呢?一直没看吗?”我问。我好像也被她的这种情绪感染了,有些春心萌动,甚至我比她还着急知道里面的内容。
“我回家想看来着,又怕被家里人发现,只好把那件衣服放在盆子里然后端着盆子到了河边。”她平静地说。
“你可以在去河边的路上看呀!”我甚至有点为她着急了。
“河边的地里有很多人在浇地,我怕被人看见。”她解释。我看见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脸上泛着红润、小鹿撞怀时害羞的情形。
“后来呢?你看了那张纸条吗?”我有些着急了,手心开始出汗。
“我顺着河堤往人少的地方走。”她好像有些激动,脸色又恢复到苍白。
“河堤边有很多蒲草是吗?那些黄色的像香一样的棒子可以吃,就是有些噎人。”我说。我嘴巴动了动,我依稀回忆起那些黄色的像雏鸟嘴角一样的蒲草果实的味道。
“嗯,我越走越远,蒲草也越来越高。”她渐渐地像在自说自话。
“那里水很深的。”我想喊住她,我的汗毛开始一乍一乍的。
“是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又说:“我的脚就这么一滑……那些水就一下子窜进我的鼻孔,像有一些冰针扎进我的脑子。”
我一把拉住了她,把她搂在怀里,这次我终于抓住了她。我喊出了她的名字,她早已是泪流满面,我用嘴唇轻轻地碰了她的嘴唇,凉凉的,我两只手捧着她的冰冷的脸,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又紧紧地抱住她,我用跟别的姑娘接吻的技术吻她,我们拥吻着,她接吻的技术很生疏,她狠狠地咬着我的脖子,我热烈地吻她,我想温暖她冰冷的身体。
我回到老家时母亲正在车站接我,她站在车站的站牌旁边,这个站牌还是十年前的样子,站牌上的字已经被雪盖住了。我母亲肩膀上落了厚厚的积雪,看来她已经等很久了。我想帮母亲把身上的雪掸落,母亲却说不用,她说这样能暖和些,雪已经下了一天一夜。
我没发现母亲的脸上有什么悲伤的神色,她一边给我往身上套白色的孝褂子一边扶着我的肩膀向她上出租车的方向努努嘴,问我:“那个姑娘是谁?”我的婚姻问题一直是母亲的心病,我只好对她实言相告,免得她产生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同学?有这么简单吗?我看见你刚才抱她了。”母亲在不停地追问。我怕母亲再问下去我会把在火车上发生的事情讲给她听。我只好说:“人家现在已是经医科大学的硕士,你儿子是个流浪汉,你觉得般配吗?”
我母亲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异样。“这有什么般配不般配的。”我母亲很不屑地说:“你去追她,实在不行我找人去提亲,你告诉我这个姑娘到底是哪个村的。”我母亲显然是兴奋了,她从出租车行驶的方向能猜个大概,这附近村子不多。我真怕她找个媒婆傻乎乎地到人家家里提亲。那样我实在是太丢脸了。我只好说:“你让我自己来行吗?”我母亲这下子高兴了,她完全忘记了躺在棺材里的外公,她一下子蹦起来说:“哈哈!被我猜出来了吧。”我没告诉母亲,我已经和她约好了三天后一起返回江城。
我和母亲在雪地里行走着,像《林海雪原》里的战士一样无声无息,快到外公家门口时,我母亲终于落下泪来。外公家的房子完全被雪盖住了,我简直像钻进一个雪洞里。
我外公躺在棺材里,脸像阴天那样灰蒙蒙的,我摸了摸外公的手指,像一截树枝那样干而硬。我看着他微张的嘴巴,希望能发生什么奇迹。
如果没有我大舅和我三舅的吵闹,时间仿佛就是静止了,我的两个舅舅从街上厮打着走进院子,在我外婆的哭声中他们扭打在一起,我大舅的一只眼睛肿得像个馒头,我三舅的一边脸像打了气一样鼓起来,他们浑身沾满了积雪,像两只北极熊。
从他们的吵闹声里我听出来了,他们是为了争我外公的遗产打起来的,我大舅说我三舅拿了一个清朝的雕花檀木箱子,我三舅说我大舅拿了一本宝书,里面夹着的全是存折,我外公曾经在东北淘过金,有过不菲的收入。
我两个舅舅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父亲和我的几个姨夫在悠闲地抽着烟,我两个舅舅此时仿佛成了拳击手,也许我其中的一个姨夫会意外地吹起一阵口哨。
除了家里人,来吊孝的人很少,雪实在是太大了,我的两个舅舅扭打一会就坐在地上歇歇,好像是局间休息。就在他们歇歇的当口,我大伯进了门,我大伯个子很矮,起初我以为他带了个白色的帽子,身子还有帽檐,后来我发现其实是雪,溶化的雪在他额前形成了一个冰沿儿。他给我外公磕了个头,然后朝我走来,他问我:“你怎么回来的?路上的雪大吧?”
我说:“南边没下雪,暖和着呢。”我大伯是位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板子,以至于老四川在看到我的手掌时以为我是篾匠,他说他老家的一位邻居就是篾匠,他的手就和我的手一样硬。当然,我丝毫没有怨恨我的大伯,也许我应该跟他说说火车上的事,我正这样想着,我大舅从屋里拿出菜刀,我三舅则拿着一把茶壶防卫。
没人相信我大舅会真的拿菜刀砍下去,也没人相信我三舅会把茶壶砸在谁的脑袋上,也许正是因为没人相信,我大舅菜刀砍到我三舅胳膊上时没人来得及阻拦,血顺着我三舅的胳膊流到地上,把地上的雪都染红了。
我三舅本能地把茶壶扔了过来,我大舅一躲,那把被我外公把玩多年印着喜鹊登枝的大茶壶像流星一样朝我飞来,我猛地一惊,好像有什么东西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醒来的时候老四川正在“咚咚”地切着空心菜,他趁切菜的功夫放了个很响的屁。中午回来,我困急了,躺在床上就昏死过去,我准是把老四川剁菜的声音当成火车了。
老四川一歪头,他操着四川口音说:“再睡会儿吧!饭还要一会才好。”我感觉自己身体很重,浑身酸疼,一阵很浓的辣椒味儿窜进我的鼻孔。
老四川看着我问:“又做噩梦了?”他很了解我。
“没有。”我说:“算不上噩梦,我梦见我的一个同学。”
“是女同学吧?”他回过头朝我笑。
我说:“是的。”
“她在哪现在?”老四川问我。我怎么回答呢?这很让我为难,但我还是想把真相告诉他,因为他是我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梦已经成为我睡眠的一部分。
“她死了。”这时我心里隐隐作痛。
“死了?怎么回事?”老四川感到惊奇。
我只想把事情说出来,像个病人那样,老四川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被我死死抓住。
“四年来我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喜欢她,包括她本人。”痛苦像把生锈的刀子,慢慢地割着我的皮肉。
“后来呢?”老四川放下手里的刀,把案板上的菜倒进一个瓷盆里。
“我给她送了一张纸条。”老四川显然是看出我的难过,他用眼神鼓励我继续说下去,他一直开导我,不要把事情放在心里,要像放屁一样把不愉快的事情释放出去。
“把纸条给她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开始哽咽了,我继续说,我不能停,一旦停下来我就会永远失去把真相讲出来的勇气,“后来我知道,她在洗衣服的时候淹死了。”
老四川开导我说:“这些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你就不要再内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也许她命该如此。”
“如果没有我,她现在也许会在某个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救死扶伤。”我泪如雨下,“她母亲在接到她的入学通知书时哭得昏死过去……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妇产科医生,本来她面对的将是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生命。”
“怪不得……”老四川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处境:三十岁的人,一直在异乡流浪,每天精神恍惚,数次在精神病院治疗,在别人看来,我已经无可救药。
有些话我还是没说出来,其实那张纸条不是我写的,是我的铁哥们,他也喜欢她,为此,我一直在怪自己。
我忍着疼痛跟老四川提议说,中午还是喝一杯吧。酒对我来说就像是止痛药和迷幻剂。我起身拿起子的功夫电话响了,是我母亲打来的。我母亲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一听就知道是哭过,她说:“你外公昨天晚上去世了,要是方便的话就回来吧。”
我没有丝毫惊奇,我说:“好。”我准备挂电话,我母亲又说:“对了,回来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咱家下大雪了,你大伯昨天来吊孝的时候差点掉到雪窟窿里,好了,不跟你说了。”我母亲急着挂了电话,我还是从电话里听出我舅舅们的吵架声。
老四川在锅里炖着汤,香味顺着厨房飘过来,我忽然记起宝通禅寺的一本经书上写道:一切皆是幻象。难道我仍是在一场梦里?庄周梦蝶的故事也许是真的,谁能证明我现在不是在梦里?
电视上正在播着新闻:总理正在某个城市的火车站和焦躁不安的旅客们握手。我究竟睡了多久?在我昏睡的日子里,整个国家都在下雪?这一切真实吗?我不敢肯定。
我躺在床上,大脑一片空白,此刻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好像发高烧了,浑身软软的,也许是这一切就要有个结果了,我应该告诉她关于那张纸条的真相,她毕竟等了那么久。我望一眼老四川,他正在沉着地往碗里舀着汤,那碗汤的味道我实在是太熟悉了,几年来,他总是在做着同一种汤,他其实是想用这种汤的味道让我顿悟。
我从床上下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变成了一条蛇,我努力地向前爬行,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爬上阳台,阳台上风不大,对面瓦蓝的楼顶已经被积雪覆盖,变成白色。我踩着那个边缘已经碎裂的花盆,准备从十八楼一跃而下。我知道自己不会摔成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因为当我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三舅的茶壶就会猛地飞过来,砸在我的脑袋上,那些茶壶的碎片会混着我的血迹像玻璃球儿一样噼里啪啦掉在我外公家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