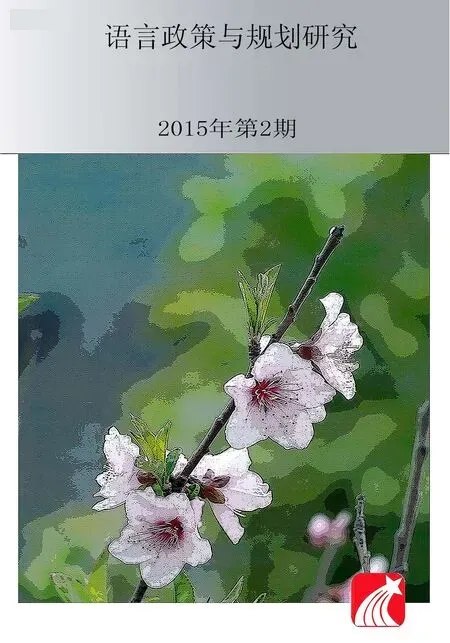《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评介*
2015-02-12南京理工大学国际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 国际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李 娟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评介*
南京理工大学 国际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李 娟
Ager, D.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Clevedon UK:Multilingual Matters. VI+210 pp.
2012年底中国语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推出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的第一种——《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颇受好评。他们又相继推出《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2013),《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二版)》(2014)和《语言:一种权利和义务》(2014),并于2014年再版影响广泛的第一本书。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首次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萌发于民族主义时期,而语言规划是民族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8、19世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二战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大学里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Wright 2003;苏·赖特 2012)。20世纪60至70年代迎来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的鼎盛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解决本国的语言问题(Bolton 2002)。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这个领域可被看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
在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专家们付出不懈努力来规划和改革汉字,推广普通话、推动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许嘉璐、道布、陈章太、李宇明、徐大明等学者深入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虽然我国有悠久而广泛的语言规划实践,但语言规划学的发展却不甚理想。李宇明(2010)指出,“中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却是外语资源利用的穷国。”因而在语言生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更为科学的语言规划,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相关研究,以促进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社会语言学家徐大明、翻译学博士吴志杰开始主编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他们选取该学科的经典之作,并聘请外语水平高且谙熟专业的行家进行翻译。Dennis Ager的著作就是丛书中的首部。李宇明在序言中倡导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并认为这套丛书能为新世纪的中国语言规划起到重要的学术借鉴作用。本书作者Ager博士与译者吴志杰博士交换过数十次邮件,多次来信解答翻译中的疑问,与译者探讨语言规划的问题,并欣然为书作序。
Ager博士是英国阿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成果卓著,尤其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方面很有建树。代表性著作有《社会语言学与现代法语》(1990)、《认同、不安全感和形象:法国及其语言》(1999)、《意识形态与形象:英国及其语言》(2003)等。《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2001年一经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6位学者为其英文版原著写书评并发表在如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Policy等有影响力的国际刊物上(Bolton 2002;Donnacha 2002;Kamwangamalu 2002;Paulston 2002;Trim 2002;Walt 2004)。该书从动机这一角度切入语言规划研究,考量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中最核心的因素之一,其语言资料丰富而翔实,政策分析中肯而透彻,分析框架全面而深入,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1. 内容介绍
本书由引言、九个章节和结论组成,一到六章以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案例详述七种动机,七到九章用表格综合评测和阐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动机过程的三种动机成分,即态度、动机和目标。在引言中,作者界定了相关术语。语言和语言行为分为作为工具的语言和作为对象的语言,语言规划谈论的是后者。语言规划指的是“通过宗教、种族或政治纽带维系的有组织的社区,有意识地尝试影响其成员日常所用语言或教育中所用语言的途径和方法,或者表示通过这样的社区影响学界、出版社或者媒体记者进行语言变革的途径和方式”(Ager 2014: 5)。语言规划通常可划分为三个应用领域: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和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并存在三种施为者:个体、社区和国家(掌权者)。作者简要回顾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动机理论,提出影响语言规划和政策行为的七种动机,并指出其动机理论来源于Gardner和Lambert 1959年的文章、Ryan和Giles 1982年的文章以及Kaplan和Baldauf 1997年的书。在引言最后作者列出了一个统领全书的表格,展现动机过程的三大成分:动机(包括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形象建构、不安全感、不平等、融入群体、提升的工具性动机)、态度(包括对语言的认知、对语言所持的情感、采取行动的愿望)和目标(包括理想、谋略、指标、需求、生理性的、心理性的、实现目标的策略)。
第一章从“身份认同”视角回顾五个地区的语言政策,即法国、阿尔及利亚、加泰罗尼亚、印度和威尔士。在法国模式下,语言政策的目标是一种朝向民族主义理想的简单同化过程。阿尔及利亚通过排斥与殖民统治相联系的法语,把另一种语言即古典阿拉伯语树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印度巧妙地利用殖民者的语言,通过改造以前的统治语言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加泰罗尼亚的身份认同不只受精英阶层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左右,还受当地人民集体意志的影响。威尔士属于“逆向语言转换”,要求确立威尔士语和英语的双语地位。威尔士的案例表明在认同本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可避免地共存。文化认同需要政治权力将其付诸实施,而政策的长久则需经济优势做保障。
第二章“意识形态”主要谈英国的语言规划和政策,聚焦于政治家和语言学家对课程大纲的论争。政治家希望确定标准英语的系统化形式,并且向所有儿童教授标准英语,同时把各类社会方言或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排除在主流教育之外。其做法背后的动机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旨在贯彻其政治谋略,建立某一特定类型的社会。Ager博士对英国本土的语言冲突提出客观评价,认为双方都有欠缺,希望政治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都要打破意识形态偏见,提出内在统一的英国语言政策。
第三章以德国、日本和欧盟为例谈论提高“形象”的动机。国家通常采用某些政策来推广本国语言,“其目的旨在构建和管理国家形象,以确保本国的历史、传统、 文化产品、宗教以及礼仪习俗受到其他国家的好评”(Ager 2014: 56)。为积极建构并维系良好的海外形象,德国通过政府资助的组织如歌德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及一些私人组织推广德语。与德国不同,日本针对海外的文化推广和语言传播项目显得谨慎保守,“日本希望在海外塑造的自我形象似乎更多是基于插花、书法之类无争议的艺术”(Ager 2014: 64)。欧盟的语言政策考虑到保留欧洲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因而欧洲大部分机构的运作需要多种语言,但关贸总协定中界定的“文化产品例外”这一概念,折射出“欧洲在文化和语言政策方面,想要保持多元和差异的动机源自复杂的考虑,其中有相当多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为除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未来担心,还有想要确保美式英语的负面形象以及与此相关的保障欧洲语言正面形象的愿望”(Ager 2014: 69)。
第四章探讨以不安全感为动因的语言政策,分别以中欧的吉卜赛人恐惧症和法语新词为例。中欧的吉卜赛人长期以来被看作外来户,这种游牧式的、无社会组织性的、甚或反社会性的群体经常在安定、规范、严格管理的政治实体中引起恐慌。掌权者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可能源自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同时也担忧这类群体让社会凝聚力化为泡影,使社会规则在管理公民时显得有心无力。因此中欧相关国家如斯洛伐克制定政策来隔离吉卜赛人。同样,在法国,当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带来新观念时,新的词汇和术语通常都从美国英语中引进。因为惧怕这些语言的入侵会危害法国文化、法国生活方式、法国科学甚至法国整个国家,法国政治当局制定如《杜邦法案》这样的政策来巩固法语的地位,抵制美语的入侵。
第五章从性别、弱势和种族三个领域的社会排斥来探讨以不公平为动因的语言政策。美国与法国制定政策以清除语言性别主义。《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承认并支持少数族群语言权利,以纠正社会不公平现象。由于种族身份,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日本的阿伊努人和朝鲜人以及中欧的吉卜赛人都遭受过歧视和迫害。如今《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致力于纠正该国的不公平现象,尽管其隐藏动机更可能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第六章介绍语言政策的最后两大动机,即融合性与工具性。“工具性动机假设个体感兴趣的只是习得足够的交流能力以实现自身特定的目标,通常是与经济指标有关的目标。融合性动机则建立在个体试图与目标社区更加紧密联系并最终融入该社区的愿望之上”(Ager 2014: 105-106)。本章以移民问题、非洲的通用语和五个深度访谈为素材,探讨个体和社区的语言行为以及这些语言行为是如何影响到语言规划和政策的。个体和社区的语言行为反映其工具性—融合性动机,如提升语言技能、增加改善生活的机会、促进个人的职业发展、提高个人收入、深入了解目标社区等。
第七章回顾“引言”中所列的三种动机成分(态度、动机和目标),考察这些动机成分的评测方法,试图弄清各个动机成分之间可能存在的特殊关联性。本章特别强调语言态度的三种层次:认知层面(语言知识)、情感层面(对语言的情感)和意动层面(该怎么做)。语言规划的目标由三部分组成:长远的理想,更实际、较可能实现的谋略和更确切的短期指标。最后Ager博士再次强调那个包含态度、认同建构和目标在内的动机过程图表。
第八章应用动机过程图表来分析个人和无权社区的语言行为。评估表明个体感觉自身境况与参照群体的境况差距越大,所追求的目标就越明确,行动的动力也就越强。这些差距有:社会地位的差距、研究对象的母语及社区与周边社区的地位之间的差距、研究对象的经济状况与其认为成功的目标之间的差距、年龄差距。无权社区的案例分析表明其语言行为受到多种动机的影响,同时其语言行为大多针对第一语言;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二语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他者的语言,不可避免被视为比无权社区的语言更具优越性和活力。
第九章考察了掌权者的语言行为,应用图表把前六章中提到的国家如法国、英国、阿尔及利亚、印度等国的语言规划和政策进行了掌权者的动机过程分析。
第十章总结全书要点,再次强调“认同尤其是社会认同的建构和持续重构,也即我们所谓的动态认同建构,及其后根据行动预期结果而产生的行动意愿,是语言政策动机的关键因素”(Ager 2014: 191)。同时作者还指出本书只描述和其三个目标层次相关的语言行为,不涉及基础层面的实际语言规划与政策。Ager博士谨慎提醒道,通过个人和社区所表达的态度、目标和动机的分析并不能完全预测他们的行为。明晰这点有利于人们认识到,在语言规划和政策制定中不能简单依赖和直接阐释一些关于动机态度的问卷调查。而动机过程图表旨在提醒大家需要考虑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动机过程的总体结构及其复合混杂性。
2. 简评
首先,本书语言资料丰富而翔实,不仅涵盖对欧洲语言现状的观察,也列举非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案例,因而对欧洲以外国家的情况也有借鉴意义。例如,讨论身份认同的动机采纳了关于法国、阿尔及利亚、加泰罗尼亚、印度和威尔士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的“标准英语”之争来探讨意识形态;以德国、日本和欧盟为例谈论提高“形象”的动机。在“不安全感”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吉卜赛人现状以及法国人对源自英语新词的态度。“不公平”一章涉及美、法消除语言性别主义的努力、欧盟立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融合性与工具性”一章列举美国的移民语言、“唯英语”运动、非洲的多语制以及不同背景下二语习得者动机的个案分析。Ager博士掌握了大量世界各地语言规划方面的细节资料,列举分析如数家珍。这些来源广泛的案例分析更强调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力系统及其驱动过程的普遍性。
其次,作者对相关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分析中肯而透彻。Ager博士在谈及很多语言规划和政策问题时,往往从语言、社会历史、政治等维度进行分析,清楚客观地描述现状并说明其复杂性。例如在介绍和评价印度的语言政策时,作者指出“印度总体的国家认同建基于‘英语+印地语’的模式,同时为数百万操其他语言的印度人留有余地,使他们同样对此种形式的国家—民族认同感到舒服自在,这一语言政策允许印度人用母语接受教育,同时也提供了印度联邦主要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的就业机会”(Ager 2014: 31)。但作者随即谈到认同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可能存在的刻意操纵行为更会影响其建构,在权力斗争中通常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群体认同是一种潜在的武器,而其实际效用取决于总体的政治环境。因而Ager博士颇有见地地评价道,“印度认同的语言因素具有一定稳定性,但也存在潜在的爆炸性”(Ager 2014: 31)。同样,在“意识形态”一章作者对支持和反对“标准英语”的双方都提出批评,指出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影响到双方的判断。
此外,本书的分析框架全面而深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前六章利用案例详细讲解分析框架中的七种动机,其论证严密、说理充分。在全面介绍的基础上,七到九章将所有动机成分综合起来以评测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过程。全书围绕动机过程图表系统展开,前后呼应,既有理论又有应用,并制定出简化的三分制评分系统:1)代表给予较低的评价;2)代表给予中间程度的或不确定的评价;3)代表给予较高的评价。读者可利用该分析框架列出某一情况下参与者在相关量表指标上的得分,取得对态度的量化评估值及其在相关态度空间或态度结构的表现形式。然而Kingsley Bolton(2002)质疑这种准社会科学分析框架的有效性。Ager博士明确指出“动态认同检验或许是描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制定中动机的关键因素的方法之一”(Ager 2014: 136),尽管认同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紧密,但个人的态度并不必然预示着行动。同时,语言规划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以及他们为实现目标可能采取的策略,也不一定只通过简单对动机和态度的分析就能预料得到。Ager博士不仅给出论证严密的分析框架,还对其保持谨慎保守态度,体现其治学的严谨。
当然该书也稍有不足。比如前六章节的前后顺序值得商榷,第一章和第三章可放在一起,因为身份认同一般会影响相应形象的建构。而第二章意识形态这一分析维度与其他动机不在一个层面,身份认同、建构形象、不安全感和不公平的问题都可以在特定意识形态的语境中产生。此外,部分案例细节的准确度也有待提高。如在谈到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语时,作者只提及古典阿拉伯语,而没有提及现今更通用的标准阿拉伯语。当然瑕不掩瑜,此书以其视角的独特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分析的动态性而位列此类研究的首选参考书。此外,翻译学博士、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吴志杰博士忠实通顺的翻译也为此书增色不少。此书中译本的问世相信能拓展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国际视野并更好地推广语言资源观。
Bolton, K. 2002. Review of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6 (2): 624-629.
Donnacha, J. M. 2002. Review of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J].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26 (1): 77-80.
Kamwangamalu, N. M. 2002. Review article: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multilingual societies [J].World Englishes21 (1): 165-174.
Paulston, C. B. 2002. Reviews: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J].Language in Society31: 790-796.
Trim, J. L. M. 2002. Review of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J].Language Policy1: 183-192.
Walt, C. 2004. Book review: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5 (1): 77-80.
Wright, S. 2003.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From Nationalism to Globalisation[M].Palgrave: Macmillan.
丹尼斯·埃杰,2014,《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第2版) [M],吴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李宇明,2010,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 [J],《外国语》33(1):2-8。
苏·赖特,2012,《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熊文新)
李娟,博士生,南京理工大学讲师。主要研究领域: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电子邮箱:lijuannjust@126.com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3092014013203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安全视角下‘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研究”(15BYY059)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语言资源与规划理论的本土化”(12YJC740112)的阶段性成果。